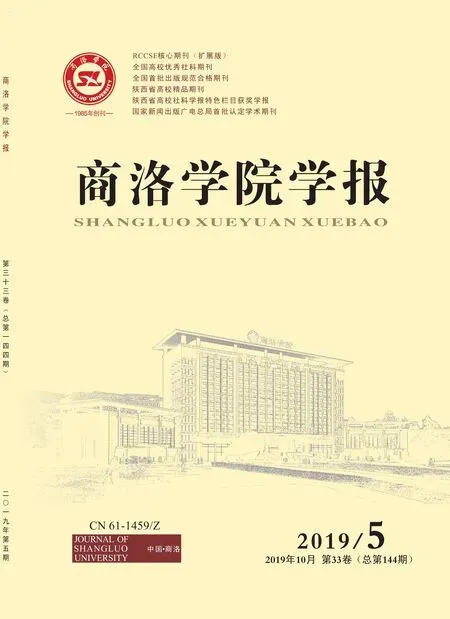《山本》“混沌”美学特色探析
董晓可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在《山本》的题记中,贾平凹这样写道:“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长江黄河,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1]1正如他描绘的秦岭一样,《山本》无疑是一部巍巍高山一般大体量的作品,也是融入了作者巨大心血和抱负的厚重之作——“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之志。”[1]1要为一座山,且是中国最伟大的秦岭“写志”,这本身就是一项至难之事。当前,关于《山本》的评述主要表现在以下诸层面:其一是从民间写史的角度来论述作品的民间性[2];其二是从文学地方志的写作倾向出发,论述作品在秦岭动植物、人与历史、神秘主义等方面传奇书写的特色[3-6];其三是从文学技法层面来呈说作品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传统叙述手法的承继[7-8];其四是从作品潜藏的先锋意识出发,来探求作品的现代性思想及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2,9];另外,还有对作品俊逸、舒朗等风格描绘,作者寻根意识、作品暴力与诗意书写等方面的评述[10-12]。而本文在以上诸多评述基础上,汲取其营养,从作品深处更能体现其风格的“混沌”美学特色出发,来探求其非凡的艺术价值。事实上,这一美学特色,在贾平凹小说新作《山本》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作为一个纵笔40 余年、已然写就15 部长篇小说的大作家,贾平凹于新作《山本》中在人为斧凿的技术层面有意隐匿了起来,而是抱朴守拙,返璞归真,做回一个谦卑的“记述人”,用40 余万密密匝匝、洗尽铅华的文字和不设章节、徐徐推进的构筑方式,为我们筑就了一种交织着本真、自然、淳朴和粗粝、烟火、世俗,融汇着历史、文化、生态和苦难、悲悯、神性的包罗万象、浩浩汤汤、广袤雄阔而又泥沙俱下的《山海经》一般的原始书写方式,这便是其“混沌”书写的艺术特色和可贵价值所在。
一、秦岭之“本”:开启“混沌”内容的三重“密码”
关于“混沌”,《庄子》中有段这样的记述: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13]
在这里,“儵”通“倏”,“倏”和“忽”合起来便有着瞬息之间急于求变的特点,而相比之下“混沌”无疑隐含着浓重的本源、本真的原始意味,代表着整个宇宙万物的浑一、稳定,而贾平凹所要尝试书写的正是这样一种天然的、广杂的“混沌”状态。在漫长的写作修行中,他渐渐意识到:“初学写作时你觉得你什么都知道,你无所不能,而愈是写作,愈明白了你的无知和渺小。越写越有了一种惊恐,惊恐大自然,惊恐社会,惊恐文字,作品常常是在这种惊恐中完成的。”[14]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惊恐,他才越来越倾心于对自然和社会天然的呈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山本》想要为山“立言”,要写出秦岭的山高水长、莽莽苍苍,写出它滋养的居住其中的众生群像,便只能用这种禾草盖珍珠的近乎原生态的混沌书写方式。这种“混沌”在作品中是通过生态、历史、文化三个维度展现出来的。
首先是生态书写方面。在《山本》后记中,贾平凹提到,按照写作初衷,他原本是想要整理出一部关于秦岭的草木记和动物记的,他甚至为此在数年间远涉秦岭的起脉昆仑山,踏足秦岭始崛的鸟鼠同穴山,遍访太白、华山、七十二道峪、天竺山和商山[1]523。只是后来又融入了诸多历史和人事的内容,但即便如此,关于秦岭原始生态的述说仍如水雾般氤氲在作品深处。在小说中,关于秦岭草木和禽兽的描述俯拾皆是,而麻县长角色的设置是有着深味的。身处乱世的他,一腔抱负难以施展,便品茗写字,寄情于秦岭奇特原生的一禽一兽、一花一叶之中。他知晓了“胆力春天在首,夏天在腰,秋天在左足,冬天在右足”[1]153的熊,知晓了长着人面的野驴、铁蛋鸟、双头龟等怪兽奇鸟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植物。不但如此,他还终其一生致力于为秦岭书写风物志,临终留下了《秦岭志草木部》和《秦岭志禽兽部》两部书。这样,通过麻县长就赋予了万千静默自然众生以“齐物”的色彩。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齐物”思想又与那段混杂着血腥和泪水的黑暗岁月纠结在一起,正如井宗秀送给麻县长的那副对联:“秦岭地,每嗟雁肃鸿鸣,若非鸾凤鸣岗,则依人者,将安适矣;万千山,时勤狗盗鼠窃,假使豺狼当道,是道教也,安可禁乎。”[1]117这样看来,这种关于秦岭自然的原始生态的呈现,便有了更多的历史悲戚和人心哀叹,而麻县长犹如山中走来的老者,是真正懂秦岭的人,他说:“秦岭可是北阻风沙而成高荒,酿三水而积两原,调势气而立三都。无秦岭则无黄土高原、关中平原、江汉平原、汉江、泾渭二河及长安、成都、汉口不存。秦岭其功齐天,改变半个中国的生态格局哩。”[1]300他仿佛在深深地感喟,感喟她蕴蓄的丰厚历史和美好风物,感喟她的多灾多难,也感喟她的包容、坚韧与伟力。这样就不难理解他在悲叹之余生出的对于苍茫大山的浩瀚无穷的惊叹。因为穿过尘世风霜,望尽千里秦岭,人同百花无异,纷纷开且落于山岭之间,皆为山之宽广怀抱温情以待。而这正是伟大的秦岭用自己气魄宏大的“齐天之功”孕育的人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的、原生的本真生态样貌。
其次是历史层面。对于历史,贾平凹有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在他看来,历史总有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纠结其中,因为“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1]523。那么,对于这段历史的呈现就只能“在贾雨村言中透露甄士隐去的某些故事”[15]。对于此,笔者姑且将其称作大历史背景下“混沌不开”的杂史、碎史和隐史。比如一个“杂”字,《山本》中包含了民风民俗、商业发展、日常生活、家长里短、人情往来、乡野争斗、天灾人祸、社会生态、中医农林、天文地理等诸多内容,且将其掺杂在历史叙述之中,仿佛秦岭的草木一般漫山遍野不可胜数,有一种包罗万象的样态。比如一个“碎”字,贾平凹曾说:“秦岭的山川河壑大起大落,以我的能力来写那个年代只着眼于林中一花,河中一沙,何况大的战争从来只有记载没有故事,小的争斗却往往细节丰富,人物生动,妙趣横生。”[1]525他真正关注的并非英雄豪杰“你方唱罢我登场”和“城头变换大王旗”,而是由无数人嬉笑怒骂的凡尘俗事构成的生活情态。贾平凹很擅长这种局部开挖的叙述,作品中那么多生生死死,恩恩怨怨,来来往往,他每一件都描述得各具特色、栩栩如生。再比如一个“隐”字,《山本》力图从原本铁板一块的历史背后翻出一个久被遮掩的更为合理的民间历史来。比如对于“革命”,作品中有为革命事业筹措资金绑架父亲致使其精神恍惚一命呜呼的事件,有血洗县城和屠杀无辜的血腥残酷和暴力,这些都是对传统革命叙述的解构和对革命正义性的反思。而在此“杂史”“碎史”“隐史”之上,也不乏历史规律的呈现。比如放眼涡镇这一历史具象,其中便有一代枭雄从成长到毁灭和在欲望面前浮生若梦的感慨。这有些像作品中的打铁花,在绚烂的历史演绎之后,落下来的是一层黝黑的铁屑,历史的真相早已混沌不开、扑朔迷离,只能在碎片中拼接、缝补和孜孜探寻。
再就是隐秘文化的探寻。在《山本》中,贾平凹延续了《秦腔》《古炉》《老生》等作品中显明的神秘巫文化思想。所谓巫文化,就是以表面上看似荒诞不经的述说,折射出神话思维或神秘主义的问题,融合着关于天地自然的敬畏和万事万物的本源性探究。这种文化的质素在《山本》中散落在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各个角落。比如神秘力量的操控:周一山因多次听到动物对话而挽救了预备团、井宗丞在被害前看到了冥花、井宗秀在梦境中看到了涡镇的代际更迭。在作品后半部分,当人们陷入无休止的疯狂攻讦厮杀的躁动中时,作为涡镇命脉根基的老皂荚树也莫名起火,为秦岭禽兽草木写志的麻县长也在战火中溺水自杀。树和人的死仿佛征兆着对一种至暗时期文化、文明、道德、人性泯灭殆尽的抗争。而“涡镇”这个名字,也似乎隐喻着一种岁月的旋涡,在这个旋涡面前,一切功名、欲望、生命都要被统统卷走,唯有留下更为恒久的天地自然。这就像作品最后,“陆菊人说:这是有多少炮弹啊,全都要打到涡镇,涡镇成一堆尘土了!陈先生说: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的尘土了!”[1]520是的,当一切归于沉寂,秦岭依然屹立在那里,没有丝毫改变。一定程度上讲,秦岭才是故事真正意义上的主角,作者是怀着无比虔诚的敬畏之心来写秦岭的,正是在秦岭这样一个几乎与时间一样恒久的神秘和隐秘的历史见证者的怀抱中,芸芸众生如万千草木般春生夏长、世代更替。是啊,本于山,长于山,敬畏于山的巍峨与神秘,最终将肉体和魂灵皈依于山,化作山中一堆尘土,这大概才是依傍秦岭这座伟大的山而居的众生,与山浓得化不开的隐秘而“混沌”的生存状态。
质言之,贾平凹通过对秦岭生态、历史和巫术文化的原始呈现,力图远离那种“枯藤老树昏鸦”式的蕴含了太多人为雕琢的历史和人事,而竭力追求关于这座“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衍生万物之“一”的秦岭更为天然、更为雄浑的自然混沌状态的呈现。
二、人性之“本”:“人之初”原生、复杂“混沌”秉性的呈现
一切书写的关键都要聚焦到“人”的问题上来,“秦岭博物志”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是关于“人”的博物志。而《山本》中的“人”字解读,无疑蕴含了更多“人之初”本该拥有的原生秉性和复杂性格的向度。
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人生是有觉解地生活,或有较高程度底觉解地生活。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人生之所以异于别底动物的生活者。”[16]他所说的“觉解”即自我了解,正是这种“觉解”使人进入了一个意义的世界,人不仅总是实际地从事着某种具体的活动,而且总是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活动,甚至会自觉追问自己从事这些活动的意义。这似乎是人的历史性和社会性长久积淀而成的基本特性。但在《山本》中,我们看到更多的却是对于这种“觉解”特性的冲撞乃至否定,是一种更大程度的麻木和蒙昧的生存状态。在涡镇,这种生存状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乱世的灰暗大幕的笼罩下,涡镇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派人人自危的境况。在这种巨大危机面前,人们的本能便是“逃避”:在逛山、刀客和各路土匪接连疯狂抢掠的可惧传闻中,涡镇的有钱人纷纷跑到悬崖上开凿石窟用于自保,穷人们则生怕钱被抢了去,唯一能做的便是成立“互济会”将钱统一保存。而当土匪五雷强行介入涡镇不走后,人们也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或不适,而是心安理得地供养着这群“不速之客”。接下来,伴随着井宗秀的崛起,涡镇几乎所有家庭都被卷入了一波波无休止的攻伐、杀戮和死亡之中;更有甚者,在这期间,还出现了诸多类似于闹剧的事件。比如在设计消灭土匪之前,原定在吴掌柜家给土匪设宴,但吴掌柜因吝啬逃跑,致使匪首王魁大怒,将其家产洗劫一空,最后吴掌柜悲愤中吐血而死。比如在安埋了因战斗而亡的51 个预备旅成员后,那十个招雇来搬尸的妇女被迫嫁给作战有功的光棍,致使妇女奔逃,追赶酿祸,最后只活下来两个;因此,光棍们去找镇上的寡妇使强用狠,闹出许多是是非非……在这些混乱杀伐和争斗中,绝大部分仅仅是出于欲望的膨胀抑或仇恨的驱遣,而在死亡的扩大中,人们除了感慨和伤痛之外,也并未有过多的悔悟和反省。可以说,贾平凹借助于涡镇这一地理空间,本真地展现了人类最原始的性情:灾难来时鸵鸟头插沙子般地一味躲避,面临功利时又蝼蚁一样疯狂厮杀,常为一己私欲而沦为特定历史中可怜的棋子,胆怯、自私、麻木不仁而又蒙昧无知。在这里,贾平凹悲哀地看到,这些近似于动物性的原始欲望和性情,在经过了千万年漫长的历史演化后,并未发生太大程度的改观,人性的变化并未与文明进程的推进同步。事实上,很大程度而言,最广大的芸芸众生并未进化到冯友兰所言说的“觉解”状态,而是依旧在“兽性的泥淖”中麻木地、蒙昧地挣扎着,这种人类原初阴暗能量的强大稳固性,让人生发出透彻的悲哀。
而伴随着这种蒙昧状态的,还有对秦岭大地上芸芸众生人性“悲剧”的独特反思。关于悲剧,奥尔巴赫在《模仿论》里引用了圣约翰·欧文在《莎士比亚全集》里的序中的一段话:
在这里我们要谈谈古希腊悲剧和伊丽莎白时代悲剧之间的巨大差别:古希腊悲剧是一种人为安排的悲剧,人物角色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它们的角色无非是按照为它们安排好的行动去死。然而,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则是直接源于人的内心。哈姆雷特就是哈姆雷特,并不是一个变幻莫测的神迫使他走向悲惨的结局,而是他内在的气质使得他别无选择,只能走向这种悲惨的结局。[17]
由此看来,古希腊时期的悲剧都可归纳为“命运悲剧”,而伊丽莎白时期的悲剧则可归纳为“性格悲剧”,但无论二者中的哪一种似乎都由强大的必然性决定,因而这个“悲”字才拥有更多天命难违的悲壮意味。换言之,偶然性在悲剧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但在《山本》中,作者穿过历史迷雾,为我们呈现的却是另一层面的、发生在华夏大地上更本土化的“悲剧”。这种悲剧除去一些确是“生来随意,死也随意”[18]的由乱世带来的偶然因素之外,更多呈现为一种独特的非天命的、人性造就的结果。首先,作品中很多悲剧蕴含着浓厚“群体性”思维的因子。由其造就的悲剧很难说是“命运的”或是“性格的”,而是透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和“冷眼当看客”的漠然与残忍。比如在打败了涡镇土匪疯狂庆贺的当晚,对于因家产被抢愤懑而亡的吴掌柜和因失去女儿而疯的井宗秀前丈人,众人表现出这样的态度:“人们在议论着今夜的铁礼花耍得好,却听到远处的哭声,这才意识到是吴掌柜死了,但没有几个人再去吴家吊唁,倒笑话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性命。而疯子……路过的人谁都没有去拉他,甚至连询问一下也没有,只当是一只狗,一块石头,一个装着垃圾的烂筐子。”[1]139这种拥有群体性质的负面、晦暗因子的悲剧,让人触目惊心;其次,作品中有些悲剧又掺杂了不少原生欲望,充斥着人性的贪婪与自私。比如肉欲,作品中有不少因之无法释放而割尘根的事件,这一被长期蒙蔽的现实欲望在贾平凹这里得到了较为严肃的书写;比如物欲和权欲,发生在涡镇内外最大悲剧的源头大概皆缘于此,这其中卷入了大多数人的厮杀和死亡。甚至当井宗秀被枪杀后,仍然瞪大着眼睛,似乎仍对自己“英雄梦”的戛然而止心存不甘。或许,这些很难上升到西方文学或哲学层面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悲剧”,但在岁月的天平上,人的生命是平等的,这些在历史滚滚洪流中无休无止地上演着的丑陋的、阴暗的悲惨故事,又何尝不是融合着一种更原生、更常态、更真实的人性意义上的悲剧?
而从另一个向度,贾平凹在对这些丑陋人性批判的基础上,又努力建构着关于人性的信仰之塔。他的这种批判并非指向某一具体个人,而是有着更为温暖的普世救赎的意味。对于历史的龌龊和人性的悲剧,贾平凹在赤裸呈现之后,却选择了更为宽仁的超越和饶恕,因而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些暗夜星子一般温暖人心的人物。比如麻县长,在每一次可以挽救生命的时候都会默默地救济或是斡旋,这同他在乱世为那些无名的禽兽花草做志是多么相似;比如安仁堂的盲人郎中陈先生,仿佛看透了世事的智者,静观岁月,不参纷争,救死扶伤;比如130 庙的宽展师傅,如同一尊活着的菩萨,在最黑暗的日子里用尺八声慰藉着众生;再比如女主人公陆菊人,仿佛善与美的化身,在涡镇这个小地方,用一己之力挽救和温暖了那么多人……正是这些美丽而高尚的灵魂,从另一个角度构筑起了“恶”的人性之外的充满了“善”的灵魂群像。
作家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19]这种“美丑对照”的原则在贾平凹的人性书写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他对人性的解读显然没有禁锢于个体的善恶是非中,而是在充分尊重欲望和关怀命运的基础上将作品引向了更为阔大和宽容的境界。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于复杂人性的整理和人间大爱的弘扬,是以秦岭这一伟大的“龙脉”为架构、支撑、烘托和升华的,这就隐含了贾平凹的那种审视整个中华民族整体肖像和复杂人性的抱负。在他看来,人,本就是这样一个万千因子组成的“混沌”结合体。我们的民族本就像一架由亿万个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个体和凝结着“历史的荣光”与“历史的龌龊”[1]526的生命构筑而成的艰难前行的“老车”,其间伴随着让人疼痛的血与泪、晦暗与卑污,也隐含着慰藉人心的温暖的爱。贾平凹在通过对黑暗历史大幕下“人之初”复杂本真的“混沌”人性的拷问,将对“人”字的解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艺术之“本”:“混沌”书写下独特审美价值的探索
在艺术世界中,“巧夺天工”是一种很高的技艺,代表着精湛、纯熟与完美的追求。但很多时候尽管倾其全力,一个“夺”字多多少少还是有着人为斧凿的痕迹,总显得不那么自然。与之相对,“鬼斧神工”便显示出了大自然惊心动魄而又不事雕琢的气魄与从容来。也许缘于从《山海经》和老庄哲学等古典文化中汲取的丰富的给养,《山本》里有着浓烈的对自然和社会原始、本真状态的致敬意味。在这种“混沌”状态的呈现中,贾平凹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印证了真正的大的艺术之美,不唯呈现为能工巧匠刀砍斧凿的单向度走向,更呈现为一种雄浑苍茫的、看似笨拙实则大气的“混沌”气韵上来,这其中饱含着他对独特而可贵的审美意蕴的探索。
首先,这种审美意蕴体现在空间构筑上。与很多现代小说过于重情节和时间推进不同,为了展示出涡镇这样一个“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式的极为特殊的混沌生存样态,《山本》有意淡化了时间的线性脉络,呈现出一种广阔而含混的空间构筑方式。作品伊始,贾平凹就以飞鸟俯瞰的方式,将我们的视域“搁置”于一个雄浑的空间场域,一条国之龙脉横亘大地,让人生发出强烈的地理认同感。接下来,焦距拉进,涡镇出场,这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镇子,如同一叶荡漾在历史波浪中的小舟。在这里,我们能真切感受到,时间仿佛静止了,而静默的自然山川也搭起了人们原生生存状态的“戏台”,“山民”们在其中生长凋零、疯狂厮杀、最后再归于沉寂。而山却不说话,寂然地花开花谢。贾平凹似乎想用这样一种空间方式告诉我们,相对于漫长的时间推移,我们的生活之于秦岭其实更多的是呈现一种相对静止的空间状态,正是在这种相对静止中,人们的生存表现为一种难以言说的“混沌”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空间艺术的探索,是建立在精致的“微写实主义”①之上的,发生在涡镇内外零零总总的事件并非一地鸡毛地纠缠不清,而是犹如一架精美的房屋,骨骼密实,有血有肉,灵魂丰满,引人入胜。
其次,这种审美意蕴体现在叙事艺术上。同空间的构筑相匹配,《山本》呈现出了独特的叙述方式。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小说创作自“五四”以后,便在除鸳鸯蝴蝶派之外的大多数作家身上表现出几乎全盘“西化”的倾向,在对西方文学模拟之路上越走越远。而在这个层面,贾平凹无疑是个“异数”,他的作品中呈现出无尽的中国传统文化营养濡染的痕迹。在《山本》中,这种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叙事方式表现得尤为突出。具体而言,贾平凹采用的是将《红楼梦》的日常书写与《三国》《水浒》的传奇故事书写糅合使用的写法。在表面的历史演绎背后,作者其实志在用一种大处写虚、小处写实的从容而精深的节奏来描写众生百态。在《山本》中,迎面而来的是一个与空间构造交相呼应的浑然一体的网状叙述结构,在这里,作者甚至不设章节,说到哪里是哪里,让全文自成一体,使人物命脉如流水一般自然流淌。而其中各色人物接连出场,大小事件错综交叉,平静生活夹杂波澜,矛盾冲突更迭不断。他正是用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在《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以历史纹路为脉的叙述格局之外,构筑起了另一种葳蕤多彩的、一树繁花式的原生混沌的叙述样态。
最后,这种审美意蕴体现在哲学思维上。钱穆说:“中国文学即一种人生哲学。”[20]而此在的“人生哲学”与西方意义上的作为万物尺度的“人的哲学”有着较为显著的区别。在西方,对于“人”的哲学思考常与宗教等因素纠结着,呈现出一种线性发展的命运意识;而中国的人生哲学,更多呈现出一种圆环式的轮回观和宿命论意味。同时,中国的人生哲学又灌注于天地自然之间,以天人合一为最高追求,《周易·文言》有语:“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21]这种中国式人生哲学,在贾平凹的《山本》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贾平凹看来,历史或许如秦岭的河流一样,呈现出季候性盈虚交替的周而复始;与之相对,在历史中的生命也如山上的花草一样,经历了无数次葳蕤与枯萎、繁茂与沉寂交替着的轮回。而这种轮回又似乎与某种敬畏天地的思维相契合。比如作品中井宗秀的英雄梦始终摆脱不了“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发迹、巅峰与最后走向毁灭的历史轮回。比如涡镇芸芸众生在炮火中化作秦岭的一堆尘土,都隐含着源于土、归于土的与天地化为一体的哲学意味。这正如安仁堂的陈先生所言说的那样:“人吃地一生啊,地吃人一口。”[1]207这样,哲学思维的本体从“人生”又回到了“秦岭”这一永恒事物上,正是以秦岭为参照,人生才显得扑朔迷离、混沌难解而又终将尘埃落定,这其中蕴含着东方哲思的独特韵味和魅力。
著名文学理论家卢卡契曾说:“对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来说……主要的是,他拥有什么样的手段,他思维和塑造的总体性有多么广和多么深。”[22]贾平凹无疑拥有这种广博的“总体性”艺术追求。他在对秦岭的一沙一石、一草一木的书写中,聚合了秦岭这一伟大的山的本真、多元而又含混的“混沌”状态。在《老生》后记中,贾平凹写道:“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在他心中,或许一直有为秦岭这座大山做志的雄伟抱负,而这“志”无疑是一个囊括万物的“博物志”,他这种“包举宇内,并吞八荒”的混沌书写,呈现出一种宏大的气韵和雄浑苍茫的艺术境界,给人以深深的灵魂震撼。
注释:
①“微写实主义”是华中师范大学李遇春教授在对贾平凹新世纪以来《秦腔》《古炉》《极花》等作品在特色分析基础上总结出的艺术特色,相关论文有《贾平凹:走向“微写实主义”》《“微写实主义”与传统的现代转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