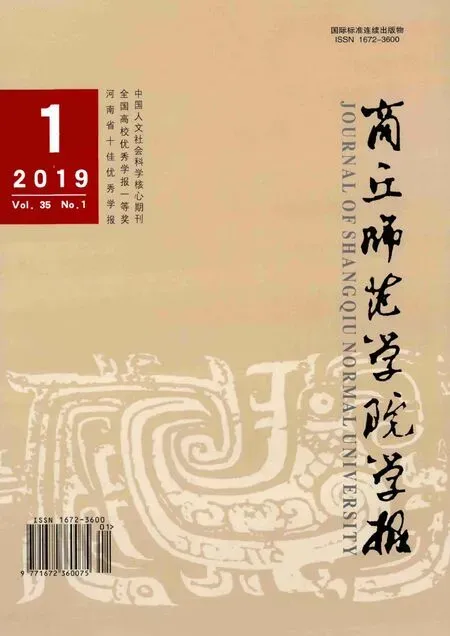合意与不合:对中国古代契约自由与平等的审视和反思
——以清代买卖契约为中心
李 秋 梅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
中国古代契约中亦充斥着大量用以表述双方“合意”的用语,如“两主先和后卷(券)”“两和立契”“两共对面平章”“两厢情愿”“自愿”“情愿”“三面言定”等,这既是民间对于交易自由、平等的诉求,也是中国古代自由与平等的契约精神的具体表现。清代是中国古代契约发展臻于成熟和完善的重要阶段,契约的订立不仅遵循“合意”原则,而且国家法律和司法实践都对该原则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因此,无论是在契约内容还是在契约实践中都能发现契约自由与平等的踪迹,从而为契约效力的有效发挥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清代对于契约自由与平等的维护
清代国家法中关于契约自由与平等的相关规定既是契约实践中“合意”立契的法律基础,也为契约自由与平等提供了重要空间。
1.清代继承了《唐律疏议》中关于买卖要“和”的法律精神,并在法律条文中具体禁止了几种买卖不“和”的现象。一是“把持行市”,就是不经双方同意,强买强卖或设置交易障碍为自己谋利。为此《大清律例》规定:“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杖八十。”[1]269第二种行为是勾结牙行,垄断市场价格为自己谋利,即“卖己之物以贱为贵,卖人之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1]269。第三种行为是在市场买卖时,故意抬高价格,迷惑买主,扰乱市场,即“若见人有所买卖在旁,混以己物。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取利者,虽情非把持,笞四十”[1]269。针对以上三种行为,清代予以严厉打击,在给予刑事处罚之外,还会依据获利的多寡加重处罚。清律规定这些不“和”的行为“若已得利,物计赃,重于八十杖、笞四十者,准窃盗论,免刺。赃轻者,仍以本罪科之”[1]269。
2.在契约订立时要求遵循“合意”,即双方自愿的原则,对于通过欺诈、强迫、偷盗等手段而订立的契约往往被判定为无效,过错方还会受到刑事处罚。清律规定:“凡盗他人田宅卖,将己不堪田宅换易,及冒认他人田宅作自己者,若虚写价钱实立文契典卖,及侵占他人田宅者,田一亩、屋一间以下,笞五十。每田五亩、屋三间,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徒二年。”[1]195-196还进一步规定:“若将互争不明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盗卖与投献等项田产及盗卖过田价,并各项田产中递年所得花利,各应还官者还官,应给主者,给主。”[1]196以维护合法所有者的权益。在条例中亦进一步规定:“军民人等将争竞不明并卖过及民间起科,僧道将寺观各田地,若子孙将公共祖坟山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内外官豪势要之家,私捏文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土,田地给还应得之人。其受投献家长,并管庄人参究治罪。”[1]196禁止强买强卖,规定把“各无抑勒、无负债准折、无重复买卖”作为财产交易的先决条件,强调契约订立时的诚实无欺原则,要求订立双方必须在知情、合法、合情的原则下进行自由交易。
3.通过对契约主体资格的限定保证交易的自由与平等。清代法律对一些具有特殊社会角色群体(如八旗子弟、文武官吏、宗教人士和外国人等)的契约主体资格在法律上作出了明确的限制,如“八旗人员不准在外省置买产业,违者产业入官,照将他人田产蒙混投献官豪势要律,与者受者同罪。其托民人出名诡名寄户者,受托之人照里长知情隐瞒入官家产,计赃论罪。受财者以枉法从重论。失察地方各官查参议处”[2]。“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1]263“传教士如在内地置买田地房屋,其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卖产人姓名,卖为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不得专列教士及奉教人之名。”[3]1347以防止特权阶层利用权势进行不公平交易,破坏正常的交易秩序。对于普通群体的契约主体资格则主要赋予了家长,清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十两,笞二十,每十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1]187虽然在具体的契约实践中,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变通,会有父子、母子、兄弟、叔侄等多种契约主体情况的出现,但基本上能保障契约订立双方相对平等的地位,进而保证契约订立的自由。
二、“合意”立契实践对于契约自由与平等的彰显
清代从国家法及相关制度层面极力维护“合意”立契,给契约自由与平等创设了一定的空间和条件,对契约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1.“自愿”“情愿”“两厢情愿”“三面言定”等类似表达双方“合意”的词语在清代买卖契约中频繁出现,俨然成了契约不可或缺的要件之一。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休宁县汪阿方卖地红契:“本都本图立卖契人汪阿方,今因钱粮紧急,自愿将……。此系两厢情愿,并无未必准折等情,从前至今亦无重复交易。”[4]1133-1134嘉庆元年(1796)大兴县王文学卖房红契:“立卖房契人王文学……今凭中说和,情愿卖与……三面言定……立此卖契永远存照。……”[5]1229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山阴县吴士猷卖田官契:“山阴县廿一都一图立绝卖田契人吴士猷,今将自己户内……挽中情愿出卖与本县族处名下为业。……”[5]1393,等等。即使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也能在其留存的契约中找到相同的话语。如道光二十六年喀喇沁左旗常明等卖山荒地白契:“立卖山荒地柴木人……情愿卖与赵福来名下耕种,永远为业。”[5]1392贵州锦屏苗族嘉庆十四年(1809)姜老祥卖田契:“立断田约人上寨姜老祥,为因缺少银用,自愿将白堵先年买荣周之田,地名白堵,出卖与姜朝甲名下。当面议定价银…… ”[6]108无论“情愿”“自愿”还是“三面言定”,其传达的意思都是契约当事人是基于自由意愿而订立的契约。
2.买卖契约的主要内容如成契理由、买卖标的、标的来源、对价、契约性质、买受人等在法律的规定内都可以自由选择。成契理由源自敦煌契,无非是要交代清楚交易行为的原因,在清代买卖契约中已经高度形式化,大多数概括为“因乏用”[4]1007“今因缺用”[4]1035等,有的干脆直接省略,如康熙十九年(1680)休宁县鲍嘉祥卖地红契[4]1024,康熙十九年(1680)歙县郑元瑞卖山官契[4]1025等。但也不会影响契约的效力。清代契约中的买卖标的只要不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都可以由契约主体在“合意”的基础上自行商定,有一定的自由度。买卖标的种类与契约主体所在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地区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情况。清代的川陕湖边、闽粤赣南边、闽浙赣边、湘西南、苏南、皖南等地山区经济较为发达,因此就有卖山、卖林和卖林木的契约,如顺治十一年(1654)休宁县许实章卖山契[4]1004的买卖标的是荒山,嘉庆二年(1797)姜映友卖杉木山场契[7]29的买卖标的是山场,乾隆五十八年(1793)姜启章卖嫩杉木契[7]22的买卖标的是林木,有别于中原地区最为常见的田地买卖契约。契约中对买卖标的来源的标注是中国古代契约的一大特色,是对标的来源权利瑕疵保证。到了清代,对买卖标的来源的标注已经高度形式化了,基本归纳为祖遗、分配、自置三大类,道光年间的官颁契纸甚至直接省略了这一要件。契约中的对价一般都是“三面言定”,出卖人要请中人与买受人就价格问题进行商议。一般来说,契约的中人具有重要的平衡作用,他们的角色往往被“设定为一种人际关系‘协调器’,而参与到清代土地绝卖契约中来的,他们能有效弥补交易双方的‘信用落差’,为契约关系的相对平等提供平衡的支点”[8]。清代进一步区分了“绝卖”与“活卖”,并通过法律确定了两者不同的权利与义务。由活卖产生的“找价”行为及补充性契约进一步平衡了买卖双方的平等关系,是当时商品经济冲击下土地自由买卖及地权分化的直接体现。由于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的土地等财产的高频转移,契约实践中的买受人已经突破了亲邻的范围,拥有了更高的自由度,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闽北南平县小瀛洲在乾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用白银购山,然后专门用于种植经济林木的情况日趋增多,买卖契约中的买受人出现了专门的“银主”,这些“银主”一般是商人地主、富裕佃种植农或二地主,有的则是外地商人。买受人的范围扩大且呈现多样化无疑强化了出卖人的自由选择权。
3.在实现和确保约定的方式上,清代买卖契约主要以订立的书面契约为主,尤其是针对田地房屋的买卖更是较少使用口头契约,以确保契约效力。在契约具体内容中还经常用“恐后无凭,立卖房契永远存照”[5]1247,“恐后无凭,立此卖契永远存照”[5]1295,“无欠少准折,其地从前不曾与他人重复交易”[4]1023等词语强调书面契约的征信功能。当事人(包括出卖人、中人、代笔等)还要在契末署押,进一步确保契约的效力,但是在采用哪种表达方式、哪些当事人、采用什么样的署押形式上(画指、签名等)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契约主体具有相当的自由度。恰恰是这种选择权的保留使得不同地区的契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其所处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呈现出或多或少的地方性或民族性的特点,彰显着中国古代社会契约的自由与平等。如贵州清水江地区的苗族买卖契约,出卖人一般不在契末署押,乾隆五十八年姜金乔卖山场契:
立卖山场约人姜金乔……
凭中 姜老五、姜老所
代笔 姜弼周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初二日 立[7]22
三、清代司法实践对于契约自由与平等的维护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清代也将“合意”“是否强买”等作为判定契约有效与否的重要标准。如嘉庆十九年(1814)山东乐陵县刘宗孔因种地纠纷伤张志勤身死案中,“庄民刘宗孔,义祖刘士超契当张志勤之父张士忠地一亩六分。十八年冬见,张志勤将其转卖与宋百顺,未向刘士超之子刘克温回赎。……最后判定刘克温契当地面,饬令张志学(张志勤的胞兄,笔者注)备价回赎与宋百顺管业”[9]667-668。在这个案例中,张志勤将当出的土地在没有赎回的情况下违规私自转卖,有错在先,因此引发纠纷。地方官的判定过程首先是“契当地面”,即通过契约认定典当行为成立;然后考察买卖契约的订立是否“合意”,因考虑到买受人宋百顺对土地情况并不知情和出卖人张志勤已经身死的现实情况,据此判定买卖契约成立;最后还采取了平息纠纷的具体办法即饬令张志学(张志勤的胞兄)备价回赎所卖土地交给买受人管业。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双方订立的典当契约还是买卖契约,在判案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证据功能,而且判官还充分考量了契约主体双方在订立契约时的意愿,以此判定契约有效与否,并且会根据法律规定维护契约订立主体无过错方的权益和契约的效力。
但是如果契约有明显违法的情况,如买卖标的在法律条文中是明令禁止买卖的,如赡养田、家族共有财产、坟地等,所立契约即使是在双方“合意”的情况下订立的也会被认定为无效。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江西龙南县民钟四妹因盗卖公田被缌麻服兄钟运德砍死案[9]382-383,钟四妹因盗卖公共祭田(该买卖标的是禁止个体买卖的)与钟勉奇,被其兄砍死,地方官最后的判定为:“钟勉奇讯明不知盗卖情事,饬令该族将田赎回,照旧管业,契据追销。……三法司核拟具奏。”显然该契约之所以被判无效,是因为买卖标的不合规。再比如牟奇翠买田一案[10]9,因买受方牟奇翠所买田地中有刘姓祖坟,虽然牟奇翠已经缴纳了契税,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但是发生纠纷以后,地方官还是认定该契约无效,并令其所出之资由出卖人的户族补偿以防止再起纠纷。
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地方官在受理与契约相关的诉讼案件后的审理程序:先是调查,了解诉状所说的被告的罪状是否属实;然后判定契约是典还是绝卖,是不是强迫买卖,契约是否是伪造、有无涂改等;最后会在综合考虑法、情、理的基础上进行最终的判定。需要注意的是,其中“合意”与基本的法律规定是地方官首要考虑的判案标准,其次才会从情理上斟酌。黄宗智先生通过对巴县、宝坻、淡新档案的户婚田土关系案件的调查后认为,“在221件经过庭审的案子中,有170件(占77%)皆经由知县依据大清律例,对当事双方中的一方或另一方作出明确的胜负判决。……只剩下11件案子(占总数的5%)确是由知县用法律以外的原则仲裁处理,当事双方都在各自的要求和利益上做了些退让”[11]65-66。由此,清代的司法实践维护契约相对自由与平等的立场与国家法的立场是一致的,为契约自由与平等提供了重要的空间与支持。
四、对中国古代契约自由与平等的审视与反思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一方面,在国家法、国家权力以及民间百姓对诚信、自由与平等伦理价值的敬畏、尊重和追求的共同作用下,体现契约自由与平等的“合意”原则在清代多数契约中得到了遵循,民间谚语“千年田,八百主”形象地说明了作为古代中国最重要财产形式的土地买卖的频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契约关系和契约自由与平等的发展。契约主体不仅用“自愿”“情愿”“三面言定”等语句表达自己的意愿,还通过权利承诺与瑕疵担保等方式,表明自己的诚实无欺,从而确保交易在相对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确保契约效力,规范契约订立双方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社会的契约被赋予了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内涵。正如霍存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古代中国虽采取的是等级的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方式,但政治、社会与家族、家庭内部的等级并未消灭经济生活中契约的平等,缘在政治、社会、家庭伦理生活与经济生活不同,在朝、在家与在外不同,古代的中国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契约本身也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12]
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中国古代社会的契约自由与平等又是不完全、不彻底的。首先是因为古代中国始终不存在完全的、自由的财产所有权。古代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地缘和血缘结合的乡族共同体,某些特殊的个体(如父家长)拥有一定的财产私有权,可以进行财产的交易、分割、继承、让渡等,但这些权利无不受到乡族共同体的限制,表现在契约订立上就是“亲邻先买权”,在实际的契约订立过程中如果得不到乡族的同意,个体就难以处置财产。乾隆《合水县志》卷下“风俗·产业”中云:“贫者售产,必先尽房族,族知其急,而故俗掯之,则先言不买,冀其价之低也。及彼出于无奈,而鬻于他姓,则又以画子之社不足而相争持。彼受地者,亦以其族不肯画字也,而虑其后患,复不敢买,甚至有半价无交、迁徙岁月者,亦有卖地银尽,而族乃告留祖业者,皆恶俗也。”[13]10这也是为什么田宅买卖交易一般都是在同族、同村等具有血缘或地缘特征的狭小的范围内进行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私人没有完全的财产所有权。此外,私人或家庭财产,尤其是土地,还受到国家权力的干涉。政府出于控制的需要,设计和编制了严密的户籍与地籍制度,将百姓牢牢固定在这个制度框架内,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交易的自由选择权与自由度。由此,杨国桢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私人土地上的共同体所有权是两重的(国家的和乡族的),它们和私人所有权的结合,便构成中国式的封建土地所有权。”[13]5所以古代中国不存在私人的完全的财产所有权,也就无法保障完全的契约自由与平等。
其次是身份意识的高度发达,严重侵蚀了契约自由与平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身份社会。“作为亲属组织的宗族或家族不仅是古代社会重要的政治、经济单元,也是流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和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网。”[14]107家族伦常的身份规则不但是国家生活的规范,同时还是一般人际关系的模式,成为古代中国各类社会关系方面的基本要素。在身份社会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伦常规则和运行机制又强化了狭隘保守的自然经济发展形态,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支配着财产的分配、交换、分割、让渡等,支配着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活动。如来自特权地主依仗政治权势的“夺买”,始终没有退出古代中国的财产分配领域。根据广东罗定州知州的逯英在其《诚求录》的记载看,“他每天接到的诉状中有七八成是诉告‘伪契占产’的”[15]369。大部分契约虽然都标明了“各无抑勒、各无准折”,但特权阶层仍然可以利用这些表面平等的契约行勒买之实。在高度发达的身份社会里,契约关系不仅领域狭小,而且往往被“身份”挤压变形,个人无法突破身份限制,自然也就发展演化不出现代契约关系。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说的那样,“一种基于合意的、法律上平权的关系能否构成普遍的社会状态,这一点不在于契约关系的有无,而取决于诸多其他因素”[16]45。清代虽然是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的成熟阶段,保留了大量的契约,但始终没能突破传统社会的束缚,契约关系仍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等级身份以及国家权力等的制约,无法真正和彻底地回归契约的本性——自由与平等,也就无法发展和演化出一种完全的、彻底的契约关系,推动社会的现代转型。
英国历史学家梅因曾指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17]109-110从身份到契约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就我国目前的状况看,在传统社会身份意识的影响下,各种身份观和身份规则仍渗透于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契约的本性——自由与平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借鉴和吸收西方契约关系及契约精神的精华;另一方面则需要从历史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挖掘和借鉴,为我国现代契约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深厚的社会土壤和文化支撑。因为现代的社会生活过程本身也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基于自由平等、自愿合意的基础上,不断签订契约和履行契约的过程。自由与平等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质。
——马鞍山市博物馆馆藏契约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