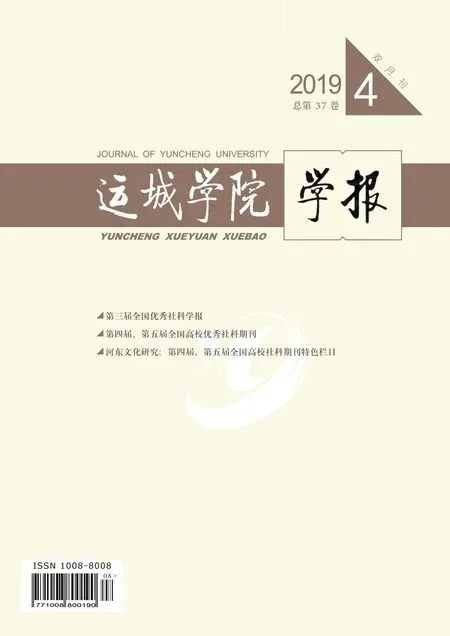清末内陆地区乡绅社会救济问题研究
——以近代晋南区域为中心考察
张 启 耀
(运城学院 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山西 运城 044000)
晚清时期,中国在西方科技、文化的冲击下,观念、学说乃至生活无不面临着变迁的局面,但传统小农经济仍以强大的生命力左右着农民的生活,将内陆地区的农民锢锁在乡土上。整个山西处在崇山峻岭之中,风气晚开,行动迟滞,对新潮流的接受,常是比较的落后。鸦片战争后,虽然晋南地区逐渐发生着一些新的变化,但由于深处内陆,各方面的变化相对缓慢,因此,与这一时代多数内陆地区的乡村相似,晋南乡村依然没有走出传统社会的生活模式。但伴随着近代以来内陆乡村的日渐贫困化,传统乡绅的社会救济状况却出现了新的问题。本文以晋南地区为主要考察范围,以内陆乡绅为考察对象,以近代发生的“丁戊奇荒”为考察重点,阐述晚清以晋南区域为代表的内陆地区乡绅的社会救济问题产生的背景、状况和影响,呈现出当时大多数内陆地区乡村社会救济的历史面貌。
一、问题的提出
论及近代内陆乡绅的社会职能,笔者经常想到的是家乡晋南地区以李子用为核心人物的李家。李家是近代晋南具有代表性的大乡绅,以“慈善”而闻名于世,现在的“李家大院”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在周边省区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山西其他区域的著名乡绅大族如祁县的乔家、榆次的常家、灵石的王家都是山西前近代商业发展的重要代表,而晋南地区的李家以彰显高尚道德的“善”文化为主要特色,最具备鲜明的精神特色,这是晋南地区在近代转型时期以李家为代表的传统乡绅“善”念不断、社会功能得到较好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体现,影响非同一般。
李家的善行代代相传,举不胜举,其所作所为与当时其他省份和山西其他地区的许多近代良绅、正绅相比,李家的道德品格更加令人钦佩和赞叹。我们并不需要一一列举李家的善行来说明问题,在此仅举近代的两例。一是清光绪三年(1877),“天大旱,人相食”,李家出资在晋南万泉一带放赈舍饭,救活不少百姓。另一次在1927年和1928年,又是晋南遭灾最为严重,连以往富庶的永济县也是“哀鸿遍野,穷黎失业,民间困苦情状不堪言喻”。[1]1391其他县份的情形更是惨不忍睹。灾荒中李家又“倾力相救,赈济灾民”。除了捐款一万多银元外,“并设三处粥场舍饭,使许多人都存活下来”。[2]11-12
这两次是李家善举中时间最长、赈款费用花费最多的两次赈灾行动。李氏家族把善行善举当己任,“为善最乐”成了他们的信仰。在整个山西的近代历史上,李家的财富不是最雄厚的,李家大院也不是最豪华的,但他们能代代相继,以道德行世,把慈善观念和慈善文化作为家族内部世代信守的行为准则,将李善人的美名传承了一百多年,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过,有一个问题是,虽然李家倾力救济,但光绪三年的“丁戊奇荒”中晋南乡村社会还是受灾最重的地区,出现“易子而食”、“道殣相望,饿殍遍野”的惨象,“人口大量死亡和逃荒,蒲、解、绛户口不及一半”,饿死者十之五六,很多家庭没有一个存活下来。[3]41,42
笔者在这里并没有对李家善举的任何怀疑,只是惊恐于如此驰名的善举也改变不了这一人间惨象。在此,笔者感觉要想真正了解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还是需要从清末的社会救济制度及深处内陆的晋南地区的具体情况入手,或许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问题产生的根由。
二、清末乡绅社会救济体系概述
在了解当时晋南乡绅的社会救济情况之前,我们先对清末的整体救济体系做简要概述。
在近代社会转型前,整个国家的基层社会救济体系基本都一样,那就是以乡绅治理模式为主的赈灾体系。这样的救济体系“经过数百年的演变与发展,对促进社会矛盾解决、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巩固统治基础、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4]也可以说,在灾荒时期,这种传统封建社会以乡绅为主的乡村赈灾和救济的作用与效果还是较好的。
有清一代,各类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救灾赈济是政府不能掉以轻心的事务。灾荒发生时,除了基层社会乡绅发挥传统社会职能而组织协调、出粮出款等之外,政府逐步形成一套自下而上奏报,自上而下拨款赈济的机制。一般由州县官员秉报省上,再由巡抚或总督奏请皇帝施行赈济。主要措施有:(1)像历朝历代一样,灾荒发生后,开放常平仓、义仓或社仓散发粮食救济灾民。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储粮备急以抗渡灾荒的救济方式,清代也是这样。官府所设粮仓称作常平仓,而民间所设粮仓则称作义仓或社仓;(2)缓征甚至减免钱粮赋税等。[5]传统的中国基层社会救济制度一直是这样。可以看到,对于灾荒,地方乡绅基本都能配合政府积极实施救济,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灾荒救济体系。但是近代以来,清代的基层社会灾荒救济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且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南方经济较发达省份与北方内陆省份的救济制度也出现了较大差别。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基层社会贫困化的加剧,以及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基层社会的传统乡绅治理模式以及赈灾体系受到了巨大冲击,尤其是伴随着北方省份基层社会的极度贫困,以前灾荒之年的乡绅救济体系和状况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相对北方省份而言,由于东南各省经济发展较快,基层社会乡绅势力较强,乡村赈灾救济体系保留得相对较好,很多地方的救济体系在近代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甚至发展,其力量也得到了不断加强。因此,近代以来的南方发达地区和北方内陆省份经济落后地区的赈济救济情况产生了较大差异。下面举例进一步说明。
首先以近代江南的乡绅治理情况和灾荒救济模式为例说明。在近代江南的乡村治理过程中,一些乡绅社会职能最显著的两个表现就是:第一,乡绅倡导善良风俗、宣讲乡约等传统教化方式仍得以不断延续甚至发扬,一些士绅还创建了善堂,专讲“乡约”,对维护江南基层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第二,一些江南乡绅能够继续秉承传统时期的社会职能,积极参加公益事业。在一些公益活动中,如救济灾民、兴修水利、设立义仓等等方面,他们不仅保留了传统乡绅服务乡社的精神和意识,而且具备实施服务基层社会的经济能力,因此,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继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样的乡绅不在少数,如清末江苏南通状元、实业家张謇,苏州状元陆润痒,江宁秀才史量才等。[6]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看出,这些江南的乡绅与北方乡绅相比,大都人数较多、实力雄厚、影响很大,对一个区域社会产生着导向性、引领性甚至是挽救性的作用。当一个区域社会发生了足以影响当地社会发展的事件或大的灾荒,江南乡绅的声望和财力足以应付自如。这与近代晋南乡绅的情况及晋南区域社会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以苏南地区的义庄为例做进一步说明。
据学者李学如研究,清代南方地区苏南区域的大大小小各类义庄就有360个左右,仅苏州在清朝末年仍有义庄200左右,对庇佑弱势群体、确保社会安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7]43义庄的出现和发展,涉及家族制度的发展变迁、乡村地权流动、家族教育、社会救助、基层社会控制,以及绅权、族权与地方政权的互动与渗透等诸多核心层面。苏南义庄的许多功能,与今天的基金会、慈善会有诸多类似之处,它涉及济贫、赡孤、养老、备荒、助学、嘉婚、恤丧等施济的主要内容,尤其在慈善解困、和谐人际、安抚人心以及社会自我调节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可知,义庄的基层社会功能在实施过程中都有较严格的制度规定和顺畅的程序安排,还有详细的应急保障机制等等。[7]261-353从这些措施中可以看到,南方发达地区的乡绅救济体制已经比较完善,在灾荒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一方面乡绅及义庄数量众多,经济实力较强,另一方面各个乡绅及义庄之间互相配合,组织完善,能较好完成救济灾荒的事务。因此,清末时期,虽然江南地区也是灾害频繁,但由于传统乡绅的社会救济体系得以传承甚至发展壮大,却仍很少造成大的社会灾难。[8]
三、清末晋南乡绅的基层社会救济状况
通过将近代南方经济发达区域与北方内陆晋南地区灾荒之年的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其结果是发人深思的。相比苏南地区,在社会职能方面,传统晋南乡绅实际上发挥的作用并不大。整个地区没有固定的和常设的乡绅救济机构,只是在灾荒发生时出于乡绅的道德和良心而临时成立了救济机构。平时本就数量不多的河东乡绅的社会功能就是简单的儒教宣传、乡村纠纷调解、数量不大的灾年救济等,完全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我们在其他文章中还有专门的探讨。以下我们以“丁戊奇荒”为例做进一步说明。虽然近代晋南乡村社会保留了很多传统时期的美德,如强调农耕、注重节俭、传承家训等等,但是晋南社会和乡绅普遍的保守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近代以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落后性。19世纪70年代,中国中部地区的山西、河南等省发生了持续数年的严重干旱,造成惨重的灾荒。这场奇重的旱灾以1877、1878两年最为严重。因这两年分别为旧历丁丑、戊寅年,故史称“丁戊奇荒”。山西在这场灾荒中受灾面积最大、受灾程度最重。1877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清政府奏报:“晋省迭遭荒早……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9]741“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者何止千人”。[9]514饥民数量、赈灾规模、资金捐募、粮食需求均达到惊人地步,赈灾活动成为一项浩繁的社会工程。
但就在灾荒发生时期,晋南地区的救济体系存在着严重问题。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各地都应设有官仓、常平仓,另外还有当地民间兴办的社仓和义仓。虽然据史料记载,“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安邑县(即今晋南地区的盐湖区)共有仓舍6座34间。常平仓额谷16000石,社仓无定额储谷12410石,义仓储谷6460石。至光绪二年(1876年),河东(即晋南地区的别称)运阜仓额存谷2931石,而实存谷仅93.1石,不及额存的1/30”,储粮缺额十分严重。何况志书记载安邑县当地的社仓和义仓也是“时兴时废,且多被土豪乡绅把持”,在灾荒中作用不大,而且早已经“放赈殆尽”。[10]98
当时灾情出现后,朝廷即根据山西巡抚上奏而要求“捐备仓谷,以济荒歉”,具体做法是“设立丰备仓之法,劝民遵办,其向有社仓者,加意整顿,其未立社仓者,赶紧捐储,事成报官,地方官不得问其出入,以杜扰累”。[9]274从措施中可以看出,政府把救济的主力放在了民间。因为根据清代丰备仓章程规定:“是仓民捐民办,专为本地备荒而设”。[11]卷三7-8但是,在近代晋南的基层社会,由于经济的落后性,民间百姓生活困顿,乡绅实力欠缺,鲜有大富之家,丰备仓的作用也大打折扣。
常平仓虽是官方最重要的粮食储备系统之一,但是,咸丰以后国力衰落,朝廷内外交困,财政拮据,传统的自上而下拨款赈济的机制遭到破坏,粮食储备严重短缺。这样,国库缺乏拨发巨额银粮的能力以及部分官方机构的耽误,确实难以解决饥民保命所需的粮食问题。何况,晋南地区交通不便,运输工具落后,靠官方为主赈济也不现实,所以,组织和发动民间力量运粮和捐输成了这次灾荒发生时的主要救济渠道。晋商作为当时活动于乡土的一支经济力量,也积极参与捐资济灾事务。他们大多是大户独设一处或数处粥棚,中小户则联合设立。如榆次常家散发家存粮食数百石,祁县乔家“于亲故之惆恤,灾歉之赈施,独倾囊资助无吝啬”。平遥较有名气的票号掌柜邱泰基“设粥棚放赈,民赖此而活者以万计”。[5]
可以看出来,在清末“丁戊奇荒”救灾过程中,政府传统慈善活动的弊端日益显露。在国家整体贫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实力极为有限,再加上救灾组织实施混乱,运送和散发粮食过程缓慢,使不少饥民在漫长无望中饥饿倒毙。晋南地区河津县乡绅周玉章在《光绪三年荒旱请求豁免钱粮文》中叙述灾年之惨状说:“予津邑不幸,天灾流行已经乎数载”,“欲把田园卖尽,而富寡贫多”,“因而父弃子,夫抛妻,千门半悬锁;毙于家,逃于野,十户九无烟”。[12]1112从这位乡绅的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河津县富有的乡绅极少,而且在遭遇灾荒之际,在很长时间,政府的赈济行动缓慢甚至没有发生的迹象。另有史料记载:“前工部侍郎阎敬铭,奉命原济,但因措施荒唐、用人不当徒费钱财,百姓并未得救。时有:‘山西有幸逢曾抚、河东无命遇阎罗’的民谣”。[13]402
救灾中商人的赈济活动虽也有补充政府“荒政”的成分,但从史料中可以看到,虽然晋商在灾荒赈济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相对山西中部地区,整个晋南地区的商人力量还是较小,赈灾人员和机构数量还很少,传统晋南乡绅治理基层社会的职能和机构并不发达和完善。结果是,在政府力量弱小的乡村社会,绝大多数晋南乡绅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如平常之年应付乡村社会传统职能尚可,但一遇较大的灾荒之年便几乎束手无策,作用并不很大。《芮城县志》记载说:“芮邑灾荒过巨,迭经蠲粮散赈无补万一,而死亡枕藉”。[14]833而“安邑原有17万人,灾后统计只余7万余人。解县6万余人,灾后幸存者3万余人,古今罕见”。[13]40
通过查阅史料以及分析受灾的程度,可以看到,灾荒救济中并没有充分体现出乡绅的社会职能,整个赈济事项从头至尾基本由零零散散的极个别乡绅来做,对灾荒救济影响不大,实在达不到救济应有的结果。因此,虽然李家是闻名远近的“大善人”,但是总体来看,像李家这样的大户在整个晋南地区的数量太少,改变不了整个晋南近代社会的保守性和经济的落后性,尤其是当地的粮食储备不足,即使是个别的大户人家,储粮的数量也是很有限的,基本上不存在古人所说的“耕九余三,耕三余一,以备荒旱之灾”的情况,这成为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至于当时晋南地区粮食储备普遍减少的原因,一些学者也有过探讨,大致原因比如由于洪水冲刷的自然因素和盲目开荒种地而毁伐山林破坏植被造成的水土流失的说法;还有就是清政府为了增加赋税和财政收入,竟允许并鼓励民众大面积种植鸦片,使耕地更为减少的说法,等等。这些研究的结果都是有史实依据的。[15]
所以,归根到底,晋南社会的普遍贫困化,是造成这次大灾荒的主要客观原因。光绪朝《山西通志》八十二卷中的荒政记对这次灾荒评论说:“(丁戊奇荒)较其情形,略与道光丙午年(1846年)相仿,即陕豫并歉,亦无甚异。以昔但借仓缓赋,不烦公家之赈,并无大伤;今则发币截漕至竭天下之财,几于不救。”[16]卷82《荒政记》从史料中可以看到,整个晋南以及山西区域在清代中期以来日益陷于贫困化,社会的整体贫困也限制了晋南地区大户人家的数量和财富,也就严重限制了晋南乡绅在灾荒之年发挥应有的社会职能。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晋南地区,每个县域的富有家庭都极为稀少,即使有个别较富裕人家有赈济行动,但由于家资有限,赈济行动的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即使如晋南地区大的富户——“大善人”李家,在“丁戊奇荒”中救济数量最多,也只能限于在晋南万泉一带设粥棚几座,救济能力和范围非常有限,遑论其他。当时晋南其他各县绝大部分乡绅在灾荒中尚难自保,更无力救济社会。如稷山县《姚家庄村志》记载,光绪三年,因周围并无救济的粥棚,姚家庄村民曹刚娃“一家五口人(有祖父母、父亲兄弟三个),三叔父被人杀死吃掉,二叔父和祖父母三口人被活活饿死”。[17]11-12新绛县在灾荒中无人救济,使“人相食,甚有骨肉相残者。饿殍遍野,坑坎皆满。村中户绝半,人十毙六七”。[17]1044从这些史料中根本看不到政府和乡绅有规模的救济迹象。看来,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当地乡绅连条件最差、最简单的救济机构都没有设置,晋南基层社会的贫困程度及政府和乡绅的救济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虽然士绅秉持社会道义和责任操守,在救灾中承担起基层社会领导者的角色,但是,近代以来,晋南区域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生产力较低,整个地区绝大多数人家都是贫困之家,可称作士绅的大家大户并不多。可以看到,相对南方地区而言,晋南乡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差异并不特别悬殊,晋南乡绅自身力量也十分有限,整个基层社会共同呈现出“普遍贫困化”的生活状况。尽管有李家在周围区域的周济,但力量仍显单薄,遇到这样的重灾,饿死者也是十之五六,并没有起到较大的社会救济作用。
四、余论
民国时期,实际上山西基层社会已经逐渐从乡绅管理体制向国家管理体制过渡了,但其中又夹杂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和因素,使得这种过渡过程并不顺利。包括晋南地区在内的许多地方的社会职能往往没有确切的担负者和责任者。也就是说政府在晋南地方社会的管理秩序还没有较好地建立起来,救济制度仍旧不完善。《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民政志》记载,虽然“清末至民国,境内(指今天盐湖区)多以官方出面或乡绅捐助开设饭厂施粥,或在冬令施舍衣食,但对贫苦百姓的救济时断时续”。因此,不管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乡绅层面都起不到真正的灾荒救济作用。[10]102甚至到了民国时期,整个山西基层社会的行政管理还是没有大的改观,一些旧的管理方法仍然存在并运行,但是县以下的行政管理机构却出现了,而且有了新的机构名称,但实际作用却不大。这种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乡绅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如果灾荒发生,仍旧于事无补。就在“丁戊奇荒”过去了整整50年的1928年,晋南地区再次发生了灾荒,但由于基层社会的救济体系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历史的悲剧又再次重演。
1927年和1928年,北方大部地区再次遭受灾荒,而晋南仍是受灾最重地区,连以往晋南最为富庶的永济县也是“民间困苦情状不堪言喻。见者心伤,闻者鼻酸”。[1]1391其他县份的情形更是惨不忍睹。“安邑、解州均有人食人的惨状。少数富有大户如车盘薛土先等。虽开仓济贫,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13]402
纵观整个近代时期,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及北方内陆区域发展的落后性,晋南地区的传统乡绅社会救济体系不仅没有得到进一步完善,反而因受到外来侵略的影响,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又受到自身地理环境的制约,这一体系支离破碎,根本没有起到应有的社会救济作用,最终在晋南及周边地区造成了史所罕见的大灾荒。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倡导“新乡贤”的引领和服务乡村的作用,而清末晋南地区乡绅的职能变化及救济状况不仅反映了近代整个内陆地区的社会变迁,而且这一问题也是历史留下的深刻教训,对当前的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