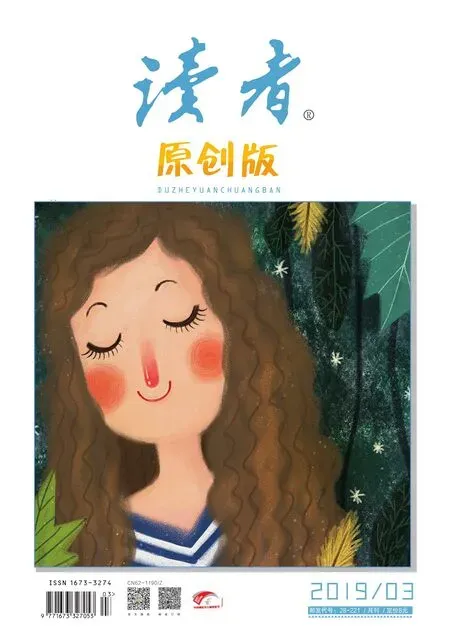罗曼蒂克不会消亡
文|韩松落

一
前段时间,看到了陆庆屹导演的纪录片《四个春天》,这是一部浪漫的电影,电影里的老夫妻,性格天真烂漫,对自然有着深切的热爱。更重要的是,他们能说会唱,老爷子会演奏许多种乐器,老奶奶开口就唱,即便是在自家的饭桌上,她也要唱几句酒令才开始喝酒。
随后就想起微博网友“蟹工船”说的几句话,大意是,我们很多“现代文明人”,特别排斥当众表演,或者是因为怕出丑,或者是因为觉得那是矮化自己,于是乎,丢弃了一份“做人的本真”。《四个春天》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的拍摄对象—那对老夫妻很特别。那对老夫妻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们没有丢掉那种做人的本真,那种生命的喜悦。那是真正的罗曼蒂克。
没有丢掉这种本真的人,其实还有很多。我的老家新疆,到现在还是一个说唱就唱、说跳就跳的地方;越剧的故乡嵊州,也是这样的地方,而且,他们至今也还在为了保持这种本真而努力。
它们都有一种罗曼蒂克的芬芳。
二
小时候,我生活在一个海派文化很浓郁的地方,经常能听到越剧,原因很简单,我生长的地方—新疆—有很多上海人,而新疆也是上海的对口援助省份,两地的交流非常频繁。在新疆的那些年,我们读的是上海的杂志,用的是上海的挂历,看的是上海的电视剧,连服装的款式,也都是参照《上海最新服装款式》。
所以很早以前,我就熟悉了袁雪芬、傅全香、尹桂芳、徐玉兰、戚雅仙这些名字,在电影院里,看过《追鱼》《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柳毅传书》《五女拜寿》。
但我真正开始了解越剧,却是从2018年开始。
2018年8月底,我去浙江杭州,看了“越剧小镇剡溪古韵朗诵会”。在朗诵会上,听了茅威涛、濮存昕、陈铎、童自荣、张凯丽、李法曾、赵敏芬、王卫国、徐涛、宋迎秋等名家,朗诵了许多首和流经嵊州的剡溪有关的诗。而诗的作者,是陆游、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安石、苏轼、汤显祖、蒲松龄、谢道韫、谢灵运。我才知道,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陆游的“名山如高人,岂可久不见”,写的都是剡溪。
为了庆祝小镇竣工,小镇举办了一系列演出,作为压轴戏的,是《山河恋》,演员是竺小招、茅威涛、方亚芬、吴凤花、陈飞、丁小娃、孔丽萍。
为了这两次演出,我做了些功课,但有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例如,为什么越剧会出现在嵊州?为什么越剧是以女性演员为主?为什么越剧的剧目是以言情戏为主?为什么建设“越剧小镇”对越剧传人如此重要?为什么开园庆典选择了《山河恋》这样一出戏?等等。
三
我找了很多和越剧有关的书来读,其中最得我心的,是姜进老师写的《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
这本书梳理了越剧的历史,介绍了重要演员和剧目,而且,从性别、政治、通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博弈、上海城市文化形成的各个角度,审看了越剧的历史。
嵊州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有着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却也有着动荡不安的过去。著名的越剧演员王文娟,曾在自己的回忆录《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里说:“曾有人把剡溪的‘剡’字分拆为两把火和一把刀,象征着家乡以前多灾多难,不是放火,就是动刀。”
乱世才有佳人,艺术往往是在动荡里产生的。多灾多难的嵊州,却是一个娱乐文化非常发达的地方。在吴迪编著的《越剧》里,嵊州地区的民间音乐、歌舞发展极盛,这个地方,几乎“村村有祠堂,堂堂有戏台,保保有庙,庙庙有舞台”,“见物唱物,见人唱人”。
越剧就在这里诞生。起初,它是贫苦人家为了谋生,发展出来的“沿门唱书”,其实就是一种乞讨卖艺的表演方式,伴奏也很简单,只有笃鼓和尺板。渐渐地,这种表演形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于是加入了表演,由说唱变成了演剧。1906年,艺人李世泉精心组织了一系列演出,有伴奏,有行头,正式宣告了这个剧种的诞生,当时,名叫“小歌班”。
用了20多年时间,“小歌班”在很多剧种乃至流行音乐里汲取营养,完善了表演形式,并且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但这个时候,它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逐渐从全男班,变成了全女班。
变成全女班的原因很复杂。从男女演员的表演能力来说,当时的女演员更投入,能力更强。当时的环境下,演员多半没上过什么学,对角色的体会不够深,在舞台上的表现往往非常粗俗;所谓剧本,其实也就是一个大致框架,全靠演员现场发挥。所以,舞台上的男人,通常浮皮潦草,点到为止。而对女性来说,能够走出山乡,获得工作的机会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她们多半非常用功,而且,故事里的悲欢离合,又常常能和她们自身的际遇产生联系,触动她们的心事,她们表演起来便格外投入,要笑就真笑,要流泪就真流泪。这就更能引起观众共鸣。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江浙一带的人们,世俗生活非常丰盛,世俗文化也非常发达,形成了一种“情文化”,注重个人生活,看重真情实感。越剧正是“情文化”的集中表达,台上台下也高度一致。就像姜进老师说的:“越剧的言情剧毫不脸红、永不疲倦、绝不吝啬地将整个舞台用作渲染爱情、人情的空间,而越剧迷们则毫不掩饰地在公共场合对自己喜爱的女演员和剧种表达出强烈的情感,虽遭一般人耻笑亦不顾。”这在别的地方、别的艺术领域,都是很少见的。
而在舞台上表达感情,讲述异性之间的情爱故事,男男搭档,男女搭档,尺度都很难把握,演员尴尬,台下的观众也尴尬,唯独女女搭档,丝毫不会让人不适。
从受众的角度来看,越剧的观众逐渐变成以女性为主,进一步影响了它的形态。20世纪是女性缓慢崛起的时代,上海作为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汇聚了大批职业女性。她们有了可以支配的收入,希望能得到适合自己的娱乐形式,也希望有社交生活,更希望能在娱乐中,发散出自己“被迫沉默和不被聆听的痛苦”,于是,她们开始走进戏院。男演员的表演,通常比较粗俗,不适合她们投射隐秘的情感,女演员就好多了。

于是,全男班逐渐被淘汰了,越剧变成了女子越剧。这可以解释后来发生的很多事:越剧在江浙一带受到的欢迎,例如越剧对情感表达、服饰、舞美的高度重视,越剧女演员对建设剧场和越剧学校的强烈渴望—女性都喜欢筑造属于自己的巢穴。
在越剧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个转折、几个实践,都和这些因素有关。
例如姚水娟、袁雪芬进行的越剧改革,她们剔除了越剧里的情色化表达,和过去的越剧划清界限;聘请文化精英来创作剧本,题材紧扣时势,“以民国上海通俗文学中流行的高度情感化的爱情剧模式取代之”;在表演上,发展出一种自然主义的表演模式,“以对爱与欲细致入微的情感表达取代了先前老套、粗俗的表演。”
她们也希望有自己的阵地,减少来自资本和民间暗社会的盘剥,建剧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越剧改革触动的不只有演员,还有观众。更多的女观众走进了戏院,和女演员紧密接触,甚至参与创作和宣传,为偶像成立各种“粉丝”组织,用这种方式来扩大社交,锻炼自己的社会参与能力。这和今天的“粉丝”组织,其实没有任何区别。
但不管怎么改,越剧的核心—一个“情”字—始终被当作越剧的精髓,爱情故事,始终是越剧的核心内容。越剧在非常年代的低谷,也和它有关。那些年,俗世和个人生活被当作“自私、琐碎的,甚至是有危害的”,“情”字不存,“越”将焉附?
一段越剧起伏史,其实也正是一部女性史。罗曼蒂克的消亡,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女性空间的消亡。
四
新的时代,要有新的罗曼蒂克。
越剧在不停地变革,从各种艺术形式里汲取营养,因为她本来就是在变革中产生的,“变”是她的开始,也是她的宿命。
但她也必须找到自己的原乡,给自己一个精神上和现实中的落脚点。幸运的是,她有。导演郭小男这样说越剧的故乡嵊州:“很多剧种都找不到原乡,不知应归属哪里。但越剧不同,她保护得非常好。当初越剧少女们从这里走出去,今天又将她送回来。”
她也必须找到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越剧小镇虽然以越剧为主题,却注册了一个面向世界的“世界戏剧联盟”。在越剧小镇的开园大典上,出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出形式,多半在户外进行,这种户外表演,取消了舞台上下的差别,因为越剧小镇的创办者想让这里变成一个到处有歌舞,到处有演出,可以让人们找到自己本真的地方。
而越剧小镇的“永久代言人”茅威涛则打算,让越剧变成一种大于原有越剧概念的表现形式。她吸收了国外舞台剧的经营、包装方式,建起小百花剧场,希望把它经营成纽约“大都会”那样的演出场所。
她甚至开始和韩国传媒集团合作,希望用韩国女团的方式来对演员进行包装。总之,在她看来,一切皆有可能。
在开园大典的宣传片里,茅威涛反复说着“梦里桃源,不负江南”。所谓桃源,所谓江南,不只是好山好水,其实也是一个能让人丢掉桎梏,找回本真的地方,一个依旧能够散发罗曼蒂克的芬芳的地方。
一如《牡丹亭外》所唱的那样:“从古到今说来慌,不过是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