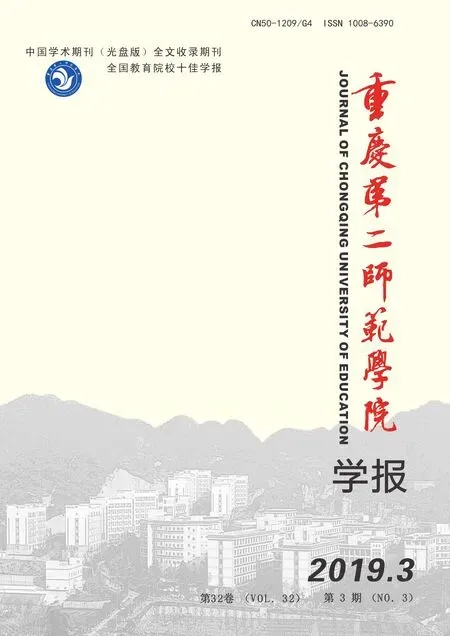劳伦斯的死亡诗及其死亡叙事语境和叙事技巧
陈贵才, 原一川
(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云南 临沧 677000; 2.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昆明 650500)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因小说的成就而为世人知晓和推崇,但他的文学之路却始于并终于诗歌创作。其诗歌是他对人生中的所到之处、所遇之人、所感之物、所悟之事、所思之境、所盼之世、所归之途、所怀之情的重要记录和曲折反映,因而诗歌最终成了他文学创作和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Hough所言:“劳伦斯的诗并不是他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而是他自身的一部分,它源于他的生活,反过来又滋养他的生活。为了写诗,他大胆地探索自己,通过写诗,他发现了自己。”[1]191从某程度上说,劳伦斯的诗是我们认识和体悟他最有效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我们可以有效地透视诗人所建构的丰富多彩的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主客观相结合的文本世界。因此,只关注劳伦斯的小说而不去深入挖掘其诗歌金矿就难以真正探明这位伟大诗人的闪光之处。虽然劳伦斯的千余首诗看似庞杂,但他的诗歌主题非常鲜明,大致可分为爱情诗、自然诗和死亡诗等。在以诗歌形式书写死亡的过程中,劳伦斯不仅表现了哲人的理性,而且表现了诗人超群的感受力、敏锐的洞察力和奇妙的艺术表现力,“对死亡的态度不仅充满理性,也不失诗性”。[2]103虽然劳伦斯在其《恋爱中的女人》《白孔雀》等小说中对死亡这一终极主题进行了诗意的书写,不仅把死亡描述为一个黑暗的王国,而且还全方位地呈现了暗淡的死亡景象,但与其小说中相对暗淡的死亡叙事相比,劳伦斯诗歌中的死亡叙事显得更加亮丽。因此,只有深入研究劳伦斯诗歌中的死亡叙事,才能有效领悟诗人死亡叙事的艺术魅力和生命诗学思想的光芒。通过梳理前人对劳伦斯死亡诗的研究文献发现,他们主要从意象、哲学、意识嬗变、异教拯救、主题和生态思想等方面展开研究,而从死亡叙事这一点切入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从劳伦斯的死亡叙事语境和死亡叙事技巧两个方面来探讨其诗歌中的死亡叙事,从而有效把握劳伦斯的死亡诗及其死亡叙事的艺术魅力和生命诗学的光芒。
一、劳伦斯诗歌中的死亡叙事语境
在劳伦斯的生命中,死亡一直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这挥之不去的阴影最终却成了他诗歌创作的闪光点,也是他庞大的诗歌文本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和必要的点缀。正是由于其众多死亡诗作的点缀,劳伦斯的诗歌文本体系才散发出迷人的生命诗学光芒。这些光芒不仅源于其爱情与死亡交织的诗作如《丧亲之痛》《爱的交战》《农场之恋》《终结》《新娘》《宛若处女的母亲》《樱桃盗贼》《年轻的妻子》《万灵安魂曲》《窗畔》等,而且源于其死亡与机械文明相关联的诗作如《我们死在一起》《当大多数人都死了》《死亡并不邪恶,机器才邪恶》《我们时代的死亡》等,甚至还源于其讲述死亡故事、表达死亡话语、展现生命与死亡的自然轮回和展示死亡与再生的诗学隐喻的诗篇如《死亡》《死亡之阴影》《召见死亡》《迎面死亡》《死亡之欢乐》《死亡之艰难》《死亡之歌》《灵船》《命运》《阴影》《疲倦》《睡眠》《睡与醒》《完全醒悟》《遗忘》《安宁的现实》《落叶》《当熟透的果子掉落时》《旅程已结束》《巴伐利亚的龙胆》《对月祈祷》《蝴蝶》《不死鸟》等。这些诗歌文本虽然不像其小说那样具备完整的叙事性,但它们却构成了劳伦斯独具特色的死亡叙事文本。在这些文本生成的过程中,劳伦斯充分而有效地植入了他的个人和家庭语境、英国的社会历史语境、英美文学语境和西方文化语境。
劳伦斯诗歌中的死亡叙事隐含着他早期痛苦的情感经历,这些经历既以小说的形式反映出来,又以诗歌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从情感经历来看,劳伦斯16岁时就“和他第一个持重的女朋友萍水相逢,他母亲本该把他推向争取独立的生活道路,可是她却把感情的纽带紧紧地系在他身上,压得几乎令人窒息”[3]17。后来,劳伦斯虽然分别结识了杰茜·钱伯斯、海伦·科克和露依·伯罗斯,并试图向她们求婚,但他始终未尝到成功的滋味。相反,他尝尽了痛苦,受尽了煎熬。直到1912年,27岁的劳伦斯才得到爱神的眷顾,真正品尝到弗丽达甜蜜的爱情。从诗歌创作轨迹来看,劳伦斯于1905年开始诗歌创作,并写出了《剪秋罗》和《绣球花》两首爱情诗。从此,20岁的劳伦斯就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并陆续创作了许多以爱情为主题的诗歌。然而,作为内心情感的重要记录和曲折反映,劳伦斯爱情诗中所刻画的诗歌画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他人生画面的现实写照:美好爱情憧憬的背后往往笼罩着凄惨的死亡阴影。这在《樱桃盗贼》和《农场之恋》两首诗中均有体现。在《樱桃盗贼》中,内心炽热的少男憧憬着美好的爱情,但死亡的阴影却成了他炽热爱情的冷却剂。在《农场之恋》中,诗人表达了“性爱的高峰体验与死亡感受具有共通性”[4]102。
劳伦斯诗歌中的死亡叙事根源于他所经历的死亡场景。在其成长过程中,劳伦斯亲身经历了三次死亡体验。1890年,不到6岁的他亲眼看见了一位当地的煤矿主托马斯·巴伯的长子托马斯·菲利普开枪打死自己亲弟弟的死亡场景。1901年,16岁的劳伦斯不仅目睹了死神降临到他23岁的二哥欧内斯特的身上,而且亲身经历了与死神搏斗的场面。虽然他赢了这一战,但对疲于奔命和病魔缠身的劳伦斯而言,死神在其日后的人生中始终对他纠缠不休。1910年12月9日,25岁的劳伦斯再次目睹了他生命中的主心骨和视他为宠儿的母亲的死亡。如果说劳伦斯童年时所目睹的死亡场景留给他的记忆是模糊的,那么哥哥和母亲的死亡场景留给他的则是刻骨的创伤记忆,而悬在他头上的死亡之剑让他切身感受到死神的强大威力和自己的无能为力。这些记忆和感受的叠加最终形成了强大的驱动合力,驱使生性敏感和超自觉的劳伦斯开启他漫长的死亡叙事之旅、灵魂救赎之路和诗意再生之途。
劳伦斯诗歌中的死亡叙事植根于英国的社会历史语境。在劳伦斯中后期的诗歌创作中,尤其是在其诗集《三色紫罗兰》和《三色紫罗兰续编》中,诗人的诗歌创作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向,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自我和自然,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工业社会中人类的共同命运。在这一转向中,诗人有效地将个人的生死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业社会中的产业工人已成了行尸走肉和自己的裹尸布,机械文明已成了戕害人类的罪魁祸首。为此,诗人发出由衷的感叹:“死亡并不邪恶,机器才是邪恶!”[5] 249作为一位负责任的诗人,看到工业社会中人性之根被无情地割断、人性之树的汁液被无情地榨干、人性之花被无情地摧残,劳伦斯为此发出了严重警告:“我们必将死在一起!”[5]228与此同时,劳伦斯又深切地祈盼着:“在死后的巨大空间,生后的轻风把我们亲吻成人性的花朵!”[5]237
劳伦斯诗歌中的死亡叙事植入了英美文学语境。在英美诗歌史上,英国诗人如莎士比亚、邓恩、济慈、雪莱、拜伦、兰陀、克里斯蒂娜、威廉·莫里斯、狄兰·托马斯、托马斯·哈代和叶芝等,以及美国诗人如威廉·柯伦·布莱恩特和狄金森等,都对“死亡”这一主题进行了不懈的探讨。他们共同铸就了不朽的死亡颂诗,共同建构了英美诗歌宏大的死亡叙事语境。在以诗歌形式书写死亡的过程中,劳伦斯不仅充分植入和有效套用莎士比亚的“死亡即睡眠”[6]21、邓恩的“死亡只不过是休息和睡眠的写照”[6]59、克里斯蒂娜·乔治娜·罗塞蒂的“死亡即进入寂静之国”[6]303、狄金森的“死神是一位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彬彬有礼的君子”[6]413等死亡叙事语境,而且还在其诗歌《灵船》中直接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个人能否用出鞘的利剑来解除生活的苦难”,沿用了狄金森的“露珠”意象。通过对英美诗歌死亡叙事语境的植入、套用、引用和沿用,劳伦斯为其死亡叙事找到了既有本可依又有源可溯的范本。从劳伦斯的死亡叙事与英美历代诗人的死亡叙事之间的互文关系中的文本线索可见,劳伦斯的死亡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体系,而是一个与英美诗歌死亡叙事传统形成语境互渗的文本体系。这一文本体系共同反映了英美历代诗人对生命和死亡的哲思,共同谱写了英美诗歌生命诗学的乐章。
劳伦斯诗歌中的死亡叙事还融入了西方文化语境。作为西方文化的集大成者,劳伦斯在其诗歌创作中充分汲取了西方文化的给养,巧妙地将他的诗歌创作融入西方文化语境中。在其死亡诗《灵船》中,劳伦斯融入了《圣经·创世纪》中的经典意象:诺亚、方舟和洪水。这些文化意象的融入一方面表明诗人已俨然成了诺亚,在遵循着上帝的旨意,为自己建造一只方舟,为即将到来的大洪水做好准备;另一方面表明他就是自己的上帝,在听从自己心灵深处的呼唤,为自己建好心灵的方舟,让惊恐的灵魂回归宁静的港口。因此,在死亡的洪水来临之际,劳伦斯心灵方舟的建造既是上帝的旨意,又是内心呼唤使然。虽然死亡的洪水势不可挡,但心灵的方舟可自由操控。当死亡的洪水到来时,脱离躯体的灵魂将扬着风帆、驾着轻舟,从生命的此岸驶向来世的彼岸,实现从死亡到再生的灵魂超度。
如果说劳伦斯的个人语境和家庭语境带给他的是个人的痛苦,那么英国的社会历史语境让他感同身受。他深刻地感受到人类的痛苦、民族的痛苦和社会的痛苦就如同他自己的痛苦。对于生性敏感和超自觉的劳伦斯而言,这些痛苦的叠加强化了他的创伤记忆,催生了他对死亡叙事的冲动。“叙事的冲动就是寻找失去的时间的冲动。”[7]48这种冲动又激起了沉寂在他心灵深处的死亡记忆。在探寻自我心灵深处的死亡记忆的同时,身为强力诗人的劳伦斯不仅将其前辈的死亡叙事语境巧妙地植入自己的死亡叙事中,而且有效地将西方文化语境也植入其中。这些语境的植入使劳伦斯的死亡叙事既呈现出个人色彩和社会色彩,又呈现出浓郁的宗教色彩。这些语境的合力最终使劳伦斯的死亡叙事变得立体、深沉、富有韵味。
二、劳伦斯的死亡诗及其死亡叙事技巧
在劳伦斯晚期的死亡诗中,死亡叙事技巧已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方面是因为他已深刻而透彻地领悟了死亡,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诗歌创作方面他已突破了传统的束缚而成了强力诗人。因此,在其晚期的死亡叙事中,劳伦斯在客观对应物的选择上总能信手拈来,在叙事技巧上总是游刃有余。这些死亡叙事技巧包括环形叙事、二元对立叙事和戏剧独白与内心独白的混合使用等。
(一)环形叙事
数学中的环形是指环状的几何图形,而几何学中的环形通常指圆环,即大圆盘在挖去一个小同心圆盘之后所剩下的部分。无论从美术学还是从几何学的角度来看,环形结构所呈现给我们的直观画面就是圆形。这极为寻常的图形如果在文学作品中恰当地运用,就会产生非同寻常的效果。由于圆形常喻指团圆或圆满,中外诗人常巧妙而娴熟地对其加以运用。中国北宋诗人苏轼《水调歌头》中的圆形隐喻让人耳熟能详。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圆规意象让人耳目一新、拍案叫绝。作为英国玄学派诗歌的继承人和开拓者,劳伦斯虽然并未在其死亡诗中直接采用环形结构,但他却把这一结构灵活运用到了极致。在读这些诗时,细心的读者既能感受到生死轮回的无情,又能从中获得无限的阅读快感,因为读者总能感受到生命犹如滑动的圆环,从起点滑向终点,又从终点滑向起点,永不停歇地滑动着。这种生死回环在其后期的死亡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在《灵船》中。在此诗中,诗人绘制了一个三维同心圆环:生命轨迹的圆环、生命始终的圆环和灵魂朝圣的圆环。
首先,诗人通过四季的循环绘制了一个生命轨迹的圆环。在《灵船》这首诗中,劳伦斯把衰败的秋景作为死亡叙事的背景,将死亡的过程追溯到生命之秋。其用意表明他已度过了萌发的春天和繁茂的夏天,现已步入衰败的秋天,而且沉睡的冬天早已向他招手。根据西方传统观念,作为小宇宙的人是大宇宙的缩影:稚嫩的青少年对应的是春天,风华正茂的壮年对应的是夏天,年老体衰的暮年对应的是秋天,死亡对应的是冬天。劳伦斯在周而复始的四季循环与人的生命轮回之间建立了恰如其分的联系。从这个联系性可发现,生命的轨迹就是一个圆环,一个从生命的起点滑向生命终点的圆环,因为“死亡既是终点,却又是新的起点,死亡能够让旧的自我走向新的自我,从而构建一个生命的轮回”[8]89。
其次,劳伦斯还用掉落的苹果这一意象建构了一个“源于尘土,回归尘土”的生命始终的圆环。在《圣经》中,苹果是生命之果,苹果树是生命之树。当苹果从树上掉落,它就失去了与树的联系,它的生命也随之终结。但是,它却与泥土形成了新的联系:苹果虽然腐烂融入泥土,但它的种子将从泥土中萌芽、生根、长叶、壮大、开花、结果,其果实又熟透、掉落、腐烂、融入泥土,然后重新萌发。从这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劳伦斯敏锐地在苹果和人之间发现了关联,最终巧妙地建立了他们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的建立在为读者呈现一个自然生命圆环的同时,也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充满宗教色彩的生命圆环。
再次,劳伦斯还用在生命此岸与来世彼岸往返的“灵船”意象建构了一个灵魂朝圣的圆环。在劳伦斯生命的晚期,由于病魔的不断蚕食,其生命之流已几近枯竭,生命之树渐趋枯萎,生命之果也即将掉落。这让他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于是准备向自己的肉体告别,“该走了,向自我道一声告别,/ 从掉落的自我中/ 寻找一个出口”[5]251。通过这个出口,他开启了漫长的灵魂朝圣之旅。为了这漫长的灵魂之旅,诗人在死亡洪水到来之前敦促自己造了一只方舟,并准备好食物和各种用品。当死亡洪水到来时,他就启航:“这就开航,/随着躯体的死亡和生命的离别,/开航。”[5]257在漫无边际的汹涌的死亡之洋上,方舟失去了方向和港湾,漫无目的地漂浮着。最终,灵魂脱离了躯体,各自走远。当死亡洪水平息时,躯体漂浮起来,灵魂回到自己家里:
洪水平息了,躯体,就像衰旧的海贝,
奇怪地、可爱地浮现出来。
小船急速回家,
在粉红色的洪水上,摇晃,渐渐消失,
易碎的灵魂跳了出来,又回到她自己的家里,
用宁静填塞心房。[5]
这样,灵魂在脱离躯体之后,“她”就乘着通达生命彼岸的航船,在死亡之洋上开始“她”的漫漫朝圣。当泛滥的死亡洪水平息之后,灵魂又回到了朝圣的原点。通过启程、远航和回归的回环,劳伦斯为他灵魂的朝圣画了一个圆环。
由于劳伦斯所绘制的三个圆环即生命轨迹的圆环、生命始终的圆环和灵魂朝圣的圆环都是以诗人或者说是叙述者为中心的,因此,劳伦斯最终成功绘制了一个三维同心圆环。通过同心圆环的绘制,劳伦斯在扩大死亡叙事空间的同时,也拓展了死亡叙事的维度,实现了从今生到来世的时空跨越,完成了从生命此岸到来世彼岸的往返,并最终获得了死亡的高峰体验,因为“死亡是人的最高限定,是生命历程的终点,又往往是精神运动的最高点和情绪波潮的巅峰”[9]46-47。
(二)二元对立叙事
在劳伦斯的死亡诗中,肉与灵、洪水与方舟、黑暗与光明、旧的自我与新的自我、痛苦与欢乐、沉睡与苏醒、死亡与再生等是较常见的二元对立结构。肉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该范畴的奠基人柏拉图认为:“处于死亡状态就是灵魂离开了肉体而独自存在。”[10]13这是从哲学的角度对死亡的定义。劳伦斯的死亡叙事中虽然有这一方面的意义,但更多的是诗意,因为他为读者呈现的是惊恐的灵魂与勇敢的自我、狼狈的灵魂与坦然的肉体。在死亡的洪水与心灵的方舟的二元对立中,虽然死亡的洪水来势汹涌,但漂泊的心灵方舟最终还是找到了宁静的港湾。在黑暗与光明的二元对立中,死亡的黑暗最终被再生的光明所取代。在新旧自我的二元结构中,灵魂告别了旧的自我,去追随新的自我。痛苦与欢乐的二元结构展现了死亡的悖论即死亡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死后是欢乐和甜蜜的,因为死后完美的生命之花和人性之花必将绽放。在沉睡与苏醒的二元结构中,短暂沉睡之后便是长久的苏醒,苏醒之后一切将回归生命的原初。在死亡与再生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新生命的孕育。正是由于这些二元对立结构的有效呈现,劳伦斯的死亡叙事才显现出巨大的张力美。
(三)戏剧独白和内心独白的混合使用
“戏剧独白指人物与臆想中的他人的对话,或者说,人物的表白、申述是说给某个人听的或写给某个人看的。”[11]90在劳伦斯的死亡诗中,诗人常把死神看作一个存在之人,继而与之进行对话。在诗歌《死亡的欢乐》[5]236中,诗人与死神进行了直接对话:
喔,死亡,
关于你我一无所知,一无所知——
关于生后,
我一无所知。
然而,喔,死亡,死亡,
我对你非常了解,
那知识在我体内,不是什么不可见的事实。[5]
在这段对话中,诗人在表达了对死亡一无所知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死亡的无所不知。这看似矛盾的认知体验表明诗人虽然对抽象的“死亡”不太了解,但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死亡体验的理解却是具体而现实的。“内心独白就是心灵的自我对话, 是将人物内心世界默然无声的意识活动展现于读者视听感官的一种写作技巧。”[12] 56在劳伦斯的诗歌《艰难的死亡》和《灵船》中,诗人心灵的自我对话展现得尤为明显。到生命的晚期,由于病魔的不断蚕食和死神的日趋临近,劳伦斯早已意识到死亡的洪水即将到来,于是他敦促自己造起灵船,为即将到来的死亡洪水做好准备,为脱离躯体的灵魂找个安身之处,为病入膏肓的自己找个心灵的寄托。在《死亡之歌》中,劳伦斯同样与自己在心灵深处进行着对话,但这时的他不是在敦促自己,而是在鼓励自己,鼓励自己“唱起死亡之歌,喔,唱起来吧”[5]263。这一心灵深处的对话让人感觉到这时的他已为死神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当死神降临时,他就扬起心灵的风帆,向死亡之洋高歌猛进。这两种独白的混合使用使劳伦斯的死亡叙事具有一定的对话性。
三、结语
劳伦斯的死亡诗是他对自己痛苦的死亡经历、死亡感受和死亡体验的重要记录和创伤性的记忆。从这些记录和记忆中我们发现诗人对死亡感受力的敏锐和感知程度的深刻。在深刻感受和充分记忆死亡的过程中,劳伦斯不仅植入了他的个人语境和家庭语境,而且还植入了英国的社会历史语境、英美文学语境和西方文化语境。这些语境的植入使劳伦斯的死亡叙事不仅具有自传性、特殊性、社会性、历史性、继承性和宗教性等特点,而且具有开创性、超验性和普遍性等特点。这些特点进一步说明身为敏感诗人的劳伦斯并未受这些传统语境的局限,相反,他开创性地把个人的生死、民族的生死和人类的生死编织到他庞大的死亡叙事网络之中。在编织死亡叙事之网的过程中,劳伦斯又将环形叙事、二元对立叙事,以及戏剧独白与内心独白等叙事技巧有效地运用到其中。这些叙事技巧的运用不仅凸显了劳伦斯死亡诗的张力美和对话性,而且扩大了死亡叙事空间,拓展了死亡叙事的维度,最终为其从此生到来世的时空跨越和从生命此岸到来世彼岸的往返搭建了诗歌艺术的桥梁。总之,劳伦斯突破了死亡视角的阴暗面,在死亡的阴影中创造了诗歌的闪光点,最终成了永生不死的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