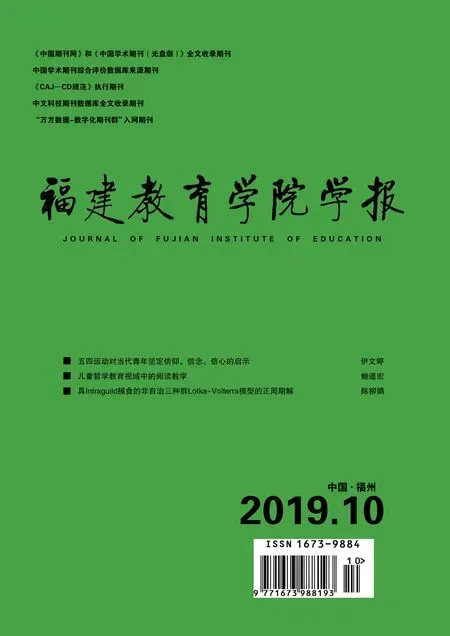语文科渗透哲学教育的应为与可为
蔡鸿菲
(厦门第六中学,福建 厦门 361000)
语文核心素养作为学生个体发展的基础,对其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门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语文科通过引导学生在积极主动的语言实践活动中,构建言语经验和言语品质,来促进他们在语言知识和能力、思维方法和思维品质、审美情趣和文化感受等方面获得发展。同时,源于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伦理”培养目的,语文学习被赋予了更多地责任,如修养身心、陶冶性情,甚至涉及提高心灵境界这一中国哲学传统范畴。据此来看,语文学习本身是被赋予了哲学教育要求的,语文科与哲学教育的联系更是毋庸置疑。正如施良方所言:“所有课程观都与哲学观存在着某种联系。离开了哲学的基础,学校课程就无法竖立起来。”[1]基于学生好奇、求知、爱问的哲学天性,通过渗透哲学教育的语文学习,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显得尤为重要。
一、语文科渗透哲学教育的应为
(一)传统哲学影响与理性缺失的补充
我国的语文教育从巫术文化及殷人造字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自殷商至清末,语文教育都是与经学、史学、哲学、政治、社会伦理等相融合的。真正独立设科,则始于《癸卯学制》;自此具有现代意义的语文科得以确立。就我国语文教育而言,无论是符合“伦理型文化”特征,以伦理学习为主、与政治相连的古代语文教育,亦或是具有技术取向、功利性与工具性特征的现代语文科教育,乃至新世纪以来确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立德树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语文学科定位等,都或多或少被“尊德性”与“道问学”两大主流思想所影响。冯友兰曾提出,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和为道的区别。为学的目的就是“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提高心灵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2]提高心灵境界,追求个人修养,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等,皆是我国传统哲学范畴所涉及的。因此,可以说我国语文教育本身是受传统哲学教育影响的。
中国哲学提高心灵境界的追求,是以体验“道”为最高目的,而不是建立在逻辑推理基础之上以追求真理为旨归。它更多的是靠感悟与想象来进行思考,而非西方哲学以概念的演绎、逻辑推理来表达绝对真理。正如潘庆玉所认为的,中国哲学没有在经验与现象世界之外,建立一个脱离事物本身的逻辑推理意义上的思辨系统。与西方“能指主义”的语言哲学观不同,中国哲学具有“受指主义”的精神气质[3]。这也影响并形成了依赖感悟联想,脱离逻辑推理的传统语文教育观。总之,这一哲学传统影响,使语文教育更加注重体验性思考与伦理规范的认识,缺乏了对真理的渴望与追求,本质上是缺乏理性精神的。因此,语文科渗透哲学教育,引导学生理性思考,显得尤为重要。
(二)语文科课程取向的必然要求
语文科的课程取向决定了语文科要面向何方;同时,又因与教育政策相粘连,所以对语文课程与教学目标有着重大的控制力。随着20世纪语言哲学转向于寻求“思维和存在”“人和世界”中介环节,探寻“思维”“语言”“存在”三者之关系;相关的研究也不再纠缠于语言文字、文学、文章、文化、语感等具体范畴,而是更多地通过关注“语言”与思维、存在的结构、功能关系,实现了从“实体性”思维向“关系性”思维的转变。这些转向都给予了语文课程取向研究重大启示。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围绕语文科课程取向进行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如“语感中心说”“培养语文能力与审美教育”等取向主张;亦或是当下语文科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取向……都涉及了语文科提高学生“心能”的作用。正如王宁所说:“语文教学就是要提高学生的心能。人的心的能力是以思维为中心的。”[4]
与课程取向密切相关的语文课程标准,也较为明确的体现了语文科渗透哲学教育的要求。例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所指出的“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5];《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规定的“发展思辨能力,提升思维品质”“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通过语言运用,获得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创造思维的发展,以及深刻性、敏捷性、灵活性、批判性和独创性等思维品质的提升”[6]等。关于语文科对思维培养的重要性,王宁曾说:“语文课在提高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同时,也必须把思维能力和品质的培养作为时代的要求来看待。因为不论是鉴赏品味的提高还是对传统文化优劣的辨析能力,都与价值观和思维能力直接相关。”[7]
(三)视觉文化转向下的哲学教育需求
在视觉文化转向下的今天,图像已居文化符号霸权地位。生活中无论是在影像、资讯、广告,亦或是畅销图书(如各类图解系列)等,各种图像符号正呈现迅猛增长趋势。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习惯于读图的便利与舒适。例如作为重要媒介的手机,更是成为人们(包括中学生)的“必备”。于是,“被机器奴役乃至统治”的忧虑开始不绝于耳。早在20世纪20年代,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中就谈到“印刷机统治时代和电视的统治时代的话语形式的差异。我们由清晰易懂的严肃而有理性,富有逻辑的话语形式转变为简短通俗,人民的思维方式不再是抽象而是具象”。而今,视觉文化转向下的读图时代更是如此;思考越来越多的受到一些具象影响,而缺乏个人的深度思考。美国学者曾撰文指出,年轻一代人的认知模式发生了改变,出现了由深度注意(deep attention)向亢奋注意(hyper attention)的转变。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到处可见的学生“低头族”现象,不禁让人们十分担心学生的成长健康性。即使那些“低头”的孩子们正在借助手机阅读网络小说,或微信朋友圈时常出现的“深度好文”……可能这种担心仍不会消减。究其原因,是此种阅读为基础、浅显的阅读,而非高级、深层的阅读。因为在手机媒介上进行阅读,本身似乎就已经包含了以具象“读图”为路径的“消遣”“了解”乃至“娱乐”的因素,而根本无法进行严肃深层的阅读思考。特别是数字媒体信息,本身就具有浅显吸睛、感性具象等特点。同时,读图时代中个体的“看”这一行为本身,便与思维一致,具有抽象、图例、分析、综合等过程。也就是说,“在纷繁的人类社会中,在特定情境迥异的文化中,看与看什么和看到什么均不是一个自然行为,而是有着复杂内容的社会行为”[8]。因此,视觉文化转向下的学校教育特别是语文科,应承担渗透哲学教育,引导学生深度思考,构建良好文化氛围的重任。
二、语文科渗透哲学教育的可为
(一)渗透哲学教育应以“语言”为核心
卡西尔在《人论》中通过考察人的本性问题,放弃了亚里士多德“人是理性的动物”经典说法,而提出“人就是符号,就是文化”[9]的论断。究其根源在于卡西尔认为理性是符号的一种功能。语言作为一种符号,被认为是世界的“代表”,是人认识世界的工具,同时也是人存在的方式。人们通过运用语言来理解世界和自己的意识,并用其来表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对自己意识的认识。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们的眼光似乎必须透过现象;然而,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式”[10]。因为语言是语文科的核心与载体,所以学生可以通过语言学习活动来提高自己的思维、表达等素养。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书面语在逻辑、形象、内涵等方面比口语有着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训练学生思维等方面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同时,语文科教材的文选型特点,也为语文学习(尤其是书面语)提供了典范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语文课程与教学中以语言为核心渗透哲学教育,需处理好几个问题:第一,敏锐发现,推理解读。引导学生敏锐发现语言现象并从语言现象中总结相关规律,进而服务与作品解读、鉴赏,实现思维、审美等方面的发展。第二,现象还原,勾连融合。融合语言的文化内涵与经验性内涵,把语言这一载体的运用规律与言语作品的思想、情感表达规律进行统一思考。[11]鉴于此,围绕“语言”渗透哲学教育,在语文教学层面,可如下进行:
1.基于语言现象还原矛盾,实现文化内涵与经验性融合。例如《红楼梦》第六回中提到“刚说到这里,只听二门上小厮们回说:‘东府里的小大爷进来了。’凤姐忙止刘姥姥:‘不必说了。’一面便问,‘你荣大爷在哪里呢?’”这段描写中,“一面”一词意义是指一个动作跟另一个动作的同时进行。但生活经验显示,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与两个人进行不同问题的交流,这种“共时”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二者只能是“历时”关系。但对上述描述,读者会通过将文化内涵与生活经验相融合,把语言现象中“一面”的“共时”看做是一种夸张形式,来体现王熙凤的做事干练以及与贾蓉的暧昧关系。又如在“林黛玉进贾府”中,王夫人在黛玉初进荣国府见面寒暄之时,问王熙凤“月钱放过了不曾”。就文章内容来看,似乎为突兀之笔,于当时情境并不合适。但融合了生活经验便可知,询问月钱的本身,是为讨好贾母并向黛玉解释之用,也使得人物刻画入木三分。
2.基于语言现象反思规律,服务思维与审美的发展。以刘成章的《安塞腰鼓》为例,文章语言风格非常鲜明,仅用一千余字便将安塞腰鼓强劲的气势与蓬勃的生命力表现了出来。在语文学习中,引导学生从语言现象中寻找原因,印证阅读中强劲、粗犷感觉的由来。通过印证、反思已知语言规律,明晰文章多用的短句、排比、比喻、叠词等语言现象,都极具民族语言特色,可以有力地表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阳刚之美。又如莫怀戚的《散步》,文章语言形式呈现稳定的结构状态,语言表述上相对较为对称,例如“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等。通过反思这一规律,进而印证这种“稳”“慢”的语言现象与文中所表现的担当、责任、和谐等是相契合的。
3.基于语言现象勾连推敲,明晰思想侧重与情感脉络。以《孔乙己》为例,文中刻画孔乙己时,将其描述为“唯一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也是唯一“只有孔乙己到店,我才可以笑几声的”,是文中唯一与孩子讲说话的大人……“唯一”本义为独一无二,有稀缺之意;但孔乙己的地位确是“使人快活,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对于他唯一的结局又是“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围绕“唯一”勾连推敲,不仅对人物形象、社会现实可以有清晰的认识,同时也能更好的推断出作者的思想情感。又如《背影》中通过对语言现象勾连推敲,可以推导出文章的三层情感脉络:父亲对我的爱,我对父爱的理解,以及父子间隔阂的消逝等。同样,学习《过秦论》时,通过梳理文章各种对比勾连推敲,可以明晰逻辑关系,从而明白作者的主张与文化意蕴。
(二)渗透哲学教育应以“语境”为基础
索绪尔认为每个符号(sign)都是由能指(signifier,即书写对应物)与所指(signified,即概念或意义)所组成,“语言的实际情况使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去进行研究,都找不到简单的东西;随时随地都是这种互相制约的各项要素的复杂平衡”[12]。的确,语言所形成的语境对于理解个体的思想、见解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个体的言语活动是受习性影响的。正如布尔迪厄认为,习性是长时期形成于人体内的行为图式,是受特定环境形态影响而形成的。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身体的形式与风格即姿势与步态、语言交流等。布氏认为,虽然“习性”是产生于特定的场域之中,但它具有强大的迁移能力和生产能力,“它们存在于语言、非词语的交往、趣味以及价值、知觉、推理模式等方面”[13]。因此,关注语言与文化所形成“语境”,渗透哲学教育,影响学生思维倾向、推理模式,是语文科课程与教学的重要责任。下面从语言语境与文化语境方面,简述语文阅读教学如何渗透哲学教育。
1.语言语境视域下渗透哲学教育的阅读教学路径
语言语境通常是指由上下文或前后语构成的有效表达某种意义的话语结构;在渗透哲学教育的阅读教学中,作用主要体现为:首先,通过发现违背常识、不合情理之处,反思怀疑,梳理阅读的困惑。在阅读学习中,学生应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对与已知、常识等相矛盾之处,生疑、质疑。其次,通过概念界说、逻辑推理、合理想象,来辨疑、析疑,来更好地理解文本。学生在阅读文本时,对“文章到底写了什么”“作者写作意图为何”等问题,多局限在渴望了解结论的“概括”之上,而非侧重于关注“文本是如何写的”“作者为何如此表达”等形式的思考探究上。培养语文核心素养要求应从“言语”的个性化实践出发,实现从“如何写”到“写了什么”的把握理解。
以苏轼的《定风波》为例,诗中“矛盾”所形成的悖论张力,是学生学习的重要途径。首先,基于语境,生疑、质疑。引导学生发现阅读中的不合常理之处,如“何妨吟啸且徐行(雨骤风狂,为何却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杖、鞋如何能轻快胜过骑马)”“也无风雨也无晴(有风有雨,却又为何说无)”。其次,基于语境,辨疑、析疑。通过概念界说、逻辑推理,界定矛盾深处的真实意蕴。如对天下大雨,苏轼却“徐行”的疑惑,通过界定“吟啸”“何妨”等词义内涵(吟啸:魏晋人士喜欢撮口为啸,以示洒脱之意。“何妨”二字:对外界事物不在意——不妨以欣赏的心态处之),进而推理想象苏子不仅不在意风雨,还更以“何妨”告诫世人:不如惬意地“吟啸”“徐行”;不但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狼狈而逃,反而缓步前行,足见其潇洒之态。同样,其他矛盾之处也可以一一推理、辨析,从而明确苏子“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不随与超脱。
2.文化语境视域下渗透哲学教育的阅读教学路径
所谓文化语境主要指在人们记忆中贮存的与说话内容有关联的知识信息,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等。在阅读文本过程中,共有的文化语境使读者得以理解作者通过某一话语所表达的意义。例如,《阿Q正传》中在赴刑场路上,“‘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本是我们共同文化背景下的俗语,且有着共同的文化理解。基于这一文化背景,此处的省略则为小说增添了无限张力,是“好汉”“英雄”,还是“虫”“懦夫”……其实基于这一点进行阅读、思考、讨论、探究的过程,本身便有着概念界定、逻辑推理、反思检验等内容,是渗透哲学教育的一种体现。
文化语境下渗透哲学教育需关注几个过程,例如,经历比较、辨析过程,将当前阅读与已有经验相比较,经反思、推理,最终促进语文素养的提高;又如,经历概念、情境辩驳过程,实现阅读学习中的对立与融合。再如,经历合理想象文本留白过程,从而拓宽思维、审美空间。以《咏雪》为例,首先通过比较辨析,推导出谢氏家族繁荣的原因,并对不同时代文化特色有更多的理解。该文开篇“乌衣之会”中,案牍劳形的谢安,召集子侄讨论学习的情形,与宋明理学下家长“重尊严”的行为相比,或与《红楼梦》中“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一幕相较,不难推导出谢氏兴盛百年的原因,以及魏晋时代的“极解放、极自由”时代特色。其次,通过概念确定,情境辩驳,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本意蕴。《咏雪》中有两处“文化情境”值得玩味。其一,家庭室内的“讲论文义”,与室外“寒雪”情境,在“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的询问下由对立走向融合;其二,谢朗“差可拟”的自嘲,和“撒盐”动作情境下所体现的男儿性格,与谢道韫“未若”的自信,及顺应自然的女性性格特征的比较,实现了从反驳走向情感的融合为一。另外,文本留白下的想象与理解,无疑能够拓宽学生的思维与审美空间。如对“拟盐”与“咏絮”评价,按说谢安本应对子侄进行点拨、引导,但他却一语未发。同时,作为封建家长按理应会“重男轻女”,寄希望于谢朗,可谢安却并未表现出一丝的偏袒或不满……由此可以想见,魏晋时期人们在生活、人格上对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尊崇,对个性之美与个性价值的尊重。
(三)渗透哲学教育应以“对话”为路径
哲学教育在语文科教学中的渗透,其本身并非是要教给学生具体实在的陈述或程序性知识,而更多的是聚焦一种探究性、反思性、创造性的活动过程本身。这与后现代范式下,具有开放性、启发性、理解反思为特征的“对话”具有相合之处。换言之,“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有力的保证了语文科渗透哲学教育的实现。学生通过运用语言符号来完成言语活动本身,正是塑造自我、认识自我,实现人与文化合一的过程。正如甘阳所说:“人的本质与文化的本质,只是以这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为中介、为媒介,才得以结合统一为一体”[14]。在语文学习中,“对话”通过交往生成、合作探究、批判性思维、指向自我等四种特质来保障哲学教育的渗透。
1.以交往生成保障渗透哲学教育的实现
“对话”的交往特性是由语言的社会本质与交往属性决定的;同时,语言交往最初便内含着“有效性的要求”,即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的声音,就是在广泛共识中发出一致的声音。而这一共识的可能场所,便是所有存在差异的话语中的普遍共同话语”[15]。在他看来,差异与统一、我性与他性存在结构上的联系。正是由于差异与统一、我性与他性的联系,在语文学习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不仅具有交往性,还具有着生成特性。简言之,语文学习中的“对话”就是通过不同主体的差异与统一的交往,而生成开放性、不确定性的问题、疑惑,并通过互动,实现思辨与探究。可以说,这一“对话”本身就是渗透哲学教育的过程。
例如,在学习《皇帝的新装》一文时,围绕学生“结局为何”的疑惑,老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开放性“对话”。首先,说明该童话结局即是如此,请学生思考如果自己来续写结局,会如何处置大臣与骗子;其次,引导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文本进行对话;通过回归文本,找出关于大臣、骗子等形象的相关信息,思考探究他们是否是“坏人”,从而摆脱以“圆形人物”与“扁形人物”的认知判断来分析童话中人物形象的误区;最终,学生在理性思考与感性理解中,摆脱简单粗暴的“要杀头以示正义”的惩罚性结局想象,而描绘各种不同却美好的结局。
2.以合作探究保障渗透哲学教育的实现
“对话”决定了在语文学习中,不是意味着仅传递已有的知识与信息,而是学生共同合作进行主题探究式或问题解决式学习。正如张荣伟所认为“构建探究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倡导‘和而不同’的交往理念——在尊重彼此观点的前提下,既可以质疑对方,反驳对方,也能够虚心地接受质疑和批评。探究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在于让判断更为准确,让理解更为深入,真正对学习的同伴负责,帮助同伴找准方向,携手并进”[16]。因此合作探究的对话式语文学习,有益于学生在共同探究、质疑思辨中成长。
例如,在学习《老王》时,针对助读系统插图进行问题解决式合作探究。通过合作探究“插图中哪些地方有益于理解文本”“插图与文本中老王形象又有哪些不符之处”“用语言描绘你认为最合适的插图并说明理由”等环节,学生在彼此对话、与教材编辑对话、与作者对话、与文本对话中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与理解。再如,围绕《归去来兮辞》一文,可以进行主题式合作探究。针对该文创作时间(陶氏归去前还是归去后)进行合作探究。学生或以“题目”中“来”字为趋向助词,意为“归去起来啊”为依据,或以序中所言“乙巳岁十一月”所写和“农人告余以春及”等春景之不符为依据,来判定该文创作于陶氏归去前。也有学生或从序言找根据,或从萧统《陶渊明传》找根据,判定创作该文为归去后。虽然最终争论不一,但合作探究过程本身,既培养了学生语文素养,也同时渗透了哲学教育。
3.以批判性思维保障渗透哲学教育的实现
所谓批判性思维,是对思维展开的思维,是使前一种思考过程接受理性评估,从而考量我们自己(或他人)的思维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符合好的标准。批判性思维对当下语文科弥补理性培养缺失,避免因过分尊重和崇拜语文知识,而颠覆其背后理性价值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弗莱雷认为:“除非对话双方进行批判性思维,否则真正的对话也无从谈起”[18]。因此,通过对话进行批判性思维,能够保证语文科渗透哲学教育的真正实现。
以《我的叔叔于勒》为例,学生对菲利普夫妇冷漠刻薄形象的把握是较容易实现的。除此之外,还应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除了批判菲利普夫妇对亲情的冷漠之外,是否也有可“悲悯”之处。首先,学生与作者对话。在该小说结尾(课文删减掉)写到若瑟夫“我”,在长大后会自觉的施舍贫苦人;这一行为本身,可以理解为对父母行为理解与无奈后的“赎罪”。其次,细读文本,与文本对话。通过探究,学生会发现菲利普夫妇的家庭现状与于勒早期行状;并进而思考——作为成人,如此拮据的家庭状况,菲利普夫妇对于金钱、家庭利益的衡量的合理之处。同时,当时社会大环境下人们相似的生活习俗和思维习惯(文中提到对于勒的放逐,是当时社会共识性的作法),也影响到菲利普夫妇的态度。通过批判性思维,学生在批判菲利普夫妇冷漠之外,也进一步对其人性的扭曲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对冷漠亲情的无奈有了更广大的悲悯与反思。
4.以指向自我保障渗透哲学教育的实现
马斯洛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自我实现说,这对教育教学有着重要的启示。语文学习中的“对话”本身,是指向自我的过程,不仅在于反省自己的推理过程,更是对自己的认识理解进行审慎的自我评估,并对自己的动机、价值观、态度兴趣等进行检查和确认,从而最终实现自我认同、自我发展、自我实现。指向自我的语文学习本身就是在渗透哲学教育。
例如,在学习《劝学》时,让学生从文中选取最有启示的一句话送给自己,并说明理由的教学环节,不仅可以理解《劝学》之意,更能反思自己求学成长之路,实现反省与自勉。又如,在学习《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时,通过明晰蔡元培对“好大学”“好学生”的定位,进而迁移到反思当下的学校与自身,并提出合理改进建议。再如,学习《愚公移山》时,学生讨论“挖山不如搬走”“整日挖山,无人嫁予,谈何子孙无穷”,可以结合文章本身的文化内涵与邻居“遗男,始龀,跳往助之”等细节,在师生对话中引导学生思考愚公挖山的大勇、能看到此消彼长的大智、挖山不为自己而为乡邻后代造福的大仁大爱,从而回到自身与自己对话,反思自己的思考出发点及为人处世的原则等。
总之,语文科渗透哲学教育是应为且可为的。在语文课程与教学中,应重视哲学教学,通过以语言为核心、语境为基础、对话为路径,来切实发展学生的思辨能力,提升其思维品质,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