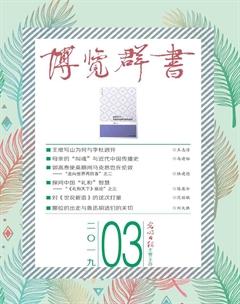母亲的“叫魂”与近代中国传播史
马建标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他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里的“当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概念”。因为,活着的人们要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困惑,把握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只能通过“历史”来实现“过去”与“现在”无休止的对话。在此过程中,实现人们心理的“自我认识”。同样,笔者在创作《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一书时,也是先有现实世界的刺激,才有拙稿的问世。
近年来,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原来高度组织化的大众传播机构在手机“自媒体时代”的垄断优势遭受严重挑战,甚至造成当代中国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催生出一个“人人都能生产信息”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结果造成无数“报纸媒体”的终结,导致媒体人社会身份、社会权力、社会资源等方面的转变。一句话,在这个“自媒体时代”,传统的传播理论已经无法解释新的社会传播现象。这就让人不由得思考,照这样下去,未来的社会将会怎么样,人们的生活命运将因此受到何种影响。这些问题也让笔者自然地对近代中国传播史有了浓厚的兴趣。
此外,笔者决心书写近代中国的传播史, 还与我童年时期在皖北利辛县的乡下所亲身经历的“叫魂故事”有关。或许是命运之神的安排,笔者的这个童年记忆竟然与我日后从事的史学研究工作发生了某种联系。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当时笔者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记得有一天,母亲带着我去村里的一位年长的老婆婆家中。老婆婆住在一个房门向西的土坯房里。她端坐在大桌子旁边,桌上点燃几根蜡烛。母亲和我跪在老婆婆的面前。只听见老婆婆口中念念有词,整个过程不超过十分钟,就结束了。当时的我,是懵懵懂懂,只是觉得很好玩。事后,我才知道,母亲是在请村里这位“通灵”的老婆婆为我叫魂!然而,我当时清楚地记得,我和寻常并没有什么一样的感觉,我的灵魂好好的。我更不知道,我曾经被什么东西给惊吓了。可是,母亲却认为我受到某种惊吓,为了保佑我的平安,才有这个叫魂之举。不管怎样,这件事却成为我人生记忆的开始。
1998年金秋时节,笔者离开哺育我的故乡皖北利辛县,来到坐落在省城合肥的安徽大学历史系读书。某一天,由于大学老师胡秋银的推荐,我阅读了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的名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在书中讲述了发生在乾隆皇帝时期的一个叫魂故事。其大意是说:1768年,浙江湖州下辖的德清县县城东面的水门与城桥坍塌了,亟待重修。1月22日,由阮知县从附近的仁和县雇佣的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带领他的班子开始修墙工作,他们首先要打木桩入河。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截止到3月6日,木桩终于打入河底,吴石匠带领一班人等开始安装新的水门。到了3月26日,吴石匠发现工地的米粮不够,于是赶回30里外自己的家乡——运河岸边的一个商业重镇塘栖去采购米粮。当他回到家中时,有人告诉他,一个名叫沈士良的农夫,找他帮忙,为的是一件蹊跷吓人的事情。农民沈士良时年43岁,与他的两个侄子居住在同一个院落。这两个侄子为人刻薄暴戾,不仅折磨他,还拐骗他的钱财,殴打其母。沈某无处可以伸冤,只好求助于神秘的阴间力量。2月间,他听过路人说德清县修建水门工程的消息。据他们说,石匠们只要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上,贴在木桩顶部,大锤击打木装时,就会给人增加某种精神的力量,这种法术称之为“叫魂”。名字被大锤击打的活人,就会因此被窃取精气,非病即亡。沈农夫闻讯之后,燃起了生存的希望,在纸片上写下他渴望的侄儿的名字。他找到了吴石匠,取出纸片交给石匠,还问:这東西有用吗?你有这个法力吗?吴石匠什么也不会。他害怕自己因此被牵扯进叫魂的罪恶勾当,于是他喊来当地的地保,将沈某扭送进德清县监狱。阮知县审讯一番之后,发现是谣言,将沈某打了25大板,就释放了。但是,这件事很快在浙江地区引发了有关叫魂妖术的恐慌,并进而波及到整个清帝国。
当我读到乾隆皇帝的这个叫魂案时,就立即联想到我在幼年时期的叫魂经历。从1768年到1980年,虽然时隔200多年,其间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笔者童年时期所生活的皖北乡村与乾隆皇帝时期浙江湖州在精神信仰上,并无多大区别,两个不同时空的人们仍然在相信“叫魂”神秘力量的存在。这是何故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皖北村民依然在继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启迪。虽然陈独秀、胡适等人在20世纪10年代后期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但是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范围其实仍局限在城里,中国广大的乡村仍然沉浸在19世纪的传统信仰里。在接受现代文明的程度上,近代中国城市与乡村存在一个明显的二元对立。造成这种文明对立的因素固然很复杂,但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现代媒介的传播问题。类似笔者童年所生活的皖北乡村,现代媒介的传播对他们的影响依然有限。
孔飞力教授的《叫魂》一书,旨在揭示大清帝国的“传播体系”“官僚机制”和“皇帝权力”之间的博弈问题。他认为,大清帝国的官僚机制试图通过操纵传播体系来控制乾隆皇帝,而乾隆皇帝则试图摆脱这种控制。简言之,他探讨的其实就是乾隆时期的权力与媒介的互动关系问题。笔者所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近代以来的权力与媒介的互动关系,同时还关注近代中国的缔造者们如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如何利用媒介传播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进而改造中国的文化,把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天下之国”改造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个问题向来为历史学者所关注,但从“传播”的角度来考察近代中国何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也许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认识。就近代中国而言,诸如以《申报》为代表的大众纸媒在满足时人的日常阅读需要,建构乡土社会的个人、群体及其与广大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方面,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虽然《申报》在1949年5月27日停刊了,但是这份创刊于1872年的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现代日报仍然作为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吸引着无数历史学者去利用它,其历史生命力依然在延续着。笔者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研期间,花费时间最多的就是阅读《申报》上的海量信息。当时,我在阅读《申报》有关“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的报道时,就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申报》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报道是如何进入中国各地读书人的精神世界,又如何在地方读书人与国都北京、大都会上海、欧洲巴黎之间建立“信息纽带”,最后把人们的爱国情绪都点燃起来。也就是达到研究系干将林长民1919年5月2日在《晨报》上的呼吁目标:“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在这里,报纸就是传播民族主义的“魔法棒”,像梁启超、林长民这样的民族精英通过报纸传播民族国家观念,拉近了精英与大众的精神距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依稀可见“现代中国”何以诞生的历史轨迹。
2016年春夏之交,笔者开始构思本书的写作计划,希望通过从传播的角度来论述媒介传播如何促进现代中国的形成。这是一个媒介使传统的“天下中国”何以成为一个“世界中国”的问题。恰巧,哈佛大学东亚系栗山茂久教授正在复旦大学访问。在与栗山教授的一次访谈中,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未来何种学科会成为“显学”?栗山教授稍作思索之后,说:“我认为,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学科当属传播学。现在是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改变了以往的传播方式,正在改变这个世界。以往的传播观念无法解释现在自媒体时代的传播问题。随着自媒体的出现,传统的权势结构正在被‘分解。”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栗山教授的这番话进一步坚定了笔者的这个写作计划。
19世纪以降,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从欧洲向全球的扩展,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也开始“日新月异”。1805年,英国《泰晤士报》首次出版“号外”,报道奥地利军队向拿破仑投降的消息。作为称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的老牌日报,英国《泰晤士报》持续不断的国际时事报道使得“世界政治”到19世纪末成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在此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历史逐渐纳入了“英帝国”的全球扩张史的进程中。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创办报刊,拉开了中国近代新闻传播的序幕。1870年,英国参股的“大北电报公司”进驻上海,把晚清帝国的通信纳入英国主导的全球电信网络。
随着报刊、电报、铁路等现代媒介技术的引入,近代中国的历史在悄悄地发生变革。如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言,这些新事物“总有一天会伸向中国社会的内部,一旦到达那里,他们就会获得新生命,并且像酵母那样再向外发酵,从而改变广大群众的性格,产生出前途雄伟的中华”。诚如斯言,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革,除了既往为大家所熟悉的内忧外患、政治变革等显著的“历史事件”外,在这些“巨变”的历史深处,还有引发人们日常生活和思想方式变革的媒介。申言之,这些媒介不仅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时人的日常生活,并且作为“信息的载体”不断地生成“历史材料”,甚至“编织着”近代中国的历史。
当今世界拥有的各种远程传播技术,除了电视与电脑之外,全部诞生于19世纪。无论是“帝国主义”扩张,还是民族主义传播,双方都依赖19世纪后半期建立起来的全球信息网络。在过去200年里,传播如何在塑造现代世界,传播如何在“编织”近代中国的历史。传播的“大众属性”注定要对既有的“社会建制”与“权势结构”进行分解。比如,“报纸”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就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是近代中国传播史上影响最大的“现代媒介”。有学者指出,19世纪后半期报纸在中国传播数十年之后,由于甲午战争的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利用报纸传播救国思想,使报纸具有“思想纸”和“政治纸”的救亡启蒙的功用,这一时期报纸的“政治化”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
追根溯源,近代中国报纸的产生都与外国人有关。著名报学史学者戈公振说,“我国现代报纸的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在这些“外人”中,1807年来华传教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对中国现代报纸的诞生具有奠基性的历史作用。故而,本书的起点是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传教说起。虽然马礼逊来华的使命是传播基督新教,但是当他和同事米怜(William Milne)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思想状况和文明习惯之后,就发现“中国人民的智力深受政治的束缚,沉吟憔悴而无以自拔”,要让中国人顺利地接受基督教信仰,当务之急的工作就是通过办报来开启民智。在200年前,马礼逊和米怜等人就在中国发现了“传播”“政治”与“民智”之间的密切关系,真的令人叫绝!在马礼逊之后,来华的欧美新教传教士都在致力于一个持续不断的工作,就是通过“现代媒介”来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进而达到改变中国的目的。
近代中国历史的两大主题是“救亡”与“启蒙”,围绕这两大时代主题而展开的近代中國人的传播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是高度政治化的。近代中国历史的“政治化”,不仅仅是中国“特色”,其实也是19世纪世界历史的“民族主义化”,而这个全球归于一的“普遍政治”很大程度上也是跨国传播的作用。1882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赫伯特·B·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在他主持的研究班上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History is past Politics ,Politics present History)。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在近代中国,“传播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传播”。简言之,近代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主题必须是,也应当是“政治”。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官绅提出的“救国”“强兵”“改革”“变法”等时代口号,无一例外地都是政治性的,而当时主流媒体的传播内容也都是围绕上述主题而展开的。至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提出的武力排满革命学说,更是一种极端的政治表现。
既然近代中国的传播活动是与政治紧密缠绕在一起的,那么与此相关的“媒介人物”在面临“权力”与“媒介”的互动关系时,他们的个体命运将遭到何种影响,他们如何摆脱“现实政治”的束缚去实现其个体的自由意志,显然也是近代传播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印刷机、电报、电话等现代媒介技术诞生之前,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只能限制在“人力所及的范围”。但是,现代媒介作为“人的延伸”,可以打破自然时空的束缚,使人类的传播能力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远弗届。然而,现代媒介技术纵然再强大,我们对“人类自身”的作用仍然不能低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仍然认为,“人”比“媒介”更重要,故而近代中国传播史的主题内容仍然是“人”,而“媒介”只能作为“人的延伸”来考虑。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人”不是寻常之辈,都是与近代中国的传播活动有直接关联的历史人物,如马礼逊、洪秀全、盛宣怀、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张元济、吴佩孚等等。笔者通过讲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传播故事,来揭示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如何游走于“权力”与“媒介”之间,其个体命运又如何因此而发生改变。近代中国之所以能够从一盘散沙的“无主之国”变成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现代中国,当然离不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驱者的提倡与实践,离不开那些传播民族国家革命观念的大众媒介的持续努力。如果没有近代中国媒介对“民族主义观念”的传播,中国的“民族精神”将无所立足。近代中国也无法摆脱一盘散沙的悲惨局面,实现“国之为国”。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新媒介技术的运用而造就了古代埃及、巴比伦王国以及中华帝国等帝国。如今,在自媒体日益活跃的今天,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式也正因为移动媒介而发生静悄悄的变革。然而,需要记住的是,媒介改变的绝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规范人们生活的观念和权力也将发生变革。正如法国学者勒庞所言:
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看上去,似乎是由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的倾覆决定的。但是对这些事件做些更为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在它们的表面原因背后,可以普遍看到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民众日常观念的变化,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而真正能够促使这种日常观念变化的“历史伟力”就蕴藏于大众媒介之中。此说不仅适用于近代中国的传播史,也可以昭示我们的未来。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一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