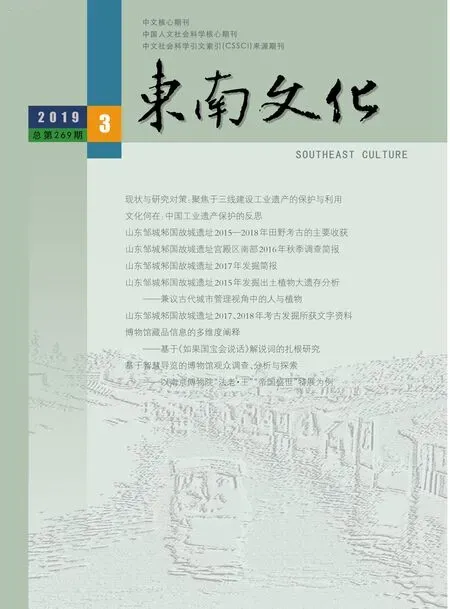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2017、2018年考古发掘所获文字资料
郎剑锋 陈章龙 王 青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内容提要:2017、2018年,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连续开展两次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丰富的东周、汉代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较为丰富的文字资料,主要包括金文、陶文两类。金文资料包括衡、权、版等新莽铜器以及印章、铜镜、钱币等,陶文资料包括豆、盆、盂、罐等陶器。时代方面,金文资料均为汉代,陶文资料均为战国时期。邾国故城遗址新出土的文字资料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区东南10公里的峄山镇纪西、纪东、纪前三村周围。该遗址早年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或复查工作;2015年,该遗址进行了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1]。2017、2018年又连续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较为丰富的文字资料。
一、邾国故城遗址文字资料既往发现及研究简史
邾国故城遗址早在晚清民国时期即以出土陶文而为金石学家所重,后又不断有东周秦汉文字出土而备受学界瞩目。因此,在对2017、2018年考古发掘出土文字资料进行介绍之前,笔者首先对此前的重要发现和主要研究进行简单的回顾与梳理。
目前收藏邾国故城遗址出土陶文的博物馆主要有邹城博物馆、山东博物馆、青岛市博物馆(陈介祺旧藏)以及济宁市博物馆等。
最早关于邹城邾国故城出土陶文的记载见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由马星翼编纂的《邹县金石志》,“这在战国时代各国陶文的发现史上是最早的”[2]。
从光绪二年(1876年)开始,山东潍县金石学大家陈介祺先生开始批量收购陶文,至光绪五年(1879年),累计收购陶文四千余件,辑为《簠斋藏陶》。其中包括不少邾国故城出土陶文[3]。
在陈介祺先生的影响下,收藏、著录陶文者渐多,其中不乏邾国故城遗址出土陶文。20世纪30年代,王献唐主持山东省立图书馆期间,购藏了一部分陈介祺旧藏陶文和拓本,并在此基础上,陆续入藏陶文两万余件,其中不乏邹地出土者,并辑为《齐鲁陶文》两种[4]。除了东周陶文,还入藏了部分邹地出土的秦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诏量[5]。其中,王献唐专注邹滕陶文,著《邹滕古陶文字》三册,第一、二册著录邾国陶文,钤“三邾古匋”印。作者还在序言中对邾国陶文特点和内容等进行了概括,与田齐陶文相比,“邹似稍逊,字亦简朴,多一字至二字,其三四字者不习觏也。器以豆、瓿为夥,鼎、鬲、爵、罍彝器所有无不备”[6]。
20世纪40年代,邾国故城遗址出土数件陶量,除少数为博物馆收藏外,其余均已破碎,无法复原[7]。根据其后出土的同类器物推测,其中当不乏带有文字者。
1951年,邾国故城(时称“纪王城”)出土一件战国陶量,内底有一陶文。时代定为春秋[8]。
1964年4—5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对邾国故城遗址(时称“纪王城”)进行了调查,并初步绘制和发表了城址的平面图。该次调查共发现东周陶文30例,文字多位于陶盆口沿或陶豆柄部,陶文除“买”“可”为阳文外,其他文字均为阴文,除1例为刻划而成外,其余皆为印文;汉代文字共发现5例,陶罐肩部1例、瓮1例、器座3例,除罐肩文字为阳文外,其余均为刻划阴文[9]。
1972年夏,遗址附近在大雨过后冲出一件青铜鼎,鼎腹内壁有铭文三行十七字,曰:“弗敏父作孟姒□媵鼎,其眉寿万年永宝用。”报导者认为,铭文中“弗”当读为“费”,姒姓,“此鼎是费国的敏父为其大女儿陪嫁而作”,“费、邾为邻国,两国统治者之间互相通婚的可能性很大,这件铜鼎可能是费嫁女儿与邾的媵器”[10]。
20世纪70年代中期,邾国故城宫殿区以南出土了两件战国陶量。两件陶量形制、大小相同,内底有一陶文。报导者根据陶量的制法、形制、纹饰等,判断其时代约为春秋晚期,认为邾与鲁为邻,又为鲁之附庸,因此这两件器物应为鲁器。作者在文中发表了其中一件陶量的照片和陶文的拓片,但并未对陶文进行解释[11]。随后,有学者认为陶文残沥,根据拓片补足残划后将其释为“鼄”,认为春秋时有二邾,“一为鲁之附庸”,“一为楚之与国”,“此器出于邹县邾国故城,当是山东境内邾国之官量”[12]。但后有学者指出,陶量内底的陶文清晰完整,并将其与山东博物馆所藏、同出邾国故城的两件“同铭陶量”进行了比较,认为陶文应释为“廪”,认为“此量时代属战国”,“邾国在春秋晚期鲁哀公时已称邹,战国时也称邹。陶量应是邹国官廪所用量器”[13]。
1980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联合邹县文物保管所对邹县古代遗址进行了重点复查,“历年来还出土了一些铜兵器、容器、车马器和大批时代确切的东周陶器,如鬲、盆、钵、罐、瓮、豆等”。陶豆等部分陶器带有文字[14]。
1990年,高明《古陶文汇编》出版,全书收集陶文拓片2622张,“举凡前此成书的陶文拓片(不论已刊或未刊)和建国后新出陶文,绝大部分均已汇集于此”,全书分省著录,“地区之内另有具体出土地点”。其中,山东地区著录邹县陶文405例,大部分当出土于邾国故城[15]。
1998年,《新编全本季木藏陶》出版,第三部著录“邾国、滕国”陶文。李零撰《齐、燕、邾、滕陶文的分类与题铭格式》一文,对齐、燕、邾、滕战国时期陶文特点进行了概括,主张邾、滕“二者地点相近,所出陶文不易再做区分”[16]。
2006年,王恩田主编的《陶文图录》出版,该书“把所得陶文资料剔除重复与破残,选用一万二千余件”,“按照断代与分国相结合的体例编排”。全书分十卷,第三卷即为邹。王恩田先生在该书“自序”中明确指出,既往所谓鲁、滕陶文其实皆为邾国陶文,并对邾国陶文特点进行了讨论,比如民营作坊产品上以单字为主,官营制陶的陶文数量较少,由两个单字印组成的两字陶文比较特殊,产品种类以豆、盆为主[17]。
2010年,郝导华发表《山东地区东周陶文的发现与研究》一文,对邾国故城东周陶文的发现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指出“邾地陶文直到汉代仍很发达,这与齐国故城是不一样的。或许说明此地与齐文化有很大的差异”[18]。
2011年,《孟府孟庙文物珍藏》一书出版,该书新刊布了几例邾国故城出土的文字资料,包括“战国刻铭陶墓砖”“西汉石质半两钱范”,并对孟府所藏邾国故城东周、秦代、汉代的陶文进行了简要的概述[19]。
2015年3—7月,山东大学邾国故城遗址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区位于皇台下西南部,布设5×5米探方36个,实际发掘面积930平方米,发现灰坑、房址、水井、墓葬、窑炉等遗迹700余个。发掘区内春秋时期的遗迹破坏严重,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出土了大量日用陶器、建筑材料和陶量。其中,陶豆、盆、罐、量等器上发现不少陶文。陶文以单字为主,但也不乏“薛其子之度同也”等多字陶文[20]。
在后续的资料整理中,又于1件陶量和3件陶罍上发现了多例戳印的“邾”字陶文。通过对器物形制的比较,研究者认为,这批带字陶器的时代均为战国早期。根据陶罍容量与陶量的倍比关系,作者进一步指出,这些带有“邾”字的陶量和陶罍是“官方发行的量器及配套使用的盛储器”,这对进一步探讨东周时期邾国量制、重新认识鲁南地区东周时期同类陶器的功能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21]。
二、2017、2018年考古发掘概况
2017年3—7月,山东大学邾国故城遗址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田野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500平方米,共发现分属春秋、战国、汉代、唐代等不同时期文化遗迹300余个,包括灰坑(沟)、水井、墓葬、房址、灶及建筑相关遗存等。文化遗物的种类十分丰富,包括大量陶器、少量铜器、铁器、瓷器等[22]。其中,编号为2017ZZF3T7512J3(以下简称“2017J3”)的水井,出土大量完整或可复原的器物,包括8件带有铭文的新莽铜度量衡器,先期进行过报道并组织了专家笔谈[23]。
2018年的发掘工作分为三个地点,分别位于西城墙北部、北城墙中段及墓葬区西南部的西岗墓地。西城墙的发掘区位于纪王村北,布设一条长150、宽4米的东西向探沟,共发掘灰坑、水井、墓葬、灰沟、灶等遗迹,分属春秋、战国汉代、汉代以后三个阶段。其中,编号为2018ZZF1T4552J2(以下简称“2018J2”)的水井出土了较多完整或可复原的陶罐,不少陶罐的肩部或上腹部发现陶文。北城墙的发掘区位于峄山街村村东,布设一条长110、宽5米的南北向探沟。城墙年代集中于汉代。城墙北侧发现同时期的壕沟。所获遗物以陶片、砖瓦等建筑构件为主。西岗墓地系抢救性考古发掘,目前清理一座带有东向墓道的“甲”字形大墓(M1)[24]。
三、2017、2018年考古发掘所获文字资料
2017—2018年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字资料包括金文、陶文两类,前者包括衡、权、版、印章、铜镜、钱币等,后者包括豆、盆、盂、罐等陶器。时代方面,金文资料均为汉代,陶文资料均为战国时期。
(一)汉代金文
金文资料主要集中于2017年J3出土的王莽时期的青铜度量衡之上,包括残衡1、权4、版3。其中,衡2017J3①︰39残存部分新莽诏书(图一︰1、2)。权铭多为重量及制作时间等方面的内容,如权2017J3①︰46铭文“律三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图一︰4);权2017J3①︰47铭文“律九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图一︰3);权2017J3①︰48铭文“律权钧,重卅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图一︰5);权2017J3①︰49一侧铭文“律权石,重四钧”(图二︰1),与之相对位置为新莽诏书铭文,共计20行、81字,内容为:“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亨传亿年。”铜权直径27.5、孔径7.9、高9厘 米。版 2017J3①︰40、2017J3①︰41铭文内容(图二︰2、3)与2017权J3①︰49诏书相同,唯行款有异。另一件铜版J3①︰45正面中心及四边正中共有铭文7字,中间为“黄金”、上面为“布”、下面为“铜泉”、左边为“帛”,右边为“絮”(图三︰1),内容与《汉书·食货志》所载“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相关。
除新莽度量衡之外,金文资料亦少量见于印章、铜镜、钱币等器物之上。
印章,1枚。2017H13︰1,保存完整。长方形,桥形钮。印文“驺司空”三字。印章长2.75、宽1.45、高0.91厘米,钮顶部宽0.91、高0.92厘米(图三︰2;图四︰1)。
铜镜,1面。2017J3①︰8,残破,后经修复。镜背饰两周斜线纹饰带,以凸弦纹为界,纹饰带之间为铭文“见日之光”四字,字间各以相同的三个符号相隔。铜镜直径6.7厘米(图三︰3)。
钱币数量不多,以圆形方孔圜钱为主,其他仅发现1枚布币。圜钱币文包括“半两”“五铢”“货泉”等,布币币文为“货泉”。2017J3②︰5,正面有“半两”二字,反面无文。直径2.3、方孔边长0.9厘米(图四︰2)。2017G10⑩︰17,正面有“五铢”二字,反面无文。直径2.5、方孔边长1厘米(图四︰3)。2017G10[12]︰1,正面有“货泉”二字,反面无文。直径2.4、方孔边长1厘米(图四︰4)。2017G10②︰25,布首及双首均较方折,周设边廓,布身中部正反面均有一条弦纹。正面铭文二字,曰“货布”,反面无文字。布币足宽2.26、肩宽2.14、布首宽1.79、通高5.76厘米,穿孔直径0.6厘米(图四︰5)。
(二)战国陶文
2017、2018年发现的陶文以单字为大宗,只发现少量的二字陶文。带有陶文的器物种类包括豆、盆、盂、罐等。
1、豆,残甚,多仅存柄部。陶文多位于柄部。
2017YL1︰4,夹砂灰陶,敞口,圆唇,浅弧盘,矮柄,素面,豆柄有一陶文“正”。口径12、通长10.1厘米(图五︰1;图六︰1)。
2017YL1︰6,夹砂灰陶,素面,豆柄有两个陶文,均为“祭”字。残高7.5厘米(图五︰2;图六︰2)。
2017T7412⑦︰4,夹砂灰陶,素面,残高5厘米。豆柄上有一陶文“得”(图五︰3;图六︰3)。
2017T7412⑦︰5,泥质灰陶,素面,残高4.4厘米。豆柄上有一处陶文(图五︰4;图六︰4)。
2017T7412⑦︰16,泥质灰陶,素面,残高7.1厘米。豆柄上有一陶文“”(图五︰5;图六︰5)。
2017T7412⑦︰27,泥质黑陶,素面,残高6.2厘米。豆柄上有一陶文“兴”(图五︰6;图六︰6)。
2017H148︰2,夹砂灰陶,素面,残高7.3厘米。柄部有一陶文“祭”(图六︰7)。
2017H149︰2,夹砂灰陶,素面,残高6.8厘米。柄部有一陶文“朿”(图五︰7;图六︰8)。
2017H303①︰4,泥质灰陶,素面,残高6.25厘米。豆柄下部有一陶文“怿”(图五︰8;图六︰9)。
2017H94④︰24,泥质灰陶,素面,残高6.8厘米。柄部有两个陶文“祭“””(图五︰9;图六︰10)。
2017H94④︰40,泥质黑陶,素面,残高6.6厘米。柄部有一陶文“”(图五︰10;图六︰11)。
2017M4填︰32[25],豆,泥质灰陶,残高5厘米。内部有一陶文“”(图六︰12)。
2、盆,数量也较多,多仅存口沿。陶文多位于口沿沿面。
2017G7︰5,泥质灰陶,侈口,折沿,圆唇,腹饰绳纹,口径44、残高11.5厘米。口沿上有一陶文“赓”(图八︰1)。
2017G10⑩︰5,泥质灰陶,敛口,平直沿,方唇,腹部饰细绳纹,残高11.5厘米。口沿偏左有一陶文“公”(图七︰1;图八︰2)。
2017J2②︰17,泥质灰陶,卷沿,方唇,敞口,上腹较直。颈部饰两道弦纹,腹饰绳纹,残高9.2厘米。沿面有一陶文“启”(图七︰2;图八︰3)。
2017J2②︰18,夹砂灰陶,卷沿,敞口,方唇,腹饰绳纹。残高6.3厘米。沿面有一陶文“㭪”(图八︰4)。
2017G6︰3,夹砂灰陶,敞口,平折沿,方唇内凹,素面,颈部饰一凸棱纹。口径约40、残高4厘米。沿面有一陶文“”(图七︰3;图八︰5)。
2017H94②︰4,泥质灰陶,平沿斜方唇。颈饰凸棱,腹部施绳纹。直径43、残高8.4厘米。沿面有一陶文“参”(图八︰6)。
2017H94④︰22,泥质灰陶,敞口,折沿,方唇,腹部施绳纹。残最大长16.1、最大宽11.2、厚0.7~1.8厘米。沿面有一陶文(图七︰4;图八︰7)。
2017H94④︰46,盆,泥质灰陶,敞口方唇平折沿,腹部饰绳纹。残高10厘米。沿面有一陶文“”(图八︰8)。
3、盂,数量较少,陶文位于唇面。
2017T7412⑦︰3,夹砂灰陶,敛口,折沿,夹砂灰陶,绳纹。口径54、残高6厘米。唇面有一陶文“”(图七︰5;图八︰9)。
2017H94①︰10,夹砂灰陶,敛口尖唇,外饰绳纹。残高5.6厘米。唇面有一陶文“”。《字汇补·贝部》记载“‘'与‘货'同”(图七︰6;图八︰10)。
4、罐,整体数量不多,但2018J2比较集中出土了一批带有陶文的完整或可复原的陶罐,资料宝贵。
2018J2⑦︰12,泥质灰陶,敞口,尖唇,卷沿,短颈,溜肩,鼓腹,平底内凹。颈部饰五道凸棱纹,肩部及以上饰细绳纹,上腹部饰弦断细绳纹,下腹部饰细绳纹。底部有叠烧痕迹。口径12.2、腹径24.5、底径 4.6、通高24.8厘米。肩部有一陶文“敚”(图九︰1;图一〇︰1)。
2018J2⑦︰17,泥质灰陶,敞口,尖唇,卷沿,短颈,溜肩,鼓腹,平底内凹。颈部饰五道凸棱纹,颈与肩相接处饰细绳纹,肩及上腹部为弦断细绳纹,下腹部饰细绳纹。口径10.8、腹径24、底径5、通高25.7厘米。肩部与上腹部有一陶文(图九︰2;图一〇︰2)。
2018J2⑦︰23,泥质灰陶,敞口,尖唇,卷沿,短颈,溜肩,鼓腹,圜底。颈部饰四道凸棱纹,肩部及以上饰细绳纹,上腹部饰弦断细绳纹,下腹部饰细绳纹。底部有叠烧痕迹。口径14.2、腹径27.4、通高30.2厘米。肩部有一陶文(图九︰3;图一〇︰3)。
2018J2⑦︰25,泥质灰陶,敞口,尖唇,卷沿,短颈,溜肩,鼓腹,平底内凹。颈部饰六道凸棱纹,肩部及以上饰细绳纹,上腹部饰弦断细绳纹,下腹部饰细绳纹。底部有叠烧痕迹。口径12.2、腹径25.8、底径9、通高27.8厘米。上腹部有一陶文“”(图九︰4;图一〇︰4)。
2018J2⑦︰29,泥质灰陶,口沿及颈部残缺,溜肩,鼓腹,平底内凹。颈部与肩部相接处饰细绳纹,肩部及上腹部饰弦断细绳纹,下腹部饰细绳纹。腹径23.5、底径7.7、残高21厘米。肩部有一陶文“艸”(图一〇︰5)。
2018J2⑦︰31,泥质灰陶,溜肩,鼓腹,平底内凹。肩部及以上饰细绳纹,上腹部饰弦断细绳纹,下腹部饰细绳纹。腹径25、底径3、残高15.7厘米。上腹部有一陶文“辟”(图一〇︰6)。
2018J2⑦︰32,口沿残损。泥质灰陶,溜肩,鼓腹,平底内凹。肩部及上腹部饰弦断细绳纹,下腹部饰细绳纹。口径12.3、腹径25.4、底径6.4、残高21.6厘米。肩部有一陶文“付”(图一〇︰7)。
2018J2⑦︰37,泥质灰陶,溜肩,鼓腹,平底内凹。肩部及以上饰细绳纹,上腹部饰弦断细绳纹,下腹部饰细绳纹。腹径22.5、底径5.8、残高20.3厘米。肩部有一陶文“纫”(图一〇︰8)。
2018J2⑦︰38,口沿及颈部残缺。泥质灰陶,溜肩,鼓腹,平底。肩部及上腹部饰弦断细绳纹,下腹部饰交错细绳纹。腹径23.5、底径3.4、残高20厘米。肩部有一陶文“买”(图一〇︰9)。
2018J2⑦︰40,泥质灰陶,溜肩,鼓腹,平底内凹。肩部饰细绳纹,上腹部饰弦断细绳纹,下腹部饰细绳纹。腹径26.2、底径5.2、残高22.5厘米。肩部有一陶文“期”(图一〇︰10)。
2017H20︰4,夹砂灰陶,素面。底径9.5、残高2.5厘米。近底部腹部有一陶文“生”(图九︰5;图一〇︰11)。
2017H149︰1,夹砂灰陶,口颈已残,素面。残高6.9厘米。上腹部有一陶文(图九︰6;图一〇︰12)。
2017H94④︰29,泥质灰陶,敞口方唇。残高6.3厘米。颈部有一陶文“买”(图九︰7;图一〇︰13)。
此外,个别器形难辨的陶片上也有少量陶文发现,如2017T7414⑦︰3、8“寿”“曹”等(图一〇︰14、15)。
四、结语
2017、2018年两年考古发掘工作所获文字资料包括陶文、金文两大类,二者的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多,内容亦较为丰富,时代分属战国、汉代,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字形演变,书体结构与地域特征,中国古代的官制、姓名、工官、度量衡、币制,手工业的生产组织,乡里等社会结构、地理沿革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有利于相关研究的开展,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总体而言,2017、2018年发掘带有文字的陶器为生活器皿,未见2015年出土的量具类陶器,文字的属性有所不同,应该是标识制造者个人名字。此外,还发现了若干此前未见著录的新文字,比如编号为2018J2⑦︰17、2017H149︰1的陶罐上的陶文(图一〇︰2、12)等。
与齐国陶文研究相比,邹地陶文的断代与分期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主要是由于邾地陶文多缺少完整的考古背景。本文介绍的文字资料均为科学考古发掘出土,地层关系明确,伴出器物组合完整。随着考古资料的全面整理与研究,可以为陶文的年代学研究提供更加细致的年代学框架。地层及遗迹单位出土的钱币等文字资料也可反过来作为判断地层或遗迹年代与分期的依据,从而为遗址的分期提供时代依据。
文字资料在对遗址的功能布局及性质的判断过程中往往具有关键意义。比如,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在宫殿区以南发现的“廪”字陶量与2015年发掘区发现的大量窖藏及陶量证明该区确为战国仓储区;2017H13出土的“驺司空”印章与夯土建筑基址同出,表明皇台一带曾是汉代衙署区无疑。随着文字资料的系统整理,有望发现更多类似的例证。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需要指出。经过历年的考古调查和三次较大规模的发掘,邾国故城出土了大量汉代的砖、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其中,瓦当的数量甚多,装饰精美,有些直径甚至超过20厘米,但目前尚未出土文字瓦当。与之相邻的山东曲阜鲁故城在早年及近期的考古工作中也无文字瓦当见诸报导[26]。这与以山东临淄齐故城为代表的鲁北地区出土大量文字瓦当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其背后的原因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27]。
(附记:文章在修改过程中得到山东博物馆卫松涛先生的无私帮助,特此致谢!)
[1]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邹县滕县古城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12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邹县文物保管所:《山东邹县古代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c.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邹城市文物局:《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2015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3期。
[2]王恩田:《陶文图录》“自序”,齐鲁书社2006年。
[3]高明:《古陶文汇编》“凡例”,中华书局1990年。
[4]王献唐:《双行精舍书跋辑存》,青岛出版社2007年,第146—147页。
[5]见1950年王献唐手书《四川运京古物目录底册》,山东博物馆藏。
[6]王献唐:《邹滕古陶文字》,山东省图书馆拓本,1934年,山东博物馆藏。
[7]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28页。
[8]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博物馆:《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51页。
[9]同[1]a。
[10]王言京:《山东邹县春秋邾国故城附近发现一件铜鼎》,《文物》1974年第1期。
[11]朱承山:《邾国故城出土的两件陶量》,《文物》1982年第3期。
[12]平生:《邾国故城陶量文字补正》,《文物》1982年第7期。
[13]受年:《邹国陶量文字辨正》,《文物》1983年第2期。
[14]同[1]b。
[15]同[3]。
[16]周进集藏、周绍良整理、李零分类考释:《新编全本季木藏陶》,中华书局1998年。
[17]同[2]。
[18]郝导华:《山东地区东周陶文的发现与研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19]郑建芳:《孟府孟庙文物珍藏》,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
[20]a.王青、路国权:《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首次大规模主动发掘》,《中国文物报》2015年10月23日第8版;b.同[1]c。
[21]刘艳菲、王青、路国权:《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首次发现“邾”字陶文》,《中国文物报》2018年7月27日第6版。
[22]a.王青、郎剑锋、陈章龙:《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考古再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17年9月8日第8版;b.山东大学邾国故城遗址考古队:《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2017年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9年第3期。
[23]a.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邹城市文物局:《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2017年J3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8期;b.王青、马新、王子今等:《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新莽铜度量衡器的初步研究》,《考古》2018年第8期。
[24]王青、路国权、郎剑锋、陈章龙:《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2015—2018年田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2019年第3期。
[25]此件豆出土于晚期墓葬的填土中。
[2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博物馆、济宁地区文物组、曲阜县文管会:《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近年曲阜鲁故城的发掘信息由山东省考古研究院韩辉先生告知,特此感谢。
[27]a.李发林:《齐故城瓦当》,文物出版社1990年;b.张文彬主编:《新中国出土瓦当集录·齐临淄卷》,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