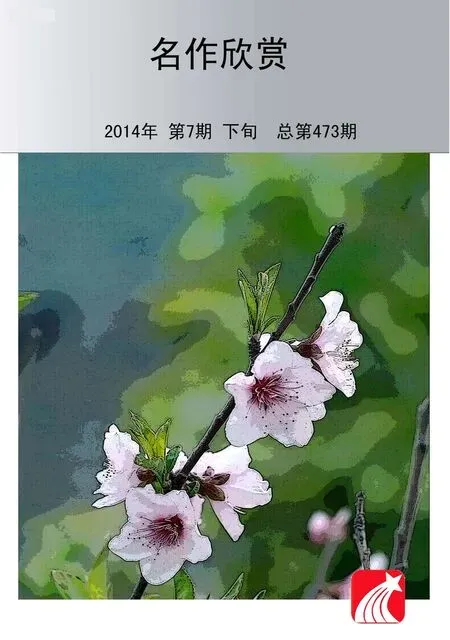“女性主义者”葛特露的三重身份建构
⊙陶文倩[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训学院, 南京 210023]
《哈姆雷特》(以下简称《哈》)作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在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厄普代克的《葛特露与克劳狄斯》(以下简称《葛》)作为后世大量对《哈》进行戏仿的著作中一部带有“前传”性质的作品,其实是在完成一个“填补空白”的工作:王后缘何再嫁?她是如何结识了克劳狄斯并与其通奸?她对前夫有何看法?厄普代克试图通过描写葛特露对命运的反抗及她与克劳狄斯的感情纠葛,来为《哈》中那个“脆弱的女人”进行平反。他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让读者走进葛特露的内心世界,为她饱受压抑的前半生而产生同情,为她摆脱命运的桎梏去追求真正的爱情而动容,更是让读者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上去重新审视莎士比亚叙述的故事。但是,除了表达对女性主义精神的肯定,作品中仍然透露出作者对葛特露这一形象的关切、悲悯和对女性主义能否真正得到彰显的犹疑和观望。
一、话语权的伪持有者
在《哈》与《葛》这两个文本中,叙述视角、人物形象、主题意蕴等都因作者不同的个人观念与写作目的而有不同的体现,就“谁掌握了话语权”这个角度而言,带有浓重男权主义思想的莎翁将话语权交付给戏剧的主角——哈姆雷特,而对葛特露的话语则是到了几乎吝啬的程度,这也导致葛特露在剧中一直处于被叙述、被指认的地位。在哈姆雷特冲动之下误杀大臣普隆涅斯这幕剧中,哈姆雷特对母亲的罪行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指责:“你的行为可以使贞节蒙污,使美德得到了伪善的名称……使婚姻犯那样的错误,无论怎样丧心病狂,总不会连这样悬殊的差异都分辨不出来的……”他甚至辱骂她:“生活在汗臭垢腻的眠床上,让淫邪熏没了心窍,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弄爱……”但即便是面对这样无情的指责,葛特露也没有为自己做出任何辩护,而是软弱地回应道:“你使我的眼睛看进了我自己灵魂的深处,看见我灵魂里那些洗拭不去的黑色的污点……”她秉承着作者的意志,在哈姆雷特的压力下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忠不义、屈从于情欲的女人。
相反,厄普代克的再叙述则是有意地将话语权转交到葛特露手中,让她原本暗无天日的“话语”被“说”出来,葛特露也因此变成了一个有思想的鲜活的个体,反倒是哈姆雷特的形象在整部作品中黯然失色。当老国王罗瑞克说服葛特露下嫁给霍文迪尔并告诫她“抗拒国王的旨意就算叛国罪”时,葛特露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甚至尖刻地指出罗瑞克做这样的决定无非是想要拿她做政治交换。她还被赋予了具有现代性的男女平等思想,认为“无论男女,死亡都一样是同等大事”。但是,厄普代克只是稍做铺垫就继续写道:葛特露与父亲两人都心知肚明,“她最终总是要妥协的——他是国王,万能而不朽,而她只有一时的明媚鲜妍,像是昙花一现,在事关王室利益、需要结盟的历史关头,总是可以被牺牲掉的”。果然,葛特露很快就被驯服了,她“发觉自己仿佛被人从身后猛击了一掌似的,一股孝敬之情涌上了她的心头,她跪倒在他的面前……她跪在他面前的样子是那么的严肃,像是奴隶的神情——被俘获的奴隶在经麻醉之后,被送上祭坛用作献祭之前的那种神情”。
类似的描述还出现在葛特露与霍文迪尔的博弈中。作为老国王相中的王位继承人,霍文迪尔来向葛特露求婚时带给她的礼物是一对关在笼子里的红雀,“笼子”的象征意味本身就已经很强烈,而厄普代克却还让霍文迪尔毫不避讳地指出,葛特露正像是这关在笼中的鸟儿——霍文迪尔对葛特露的掌控,毫无疑问是胜券在握的。虽然葛特露厌恶霍文迪尔的虚伪与残酷,而且早就质疑那些满足于成为被驯服的猎物、甘愿做男性奴隶的女性——“她们头脑麻木,虽然地位卑下却仍然兴高采烈”,但实际上,葛特露自己也无法避免地走向“自我弃绝”的境地,成为这类女性中的一个。就像她在父亲的施压之下很快就选择了妥协一样,她面对着霍文迪尔,“感觉到自己像是被一些有图案的织物紧紧包裹着,怦怦乱跳的心在千头万绪中渐渐平静下来……这桩命中注定的姻缘,属于她”。她心中燃起的女性主义的星星之火很快就熄灭了下来,她再一次将主动权交还给霍文迪尔。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葛》三幕剧中的开头是十分整齐划一的“国王被激怒了”。厄普代克以笔墨之力将男性的愤怒情绪贯穿整部剧作,实际上也就暗示了葛特露这个所谓的话语权持有者的一生都被笼罩在浓重的男权主义阴影之下。三位被激怒的国王分别是罗瑞克、霍文迪尔和克劳狄斯。在第一幕中,罗瑞克愤怒的原因是“他的女儿,声称不愿意嫁给他选中的贵族霍文迪尔,那个朱特人,一个像公牛一般结实的勇士”。在第二幕和第三幕中,两位国王被激怒的原因都是王子哈姆雷特不愿意听从国王的旨意留在宫廷学习为君之道,而是要留在德国威登堡。在后两个情境下,虽然葛特露本人并不是导致国王发怒的直接原因,但她所扮演的角色却始终是那个承担国王怒火的人——她永远不会成为那个被激怒的人,即便她偶尔会反驳,最终也会败下阵来;即便她怀有崇高的女性主义精神,她的反抗性也注定是短暂的,在她骨子里流淌着的血液也不过只能让她恪守一个妇人家的本分罢了。对于这一点,无论是书中的男性人物还是葛特露本人都心知肚明,因为长期以来,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对女性的行为做出了规约,并将一种无形的责任强加在她们的身上。而葛特露自己也早已将这种责任感内化于心,她清楚只有遵从上帝的愿望,才能为自己迎来讲求实际和通情达理的好名声。由此,厄普代克倾尽笔墨刻画的女性主义者葛特露又彻底沦为一个可悲的边缘人物。
读者在阅读《哈》时不免会产生疑问:如果不是莎士比亚刻意先发制人夺走了葛特露的话语权,那么葛特露将会如何为自己做出反驳,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葛特露的反驳》就用葛特露的七个反诘填补了《哈》中哈姆雷特质问母亲时她的“失声”片段,读来大快人心。而厄普代克却别出心裁地先让葛特露“发声”,并透露出他对女性主义精神的肯定,但是随后他又“逼迫”葛特露屈服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主动交出话语权。厄普代克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放在了罗瑞克、霍文迪尔、哈姆雷特,甚至克劳狄斯的同谋者的位置上,让读者看到葛特露“话语权的伪持有者”这一真实身份,这也恰恰反映了厄普代克对男女社会关系的深刻反思。
二、“堕落或回来”之外的第三种娜拉
“娜拉走后怎样”这一命题是鲁迅先生于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一次文艺讲演中提出的,对于这个话题他给出的两种预想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伤逝》中的子君为“回来的娜拉”做了最好的诠释,而丁玲笔下的莎菲则是“堕落的娜拉”。百年来,“娜拉出走”成为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母题,那些形形色色的新女性形象也一同构筑了一道别样的文学景观。葛特露作为厄普代克文本重构下的女性主义者,则向读者展示了娜拉“堕落或回来”之外的第三元困境。
葛特露对自己的命运看得很透彻,“她的生活似乎一直是一条石头铺就的通道,通道的两边有许多窗户,但没有一扇可以通出去的门。霍文迪尔和哈姆雷特就是守卫这条通道的两个霸道的士兵,在通道的尽头等候的,则是无法逃脱的死亡”。与霍文迪尔平淡的婚后生活让她内心深处的欲望被长久地压抑着,冷漠的母子关系更是让她感到心烦意乱,人人都以为三十五岁的她已经老了,但是只有她自己知道,在这种极端压抑的环境下去凝望窗外波涛汹涌的大海,还是会去想象另一种生活会是什么情形。此时,冯贡(克劳狄斯的原名)的出现则适时地填补了她内心的空虚,让她找到逃离那条通道的出路。作为霍文迪尔的弟弟,冯贡就像《哈》中的葛特露一般,长期处于一个被叙述的地位,老国王罗瑞克与霍文迪尔口中的他似乎生来就是为衬托霍文迪尔之伟大而存在的。但是随着情节的推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冯贡却一反他人的成见,温柔风趣、强健勇敢,成为第一个愿意倾听葛特露心声的男性。他和葛特露一起探讨彼此的信仰、善与恶的抽象思想,而“霍文迪尔和哈姆雷特总是在她话说了一半的时候就走开去,交换他们之间属于男人的话题,进行他们私下的算计去了”。用葛特露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冯贡让她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于是,她对克劳狄斯的好感与日俱增,以至于冲塌了心的堤坝,奔流千里。
但即便是如此善解人意的冯贡,仍不免和罗瑞克、霍文迪尔有着共通之处。他对葛特露有着极为深刻的洞察,清楚她致命的弱点就是顺乎自然、屈从让步,“假如处于自己的压力之下,她也会屈从的”,所以“她应该属于他,因为只有他才能真正懂她”。事实上,冯贡的这种男权主义心理早在他带葛特露去参观鸟厩时就已显露端倪,只不过他表现得并不像霍文迪尔那样咄咄逼人罢了。在冯贡的鸟厩中有为数不多的几只猎鹰,它们原本都是自由自在的鸟儿,但驯鸟人按照冯贡的旨意用专门的训练术将它们驯化为供人消遣的玩具,一只猎鹰的眼睑甚至也被缝合了起来。对于如此残忍的做法,冯贡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它,让它彻底打消自己还有自由的希望。冯贡冠冕堂皇的话并没有影响葛特露理性的判断,她知道“这就和男人用他们势如破竹、战无不胜的誓言降服女人是一个道理”,但事实上这片刻的理智也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厄普代克还在文本中运用了许多以鸟喻人的情节。冯贡送给葛特露的第一件礼物是一只孔雀形状的珐琅彩挂饰,他告诉葛特露:“孔雀虽然羽毛华丽,但它们发出的却是一种足以让人发疯的叫声,所以孔雀常常代表着一种正在忍受折磨的灵魂。”此时的葛特露正处于背叛已有婚姻且无法做出决断的尴尬境地当中,她那饱受折磨的灵魂正与孔雀如出一辙。冯贡带给葛特露的第二件礼物则更有深意,那是一个雕刻着凤凰的酒杯。如果说第一件礼物暗示着冯贡对兼具孔雀华美容貌和痛苦灵魂的葛特露的同情与关怀,那么第二件礼物则表现了冯贡对葛特露浴火重生,从孔雀涅槃为凤凰的愿望,即便这背后的代价是背负永恒的骂名。毫无疑问,葛特露的涅槃必定会为冯贡的人生带来转机。冯贡甚至曾亲口对葛特露描述过自己的一个梦境,在这个梦境中葛特露变化无常,而自己则戴着王冠。笔者认为,冯贡对葛特露自然是有爱情的,否则也不会在自我放逐十年后再度回到她身边。但是这种感情却掺杂了某种更深层次的心理动机:对兄长的妒忌让冯贡心中长期蛰伏着报复他并取而代之的野心,而占有王后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先决条件。女性是脆弱的(不仅是莎士比亚这样说,试图为葛特露翻案的厄普代克也难免将这种论调带入他的文本中),这种缺陷在女性感知到爱情时更是会被无限放大,而冯贡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成功地获得了他觊觎已久的权力。
两人私情败露之后,冯贡很快做出了谋杀霍文迪尔的决断,因为在这时葛特露已经“不再是他心目中的光明之神,而是变成了一件他必须夺回来的珍宝,一块他不能失去的领地”。也正是由此,冯贡那原先自己都不一定意识到的心理动机被瞬间放大以至于上升到了行动的层面。一切都顺利地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着,国王被毒死后,他接替了王位,而对实情一无所知的葛特露则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她再嫁的命运,帮助冯贡埋葬了令他惶恐不安的历史。随着第三幕开启,冯贡摇身一变成为克劳狄斯,也正是在这个时间分割点,他对葛特露的感情产生了细微的变化。葛特露无可奈何地发现冯贡已不再是冯贡,而是成为一个叫克劳狄斯的陌生男人,因为他在和葛特露说话时一改往日的风度,代之以一种专横跋扈和责难的语气,端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子,他也逐渐流露出一种一心想胜过别人的倾向——这一切都像极了之前坐在宝座上的那个人。但葛特露却宁愿相信王冠落到了他的头上只是由于一件令人不快的偶然事故,她甚至卑微地为他辩护以便自我安慰:“地位高高在上的人是必须谨慎的,以防突然失去一切。”
不同于“回来的子君”和“堕落的莎菲”,葛特露的困境在于她的出走只是一个让她不断成为男性附庸的过程——她“这块领地”从老国王罗瑞克那里经由霍文迪尔终于转移到了克劳狄斯手中。葛特露的命运就像是被安置在了一个没有出口的巨大迷宫里,她在那里上下求索,找到的“出路”不能带她看到迷宫外的世界,只能指引她走向另一条暗无天日的通道。
三、“为自由”的掘墓人
厄普代克对《哈》进行文本重塑的过程中着重回答了“葛特露缘何与克劳狄斯结合”这个问题。也正是由此,葛特露从一个“荡妇”变身为大胆追求自我的新女性形象。在遇见冯贡之前,葛特露深知:她是父亲的女儿,后来成了一个精神狂躁的丈夫的妻子,还是一个总不在家的儿子的母亲,但她始终不是她自己;她一直在侍候着那个自己不得不将命运与之联系起来的人,没法回避他的意志,无法表达出自己真正的声音。冯贡的出现成为葛特露人生的转折点,而葛特露本人对冯贡的定义也一直都是“一个让她找到自我的人”,但笔者认为葛特露是否真正找到“自我”仍有待商榷。
首先,葛特露在意识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时,始终在强调冯贡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却无视了自己的主体作用,反而认为自己是他者。对于她,爱情不是“她同她自己”的中介,因为她并未获得自己的主观生存,她仍然淹没在不仅被男人所揭示,也被他所创造的这个恋爱女人当中。这种自我认知的视角必然会导致她的女性主义精神摇摆不定,脆弱不堪,因为她仍然没能把握通过自己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而是将其交给了她身边的男性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谁,只要掌握了主动权,就足以让她以那种驯顺的秉性服从自己的意志。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两人私情暴露后,冯贡清楚地认识到: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和忏悔以后,葛特露必然还是会再次回到霍文迪尔的身边,将曾经属于他的爱情投射到霍文迪尔的身上。
再者,葛特露自我的实现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的,得到的自由也只是为自己选择爱情的自由,但她却误以为追求并得到了这份爱情就是个体自由的实现、个人价值的彰显,并希望以此填满虚无的生活。事实是,一旦失去了冯贡的爱情,葛特露就又要变得“一无所有”了。厄普代克也在文本中提出“女人一旦产生了爱情,除非遭受巨大的痛楚,否则是无法遏制这种感情的”;相较之下,男人的爱情则强烈而短暂,他们希望爱情是以生活中的一剂调味品的形式存在着,能为沉重的压力带来安慰,而不会允许爱情占有自己全部的生命。读者无法预料,在冯贡成功迎娶葛特露后,激情褪去,他是否会感到厌倦。冯贡与葛特露的婚姻虽说是爱情的结晶,与霍文迪尔和葛特露的婚姻迥然不同,但是前者却未必能比后者维持得更长久,让葛特露找回自我的冯贡也未必不会让这不成熟的自我再度走向覆灭。
文学史上的许多女性,诸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鲁迅的子君,都与葛特露有着共同的精神谱系——她们为冲破枷锁做出的种种惊世骇俗之举都彰显了对女性个体自由的追求。但是与其说她们追求的是女性个体自由,不如说是女性的爱情自由;与其说她们在意的是纯粹的自我,不如说是纯粹的爱情,因为爱情才是她们行为的出发点。这些牵动人心的女性文学形象“为自由”的努力如昙花一现,片刻的欢愉过后便是永恒的沉寂,她们终于还是做了自己的掘墓人:包法利夫人服毒而死;安娜卧轨而死;子君却死得不明不白,“谁知道呢。总之死了就是死了”。而对于葛特露,厄普代克没有继续写她之后的命运,却在结尾留下一句:“一切都将正常进行下去。”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病态即正常。那么,葛特露将何时走到那条通道的尽头、如何走到那条通道的尽头,这就又是厄普代克留给读者的谜题了。
四、结语
在厄普代克的文本中,葛特露看似是故事的主角,掌握着情节的走向,实则从未获得话语权;看似成功挣脱被束缚的命运,实则再度回归附属品的身份。厄普代克一方面是葛特露自我价值实现的助推者,另一方面也是罗瑞克等人的“同谋者”,他的双重身份也让文本呈现出了葛特露“女性主义者”的表象与“驯顺脆弱”的内里之间试探性的碰撞、艰难的融合,使作品主题意蕴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葛特露还远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她追求自我的道路还在继续,千千万万的“葛特露们”亦然。
①② 〔英〕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朱生豪译,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173页,第173页。
③ 约翰·厄普代克:《葛特露与克劳狄斯——〈哈姆莱特〉前传》,杨莉馨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代译序部分)。
④⑤⑥⑦⑧⑨⑫⑬⑭⑮⑯⑱⑲⑳㉒㉓㉕ 〔美〕约翰·厄普代克:《葛特露与克劳狄斯——〈哈姆莱特〉前传》,杨莉馨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第7页,第9—10页,第15页,第18页,第3页,第54页,第49页,第74页,第61—62页,第115页,第156—157页,第177页,第95页,第155页,第25页,第224页。
⑩ 鲁迅:《鲁迅杂文精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⑪ 薛晨鸣:《“出走”与“归来”的二元困境——现代作家笔下的“娜拉出走”母题分析》,《名作欣赏》2018年第8期。
⑰ 刘辉:《葛特露:一个被消费的女性主义者》,《学术交流》2013年第7期。
㉑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55页。
㉔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