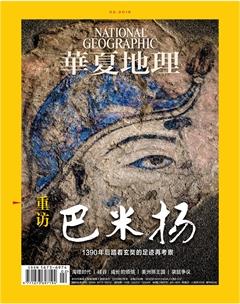硅谷在成长(算是吧)
米歇尔·奎因 黄秀铭译

在圣克拉拉的一次“黑客马拉松”编程集会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靠零食、能量饮料和健怡汽水提神,为开发一款供摄影师使用的增强现实应用程序出谋划策。
停车场里有12个电动车充电站,特斯拉司机们争先恐后地抢位。这是在计算机历史博物馆,前厅聚集了一大群人,多半是男性。有些人互相拥抱致意。有个人向房间另一头的什么人喊了一嗓子:“我的投资怎样啦?”钟声响起,我恍惚间好像置身教堂。喧闹的人群鱼贯进入礼堂。门一扇扇关上,演示日即将开始。
在接下来两天里,来自132家初创公司的企业家们就如何改变世界发表了经过精心排练的两分钟演讲。原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多得数不清:养老院卧室天花板上的雷达传感器,检查公用设施线路的无人机,为货运公司设计的机器学习,针对男性的洗衣用品订购服务。
创业孵化公司“Y组合子”首席执行官兼合伙人迈克尔·赛贝尔告诉硅谷的投资者们,平均下来每个演讲日会产生一个日后规模上十亿美元的公司。“你的任务是判别哪个创意会中彩。”他的公司专门帮助创业者开发创意。
第一个上场的项目是“公共休闲”,创意是为订购其服务的用户组办集体健身活动,场地选用停车场和其他开放空间。人们纷纷鼓掌的时候我在想,这市场够大吗?怎样应付雨、雪、蚊蝇?但紧接着,下一个了不起的创意已经上台——使用预测算法优化港口集装箱。会场静了下来,是一种出于敬意的安静。
作为记者,多年来我一直在写关于硅谷的文章。见多不怪,我已经学会不再一听到匪夷所思的创意就哑然失笑。我曾经斥之为儿戏的一些初创公司如今已经赚了几十亿,它们推出的产品或服务我以前压根儿没想到会有人需要。如果A计划不灵,“公共休闲”就转而采用B计划,直播平台Justin.tv就是这么干的:它最初只直播贾斯汀一个人的無厘头搞怪,接下来扩展到随便什么人的搞怪,然后变身为游戏视频社区Twitch。2014年亚马逊公司以9.7亿美元的价码将它纳入麾下。
长期观察硅谷的保罗·萨佛说,硅谷是一个总在“遁入未来”的地方。在演示日,创业者们描绘着一幅因为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增强现实、机器人、无人机和传感器而变得更加美好的生活画面。

苹果是第一家价值万亿美元的美国上市公司,在硅谷开创先河,并在持续扩大其影响力。苹果设在库比蒂诺的新总部大楼于2017年投入使用,人称“太空船”。大约有1.2万名员工在那里工作,不到苹果湾区阵容的一半。最近,苹果公司一直在对硅谷提出批评,强调保护客户隐私的重要性,抨击某些科技公司的做法。
硅谷的乐观主义和使乐观精神长盛不衰的务实梦想家们一直令我着迷,但近来却出现了某种迷梦知返的趋势。
“责任”和“共情”是最新流行语。硅谷知道,人们正在把一切变化归因到它头上:劳动力的人口结构特征,被颠覆的传统产业,技术带来的失业之痛。连一些年薪六位数的工作人员都为高房价或高房租所困。在世界其他地方如玻利维亚,新型电子产品暴增所推动的锂矿开采引起人们对资源剥削和环境污染的担忧,而那些产品正是硅谷的发明。
技术主宰未来,但业内之人也不得不勉强承认:有时我们的初心是为了让事情变得更好、更有效率,但执行中难免有人会受到伤害。
安妮·武伊齐茨基说:“我们身边尽是胸怀大志的人。”她是个人基因组学生物科技公司“23和我”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硅谷的现状是顺应历史流向的——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世界已经变了。我认为,对于所有受到转变冲击的地方,我们都有一份责任。”
人人心怀梦想
外地人常常问我:“硅谷在哪儿?”硅谷没有首府,没有发源点。山坡上没有好莱坞式的醒目标志宣示“高科技城在此!”硅谷是一片马蹄形的平原,布满办公室和居民区,东边和西边有一些不高的山脉。在硅谷的中心地带,旧金山湾碧波荡漾。我把脸书公司的大拇指“点赞”标识指给来客们看——在该公司不断扩建的总部外面一眼就可以看到。脸书不对访客开放参观,大多数科技公司也一样。
当然,“点赞”标识也许并不让每个人都开心。据悉脸书的数据政策未能保护好用户,因为一名研究人员将个人信息出售,随后有人利用这些信息向用户发送政治广告。俄罗斯特工还把脸书用作宣传工具,在美国煽动政治纷争。硅谷科技的中心可能是山景城的一个住所,晶体管的发明者之一当初在这里创办了公司。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曾专程拜访此地,只为触摸一下那栋房子,见证历史标记。中心也可以是在洛斯阿尔托斯一条死胡同的住宅里,一名印度裔软件工程师晚上把孩子们安顿上床,然后回到网上继续筹划创业。或者,中心竟是斯坦福大学附近停放的一辆房车,四个轮胎有三个是瘪的,从海军陆战队退役后做勤杂工的吉姆和他的狗住在车里,每天只能用湿纸巾擦洗身体。
我曾经斥之为儿戏的一些初创公司已经赚了几十亿,它们推出的产品或服务我以前压根儿没想到会有人需要。
如今的硅谷与1982年相比,景象已大不相同。当年,《国家地理》杂志曾描绘硅谷“放任自流的平等主义取代了乡村的生活节奏”,并说“这种动态增长发生在一个看似平静的外表后面……一片 单调的低层长方形建筑物,各家公司的名牌卖弄着高科技词汇的杂烩,很难看出建筑物里面在干什么。”
周围山坡上道路蜿蜒,鹿低头吃草,令人不禁遐想此间人们乡村生活的闲适节奏。这个山谷曾有多座杏、李果园,而今年刚刚见证了一个地标性水果店的关闭,大萧条期间于圣何塞创立的“果园五金器具”(连锁店也已经关门大吉。尽管如此,硅谷仍然可能骗过你的眼睛:这里的气氛看起来平等、开放、随意,首席执行官穿着连帽衫,风险投资人穿着自行车紧身短裤,随性之举随处可见,比如工作场所要求人们脱鞋,或允许员工带狗上班。
但硅谷对它的勃勃雄心毫不轻忽。24岁的特里斯坦·马提阿斯抱怨道:“人们只对你的初创公司感兴趣,你叫什么名字才没人在意。”
硅谷如今的吸引力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以一名记者的身份来到这里,还感觉这地方有点死气沉沉。冷战结束后国防工业衰落和经济衰退导致了整个加州的裁员潮。当时的热门产业类别是多媒体光盘和电子游戏。
一个想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传播开来:如果人们可以凭借计算机互联,生活就会随之改变。“美国在线”公司问世,推出数字商城,人们可以上网买花。其服务反应迟缓,难以使用,但一件意义非凡的事物已经初露端倪。
在北边的西雅图,一场派对就要开场。微软公司正在使计算机大派用场,并因此财源滚滚。1995年8月,微软就像一场赢家通吃的技术竞赛的胜者,高管们午夜时分在电器商店外面跳舞,庆祝Windows 95操作系统推出。与此同时,一枚“炸弹”正在硅谷引爆。
网景公司造出了供用户在互联网上游逛的浏览器软件,并在其标志性产品發布不到一年后上市。尽管网景是一家尚未证明自己实力的公司,警示投资者的风险概述占了好几页,其股票仍在开盘日收于58.25美元,使公司的即时市值高达29亿美元。
网景首次公开募股(IPO)是互联网热潮的开端,大潮中,人们见证了亚马逊和雅虎等伟大公司的诞生,也目睹了若干公司的倒闭。
互联网上可以做的一切——卖化妆品、租卡车、找约会对象等等——令人激动,进而引发了投机性股票市场。仅1999年就有四百多家公司上市,其中大多数是科技股。
接下来的2000年,市场崩溃。二十多万个工作岗位被淘汰。
尴尬。痛苦。然而,“所有那些初创公司都是对的,”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告诉我,“关于互联网能为人们做些什么。但问题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能那么快改变。”
对于如何把坏事变好事,硅谷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迭代”意味着先让产品进入市场,即使其并不完美——微调的事可以过后从容进行。“战略转向”(要面不改色地说出来)表示趁钱还没烧完赶紧改变经营方向。
失败和挫折为新创意和后来者扫清了道路。谷歌占据了“硅图”原址的一部分,后者是一家计算机公司,其联合创始人参与创立了网景。脸书在扩展地盘的过程中改造了曾经的“太阳微系统”园区。把互联网和电视连接起来的努力遇到过重重难关,然后来了油管视频。

乔书亚·卡彭蒂尔是帕洛阿尔托一家初创企业的员工,在由“游戏场全球公司”提供的办公室上班,可以坐在游乐区工作。场地提供方资助并支持初创企业开发新技术,重点是人工智能。卡彭蒂尔说:“我上班时坚持每天去滑一次滑梯,提醒自己要享受乐趣,别把手头的事看得太严肃。”去年10月单位裁员30%,卡彭蒂尔也被下岗了。
社交媒体时代来临。脸书的联合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搬到帕洛阿尔托,用黑客信条“行动迅速,打破常规”来发展公司。在旧金山,一群朋友和同事找到方法,让人们能随时用140个字符进行消息更新,推特由此诞生。
硅谷的洪流掩盖了个人的遭际。对许多人来说,创新带来的巨大“创造性破坏”周期不是从10公里外观察到的现象,而是个人层面上的切肤感受。失业,技能过时,家庭倾覆。
苹果提供了另一个模板:复出。1997年,在苹果收购了史蒂夫·乔布斯创办的另一家公司NeXT之后,乔布斯重掌帅印,苹果随之开始缓慢复苏。公司发布了iPod,继之以数字娱乐商店iTunes。iPhone于2007年推出,兑现了十多年前做出的智能设备承诺。快进到今天,科技公司正想方设法解决高科技对人们生活的巨大冲击所带来的问题。它们的掌门人被召集到美国国会,就客户数据的使用、境外分子如何利用重要技术扰乱选举、控制人们所见信息的算法中的潜在倾向性等问题作证。
随着人工智能——学习像人类一样思考的计算机——的出现,数据和计算速度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正如旧时代的石油。如果计算机有一天能“思考”并做出决策,世界会怎样?
“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近旁,100万美元一栋的房子正在兴建。”——保罗·贝恩牧师
在三千多名谷歌员工签署抗议信后,该公司决定不续签与国防部合作使用人工智能来分析无人机图像的项目合同。随后在11月,全球两万名谷歌员工罢工抗议公司对性骚扰和薪资公平问题的处理。“销售力”软件公司在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署的合同遭到批评后,设立了“符合伦理和人道的技术使用办公室”。
我拜访了斯坦福大学前校长约翰·亨尼西,他现在是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董事长,人很随和,但少了学术界人士常有的那份放松。他说,科技行业目前经历的“报应”引来更深层次的问题——关于硅谷存在的意义。
“现在的棘手事情是,各个公司要考虑如何承担责任,对公司的治理不仅要符合股东利益,还要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他说。
创业生活
外地的年轻人不断涌入。
“坐在咖啡馆里,听见邻座在拉投资,或一帮人大侃加密货币和谷歌,诸如此类的东西会让一些人生厌,但我喜欢。”来自纽约州北部的产品经理施丽娅·内瓦蒂亚说道。她从塔夫茨大学毕业后离开了波士顿。
在一个林木葱茏的帕洛阿尔托社区,乔舒亚·布劳德坐在后院泳池边。2004年夏天脸书开始流行时,老板扎克伯格就住在那里。房子里面,布劳德的几个同事坐在餐桌旁,调试他公司的手机应用DoNotPay。这个程序扮演机器人律师的角色,能就停车罚款单提出抗辩,或寻找航空公司和酒店预订的价格漏洞。但这只是黑客式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工作、吃饭、睡觉全在一个地方,一切只为尽早推出产品。在科技公司传奇中,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人们生活、工作、向科技公司投资。沃兹尼亚克是一位广受欢迎的演讲者,每年收到超过一千份邀请。他的吸引力部分在于,他是硅谷最被人津津乐道的苹果公司发家史中“另一位史蒂夫”。他经常复述一个故事:1980年公司首次公开募股时,他以IPO前的便宜价格把自己的部分苹果股票卖给了80名员工。
他说:“我很在意财富的分配。”
“兄弟文化”经久不衰
如今,硅谷也不妨称为移民谷。外国裔的涌入有助于抵消人才向美国其他地方的流出。在一些领域,如计算机和数学,外裔员工现在占60%以上,78%的女性员工生于他国。印度人、中国人、越南人是该地区科技行业的主要外国人群体;2015年硅谷的技术岗位有42人来自津巴布韦,106人来自古巴。
硅谷的国际性意味着这里的公司不论大小,已经成为诸多文化和语言的融合体。但这也凸显出哪些人没有实现硅谷梦。平均而言,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加起来只占主要科技公司劳动力的12%。在所谓的硅谷“兄弟文化”中,女性所占比例也非常低:谷歌、苹果和脸书的员工中,女性仅略多于30%。2018年9月發布的一项调查发现,女性仅占初创公司创立人的13%,持有创始人股权的6%。
但女性获得的支持在逐渐增加。根据非营利组织AnitaB.org对80家美国公司的调查,2018年女性占技术岗位的24%,公司领导层的18.5%。
在薪酬方面,招聘公司Hired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超过60%的情况下,从事科技行业的女性在相同职位上获得的薪酬低于男性 (平均差距为4%)。各大科技公司表示,他们乐意拥有更多样化的团队,但是很难一下子改变员工的人口结构特征。
“我曾经听到年轻女性说硅谷对女性很苛刻,她们是咬紧牙关才挺下去的,” 产品经理施丽娅·内瓦蒂亚一边喝茶一边告诉我。她创建了一个名为“紫色社会”的团体,帮助女性和非二元性别人士在闯荡科技领域的头十年里创业。她对男性的广泛人际关系网很感兴趣,这种关系在大学期间通过同学、室友关系建立起来,并在早期职业生涯中得到发展巩固。通过看似偶然的联系建立起来的公司,实际上是经由这些人际网络产生的。“我们需要更多女性来促成或然事件发生,”内瓦蒂亚说。
在繁荣的重压下
随着外来人口持续涌入硅谷,推高房地产和租赁价格,许多游离于科技经济之外的人——也包括一些身在其中者——发现生活变得日益艰难,主要原因是居住成本上涨。
东帕洛阿尔托可能比什么地方都更难挤进去。这是一个拥有大约3万人口的城市,夹在令人生畏的邻居中间:北倚脸书,南临谷歌。过去50年间,此地大体上是一个非裔和拉丁裔家庭杂居的城市。现在许多新家庭正在搬进来,很多是白人和亚洲人。据地产数据平台Zillow统计,此地的房价中位数已经超过100万美元——而2011年是26万美元。100万美元,在这座从旧金山延伸到圣何塞的半岛,已经算是比较可以负担的住房价格。
对许多居民来说,他们并没有从当前的科技繁荣获益,租金一再上涨,而购房根本没有可能。许多人只好搬到远郊,上下班要开车几个小时。或者,干脆撤离这一地区。“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旁,100万美元一栋的房子正在兴建,”牧师保罗·贝恩斯说。他和妻子谢丽尔在东帕洛阿尔托经营一家非营利救助机构。
帕特里夏·卡特住在东帕洛阿尔托,有一大家子人:已经成人的儿子和他自己的三个年纪都在四岁以下的小女儿,她女儿,再加上儿子的前配偶——也就是三个小女孩的母亲,眼下租住在她家车库里。帕特里夏是个运货卡车司机,2003年以44.7万美元买下这栋三居室住宅,后来险些因付不起按揭而被银行收回拍卖。
“Y组合子”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赛贝尔认为,如今硅谷已经发生了属跨代性质的转变。较年轻的从业者希望公司雇佣的员工更加多样化,在公司运营中体现更高的社会良知。
赛贝尔的目标是什么?从耶鲁大学毕业时,赛贝尔打算在二十来岁时挣钱,三十来岁时养孩子,四十来岁时从政。他2006年搬到旧金山,创立了一家公司。他曾是Justin.tv和Socialcam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后者在2012年出售给欧特克公司,而Justin.tv最终变身为Twitch。现年36岁的赛贝尔刚刚成为父亲,但从政已不在计划之列,他觉得现在的身份拥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如果硅谷有其精神中心,那可能就是互联网档案馆,它是设在旧金山一座前教堂里的非营利组织。在那里,服务器日夜不停运转,以多种形式将无数公共网页存档。维基百科的几乎每篇文章,每天大约400万条推特,每周逾50万个油管视频。该馆已经归档了超过3400亿个网页,堪称互联网的失物招领处。
在档案馆大厅散布着超过120尊1米高的塑像,纪念为该馆贡献了至少三年时光的人们。互联网的兵马俑。这个场景既诡异又极具震撼力,其中一些人我能叫出名字。
栩栩如生的群像有点瘆人:有的手里拿着书,有的端着杯子,有的抱着吉他,仿佛被来访者打扰前正在做项目或飙歌;又或者,是在争论接下来怎样做才问心无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