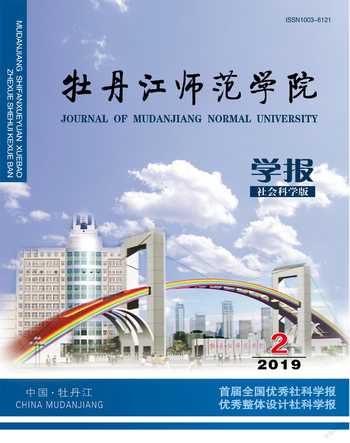《呼兰河传》英译本中民俗翻译的创造性叛递
张白桦 孙晓宇
[摘 要] 《呼兰河传》是中国现当代女作家萧红的代表作,展现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其中含有大量的民俗描写,包括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通过系统分析葛浩文译本在三种民俗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探究制约翻译的深层文化因素,发现葛浩文凭借出色的双语能力,灵活运用归化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在中西方文化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在保证忠实原文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出色地向西方译介了中国文化。
[关键词] 《呼兰河传》;创造性叛逆;民俗翻译;葛浩文译本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呼兰河传》的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因翻译诺贝尔奖得主莫言的作品而走入公众视野,他曾谈到:“我的翻译最早也是从萧红开始的因为研究萧红我要向美国汉学界介绍她就开始翻译她的作品,后逐渐就完全转向了翻译”[]。对《呼兰河传》的翻译,是葛浩文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开山之作。
《呼兰河传》中充满了许多东北民俗描写,而民俗因为其独特性和地域性,成为了翻译的难点所在。葛浩文在翻译这部作品时,他从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出发,特别是在译介东北民俗文化时,进行了一些叛逆化的处理。系统地研究他在译介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探究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更好地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契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主旋律。
二、“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及研究价值
法国著名文论家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最先提出了“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他认为只有大家在接受了这一前提,才能解决翻译这一带有刺激性的问题。当译作由一种语言被翻译到另一种语言时,由于参照体系和文化语境的变化,作品的面貌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译者通过其努力,赋予了译作新的面貌,这一工作自然而然充满了创造性。
谢天振是最早将“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的学者,他的《译介学》于年出版,在书中,他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虽然“创造性”和“叛逆性”可以在理论层面被分开进行讨论,而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这两者却是和谐统一的。尽管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做到忠实原文,但是由于语言、文化以及诸如意识形态等其他因素的制约,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距,这也就印证了“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
“创造性叛逆”跳出了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桎梏,让我们将研究的重心从源语文化转到译入语文化,探究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契合了当今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大趋势。同时,“创造性叛逆”是一个中性词汇,无任何褒贬色彩,只是对翻译中出现的一种客观现象的描述,所以“叛逆”并无好坏之分,我们自然也无须探讨如何拿捏“创造性叛逆”的程度,“创造性叛逆”也无法作为提升翻译质量的指导方式。
此外,大多数译本分析的论文在谈论翻译时,大多停留在语言层面,即对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的探讨,缺乏对制约翻译的深层文化因素的探究。一些谈论翻译的著作,其中所举的例子也稍显陈旧。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在参照原文本的基础上,适度地进行叛逆,来使译作在新的语言文化環境中延续生命。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文学的传播和接受将变得步履维艰”[]。所以继续挖掘成功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探究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的必要性就不言而喻,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三、“创造性叛逆”在《呼兰河传》民俗翻译中的体现
我国学者钟敬文给民俗作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民间风俗习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在长期的历史生活过程中所创造、享用并传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而民俗“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即物质民俗,以人们吃、穿、住、用为主要内容;社会民俗主要包括:家庭、家族、村落、民间组织、岁时及人生礼仪等;精神民俗,诸如宗教信仰、道德、禁忌、民间文学等。所以,民俗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普遍存在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且如今的民俗不仅局限于“乡村”和“原始”这样的狭义概念,泛指任一群体所共享的传统的行为方式。
在《译介学》中,谢天振将“创造性叛逆”划分为“个性化翻译”“误译和漏译”“节译与编译”和“转译与改编”四种类型,而体现在《呼兰河传》民俗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主要表现为“个性化翻译”和“误译”。“个性化翻译”以“归化”为主要表现形式,即译者要照顾到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喜好,将一些异质性的元素转换为本族的常见文化意象。同时,个性化翻译也包括“异化”,意在向目的语读者传递原汁原味的异质性的源语文化。
关于误译能否算作是“创造性叛逆”,学界也存在着争议,本文所采用的是谢天振对“创造性叛逆”的界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化研究,其实质是两种文明与文化的比较,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自然也具有了文化研究的属性。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误译”被嗤之以鼻,被认为没有太多的研究价值,而在译介学中,“误译被视作一种更为特殊的创造性叛逆,因为有些误译往往反映了某一特定的个体(译者)或群体(民族)在接受或解释外来文化时所表现出的特殊趋向”[]。误译包括有意识的误译和无意识的误译,且大多误译都属于无意识的。如果译者对源语缺乏透彻和深入的了解,就会造成无意识的误译,而有意识的误译更是反映了译者在平衡两种文化过程中作出的权衡与取舍所以“误译”不仅反映了文学和文化交流上的阻滞与真空,更反映了信息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失落、扭曲与变形,系统地对文学翻译中的误译展开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译者将“香荷包”翻译为"Perfume satchels",这里涉及到翻译准确性的问题。"satchel"的英文含义为"bag for carrying things: a small bag, especially one with shoulder straps used for carrying schoolbooks",這个词一般用来指装教科书或者课本的带肩带的书包,而“荷包”也叫做“香缨、香囊”,是中国传统的民间工艺品,一般只有手掌大小,可以装一些小的物品,也可以作装饰之用。而译者将其翻译为"Perfume satchels",显然是将小小的荷包“放大”成了带肩带的书包,给国外读者造成了误解。
“马蹄袖”为满族服饰所特有,因为形状很像“马蹄”,故被称之为“马蹄袖”。满族人也称之为“哇哈”,是把一个半圆形的“袖头”接在本就很狭窄的袖口的前面,具有可拆卸的特点。如果译者将其直译,会让从来未见到过这种服饰的国外读者很困惑,因为“可拆卸”是该袖子功能方面最明显的特点,故葛浩文采用了个性化翻译中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其翻译成"Detachable over sleeves"。
他用同样的手法将“太师椅”翻译为"Armchair",“太师”在朝廷中位高权重,“太师椅”以官名命名,也自然象征着坐在椅子上的人的身份高贵,这体现了中国等级森严的封建礼制和习俗文化。如果直译,则会因为缺省这一隐含文化信息,给外国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而“太师椅”的主要特点是靠背与扶手连为一体,体态宽大,所以译者根据“太师椅”的外观来进行翻译。类似这种根据功能、外观进行翻译,而对其他深层含义进行取舍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下面这个“绳甩子”的翻译。
例2.只是有二伯一声不响的坐着,他手里拿着绳甩子,东甩一下,西甩一下[7]142。
Second Uncle You alone sat there without saying a word, flyswatter in hand, which he flicked from side to side.[8]232
“绳甩子”的学名叫做“拂尘”,有时也被称作“云展”,在一根手柄前端附着上丝状的织物或兽毛,即可制成。在日常生活中,其可用于拂去尘埃或者驱赶蚊蝇。而在道教文化中,“拂尘” 是道士经常携带的法器。在汉传佛教中,它同样被作为法器,象征着扫去烦恼。在一些武术流派中,“拂尘”也被当做武器。虽然“绳甩子”具有一定的文化象征意义,但考虑到《呼兰河传》的发生背景是在农村,“绳甩子”在平常百姓家的用途也仅限于驱赶蚊蝇,且国外没有这种物品,所以葛浩文根据其用途,省略与原文语境无关的文化含义,将其直接翻译为“苍蝇拍”,简洁明了。
例3.于是人们说着,就把冯歪嘴子应得的那一份的两个肉丸子,用筷子夹出来,放在冯歪嘴子旁边的小蝶里,来了红烧肉,也是这么照办;来了干果碟,也是这么照办[7]184。
Then someone would pick up Harelip Feng's share of meatballs with his chopsticks and place them on a small plate beside him.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when the braised pork was served and the dried fruit was put on the table.[8]267
在《新英汉大辞典》中“干果”有两种含义,一则为有硬壳而水分少的果实,一般指坚果;二则为晒干了的水果。《呼兰河传》故事的发生地是位于黑龙江省的边陲小镇呼兰河(今哈尔滨市呼兰区),在东北乡下的酒席上,没有供应水果干或者坚果类实物的传统,所以这里的“干果”并非指“水果干”,而是一种东北乡间酒席上的特色美食,是将面粉、鸡蛋、白糖、水按一定比例混合,揉成菱形,经过油炸而制作出来的一种口感酥脆的小吃。由于没有东北农村的生活经历,葛浩文将其翻译为“水果干”,如果将其翻译为"fired snacks",可能更为恰切。除此之外,译本中还有一些因为缺少东北生活经历造成的误译,译者因为看到了“被格”中的“被”字,想当然地觉得这个物品将与休息和睡觉有关,将其翻译成了"bed"。其实“被格”是放置在炕上的的“被橱”,也叫“炕琴”,分为两个部分,下面的柜子可以存放一些衣物,上面可以放置被褥。这个词对于没有北方农村生活经历的中国读者都会很陌生,更何况对于一直生活在美国的译者,误译也是情有可原。
这段话的上文叙述的内容是:在仓房里,萧红和祖父找到了之前家里开烧锅时用的帖板,祖父将帖板刷上墨,给她印制帖子以供消遣,所用的就是“鬼子红”。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人们为了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将其蔑称为“鬼子”,而“鬼子红”,究其缘由,可能会有两种含义,一则是这种红色的墨水的制作工艺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再者就是日本国旗正中间就是红色,且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萧红在写《呼兰河传》时,抗日战争正在进行,在《呼兰河传》中用一个小女孩的口吻来称之“鬼子红”,也表达了她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但如果将“鬼子红”中蕴含的的文化和历史内涵进行注释,也势必会影响阅读体验,所以译者直接译为“红墨水”。
同样,原文中说,祖父和萧红在储藏室中找到了一个红玻璃做的灯笼,祖父把灯笼擦干净,在里面点上“洋蜡烛”。由于这种蜡烛是从西洋(泛指国外)传来的,在东北,人们指称舶来品的时候,通常要在前面加上一个“洋”字。但是“洋蜡烛”的本质属性仅仅是“蜡烛”而已,并没有区分于其他“蜡烛”的特点,如果译为"foreign candle",反而会与文章朴实的语言风格格格不入,所以葛浩文直接将其译为“蜡烛”。此外,他将“白洋铁”翻译成"galvanized iron",即“白铁”或者“镀铁”,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例5.我还看见了一座小洋房,比我们家的房子不知好了多少倍[7]76。
I also saw a small Western-style house that looked ten times better than our house.[8]171
第三章第六節中出现的“小洋房”,即按照西方建筑风格建造的房子,与上文的“洋蜡烛”只被翻译为“蜡烛”不同,因为“西方风格”是这座房子的独特属性,所以译者并没有进行省略,将其翻译为“西方风格的房子”。葛浩文将后半句的“比我们家的房子不知好了多少倍”翻译为"ten times better than our house",运用了虚实转换的翻译手法,“虚实转换是指词汇抽象概念与具体意义的相互转换”[9]50。抽象和具象的思维方式会在语言表达上得以体现,具体表现为用词习惯的不同,抽象思维的人倾向于用一些表示抽象的概念的词语来陈述事件。在汉英翻译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词语的虚实意义的相互转换,以确切传达原文中某些词语的语义,便于英美读者的理解。“好了不知多少倍”是一种虚指,其核心含义就是“要比我家的房子好的多”,而葛浩文将其译为"ten times better"译为“好数十倍”,使读者清晰地感受到“好”的程度。这种虚实转换的方式在译本中随处可见,译者将“笑了半天功夫才能够止住”翻译为"I'd laugh for the longest time before I could stop",还有将“等了好久”翻译为"the longest time went by",其中的“半天功夫”和“好久”都是虚指概念,通过虚实转换,使得译文更加生动形象。
(二)社会民俗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称谓语是社会民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华民族具有厚重的历史与文化,被称作礼仪之邦,闻名遐迩。《左传》是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早在古代,得体的交际礼仪就受到了广泛的推崇,称谓语是语言交际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透过称谓语,我们可以洞悉人物的性别、年龄、身份、地位、人物之间的亲疏关系。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称谓体系,中西方也因为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在称谓语上也呈现了不同的特色。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血缘关系是维系亲族关系的纽带,社会也正是由许许多多的同姓宗族构成。西方虽然也经历过封建社会,但是家庭成员居住较为分散,血缘观念比较单薄,亲属关系性对松散。“重名分、讲人伦”的封建伦理观念一直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而在西方社会,人们秉承着“人为本、名为用”的价值取向,两种语言在称谓体系上存在差异也就不足为奇。“童养媳”是旧时在我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由婆家养育的幼女,待到成年时正式结婚,地位低下。《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只有12岁,所以译者将其意译为“Child bride”,虽然是对原文的叛逆,但却在深层含义上达到了忠实,使国外读者对这种封建社会的婚姻现象一目了然。
“妯娌”是指一家如果有两个儿子,他们的妻子之间的关系就是“妯娌”,所以译者将其直译为"Two daughters-in-law"。“英语中的常用亲属称谓词只讲辈分,不分长幼”[9]56,没有中国如此之多的诸如“二舅母”“二姑”“三姨”和“大娘婆婆”这样的称谓语,而将其统称为"aunt",所以译者对这两个称呼进行直译,将中文的 “排行+亲属词”译为英语的“序数词+亲属词”,但汉语排行中所反应的民情风俗,译入语读者还是难以感同身受。在丈夫的家族中,妻子的称谓排行以丈夫的排行为准,而翻译“二舅母”的时候,译者采取了个性化翻译中的归化翻译策略,增添了"maternal",指的是母亲这边的亲戚,最大限度地接近了原文。
例7.小养汉老婆……你奶奶,一辈子家里外头没受过谁的大声小气,今天来到戏台底下受你的管教来了,你娘的……[7]49
Your husband-stealing slut……screw your grandmother! Never in my life have I heard a harsh or angry word from anyone, and now you expect me to let you tell me what to do…… up your mother's……[8]144
这段话位于《呼兰河传》第二章第三节,叙述的是在唱野台子戏时,戏台下发生的两位农妇的骂战,内容极其庸俗。“养汉老婆”是东北的俗语,指的是背着自己的丈夫,在外面和其他男人有婚外情的妇女。译者抓住了其精髓,将其译为"husband-stealing slut"即“偷丈夫的荡妇”,一则表明了这一妇女的已婚身份,二则指出该妇女品德不好,是个“荡妇”,简明扼要地传递了隐含的文化信息。
这样的处理也被应用于翻译“三年前他和一个妇人吊膀子”这句话,这句话的上下文是在叙述“李永春”药店的厨师,和一个妇人发生了奸情,被骗走所有钱财的事情,其中的“吊膀子”就是指“与别人保持不正当关系”,所以译者将其翻译为 "having an affair with",可见译者深厚的驾驭语言的能力。而且后面的“你奶奶的”,也是骂人的恶俗词语,译者在这里增添了"screw",即“性交”,足以见得译者卓越的汉语水平。此外,译者将“一辈子家里外头没受过谁的大声小气” 译为"Never in my life have I heard a harsh or angry word from anyone"译文中省略了次要信息“家里家外”,且抓住“大声小气”的核心含义,即"a harsh or angry word",虽然从形式上叛逆了原文,但却达到了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忠实。
(三)精神民俗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例8.请了和尚道士来,一闹闹到半夜,所来的都是吃、喝、说、笑[7]76。
Buddhist monks and Taoist priests were brought over, and the commotion of all that eating, drinking, talking, and laughing lasted late into the night.[8]170
“和尚”和“道士”都是中国所独有的,因为西方人的主流宗教是基督教,“monks”指的是一些信奉基督教的修道士,而中国的“和尚”所信奉的是佛教,当中西方文化出现差异的时候,译者采取了个性化翻译中的异化翻译策略,增添了缺省的信息,让西方读者知道这些僧侣所信奉的是佛教。同样,“道教是中国固有宗教之一,与佛教、儒教并称中国三大宗教”。[10]道教的创始人为老子,其著作《道德经》被封为道教的经典之作。在道教多年的发展、进化、演变的过程中,将诸多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都吸收进来,诸如巫术、古代的鬼神思想和神仙方术,等等。正因其兼收并蓄的特点,道教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辐射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方面面。但在英文中只有"priest",指的是信奉东正教或者天主教的牧师,无法找到和“道士”相对应的词,所以译者将其译为“牧师”或“神父”,增添了"Taoist",指出这些人所信奉的是道教,意在向西方传递中国的宗教文化。
例9.“回家”这两个字,她的婆婆觉得最不详,就怕她是阴间的花姐,阎王奶奶要把她叫了回去,于是就请了一个圆梦的。那圆梦的一圆,果然不错。“回家”就是回阴间地狱的意思[7]128。
In the eyes of the girl’s mother-in-law the words "go home" were the most disquieting of all, for she imagined that the girl might be a reincarnated daughter who was being summoned home by the Queen of Hell herself. And so she sent for a reader of dreams, whose explanation was just as she'd feared: "Go home" did, in fact, mean return to the nether land.[8]221
原文所叙述的内容是小团圆媳妇自过门以来,就多灾多难,她的婆婆担心她是“花姐”。“花姐”是民间封建迷信的说法,又称“花仙”,是被贬下凡的仙子,她们大多聪明美丽,但从小多病多灾,命运多坎坷,花仙都不能出嫁,一旦出嫁,必會夭折。如果直译为"flower sister",则会让外国读者不知所云,而且其封建迷信的含义也无从说起,于是葛浩文“阴间的花姐”将其译为"a reincarnated daughter",即“转世的童女”。“轮回转世”是佛教、道教还有一些印度宗教的主要观点,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也认同此观点,强调人有前生来世,生生死死轮回不断。具体表现为人死后,他的灵魂会在另一个机体中得以继续存活,所以现在每个人的生命是来源于过去的某个人的转世。而西方主要信仰的为基督教,人们并不相信转世轮回,但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从一份报告中窥探出葛浩文如此翻译的原因。美国南部是基督教福音派的流行地区,1989年的一份宗教调查报告指出:“在美国18-24岁的青少年中,31%的人相信轮回转世思想”[11]。美国是个大熔炉,多元宗教得以生存和发展,受到东方宗教对美国基督教的冲击,“轮回转世思想却从未在美国停止传播”[12]。而葛浩文采用了这种译法,在明确一部分西方读者对“转世轮回”概念并不陌生的前提下,借此向西方传递了来自东方的异质性的宗教内容,进一步传播了东方文化。
此外,在早期佛教神话中,阎罗王是地狱唯一的王,民间俗称“阎王爷”,其原型为印度神话中的阎魔王。“阎王奶奶”作为“阎王爷”的妻子,故被翻译为“地狱的王后”。“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特有的地狱学说与华夏本土的冥界信仰产生碰撞融合,诞生出一种兼具梵汉特征的宗教意识”[13]。这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寻常百姓心中的地狱观的来源,而直到基督教文化主导西方社会的时候,其地狱观念成为正统,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也都来源于此。虽然中西方宗教文化中对于“地狱”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演变过程以及观念上的差异,但是中西方人眼中的地狱都是指人在死亡之后去接受惩罚的地方,充满了无尽的黑暗和罪恶,所以译者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力求在中西方文化中取得平衡,将“阎王奶奶”翻译为"the Queen of Hell"。
原文中“请了个圆梦的”,其中的“圆梦”,和我们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的“使梦想成真”并不是同一个含义,“圆梦,也叫做‘占梦’,是一种发源于汉族的占卜方式”[14]。人们可以通过解梦的方式来预测即将到来的旦夕祸福,僧人、道士、祭司、巫觋、算命先生都可以充当圆梦者。如果占卜的结果为吉兆,人们会觉得十分欢喜,如果为凶兆,则要采取相应的方法来进行破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周公解梦》,西方也有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但两者有所不同,我国的占梦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禁忌和注意事项,而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所提出的释梦的方法则较为简单,他始终强调‘梦是愿望的实现’”[15]。尽管中西方关于“解梦”的方法论上有诸多差异,但是中西方在“解梦”这一传统上是存在相似之处的,所以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译者将“圆梦的”翻译为"a reader of dreams"。
例10.他还有一个别号,叫云游真人,他说一提云游真人,远近皆知。不管什么疼痛或是吉兆,若一抽了他的帖儿,则生死存亡就算定了。他说他的帖法,是张天师所传[7]115。
This man had a nickname—the Wayfaring Immortal—and people far and near knew of whom you were speaking when you mention his name. Whatever the disease or discomfort, whether the signs were good or evil, life and death was settled for all time with the drawing of one of his lots. He told them he'd learned his divining skills from the head priest of the Taoists himself, Zhang Daolin, Master Zhang.[8]207
“真人”是道教的说法,指那些存养本性和修真得道之人,也泛称“成仙”之人。“云游真人”中的“云游”指的是僧人或道士漫游四方,行踪不定,所以译者将其翻译为"Wayfaring Immortal",即“徒步旅行的神仙”之意,虽少了一丝中国语境里的神秘和悠然的气息,但基本含义得以准确传达。“张天师”所指的是张道陵,天师道创始人,时人尊称张道陵、葛玄、许逊、萨守坚合称四大天师,而这却对国外读者十分陌生,所以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运用了释义的方法,补充了缺省的信息,向外国读者传播了中国的道教文化,将其翻译为"the head priest of the Taoists",即“道士首领”之意,此外还增加了人名“张道陵”,又将“张天师”直译为"Master Zhang",可见译者为传播中国文化所作出的努力。
四、结语
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文化、沟通世界文明的方式,在当今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独特的民俗文化更是一国文化的瑰宝,更是一国民众生活的精华所在。同时,因其地域性和独特性,民俗文化的翻译也成为了翻译的难点所在。本文系统考察了《呼兰河传》英译本中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分析制约了民俗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我们可以看出译者葛浩文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沟通中西文化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他采取了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在保证忠实的基础上,适度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通过“创造性叛逆”,求同存异,试图在中西方文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出色地将《呼兰河传》译介到英语国家,虽然其中有少量的误译,但是由于生活环境、生活经历的差异,也不可避免。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要想更好地译介中国文学,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除了关注语言层面上的翻译,我们要更多地把视角转向到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上来,才能翻译出更多迎合目标读者的作品,达到传播文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9(6):45-56.
[2](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译.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138.
[3]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4,137.
[4]曹顺庆.翻译的变异与世界文学的形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1):126-129.
[5]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2.
[6]张文生.历史学与民俗学关系析论[J].史学理论研究,2003(2):86-90.
[7]萧红.呼兰河传[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6:49,76,115,128,142,184.
[8]Howard Goldblatt: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 Tales of Hulan River [M].Boston: Cheng & Tsui Company, 2002:144, 170, 171, 207, 221, 232, 267.
[9]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50,56.
[10]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的研究意义[J].宗教学研究,2013(1):1-21.
[11]George Gallup. Jr. & Sarah Jones. 100 Questions & Answers: Religion in America[M]. Princeton: Princeton Religion Research Center, 1989:30-31.
[12]刘澎.当代美国宗教[M].北京:社會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0.
[13]王凯北,傅治夷.从地狱观看中西方宗教文化差异[J].海外英语,2016(1):158-159+169.
[14]潘倩菲.实用中国风俗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532.
[15]汤叶舟.以《周公解梦》和《梦的解析》为例研究中西方释梦差异性[J].文化学刊,2015(11):84-86.
[16]肖勇,李丹.诗歌翻译质量评估框架的构建[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99-106.
[17]黄伟龙.第三空间中的文化杂合——汤亭亭《女勇士》文化翻译研究[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19-122.
[责任编辑]甄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