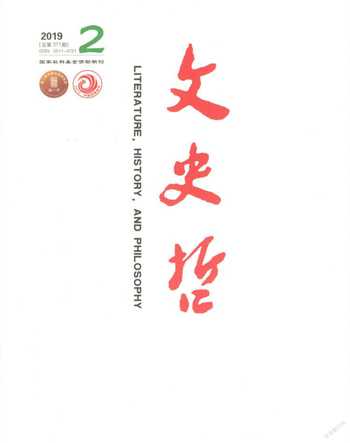社团传播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品格的影响
泓峻
摘要: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初十几年时间里最主要的组织文学生产的平台,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输入与传播,主要也是由身处文学社团之中的理论家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社团,与中国古代文人结社这一传统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理论生产方式及文学观念通过社团传播这一途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早期形态及理论品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多采取论战性的姿态与论争性的理论形态,许多文章文风生动活泼,与文学创作实践、文学批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影响力;与此同时,社团传播也使得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系统性、学理性及理论深度受到一定影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社团传播;文学传统;文学研究会;创造社
一
诞生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最初的十几年里,由文人结社而形成的文学社团,是其最主要的组织文学生产的方式。而在1920年代,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进入中国,被中国的理论家接受与传播的时候,也主要是经由文学社团这一平台完成的。一个理论家在当时流行的多种文艺理论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接受与传播的对象,而且在可能接触到的具有不同理论指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流派中,选择具有某一种指向的理论流派作为接受与传播的对象,并不完全是由理论家个人对文学问题的前理解与理论兴趣决定的。对多数理论家而言,他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所在的文学社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文学立场,以及特定时期文学实践的需要有关。而导致理论家在对所接受的理论进行解释时向某一方向发生偏离的原因,也往往与其所在文学社团的文学立场与文学实践需要有关。
“新文化运动”开始前后的几年间,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传入中国,但人们还仅仅把它当成是一种政治学说或经济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并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整个1920年代的中共领导人,包括对文学有很大兴趣的陈独秀、瞿秋白,在领导人的岗位上时,都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应付十分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国际政治斗争形势上面,根本无暇参与文艺战线的斗争,也没有认真关注过国际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状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更没有列入中共中央的工作日程上。瞿秋白虽然早年在苏联时关注过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实践,但他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实际上与他1931年初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王明等人排挤出政治局常委,在“赋闲”的状态下开始介入“左联”的事务有关。比较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才开始进入中国的。在当时,参与并推动“革命文学”论争的,主要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太阳社等文学社团,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体,也是身处文学社团中的理论家。
据文学史家考证,最早提出“革命文学”这一主张的,是文学研究会:1921年7月30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郑振铎就发表了《文学与革命》一文。文学研究会也是中国较早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学社团之一。1924年,郑振铎出版了《俄国文学史略》一书,这是中国系统介绍俄国文学的第一本专著,书中列专章介绍评述了对后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理论观点,并高度评价了高尔基的创作成就及其文学思想。茅盾在1925年的《文学周报》上连续发表了长文《论无产阶级艺术》,主要结合苏联的文学实践,对无产阶级艺术的发展情况,以及无产阶级艺术的形式特点及其思想内涵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文学研究会的理论家之所以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生兴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立场与观点,同他们最初提倡的“写人生”“人道主义”“血和泪的文学”“泛劳动主义”“文学是一种严肃的工作”“自然主义”等文学理念之间有着可以对接的地方。茅盾是文学研究会最重要的理論家,同时也是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在建党初期(同时也是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虽然茅盾也在尽力为党工作,但在文艺主张上,他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文学观。而茅盾从早年宣扬自然主义文学观,到后来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并不使人感到突兀,这主要是他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中提取了现实主义的立场与方法,从而与之前的文学主张很好地实现了对接。在接受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候,茅盾的身份主要还是文学研究会的理论家,而不是中共文艺思想的代言人。没有资料显示,茅盾是受到党组织的指示,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工作的。而据茅盾自己回忆,文学研究会刚成立时,他在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只是因为其工作环境的方便,受党的指派,承担了外地党组织或党员与在上海的党中央之间联络的工作。[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784页。]正是因为茅盾代表着文学研究会的理论立场,使得他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创造社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创造社是在国内发动“革命文学”论争的主要文学团体。而早在挑起“革命文学”论争之前,创造社中的一些人物就开始接触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来的创造社领导人在介绍创造社的历史时,常常强调国内第一篇将文艺问题与阶级斗争学说联系起来的文章是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这篇文章发表在1923年5月27日《创造周报》第3号上。尽管他们也承认,郁达夫当初在文章中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还存在较大差距。创造社的灵魂人物郭沫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早的记载是1924年,这一年,他在日本翻译了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1925年,郭沫若宣称完成了文艺思想的转变。[ 宋斌玉等:《创造社十六家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23—24页。]1926年,他相继发表了《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两篇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宣扬“革命文学”的文章,提出“革命文学”“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等主张。而在从事上述工作时,郭沫若并不是中共党员。他直到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之后才加入中共。创造社后期的理论家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等人,在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在1920年代中期,其思想深受当时在日本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派“福本主义”的影响。而随着他们在1927年回国,作为创造社的新生力量,以“革命文学”为口号发起对鲁迅、茅盾、张资平等人的批判,这种带有强烈的“左倾”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被带进了国内。这时候,他们也都不是中共党员。创造社后期的骨干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李铁生等人加入中共,是在1928年中共宣传部门的领导人潘汉年出面调停左翼文学内部关于“革命文学”论争,阻止他们对鲁迅、茅盾等“五四”作家进行攻击的时候。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说文学研究会的理论家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提倡等等,与他们之前的文学主张在许多方面可以契合的话,那么创造社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则是在经历了一次十分明显的转向,对自己前期的许多文学主张进行了大胆的否定之后。这种转向,当然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对创造社成员思想的影响有关,但同时也与创造社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在经历了一次低谷之后,需要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提倡,在国内的文坛上重新树起自己的旗帜,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有关。
创造社在酝酿的时候,曾提出国内没有纯粹的文学社团,因此要填补这方面的空缺。他们最初提出的口号,以及给国内文坛留下的印象,是唯美主义的,专心致力于文学艺术发展的。创造社的这一文学姿态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针锋相对,在刚提出时曾经对国内文学青年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使创造社获得了最初的成功。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创造社又面临了很大的生存困境,急需为自己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造社元老郑伯奇在日本与一帮年轻人一拍即合,决定回国发起一场“文学革命”。这场“文学革命”要将包括鸳鸯蝴蝶派作家、新月派作家、文学研究会的主要作家,以及鲁迅这样的文坛领袖,都作为革命的对象,试图借助于对封建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小資产阶级文学的全面批判,重新确立创造社在国内文坛的地位,再造创造社早期的辉煌。而且,他们一开始实际上把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了左翼文学内部,与太阳社、文学研究会以及鲁迅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因此,1920年代中后期的“革命文学”论争,很大程度上是文学社团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它既不是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文艺运动,对于中共的文艺事业发展也有不利的地方,以至于到后来不得不由中共出面中止了这场论争。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入中国并得以传播的过程中,除茅盾(1921年入党)、蒋光慈(1922年入党)等极少数中共早期党员外,许多人,如鲁迅、郑振铎、冯雪峰、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以及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后期成员冯乃超、李初梨等人,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都不是中共党员,有些人终生也没有加入中共。即使是像茅盾、蒋光慈这样的中共早期党员,在1920年代开始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也主要是以文学家的身份在活动。整体上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20年代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并不是基于政党理论宣传的需要,也不是在政党的直接领导与策划下进行的,文学社团是19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接受与传播的最主要的平台。这种状况,到1931年“左联”成立以后,才有所改变。
因此,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怎样被本土理论家接受与传播这一问题时,那些本土理论家所在的文学社团的文学立场与文学实践需要,也是一个应该被考虑到的因素。在对诸如茅盾、成仿吾、冯乃超、蒋光慈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进行个案研究时,必须考虑到他们作为特定文学社团的理论代言人这一身份。而像鲁迅这样的理论家,在文学社团林立的现代文学史早期,虽然选择了相对独立的姿态,与文学社团之间的关系不像茅盾等人那么密切,但是,一方面,在192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他仍然属于语丝社,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选择性接受,与语丝社的文学立场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他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兴趣,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者与传播者,与其在“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试图回应来自创造社、太阳社这样的文学社团的批判有关,这也可以视为文学社团这一文学组织方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影响的延伸。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的接受与传播主要借助文学社团这一现象,与同时期世界上其它国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成与传播相比,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在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初来源地的苏联、日本和欧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或者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指导乃至于直接领导,或者是作为相对独立的学者,以较为纯粹的学术态度从事理论工作的。而在此之前,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也不像大多数中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那样,主要以文学社团代言人的身份,根据文学社团自身的现实需要从事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初在中国被接受与传播时,其接受与传播平台的特殊性,是值得关注的。
二
实际上,通过文学社团这一方式组织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艺理论研究在内的文学生产,并非是现代作家的独创,而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这一传统的延续。而当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经由文学社团这一中国故有的平台进行理论选择与理论传播时,这一平台背后的传统因素,必然会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早期形态及之后的理论品格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这种影响的过程及其具体表现形态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把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学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社团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2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蓬勃发展的时期。以1930年代初期“左联”的成立为标志,此后文学社团这一组织形式经历了一个被逐渐改造、淘汰的过程。到了1940年代,文学社团已经走向衰落。而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带有太多“前现代”的文化基因,因而并不符合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的方向。一位西方学者曾敏锐地指出:“民国时期的文学与传统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在生产的文本中显然并不多,但却大量存在于文本生产所处的社会语境里。无论什么样的文体的生产者,都共享着流行的在文学社团工作中的习性”。 [ [荷兰]贺麦晓:《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7页。]也就是说,文学社团这一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结社传统的组织形式的存在,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在文学观念、文体形式等方面比较多地借鉴西方资源的同时,作家的写作方式、相互之间的交往方式,以及不同文学主张间进行竞争的方式仍然受到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
现代文学学界在关于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中,为证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比较多地强调了现代文人结社与古代文人结社之间的差异。比如,有学者就认为,“新文学”与“旧文学”在文学运动方式上的差异“几乎是本质上的”,因为古代文学史上的“公安派”、“桐城派”等文学组织模式,本身有着明显的地域上的局限性。而“新青年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派”、“现代评论派”等文学社团,则打破了地域的隔绝,形成了地域之外的新空间。“现代文学活动是在这种新的空间下开展,现代的文学流派就是在这种空间中生长出来的,现代的文学运动也是在这种新的空间中得以形成与推广的”。[ 钱文亮:《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74页。]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现代文学社团与古代文人结社传统之间的关联,是不全面的。
其实,从一些现代文学社团的人员构成上,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基于同乡关系的联结,如语丝社主要成员周氏兄弟、孙伏园、孙福熙、钱玄同等人都是浙籍作家,且多为绍兴人;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以山西人为主干;浅草沉钟社的成员都来自四川等等。这表明,古代文人结社常常依托的同乡关系,在现代一些文人结社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文人结社也不全是以同乡关系为依托的,其结社活动的地点也不一定就在社员的家乡,其中有些文人结社也依托中心城市。因此,早在宋元时期,就形成了北方以开封、洛阳为中心,南方以临安、苏州为中心的文人结社版图。古代文学社团成员之间的联结,则在同乡关系之外,也有依托于官场同僚关系、科场同年关系或师生关系的。有些时候,使不同的成员走到一起的,主要是共同的文学兴趣或文学主张。如引发后世文人纷纷仿效的唐代“香山九老会”就以白居易为核心,在洛阳这一“京畿之地”形成。当时,白居易仕途受挫,心灰意冷,终日与朋友酌酒赋诗打发晚年时光。“九老会”的成员多为白居易的官场同僚,另外也有僧人加入其中。古代社会由身居同一文化中心的文人,出于共同的文学兴趣结成的文学社团,与现代文学史上同处上海,或同处北京的文人聚集起来形成的文学社团,以及在大学校园里,由同事、师生关系结成的文学社团之间,就其结社的缘由而言,并无二致。而在明朝末年,已经形成过复社那样的跨越苏、浙、赣几大区域,社员人数达几千人的文人社团。这样的社团,完全打破了地域局限,而且其所跨地域之广,社员人数之多,社团内部结构之复杂,并不亚于任何一个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型社團。
因此,古代文人结成的文学社团,实际上是现代文人结社时可资借鉴的样板。只不过在现代文学社团运行过程中,一些古代社会没有或者是发展得不太充分的因素,如商业化的出版机构与现代报刊,介入到了文学社团的运作之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文学社团与古代文学社团间的差异肯定是存在的,但其间的传承关系也相当明显。许纪霖在谈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交往方式时曾这样讲道:“即使在现代城市公共网络中,传统的血缘、地缘自然关系虽然不起主导作用,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发挥着其潜在的影响,宗亲关系、同乡关系,深刻地镶嵌在现代都市的人际交往中,与现代的文凭身份等级、意识形态认同和都市地域文化交织成一个巨大复杂、相互缠绕的交往关系网络。”[ 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页。]现代文学史上以文学社团为依托形成的作家之间的社会联结,同样是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状态,其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
三
中国的文人结社活动,从唐代开始,由宋入元、在明代达到高潮。入清之后虽遭统治者的禁绝,但仍然持续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逐渐走向衰落。到了晚清,一方面革命党人模仿明末清初的政治社团模式建立了许多反清组织;另一方面,受明末复社等文人社团的直接影响,以“南社”为代表的文人结社活动也开始活跃。这是1920年代文学社团层出不穷的重要历史背景。因此,如果说1920年代的文人结社活动是对中国古代文人结社活动的继承的话,这种继承是有选择性的:它更多地继承了明代中后期文人结社的传统。对于文学主张十分明确,同时还持有明确的社会变革诉求或明确的政治主张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等文学社团来讲,更是如此。
有学者把明代的文人结社分为四个时期,(一)元末明初时期;(二)“台阁体”兴盛时期;(三)文学复古时期;(四)党争时期。明代文人结社的高峰出现在后两个时期,即明代的中晚期。就其特点而言,第三个时期“文人结社伴随文学复兴而兴盛,社团性质亦因此有了改变,由前一时期怡老诗社为主流发展为这一时期以文学性团体为主流,在文人结社基础上文学流派迅速兴起。”到第四个时期,“在前一时期卷入文学论争的文人团体至此卷人晚明政治风潮之中,党争与结社一体化,文人结社的性质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何宗美:《明代文人结社综论》,《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 ]明代中晚期,工商业在江南许多城市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市民阶层兴起,各种思潮渐趋活跃,文坛上流派林立,新说迭起,政治上则党争不断。文学社团对于当时许多社会思潮的传播、文学流派的形成、甚至是朝廷的政治走向,都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这种情况,与现代文学史上最初十几年的状况的确有很多类似之处。
重视理论建设,具有鲜明的文学主张,是明代中晚期文学社团的一个重要特征。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诗社,旗帜鲜明地倡导复古主义,并形成了系统的复古主义理论;而归有光参与的南、北二社,则大力推行其“唐宋文学”主张,并有不少理论建树。另外,像“性灵说”“童心说”等进步学说的产生,都有文学社团的背景。有不少文学社团在立社之初就将文学主张的宣扬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或在立社宗旨中表明,或在社约中明确规定下来,表现出鲜明的文学倾向。
明代中晚期的文学社团另一个特点就是用社团特定的文学主张与文学立场品第作品,在社员间相互标榜。作品的品第与标榜对于社团人心的凝聚与社团统一的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在品第、标榜这些具体手段之后,所体现的无疑是一种群体精神,它们在维系、调节群体内部关系,使群体保持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手法犹如润滑剂,使诗社活动这部‘机器’处在一种良性互动的状态中。在此基础上,诗歌流派的脱胎而成,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 13—14 页。]
另外,明代中晚期文学社团往往是在十分复杂的文学环境与政治环境下,通过激烈的理论论争与政治斗争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尤其是到了第四个时期,党争与结社一体化,文学立场与政治立场的表达、文学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争夺往往不分彼此,观念、立场的论争往往达到白热化程度。这也导致当时的文学批评往往十分尖锐,甚至充满偏激。因此,郭绍虞先生曾这样讲:“我总觉得明人的文学批评,有一股泼辣的霸气。他们所持的批评姿态,是盛气凌人的,是抹煞一切的。因其如此,所以只成为偏胜的主张;而因其偏胜,所以又需要劫持的力量。这二者是互为因果的……我们统观明代的文学批评史,差不多全是这些此起彼仆的现象。易言之,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13页。]
明代中晚期文坛重视理论建设、文学社团内部成员间相互标榜,社团之间相互竞争甚至相互攻击,文学立场与社会变革立场、政治立场相互交错的现象,在1920年代的文坛上,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四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造社是一个在不断地与国内文坛其它社团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显示自己存在的文学社团。它在成立后不久,就首先挑起了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之后,与其它社团的一次次论争,贯穿了创造社十年的历史。对创造社而言,挑起论争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生存策略。
创造社成立时,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就是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在1921年成立后,吸纳了“五四”以来大多数最重要的“新文学”作家。而且,在它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成为向文坛推介文学新人的最重要的平台。文学研究会在刚成立时,确实像创造社后来所攻击的那样,是具有“包办国内文坛”的雄心的。它在组织框架上采用的是“工会”式大联合的形式,在成立宣言中就声称,要建立覆盖全国,对一切文学创作者开放的“著作工会”,作为“同业联合的基本”。[ 《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资料》,第3页。]这种社团运作模式,有着南社的影响,而南社的模版则为明末的复社。尽管茅盾后来讲,这种“著作同业工会”决不是“包办”和“垄断”文坛,但当创造社的年轻人试图进入国内文坛时,却发现文学研究会内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来的老作家、已经成名的新作家、刚刚崭露头角的作家,以及渴望成名的文学青年之间的等级关系。这就使得刚刚开始写作的创造社的年轻人感到压抑,从而产生了強烈的在文学研究会之外另起炉灶的冲动。但是,还在日本求学的创造社成员,根本没有文学研究会那样充足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尽管他们凭着与时代精神相呼应的浪漫热情与反叛精神,以及骄人的文学业绩,在1920年代之初那样一个新事物新思想不断涌现的时代,赢得了许多青年人的同情,取得了短暂的辉煌。但两、三年之后,经济上、政治上、人事关系上的各种压力与困难使这个社团已经难以为继,走向低谷。在这种时候,借助于在国内提倡“革命文学”这种更具反叛意味的文学举动,创造社把自己再一次推向了文坛核心。
在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几个比较重要的文学社团除了有自己最权威的作家之外,也都有一个或多个在社团内部地位很高的理论家——文学研究会有周作人、茅盾,创造社有成仿吾,新月社有梁实秋、饶孟侃,语丝社有鲁迅、周作人,太阳社有钱杏邨、蒋光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920年代的文坛像明朝中晚期的文坛一样,一个文学社不仅要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绩立足,而且还需要有人能够把自己社团的文学主张用理论的方式表达出来,将自己社团的代表性作家,以及新人新作,以评论的方式推介出去。同时,还要有人在社团之间的论争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占据舆论的上风。这些人大多身兼理论家、批评家、作家三重身份,他们在阐明社团的主张、推出自己的作家,以及在社团之间的论战中,起着只从事创作的作家们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即使他们创作水平不高,或者在成为理论家后很少再从事创作(如创造社的成仿吾),也会与重要作家一起,被视为社团的灵魂人物。
现代文学初期的这种生态,对现代文艺理论,特别是192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曾经有不少学者指出,现代文学史上包括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在内的文学社团,其所提出的文学主张,比如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与写实主义,创造社早期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其实并不能代表社团全部的创作倾向。从创作的具体情况而言,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的分野远没有那么明显。绝然对立的文学主张的提出,以及围绕这些主张展开的激烈的争论,实际上是为了借此扯起属于自己的文学旗帜,显示自己在文坛上的独特存在。郭沫若后来也承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和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自传》,北京:求真出版社,2010年,第261页。]而许多影响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文章,就是文学社团在自我标榜与相互论争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
茅盾在1979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1920年代文坛不同社团流派之间论争的情况。他说,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三、四年的时间里,“不得不同时应付着三个方面的论战,一是与鸳鸯蝴蝶派,一是与创造社,一是与学衡派”。接下来,他具体回顾了与创造社三个回合的论争,并认为论争的双方虽然是“一条路上走的人”,但论争涉及的问题则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立场密切相关——作品是作家主观思想意识的表现呢,还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创作是无目的的无功利的,还是要为人生为社会服务?在这篇回忆录中,茅盾列举的自己及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这些论争中所发表的文章有十多篇。[ 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文研会资料》,第784-809页。]而当我们翻开创造社的历史时,会发现自始至终,创造社成员的理论批评文章,包括后期创造社谈论“革命文学”的文章,几乎都是参与文学论战的产物。这其中包括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麦克昂(郭沫若)的《桌子的跳舞》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生成的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文章。与此同时,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文艺与革命》等著名文章,也是在论争中产生的。
五
以深具中国自身文化特征的文学社团这一组织形式为主的接受与传播活动,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品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的是積极的,也有的可以视为是负面的。
从正面看,它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开始就与文学实践密切结合,对文学创作实践具有强烈的介入性与切实的影响力。
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建构三位一体,而且理论观点与理论立场常常在文学批评中呈现,本是中国古代作家写作的常态。这种状态在现代文学建立之初得到了延续。1920年代中国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几乎都同时从事创作与文学批评。他们当中,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顶尖的作家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等。另外一些理论家,如瞿秋白、冯雪峰、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人,虽然文学成就不是很高,但也都有从事文学创作的经历,而且最初都是从文学创作入手而进入文坛的。无论是前一种理论家,还是后一种理论家,他们都身处一个或多个文学社团之中,有着切身的文学创作体会,对于新文学作家,对于当时文坛上的各种现象与出现的各种问题十分熟悉。出于社团之间竞争与论战的需要,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绝大多数都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纯学术化的介绍与阐释,而更多是借助于对作家作品与文坛现象的分析与批评,阐发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其中有些文章还是以杂文这种文体形式,或者是富有感染力的演讲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些文章,一方面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与立场,另一方面也品评了作家,对文坛上出现的各种现象与各种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与立场,对作家与文坛的发展方向有着很切实的影响。比如,文学研究会成员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1928年发表时,正值“革命文学”论争的高潮期,创造社成员有人在发表的文章中对叶圣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茅盾借此机会写出长篇论文《读<倪焕之>》,称赞这部小说是一部“扛鼎之作”,并回顾了“五四”以来的文学发展道路,阐明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充分肯定了叶圣陶对新文学的贡献。茅盾对叶圣陶及这部作品的充分肯定,对作家本人及这部作品文学史地位的奠定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社团传播的积极影响还表现在,由于许多文章都是在社团论争中产生的,论战性的理论姿态,特别是在文艺论争中创造的杂文这种文体形式,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的魅力,起到了帮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好地传播,增强其社会影响力的作用。论争性的文章往往观点尖锐,立场鲜明,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针对性,在批评与反批评的一次次往还中,许多文章都能够在文坛引起很大的关注与广泛的反响;论争本身,也往往会成为文坛上轰动一时的文学事件,吸引许多人参与其中。1920年代后期,中国“左翼”文学之所以逐渐地占据了文坛的中心,一方面固然与其文学创作实绩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这些具有“左翼”色彩的文学社团中的理论家们通过“革命文学”的论争产生的广泛影响有关。当时许多出版商愿意冒政治风险与“左翼”文学组织合作,印刷出版“左翼”文学组织的作品,包括理论性著作与刊物,除同情革命外,也有人是看中了这些出版物的广泛影响,以及由此得到的很好的商业回报。
然而,社团传播的途径,尤其是围绕社团间论争进行的传播,也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在论争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与把握,显然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不同的文学社团由于具体的理论倾向不同,因而在接受与解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就更愿意选择那些与自己社团整体的文学立场一致的理论。
艾晓明在《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一书中,曾注意到1920年代中期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刚开始传入中国时,“蒋光慈、茅盾、郭沫若、鲁迅这些不同文学社团的代表人物,各自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或开始思考苏俄文艺论战的基本问题”。[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8页。 ]温儒敏先生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认为,受苏联不同倾向的文艺理论影响,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派:一个是“自动论派”,着重文学的认识功能与宣传功能;另一个是“决定论派”,强调文学反映现实,并要遵行文学本身的规律。就中国而言,创造社、太阳社主要受“自动论”一派影响,理论来源主要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及其后的“拉普”,其中以波格丹诺夫组织生活论影响最大;而论争的另一方鲁迅、茅盾以及一部分“语丝派”作家,则比较倾向于“决定论”,从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沃隆斯基等人的理论中吸取过有益的成分。[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
除苏联外,在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入中国的另一个基地是日本。对于日本理论的接受,中国的学者也有着明显的基于社团先在文学立场的选择性:创造社的理论家接受的基本上是“福本主义”的文艺理论,这一派文艺理论本身就受到苏联“岗位派”、“列夫派”以及后来成立的“拉普”的文学观点的影响,偏重于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以及文学的宣传功能;而太阳社成员蒋光慈、林伯修等人,则对藏原惟人的“新现实主义”文艺观比较感兴趣,因为藏原惟人的文学主张不仅强调“用无产阶级前卫的眼光看世界”,同时也强调文学是生活的表现。而是否认可“文学是生活的表现”,正是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的分歧所在,也是他们曾经发生论争的原因。与此同时,鲁迅等语丝社的成员也对藏原惟人的理论感兴趣,因为藏原惟人的文艺理论建立在批判“福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强调了认识生活与客观表现生活对于文学的重要性。
基于自身文学立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选择,导致了文学研究会、太阳社、创造社、语丝社所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自己先在的文学立场的延伸。他们不仅从当时苏联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中选择了符合自己立场的理论派别进行介绍,而且在介绍的过程中,还对一些理论流派的观点进行了符合自己立场的简化与改造。这种抱着各取所需的态度进行的理论选择与理论改造,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初期出现,不利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完整的、系统的理解与把握。
至于郭绍虞先生所批评的明代文人在表达自己观点时那种“泼辣的霸气”“盛气凌人”的作风,以及“抹煞一切”的“偏胜的主张”,在文学革命论争中,也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对于这一问题,现代文学史研究已经形成共识。而对这种情况产生的深层原因,郭沫若在后来回顾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当时的论战时讲得十分透彻,他说,“在我们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养成的旧式文人相轻,更具体地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自传》,第261页。]
193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了延安时期,以社团为主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形式已经得到了改变。“左联”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就已经开始在政党的指导与规划下展开;到了延安时期,更是建立了鲁迅艺术研究院、抗日军政大学等教育机构,随着教学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在课堂上进行传播,因而产生了一批职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与翻译家。但是,之前文学社团传播时期的正面的影响与负面的影响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消失。因此,在考察1920年代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时,传统的文人结社这一形式的影响,仍然是一个应该考虑的因素。
[责任编辑 刘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