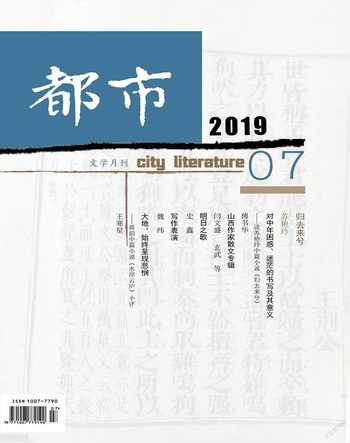草莓之歌
薛振海
翅膀
小时候,妈妈给我一双塑料翅膀。她说,背上它,你会飞得更高,走得更远。那时,我的脚下是无边无际的泥泞与野花,头顶是甜得发苦的云朵。我发誓,一定要找到翅膀的故乡,把翅膀还给她。妈妈的呼吸充满死亡的气息,我听到身后长长的叹息。
长大后,世界给我一双钢铁翅膀。她说,戴上它,你会睡得更沉、更实,永远不被侵扰。那时,我的四周全是一望无垠、赤身裸体的男女。他们躲在翅膀后,追逐着、嬉闹着,把时间统统杀死在翅膀坚硬的羽翼下。妈妈说,他们不会长大,你也不会长大,加入他们吧,祝福你!妈妈的呼吸已被死亡的利箭钉在原地,我听到渐渐冷却的胸怀下含混的喘息声。
今天,我已没有翅膀。我坚决抛弃了它们,只剩一具生机勃勃、喘着粗气的肉体。我听到妈妈的哭泣,听到四周的男女吃吃吃地冷笑。我上下打量着这一具更加一无所有、赤身裸体的肉体,不,不,它还冒着热气,还未冷却到只剩被死亡蔑视的呼吸。它低头,拼命擦拭自己的脚踝与胴体。我问他,你是要赶回翅膀的故乡,重新找回翅膀?还是要寻觅可以休憩的钢铁翅膀?他的目光里只有坚毅。这时,我已听不到妈妈的呼吸,再也得不到她的祝福!
我与肉体紧紧相拥。明白了,出生以来我从未拥有过一双属于自己的翅膀。只有肉体深处才能长出反对死亡、逃离死亡的翅膀,才能把肉体带到辽阔、温暖的远方,但绝不是什么故乡。翅膀永远没有故乡!如今,我一遍遍擦拭着肉体,听到从肉体深渊传来阵阵悸动———爱与勇气的呼吸,而不是妈妈微弱、单调的呼吸。它们一定会长出一双崭新的翅膀,一定会把肉体带到一个新世界!
冷时代
十一月把所有的热压榨、再压榨,推向一个出口:时代有多热,你就有多冷!
对果实来说,腐烂显然低估它重新起身的能力。
把寒冷锻造成熊熊燃烧的命运之火,是短尾鸭与水和解的秘密。
在多么喧嚣的酷热中梦游。你千辛万苦编制的非理性之筏,永远找不到抛锚的港口。
冷———没有喙却刺耳尖叫的鸟,不能翻身却游移不定的鱼,丧失欲望却鼓吹梦想的肉体,一尘不染却冒烟的空气,一览无余却只生产废品的果冻工厂,没有主人却川流不息的筵席。一个只生产冷出售冷的帝国!一个只信仰幻象的帝国!
戈多你好!外卖小哥你好!
没有底片的世界,把词语之唇埋得更深。
没有影子的时代,请听亡灵喋喋不休的布道。
一种冷把你裹得更紧!是时候了,把寒冷铸造成更多的精神之盐!
土豆花
十岁时,我是泥土下跳舞的娃娃,嘴唇刚好吻到天空。天空蓝得叫人发慌,似乎每天要我起立,准备迎接并不存在的太阳。太阳也是泥土中跳舞的娃娃,手拉手,没有家乡。
二十岁时,我是泥土下练习飞翔的朝霞,嘴唇已经咬破天。十岁时,我是泥土下跳舞的娃娃,嘴唇刚好吻到天空。天空蓝得叫人发慌,似乎每天空。天空渗出殷红的血,一大朵一大朵血红的花教育我:生命是时明时灭的灯盏,需要你终生点燃。但头顶的收割机昼夜割呀割,你眼里的朝霞从未来得及发芽。
五十岁时,我是泥土下沉睡的侏儒,嘴唇已被天空烤得发黑。天空运来阵阵乌云,我收拾行装,毁掉胎记,用泥土把自己埋得更深更深。一阵风吹过,我就老了百岁。一阵雨飘过,我再也不会思念那些长不大的跳舞的娃娃。
八十岁时,我是泥土下热爱命运的一团烂泥,嘴唇与泥土融为一体。天空像转瞬即逝的一个幻象,看不清,道不明。我既不赞美也不诅咒生命,坦然接受腐烂命运的捶打。身体空空,混沌又盲目,仿佛废弃千年的仓库,等待彻彻底底地融化,彻彻底底地消失。
零岁时,我是泥土下哼着歌谣的土豆花,嘴唇已被天空堵死,像随时奉献自己的战士。“土豆花,土豆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天空一无所有,空得令人抓狂。幸好娃娃、朝霞、侏儒、烂泥已经腐烂,幸好我又可以重新发芽。芽倒长天空下。天空如镜,倒映它痛得发红的根须,如根根铁丝网把所有的死亡封锁。土豆花,土豆花,与死亡赛跑的花,义无反顾的战士,你的生命该怎样计算?
奇迹:冰封生活
唯一的奇迹是冰下一翕一开的肺叶。冰封如盖,呼吸是你仅有的财产,活着的证明。天丢了,地丢了,躯体丢了。呼吸如巨大的风扇抗议:变小点,再小点,直到末日来临,像一粒尘埃!但你还有一个梦想———呼吸是唯一的发动机。如今,你的梦想垂挂天际,如绵延不绝的裹尸布,一动不动。感谢呼吸,让你还会对死亡投下最后一阵悲悯之沙!
唯一的奇跡是冰下不能闭合的眼睑。冰封世界,一个多么喧嚣又多么单一的世界,一个被噩梦层层包裹、童话般的世界。如果诗歌还能见证,那么靠梦幻喂饲的眼睑所能窥伺到的世界是多么单纯与无辜?如果只剩一双昼夜难以闭合的眼睑,那么你的瞳孔除了收获虚无和不断冒烟的灰烬还有什么?可怕的循环!一个受死神诅咒、蛊惑不断出走又不断回返的循环!父亲,借我一双眼睑!我知道,你从未从昏睡中清醒;也知道,你从未存在过!
唯一的奇迹是冰下原地踟躇的脚踝。冰越厚,你越狂喜,这样就有了出发的理由!又盲又老的你,只能感到脚踝下巴掌大的地方,这并不妨碍你一次次从心底燃起对乌有之乡渴念的烈火。一个被死亡唾弃、出卖而无法死去的人,除了脚下的路还有什么?一个死亡之路已经堵死的孤魂野鬼除了生还能奔向哪里?你听到眼睛烧得通红的黑暗天使,冰刀磨得嚯嚯巨响。收获的时刻到了!祝愿被冻得僵硬而犹豫不决的脚踝,祝愿一百年来聒噪不绝于耳、拖着长舌头的天使。今天,你收获的绝不仅仅是死亡!
唯一的奇迹是冰下阵阵忧伤后不肯停息的风。肮脏的母亲,肮脏的父亲,和我聊聊,在这个透明的世界上,你们都看到了什么!一代代软弱又无用的魂灵正被食蚁兽出售给贪婪的罐头包装商,一遍遍野蛮又武断的布道像墓志铭一样烧红了喉咙!大地好干净,缺少一个守夜人!谁不知道无所事事的守夜人只有一颗非人的心。他只能闻到阵阵忧伤的风后血腥的味道,而不知道风到底来自哪里。风刮着,从子夜到子夜,从冰上到冰下,从头顶到脚趾,你除了认识一颗冰封多年的枯老魂魄,对世界又知道多少?
活着的人不需要解释
活着的人不需要解释,因为他们的存在那么远,那么远!
那么远,那么远,仿佛他们不再存在,仿佛他们必须以一种非人的存在来证明不存在。他们如此稀薄,如此遥远,仿佛不在这个星球,完全可以抹杀,完全可以回避,完全可以当作一桩人间丑闻来祛除。
那么远,那么远,仿佛他们不再活着,仿佛活着必须要以死亡来证明。不要靠近,不要惊扰他们,否则他们一定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他们不再需要任何证明。如果一定要叫出一个名字,就必须抹除任何名字,前世的,今生的,仿佛他们只是一阵无名的风,如此沉默,如此拒绝,如此艰难。
那么远,那么远,仿佛他们黑色的背已完全可以撑起一个天空。在那个天空下,非理性的雪飘了一个又一个世纪,落满他们的一生,辨认他们,告慰他们,呼唤他们。而他们一如往常地吃饭、睡觉、工作、享乐,完全遗忘了还有另一个尘世,另一重生活。
那么远,那么远,仿佛他们已抵押了足够多的幸福才如此决绝。他们如此喧嚣地活着,如此挥霍地活着,如此任性地活着,仿佛人类的面孔再也刻不下第二个字,仿佛闭上眼就再也不会醒来。他们孤注一掷,拼命抓住每一粒尘土,每一句誓言,每一个鸽子,每一具肉体,仿佛生不过是一场没有结局的饕餮欢宴,只剩一个硕大无比的动作。
活着的人不需要解释,因为他们从未这样远,这样远!
废墟
———给佩索阿
我的一生是一座倒着生长的废墟。
我的理想是成为废墟主人。不吃也不动,像个游魂,守着她,永恒地占有她的欲望、梦想与荣誉。
那时,废墟生下我,我还有一颗纯洁无暇的魂魄、一副矫健柔韧的身躯、一双动物般清澈透明洞若观火的火眼金睛,但我注定是一个多余者、一个无父无母的弃儿,像个不得不躺在冰冷的泥地上、茫然四顾的幼兽。
我是大废墟下一座小小的废墟,气若游丝,无足轻重。我的命就是向废墟回归,就是倒着生长,最终回到不可分割、血肉模糊的废墟中,成为魂飞魄散、坚如磐石、冷若冰霜的一块血肉,结晶的血肉。
他们说,带着你的魂魄飞翔吧,远离废墟。我的魂魄虽然空空蕩荡,但上面打满黑色的封印,重得难以起飞。
他们说,带着你的魂魄回归大地吧,把你埋得更深,远离废墟远离你的命运。但我的魂魄长满不结籽的稗草,只能成为滋养废墟的废料。
我是一座生长千年的废墟,废墟里住满了失明的盲魂。既不渴望生长,也不盼望睡去,只希求永恒地占有这黑漆漆的废墟,成为既不会受孕也不会流产的一团血肉。
废墟外狂风怒号,废墟内的我夜夜笙歌,寻欢作乐。如今我对如影随形的魂魄已厌倦透顶,它同样对我恨之入骨。它曾苦苦哀求成为一团空气,一堆血水,但它毕竟是我的终生伴侣!我希望有一只巨掌能够平息它的愤怒,让其知晓它毕竟有一副人的面容!我还希望一阵阵强烈的吻降临,把它与我紧紧地搂在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