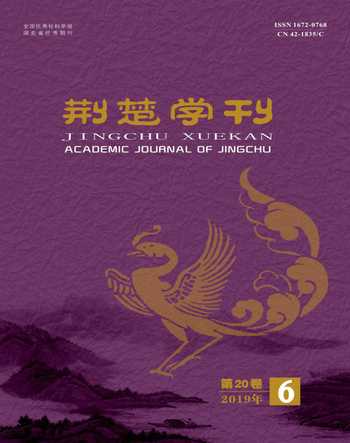《离骚》“筳篿”考论
马志垚

摘要:《离骚》“索藑茅以筳篿兮”中的“筳篿”一直是楚辞研究的难点之一,其旧说可归为四类,分别是“筳”为“竹”、“篿”为“卜”说,“筳篿”合释为名词“折竹”说,“筳篿”分释为“直竹茎”和“圆竹格”说,“筳”为“折竹占”、“篿”为“结草占”说,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当代楚辞研究者闻一多和朱季海有关“筳篿”的新探,得出的结论也未能使人完全信服。通过对四类旧说及闻、朱新解的全面梳理和辨析,并在闻一多和刘永济论争的启发下,进而结合朱季海的研究成果,得出“筳”为动词,“篿”为名词,“筳篿”为动宾结构,合释为“折竹六寸”的推论,以期较合理圆满地解决这一疑难问题。
关键词:《离骚》;筳篿;古注;闻一多;朱季海;考论
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19)06-0016-07
《离骚》之注本,现存最早的是王逸的《楚辞章句》。王注较于后世诸本,和屈原生活的时代相去未远,按理说其阐释最贴近作者原意,但是它对于《楚辞》各篇作者和创作背景的说解,以及某些字词的训诂、章节的分割、义理的疏通还是存在着不少令人费解的地方。有关《离骚》中“筳篿”的种种新奇的说法和旷日持久的争论即由此而生。
一、古注“筳篿”四说辨义
“筳篿”古注众多,经提炼归纳,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分别为:“筳”为“竹”、“篿”为“卜”说,“筳篿”合释为名词“折竹”说,“筳篿”分释为“直竹莖”与“圆竹格”说,“筳”为“折竹占”、“篿”为“结草占”说。囿于时代所决定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四说的缺点都较为突出,不仅无法针对“筳篿”衍生的诸多问题提出圆满的解决方案,还大大地增加了“筳篿”一词的神秘色彩。以下对古注中“筳篿”四说之得失作简要评析。
(一)“筳”为“竹”、“篿”为“卜”说
该观点以王逸为代表。《楚辞章句》在“索藑茅以筳篿兮”句下注曰:“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篿。”[1]在王逸看来:“筳”即“小折竹”,作名词。“结草折竹以卜”是一个以动词“卜”为中心、“结草折竹”为状语的偏正短语。“筳”是否作名词有待考证,姑且不论,释“篿”为动词则令人匪夷所思。廖序东就指出:“王以‘篿’为动词,则‘索藑茅以筳篿’为连动结构。《离骚》并无此句法。”[2]按照王逸的理解,“索藑茅”为动宾结构,“以筳篿”为状中偏正结构,则“以”字构成介宾短语“以筳”作动词“篿”的状语。这样,“索藑茅”和“以筳篿”两个动词词组之间既无语音停顿、又无关联词语,正如廖序东所言,是不符合《离骚》语法结构之规范的。屈作中凡一句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短语,则必定用介词或连词“以”来衔接,如“擥木根以结茝兮”,“聊逍遥以相羊”。以此看来,王说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
廖序东认为王逸把“以筳篿”当作一个整体虽然不无道理,但他也忽视了可能存在的另一种情况:单独的名词“筳”也可以作动词“篿”的状语。秦汉典籍中不乏类似的例子,如《史记·商君列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中的“车裂”[3],《汉书·霍光传》“臣请剑斩之”中的“剑斩”[4],都是工具名词作状语的典型例证。从这个角度考虑,如果作状语的仅仅是“筳”而不是“以筳”,那么王说是否就合理了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以”的判断。若“以”作介词,则“索藑茅以筳篿兮”实为“索藑茅以(之)筳篿兮”,省略的“之”指代“藑茅”,这样一来,“藑茅”就与表示工具的“筳”相矛盾(1)。若“以”作连词,则同于“乘骐骥以驰骋兮”中的“以”,表顺下相承之义。依王说,“篿”可兼指“折竹”和“结草”两种占卜方式,但状语“筳”已经限制了“篿”在此处只能表“折竹以卜”的含义,与“索藑茅”无法构成顺承关系。所以不管王逸是否真的把该句理解为连动结构,他的说法都有失偏颇。
(二)“筳篿”合释为名词“折竹”说
该观点以颜师古为代表,也是学界的主流观点。《汉书·扬雄传》引《反离骚》“又勤索彼藑茅”句,孟康曰:“《离骚》云‘索藑茅以筳篿’。”颜师古注:“索,求也。藑茅,灵草也。筳篿,折竹,所用卜也。”[5]颜师古认为“筳篿”为名词“折竹”,不需要分释。颜说被汪瑗、戴震所继承,汪瑗云:“筳篿即今签挺校杯之类。摘草为卜,抽签掷校,至今尚有其法,皆巫祝之事也。”[6]又云:“即取藑茅而占之,又取筳篿而占之,再三反复,欲其审也。”戴震云:“小断竹谓之筳篿。”[7] 今人游国恩、陈子展、汤炳正、胡念贻、廖序东、熊任望、殷光熹、赵逵夫等也均持此论(2)。
戴震和游国恩皆将“以”释为连词“与”,那么依其所见,“索藑茅以筳篿兮”整个句子为动宾结构,“藑茅”和“筳篿”两个名词并列共同充当动词“索”的宾语。该情况即便是在所有楚辞作品中都十分特殊。首先,据廖序东统计,“以”字作连词可分为四种类型,而连接两个并列的名词的仅有一例“索藑茅以筳篿兮”[2]133-141,孤证难立,这使得“筳篿”为名词的说服力大大降低。其次,若“以”连接两个并列名词,则“索藑茅以筳篿兮”可通过层次分析法分为两层,即“索+(藑茅+筳篿)”,“以”属于第二层。这种情况在《离骚》其他“以”字句中也是很少见的。例如与“索藑茅以筳篿兮”相近的“驷玉虬以乘翳兮”,两句在结构上都是“动词+名词+以+并列成分”,但后者中的“以”显然属于第一层。再次,屈作中存在较多一般动词领起的“以”字句,无论“以”字在这些句子中或作介词还是作连词,句首动词的作用范围仅限于与其相接的名词,并不与“以”字之后的部分在意义上存在牵连。如“矫菌桂以纫蕙兮”,“以”为介词,“矫”的对象是“菌桂”,“纫蕙”所使用的工具则为经“矫”过的“菌桂”,与“矫”这一动作没有关系。而“索藑茅以筳篿兮”中动词“索”却与“以”后的部分不仅语义关联,且直接构成动宾结构。
以上特殊之处表明,从颜师古到游国恩所支持的“筳篿”合释为名词“折竹”说仍包含一些疑点,需作进一步的考量。
(三)“筳篿”分释为“直竹茎”和“圆竹格”说
该观点以方以智为代表。他先引《说文》“筟,筳也,繀丝筦也”,据“筟车,即纺车”推断“筳”是纺车上的“小筦”。又以《急就》中有“槫榼椑榹”得出了“槫与篿通,竹木异耳”,“其实篿圆竹器也”的结论。并认为“索藑茅以筳篿兮”之所以“并举而言”,是因为“筳为直竹茎,篿为圆竹格”。他还从语音角度切入,提出《六书故》中“音篿为徒官切”,“正与此合”。言其“以竹片围编而成,或以筥,或以圈,皆是也”[8]。方以智不但能够注意到字义之间的“同义互训”,从《说文》中发现“筟”与“筳”存在的联系,还敏锐地捕捉到其他典籍中的异文现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间接材料”的研究方法。
虽然方以智对“筳篿”研究创新颇多,但其观点本质上还是不脱前人窠臼。因为不管“筳篿”合释为“折竹”还是分释为“直竹茎”和“圆竹格”,他和颜师古等人一样,都认为“筳篿”是名词。这样,上文所论述的颜师古“折竹”说衍生的诸多疑点同样存在于方说中,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合理地回答“筳篿”的词性问题是讨论其词义的大前提,如果舍弃了这一点,结论必定难以稳如磐石。方说虽有纰漏,不可否认的是其对“筳篿”别具一格的注解仍具有较高的可供参证的学术价值。
(四)“筳”为“折竹占”,“篿”为“结草占”说
该观点以李陈玉为代表。他认为:“筳,是折竹为占;篿,是结草为占。篿法至今不传;篿即楚人所谓茅卦,今民间犹往往用之。索藑茅则是问篿,而并言筳者,犹言筮者动曰卜筮也。”[9]李陈玉的看法可以提炼为三个要点:其一,“筳”和“篿”都是动词。其二,“筳”和“篿”俱为“卜”义,不同之处体现在使用工具的差异上:“筳”用折竹,而“篿”以结草。其三,“篿”即茅卦,虽然“藑茅”和“筳”没有关系,但《离骚》之所以將“筳”和“篿”并称,是因为其与“卜筮”相类,属古汉语语法中“同义词连用”一种。
李说把“筳”和“篿”作为动词,从语法角度看的确比颜师古和方以智的“筳篿”为名词说更具说服力。《离骚》中不乏“以”字后两个相近动词连用的例子,如“忽驰鹜以追逐兮”。但把“篿”与“结草”联系起来不符合客观事实。首先,“篿”字在如今本《楚辞》中作“篿”,从竹而非艸,王逸和洪兴祖都没有提到其他异文。其次,“篿”及由“專”引申出来的新字中为有“蓴”与草相关,但该字同“莼”,没有“卜”义。王逸《章句》中注曰“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篿”,李陈玉很可能注意到了“藑茅”与“筳篿”部首的不匹配,但又拘于王说,坚持该句中涵盖“结草”和“折竹”二法,所以才“强为之”,将“筳篿”分释为两个动词,以达到既与句义相合、又不悖王说的目的。虽然古汉语语法中确有不少同义词连用的例子,但在没有足够多的证据可以证明“篿”与“结草”之间存在联系之前,谨防张冠李戴的错误还是有必要的。
“筳篿”古注诸说虽然不能够使人完全信服,但正是前人对真理孜孜不倦、永无止息的探索求实,为当代楚辞研究创立了高远的视野和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
二、“挺抟”说考论与“闻刘之争”提供的新思路
有关“筳篿”的讨论,在当代楚辞研究中也从未止息,最具代表性的是闻一多提出的“筳篿”即“挺抟”说。闻说不拘成见,着眼于探寻《离骚》异文,推断“筳篿”实际上是一声之转,相较于方以智的“因声求义”更进一步利用“声训”考证本字的研究方法。但因假设大胆、思维跳跃,“挺抟”说招致了一些批评,其相关问题也引发了闻一多和刘永济有关“命灵氛为余占之”中“占”是否可以替换为“卜”的论争。
(一)闻一多“挺抟”说考论
闻一多针对“筳篿”的含义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假设。首先,他列举《玉烛宝典》《艺文类聚》及五百家注《韩集》中存在所引“筳篿”作“莛蓴”的情况,说明“莛蓴”可能是“筳篿”在其他《离骚》版本中的异文。又以《汉书·扬雄传》和《后汉书·方术传序》中关于“筳篿”注文中均无“结草”二字证明“筳篿”和“莛蓴”两个版本并存的观点。其次,举《归藏·本筮篇》“蓍末大于本为上吉”一段,认为“古卜筮之具或用竹,或用草”。据“索藑茅”可以确定占卜工具是草,再结合“筳篿”从竹而异文“莛蓴”从艸,得出“莛蓴”应是本字的结论。最后,认为“莛蓴”双声连语,实为《卜居》中“端策”之“端”[10]。
从语法角度来看,闻一多以“筳篿”为动词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其一,《离骚》中“以”字连接前后两个动词或动词结构的句子不胜枚举。其二,王逸和李陈玉虽然对“筳”的理解有异,但在“篿”的认识上李陈玉还是基本因袭了王逸的看法。闻一多将“筳篿”合释为动词,可以说是对王李“动词派”的继承,与颜师古的“名词派”泾渭分明。其三,闻一多提出的“草竹并用,于古未闻”并非空言。周去非曾言及“南人茅卜法”:“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断之,以授占者,使祷所求;即中折之,祝曰,奉请茅将军、茅小娘,上知天网、下知地理云云。遂祷所卜之事,口且祷、手且掐……尝闻楚人篿卜,今见之。”[11]可见周去非是直接把“茅卜”当做“篿卜”的,并未提到所用工具“茅”之外还存在“竹”的情况。王夫之和朱冀也主张“藑茅”仅仅起着“筳卜”时“席地”的作用,否认该句中所谓的“茅卜法”的存在。王夫之曰:“筳,折竹枝;篿,为卜算也。楚人有此卜法,取瓊茅为席,就上以筳卜也。”[12]朱冀曰:“藑,香藑也。《韩诗》云,参差席香藑。茅,白茅也。《易》曰,籍用白茅。二物皆芳洁而柔耎,可以为物之藉,故先索取之以席地,而后用折竹以卜之也。总是大夫托物见志,以自明其芳洁耳。《集注》释以灵草,则同为卜具,与筳相混矣。”[13]
然而闻说并非毫无破绽。首先,从“筳篿”到“莛蓴”的跳跃很大。闻说举出的异文出自《玉烛宝典》《艺文类聚》和五百家注《韩集》,皆为引文,不见于各《楚辞》版本中,其可信程度不高。除异文之外,闻说坚持“筳篿”为“莛蓴”还有一些判断依据,如“此云‘索藑茅’,明是以草卜,故知下‘筳篿’字当从艸”[10]。仅仅因“藑茅”从艸而出于文义疏通的目的便草率变动“筳篿”的部首,这样的做法不能算是治学态度严谨的体现。其次,闻说称《汉书·扬雄传》和《后汉书·方术传序》注文中“俱无结草二字”,而注释音辨《柳先生集》中《天对》注文所引的王逸注也没有“结草”二字,因此疑别本“筳篿”字从艸,今本“筳篿”难解是由于“后人两合而并存之”导致的。闻氏以注文为据推测校对原文,不但方法本末倒置,而且所引材料亦难称实事求是,刘永济也曾指出这一点(3)。再次,闻一多建构起了“筳篿→莛蓴→挺抟→抟→揣→諯/端”这样一条逻辑链条。即便这些字词之间真的存在如此复杂的音义转换关系,以“筳篿”为“端”在语法上也是不能成立的。据《卜居》“詹尹乃端策拂龟”,及《淮南子·说林训》“筮者端策”[14],可知“端”作及物动词。若“筳篿”为“端”,则“索藑茅以筳篿兮”构成“动词+名词+以(之)+及物动词”,不符合楚辞语法。《离骚》中介词“以”表“用”时,其后皆跟“及物动词+宾语”的结构,如“折琼枝以继佩”,并不存在及物动词独立使用的情况。
综上,闻一多的“挺抟”说未能够彻底了结这一学界公案。
(二)“闻刘之争”的焦点与解决的新思路
有关“索藑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上下两句中,“占”与“慕”不合韵的问题从来都是楚辞研究者们重点讨论的对象。刘永济认为与其把重点放在“慕”字的拆解上,还不如直接改“占”为“卜”。这个观点招致了闻一多的批评。闻一多“深恐后人轻信”,便在《楚辞校补》中证明“占”大异于“卜”,两者不能简单混用。而刘永济在知悉此事后也撰文予以回应。他以王注中“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篿”和“乃取神草竹筳结而折之,以卜去留”均有“卜”字重申观点,且针对闻一多的“占”“卜”之辨,提出“赋家用字与散文家记事不同”的说法,认为“占”是名词,而“文家用字,动词可以作名词用,名词亦可以作动词用,原不必悉合训诂之例”,无论作“卜”还是作“占”,于义无别(4)。
“闻刘之争”表面上是“占”与“慕”不叶韵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实质上其焦点却是关于“占”与“卜”之区别以及在“命灵氛为余占之”一句中“占”是否可以替换为“卜”的讨论。第一个问题“占”与“卜”的区别刘永济已然给予详细解答。第二个问题是争论的症结所在,不但闻、刘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迄今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事实上,材料论证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纵使闻、刘罗列了大量的文献进行说解,由于《离骚》作为诗歌,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修辞设色和遣词造句的特点打破了传统散文语法的壁垒,使得这些努力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刘永济的观点不容易从正面证实,但从闻一多的角度出发,尝试探究该观点的缺失和纰漏,否定其可行性,不失为解决争端的新思路。“若藑茅以筳篿兮”与”命灵氛为余占之”前后衔接,若按照王逸的说法,“篿”为“结草折竹以卜”,那么“占”字就絕不可能替换为“卜”字,因为上文中已经提及“卜”,考虑到遵从叙事顺序和避免语义重复,“灵氛”所从事必定只能是与“占”不同且与其构成前后动作关系的“卜”。当然,上文已经提出了对王说的种种怀疑,这里仅仅是以王说为例而作出的假设。如此一来,“占”是否可以替换为“卜”的问题就转化为能否证明“索藑茅以筳篿兮”存在“卜”义的问题。先看“索藑茅”,关于“藑茅”扮演的角色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朱冀认为,“藑茅”所起的作用限于改善条件、增加占卜者的舒适程度甚至达到“托物见志”以“明其芳洁”的目的,并非楚人占卜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胡文英以“藑茅”为卜具,恰与之相对。不管“藑茅”是否为卜具,“索”字已经决定了其尚处在占卜之前的准备阶段,所以破解该句是否存在“卜”义的关键就落在了“筳篿”上。据周去非“南人茅卜法”,胡文英“楚中或折草、折竹、折注香,信手布卦,以占吉凶”[15],闻一多“古卜筮之具或用竹,或用草”[10]15,可以认为将草或竹折断是楚人占卜程序中主体部分。所以只要能在“筳篿”和“折竹”之间建立起直接关系,刘永济的观点自然不攻自破(5)。得益于朱季海《楚辞解故》的启发,下文将重点探讨的“筳”为动词、“篿”为名词说的理论依据。
三、关于“筳”为动词、“篿”为名词的假想与证明
朱季海探究“筳篿”的方法不同于闻一多的“因声求义”,而是利用字书中“同义互训”在形貌不同的字与字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寻找词义与“索藑茅以筳篿兮”语境相符合的“筳篿”本字。“筳”为动词、“篿”为名词之推论亦是在朱说的基础上提出。
(一)朱季海“珽專”说的合理与误区
实质上,朱季海在“筳篿”问题的探讨上属于颜师古一派,只是在“筳篿”本字的考证方面持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因为朱说所引用的材料较多,为了方便理清其中的因果关系,特列表1如下:
基于以上内容,朱季海认为:“盖珽者筳也……笏、簿、專,犹篿也,后世益文,乃以玉、象,别益之耳……要之筳篿之于珽專,本由一言孳乳,其形与名,皆起于折竹耳。《离骚》此文,正谓求灵草与折竹而卜之也。”[16]朱季海以“筳”为“珽”,“篿”为“專”,“專”“簿”“笏”古义相通,得出“筳篿”实为“珽專”、义同名词“折竹”的结论。虽然朱说材料翔实、逻辑严密,但依然属于颜师古将“筳篿”合释为名词“折竹”的范畴。颜说所包含的种种疑点,朱说仍不能提供合理解答。此外,《说文解字》中“專”作“六寸簿”[17],其他文献中却未见言及“六寸”这一疑似“簿”所具有的显著特征。而据《礼记·玉藻》记载,与“簿”同制的“笏”“度二尺有六寸”[18]。面对“簿”与“笏”尺度不同的问题,段玉裁解释为“六寸未闻,疑上夺二尺字”[19],朱季海也深以为然,但事实却还存在一种可能。从上表中的材料②可知,“簿”和“笏”同物而异名,《玉藻》“笏度二尺有六寸”说得已经很明确,那么“簿”的长度也必为二尺六寸。“笏”的使用人群非常广泛,既能“施于人事,用诸朝廷”,又能“以为卜具,且格于神明,用之齐民”[16]。这样一个常见的的东西,《说文解字》这样的字书不太可能犯将“二尺六寸”记为“六寸”这样的低级错误。如果不考虑传世造成的文本缺失,较合理的解释就是:“簿”的长度为二尺六寸,而《说文解字》所言的“專,六寸簿也”实际上说的是“專”是六寸长的一种“簿”,并非“上夺二尺字”。
尽管朱季海的“珽專”说未能圆通,但其所用的新方法与新材料却在一定意义上为探索“筳篿”最有效的解释奠定了基础。
2.“筳”为动词、“篿”为名词的推论
虽然朱季海失察于“專”和“簿”的长度区别,但综合朱说可以发现,“簿”由二尺六寸截为“六寸”便可称为“專”,这其中所包含的“折竹六寸”之义自然使人联想起来“折竹以卜”的“筳篿”。关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客观联系,可从多方面进行考察。
据上表材料④可知“珽”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一,出现和被使用的时间较早;二,体长六寸;三,便于握持。又由材料⑤可得,遵照礼制,天子所使用的称“珽”,诸侯和大夫使用的分别叫“荼”和“笏”,三者之间只存在材质上的差异。这就导致《玉藻》与《相玉书》关于“珽”之长度的观点完全牴牾。《相玉书》言“珽玉六寸”[18],便于握持,而《玉藻》认为“珽”为“笏”的一种,皆为二尺六寸。相较之下,还是《相玉书》更合理。据材料②中徐广《车服仪制》“古者贵贱皆执笏,即今手版也”的描述[20],“笏”在上古时期不是某件物品特定的称谓,而是如同后世的“手版”一样,为可以充当某种用途的一类物品的统称,不管是“珽”“筡”还是“笏”,只要用作“手版”,都可以叫“笏”。材料⑤中《方言·第十三》说“析竹为之筡”[21],《礼记·玉藻》注“是以谓笏为荼”[18]788,将原材料之“竹”易为“象”则“筡”就变成了“荼”,也佐证了早期“笏”的定义应该是非常宽泛的。《玉藻》中所提出的“笏度二尺有六寸”窃以为指的是“天子御珽,诸侯御荼,大夫服笏”中的“笏”,非“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中的“笏”。所以,《相玉书》中的“珽玉六寸”与《玉藻》中的“笏度二尺有六寸”并不矛盾,后者特指早期为大夫所持、渐成定制之“笏”。
由“專”与“簿”、“珽”与“笏”的辨析已然知道“珽”是便于握持的六寸的玉,而“笏”同“簿”都长达二尺六寸。若据朱季海的观点,“專”与“簿”都属于“笏”一类,则“珽專”一词之中“珽”短而“專”长,在卜卦时为了方便握持,使较长的“專”截取为六寸的“珽”,不正与王逸所言“折竹以卜”中的“折竹”这一动作暗合吗?该假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首先,楚辞中存在很多和“索藑茅以筳篿兮”在文义和结构方面都十分相近的句子,廖序东和刘永济都针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统计。刘永济在《屈赋释词》中认为:“(以)用同‘与’者,前后两动作或情况相等或相同时,用‘以’字连系之,‘与’‘以’同为之部字,可以互用。”[22]并举《离骚》中“揽木根以结茝兮”“矫菌桂以纫蕙兮”“驷玉虬以乘翳兮”“索藑茅以筳篿兮”以及《九章》中“捣木兰以矫蕙兮”为证。据此,“以”作连词连接两个并列的动宾结构的情况在楚辞中并不罕见,“动词+名词+以+动词+名词”是屈作惯用的一种句法。而“索藑茅以筳篿兮”中“索藑茅”明显为“动词+名词”的形式,所以“筳篿”构成动宾结构正与该句法相合。
其次,名词活用为动词在秦汉典籍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战国策·赵策四》中有“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23],这里的“脯”就是“使成为肉脯那样”的意思。名词活用为动词有使所跟宾语具有名词某种显著特征的作用,“珽”为天子所持之玉,六寸的长度是它与其他物品最重要的区别之一,而“珽專”正是依据“珽”之六寸对较长的“專”进行截取加工,使“專”附加上“珽”的特征。因此“珽(筳)”也具备作动词的可能性。
再次,如果“專”需要“珽”为六寸,如何解释《说文解字》中“專,六寸簿也”的说法?朱季海认为“盖珽者筳也”,“笏、簿、專,犹篿也”,在这里他是把“篿(專)”视作“笏”“簿”“專”竹类的一个统称,正如“笏”可以作为“珽”“荼”“笏”的统称一样。《说文》直接以“專”为六寸,很难排除是由于经常以“珽”之尺寸截取而渐渐形成的,毕竟词的内涵和外延伴随着社会实践和语言变化在不断地演进。所以“篿”在“索藑茅以筳篿兮”中泛指竹类也能够疏通。
综上所述,“筳篿”为动宾结构,脱胎于“珽專”的“折竹六寸”之义,不但在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上都较为合理,而且确定了“索藑茅以筳篿兮”所含“卜”之含义,解决了闻一多和刘永济在该问题上的争端,进一步为探究“占”与“慕”是否因异文而不叶排除了一种可能。窃以为裨益良多,可备一说。
四、余论
王鸣盛在《屈骚指掌》序中说:“其有刊落旧说、别树新意者,盖必稽之往籍、按之目验而后著之,未尝苟驳前师,讕辞脞说以相诋讦。”[14]10599-10600本文虽通过运用文献参证和逻辑推导等方法,一方面对前人旧说爬析梳理,另一方面提出了“筳”为动词,“篿”为名词,“筳篿”为动宾结构,合释为“折竹六寸”的观点,以期较合理圆满地解决有关“筳篿”释义的疑难问题,但仍有立论难以圆通、观照不免碎裂之处。愿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该问题引起其他学者关注。
注释:
(1) 王夫之曾提出一种“藑茅为席”的说法以回避句中“藑茅”与“筳篿”的“草竹”冲突,但据姜亮夫的考证来看是不可靠的。参见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姜亮夫全集》第五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1页。
(2) 参见游国恩:《离骚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53页;陈子展:《楚辞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页;汤炳正等:《楚辞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页;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313页;廖序东:《楚辞语法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年,第136页;熊任望:《屈原辞译注》,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殷光熹:《楚辞注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6页;赵逵夫:《屈骚探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72页。
(3) 参见刘永济:《答辩闻一多辟余改离骚“命灵氛为余占之”为卜之说》,载《屈赋通笺 笺屈余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53页。
(4) 闻说参见闻一多:《楚辞校补》,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18页。刘说参见刘永济:《答辩闻一多辟余改离骚“命灵氛为余占之”为卜之说》。
(5) 可靠的证据至少还有另外两处。其一,“命灵氛为余占之”句下有两“曰”字,若前“曰”是繇辞则后“曰”必定是据繇辞所下的断语,而刘永济据《左传》提出“其曰‘占之’者,皆筮史据繇辞所下断语也”,如此《离骚》该部分则少“灵氛占之”一段。这个观点是刘永济为了自圆其说提出来的一种可能,并最终将原因归结于“略去灵氛占之之文,读者亦可知为灵氛之语”,其辞含糊难以使人接受。其二,刘永济提出:“屈赋换韵者,辞意亦属另起,未有意属上文而韵协下文者。”观“曰两美其必合兮”,四句为一气,“曰勉远逝无狐疑兮”,四句又为一气,则可以基本推断出前“曰”句为繇辞、后“曰”句为断语。正与“索藑茅以筳篿兮”表“卜”事,“命灵氛为余占之”表“占”事相互对应,若合符契。以上两个证据只能间接地佐证“筳篿”句含有“卜”义,而唯有直接证明“筳篿”为“折竹”才能直击该论题的核心。
参考文献:
[1] 王逸.楚辞章句[M]//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27.
[2] 廖序东.楚辞语法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136.
[3] 司马迁.商君列传[M]//史记:卷68.北京:中华书局,2006:422.
[4] 班固.霍光传金日磾传[M]//汉书:卷68.北京:中华书局,1962:2938.
[5] 班固.扬雄传[M]//汉书:卷87.北京:中华书局,1962.3520.
[6] 汪瑗.楚辞集解[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85.
[7] 戴震.屈原赋注[M]//丛书集成续编:第11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252.
[8] 方以智.通雅[M]//游国恩.离骚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350.
[9] 李陈玉.楚辞笺注[M]//吴平,回达强.楚辞文献集成:第8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5216.
[10] 闻一多.楚辞校补[M].成都:巴蜀书社,2002:16.
[11] 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M].杨武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444.
[12] 王夫之.楚辞通释[M]//吴平,回达强.楚辞文献集成:第10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6848.
[13] 朱冀.离骚辨[M]//吴平,回达强.楚辞文献集成:第12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8146.
[14]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178.
[15] 胡文英.屈骚指掌[M]//吴平,回达强.楚辞文献集成:第15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10662.
[16] 朱季海.楚辞解故[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91.
[17]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華书局,2013:61.
[18] 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810.
[19]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38.
[20]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3781.
[21] 章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6:878.
[22] 屈赋释词[M]//刘永济.屈赋通笺附笺屈余义 屈赋音注详解 屈赋释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547.
[23]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376.
[责任编辑:黄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