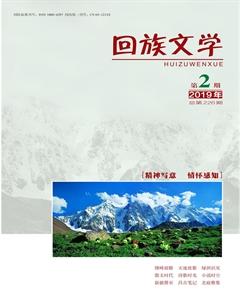西沙窝的天地(组篇)
西沙窝的沙尘暴
听说或经历过沙尘暴的人都对沙尘暴极其恐惧。聽说过的是把沙尘暴想象得有多么可怕,经历过的是感受到了沙尘暴真的可怕。那仿佛是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刚从地狱里走过来一样,想起来都有些心有余悸和后怕。
但西沙窝的人就不那么在乎沙尘暴。他们不是不怕,是怕也没用。因为他们常年就生活在沙尘暴的风口浪尖上,就像遇到刮风下雨天一样,沙尘暴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他们不是怕,更多的是讨厌沙尘暴。那种暗无天日、昏天黑地的日子,没有哪个人会喜欢的。
对于这个沙漠边缘的村庄,不管你是怕还是不怕,喜欢还是不喜欢,沙尘暴都会如期光顾的。每年的四五月份,那是沙尘暴最猖狂的季节,好了十天八天一场,不好了三五天就是一场。
我没见过其他地方沙尘暴是什么样子,但我却是无数次地经历过西沙窝的沙尘暴。那时候似乎还没听说过沙尘暴这个名字,我们西沙窝的人都叫它“黑风暴”。沙尘暴一般都是在下午或傍晚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如果你一直面向东南方向的时候,你丝毫感觉不到灾难的降临,你看到的仍是万里无云的天空和恬静、安详的大漠原野。可是,当你回过头来面向西方的时候,就会让你大惊失色。刚才美好的心情荡然无存,似乎一个美丽无比的少女顷刻间变成了狰狞、丑陋的妖孽。
即便是刚开始的那一刻也是非常恐怖的:整个西部像一条巨大、昏黄、似乎能够毁灭一切的恶龙一样,急速翻滚着压过来,又像一张巨型的网在快速、急切地张开,铺天盖地地扑过来,似乎要把大地的一切都毁灭、吞噬……望着西边那浓烈、越来越黑的天际,让人感到有种毁灭感。
天渐渐昏暗起来,一阵阵更急、更骤的凉风吹过来,这阵阵阴风其实是沙尘暴巨大的张力和惯性形成的,它们可以说是沙尘暴的急先锋。它们在沙梁上、空地上打着旋,带着一些尘沙、野草翻滚着由西向东冲去,这时候,沙梁下面那片沙漠空地,长满骆驼刺、花花柴和苦豆子的大草甸子整个晃动起来,万头攒动,像千军万马。特别是那些浑圆而又硕大的绣球草,一排排翻滚着从人们身边急速滚过,从西向东冲去,似乎也在刻意地躲避这即将到来的灾难。
这个时候,无论人们在哪个方向,都会同时奔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回家的方向。所有人都希望在沙尘暴到来之前赶到家,如果到不了家,那个惨象就可想而知了,那就只能在沙尘暴里疲于挣扎了,能不能回到家全看你的造化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在路上,那还好一点,尽管狂风肆虐,天昏地暗,但脚下的那点路还是能看清的,顺着那条熟悉的路你总能找回去。但如果不是在路上的,比如是正在野滩里放羊的,抑或你是抄近路到哪个老乡庄子的,那可就危险了。那个地方你尽管去过无数次,但一场黑风将一切地形地貌都改变了,每一次狂风都是对大漠的一次重新洗牌,你记忆中的一切都改变了原有的模样,关键是这时候无数个沙粒打得你眼睛都睁不开,什么都看不见。你在沙尘暴中跌跌撞撞、左冲右突,总认为凭着记忆不会搞错方向,能找着一条回家的路。其实不然,你拼命地跑来跑去,折腾来折腾去却发现你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这时,你最好冷静下来,辨清方向,如果走对了你就能回到家,要是走不对,那就只能找个避风的地方在荒郊野外过一夜了。
如果你是骑着马或赶着车的,那么你最好什么也别管,任由它们去走,它们比你认路,它能拉着你或驼着你找到回家的路。当马或车在昏暗的狂风中突然停下来的时候,当你还稀里糊涂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搞不清怎么回事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已经到了家门口。你晕晕乎乎四周看了半天,当看到从家里的窗户里透出的微弱灯光,才搞清怎么回事。当你进到屋里看到家人正在焦急地等你的时候,一种久违的欣喜和温暖立即涌上心头,你悬着的一颗心才算是放下来。家人看到你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惊喜,接着就是开始笑话你了。因为那时候你已经面目全非,你已经不是你了,头发里面全部灌满了沙子,成了白头翁,整个面部,眼睛里,耳朵里,鼻孔里,全都是沙子,你完全变成了沙人。家人在嬉笑中为你打来洗脸水,拿来毛巾,你经过一番洗漱后才又回到家人认识你的那个样子。
如果你是放羊的,不过放羊的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每人都有一个收音机,这是他们每天必带的物件,就像每天都要带干粮和水一样。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放羊的寂寞;另一方面可以听天气预报,哪天要刮沙尘暴,他们都提前知道,即便不知道,一起放羊的也会告诉他。知道哪天要刮黑风,哪天就不敢走远,并不时朝西边看,看见要起沙尘暴了,就早早把羊往家里赶,一般都能赶到风前头到家。要是没能提前回了家的,那有可能是那两天收音机坏了,刚好又是单独放羊,所以就落在风里面了,像这样的情况极少发生。但真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就全靠牧羊犬和领头羊了,它们都熟悉路,主人在后面拼命赶,狗就看两边,不让羊群乱跑,领头羊在前面带路,这样也能回到家。平时看着人比谁都聪明,但到了这种情况下,哪种畜生都比人强,哪种动物人都比不了,人变成了最笨的东西。
平时把羊赶进圈时,一个人守在圈门口要清点数字,万一点错了还要赶出来重点,直到点对为止。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法点了,虽然羊群进了圈,主人一夜心里都放不下,总觉得羊不够数,是不是在大风中跑丢了。到了第二天早上,主人早早地就把羊赶出来点数字,点对了就全家高兴,点不对就全家都去顺着昨天回来的路去找羊。找着了就算是虚惊一场,找不到也就只能认倒霉了。
沙尘暴一般都是头一天下午或晚上开始的,到第二天清晨就结束了。半夜还是天昏地暗的像是世界末日,早晨起来已经是晴空万里、碧日当空了,简直都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当然也有刮得时间长的,刮个三天两天也是常有的。
沙尘暴过后的西沙窝是很惨的:首先是家家户户所有的房间都被沙尘暴洗劫了一遍。尽管有许多人家的门窗都很严实,但那也经不住沙尘暴见缝插针的渗透,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挡得住那些细微的沙粒。夜里刮风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凄厉的风声和刺鼻的土呛味,等到早上起来一看,所有的锅碗瓢盆、杯盘灶具里面全都是沙子,包括那些床铺被褥也都是沙子。讲究的要全部清洗一遍,不讲究的也就是锅碗瓢盆洗一下,其他被褥什么的也就拍拍打打一番后,再用毛刷子扫一下就算了,反正天天和沙子打交道,即便平时鞋子、袜子里也都是沙子,放羊的还天天在沙包上睡觉,因此,他们也从来不把沙子当成什么脏东西。爱干净的,一场风过后要洗个澡,不在乎的,连澡都懒得洗,一年最多就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时洗个澡,平时脚上的垢甲能有指甲盖那么厚,洗的时候垢甲经热水一泡,拿刀子一刮就是厚厚的一层,尽管刮下来的是垢甲,但总归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东西,看着一堆一堆的,想通的觉得洗得挺过瘾,想不通的还感觉有些可惜。
遭殃的不仅仅是家里,损失最惨重的还是地里。如果是在四月份刚播下的种子还好一點,最多就是把靠近地边的地埋得厚一点,到时候还得人工扒苗,虽然很麻烦,要一点一点把苗扒出来,很是费工费力,就像考古学家清理刚发现的古墓一样小心翼翼,搞不好就把苗给碰断了;要是五月份刮的黑风暴,如果再刮个三天两天,那就麻烦大了。七十年代的时候地里是没有地膜的,播下去的苗刚长出来,原本一片嫩绿煞是喜人,一场风过后你再看,那些苗就全让沙子给打光了,连个杆子都找不到,变成了光秃秃的一片,靠地边的还连打带埋。你别看那些沙子很小,但是在狂风力量的作用下,那些沙子打在苗上,水滴都能穿石,何况那些弱小的幼苗呢。这样倒是省事不用扒苗了,但一场心血也白费了。于是,还要花上种子、人工和机耕费,重新播种。即便是墒情还可以,但减产已经是铁板上的钉子了,因为季节已经过去了,庄稼是有生长期的,晚几天到了秋天的收成都大不一样。
受损失的还有那些刚刚清好、修好,浇过头遍水的渠道。有些离沙子远一点或渠边上草多的还好一点,也就是在渠底子上有一些沙子,但那些离沙包近的,更甚者是那些在沙包中蜿蜒穿行的渠道,一场风过后,这些渠道大部分又被沙子填埋,好一些的埋掉小半边渠,不好的多半都让沙子埋了。这样的话,在下次浇水之前,还要发动全连的人去清渠,像这样白白浪费人力物力的活每年都要干那么几次。
还有受损失的就是那些路,那都是些没有经过任何人工修筑自然形成的土路。有几段是用推土机直接把沙梁切断变成路的,那是西沙窝通向外面的唯一出路,一场沙尘暴过后,那几节路又让风沙给埋住了。于是,连队还得派上链轨式推土机把那些沙子推开,要不然什么车都过不去,那西沙窝就真的算是与世隔绝了。
如果说还有哪些损失的话,那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了。比如说,谁家的草棚被风掀翻了,谁家的树让风给刮断了;谁家的草帽子,谁家院子晾的衣服,谁家房顶上摊的剥桃花(就是入冬前收的还未成熟吐絮,呈桃子状的棉花),谁家的锅盖都让风卷跑了等等,反正谁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多少都有些损失。
在西沙窝生活的人都非常痛恨沙尘暴,经常骂它是“妖风”、“鬼风”、“骚风”等。但再骂也不起作用,它就是一股风,再骂它也听不见,它该刮还是刮,你再痛恨,再不高兴,再不喜欢,你该受着还得受着。
西沙窝的冬灌地
西沙窝新湖三场九连,在每年入冬前都有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要灌溉几千亩的冬灌地,那几乎是囊括了西沙窝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其实这也不单是西沙窝这样做,其他各个连队都是如此。
过去秋收完了,连队职工们就渐渐地闲下来了,忙一些的最多就是赶着毛驴车,来到田间地头,拉回那些早就割下来捆成捆子的秸秆、野草,或是到荒郊野外去捡些柴火,以备冬季人、畜的过冬之用;闲一些的就去场部商店买点什么东西,或走走亲戚串串门。那时候是秋高气爽的季节,气候不冷不热,无论是干点小活的还是串门的,心情都感觉特别地好。
但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就不行了,即便是秋天庄稼收完了,人也闲不下来了,那就是要浇冬灌地。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他几乎是把来年春天所有要浇的地,都提前在入冬前浇完了。不过也有些好处,那就是给来年忙得贼死的春播季节省了不少心。冬灌的时候关键还不是光浇地,浇地还是最后一个环节。首先要做到场光地净,就是要把所有地里乱七八糟的秸秆啊野草啊都收拾干净,接着要平地埂子,因为有那些横七竖八的地埂子在,拖拉机就没办法犁地,然后这才开始犁地,要把所有明年要种的地全都犁出来。这就有点像城里工厂的流水线作业。人们清出一块地来,拖拉机就犁出一块地,然后就在犁好的地里再把地埂子打起来。直到这个时候才开始浇水,相比之下,浇水是最慢的。直到前面的工序都干完了,浇水还在不紧不慢地进行,因为水就那么大,急也没用,只要第一场雪还没下,就不会封冻,就可以继续浇,直到把所有要浇的地全部浇完,好一点到十一月初就完了,不好的时候都能浇到十一月中旬。
其实最开始地少的时候,是只有春灌地而没有冬灌地的,这是过去长期保持并遗留下来的种地习惯,认为种地本来就是春种秋收,春天犁地、浇水、播种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后来开得地多了,春天大家都浇地,都用水,这水就很紧缺,每年春季把新湖坪水库里的水都放干了,库底子都露出来了,连水库里的小鱼小虾都放下去了,可水还是不够用,搞得好多地都浇不上水,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而出现的另一个相反的情况是,到了秋天,地里的庄稼都收光了,也不用水了,水库的水却装不下了,地里不用水也得放水,总不能把水库憋坏吧?还得放闸。于是那水就顺着大干渠、各支渠胡球乱淌,淌到哪算哪,最后经过人工引导,大部分都淌到戈壁荒滩上去了。
于是,农场领导就考虑,能不能把秋天的这些水也利用上,以解决春天水不够用的难题。先是在秋天庄稼收完后,犁上几块地,然后在入冬前用这些闲水把地浇上,看看第二年春播的效果,这样从此就有了冬灌地。
到了第二年春天播种出苗后,春灌地和冬灌地就渐渐显示了各自的不同之处。开始的时候,看着还是春灌地好,苗出得快,长得也快,春灌地的苗都显行了,可冬灌地的苗还跟个缩头乌龟一样,有的东一颗西一颗刚冒出头来,更多的还藏在土里就是不肯露头。等到春灌地的苗绿油油的一片连白地都看不见了,冬灌地的苗才像刚睡醒的千年王八一样,一个个疲疲沓沓刚露出头来,但怎么看着都像扽不展的“死娃子”一样没来头。
但等到五月中旬一过,地温一上来,那就不一样了,先前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到了六月中旬以后,冬灌地的苗就已经完全赶上春灌地了。而且越往后,春灌地的苗不如冬灌地的迹象也就更加明显,差距也越来越大。那时候你再看,春灌地的苗都开始蔫头耷脑没精神了。而这时候你再看冬灌地的苗,个个叶子黑油油的,杆子粗粗壮壮的,一天一个样子,像是吃了大力神丸似的,不知从哪里来的那股子邪劲。
后来,冬灌地种多了,经验也就多了,农业专家们就对此现象进行了总结。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方面春灌地的水是春天的水,比较暖,是热性的,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水浇得浅,浇得急,水都浇在了上面的虚土上,而下面的硬土还是干的。因此,这样的好处就是来手快,地温提升快,苗也长得快。但长着长着就不行了,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缺水,下面的水分跟不上了,所以就不长了。一般都是从春天四月份把种子播下去,苗期的第一水都要等到六月中旬以后才有水浇,于是,每年等不到那个时候,春灌地的苗就受不了了。
而冬灌地恰恰相反。浇冬灌地的时候都是在入冬前,只要是在没下大雪封冻前浇的地,都是冬灌地。到了后期,夜里都有零下好几度,在太阳还没出来的清晨,在浇过的地里凡是有积水的地方,都能看到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冰碴子。这个时候看着天空晴朗、阳光明媚,但已感觉不到她能给人有多少的温暖,因此,浇到地里的水也几乎没了什么蒸发。上面不蒸发它就往下渗,一直渗到下面那些从未被人翻动过的老土层里,这样新土老土就变成了一个整体。
春天冰雪消融的时候,温度一般都是一点一点,一层一层地从上往下走的,由于春灌地浇的是春水,一浇到底,下面没有冻层,因此它没有那么费劲,它可以一热到底,地温也随着春天温度的快速提升而同步提升。而冬灌地就不行了,经过一冬天的严寒和冰冻,那些地全部都冻透了,水和土无间隙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足有六七十公分厚的冻层。因此,在开春的时候,即便温度提升得很快,你也只能一点一点从上往下渗透,而下面的寒气还往上蹿,这些寒气又抵消了许多往下渗透的热量。所以,冬灌地前期的苗不好好长,长不起来就是这个道理,原因就是地温起不来。
春灌地开始苗长得快,但地里水分也蒸发得快,到了六月份就不行了,由于春灌地里水分的快速蒸发,水分也就渐渐跟不上苗的需求了,庄稼也就渐渐停止了生长,一个个都蔫头耷脑的在苦撑待水。而冬灌地恰恰相反,冬灌地开始苗长得慢,水分也蒸发得慢,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地温也真正上来了,下面充足而丰富的水分源源不断地满足着整个苗期的需求,在春灌地弹药不足苦守待援的那段时间,冬灌地全副武装,一个冲锋不但追上了春灌地,而且很快就把春灌地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一般苗期的头水都是紧着春灌地先浇,即便春灌地十天八天的都浇完了,冬灌地的苗看着还不怎么缺水,还是那么劲头十足。想想就觉得很日怪,冬灌地是头一年十月份浇的水,春灌地是来年春天四月份刚浇的水,两下里差了将近半年,春灌地还没有冬灌地耐旱,你说它就是这么地日怪。
如果打个比方的话,春灌地像西药,来手快,见效快,但就是三锤两棒子,来得快去得也快,能治好就治好,治不好也就没辙了,而且可能还会落下后遗症、并发症什么的,如红蜘蛛,蚜虫,杂草疯长等;而冬灌地更像中药,虽见效慢,但持续时间久,不但把你的病治好,还能把你的身体调理好,而且还绝对没有后遗症。如果再把她们比作女人的话,那春灌地就是现代版的女人,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和享受,把种子一种到她身上,她自己就大吃大喝,等孩子一生出来,她就开始娇惯孩子,给孩子天天好吃好喝,都吃得虚胖,吃得营养过剩,等到没钱了也就干瞪眼,天天看着孩子没吃没喝的也没辙了;而冬灌地无疑就是一个比较传统型的女人,讲究的是细水长流,还懂得教育孩子,从小就让孩子多吃些苦,让他知道来日方长,即便是家财万贯,也从不去娇惯孩子,只给他提供够他健康成长的营养就行了。而等到孩子身体健硕,真正需要大量营养的时候,母亲也毫不吝啬,源源不断地满足他的身体成长的需要,最后把他们个个都培养成有用之才。
事实就是这样的,经实践证明,冬灌地的产量都比春灌地的产量高,品质好,即便冬灌地比春灌地少浇一水,产量都不比春灌地低。而且冬灌地的杂草少,作物病虫害也少。病虫害少的原因就是,冬翻的时候都把虫卵深埋在下面,经过一冬天长时间的冷冻,很多虫卵都被冻死了;再一个就是很多病虫害都是在苗期旱水的时候染上的,苗期一旱水,那时候是苗的抵抗力最弱的时候,就很容易得病,什么“红蜘蛛”、“蚜虫”等都来了,棉花最怕“红蜘蛛”,只要染上,那棉花就必定要减产。而冬灌地从不缺水,始终保证苗期水分营养的正常供应,苗们也都一直保证良好的身体素质,因此它得病的几率就比春灌地低多了,除非是重茬子地,那就不敢保证了。杂草少也是因为冬翻的时候把它埋得深,种子是播在上面的,可以正常发芽出苗,而草籽是埋在最下面的,下面的地温低,它就没条件发育生长,一时出不来就把它憋死了,腐烂了,所以冬灌地草也少。冬灌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特别保墒,因为经过一冬天的冷冻,那土都冻酥了,因此土质就特别地细酥和柔绵,不像春灌地的土质,怎么处理都是疙疙瘩瘩的。
因为看到了冬灌地的好处多,人们就开始更多地青睐于冬灌地了,渐渐地春灌地越来越少,冬灌地越来越多。这样就把秋天的那部分闲水也充分利用起来了,真正做到了水源合理配置和利用。后来,由于塑料薄膜的出现和应用,又从根本上解决了冬灌地春天地温起不来的弊端,冬灌地的优势就更加凸显,它彻底地改变和颠覆了传统的耕种习惯,以至于最后春灌地都无人问津。但为了保证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还是要安排一定数量的适合春灌地的早熟作物。
冬灌地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农业结构,为此还出现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最开始浇冬灌地的水是不要钱的,后来适当收一些钱,进而一路见长,最后和其他水费一样。就这样还争抢得打破了头,还不定都能浇得上。它从无人问津变成了主宰农业的霸主,可见冬灌地在现代农业中具有多么高的地位。
西沙窝的那些旦干渠道
西沙窝新湖三场九连,是新湖农场深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最偏远的一个连队,因此,在三场所有的连队中,它也是渠系最长的一个连队。那渠道不光是長,还特别旦干(差劲)。这些烂干渠道可以说是西沙窝人心中永久的痛,它就像庄稼地里那些无形生长的“黄缠”(一种寄生在农作物身上,黄色的藤蔓形野生植物,它无根、无籽、无花、无果,生命力极强,对农作物危害极大),它们始终缠绕在农作物身上,剪不断理还乱,让你欲罢不能,痛不欲生,苦不堪言。
在先前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沙窝作为三场四连牧业点的时候,渠系是从三场四连过来的,在路过四连农庄、农田的时候还算是比较正规的,但一过四连地界,那水也就像西沙窝的羊群一样,任由它们胡球乱淌了。因为后面就没有什么正规渠道了,而是顺着一条历年被洪水冲刷而成的自然沟流淌。这条沟叫“羊肠沟”,只因为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弯弯曲曲、七拐八拐,一会儿宽一会儿窄,简直不成个样子。这条羊肠沟一路向西,一直流到西沙窝最下面的一片苦蒿子地,并在那里形成了一片湿地。
但西沙窝的居民点在苦蒿子地东北方向的两三公里处,必须要把水引到居民点的涝坝里。前面顺着羊肠沟胡球乱淌可以,还省了人们挖渠的力气,后面就不行了。于是,西沙窝人就在羊肠沟的上游处截断,重新挖了一条两公里的渠,把水引到了居民点,而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新挖的两公里渠道上。
要流到西沙窝居民点,这渠就必须从高处挖,而西沙窝的高处在哪里?就是那些七高八低的沙包。在沙子上修渠,不要说那水的渗漏有多大,就单说那挖渠的难度有多大就可想而知。那沙子就像水一样,挖一锨就跟没挖一样,挖多少又流下来多少。这条渠还必须围着一个个沙包转,否则这水就流不到居民点,就这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挖好了。等到淌水的时候你再看,由于那沙子渗漏大,那水淌在渠里就跟没淌一样,半天都走不了一米。水大些还好些,水小了就不淌了,全渗到沙子里面去了。其实当时就是为了解决西沙窝几户人家人畜的饮用水问题,就是为了把那个涝坝灌满,可灌那么一个不大的涝坝,感觉比把那整个新湖垦区都用的新湖坪水库灌满都难,每次都得个两天两夜,比浇上千亩地都费水,好在那个年代种植面积不是太大,水还没有那么紧张。经过多年使用,渠道两边渐渐长满了植物,由于植物根系的作用,沙子也不再往下继续流淌,起到了水土不再流失,保护渠堤的作用;同时,由于流水长期的冲积,渠底上也覆盖了一层上游带下来的淤泥,也减少了渗漏,流水也越来越快,水也费得越来越少了。
似乎挖渠和渗漏的困扰都解决了,其实不然,这还仅仅是开始,更大的挑战,更多的麻烦还在后面,这就是没完没了了,无休无止的清渠,这极度地挑战着西沙窝人的耐心和毅力。
其他连队的清渠基本上就是每年春灌的时候清一次,把一秋一冬风刮的,羊踏的,以及自然遗落在渠里的杂草、树枝、泥土等杂物清干净,以减少流水的阻力,影响水的流速,或再把渠两边的野草铲一下,基本一次到位,后面就再没有什么事了。而西沙窝就不行了,西沙窝不仅是清渠,而更多的是在挖渠。因为西沙窝地处沙漠之中,风大不说,许多渠都是修在沙包上的,一场沙尘暴过后你再看,围着沙包转的那些渠道,基本上又被沙子填平了,好一点的填了半拉子渠道,不好的聚得沙子比原来的渠帮子还高。怎么办?只能重新挖开。渠底子要挖到原来冲积的黄泥巴上,渠两边还要小心一点,不能随意挖,不能把那些长了多年的草根挖掉,要保护植被,那些可都是渠帮子最好的保护层。因此,每次清渠都等于重新挖了一次渠。还不光是沙尘暴的破坏,还有那些羊群。那条横穿西沙窝的渠道,你不能不让羊走,连现在伊犁的高速公路,在转场的时候都让羊走,何况你这戈壁滩上的烂渠道了。不让羊走你还怎么放羊?因此,那羊群过渠道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一群几百只的羊,从那沙包渠道过后你再看,那一截渠道基本上让羊就给踏平了。靠沙包那边的把沙子踏进了渠道,另一面的基本上把渠帮子给踏没有了。尽管每次修那几截渠的时候人们都要骂几句那些放羊的,但骂归骂,那羊群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
后来西沙窝不归四连管了,变成了三场九连,归场部直接管,而且渠道也不从四连走了,而是挖了一条新渠,从场部直接到西沙窝。那渠一路下来都好好的,顺畅得很,但一到西沙窝就不行了。问题还是出在到居民点的那截两公里的渠道上,你要挖一截新渠直接到居民点,比老渠可以省一些路程,但这新渠也还得围着沙包转,等于从头开始。算来算去,还不如用老渠道,起码这截渠经过这些年的流淌,渠道的牢固程度已经很稳定了,而且渗漏问题也基本解决了,虽然挖一条新渠要节省一公里左右的路程,但又非常费工、费力、费水,怎么感觉都不划算,于是这条新渠没有拐弯,而是直插下去又连到老渠道上了。虽然这条新渠比原来从四连走要减少两三公里的路程,比原来快了许多,也减少了许多渗漏,但西沙窝人年年挖渠的困扰丝毫没有解决。
关键是这渠道还不是一年只挖一次,西沙窝变成三场九连以后,已经不仅仅是放羊了,也不单单是装满那个涝坝了,也开垦种植了几千亩土地,那种地浇水的次数和周期都比以前的多了,长了,因此每次浇水都得挖。因为每次浇水的间隔时间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多月,而在这段时间里,少则三五场风,多则十场八场,不用多说,有两场风就能把渠填平了,至于后面刮再多场风也都是那样了,也都是风在那里瞎忙活了,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在八十年代以前,西沙窝人几乎每年最少都要挖三次渠,春灌一次,苗期最少要浇两水,也就要挖两次。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浇冬灌地,因此,西沙窝人也跟着又增加了挖渠任务,这样的现象一直保持到九十年代,直到1993年我离开西沙窝的时候,还是如此。
2013年夏天,我帶着妻子女儿,从乌鲁木齐驱车专门去了一趟西沙窝,一路过去,再也见不到西沙窝原来的样子了。一条柏油路从场部直接通到了西沙窝,路两边也再见不到连绵起伏、高低不平的沙包了,全被人工种植的胡杨、红柳、梭梭柴等植物所覆盖,那个偏远的西沙窝也不再遥远,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都在这里呈现,而那些每年春夏三天两头就刮一场的沙尘暴也几乎绝迹,治根治源,因没了那些个沙尘暴,那些渠道也就安然无恙了,西沙窝人年年挖渠的现象也就渐渐成了人们记忆中的历史了。
毛玉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新疆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新疆作家协会理事。在全国报刊发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作品。曾在新疆昌吉州兵团某农场工作。现定居新疆昌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