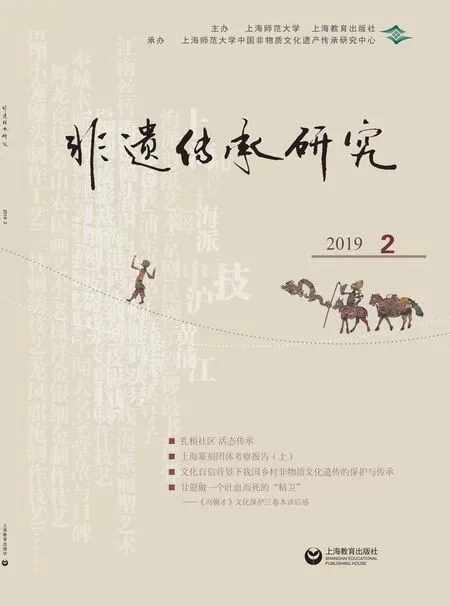评弹艺脉的传承与创新
口述:吴宗锡 整理:王月华
评弹,江南文化的奇葩,流传于民间已经有数百年。然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和大众欣赏趣味多元化,评弹的听众日趋减少,面临着需要抢救的境遇。一些观众抱怨许多书场变为咖啡馆,想听听评弹煞是困难;一些评弹名家忧心忡忡,年轻人想学评弹的越来越少;不少评弹团更是面临窘境,去大城市演出成本高,如果政府没有补贴,剧团还会亏损。到农村演出,许多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只有老人与小孩在家,也未必能有多少人观看。面对这一切,1945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新中国评弹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中国著名评弹理论家、2012年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吴宗锡先生认为:评弹传承与创新并举,重视艺脉的延续和发展,悉心培植评弹听众,加大剧本的艺术含金量等是当务之急。
传承与创新并举
我认为评弹上座率低,不是书场里没有评弹演出,这些年来政府通过拨款和培养艺人等途径在振兴评弹,而是评弹缺少适应时代和听众的剧本。老艺人们的相继萎谢和退出书坛,传统书目的演出越来越少,新的优秀剧本创作较难见到。此外确实有不少听众对评弹不感兴趣,喜欢现代娱乐样式。
评弹是视听表演艺术,其书目尤其是传统书目的文本,都经过文人与艺人多次甚至几十次的修改,才既有文学性又有艺术性,且有评弹的特有内涵。所以传承评弹这一具有江南文化、乡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保存和弘扬的是艺术内涵,具体地说是保存和发展其说噱弹唱演的表演艺术。而传承书目,主要是传承其具有艺术含量的演出脚本。
传承不是全盘保留,而是要不断创新。如果说传承是对艺术特性、手段、经验的守护和承续,那么创新则是在扬弃过程中,丰富其内涵,提高其艺术水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出于蓝是传承,胜于蓝便是其创新发展。脱离了艺术特性和前人艺术经验的根本,创新就不会成功。有人说,创新书目的水平决定于编演者的传统艺术水平,也正是这个道理。传承而不作创新,固步自封,就会妨碍艺术的发展和提高。
传承是艺术创新的基础。而传承需要有“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决心,用心学习前人和大家的艺术理论和表演技艺。在掌握了其特性、规律及基本技艺之后,才能推陈出新,求得评弹艺术的提高,所以传承与创新并举才是发展评弹艺术的唯一出路。如著名评弹演员刘天韵曾将其传承经验总结为“学、摸、化”三字艺诀。学,是传承;摸,是对学得之艺术进行研习;化,便是结合内容,结合自身条件进行创新发展。评弹艺术就是在传承与创新中,由一般的说书发展成了说唱表演最为精熟的综合性视听艺术的。
所以,我认为评弹作为视听艺术,艺人是其创造者和体现者。仅有文学性的脚本,没有演员演唱的技艺,即体现在演员表演中的说噱弹唱演综合艺术,评弹是不可能成为活的艺术的。其实不仅演员知道此理,听众也早就明白听评弹书目与演员并重。所以,他们总说,去听某某演员,而不先说听某某书目。因为当一部传统书目听过多遍之后,到书场去欣赏的便是演员的艺术了。因为优秀的评弹艺人在传承前辈的技艺过程中,自己的技艺也在不断揣摩与自身的努力之中得到升华。薪火相传,继承是艺术发展的生命线,传承是发扬光大评弹艺术的必经之路。
重视艺脉的延续和发展
为此,我认为,重视艺脉的延续和发展是当前拯救评弹的重中之重。所谓艺脉,就是传承决定着评弹艺术存亡继绝的生命线。这犹如长江之水从源头汹涌澎湃,奔腾而下穿越中游,并川流不息汇入浩瀚的东海卷起惊涛骇浪。由于和其他戏剧样式不同,评弹的剧本是艺人根据自己对剧本的理解和审美情趣不断进行加工与调整的。而评弹艺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师父带徒弟的传承方式,又因为师徒对剧本的理解不同而进行调整和磨合。一般来说,评弹老师培养徒弟的方法是让徒弟坐在书场里一遍又一遍地和听众一起,观摩老师的演出。这样徒弟既可以在观摩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师父的言传身教,同时又结合听众的反应和演出效果,加深对师父艺术的领会和对剧本的理解。正是不断地进行摹学、练习,才使剧本在保持其基本内容的同时,转化为自己的演出剧本,形成自己的表演艺术。这种似乎原始的师徒培养模式形成了评弹非物质文化艺术的显著特点,也就是评弹的艺脉。
我认为,以个体形态表演的评弹艺术,其表演都带有表演者的个性特征,形成了其艺术风格。风格是评弹审美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风格的传承,流派的发扬,皆在于师父对艺术言传身教同时的濡染熏陶。为此,评弹传承更需要老师的亲授。之所以强调一个“亲”字,就在于授艺学艺都要有师徒之间的零距离的亲密接触。过去,评弹学徒观摩老师表演称为“拍照”,意即对老师表演时的音容笑貌、举止动作,在脑海里留下第一手的深刻印象。用现在电子时代的语言,或可称作“扫描、下载”。这些下载在脑海里,保留在记忆中的印象,在登台演出时,会自然地流露并转化到学生身上。或者说,身上有了老师的影子,再经过学生认真地研学揣摩,艺术便得到了严谨精确的传承。
为此,在实践中,评弹演员对传承采取了多种辅助的措施。如在跟师阶段或跟师出道之后,与老师拼档,当下手或“插边花”(坐在边上,只作少量说唱搭口),实为作见习演员。由此,能更多感受到老师的技艺(呼应、节奏等)。在评弹团的群体里,青年演员经常与资深的名家拼档,或同台演出中篇、选回,通过排练、辅导,同时也进行着艺术的传承。如苏似荫进上海评弹团时,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他经过与刘天韵、蒋月泉、姚荫梅、张鉴庭等同台演出,感受、吸纳了这些名家的艺术,后来成了评弹艺术的中坚骨干,被誉为“硬里子”。华士亭原师从擅说《三笑》的名家徐云志,在评弹团,曾多年任刘天韵的下手。在其熏陶下,他说的《三笑》兼得两家之长。他说《三笑·追舟》等选回,颇具刘天韵的风貌,艺术的真髓在其实践中获得了传承。
为了让青年演员传承艺术,评弹团又采取了培训班的方式。在一定时间内,将青年演员组织起来,由老师授艺,并作示范演出,又辅导排练若干选回、选曲。这样,既有观摩、辅导,又有实践,对传承传统艺术,也是行之有效的。20世纪50年代,曾举办过多次培训班,当时的青年演员,如余红仙、刘韵若、严燕君等,后来均艺有所成,得益于培训班者良多。
当时,评弹行会起名为“光裕社”,就是希望评弹艺术能光前裕后,前后衔接,光耀发展。为此,光裕社建立了“出道录”的名册,登录了历年跟师出道的人名,犹如家族的谱牒,其实也是其艺术薪火相传的历史记载。光裕社订立了严格的拜师制度和仪式。艺人须达到一定水平,经资深前辈审核认可,方能收徒。徒弟拜师要有中间证人(“赠行”),行跪拜礼。这些仪式的制定,说明了行会对艺术(也包括其知识产权)的尊重和崇敬,也是对传承的尊重和崇敬。对以评弹为谋生手段,也是终身事业的艺人来说,艺术无疑是神圣的。因此,他们敬重其传承关系。过去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师徒之间是一种神圣的伦理关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些制度仪式的建立,因为传承是这门艺术存亡继绝的生命线。
当然,这种亲授、亲炙,反过来对老师也必须有严格和规范的要求。过去,光裕社制度规定,演员要在艺术上达到一定水平,经行会中权威人士认可,始能收徒授艺,称为“出大道”,以保证艺术传承的质量。好的老师,授徒时,其说唱能教一百遍都不走样。常说的名师出高徒,虽然不是说凡名师必出高徒(名艺人的子弟也未必都能成材),但应该说,要出高徒,必求名师。老师艺术品位低俗,不但会误人子弟,更不利于艺术的发展。有了艺术造诣高的老师,得到亲授,才能有流派艺术的正宗嫡传和真传,并使之不断繁荣发展。
学艺者都想投拜名师。但是,过去有造诣的名家响档索要很高的拜师金,有的还有“跟三年,帮三年”(即跟师三年后,还要无偿地帮老师做三年)的苛刻条件。家境清贫的,拿不出高额的拜师金,只得退而求其次,投拜艺术中流的老师。但名家响档中也不乏爱惜人才,热心提携有潜质的。如张鉴庭在未成名时,就得到大响档夏荷生的提携,破例允许观摩其演出。正是这种现场的观摩和指点,使张鉴庭的艺事大进,终成响档。有的艺人为求广学博修而转益多师。如蒋月泉在学艺阶段,先拜钟笑侬、张云亭为师,后又不计辈分,拜隔房师兄周玉泉学艺。因周玉泉的书艺较符合其个性、情趣,蒋月泉经过勤奋研习,终成一代大家。又如邢晏芝在成为响档之后,为了学得“祁调”的真传和提高自己的艺术品位,又先后拜祁莲芳、杨振雄为师。在评弹的发展史中,颇多这类范例。这也是评弹艺术兴盛的一个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集体制的团队建立,为了培养青年演员,各地相继举办了随团学馆乃至专科学校,并采用了课堂教学的方法。但后来经验证明,课堂教学对学习文化和打好说唱基础是有其优越性的,但是对演出长篇书目和说噱弹唱演等综合艺术的全面传承,仍需要其符合个体形态的传承方法,跟师学艺,俗称“跟先生,学长篇”。这“长篇”指的是具有艺术含量的演出书目。这说明对于以个体形态表演的“口头和非物质”的评弹艺术来说,师父带徒弟,还应该是传承的基本方法。
评弹界还特有茶会谈道,即过去茶馆有为评弹艺人专设的上午茶,评弹艺人称其为茶会,艺人们习惯每天上午在那里聚会,饮茶交谈。所谈内容除了演出业务之外,主要的便是谈书道。道,便是演出经验、艺术理论,资深的艺人对艺术切磋交流。青年艺人们陪坐恭听,获得教益。这也是艺术思想、艺术理论的传承。由此可见,评弹兴盛时期,无论评弹艺人还是社会各界,都具有适应评弹艺术发展的土壤。尽管这些方法是辅助性的,但是至少说明评弹的兴盛与社会的支持和民众的追捧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要传承评弹艺术,需要那时的氛围和生存的环境。
悉心培植评弹听众
我认为重视宣传江南文化,悉心培植评弹听众是很重要的,因为听众是艺术的欣赏者,同时也是评判者。评弹艺人过去称听众为衣食父母,这是从谋生角度说的。其实从艺术的角度讲,听众是审美的主体,评弹是其审美的对象。评弹没有了听众,便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听众对评弹艺术的形成、存在和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过去我们常说评弹编演人员是艺术的创造者,听众是艺术的欣赏者。然而现在看来评弹艺术是剧本作者、演员与观众一起互动才使其成为雅俗共赏的江南文化艺术的。
在评弹界流传着不少听客听书入迷的逸事传闻。有人坐在水缸盖上听书,不慎翻落缸里,半身浸湿,仍不愿为了换衣服而离开,坚持听到结束。有人家里孩子来喊,说是有事,要他回去,他却说,不能因为家事,误了我正在听的国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评弹团每上演新排的中篇,排队买票的人绕场数匝,有时竟要通宵排队。在江南水乡,每有响档开书,附近河浜中鳞次栉比地停满了船只,其热闹拥挤,犹如庙会、节场。《苏州》杂志有一篇关于评弹的随笔中讲到,“一位年轻先生”说书时有许多“话搭头”,小落回时收到台下递上来的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是一把西瓜子和五香豆,并附打油诗一首:“多少‘奈末’‘老实讲’,好像念经老和尚,瓜子豆粒代记数,请你自己数清爽。”说是欣赏者,这是较易理解的。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视听艺术,有人把演出对受众的功能归结为:“感官的享受,情感的宣泄,心灵的净化,知识的丰富,情绪的愉悦”,可以说是作了基本的概括。有的老听客称之为“人生一乐”。他们把听评弹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为生活带来乐趣的一部分。这些热情听众,既是为了听故事情节,更是为了欣赏艺术。人物、情节和书中的关子、悬念,只有通过优美的表演,才能吸引人。当其以内容美,融合于艺术美之中时,才给听众更大的欣赏乐趣。
评弹听众是明确的。他们难得称是去听某部书,而总是称去听某某演员(比如,他们一般不说去听《玉蜻蜓》,而是说去听蒋月泉)。我曾对一位名家先生打趣说,人家不是来听你的书而是来听你的,人家也不是来听你的而是来听你的艺术的。他沉思了一下,点头称是。演员是艺术的载体。听众欣赏艺术,同时也萌发了对演员的喜爱与钦佩。在听众中产生了书迷,也同时产生了演员迷。
同时,我还认为,虽然听众的文化素养、生活体验和审美经验不同,但应该看到,听众对不少名家响档精彩演出的欣赏水平,是很高的,令演员都钦佩。为此,旧式书场在前排正中常设置一长形方桌,称“状元台”。一般成了资深听客的固定专座,以示书场和演员对一些老听客的尊重。这些听客的欣赏标准较高,偏重于技艺的赏析和理念的鉴识,往往好挑剔,难满足,反应也较冷。这些老听客,往往就是一些资深的评论家,他们为艺人所尊重和敬畏。在缺乏传媒舆论的社会中,听众的“口碑”议论,常具有权威性的影响。这种评论有时是即兴的直接的,那就是艺人常说的当场“扳错头”。
即使有一些听客是“听站书”的,或称听“戤壁书”,也都很有欣赏水平。这是一些买不到或买不起书筹、书票的听客,他们往往是听众中听得最入神,最着迷的,也是对评弹最爱评头品足的群体。听不同层面、不同段位的听众,所获得的审美感受和愉悦是各有千秋的。资深的听客,深谙评弹美学的三昧,自能识深鉴奥,审美的感受既多,兴味更浓。但是那些初入门的,听戤壁书的,也常能热忱投入,酣然动情,进入深沉感受的境界。
我谈到这些,不由得有些激动。我们对听众除了要他们讲文明,要尊重演员,别的还能有什么要求呢?听众不但应该有选择演员的自由,而且还能自由选择进场和退场的时间。当演员表演的书情书艺不能吸引或满足听客时,他们可以随意抽签退场。在几档演员同场合演时可以允许他们自由评论,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在研究评弹传承时,要有这种胸怀,那就是听众是上帝,他们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回忆起“文革”的教训:那时编演的样板化评弹,由于违反并破坏了评弹艺术,被听众斥为“评歌评戏”,受到唾弃。连热爱评弹的陈云同志也说:“一九七五年,到了上海……在收音机里听到评弹,已改得不成其为评弹了,很扫兴。”(见《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第84页)他认为之所以扫兴,是因为在审美活动中,引起听众的兴趣的艺术没有了。所以他再三提出,在传承评弹艺术时,一定要尊重听众的审美观和欣赏意愿。
加大剧本的艺术含量
我清晰地记得,1981年4月5日,陈云同志在上海找我谈话时就指示:“要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财政是次要的,体制可以变,有些框框可以打破。”所以我们在思考评弹传承时要学习和贯彻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要认识到评弹的书目繁多,流派各殊。每一书目,不同流派的当老师者便是其传承人。这是客观存在的,需要评定的是老师的资质,不需另评艺术的传承人及其等级。如今,传统书目多有沉没,艺术流失,传承人需搜求查访,但不能由上级指定任命,也不能如职称评定,限定名额。寻觅发掘优秀传统演出书目的传承人,并踏实细致地落实传承工作,实是当务之急。
剧本创作要讲艺术审美,包含对善恶的评定,真伪的辨别。正因为真与善是和艺术的美相辅相成的,听众要求看艺术中的真与善,追求新鲜、新意、新奇,所以缺乏新鲜感的剧本和重复演出是听众所厌弃的。由此不管是当代题材还是历史题材,都要重视艺术审美。对听众来说,当代题材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的书目,固然欢迎。当代题材若窥劣粗浅,那就不如艺术性高的其他题材的书目了。
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省内祖籍江浙的人士思念家乡,收罗大陆编演的评弹节目的录音便于聆听。即使是表现革命题材的,只要是艺术上乘的,照样欢迎,所以要考虑听众的兴趣。正因为各有偏爱,各有侧重,因此不能要求书目题材千篇一律,要根据听众的喜爱以及自己所长选择题材,创作书目。这正如俗话所说“百货中百客”。同时也要考虑到听众的兴趣随着年龄、经历等变化是会转化的,有人趣味宽广,有人就相对褊狭。正是由于众多的听客有着众多的审美趣味,才使得多种艺术手段、多种艺术风格能百花争鸣,百花齐放。宽广的趣味点燃起炽烈的、喜爱艺术的热情。
评弹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能容纳褊狭的口味,即听众对一门艺术、一位演员以及其艺术风格爱得执着,爱得专一,爱得风魔。所谓书迷(演员)迷,都是狂热的爱好者。这种狂热是催发艺术繁荣的动力,剧本作者也需要知晓,可在创作中予以兼顾。又如评弹与其他戏剧不一样,要有一定的宽松度。20世纪50年代,上海评弹团受国外剧团来沪演出的影响,曾在演出中篇时,推行幕间入场的制度,听众很难接受,最后只得放弃。听众只服从艺术欣赏所需的约束,当他们为艺术所感染,兴味盎然时,他们自会屏气凝神,注目侧耳,悄然无声。
作为评判者的听众,在听书过程中,对演出的感情上的共鸣和理性的评定是互相交织的。作为评论者,他们鉴裁着书中人物和伦理道德的是非曲直,判断着说书人的逻辑理念和观点,同时也品评着演员技艺的优劣高下。这一切或在现场,或在散场以后,通过多种渠道反馈给演员。正是这种群众性的评论、口碑,成为推动评弹艺术不断提高的一股不小的力量。
自然,归根到底评弹的生命在于不断地在各个环节上进行融合和提高,她需要观众予以积极支持,尤其是南方地区的民众要通过对江南文化的理解和热爱,为传承评弹创造良好的氛围。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迫切感,因为中国文化是世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评弹和创新评弹也是为人类和世界文化尽了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