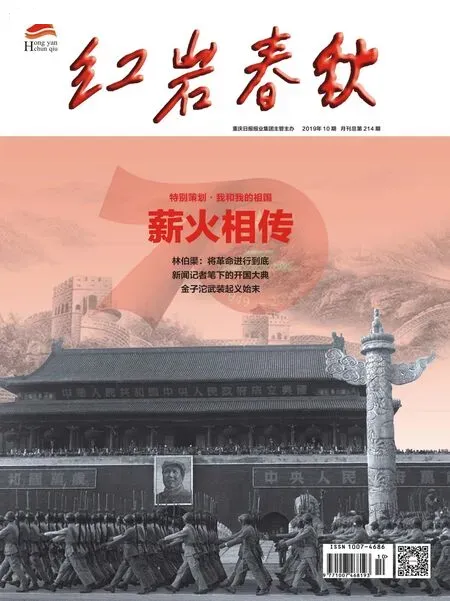历史的叩问
■简 奕
中山四路是藏于重庆老城区的一条小街,不足一公里,却被数十年树龄的黄葛树铺满。小街上,处处是民国时期的老建筑。我的家,一度就在小街里。
无数次散步在小街,在老建筑庄重的凝视中,任思绪飞扬。
走过人民小学,这是著名的“马背上的摇篮”,随刘邓大军一路征战的风尘,来到重庆,从此扎根。走过桂园,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就驻足于斯。走过重庆市委,里面的蒋介石官邸、美龄楼、民国政府行政院大楼等重点文物,保护完好,至今仍供办公使用。经过戴笠公馆,老街的尽头,曾家岩50号周公馆已在眼前。小广场上,有一尊周恩来铜像,他眼望远方,正迈步前行,似乎有着无尽的征程。
我的工作如同这漫步,每天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我供职于党史研究室,早年常会见到很多老人。“叩—叩—叩……”一个患了帕金森氏症的老人来了,伴着拐杖敲击老式木地板的声音,挪到我们办公室。白发的老主任与他非常熟稔,一边拍着他的肩大声谈笑,一边不忘以略带调侃的语气向端茶送水的我等小辈介绍:这是大少爷哦,当年参加华蓥山起义,他是坐着滑竿赶去的……
这样的氛围,使我的研究自然格外关注宏大事件背后那些处处可见的感动和细节——
它是中共早期重庆地委一场民主生活会的记录。倍受中央关注的重庆党内团结危机,其实源于种种误解,而通过民主生话会,终消释于坦坦荡荡的陈述事实、见骨见血的批评反省中,从而勃然怒放出幼年时期的党如火如荼的朝气。
它是朱德口中的“天下红军是一家”。长征途中,面对党内巨大的分裂危机,朱德要解决的不是“怎么走”,更不是“跟着走”,而是怎样弥合党内分歧,团结同志跟着中央“一起走”。
它是陕甘宁边区党心民心的水乳交融。从“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到边区百姓送匾“人民救星”,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对毛泽东态度的变化,体现出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宗旨和情怀。
它是新中国第一任监察部长钱瑛弥留之际说的“我朝前看”。这位党内有名的“女包公”铁面无私,“文革”时哪怕受尽折磨,却始终相信自己的追求,相信党的前途。她在病床上预言前行的光明,而对自己的结果,又何其坦然。
这些细节与感动并不遥远,它们就在一份份白纸黑字的史料中,只要你潜心读罢,其中的人和事就会鲜活而厚重。
古人常常叹道:“微斯人,吾谁与归?”而被优秀传统文化和共产主义理想理念所锤炼造就的,正是这样的一批共产党人。他们“不怕鬼”,有信念,能战斗;他们扛上历史的责任,担着国家民族的使命,向前看,不回头;党性在他们身上,绝不是干巴巴的几句概念,而是如此生动、真实地存在着……
又一次漫步在小街,停在周公馆前。这次,我想起了费正清。
当年费正清和谢伟思等美国人,也常在饭后沿着这条路走到周恩来办公室做客。在频繁的交流中,他们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有了自己西方式的解读。费正清说:“在周恩来所住的阁楼里,臭虫可能会从顶棚上掉下来,雨水也许会漏到床上,但他们的宗教热忱和思想信念照旧如火如荼,绝不动摇。”
想着费正清的话,我伸手欲叩周公馆小小的院门,却又停住,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吁出一口长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