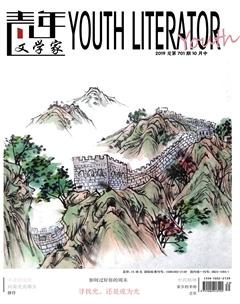论世阿弥能乐论中的“幽玄”思想
摘 要:“幽玄”本复杂多义,但贯穿整体的特性最终都归纳于“深度”二字,及至世阿弥时代,“幽玄”又增添了高雅、细致的“艳”的色彩。世阿弥特有的着眼点,令“幽玄”本身的内涵不断得到扩充,成为适用于能乐世界的理论标杆。本文从“梦幻能”、“三体论”、“花”及“九位”的角度切入,旨在分析世阿弥追求“余情”的意识,探寻世阿弥极致的“幽玄观”,阐释其“幽玄”思想里的超自然性。
关键词:日本艺术;能乐;世阿弥;“幽玄”;“余情”;“花”
作者简介:王卉怡(1995-),女,汉族,江苏省镇江市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系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日本文学、艺术。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9--03
日本的“幽玄”思想贯通于茶道、文学、美学等多领域,藤原俊成统括“心姿”妖艳、恍兮惚兮的“余情”等种种风格时提出“幽玄”这一概念,促使日本和歌诗人逐渐注重对意境的把握。能乐鼻祖观阿弥曾积极将藤原俊成所提倡的“幽玄美”意识融入能乐之中,凭借“幽玄”风格的表演形式提高了演出质量。世阿弥经青年将军义满发掘,又受二条良基等人宠爱,集新兴武家社会关心于一身,在雄厚的经济支援下,和父亲观阿弥一起,将曾经不过是乡间娱乐的猿乐推广至文化圣地京都,最终将能乐发展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国性的舞台艺术。
“幽玄”该概念有着相当复杂的历史,可以参考能势朝次博士所著的《幽玄论》。小西甚一(1954:167)在《世阿彌十六部集》①末尾“解说”部分提到,虽然“幽玄”用例复杂多义,但贯穿整体的特性最终都归纳于“深度”二字,及至世阿弥时代,“幽玄”又增添了“艳”的色彩。“艳”意指高雅、细致、年轻贵妇人般的美感,在此基础上蕴含深度后,便发展为世阿弥主张的独特的“幽玄”。“私は、世阿彌の使っている「幽玄」を、たいてい「優美」と譯しておいた。いくらか原語よりも幅と奥行が足りないけれど、まあ八十パーセントぐらいは當っているであろう。”(我大抵将世阿弥使用的“幽玄”翻译为“优美”,虽然和原词相比,幅度、深度都不够,但也八九不离十了吧。)②比起现实中的“幽玄”,作为憧憬而衍生的“幽玄”是更纯粹的美学。小西甚一(1954:168)表示,世阿弥将纯粹的“幽玄”于舞台上再现,因此,他所提倡的是一种理念上的“幽玄”。
世阿弥独特的着眼点,令“幽玄”本身的内涵不断得到扩充,成为适用于能乐世界的理论标杆。本文旨在从“梦幻能”的角度思索世阿弥追求“余情”、内敛美的意识,分析“三体论”以探寻世阿弥极致的“幽玄观”,并围绕“花”及“九位”艺风体系,阐释能乐家的精神向往与人生目标,研究世阿弥“幽玄”思想里的超自然性。
一、“余情”浸透的“梦幻能”
观阿弥生前周游各地,主张“现在能”,即尽可能取材于普通民众熟悉的故事,反映现实主题。然而,世阿弥继承“座主”以后,首先突破“现在能”的束缚,在题材上创新,演出并确立了描绘现世“此岸”与死后“彼岸”关系的“梦幻能”格式。“梦幻能”前场是亡灵、神灵、精灵等的化身在旅行者面前显现,边诉边舞间讲述死前桩桩旧事,而后消失,于后场才表现真实面目,题材多取自《伊势物语》、《平家物语》等背景为贵族社会的文学作品。其中,《伊势物语》是由120多篇简短章节组成的歌物语,以在原业平一类人物的恋爱为主线;《平家物语》为战纪物语,记述以平清盛为核心的平氏一门的兴亡,经琵琶艺人的说唱传播甚广。
世阿弥从文学作品中选取适合编入歌舞的题材,将抒情与叙事相结合,创作出的“梦幻能”韵味无限、“余情”袅袅,至今仍被频频效仿。从“现在能”过渡到“梦幻能”,标志着世阿弥由表象美转为追求内敛的意识美。“梦幻能”作品结构虽类似,但内容不尽相同,情节多样。巧妙引用古文修辞,使之文辞瑰丽,在视听之间,观众之前,打造“余情”美丰沛的艺术世界。
连歌大家二条良基多用“幽玄”一词,在连歌论《连理秘抄》和《筑波问答》里都有涉及,他的论说也影响了世阿弥。藤原定家将“有心”、“余情”归为价值概念,将“幽玄体”归为样式概念,明确区分。而二条良基却并未刻意区分,他将“幽玄”与“余情”相结合,主张美学内容上与藤原定家的“妖艳”相似的“幽玄”样式概念,且这种“幽玄”本身就自成一种价值格局。
世阿弥的“幽玄”思想和二条良基的主张一样,都通达艺术的理想境地,具备很深刻的价值意义。定家主张的“余情妖艳”及“幽玄”与长明、良基、正彻、心敬主张的“幽玄”有相通之处,都认可“幽玄”中涵盖的价值性意义,世阿弥的“幽玄”思想也强调样式概念,根植并浸透着“余情”。“幽玄”与“余情”连接之处,乃是能乐创作者、能乐演员与能乐观赏者心境所达之点,是一种体会到虚无缥缈的境界。高桥和幸(1982:25)在论文《世阿弥における幽玄と餘情の相関》中阐述到,日本中世艺术以“余情”理念为基盘,致力于追寻“妖艳”及“幽玄”,而世阿弥所说的“幽玄”、以及他一生撰写的能乐理论、能乐构造中毫无例外遍及“余情”,其性质与“余情”不可分离。
世阿弥的努力促使能乐迈入文学殿堂,更是日本美学界歌颂的对象。然而,笔者认为这种重心都放于贵族文化的做法未必完美无缺,后世研究时也不可绝对地判定“梦幻能”优越于“现在能”。宿久高(1997:47)就指出,“梦幻能”的出现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情趣上都迎合了以“公家”和代家权力阶层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口味、恶好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出“梦幻能”这一戏剧艺术形式的虚幻性、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
二、女性化、贵族化色彩
世阿弥认为“幽玄”是所有艺道的最高境界,在能乐中“幽玄”风体更是第一重要,然而,他亦清楚并非所有演员都能真切领悟“幽玄”的精髓。“幽玄”是特別的感情,为便于普通人理解,世阿弥以王朝贵族为例,强调朝臣贵人们品性高雅,持有高度的优美和柔和,其姿态风度可谓“幽玄”。朝廷的用语、音曲、舞蹈优雅华丽,可谓“幽玄”的代表,他将这种形式的“幽玄”看作能乐美学的中心,不断精进追求。
对此,井上正(2016:55)提出了自己的观点“ところで、元来、「幽玄」は「光の届かない暗く奥深い存在」であり、世阿弥のいう優雅艶麗とは、ほど遠いように思える。つまり一般にいわれる「幽玄」は、無常感ただよう亡びの美学に対し、世阿弥のそれは、女性的、貴族的で明るさがある。”(原本“幽玄”是指“光触碰不及的、阴暗深奥的存在”,与世阿弥所言的优雅艳丽相差甚远。即,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充满无常的凋零美学,世阿弥主张的“幽玄”带有明丽的女性化、贵族化特征。)
世阿弥所言的“三体”即三类角色的特征又可总结为,“老体”是“闲心远目”,“军体”要动用全身力量,而“女体”不可太用力,应以心境为主要支撑。“老体”、“军体”自然也需“幽玄”,但柔和优雅的“女体”更直观体现了世阿弥极致的“幽玄观”。“而して、その理由とするところは、女体はその姿態上、舞歌と最も自然に一体たり得るにあるものの如く、「舞歌一心妙得の感風」が、この女体の幽風にあるからであるとしている。われわれはここに於いて、再び、彼の幽玄が優美·閑雅を内容と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を覚ると共に、これもまた、児姿の稽古を基礎にして成立するもの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ところに、その優雅が深い洗練の成果であることを思わねばならぬ。”(“女体”姿态与歌舞最为融合,其幽玄风趣里恰恰具有“舞歌一心妙得之感風”,可以说世阿弥的幽玄思想中,优美闲雅是核心内容,以孩童时期的习艺积累为基础,是精炼考究而至的成果。),西尾实(1974:114-115)在《世阿弥の能芸論》一书中探讨“幽玄”与其艺态论关系时,如是总结。
世阿弥的能乐理论里,“幽玄”成为必不可少的构成条件,将其具象化解释,可理解为孩童、贵族、女性或天鹅的姿态,让人联想天女飘逸的舞姿,婉转音曲之间充分展现演绎者的艺术风派。“幽玄”之美是相对于“俗”的“雅”,虽有重要的“老体”“军体”角色,但相对于“男性化”更偏重“温柔雅致的女性化”,相对于“平民性”更注重“贵族性”,“温和”“柔软”“高雅”是绕不开的关键词。
实际上,这种改善发展的途径是势在必行的,毕竟能乐起源于下层庶民间的娱乐,若想拔高层次,将其提升至艺术殿堂,终究要学会汲取王朝贵族中的传统美学再加以革新,因此世阿弥才不遗余力地推崇高雅式的“幽玄”,以期创造出大众文化的新局面。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及一般,世阿弥革新的能乐可能过度迎合了贵族即统治阶级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宿久高(1997:46)表示:“无论是猿乐能还是田乐能,都是在地方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得到统治者的垂青后方得以进入宫廷幕府,从而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艺术。”
但是能乐的体系是不断扩充叠新的,世阿弥之后,其女婿金春禅竹深得《六义》、《拾玉得花》等的真传,极尽全力将佛教哲理导入能乐论,铺下幽深的宗教哲学基础,同时又有一定的创新。金春禅竹从佛教的立场,主张“泛幽玄化”,将“幽玄”与佛家的“六轮一露说”相联系,把“寿”、“坚”、“住”这作为“幽玄论”的根源,以此解释世阿弥的“九位说”。能乐在金春禅竹的探索下愈发独特,“幽玄”思想也被赋予更耐人寻味的解读。
三、习艺理念与艺风体系里的超自然性
《风姿花传》中世阿弥以“花”论述了“幽玄”之美,他认为“花”是能乐的精髓,象征着一种艺术魅力,从能乐演员的角度切入,“花”被喻为获得幽玄的艺术境界所需要的途径,亦是一种成果体现。达成“花”需要不断地习艺, “花”这一概念阐释了能乐家的精神向往与人生目标,可以说《风姿花传》不仅具有能乐论指导意义,还具备超脱戏剧,超脱物质形式的自然艺术性。
世阿弥獨特的着眼点,令“幽玄”本身的内涵不断得到扩充,成为适用于能乐世界的理论标杆。例如,他提出以歌舞二曲作为游乐的根源,以三体作为模仿的基础形态,其中,二曲的基础风派又能在孩童的歌舞中体现,此也为“幽玄”的根本艺风。在《年龄习艺条款》“七岁”一项内,世阿弥称孩童自然的表现里就有拿手的演技,不要轻率地教导好或不好,过度提醒可能会导致孩童失去干劲,厌倦习艺,停止艺术方面的成长;至于“十二三岁”的孩童习艺者,世阿弥依旧充分肯定他们的天赋,认为他们凭借童颜无论什么动作皆具备可爱的美感,是一种幽玄,其声音也清晰明朗,靠这两处优势,其余的缺点也不再显眼,优势反而更散发魅力,从中可看出世阿弥对于纯真性与自然性的尊重。
然而,他也清楚这些不过是“时分之花”,即短暂时期内的魅力,不是真正的艺术功底,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逝,若坚持加强练习,则可能实现“真之花”,即不会消逝的魅力、实在持久的艺术性质。表演之“花”与演绎者内心之“花”截然不可分,若想知花,先要知种,以花为心,以种为技。结合“时分之花”的实际情况,成立“真之花”,世阿弥遵循自然性的同时,不断谋求超越自然,探寻永不消逝的幽玄,这便是他强调的习艺之精髓。
《至花道》中,世阿弥还提出了“皮、肉、骨”的概念,将能乐表演比喻为人的身体,对于能乐演员来说,天赋的才貌是“骨”,后天在舞蹈歌曲上的努力修炼是“肉”,两者相结合创造出的“幽玄”风姿,即所谓的“皮”。在世阿弥看来,当时不少能乐艺人仅是略微演出了“皮”的风姿,还停留在表面的模仿,并非真正融合这三种概念。表演结束,观众沉醉于演技,静静回味依然觉得没有可挑剔的因素,才算演员“骨风”到位;无论怎么回想,演技的妙处无穷无尽,才算演员“肉风”到位;百般品味,仍承认演员行姿优美,才算真正的“皮风”。归根结底,无论是“花”,还是“皮、肉、骨”,世阿弥都要求演员达到真正的境界,而这一切必然要靠日积月累的习艺修行去实现。
就“皮、肉、骨”概念,李东军(2008:269)在著作《幽玄研究》中以“皮相”、“肉相”、“骨相”代称,他指出:“世阿弥将天赋比喻成‘骨相似乎并不妥,因为光靠天赋而不努力练习也是不行的,所以还是将‘心视为‘骨相方为妥当”。同时,李东军(2008:270)认为,世阿弥在《至花道》中使用“皮风”、“肉风”、“骨风”等“风力”说明“幽玄美”(皮相)、“习力”(肉相)与“心力”(骨相)之间的关系,这与刘勰所说的“风骨”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