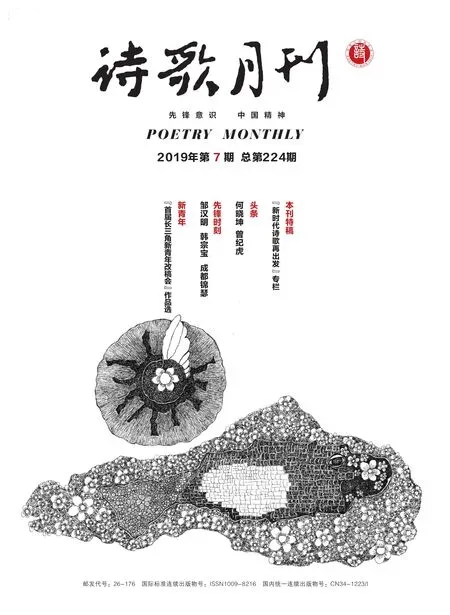自我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在我不在的地方(创作谈)
曾纪虎
阅读与写作汉语新诗以来,我并未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必然的“诗人”身份——我对俗世生活的依赖远远超过了对文学艺术的依赖。或者也因为,潜意识中认为人的生活是多样性的,我没有可能在某一角色中获得完满的自证。
能使人处于巨大焦虑之中的是对于生活与身体本身的忧患,而不是对于诗意更新的担忧。出生于1970 年代的江西的农村,父辈已化身为新时代的农民。村子靠近小县城,他们在农闲时节侍弄几分自留地,种植蔬菜,挑到城里沿街叫卖;家人每日忙碌而劳累。家里兄弟姐妹众多,我又是最小的一个,很少沾染农活;所以,年少生活贫贱如丐儿,却又能悠游无垠,体会穷困生活中闲散而忧愁的精神状态。身边玩伴,那些强壮的乡村顽童只使得我感到莫名的悲伤,今后,他们要过早地投入到农民身份中去,变为更加粗糙的人物。身体的羸弱和变故更为我带来了乡村的歧视,也为我赢得了似乎是超越的视角。我固执地知道自己以后会离开他们而生活,包括我的父兄姐妹。
十六、七岁的时候,由于一个缘分,我接触到了由汉语翻译过来的西方诗歌,我的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们似乎能连接到我在贫瘠的乡村生活中(虽然我还在继续,并未有脱离可能的乡村生活)所滋生出来的广袤无垠的幻觉状态。我获得了短暂的消极的逃离——不仅仅是逃离,而是藉此看到了,俗世生活在作用于可见的个体身上的同时完成了对于生活的某种奇妙的否定;也是对于固有的本质意义的“自我”的否定。接下来的读书、写作汉语诗歌等等或许是对这种状态的延续。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我开始需要面对自己已经完成的一些习作,发现一切都显得糟糕:写作的观念、词语、节奏感和句式的选择、以及诗歌中常常出现的主题都到了让自己产生疲倦的状态。沮丧、不完满、怀疑等情绪笼罩了我,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而我错误地以为,无力继续下去意味着我与自己依附的生活距离太近,我的生活要发生一些变化,我要和人群距离更远些;我的生活需要更新与对抗,以此换来诗歌技艺的更新。现在看来,我当时缺乏的是可靠的知识与机缘;需要的是对诗歌中“写作自我”的更进一步的认识。
年轻而危险的诗歌写作者常常是一个可怕的励志者,在加强自我的抗拒之时,走向了一条对抗之路。其实,我更应该是一个逃离者与观察者,对抗并不适合我;对抗是生命欲念的加强。认定了人的生命欲念的本能之恶;避开日常生活并不全然是懦弱行为,而是对于生存之恶的尽可能的规避。“美”与“良善”的幻觉不是我在少儿时代所要悠游其中的吗?虽然当时只是以一种未来的状态填塞在一个未成年人的胸臆之中。我个人成年的漫长年月,因偶然的机缘,要用现代汉语诗歌来完成;它瓦解了我面临的必然性的障碍,我曾获得了确确实实的我愿意知悉的愉悦。
大多数情况下,源于已获得的惯性知识,我们确定了本质意义的“自我”;个人经历、阅读、写作、体悟都建立在一个固定的自我身上,强调了“我”的历史的同一性。这种固定的生活常识是使自己获得安全感的重要模式;但是,生活经历无不在考验、磨难它。我个人没能做好,也因此排除了某种确定“自我”的模式——我真的一直是这个可以确定的逃离者吗?或者说“逃离者”拥有稳定的状态吗?臆想中的逃得更远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在诗歌的写作中强调逃离的绝对性曾使得我的阅读、写作与生活陷入困境。所以,我现在倾向于认为“写作中的自我”拥有的是有限的同一性。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生命、文化、美学表现、社会生活都如此;建立在变化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写作中的自我”可面向自我的差异性存在。
倘若“灵魂”有可靠的基础,即它是具体的存在而非被抽取了具体存在的概念;那么,个体并非是某个大的“灵魂”的分有,他本身即是“灵魂”一词的不可或缺的推动者。个体与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保证了这一词语的有效。个体的不同阶段也将拥有不同的“自我”。个体生命的阶段性存在是个体得以延续的基础,个体的成长因之才获得了意义。并因如此,记忆,以及用以留下记忆痕迹并进行推断的各种文化符号才得以展示各自的魅力;诗歌,也是与记忆痕迹相关的诸种符号体系之一。在诗歌中,写作者自我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微妙把握实为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自我内部的短暂平衡、否定性的直觉、求新的欲念在含混的背景下告知了未来生命的价值;我们每每愿意为之做出努力,牺牲暂有的自我的平衡性而将自己放在一个可能未来的不可知的端口。这个行为,实际上是认同了自我的差异性;在诗歌写作中,它是推动继续写作的一个动力,即面向不可知的探索行为;同时,写作也有了面向未来的品质。与大多数诗人的给予心态不同;我认为好的诗歌是具有开放意愿的、是解释性的;认同了自我的差异性的存在,为此,我愿意认同广泛他者的存在。交流与传播发生在各个有效个体之间,而不是发生在无效个体之间。向内看去,我持有的会是什么,那个大致同一的自我持有的不过是某些可能成立的美与良善的瞬间;我们把它传递出去,以形成人的活动与意志;如此,各类作者将处于绵延不绝的相互阐释的状态。每一特定期间,每一特定的自我所完成的阐释状态无不为后来的诗歌艺术提供潜在的文本。
不同阶段、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诗人”的涵义不同;我自身的经历让我不曾有意识地给予自己一个纯然的诗人身份。生活有如一场漫无目的的劳役,我身在其中,或许有过逃离的愿望,但是,这并不够。所以,我的阅读与写作不是一个有预谋的逃离或超越的过程,而是,时不时地为生活所挤迫;更多的阅读,更多的写作,更多的交流——只是为了在现世生存中有更好的机缘面对自己。面向生活,面向诗歌,或面向其它;因此,我以为,我在转换不同的身份,为了活着本身这个事情。对生存的超越性的需求或许是漫长的文化积累中的某条线索,我却看到了其中的虚妄;我写作诗歌、阅读诗歌,不是为了超越现世;是为了就我自己的状态来更真切地体会自己的生存。或许,文明之中有很多优秀的超越者,但是很遗憾,我是那个脚跟被生活之手抓得很紧的那一个。我的写作只涉及我个人的生存与思索,我尽可能诚挚地将它们呈现在你面前。
——浅评电影《道士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