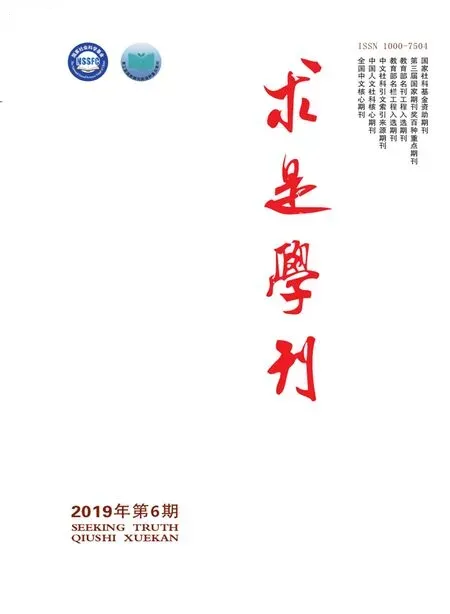对“作品”一词内涵外延及其适用方法的法逻辑诠释①
张继成
近来,一些侵犯著作权的案例引发了法律实务界和学术界关于“作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与法律适用方法的热烈讨论,②主要讨论参见赵海燕、米江霞:《关于不同类型作品及其法律保护的探讨》,《西部法学评论》2013年第5期;李琛:《论作品定义的立法表述》,《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陈博:《作品的界定:作品类型与作品独创性标准》,《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82—85页。例如,李琛在《论作品类型化的法律意义》(《知识产权》2018年第8期,第3—7页)一文中指出,学界和实务界主要有四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方案认为争议案件虽不属于立法明确列举的类型,但符合作品要件时,援引《著作权法》第3条第(九)项予以保护;方案二认为争议案件虽不属于立法明确列举的类型,但符合作品要件时,援引《著作权法事实条例》第2条(作品的定义)予以保护;方案三认为法院在《著作权法》第3条规定之外无权设定其他作品类型,并认为第(九)项中的其他作品只能是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规定的作品。也就是说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的都不应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等等。也引申出对“作品”概念的构成要件及相关法律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深层次思考。笔者从事法律逻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多年,认为这是认识法律逻辑学重要作用的一个活脱脱的生动案例,故不揣浅陋,希望就“作品”概念的逻辑特征及法律适用方法谈一点自己的想法,并向知识产权法领域的专家学者讨教。
一、“作品”概念的内涵、外延是通过多种定义方法揭示出来的
1.“作品”概念兼具法学概念、法律概念和日常概念三重身份
法学概念是人们在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法律解释以及立法建议中所使用的概念。“作品”一词在《著作权法》颁布之前,就广泛出现在中外法学界的学术著述之中,并且至今依然是出现在各种法学研究、法学教育等领域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因此,“作品”是一个标准的法学概念。
法律概念就是在有效法律规范中出现的,反映法律所调整的行为、事件等思维对象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法律概念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必须存在于有效法律规范之中,是现实的而非历史的。不存在于法律规范体系之中的概念都不是法律概念。法律概念的第二特征是法律概念具有规范性的意义,法律概念反映的对象都是法律所调整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的概念。这两个特征就是判断一个概念是否属于法律概念的基本标准。法律概念的功能:(1)法律制度确定概念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形成法律规则和原则的。(2)法律概念是识同别异的思维工具。(3)法律概念是进行法律思考和交流的工具。没有法律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智地思考法律问题。没有法律概念,我们便无法将我们对法律的思考转变为语言,也无法以一种易懂明了的方式把这些思考传达给他人。(4)法律概念是法律价值的储存工具。(5)“概念是司法推理的有价值的工具——没有概念,司法活动就不能得到准确的实施。”①参见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470页。
从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颁布《著作权法》之日起,在我国大陆地区,“作品”这个概念就不仅是一个法学概念,而且是一个具有法律规范性的法律概念了。因此,法学概念与法律概念是紧密联系而且是可以相互转化的:(1)法学概念一但被立法者所采纳,进入有效法律规范之中,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此时便转化为法律概念了;(2)法律概念也可以转化为法学概念,当某一概念所反映的对象不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时,它就转化为法学概念,如“反革命罪”“投机倒把罪”等概念就是例证。一国的法律概念对另一个国家来说仅仅只是法学概念。
法学概念与法律概念的区别在于:法学概念没有在法律规范中出现,不具有规范效力。在没有成为法学概念、法律概念之前,“作品”概念还广泛出现在各门具体科学以及日常用语之中,因此,“作品”概念也是一个标准的日常概念(我们将法学概念、法律概念之外的概念统称为日常概念)。
2.“作品”概念既有学理定义又有法典定义
对于一个日常概念、法学概念或法律概念,从学理的角度揭示其内涵或外延的就是学理定义(又可以称之为教义学定义),在正式法典中给一个概念的内涵或外延做出说明或规定的就是法典定义。
对日常概念“作品”,《现代汉语小词典》给出的学理定义是“指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品”,《现代汉语辞海》给出的学理定义是“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创作成品”。对法学概念“作品”,《百度百科》给出的学理定义(法教义学定义)是“通过作者的创作活动产生的具有文学、艺术或科学性质具有独创性而以一定有形形式复制表现出来的智力成果”,等等。
对概念“作品”,《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给出的法典定义是:“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日本著作权法》第二条给出的法典定义是“指文学、科学、艺术、音乐领域内,思想或者感情的独创性表达”。
日常概念、法学概念、法律概念的定义可以只有一个,也可以有多个。学理定义与法典定义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不是每个法律概念都要给出法典定义。因为,如果对每个法律概念都给出法典定义,这将使得每个法律规范体系无比冗长繁杂。所以,在立法实践中,只有少数法律概念才有法典定义,大多数法律概念或日常概念的内涵外延只能从学理角度来明确其内涵外延。
在法典制定过程中,哪些法律概念应该给出法典定义,哪些法律概念无许给出法典定义,学术界至今没有给出一套明确的标准。笔者认为,并非每个新的法律概念都要给出定义,也并非每个旧的法律概念都不给出定义,是否给出定义,关键要看它在构建一个法律规范体系过程中的地位、功能、重要性。
笔者认为,由于著作法中的所有权利与义务都是围绕“作品”概念展开的,“作品”是整个著作权法的基石,又由于著作权法并不保护所有类型的作品,所以,必须对这个概念给出明确的法典定义,否则,对一个作品是否就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外延的判定活动将无法进行。
从上述若干个定义可以看出,与一般情况相反,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外延范围远远超出了日常概念中的作品概念的外延范围。因为,日常概念中的“作品”主要指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法学概念和法律概念中的“作品”不仅包括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而且还包括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类实践活动中所创作出来的所有作品。
3.“作品”概念的说明性语词定义与规定性语词定义
我们将说明以语词形式所表达的概念具有何种含义的定义方式叫作说明性定义。上述《现代汉语小词典》《现代汉语辞海》以及百度百科对“作品”概念的含义都是说明性语词定义。说明性语词定义不具有规范性和强制力。
我们将给以语词形式所表达的概念(客观事物本身)规定出一些属性的定义方式叫作规定性定义。《著作权法》第10条中的所有定义,《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第3条、第4条、第5条中的所有定义都属于规定性语词定义。规定性语词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规范性、强制性,但它的规范性、强制性只有在完整的法律规范命题(即该命题中既有法律事实的构成要件又给该法律事实赋予了某种特定法律效果)中展现出来,孤立的规定性语词定义是没有直接的规范性和强制力的。具体而言,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在遭受第47条、第48条所列举的侵权行为侵害时,行为人将承担第47条至第54条规则所列举的民事责任。
4.“作品”概念的内涵外延是通过积极定义和消极定义的方式展示出来的
在法典定义中,立法者如果仅仅只从正面直接指出一个法律概念具有哪些属性,包括哪些外延,我们将这种定义方式称为法律概念的积极定义。积极定义的作用在于,任何一个具有法律概念内涵的对象,都属于该法律概念的外延,都成为该法律概念的示例。
在法典定义①法典定义“很少有精确定义的原因有二:(1)对于法律语言中使用的概念,通常无法非常精确地下定义,以及(2)人们往往想要留一些决定空间,以求保留法律适用的弹性。”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蔡圣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页。中,立法者如果仅仅只指出客观对象(被定义项)不具有哪些属性,或者指出哪些对象不属于该法律概念外延的范围,我们将这种定义方法称为消极定义。消极定义的作用在于通过排除的方法确定法律概念的外延。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就从正面指出“作品”是指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这两种本质属性的智力成果,因而这个定义就是一个积极定义。《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中关于文字作品、口述作品……模型作品的定义也属于积极定义。
著作权法不仅对“作品”概念给出了积极定义,而且也给出了“作品”概念的消极定义。例如,《著作权法》第4条指出“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里,立法者间接告诉我们:凡是具有违反宪法和法律、损害公共利益两种属性的作品都不是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凡是没有违反宪法和法律、没有损害公共利益的作品都是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
不仅“作品”概念的内涵是通过积极定义和消极定义的方式给出的,就连这个概念的外延也是通过积极定义和消极定义的方式给出的:《著作权法》第3条正面指出哪些属于“作品”的外延,《著作权法》第5条则从反面指出哪些对象不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的外延。
5.“作品”概念的完整定义与局部定义
在法典定义中,如果“特别要以能够(一并)掌握那些(也应该包摄到此概念下)最外围的边界案件为导向”,那么这个定义就是一个完整定义。①英格博格·普珀著:《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蔡圣伟译,第34页。譬如,在定义“身体伤害”时,就要让所下定义也能够包含甩巴掌、吐口水或是剪下胡须的情形。正因为如此,法律定义往往是模糊的、不精确的。我们强调法律概念的模糊性、抽象性,但并不能否认有些法律概念是能够给出精确定义的。例如我们给部分量化概念所确定的定义就是精确、明白、清楚的:“重大之财产损害,是指5万欧元以上的损害。一个对象若是具有750欧元以上的价值,即属‘贵重物品’。一个对象的价值若是在50欧元以下,即属‘价值低微之物’”(35页)。如果法律定义并不是以掌握某概念的所有边界案例作为目标,而是给出实现其上位概念的充分条件的定义就是局部定义。②参见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蔡圣伟译,第41—42页。立法实践中,严格意义上的完整定义是十分少见的,它通常是以既对一个法律概念的内涵给出完整说明或规定,又对该概念的外延给出明确说明或规定的方式实现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2条关于法官的定义,“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内涵定义——作者注),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外延定义——作者注)”就是一个完整的法典定义。
在《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立法者对“作品”概念的定义是以局部定义的方式完成的。要对“作品”概念的完整内涵和外延有一个全面了解,就必须整合以下各个条文。笔者认为,作品概念的内涵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本质(实质)要件(T1):《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在《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立法者给出的所有属性中,独创性(T11)、可复制性(T12)才是“作品”概念的本质属性和实质要件,下面四个构成要件所描述的属性只是“作品”概念的特异属性和形式要件。
范围要件(T2):《著作权法》第3条中所说的文学(T21)、艺术(T22)、自然科学(T23)、社会科学(T24)、工程技术领域(T25)的作品;
主体要件(T3):《著作权法》第2条中所说:
中国公民(T31)、法人(T32)或者其他组织(T33);
根据其作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的外国人(T34)、无国籍人(T35);
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外国人(T341)、无国籍人(T351);
首次在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成员国出版的,或者在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同时出版的未与中国签订协议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的国家的作者(T36)以及无国籍人(T3511)。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著作权法所说的主体不包括“智能人”“机器人”;也就是说“智能人”“机器人”创作的作品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法律、道德要件(T4):《著作权法》第4条中所说作品,就是那些没有违反宪法(T41)和法律(T42)、没有损害公共利益的作品(T43)。
期限要件(T5):《著作权法》第21条所说的:
自然人的作品是在作者终生或死亡后第五十年12月31日之内的作品(T51);
如果是合作作品,该作品是在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12月31日之内的作品(T52);
如果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该作品是在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12月31日之内的作品(T53);
如果作品自创作完成后五十年内未发表的,则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T54);
如果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摄影作品,该作品必须是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之内的作品(T55);
如果该作品自创作完成后五十年内未发表的,则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A=具有T1∧T2∧T3∧T4∧T5的智力成果(B)。
当然,上述内涵只是判定一个作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概念外延的一般构成要件。至于职务作品、委托作品等概念除了应具备上述一般构成要件之外还应具备一些特殊构成要件,这里不再赘述。
作品概念的外延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
X.《著作权法》第3条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X1:文字作品;X2:口述作品;X3: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X4:美术、建筑作品;X5:摄影作品;X6: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X7:(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X8:计算机软件;X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但事实上,除《著作权法》之外,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行政法规对这里的“其他作品”做出过明确规定,因此,实际作品的外延类型上只有八种。①我们也可以将此称为“作品”的外延定义。“外延定义就是指被定义的普遍词项所适用对象的汇集。”参见欧文·M.柯匹、卡尔·科恩:《逻辑学导论》(第11版),张建军、潘天群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7页。一般而言,定义都是内涵的,即通过揭示被定义项本质属性的方式来明确概念。希望未来有某个特定法律、行政法规能够开创先河)。
Y.《著作权法》第6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但非常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国务院并没有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外延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概念的外延。
Z.《著作权法》第5条所规定的以下三种形式的智力成果不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一)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二)时事新闻;(三)历法、通用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来说,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的外延范围应当是:
A=(X-Z)+Y(因为Z的内容都属于X中的文字作品,所以应该减去)
但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实际的外延,所以,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的实际外延范围是:
A=(X-Z)。
上述公式分别从内涵、外延两个方面给出了《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概念的(相对)完整定义。
二、“作品”概念的法律适用方法
“在学术界,为了清楚、明了并且尽可能精准地确定概念的意涵,就要对概念下定义。”法律定义的目的是要满足“让被定义的概念更加清楚、明白、明确”。法律人学习、背诵法律定义的理由在于“法律人有证立(说明)其包摄的需求”②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蔡圣伟译,第29、35页。在该书第37—41页中,普珀介绍了两种将个案事实归属到法律构成要件之中的水平概念锁链方法和垂直概念锁链方法。(即完成将案件事实归属于某个特定概念之下的任务)。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判定作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的方法有三:
1.内涵判定法,即凡是符合“作品”概念的完整内涵(上述五个构成要件)的作品都属于它的外延,不论该作品是否在《著作权法》第3条所列举的九种类型之内,该作品都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作品”的外延范围。
2.外延判定法,即不论作品是否符合上述五个构成要件,只要它在《著作权法》第3条所列举的九种类型之内,那么,就认定它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的外延。
3.内涵外延综合判定法,即先根据内涵判定法看其是否具备上述五个构成要件,将那些不符合构成要件的排除在外,然后,再看该作品是否在《著作权法》第3条所列举的九种类型之中:在,则认定其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的外延;不在,则认定其不是《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的外延。
在上述三种方法中,第二种方法明显是我们应该抛弃的判定方法。因为仅仅根据被判定作品在上述九种类型之中而不对它进行内涵审查,就会将大量不符合实质要件、主体要件、法律道德要件、范围要件、期限要件的作品当作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这种认定既不符合形式正义,也不符合实质正义。
在笔者看来,在判定一个作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外延的方法或标准中,作品的本质属性或五大构成要件具有决定意义,《著作权法》第3条所列举的九种类型仅仅有参照意义。
第三种判定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是理想的法律适用方法。这是因为,这种方法虽然首先将不符合构成要件的作品排除在外,最大限度地防止了不符合形式正义的情况出现,但它还要看被判定作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第3条中所列举的那九种类型之中的作品:属于,则予以保护;不属于,则不予保护。但这种方法却将那些真正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的作品排除在外了,违反了同样情况同样对待的法律原则。当今社会是鼓励创新的时代,新生事物每天都在不断涌现,许多新生事物也可能具有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的所有构成要件,如果仅仅因为这些新生事物不在上述九种类型之中,就将其武断地排除在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的外延之外,这将与《著作权法》“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的立法目的是背道而驰的,是不合理的。
笔者看来,如果仅仅因为某一待认定新作品不在上述九种类型之中而不予保护,那就是告诉人们在进行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只能按照上述九种类型进行创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著作权法》就不是一部促进、反倒是一种阻碍“真正的”理论创新或实践创新的法律规范了。
因此,笔者倾向于将第一种判定方法作为判定一个作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的外延范围的法律适用方法。这是因为,从逻辑的角度看,“作品”是一个不可数的普遍概念,其外延无法穷尽。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判定一个作品符合上述五个构成要件(内涵),同时也能将该作品归属于《著作权法》第3条中所列举那些类型中的某个特定类型之下。因此,这种判定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既具有形式正义的法律属性,也具有实质正义的法律属性。在个别情况下,只要一个作品符合了前述五个构成要件,即使它并不属于上述九种类型中任何一个,这种作品也应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的外延范围(这样,即使没有具体给出民间艺术作品的外延范围,只要符合作品概念的内涵,就可以将其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因此,在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不能并存的情况下,这种判定方法更重视法律的实质正义,实现个案正义。
在第三种判定方法中,对被认定作品进行价值评价至关重要,其中具有独创性和可复制性的作品是否“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和“存在违反宪法、法律,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就是价值评价标准:符合上述价值标准,即使不在上述列举范围之内,也应保护;不符合上述价值标准,即使在上述列举范围也不保护;存在违反宪法、法律,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即使在上述列举范围之内,也不保护;不存在违反宪法、法律,不存在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即使不在上述列举范围之内也应予以保护。
笔者认为,当今社会每天都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出来,而人的认识能力又是有限的,立法者不可能将未来出现的新生事物概括无遗。而制定著作权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鼓励创新、保护创新。如果被认定作品具有独创性和可复制性(并符合其他构成要件),而它又没有在上述列举范围之内,这恰恰说明这些作品是我们以前没有认识的,是新生事物,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三、“作品”概念法律适用中的三种解释方法
为了避免仅仅因为新型作品不在上述九种类型之中,就将这些作品排除在《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概念的外延之外的情况出现,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法律解释来修补立法的缺陷:
第一种方法,就是将涉案的新型作品与《著作权法》第3条中最近似的类型相类推。
第二种方法,就是对涉案的新型作品进行目的解释:设立《著作权法》的目的在于促进和保护知识创新、科学创新,涉案的新型作品不仅内容新而且形式新(因为它不是上述九种类型中任何一种,所以是一种形式创新),如果著作权法不保护这种新型作品,这是与《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相违背的,所以,应当保护这种新型作品。
第三种方法,就是对涉案的新型作品进行当然解释:《著作权法》对符合构成要件且在上述九种类型的作品进行了保护,那么对符合构成要件但不在上述九种类型中的作品更应该保护,因为《著作权法》是保护创新的法律规范。既然前者这种仅仅只有内容上的创新性《著作权法》都予以保护,那么对后者这种不仅在内容上具有创新性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具有创新性的作品就更应该保护。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审判实践中那种——仅仅因为被认定作品不是第3条所列举的九种类型中的对象,即使判定它具有独创性和可复制性,符合构成要件,即使认定它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也不予保护——做法本身就是有法不依的表现。这种做法大大限缩了《著作权法》的适用范围,法官的这种行为是对立法目的的公开背离,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渎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