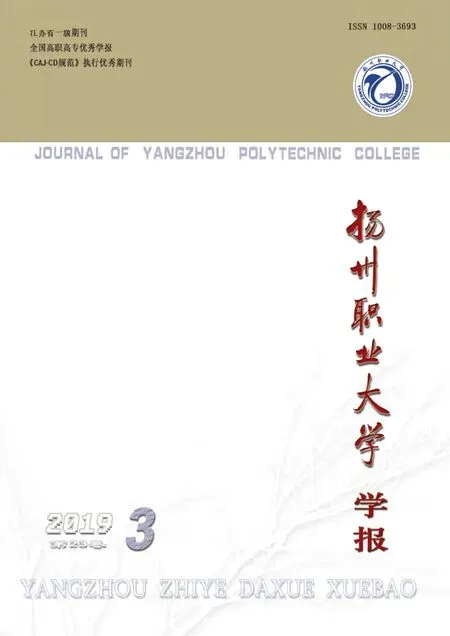扬州籍名臣徐铉佛禅诗谫论
黄文翰
(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徐铉(917—992),字鼎臣,是一位由五代入宋的扬州籍著名学者、文学家、政治家。与弟徐锴皆精于《说文》之学,并称“二徐”。仕南唐为吏部尚书,入宋官至散骑常侍。徐铉文学创作的实绩亦令人瞩目。单就其诗歌作品而论,《全宋诗》第一册即收七卷三百五十余题。近十年来,以《徐铉诗歌研究》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有西南交大郭格婷与广西师大刘尧的两部。2016年,又有李振中的专著《徐铉及其文学考论》面世,对徐铉的诗文创作进行系统研究。至于其他分时段、分题材、分体裁对徐铉诗歌进行相关考察的学术论文,则为数更多。以上诸家对徐铉诗歌的研究,皆不无精见。然对徐铉诗歌中存在的一批佛禅类作品,似未及多论。
对于佛禅类诗歌的界定,或可粗略划分为两种标准。狭义上讲,文本中明确涉及佛禅语词、思想的作品,才称得上佛禅诗。广义上讲,文本中虽无明确的佛禅语词、思想,但含有禅意的,也可称为佛禅诗。由于对“禅意”的定义与解读,言人人殊,故笔者选择从狭义角度,对前贤时彦着墨不多的徐铉佛禅类诗作,进行文学文化考察。
1 游寺栖禅
徐铉曾游览的具名寺院,至少有四座。南唐升元二年至四年间(938-940)(1)本文关于徐铉诗歌的系年,皆取李振中对《徐铉集校注》之说。,诗人游镇江甘露寺,作《登甘露寺北望》[1]16。南唐保大二年(944),诗人游南京爱敬寺,作《爱敬寺有老僧,尝游长安,言秦雍间事,历历可听,因赠此诗,兼示同行客》[1]28。保大八年(950),诗人作《亚元舍人,不替深知,猥贻佳作三篇,清绝,不敢轻酬,因为长歌,聊以为报,未竟,复得子乔校书示问,故兼寄陈君,庶资一笑耳》。诗中深情回忆与乔亚元、陈子乔游览扬州禅智寺的情景,流露出如今天涯相隔的落寞心绪:“禅智寺,山光桥,风瑟瑟兮雨萧萧。行杯已醒残梦断,征途未极离魂消。”[1]96宋太祖开宝三年(970),诗人与友人同游南京光睦院,作《又和游光睦院》:“寺门山水际,清浅照孱颜。客櫂晚维岸,僧房犹掩关。日华穿竹静,云影过阶闲。箕踞一长啸,忘怀物我间。”光睦院,《徐铉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言“当在金陵附近,具体未详”。[1]235清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十七:“光睦院,徐铉有《和游光睦院》诗。”[2]“上江两县”即上元县、江宁县,今属南京。诗人行船长江,傍晚泊岸游寺。置身寺院清幽的自然环境,体验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徐铉游览的不具名寺院,尚有数座。保大二年(944),诗人作《宿蒋帝庙明日游山南诸寺》。山南诸寺“松盖遮门寒黯黯,柳丝妨路翠毵毵”的幽景使诗人产生了“登临莫怪偏留恋,游宦多年事事谙”[1]26的感慨。自两汉之际传入,至诗人生活的十世纪,佛教与中土的因缘已绵历千载。佛寺除了继续履行其栖居僧侣的基本职责外,还渐渐成为士大夫诗酒游赏的佳处。徐铉作于保大七年(949)的《寄江州萧给事》就曾说道:“朝车载酒过山寺,谏纸题诗寄野人。”[1]72戒律中对于僧侣饮酒是遮止的,然而比丘们却对士人寺中剧饮的行为并不介意。孙昌武先生谈及外来的佛教在中国之所以能发展的原因时说:“佛教和随之传入中土的佛教文化又具有开放的、包容的性格。”[3]10徐氏此诗或可作一注脚。作于保大七年(949)的《送郝郎中为浙西判官》更是直接传递出寺院已成为士人心目中游赏佳处的信息:“大藩从事本优贤,幕府仍当北固前。花绕楼台山倚郭,寺临江海水连天。恐君到即忘归日。”[1]74-75诗人送郝郎中赴官浙西,认为其“到即忘归”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大藩优贤;二即山花楼台、碧水古寺的秀美风光,易使人流连忘返。
2 交游僧侣
徐铉交往的僧侣,至少有十四人。一位法号为“明”的僧人,徐铉曾与之两度酬唱,还曾为其作赠行诗一首。《和明道人宿山寺》通过描写明道人“闻道经行处”的清幽环境,表达了“羡师闲未得,早起逐班行”[1]40的艳羡与无奈之意。道人,即修学佛道(佛教之道,而非佛与道)之人(道教之出家众,则多称“道士”)。经行,即往复行走之谓,用于对治昏眠、积食、疲倦,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方式。《十诵律》卷五十七:“经行法者,比丘应直经行,不迟不疾。若不能直,当画地作相,随相直行。是名经行法。”[4]作于保大十三年(955)除夕的《和明上人除夜见寄》是一篇以诗代书的作品,作者感叹“长年逢岁暮,多病见兵兴”,对健康与时局的担忧令其“愁襟默自增”。诗歌以“汤师无别念,吟坐一灯凝”[1]140-141作结,将明上人比作南朝宋诗僧汤惠休,表达作者对于明上人禅心不动、兀自闲吟的嘉许。《明道人归西林求题院额作此送之》是一篇赠行之作,由诗题可知,明道人本是庐山西林寺僧,曾云游他方,如今意欲归山。临行之际,明道人向诗人索题寺院匾额,徐氏欣然“含情题小篆”[1]241,并作此诗记之。徐铉亦与一位法号为“净”的僧人交好,曾作《送净道人》[1]618《送净道人东游》《送文懿大师净公西游》《奉和武功学士舍人纪赠文懿大师净公》等四题十二首诗。《校注》认为文懿大师净公“当是宋净土宗僧省常”[1]632,然未明所据。笔者曾对省常大师的西湖莲社进行过相关研究(2)详参笔者《试论释省常西湖莲社之特色——以〈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为中心》(《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85-88页)一文。。在考察省常大师生平时,未见其得“文懿”赐号的文献记载。审慎起见,本文不取《校注》之说。《送净道人东游》记其“身服竺乾教,心为邹鲁儒”[1]627,俨然一位披着袈裟的士人。《奉和武功学士舍人纪赠文懿大师净公·其八》以净公比谪仙李白:“高情丽句谁偏重,圣代词臣李谪仙。”净公文学造诣颇高,“京华才子多文会,众许清词每擅场”(《其五》)。士大夫多乐与之交,“群公竞有诗相赠,组绣珠玑满袖中”(《其六》)[1]632。净公还曾云游终南。《送文懿大师净公西游》:“厌栖庐岳莲花社,却访南山紫阁峰。”[1]630-631莲花社是净土信仰者起建的佛教修习社团,净公亦当具净土信仰。
与徐铉相交的僧侣,多为善诗、善书的艺僧。上文中的明、净二师即善诗。其他善诗者还有德迈、旻道人、元道人。《送德迈道人之豫章》:“莫道空谈便无事,碧云诗思更无涯。”碧云诗思,《校注》:“比喻远方或天边。用以表达离情别绪。江淹《休上人别怨》:‘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1]247《休上人别怨》又名《拟汤惠休诗》。汤惠休,南朝宋诗僧,这里以之比德迈道人。《和旻道人见寄》是一首奉和之什,作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诗人时年六十三岁。徐铉通过自慨“戎服非吾事,华缨寄此身。谬为金马客,本是钓乡人”[1]620,表达了对晚年身劳王事的厌倦之意。《送元道人还水西寺》:“李白高吟处,师归掩竹关。道心明月静,诗思碧云闲。”[1]656这首诗再次使用“碧云”典故,将元道人比作刘宋诗僧汤惠休。又,水西寺,《校注》以同名寺院颇多,未明所在。据诗意,元道人所归之水西寺,曾为“李白高吟处”。《全唐诗》卷五百二十一录有杜牧《念昔游三首》。《其三》有“李白题诗水西寺”一句。句下小注曰:“宣州泾县。”[5]知元道人所归之水西寺,在安徽泾县。又有应之道人,诗书兼善。《送应之道人归江西》即盛赞其“名题小篆矜垂露,诗作吴吟对绮霞”。应之与诗人相交二十余年,是徐氏的长辈。诗人自述“曾骑竹马傍洪涯,二十余年变物华”。洪涯,道家仙人之名。这里以之比应之。徐铉初识应之时,尚为一“骑竹马”的儿童。应之,俗姓王,其先闽人。举进士不第,后为僧。曾为南唐中主以柳体书《楞严经》,事详马令《南唐书》卷二十六《浮屠传·应之》,此点《校注》已言及。又检《宣和书谱》卷十一《五代·释应之》:“尝以文绢写进士沈崧《曲直不相入赋》,颇有气骨。”[6]
五代宋初的净土信仰热烈,结社活动风行[7]。与徐铉相交的僧侣,即有多人具有净土信仰或曾起建莲社。上文“厌栖庐岳莲花社,却访南山紫阁峰”的净公即是一位。又有不具名的越僧。《和元少卿送越僧》:“莲社故人今暂别,稽山旧隐与谁登。”[1]649诗人称越僧为“莲社故人”,表明徐氏也曾有莲社修习经历。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徐铉作《送赞宁道人归浙中》。赞宁是五代、宋初著名高僧,因持律精严,有“律虎”之称。吴越时任两浙僧统,入宋为左、右街僧录,撰有僧史名著《大宋高僧传》。诗歌称赞赞宁“故里夫差国,高名惠远师”[1]648,将之比作东晋庐山莲社发起人惠(慧)远法师。这个比附并不是一时兴到之词,宗鉴《释门正统》卷八《护法外传·赞宁》引“孤山拜像诗”曰:“寂尔归真界,人间化已成。两朝钦至业,四海仰高名。旧迹存华社,遗编满帝京。徘徊想前事,庭树晚鸦鸣。”[8]孤山,即宋初天台宗山外派名僧孤山智圆。“拜像诗”见智圆《闲居编》卷四十七,题作《经通慧僧录影堂》,文字与《释门正统》小异。通慧,即赞宁之赐号。诗句“旧迹存华社”之“华社”,当即净土莲花社。知赞宁曾有结莲社之举,故徐铉诗将其比作慧远法师。
与徐铉相交之僧侣,还有勋道人(《送勋道人之建安》)[1]138、达师(《送表侄达师归鄱阳》)[1]625、清道人(《送清道人归西山》)[1]672、德明(《送德明道人还东林》)[1]674、頵道人(《送頵道人还西山》)[1]681等具名者五人。其中,达师还是徐铉的表侄。另有不具名者一人。作于宋太祖建隆三年(962)的《文彧少卿、文山郎中,交好深至,二纪已余。暌别数年,二子长逝。奉使岭表,涂次南康。吊孙氏之孤于其家,睹文彧手书于僧室。慷慨悲叹,留题此诗》写道:“孙家虚座吊诸孤,张叟僧房见手书……珍重远公应笑我,尘心唯此未能除。”[1]186-187诗歌末句“笑我”之“远公”,或即文彧手书所在之僧房的主人,徐铉将其比作庐山结社的慧远大师。
3 轮回观念
徐铉具有明显的三世轮回观念,其诗歌作品中多见前世后身之词。轮回转世之说自非佛教中精密繁难的教法,但却是影响、改造中华民族心灵的最重要的佛教法义之一。保大五年(947),诗人作《谢文静墓下作》。是年,契丹南下灭后晋。南唐与吴越亦在福州交兵,可谓多事之秋。谢文静即谢安,文静(靖)为其谥号。诗人凭吊谢安之墓,“岂惮寻荒垄,犹思认后身”[1]37,希望世间能再出现一位像谢安那样,指挥淝水之战、击败苻秦敌虏、维护国家安定的英雄人物。保大七年(949),诗人作《病题二首》。《其二》曰:“人间多事本难论,况是人间懒慢人。不解养生何怪病,已能知命敢辞贫。向空咄咄烦书字,与世滔滔莫问津。金马门前君识否,东方曼倩是前身。”[1]71东方曼倩即西汉东方朔。朔颇有抱负,然被汉武帝俳优视之,一生郁郁不得志。诗人病中意恶,感到志不得伸,感叹自己即为东方朔之前身。保大十四年(956),诗人作《和表弟包颖见寄》。诗中感慨“旧游半似前生事,要路多逢后进人”[1]104。表现出前欢难追的伤怀与后进辈出的危机感。“追忆往事,有如前生”的相似表述,还有《送王监丞之历阳》的“青襟空皓首,往事似前生”[1]623。又,《奉和武功学士舍人纪赠文懿大师净公·其七》赞美净公“南朝人物古犹今,只恐前身是道林”[1]632,以净公为东晋名僧支道林的前身。
值得附带一说的是,徐铉早年即与佛禅有缘。前引《送应之道人归江西》“曾骑竹马傍洪涯,二十余年变物华”句,即是其青少年时代就与僧侣过从的明证。又有作于升元二年(938)诗人二十二岁时的《早春左省寓直》写道:“时清政事少,日永直官闲……终军年二十,默坐叩玄关。”[1]13诗人虽自比汉武帝时愿赴南越、俘虏其王的终军,但在诗中,请缨缚敌的英雄少年,一变而为参禅默坐的“维摩居士”。知徐铉早年不仅交游僧侣,亦在修习实践上有参佛坐禅的行为。
4 结语
经过梳理、考察徐铉存世的佛禅诗,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之参佛坐禅、游寺结僧,自少至老而不稍倦。在他的观念世界里,寺院更多是以游赏景点而非宗教场所存在的。这一点无论是在诗人生活的五代时期,还是上溯前朝的李唐,抑或下溯赵宋以后,举凡有数卷别集存世者,大都能找到相同的例证。诗人所交结的僧侣中,半数具有文艺才能。他们或可称作“披着袈裟的知识分子”[3]28,这种面貌与早期印度佛教中常见的灰身灭智的头陀形象大为不同。僧侣与士人的亲切交往,亦是唐宋以来各家别集中的常见内容。又,徐铉诗歌中数数言及的轮回转世之词,是佛教成功熏染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与心灵世界的一个例证。前身后世之说,无论是作为结构诗文的语料,抑或一种观照生死的视角,它对中国人的深刻影响,有时甚至是日用不察、难以自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