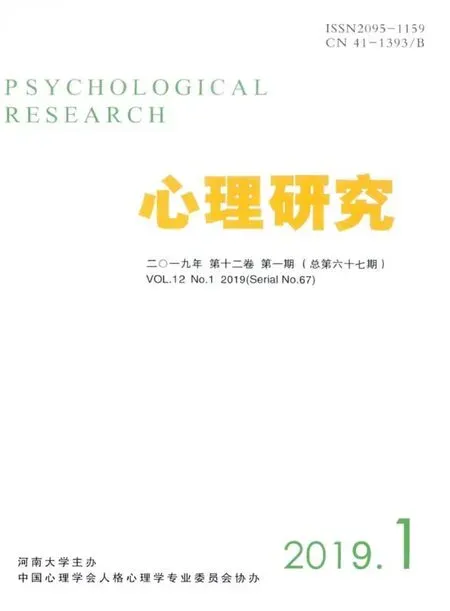向前敲瘦骨 犹自带铜声
——中国实验心理学家沈迺璋的学术贡献与风骨
王蕴瑾 王 勇 陈 巍,3
(1台州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台州 318000;2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绍兴 312000;3浙江省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绍兴 312000)
1 沈迺璋的生平简介
1911年11月24日,沈迺璋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今属湖州吴兴区),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心理系,同年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心理系。在孙国华教授的指导下,他以《白鼠视辨大小之差阈及视型明度对于视辨反应之影响》和《左右手同时举重实验》两项研究于1936年获硕士学位。同年,由于天赋出众且成绩优异,清华大学资助沈迺璋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进修,受业于当时世界闻名的神经症专家Pierre Janet。在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时,他深受巴黎大学悠久的实验心理学与临床变态心理学传统影响,并受Janet启发,以心理变态个体为被试,开展光点自动运动实验,率先对其认知特点展开了讨论。该项研究成果最终发表在法国 《心理学年报》(1937-1938)上。对此,沈迺璋指出:“普通人类变态行为之研究,多在其发生变态之后,吾人尚能在变态行为发生之前观察其由来,而研究在何种情形下发生变态,则对治疗之法当有相当之把握。”(项文惠,2004)
1938年秋,沈迺璋学成归国,因不愿为日本人服务而赋闲在家,几个月后才担任了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讲师,1939年起仅任教燕京大学心理系,讲授普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感觉心理学和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等课程。他讲授的变态心理学既遵循法国的实验传统,又有丰富的临床素材,在当时的中国很有特色(张玮瑛,王百强,钱辛波,1999),还多次在课堂上当场演示实验过程,课堂延续了他一贯的幽默风趣,颇受欢迎。在燕大教书时,沈迺璋被称为“胡子先生”,美髯成为他的标志。在接受燕大学生记者采访时,他曾提到自法国留学时开始蓄胡须,收藏烟斗,虽然烟瘾不大,却有五六十个不同的烟斗,这已成为一种生活乐趣 (佚名,1938)。
抗战爆发后,燕京大学并未与北大、清华一起南迁,成为当时北平的“孤岛绿洲”,为沦陷区的学生保留了一处可以继续求学的地方。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翌日日本宪兵就封闭了燕京大学,30多位燕大师生被捕入狱。沈迺璋宁可赋闲也拒绝为伪北大任教。1945年,燕京大学复校,未名湖畔钟亭里的大钟在沉寂了1036天之后,终于再次敲响。沈迺璋热忱响应陆志韦号召,任心理系主任的同时承担起大一概论课的教学和新生导师。1950年,沈迺璋与周先庚、孙国华、陈立等8位心理学家一同入选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委员。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取消,燕大心理系被合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沈迺璋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专业任教授,并兼任心理学教研室主任,在哲学系开设心理学方法一课。1953年秋,沈迺璋、孙国华和邵郊合作成立了新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条件反射实验室。条件反射实验室的建立,对于当时全国范围内成立条件反射研究室起到了促进作用(李艳丽,阎书昌,2014)。
1957年,沈迺璋响应“双百”运动号召,理性客观地表达了对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心理学系的举措的质疑,这也导致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沈迺璋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沈迺璋与聂崇岐、齐思和陈芳芝三位先生被称为“四兄妹”、“骂人团”后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1966年10月6日,沈迺璋在家中服毒药自杀,享年55岁。
2 沈迺璋关于感知觉的实验研究
沈迺璋学术兴趣广泛,从事过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等研究工作,但其学术重心始终围绕于感知觉的实验研究,研究主题涉及举重、偏手性、颜色偏好、视域视差等,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2.1 左右手同时举重实验研究
沈迺璋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心理系就读时,曾致力于左右手同时举重实验的研究,完成了硕士论文《左右手同时举重实验》(Simultaneous Lifting of E-quallyHeavyWeightsbybothRightandLeft Hands)(Shen,1935)。在系列举重实验中,被试需要先举起“标准”的重物,后举起一个“对照”重物与之比轻重(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标准”重物会伴随有3个或5个“对照”重物),以先“标准”的重物再“对照”重物顺序往复进行实验。为了消除左右手先后举起重物中所存在的时间差而引起的实验误差,沈迺璋首先对双手同时举起一对相同重量的物体所产生的身体的感知进行了研究。而在沈迺璋之前,除了Arons和Irwin的一个相关调查之外,还未有研究者对左右手同时举重的身体感知进行过研究。
Arons和Irwin的实验中,提供“标准”重物,要求被试连续多次同时举起“标准”重物和“对照”重物,以此对相同重量物体的心理量进行研究(Arons& Irwin,1932);而相较之下,沈迺璋有其创新之处,即在实验中主试会事先告知被试需要用左右手同时举起等重量的物体,而在正式实验中,主试不提供“标准”重量和“对照”重量,一切由被试按照“自由意志”进行判断。对此,沈迺璋的实验目的是:左右手在同时举起相同重量的物体时,是否会依据其中一只手(惯用手或非惯用手)作出相较于另一只手“较轻”、“相等”还是“较重”的判断? 如果是,(1)依据与其中一只手所做的“较轻”、“相等”还是“较重”这三个判断类别中,某一个会被作出更多的判断吗?(2)是什么决定了被试对这一类别作出更多的判断?
实验共选取了10名成年被试,其中5名为心理学系本专业学生(有心理实验培训经历),其中3男2女,1名为心理系助手,其余4名为其他专业未毕业的学生(无任何心理学实验经历)。所有被试均不知实验目的,只被要求对放在他们面前的盒子(高和直径均为2英寸的黑色圆柱形木盒,内部用树枝和石蜡填充)做相等重量判断。盒子分为五种重量,分别是88、94、100、106和112克,为了避免被试可以熟练地识别特定的重量,其中重量为88、94、106和12克的盒子各有四个,而100克的有10个。正式实验开始后,主试将盒子放于被试面前,并告知被试需要同时举起面前的一对盒子并做出重量比较判断。在被试举起盒子时,需注意:(1)用左、右两只手同时举起一对盒子;(2)把盒子举到同一高度;(3)需同时放下盒子。最后,被试用“较重”、“较轻”或者“相同”来报告判断结果,并告知主试是依据哪只手作出的判断。在实际实验操作时,大部分被试不能一次就可以对盒子重量进行判断,均需不止一次地同时举起一对盒子后才给出判断结果(Shen,1935)。
实验结果如下:(1)10名成年被试中,有9人的判断一直为左手“较重”,剩余一名给出的判断为“左手较轻”,因为她自然地将左手作为参照来判断一对物体的重量。(2)身体上同等物理重量被判定为“相同”心理量的仅占平均水平的24%,这说明物理量与心理量远非完全是同等重量。(3)此外,一半被试给出“右边较重”的判断多于“左边较重”的判断,然而,在对一对同等重量的判断上,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说,“右重”和“左重”的比重应该是均等的;而从偏手性来讲,在这项实验研究中,偏手性并没有在两只手同时举起同等重量的重物时产生明显的影响。对此,沈迺璋给出的解释是:这可能是因为实验选取的重物太轻,因此,若要在举重实验中研究偏手性的问题,选用尺寸较小且较重的物体是更有效的(Shen,1935)。
2.2 举重实验中的偏手性实验研究
带着疑问,沈迺璋对举重实验中的偏手性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于1936年完成了另一篇论文《左右手同时举重的偏手性研究》(Handedness Effect in Simultaneous Lifting of Weights by both Hands)(Shen,1936b)。
此研究假设为:当两只手举起相同重量的物体时,优势手能够提供更大的力量,因此与另一只非优势手举起的重量相比,会较低地估计所举物体本身的重量。沈迺璋选取了10名右撇子的成年男性作为实验被试,6名被试为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4名被试为此部门助理。在预备实验中,主试将被试的眼睛蒙上,然后要求被试双手同时举起重物,一只手上为“标准”重量,另一手选择一个与之前重量相匹配的“变化”重量举起。在左右手分别放“标准”重物6次,共进行12次预备实验。实验中被试不知道物体的实际重量,只是左手和右手尽量将重物举到相同高度,然后再同时将重物放下,如此重复进行,直到找到正确的与标准重物相匹配的重量为止,并予以记录(Shen,1936b)。
实验发现:“右撇子”的被试倾向于低估物体的重量,而“左撇子”的被试倾向于高估物体的重量。换言之,用右手和左手举起同等规格重量的物体时,“右撇子”的人生理上感受到的重量要高于“左撇子”的人。而对于改变这种偏手性在举重上的影响,练习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效果。对此,沈迺璋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偏手性而使得个体在举起相同重量物体时感受到的心理量有差异,这是由人们的态度所决定的,即个人期望因素,而不是用手习惯。这也就说明,想要改变偏手性在举重物上的影响,可以从改变人们的期望心态入手(Shen,1936b)。
除了偏手性对感觉的影响之外,1963年,沈迺璋发表了《正常成人的形重错觉》的实验报告,通过对人在感觉一斤棉花和一斤铁时产生的不同感受这一有趣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形重错觉”这一概念,即人在提举同重量不同体积的物体时,眼见的大小决定了提举时用力之不同(沈迺璋,1963)。
2.3 颜色偏好研究
1935年,沈迺璋与周先庚、陈汉标共同发表《颜色爱好的民族差异》于美国 《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沈迺璋在周先庚和陈汉标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学生颜色偏好注意进行了研究。在周先庚和陈汉标的研究中,他们把中国学生作为被试。研究发现,“白色”是最被喜欢的颜色,与之前的不同肤色人对不同颜色偏好研究结果相反。对此差异,沈迺璋分析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在之前的研究里,用中国色彩人物代替实际的颜色,而在中国色彩人物形象里,与其他颜色人物相比较,“白色”的性格特征特别清晰(Shen,1936a)。
为了证实自己的这一猜测,沈迺璋对先前所做的实验进行了重复并予以改进。他把实验材料中所有有关中国色彩的人物等价替换成了英文颜色词汇,同时,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所有呈现给被试的英文颜色词汇的右边都添加一个采用中文最原始形式呈现的问题。
沈迺璋选取了两所大学组和两所中学组进行测试。大学组用写的方式简单地告诉被试英文颜色名称所对应的中文。中学组在正式测试开始前先对其进行为期两周的有关英文颜色单词的学习培训。在正式实验开始后,向被试提供大约10×10英寸(1英寸=2.54厘米)大小的彩色纸,以及给被试呈现9种颜色的英文单词,要求其划出最喜欢的颜色。测试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36对成对比较的9个颜色单词组成,分别为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灰色和黑色;第二部分需要被试回答42个关于上述9个颜色的喜好问题。最后,沈迺璋得出以下实验结果:
(1)第一部分测试结果显示,男生偏向于喜欢橙色、蓝色和紫色,不太喜欢灰色、黑色和黄色;而女生偏向于喜欢白色、蓝色和绿色,不太喜欢黑色、灰色和红色。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与女生偏好的颜色相比,男生特别偏好的颜色为暗色类;而男生尤其不偏好的颜色比女生不偏好的要明亮。
(2)第二部分测试显示,除了男生喜欢把灰色放在颜色偏好靠前的位置外,男女颜色偏好不存在性别差异。
沈迺璋认为以上研究结果是以颜色词汇为实验材料,若以实际颜色代替颜色词汇作为实验材料,以上研究结论是否还会成立?1937年,他进一步对中国人颜色偏好进行了研究。本研究共选取了1368名被试,其中847名男生,521名女生,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初中生(相当于美国的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年级)。这些被试里有64名色盲,而有关色盲人群的颜色偏好在过去从未被涉及,因此这64名被试对本研究的影响也不能完全被考证。而就实验后期得出的结论看来,惊喜地获得了一些关于色盲的颜色偏好结论。他发现,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成长以及受到相同的文化培养的色盲对于颜色词所象征的意义和正常人是一样的,但是,在感知颜色是什么时,色盲可能不同于正常人,而文化培养可能会影响甚至决定色盲感知到的颜色是否和正常人的感知相同。此外,实验还表明色盲对白色的偏好比正常人低得多,这对于颜色偏好研究具有重大意义(Shen,1937b)。1946年,他在《大中》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色盲》的论文,该文从正常个体对颜色的感觉入手系统分析了色盲患者的色觉,并建议用一种简捷可靠的色盲检查法来对色盲的种类和特征进行说明 (沈迺璋,1946b)。
在颜色偏好实验的颜色的选择上,沈迺璋选择了六种饱和的Brady Milton颜色(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和紫色)和非彩色的白色。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采用了成对比较法,即将以上七种颜色两两配对,为了避免颜色组合的顺序导致的误差,配对数由先前的21对增加到42对。所有颜色均以2.5英寸(1英寸=2.25厘米)的正方形彩纸呈现,而每一对颜色的纸都被并排粘贴在一张灰色的纸板上。配对颜色纸板由测试人员事先确定好的顺序随机呈现给不同组被试进行测试(Shen,1937b)。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学生的颜色偏好按照偏好依次递减,分别为:白色、红色、蓝色、绿色、黄色、橙色和紫色。其中,男生最偏好的前三种颜色分别为:蓝色、白色和红色,而女生最偏好的前三种颜色分别为:白色、红色和蓝色。显然,中国学生,无论男女,白色是其最偏爱的颜色,由此可推论出白色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不过,这与中国人喜欢喜庆的红色,而很少使用葬礼的白色的常识有所冲突。沈迺璋在前人的理论和实验数据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人偏好白色可能受其传统的诗歌、散文对颜色词汇的使用频率以及多种语言表达形式的双重影响而导致。从种族心理学上来讲,这一研究发现有着重要的心理学意义,即就当时的心理学研究发现而言,还未曾发现白色是某个种族最偏好的颜色。且有研究者指出,中国人偏好白色可能是受其语言环境的影响所导致的(Shen,1937b)。
2.4 视辨差阈及视型明度对其反应的研究
1937年,沈迺璋以其硕士论文为基础,在《中国心理学报》上发表了有关《白鼠视辨大小之差阈及视型明度对于视辨反应之影响》(Shen,1937a)的实验报告。在对白鼠辨别大小的阈限进行研究之前,有必要先对白鼠辨别大小的阈限是否完全为真正大小的阈限以及和明度总积有无关系进行实验研究。
此先导实验分为三个问题入手:(1)过度的训练是否会改变辨别反应的性质?(2)辨别大小的阈限是多少?①和过度的训练有何关系?②和物体的绝对大小有何关系?(3)辨别大小的阈限是否为明度所规定?实验操作是在两片黑色纸板上画两个白色圆圈,一大一小,置于Lashley的跳跃仪器上,让白鼠选择其中较大的那一个圆圈。
实验一让四只白鼠分辨分别以4厘米和6厘米为直径的白圆形,训练至连续30次均选择6厘米直径白圆形无失误后,加以过度的训练:甲30倍,乙15倍,丙7.5倍,丁3.75倍。之后让白鼠去辨别直径分别为6厘米和16厘米的白圆形。结果,除丙鼠60次之中只有24次选择16厘米白圆形外,其余3鼠无失误,即每只每次选择均为16厘米白圆形。由此得出结论:过度的训练会相对增加大小辨别反应的能力。由此可继续实验二。
实验二除上文提及的实验对象甲乙丁三鼠外,又加戊……癸六鼠。对新六鼠也进行预实验,即壬癸二鼠辨别直径为5厘米和7.5厘米的白圆形,其余四鼠辨别直径分别为4厘米和6厘米的白圆形。与前三鼠不同,新六鼠训练至三十次无误为止后不受过度的训练。正式实验中,甲乙丁三鼠接受三次大小辨别的阈限测验,目标大圆直径分别为5厘米、7.5厘米和9厘米,而新六鼠只接受一次测验。结果显示:视觉大小辨别的阈限的正确率介于8.3%和13.3%之间,因此阈限不因过渡的训练降低或增高。
实验三将戊……癸六鼠作为实验被试。实验假设为:(1)阈限值如果全关乎圆形明度而不关乎圆形大小,则A.当两个圆形大小相等而明度总积保持原有的差别时,白鼠的反应正确率应随着明度的增高而增加;B.当两圆形明度总积相等而大小保持原有差别时,白鼠应完全不能辨别大小。(2)如果阈限全关乎圆形大小而不关乎明度,则A、B两项结论必全然不同。实验结果为A项结论基本得到证实,而B项结论没有,即白鼠若能利用明度进行辨别物体形状时反应则十分迅速;而不能利用明度时,也会利用物体的大小,但反应不迅速,因此,当物体形状的差别很小时,明度影响自然要高于物体大小的影响(Shen,1937a)。
这项研究奠定了沈迺璋在中国感知觉心理学领域的地位,而他对感知觉的研究兴趣一直持续终身。1956年,他在《心理学报》上发表了《在用电流刺激狗的乙状回时电流的频率与其刺激效果的关系》。该研究通过给一只5个月大的小母狗装上可以直接接触到乙状回皮质的电极,并对其做电刺激的实验,得出了以下结论:(1)引起反应的最低电压与电流的频率之间存在着有规律的关系;(2)电流的改变不仅影响到一起反应所需的最低伏特值,而且影响到所引起的运动的性质,即当频率低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起另一种反应;(3)直接作用于乙状回皮质上一定点的电流,当其频率降低到某种程度时,可以使运动反应的性质改变(沈迺璋,1956)。
此外,沈迺璋也非常重视系统引介与传播国外相关领域的前沿进展。在1956年至1958年期间,他先后为《心理学译报》翻译了一系列苏联心理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如《言语动觉的电生理学研究》(沈迺璋,1955)、《用“双联反射计”同时研究人的特定动作反应和普通动作反应》(沈迺璋,1959)、《苏联心理科学对于感觉理论的贡献》(沈迺璋,1958a)、《论感觉的生理基础》(沈迺璋,1958b)。虽然这些译介工作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烙印,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窥得即便是身处学术让位于政治的压抑氛围之中,心理学学科承受重大挫折之际,沈迺璋仍在利用极为有限的条件开展学术研究。
3 影响和评价
纵观当时的时代背景,即为了促进作为纯粹舶来品的心理学在近代中国的广泛扎根与迅速萌发,第一批留学归国的中国心理学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部分放弃了自己在国外学习期间主攻的心理学学术方向,而投身于心理测量、汉字阅读心理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普及等本土化的探索之中。纵使这种研究模式对于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奠基功不可没,但毕竟是以牺牲研究者本身的学术生命为代价的。身处时代大背景下的沈迺璋,对于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感知心理学等均有系统涉猎,但始终坚持感知觉的实验心理学研究,即无论是举重实验、偏手性研究、颜色偏好研究、视域视差研究,始终保持自身鲜明的学术旨趣。此外,沈迺璋还是中国较早强调对变态心理现象进行实验研究的心理学家。其独立的研究品格与敏锐的学术眼光在同时代的中国心理学家中极其罕见,也是难能可贵的。
沈迺璋先生学识渊博、兴趣广泛、推崇学术自由和民主,更愿以不同的方式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最近,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黄希庭先生在接受访谈时也提到沈迺璋的教学方法。沈先生开出一张书目给当年刚刚入学的黄先生,黄先生找沈先生四次终于了解后者是要学生懂得自学,靠自己寻找答案,引导学生无师自通(黄希庭,陈红,2016)。
沈迺璋私底下是个非常率真可爱之人。留学法国时,考古学家夏鼐某日下午在法国卢浮宫及国立图书馆参观,买了一大批画片后至沈迺璋处闲谈,沈迺璋便自我打趣道“来法一年,仅购12法郎之《心理学》,系其老师之著作撮要,不能不买也;由国内买来一大批上海一折书,都是新小说及笔记,以预备上床后睡不着时翻阅,邮费比书价还昂”(夏鼐,2011)。然而,这位率真可爱的沈迺璋先生更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傲然的风骨。
遗憾的是,沈迺璋的人生际遇如同燕京大学一样令人扼腕,也昭示了现代中国心理学事业发展的坎坷命运。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沈迺璋被软禁在燕京大学近三个月,让其交代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周文业,2015)。
沈迺璋初回国以及在燕京大学被迫封闭时期,就屡次因不愿为日本人服务而赋闲在家,面对前来游说的特务,一句“我的个人生活你管得着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海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便拂袖而去,坚持内心的信念,大义凛然。沈迺璋在反思社会现象时的严谨与较真同样让人刮目相看。1946年,他在《大中》上发表了《论“天才教育”》一文。文章言辞犀利,语言幽默,读起来倒是十分爽快。文中对国内已经提出的“天才教育”说表示质疑。他犀利地批判道:“西方研究了数十年都没有研究出结果,而在中国已经出现了 ‘天才教育’为今后某地区的教育目标。本来教育的最大前提为合适的国情,我们的文盲多于文通,我们的成人文盲数远远超过了其他文明国家,所以我们的急需是广大小学义务教育和成人文盲的义务教育,先减少文盲,然后再完成全消除文盲。自然高等教育不能等文盲全成了文通以后再开始辩理,可是天才的高等教育还不必太急于入手。”(沈迺璋,1946a)
1958年“心理学大批判”运动中,心理学家们的“自我适应”能力不断地被消磨,直至中国心理学学科被全盘推翻。然而,沈迺璋先生仍然以学界清流之姿,仗义执言,直抒胸臆。1959年,鉴于当时的心理学学术氛围,中国心理学界就心理的研究对象、任务、性质、方法等问题举行了一场为期5天、规模庞大的研讨会,200多位国内心理学精英与骨干悉数赴会。会议气氛异常激烈,与会者在心理学的对象和任务的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一些学者受当时政治空气影响,唯苏联心理学马首是瞻,独断地认为所有心理现象都具有阶级性;而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曹日昌为代表的学者则主张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反应过程,并不随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沈迺璋旗帜鲜明地支持曹日昌的观点,并进一步强调按照心理学学科分支的侧重,普通心理学就应该专门研究心理过程,不必研究个性(北京心理学界讨论心理学的学术问题,1959)。半个多世纪后,北京大学心理系任仁眉在回忆亲身经历的批判心理学运动时痛心地疾呼:“希望每个人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要真正地想明白再说再做,如有压力,就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做;不要人云亦云,言不由衷,跟风随大流。研究科学的人说话是要有根据的,不能胡说八道。”(任仁眉,2010)或许,读到这里我们才能深切地体会到沈先生这番切中肯絮的发言是多么宝贵。
文革期间,心理学家们的“自我适应”被代之以“生存适应”(李艳丽,阎书昌,2014)。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心理学家的“生存适应”一次次被打压,乃至遭受严重的身心摧残。李贺《马诗》有云:“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这可堪沈迺璋先生的最佳写照。虽然他在这一期间遭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以高贵的头颅与铮铮傲骨反抗那些荒唐的人身攻击,直至服毒自杀。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心理系教授沈迺璋得到了平反(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2008)。同年12月23日,沈迺璋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翻开中国科学院1949年-1950年全国科学专家调查综合报告,沈迺璋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心理组的第19位 (共67人)(中国科学院1949年-1950年全国科学专家调查综合报告,2004),这般傲人的学术成就连同他的高洁风骨注定一起被载入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