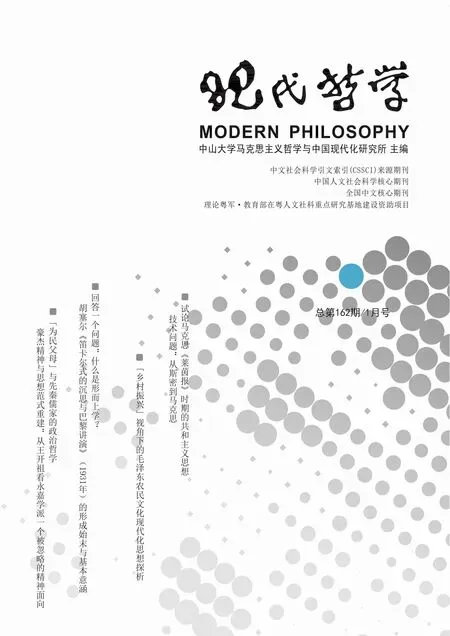舍勒的受苦论与佛教的受苦论的异同
李革新
舍勒是一个对情感现象有深入洞见的现象学家。他突破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创立了情感现象学,并且对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爱、羞耻、怨恨、痛苦等情感现象的研究都是很有启发的,对于我们理解现象学和人的情感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在《受苦的意义》这篇论文中,他深刻探讨了苦的问题,也对佛教进行了深刻的评论。但是由于他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佛陀语录》、《不朽的佛陀》等少数资料,所以他对佛教既有非常准确精辟的评价,也有显得片面的看法。比较舍勒和佛教对受苦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舍勒的现象学和佛教的哲学思想,以及更好地面对人生的痛苦。
一、苦的概念
舍勒首先肯定了情感的意义。传统的理性主义认为情感是混乱的无意义的。舍勒认为情感具有独特意义。“个体的情感生命,其实是自然的启示和征兆的一个非常精微的体系,个体正是在其中呈露自身。在体验本身之中,一定层次的情感,至少给定了某种‘意义’,某种‘含义’,通过他们,情感又给定了一种存在、一种行为”。[注]马克斯·舍勒:《舍勒选集》(上),刘小枫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629页。例如幸福感、羞耻感、饥饿感、疲劳感等,可以激励人们去做某事或者不做某事。在《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和实质的价值伦理学》中,他区分了意向性情感和状态性情感。意向性情感指向一种价值,在这种情感活动中有一种价值显现出来。状态性情感是一种价值实现的结果,例如快乐和痛苦。状态性情感是不变的,但是对于状态性情感的承担却是随着个人和历史的价值取向等变化的。“通过这类释义,个体的感受超越自己的直接体验,被嵌入世界及其(神的)根基的关联之中,成为其中的一环。因此,任何(哲学的)受苦学说都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关于人之心灵动荡的符号性意义,以及一种引示,将各种引导性的、富有意义或空无意义的力量引入心灵动荡的形形色色的情感游戏。”[注]同上,第631页。所以在人们的情感活动之中,存在巨大的意义领域和自由领域。人们面对情感活动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这是我们讨论受苦的技艺的基础。
舍勒认为受苦是有意义的。“造物的一切受苦和痛苦,皆有一种意义。至少有一种客观的意义。”[注]马克斯·舍勒:《舍勒选集》(上),刘小枫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631页。他把苦和牺牲联系起来,认为受苦的意义就是牺牲。“在我看来,牺牲的概念是纯形式的和最一般的大概念,它可以涵盖一切受苦(从痛感一直到形而上学-宗教性的绝望)。”[注]同上,第634页。牺牲总是“为了什么”而牺牲。具体而言,在实现一种较高的肯定价值或避免较高层次的不幸而与较低层级的不幸联系在一起时,受苦就产生了。“一切痛苦和一切受苦,就其形而上学及纯形式的意义而言,乃是部分为了整体以及较低值的为了较高值的牺牲体验。”[注]同上,第634页。也就是说,牺牲不是为了自己将来可以获得更大的快乐而放弃现在的快乐。牺牲是彻底取消自己的利益和快乐,而不以其它形式重新获得。因此牺牲是最彻底意义上的受苦,是受苦的最严格意义。只有包含牺牲的受苦才是受苦,不具有牺牲意义的受苦不是受苦。换言之,单纯的受苦或者有意追求痛苦是毫无意义的,例如痛苦癖或者受虐狂等。当然,这种受苦的定义是不是太狭窄了呢?
舍勒认为苦有两种类型,一个是部分对整体的抵抗,部分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而反对整体。这种痛苦是无能的痛苦,本质上是生命个体的衰弱、匮乏和衰老等。一个是部分具有超常的生命力和主动性,整体因为机体组织的僵化而压制部分的生长。这种痛苦是生长的痛苦,生成的痛苦。舍勒贬低前一种痛苦,推崇后一种痛苦。前者是更普遍的痛苦,后者是更高贵的痛苦。前者是生命衰弱的标志,后者是生命超生的标志。前者类似于叔本华的生存哲学,后者类似于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应该说,这种苦的概念受到了尼采的生命哲学的强烈影响。
舍勒看到了受苦的不可避免性,提出了“受苦的本体论”的概念。“我在此主张,从牺牲的这种纯形式的概念出发,一切种类的痛苦和受苦(无论受苦者对它们持何种态度),本身只是对(客观的)牺牲事件的主观的心灵上的反映和相关者,它们是产生效力的趋势,在其中,较低级别的一种利益,为了较高级别的一种利益而被舍弃(受苦的本体论)。”[注]同上,第637页。也就是说,舍勒看到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痛苦。为了生命整体的存在和更高生命的发展,牺牲是必需的,所以痛苦就是不可避免的。个体生命应该为了整体生命牺牲自己,或者低级的价值应该为了更高价值而牺牲自己。他肯定了受苦和牺牲的必然性,但是似乎也让人感到了某种不安。
舍勒认为快乐也是真实的积极的。“任何快适的自我肯定都均毋庸置疑,断难予以驳斥。快适无需以任何形式证明其价值。它‘在’,当它在时就已富有价值。”[注]同上,第649页。他认为生命的快乐来自于生命力的过剩,是第一性的。而需求满足的快乐是第二位的。人类的精神创造也是如此。艺术创造的快乐大于艺术享受的快乐。提升生命的快乐大于维持生命的快乐。他认为生命本身的痛苦和快乐不是出于匮乏,而是出于生命本身的进化和提高。匮乏和需求并不推动生命的进化。他认为像叔本华那样否定快乐,肯定痛苦是错误的。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都不能正确地面对快乐,它们最终都会导致悲观主义。
佛教也非常重视苦的问题。关于苦的认识被称为苦谛。佛教认为轮回中的有情都处在苦中。苦分为三苦、八苦等。三苦就是苦苦、坏苦和行苦。苦苦就是普遍承认的苦,例如疾病、离别、死亡等。坏苦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快乐。一切快乐都是不长久的,人在快乐失去后就会感到痛苦。如《佛子行》说:“三有乐如草尖露,乃是瞬间坏灭法”。世间的快乐也是痛苦,就像是在饮用高浓度的盐水之后喝一点低浓度的盐水一样。众生往往认为存在真实的快乐,拼命追求这些快乐,但是最后总是获得痛苦。如《入行论》所说:“众生欲除苦,反行痛苦因。愚人虽求乐,毁乐如灭仇。”行苦就是指一种身不由己的迁流变化而导致的痛苦,例如我们都不想老,但都不得不老;都不想死,但都不得不死。《法华经·信解品》中说:“以三苦故,于生死中,受诸热恼。”八苦则是指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和五蕴炽盛苦。生老病死都是苦,相爱的人最终会分别,怨恨的人总是会相遇,想要的总是得不到,色受想行识的活动都是苦的流转。因此,只要不从轮回中出离,每个有情生命都不得不感受到这些痛苦。如果我们正确地认识了这些苦,就证悟了苦谛。证悟苦谛是生起出离心的基础。《入行论》中说:“乐因何其微,苦因极繁多。无苦无出离,故心应坚忍。”世亲论师的《俱舍论》就是依据苦、集、灭、道的次序写成。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对苦谛进行了广泛的宣说。而诸佛菩萨出世说法的目的就是帮助众生出离轮回苦海。《入行论》中说:“我于十方佛,合常诚祈请,为苦惑迷众,燃亮正法灯。”
舍勒推崇佛陀对苦的认识。他认为佛陀对苦的揭示不是出于个人的痛苦经验,而是出于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他否认佛教是悲观主义,因为悲观主义包含了愤慨、归罪等情绪。他敏锐地指出,受苦论并不是佛教的一个部分,佛教总体上就是一种受苦论。但是舍勒对苦的界定和佛教是不同的。舍勒的苦等同于佛教的苦苦,对行苦和坏苦是否定的。他仍然肯定了快乐的真实性。佛教认为快乐是把有情束缚在轮回中的毒药,所以应当坚决予以断除。所谓“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舍勒则是站在生命进化的角度来定义苦,认为受苦的意义就在于牺牲。但是我们的很多苦都和牺牲没有直接关系。例如我在路上摔了一跤,这是不是受苦呢?所以牺牲意义上的苦和我们的日常受苦经验是相去甚远的。佛教也肯定了痛苦的价值和意义,但不是在牺牲的意义上,而是在痛苦可以使人不再贪执轮回的意义上。《入行论》中说:“苦害有诸德,厌离除骄慢。悲愍生死众,羞恶乐行善。” 我们如果简单把受苦和牺牲联系起来,容易产生盲目追求受苦的问题。
二、苦的原因
舍勒认为痛苦来自于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结合关系。部分不仅在整体中而且为了整体而起作用。部分为了整体而牺牲,这是痛苦产生的一般原因。“独立的自具法则性的部分,对自己在整体中的功能位置的抵制(部分与整体团契,并归属于整体),才是构成世界上痛苦和受苦的(理念性的的)可能性的最一般的本体论的第一原因。”[注]马克斯·舍勒:《舍勒选集》(上),刘小枫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638页。具体说,部分对整体的抵抗或者整体对部分的抵抗,就是造成受苦的一般原因。如果消除了这种抵抗,或者部分完全顺从整体,就不会产生痛苦。
他指出,整体和部分的团契的结合是产生痛苦的根源。如果没有这种团契的结合,就不会产生痛苦。在一个纯粹数量和机械的世界中并不存在受苦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世界不是一个整体,其中的各种事物也不是整体的部分。一个纯粹目的论的世界也不存在受苦的问题,因为在目的论的世界中不存在独立的个体,每一个事物都是为了其它事物而存在。同样,因果性的有神论、机械论的唯物论和抽象的泛神论一元论都不存在受苦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痛苦只是因果的报应,那就是罪有应得,也不应该看作是受苦。
舍勒进一步认为整体和部分的结合本质上是一种爱的关系,所以爱是痛苦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例如性爱就是快乐和死亡的结合体,而死亡则是最大的痛苦。“爱与痛苦必然内在地结为一体。爱是一切构成(在空间上)和一切殖生(在时间上)的原动力,它因此创造了既是死亡又是殖生的‘牺牲’的先决条件。”[注]同上,第640页。生殖和死亡都是生命超越自身的形式,两者共同根源于爱。“痛苦和死亡都源于爱,没有爱,恐怕就没有痛苦和死亡。”[注]同上,第640页。舍勒认为,爱、死亡、痛苦、结合构成和生命机体层次的提高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牺牲或者痛苦应该在这种统一性整体之中来理解。因为部分和整体之间的爱,部分奉献给整体,较低层次奉献给较高层次。部分替代整体受苦和死亡,使整体获救、进化和提升。从这种角度看,一切受苦都是替代性的和自愿的。个体的死亡都是替代,是为了整体能够免于死亡,并且以此效力于生命整体本身。“一切爱都是牺牲之爱,即一个部分为了一个换形的整体在意识中的(主观的)牺牲之回音。”[注]马克斯·舍勒:《舍勒选集》(上),刘小枫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641页。爱就表现为牺牲,不愿牺牲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所以爱也就必然和受苦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爱,也就没有牺牲和痛苦。“没有死亡和痛苦,就谈不上爱和结合(团契);没有痛苦和死亡,就谈不上生命的更高发展和生长;没有牺牲及其痛苦,就谈不上爱的甘美。”[注]同上,第641页。爱是团契的结合的基本精神。没有爱,就没有团契的结合,因而也就是没有受苦和牺牲。恰恰在牺牲中,爱的光芒才变得光明亮丽。爱和团契的结合是一回事。因为爱才有牺牲,也才有苦。
舍勒也进一步看到,牺牲不仅包含了受苦,也包含了快乐。牺牲同时包含了哭和笑。“快适与痛苦毕竟同样本原地植根于牺牲和牺牲之爱;一旦试图否定快适与痛苦,或两者之一,这大概意味着否定生命本身。两者在最纯粹和最高级的爱之牺牲中的合一、凝聚、综合,才构成生命的顶点;得与失在爱之牺牲中同一。”[注]同上,第642页。牺牲本身是痛苦,但是牺牲又来自于爱,是部分对整体的爱,是低级层次对高级层次的爱。同样,牺牲也会带来快乐。牺牲和受苦会让人产生高贵和神圣的自豪感,在牺牲中自我的意义获得了最高的肯定。牺牲中包含了爱的快乐和为所爱者付出生命的痛苦。牺牲是在快乐和痛苦之前的,快乐和痛苦是个体生命的牺牲的结果。在牺牲中,快乐和痛苦结合在一个行为中。特别是在自由的精神位格的牺牲中,人们同时体会到爱的快乐和舍弃生命的痛苦。舍勒认为痛苦和快乐的对立冲突只有在感官生活的最低级和最边缘的范围内才是相互排斥的。越是深入到人的自我深处,特别是精神位格的深处,就越是相互融贯的。所以生命本身就是由牺牲、痛苦、快乐和爱构成的整体。如果牺牲只是痛苦,没有任何快乐,人们也是无法承担的。人都是追求快乐的,有人追求牺牲中的快乐,所以牺牲中的快乐也是产生受苦的原因。
舍勒还分析了受苦的文明根源。在西方现代文明中,随着人和人的结合构成和结合关系的日益紧密,人和人的依附性越来越强。这种整体性的结合关系导致痛苦在质和量上的增长。原始人的那种和谐而持久的快乐消失了。现代人感受到更多的孤独、责任、无助,与自然、群体和传统也日益疏离。虽然痛苦本身没有变化,但是现代人对疼痛感的忍受能力则在下降,这意味着受苦比幸福增长更快。因此卢梭、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都在幸福论上否定了现代文明。文明的进步必然导致痛苦的增长。这体现了舍勒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佛教认为苦是一种恶业的果报。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教一方面讲万法皆空,这属于性空的本体的方面。一方面讲因果不空,这属于缘起的现象的方面。所谓“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所以因果不虚是佛教的基本观念。佛教认为造作恶业的原因是无知或者无明。在《俱舍论》中,无明就是指对四谛的无知。在中观宗中,无明就是指认为有真实的我的邪见。在唯识宗中,无明就是指邪见和未解中的无知。总起来说,无明就是对诸法实相的无知。因为无明愚痴,我们认为有实有的世界和自我。依据这种实有的执著,就产生了贪、嗔、痴“三毒”。这三种烦恼推动我们去造作各种恶业,这些恶业则推动我们进入下一世的轮回,如此流转不息,永无尽头。
佛教用“十二缘起”来具体说明痛苦产生和轮回流转的原因。缘起法是佛教最基本的思想,其基本观点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十二缘起分为老死、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名色、识、行和无明。其基本关系就是老死缘生,生缘有,有缘取,取缘爱,爱缘受,受缘触,触缘六入,六入缘名色,名色缘识,识缘行,行缘无明。这十二缘起是“前前为因,后后为果”的关系。有了前一个,就必然产生下一个。其中,爱、取、有是导致生死轮回的重要原因。佛教对十二缘起的揭示就是集谛。集谛主要是说明痛苦产生的原因。
舍勒认为苦的原因是部分和整体的结合关系。这种结合来自于爱,因此爱也是苦的根源。这种结合的概念和佛教的集谛概念有点相似。他也看到,爱是牺牲的原因,快乐是牺牲的果。他对牺牲、爱和快乐都是比较肯定的。佛教也肯定了每个众生和所有众生的团契关系,例如“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强调我们和众生的一体性关系。佛教还认为在无始的轮回中,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这也是一种整体性的关系。佛教也看到,爱和取是重要的缘起支,但爱是我们受苦的原因,是要断除的。佛教也不承许一种所谓的爱之牺牲。佛教认为布施自己的身体只有证悟空性的登地圣者才能做,登地菩萨为了众生牺牲自己也是非常快乐的。但是佛教禁止凡夫布施身体或者牺牲,因为凡夫会产生痛苦和后悔心。佛教也不承认生命的进化,生命的存在是一种无始轮回流转。虽然轮回有成、住、坏、空的不同阶段,但是其中没有所谓的进化和退化。佛教虽然认为当代世界是末法时代,但是佛教认为这是众生根基败坏的表现,现代文明乃是这种败坏的根基产生的。所以重要的不是反对现代文明,而是改善自己的品性。
三、灭苦之道
在受苦的技艺问题上,舍勒首先讨论了历史上的七种受苦的技艺或学说。第一,使受苦对象化和听天由命。第二,享乐主义地逃避痛苦。第三,漠化痛苦乃至麻木。第四,英雄式地抗争并且战胜痛苦。第五,抑制受苦感,并且以幻觉论否定受苦。第六,视一切受苦为惩罚,并使受苦合理化。第七,基督教的受苦论,即福乐的受苦;内心充满福乐的以自由态度承担痛苦,并且通过上帝之爱使人从受苦中救赎出来。他称之为“十字架的大道”。“基督教率先以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方式,即以关于上帝自己在基督身上出于爱自由地替人受难牺牲的思想,照亮了痛苦的事实,除非人们以这种牺牲理念去把握受苦,也许才可能接近一种更深刻的受苦的神正论。”[注]马克斯·舍勒:《舍勒选集》(上),刘小枫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636页。基督教并不否定痛苦,也不试图彻底消灭痛苦,而是强调福乐地自由地受苦。
舍勒对基督教受苦论的分析依据的是情感的深度层次理论。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质的价值伦理学》中,他把人的情感体验分为四种,即感官情感、生命情感、心理情感和精神情感。感官情感是最表层的,精神情感是最深层的。这种理论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的内心世界存在不同层次的情感深度,不同层级的情感可以同时存在。第二,这些不同层级的情感之间不会相互抵消和干扰。第三,越是深层次的情感越不受主观意志的控制,越是深层的肯定性情感越具有恩赐性。第四,人越是在深层次情感中不满足,就越是在外在的感性区域寻求代偿。越是在深层次情感获得满足,就越是在外在的边缘区域中轻松福乐地受苦。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快乐,主要取决于他的深层情感,而不是外在的表层的情感。我们越是在内心深处中充满了爱和快乐,我们就越是可以承担和战胜表层的痛苦。
以此理论,舍勒认为上帝之爱涉及到人的深层的精神情感的满足。如果我们与上帝的爱有了深层的团契,让上帝之爱和仁慈充满内心世界,那么我们就能够承担表层的痛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受苦和牺牲就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基督教的受苦学说所要求的绝非仅是忍耐地承当受苦。它要求——确切地说——揭示一种福乐般的受苦:最核心的观点是:只有福乐的人,即与上帝同在的人,才能以正确地方式承当受苦,才能爱受苦并在必要的时刻寻求受苦。”[注]同上,第670页。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个体精神位格和上帝的无限位格联系起来,我们的最内在的精神情感就能够获得最大的福乐。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快乐,一点点痛苦就可以使我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和正义。舍勒认为基督教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提出了面对痛苦的新方法,也是符合人性的深度情感层次的方法。
所以,在舍勒看来,消除痛苦的方法就是对上帝的信仰和爱。我们应该依靠对上帝的信仰和爱而承受痛苦。通过表层情感的受苦,人们才能深入灵魂的城堡,深入更深刻的精神世界。为了感受上帝之爱,人们会追求受苦。“基督教对待受苦的态度有独特的循环过程:首先放弃凭自己的理知和以‘我’为中心的意愿去享乐地逃避受苦,放弃以英雄的姿态去战胜痛苦,放弃以斯多亚式的坚韧去承受痛苦,当他通过基督向上帝的强力敞开自己的灵魂,将自己引荐并托付给上帝的慈爱,精神性的福乐就会恩赐般地降临到他身上,这种福乐使他极度幸福地承受任何受苦,视受苦为十字架的意义图景(Kreuzessinnbild)。”[注]马克斯·舍勒:《舍勒选集》(上),刘小枫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672页。我们越是和上帝之爱同契,我们就越是可以无苦地承受痛苦。所以最重要的是内心充满对上帝的爱和信仰,那么我们的人生中的痛苦就无足轻重了。“上帝、基督和基督徒所践行的爱,即‘在上帝之中爱一切’这一意义上的爱将基督徒引向受苦和牺牲,但此爱也是福乐之源。爱使基督徒能福乐地承受受苦。”[注]同上,第672页。基督徒不会以享乐的自私的方式逃避痛苦,反而会主动地寻求受苦。例如在一部二战电影中,在集中营中,当一个逃跑者要被纳粹军官枪毙时,另一个人主动站出来替那个人而死。
针对受苦的文明根源,舍勒认为现代人不再信仰上帝,他们内心深处充满痛苦,所以他们拼命追求表层的快乐。但是他们反而感受到更深的痛苦。所以现代文明应该专注于提高精神性的爱和快乐。“除非日益增长的文明和文化在爱之中,在不断自我完善的日益增长的牺牲之爱中,同时产生隐秘的福乐感,这些感受可以补偿一切增长的受苦,并使灵魂的核心超越这些受苦,增长的文明和文化,使人蒙受的无疑呈上升趋势的受苦,最终才是‘值得的’。”[注]同上,第649页。如果现代文明不能提高人的内在的快乐,就是无法持续的。
佛教认为消除痛苦的方法就是如实地认识世界和人生。佛陀把消除痛苦的方法名为八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是从身、口、意三个方面对人进行引导和规范,其基本精神就是按照四圣谛的基本思想来认识世界和人生。例如一般认为世界是常、乐、我、净,佛教认为世界的真相是无常、苦、空、无我。这种修行方法就被称为道谛。
八正道也可以分为戒、定、慧三学。戒就是对人的身口意进行约束和规范。《俱舍论》指出戒是佛陀出于悲心而制定的,戒律具有防非止恶的作用。定是一种心的寂止,就是“心一境性”,即内心的专注和安宁。佛教的禅定是止观双运,在静定中,修行人对诸法实相才会有更深刻和真实的认识。慧是认识到诸法实相,特别是对无我的认识。佛教最核心的教义就是无我的智慧。小乘有部虽然承认实有的微尘和刹那,但是也同样承认无我的观点。唯识宗虽然承许实有的心识,但是也承认无我。中观宗则进一步否定了实有的心识,达到了最彻底的无我空性的智慧。无我的智慧就是空性的智慧。所以要获得解脱,就应该“勤修戒定慧,消灭贪嗔痴”。
大乘佛教还特别强调菩提心的重要性。因为痛苦的根源就是我执,如《入行论》中说:“世间诸灾害,怖畏及众苦,悉由我执生,此魔我何用?”而菩提心就是对治我执的最好方法。所谓菩提心就是利益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如来正等觉果位的希求心。《华严经》中云:“善男子,譬如金刚宝虽坏损,亦胜过一切上等金饰,且不失金刚宝之名。善男子,同理,发菩提心之金刚宝纵然离开勤奋亦胜过一切声闻缘觉功德之金饰,亦不失菩提心之名,复能遣除轮回之一切贫困。”《入行论》中说:“欲灭三有百般苦,及除有情众不安,欲享百种快乐者,恒常莫舍菩提心。”《现观庄严论》中说:“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所以菩提心是区别大乘和小乘的根本标准,也是我们消除我执和痛苦的最好方法。
佛教对人的深层精神情感,特别是精神的喜乐,有深刻的揭示。一方面,佛教排斥表层的感官的快乐,认为这种快乐是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源。另一方面,佛教认为在修行中存在大乐。一个是禅定的快乐,所谓“禅悦为食”,即在三禅中是最快乐的。但是这种乐也会把有情束缚在轮回中,所以要克服对这种乐的贪执。其次是证悟空性的大乐。这种快乐是一种见到诸法实相的真理的极乐狂喜。再次是利益众生的乐。《入行论》中说:“珍贵菩提心,众生安乐因,除苦妙甘霖,其福何能量?仅思利众生,福胜供诸佛,何况勤精进,利乐诸有情。”再次是佛教净土宗信仰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永远断除苦。最后是佛教的最高修行目标即获得圆满佛果的涅槃之至乐。这些深层的精神快乐也都可以说是佛教徒精进修行和承受痛苦的动力。
舍勒认为基督徒必须放弃自己的理知和“我”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而上帝的恩典是我们获得深层的福乐的根源。这和佛教是非常一致的。佛教也认为修行要放弃自己的分别念,放弃我慢、我执、我爱等,才能获得正知正见,才能获得诸佛菩萨的加持,最后才能够成就佛果。佛教也强调对诸佛菩萨的信仰,认为“信是道源功德母”。有的人凭借信心就可以获得成就。佛教认为诸佛菩萨无时无刻不在加持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的业和烦恼的障覆,我们不能得到这种加持。只有清静业行,才能得到加持。但是信仰在佛教中并不占据首要的地位。佛教的修学次第是信、解、行、证。佛教强调的是最终的证悟。没有证悟就不可能成就佛果。所以佛教特别强调空性智慧在信仰和修行中的重要性。但是在基督教中,对上帝的信仰是最重要的。可以说,佛教和基督教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对空性智慧的认识。
四、苦的熄灭
从某种意义上看,舍勒并不承认苦的熄灭。他强调的是苦和乐的共存。一方面,我们是受苦的。因为痛苦和个体生命的牺牲、和整体生命的进化是联系在一起的。生命的进化是不可能停止的,部分和整体的同契是不可能解除的,牺牲、痛苦和生命的进化是一致的,所以受苦也是不可能消除的。在精神位格的领域中,我们的有限位格的进步也是不可止息的,我们的有限位格和上帝的无限位格的同契也是不可能停止的,所以受苦也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关键不是彻底消除痛苦,而是以爱和快乐来福乐地承受痛苦。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快乐的,因为上帝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中。和上帝的爱相比,和信仰带来的快乐相比,我们的受苦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应该全神贯注于上帝的爱和乐,而不是自己的表层的苦受。一个基督徒应该在爱中受苦,通过受苦更深地与上帝之爱同契。“与基督的十字架同契,并在基督中受苦,这个基督教的吁求,植根于另一个更重要的吁求:像基督那样并在基督中去爱。换言之,不是爱的同契植根于十字架的同契,而是十字架的同契植根于爱的同契。”[注]马克斯·舍勒:《舍勒选集》(上),刘小枫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669—670页。受苦不是脱离爱的同契,而是回归爱的同契。受苦是为爱的行动而准备,是像基督那样为爱而牺牲。恭顺、忍耐、谦卑地受苦等被动的德行从属于爱的行动的主动德行。这就是舍勒对受苦的熄灭的回答。如果舍勒还承认苦是最终可以熄灭的,那么就是死后灵魂进入天国,和上帝同在。
舍勒批判了那些试图想彻底消除痛苦的学说。他认为西方文明和佛教都试图彻底消灭苦。古代西方文明走的是英雄式的抗争之路。不论是犬儒主义还是斯多亚派,他们都试图以理性认识彻底否定痛苦的存在。这种英雄主义对爱和属于爱的快乐是一无所知的。现代西方文明是从外部反对痛苦产生的客观根源,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原因。现代文明认为只要我们发展了技术、医疗、工农业等,消灭了痛苦产生的根源,例如贫困和战争,我们就可以最终消除痛苦。现代文化是主动型的英雄式的反抗痛苦。佛教试图从内部彻底消灭痛苦。佛教将万物和个体都转变为幻象,痛苦也最终非实在化。舍勒认为佛教不是要消除痛苦本身,而是要彻底消除对痛苦的抵抗。我执和烦恼是痛苦的根源,所以破除我执和烦恼才是最根本的。他看到:“佛陀之信念与西方英雄主义这两种看似对立之两极的思想方式均不认识(使人升格的)受苦和非高贵的(使人降格的)受苦之间的区别,以为凡受苦均是坏,应当消除。”[注]马克斯·舍勒:《舍勒选集》(上),刘小枫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654页。他认为基督教是被动型的英雄式的承担痛苦,是一种“受苦英雄”的理念。基督教既完全承认痛苦的存在,又不会对痛苦和不幸听之任之,而是以恭顺和福乐的态度主动承担痛苦。
对于佛教来说,苦的熄灭就是涅槃。佛教追求的理想就是通过修行达到寂静解脱的涅槃境界。涅槃是断灭一切烦恼习气的寂静妙乐的状态。《阿含经》指出:“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是名涅槃。”涅槃寂静和普度众生是佛教追求的理想。这种最终的理想被称为灭谛。
小乘佛教的涅槃就是成就阿罗汉的果位。阿罗汉是指依照佛的教导修习四圣谛,脱离生死轮回达到涅槃的圣者,意译为应供、杀贼、无生。所谓杀贼就是指杀掉烦恼之贼。阿罗汉通过最后的灭受想定而入有余涅槃或者无余涅槃。之所以把烦恼称为贼,是因为佛教认为真正的敌人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心的烦恼。应供是指阿罗汉因为证得了道果,堪受人天的敬仰、供养、礼拜,为众生作大福田。无生就是指阿罗汉断了见思烦恼,跳出了三界生死轮回,最后进入无余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不受后有”。
大乘佛教反对小乘佛教仅仅追求自我寂灭的涅槃。大乘佛教的涅槃则是指成就佛果。在《涅槃经》中,涅槃境界被看作是常、乐、我、净。佛果具有断和证两种功德。断就是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证就是获得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佛具有三身四智、无眼六通的功德。“三身”是指法、报、化三身。“四智”就是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平等性智和大圆镜智。“五眼”就是指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六通”是指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他心通、神足通、漏尽通。所以佛果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境界。当然,成就佛果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自我的安乐,而是为了度化无边无际的众生。
舍勒关于在爱和乐中受苦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他可能认识到,试图彻底消灭痛苦的思想会导致对痛苦的拒绝,这样反而会导致更大更多的痛苦,因此以福乐的心态忍受痛苦才是最好的方法。这种观点和大乘佛教的在轮回中度众生的思想是比较相似的。大乘菩萨的精神是“智不住三有,悲不入涅槃”。也就是说,菩萨的智慧使他不会再堕入轮回,菩萨的慈悲使他自愿在轮回中救度众生。《华严经》描述菩萨的境界是:“犹如莲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著空。”但是佛教强调这种境界必须以空性智慧为基础,没有这种空性智慧,就无法真正度众生。如果说舍勒还承认一种苦的最终熄灭,那就是死后往生天国。这和净土宗的往生西方是比较相似的。但是佛教强调往生西方后并不是一种静止的死灭的状态,而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继续学习和修行,最终成就佛果、普度众生。
五、结束语
人生在世,苦多乐少。人人都在避苦求乐。快乐和痛苦是每个人都面对的根本问题。只有认识了快乐和痛苦的奥秘,我们才能认识人性的奥秘。古往今来的智者大多都在寻找避苦求乐的方法。这也应该是我们研究哲学和宗教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当代哲学似乎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学院式的概念思辨和逻辑研究中。其实,我们只有认识了快乐和痛苦的奥秘,才能理解什么是哲学和哲学何为,否则我们的哲学研究就只是一些繁琐而空洞的概念游戏,对于人生没有什么意义。或许,只有把苦乐作为思考的重要问题,哲学的复兴才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