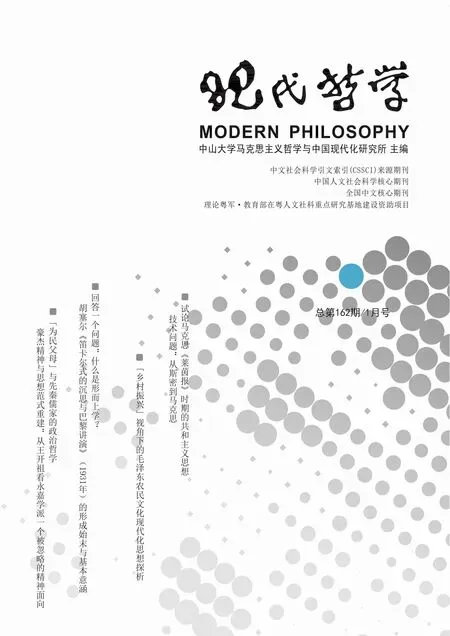郭象删定《庄子》文本及其诠释学问题试析
李耀南
本文旨在论述郭象在庄学史上最早删定《庄子》文本,以及其中隐含的诠释学问题。
一、依“庄子之意”删定《庄子》文本
学界多注意到郭象《庄子注》是庄学史上诸多注庄、解庄之作中最具独创性的一部,然郭象作为最早删定《庄子》文本之人,则似鲜有论及。
郭象注庄的前提是要确定一个可靠的《庄子》文本,如此方见得是为《庄子》作注。论者有以为:“首先辨庄子之伪作者,实为苏轼而非韩愈,”[注]简光明:《〈庄子〉辨伪始于韩愈说之检讨》,载《诸子学刊》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7—173页。然就现有材料看来,庄学史上首先留察《庄子》书中之伪作,非为苏轼,而是晋人;详细辨别庄书中有非庄子所作之文,并删定《庄子》,当属郭象;最早注意到晋人及郭象删定《庄子》事的是经隋入唐的陆德明。
有关庄子著述,《史记》本传载:“庄子者,……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注][汉]司马迁:《老子韩非子列传》,[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63,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43—2144页。值得注意的是,史公但言庄子之若干篇名,所称庄子系庄子其人而非书名,有学者据此疑其时尚未有《庄子》书名;[注]此参余嘉锡之说,余氏据《史记》引管子、商君、庄子之所著但言篇名而断言“诸子著书,皆只有篇名,无书名。”(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3页)然淮南王有《庄子略要》《庄子后解》,其中“庄子”或应指书名。史公未言篇数,则庄子所著篇数尔时抑或未定。史公以十余万言悉为庄子所著,未言其中有非出庄子的篇章文字。
东汉班固之《汉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汉志》是对于刘歆《七略》“删其要”[注][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汉]班固撰、[清]王先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汉书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899页。而成,《七略》又是摘取刘向《别录》以为书[注]参见姚名达撰、严佐之导读:《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8—39页。,刘向校勘整理过庄书,且“很可能还撰写过《庄子书录》”[注]邓骏捷:《刘向校书考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4页。,《汉志》所载《庄子》五十二篇本“即刘向校订之本”[注]邓骏捷:《刘向校书考论》,第174页。。按照刘向、班固“审定伪书”的通例,《汉志》对于那些疑为依托古人而实属后世制作的书籍逐一指明[注]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释例》,载张舜徽:《张舜徽集·广校雠略 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0—131页。,而《汉志》唯于《庄子》无有疑词,则刘、班一以五十二篇《庄子》本咸为庄子所作可知。班固以下,郭象之前,从陆德明《庄子音义》辑录的注文中得知,为庄文施注的除了班固以外,尚有王逸、服虔、韦昭、高诱、许慎、宋均、王肃等等未见诸贤尝言庄书内有非庄子之文。
经隋入唐的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庄子》:
然庄生弘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说,若《阏弈》《意脩》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庄子》,载[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页。
《序录》载有晋人司马彪、崔譔、向秀、郭象等若干家《庄子》注、音,今就“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注者以意去取”数语看来,晋人各家注都有《庄子》内篇,所不同的在于外杂篇,有的有外篇无杂篇。陆氏所见到的各家《庄子》注的卷数参差不同的原因是各家对于《庄子》有所删裁与简择,各家何以于《庄子》有所“去取”呢?从“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来看,晋世注家已经见出《庄子》书中有后人增加而非庄子所作的部分,足见对庄书辨伪晋世已有之,惟今各家《庄子》注不存全璧,故不知其去取之崖略。
日本高山寺钞本(下称寺钞本)庄子郭注残卷之《天下》篇末所附一段文字:
夫学者尚(当)以成性易知为德,不以能政(攻)异端为贵也。然庄子闳才命世,诚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不能畅其弘旨,而妄窜奇说。若《阏亦(奕)》《意脩》之首,《尾(卮)言》《游易(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若此之类,十分有三。或牵之令近,或迂之令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或出《淮南》,或辨形名,而参之高韵,龙虵并御,且辞气鄙背,竟无深澳(奥),而徒难知,以因(困)后蒙,今(令)沉滞失乎(末)流,岂所求庄子之意哉!故皆略而不存。令(今)唯哉(裁)取长(于)达致、全乎大体者为卅三篇者[注]引文据刘文典《庄子补正》(中华书局,2015,第902页),括号中字凡未加注者俱为日人武内义雄、狩野直喜校正。其中“长(于)达致”之“于”字据涂又光校补(《楚国哲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350页注1)。
寺钞本的这段文字不见于宋以后的庄子刻本《序录》所引郭象语悉见于寺钞本,其它文字也有与寺钞本相同的内容,足见陆德明《序录》与寺钞本这段文字关系密切。就古人著书体例来看,寿普暄以这段文字为“郭象《后序》”[注]寿普暄:《由经典释文试探庄子古本》,《燕京学报》1940年第28期,第92页。之说可从。
郭象明确提出庄书有十分之三的部分非庄子所作,原因是这些内容辞气粗鄙偏背,毫无深奥的意义,却又徒增理解庄子的困难,其中有的是人为牵合使之近于庄子,有的迂远而荒诞,有的像《山海经》,有的类似占梦书一类的文字,有的出自《淮南子》,有的是辨别形名问题,这些内容中也掺杂了一些韵致高远的文字,所以郭象称之为“龙蛇并御”。值得注意的是,郭象对于庄书掺入《淮南子》的这部分内容,不同于前文之或“似”某某,而是径定其“出”于《淮南子》。郭象删定的大体情况为:《尾(卮)言》《游易(游凫)》《子胥》这些篇章是整篇删除,《阏奕》《意脩》两篇只删除了开头的部分,其他出于淮南王书的篇章自当悉数去掉,删定的三十三篇《庄子》在他看来才真正是庄子的著述。
所以,从存世的《庄子》注来看,我们可以把郭象定为最早辨别《庄子》中之伪作并删定《庄子》的第一人。至于苏轼之后直至今人,都只是在郭象所删定的《庄子》三十三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辨别庄书之中非出庄子的篇章。
二、郭象依“庄子之意”删定《庄子》文本所隐含的诠释学问题
郭象依据“庄子之意”来删定《庄子》文本非止有版本学的意义,其隐含的诠释学意义不可忽视。文本是诠释的基础,有什么样的《庄子》文本,就会有什么样的庄学诠释。可靠的《庄子》文本是郭象注庄的前提,潜在与显在地影响、制约着诠释过程与结果。只有确定哪些属于庄子所作,哪些非庄子之文,而后才能基于庄子之文来注庄解庄。郭象对此有明确的理论自觉。郭象把那些在他看来无法“求庄子之意”的内容剔除,此举是为注庄奠定基础。
郭象立足于“庄子之意”来辨别庄子书中的伪作,以求存庄子之真,合乎庄子之意的则留,不合则去。郭象删去《阏奕》《意脩》等部分的原因在于这些内容根本不可能是“闳才命世,诚多英文伟词”的庄子所作,不能据以寻求“庄子之意”。这意味着,在郭象看来,能据以求“庄子之意”的才是庄子之文,否则就不是庄子所作,于是“庄子之意”成为郭象判定是否庄子之文的根据。
首先,什么是郭象所说的“庄子之意”呢?西方解释学关于作者原意和文本原意有很多争论,比如怎样界定作者,作者又有源作者和事实作者之分[注]周宪:《文本阐释与作者意图》,《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期。,有无作者原意,作者原意是否能够重构复原,文本的意义是否来自作者的赋予等等,例皆聚讼纷纭。尤其罗兰·巴特1968年的《作者之死》一文完全否定作者对于作品意义的支配地位,主张作品的意义来自读者的解读,而不是作者的精神灌注。
反观郭象则不同,郭象肯定作为著者的庄子对于《庄子》一书之意义的支配位置。“庄子之意”包含两重意义,一是指作为作者的庄子本意,一是指《庄子》一书的原意。尽管庄子之意见于其所著之文,郭象无法离开《庄子》来求取庄子本意,对于“庄子之意”的追寻要通过对《庄子》一书之探寻来实现,但郭象的“庄子之意”根本上是指作为作者的庄子之意,而不是《庄子》一书之意。在郭象看来,作为作者的“庄子”本意是可以把握的,郭象注庄有以求取“庄生之旨”的明确目的[注]案:郭象注庄有以求取“庄子之意”“庄生之旨”为鹄的,对此笔者另文耑论。。求取作者之心是古人读书的普遍取向,“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注][清]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页。根据古人注书的通例,“注释的目的在于诠释古籍,而其最高境界乃是追寻原意,求契作者之初心。”[注]许逸民:《古籍整理例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7页。“传注的职责,既以解说古书为主,自以不失古人原意为最大目的。”[注]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4页。这些非常适合用来说明郭象注庄的目的。郭象与古代大多数为经典作注的传注家一样,是把著者之意作为注释所要达到的终极鹄的。陆德明《序录》:“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4页。《天下》篇末陆德明注:“子玄之注,论其大体,真可谓得庄生之旨矣。”[注][唐]陆德明:《庄子·天下》注,[唐]陆德明撰、张一弓点校:《经典释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14页。陆氏是在与其所见之其他各家注的比较中独推郭注,其原因就在于郭注能得“庄生之旨”。
其二,由此涉及到的问题是,庄子之意必须通过庄子文本的理解而获得。郭象首先面对的《庄子》文本又是包括了那些在他看来不合庄子之意的篇章,所以郭象对于庄子之意的把握又是基于包括不合庄子之意的篇幅在内的《庄子》。他要判别这个文本中哪些出自庄子,哪些非出庄子。当他对文本做出这种区分之初,胸中必先有一个庄子之意,这个庄子之意是如何获得的呢?郭象《天下》注:
昔吾未览庄子,尝闻论者争夫尺棰连环之意,而皆云庄生之言,遂以庄生为辩者之流。案此篇较评诸子,至于此章,则曰其道舛驳,其言不中,乃知道听涂说之伤实也。[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1114页。
郭象自道其未读《庄子》时,通过他人获得了对于庄子思想的印象,并接受他人的看法,把庄子视为辩者之流。从诠释学来看,这算做郭象对于庄子的一种“前见”,这个前见在后来的读庄和研究过程中得到修正。可见郭象所把握的庄子之意经历了不断修正补充丰富的过程,同时又以所把握的庄子之意,对于《庄子》文本进行不断别择、排除与厘定。这样郭象的庄子之意以及选择符合庄子之意的文本,剔除不合庄子之意的篇章,这之间有一种互为前提、递相促进的循环关系。
其三,郭象基于“庄子之意”删定《庄子》文本,这种处理文本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不会发生讹误?郭象所认定的符合庄子之意的文本是否可以确定为庄子所作?其中有无他人文字掺入?郭象删除的那些不合庄子之意的部分是否就一定不是庄子所作?其中是否会有出自庄子而被郭象误删的内容?这些都是郭象删定庄子文本所留下的问题。清人姚鼐云:“夫《庄子》五十二篇,固有后人杂入之语。今本经象所删,犹有杂入,其辞义可决其必非庄生所为者。然则其十九篇,恐亦有真庄生之书,而为象去之矣。”[注][清]姚鼐:《庄子章义序》,[清]姚鼐撰、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3页。这是说郭象所删除的那一部分可能有真是庄子的著作,而所保留的部分也有不是庄子所作。王叔岷认为郭象删定的《庄子》三十三篇“既非庄书旧观,而定于郭氏之私意。”[注]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八,1999年,第1444页,此说或有可榷,如曰郭象纯出主观私意删定《庄子》,则或言之太过;倘谓郭象据以删定《庄子》的“庄子之意”渗入了郭象的“私意”,也就是郭象的个人之见,此则近于情实。由此看来,郭象依“庄子之意”删定《庄子》,此举的解释学意义高于文献学的意义。
其四,在诠释学角度来看,由“庄子之意”来判定庄子文本的方法所存在的问题当予深察。郭象之后直至当今,一直存有对于郭象删定的三十三篇《庄子》本进一步辨伪的事情,其目的乃是试图复原庄书之旧,得庄子之本怀,这一点与郭象一脉相承。苏轼基于糅合儒道的立场,认为庄子实际上襄助孔子之学,但文辞上却显得是在批评诋訿孔子,这是“阳挤而阴助之”,而《盗跖》《渔父》两篇却像是真在抨击孔子,《让王》《说剑》则“浅陋不入道”[注]苏轼:《庄子祠堂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48页。,所以他将这四篇从《庄子》中剔除。苏轼剔除的根据是这四篇内容与庄子尊孔之意不合,苏轼同样是根据他所理解的“庄子之意”来删除非庄子所作之文。罗根泽疑《天下》篇为庄子所作的原因在于《天下》篇中的“‘天下大乱,……道术为天下裂,’正是庄子的根本意思。”[注]罗根泽:《〈庄子〉外杂篇探源》,罗根泽撰:《罗根泽说诸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庄子的根本意思”成为罗氏推断《天下》出自庄子的理由。张默生把《大宗师》中“文理思想与庄子不合者,删去自‘故圣人之用兵也’至‘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若干句,及自‘以刑为体’之‘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若干句。”[注]张默生:《庄子新释》,台北:天工书局,1993年,第161页。张氏删除的依据也是这些文字与庄子思想,也就是庄子之意不合。张恒寿是“依据《天下》篇所述庄周思想、作风,考察它和今本《庄子》各篇有没有显然符合之处。”[注]张恒寿:《庄子新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页。这里同样以是否合乎“庄周思想”,也就是庄子之意来甄辨庄书各篇是否庄子所作的重要根据。所有对庄书进行辨伪的背后都有一个是否契合庄子之意的深层背景,合乎各家所认定之庄子本意的就被视为庄子所作,与庄子之意相悖的即非庄子之文,这种区分的思路和判别的标准可谓遥契郭象。
文献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既是因事为文,则其书不作于一时,其先后亦都无次第。随时所作,即以行世。”[注]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第265页。先秦子书都是“应时而作,旋即流传,……往往多是单篇流传。”[注]邓骏捷:《刘向校书考论》,第168页。《庄子》也是包括庄子及其后学学派之作在内的一个文集,非出庄子一人之手。《庄子》的作者除了庄子之外,还有庄子后学及其学派的若干作者,且在辗转传抄以及汉人整理庄书的过程中,其中会发生何种文字内容的损益以及章节段落的编排,实难臆测。如此《庄子》一书除了庄子之意,还有其他作者之意,这样《庄子》一书就包括了“多人之意”。仅就庄子而论,即便同为庄子所作的篇什,因为作于不同时间,所涉事情不同,每一篇和其他各篇的意义可能差别很大,如此则“庄子之意”更为复杂。我们究竟选择哪种“庄子之意”作为依据,来分辨庄子篇章之或真或伪呢?于是“庄子之意”与确定的《庄子》文本之间陷入更深的纠缠关系。
进而言之,“庄子之意”不是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绝对的“庄子之意”是无法达到的,即便能够确定庄子所作的篇目,读者的“庄子之意”是基于庄文的理解和诠释而来,这种理解和诠释总有个人思想作为理解之前见的介入,所谓“庄子之意”实际上是理解和解释的结果。因而,据于“庄子之意”以辨庄书之伪作,自有其无法跨越的理论障碍。本文并不简单否定考订《庄子》内外杂篇的可能作者以及撰述年代的相关研究的意义,只是对于郭象以及后来诸多以“庄子之意”作为判定庄子之文的根据所存在的诠释学问题加以检讨剖析,以求引起当今学人的注意,当他们仍在依据“庄子之意”来对《庄子》进行辨伪时,应该对此有所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