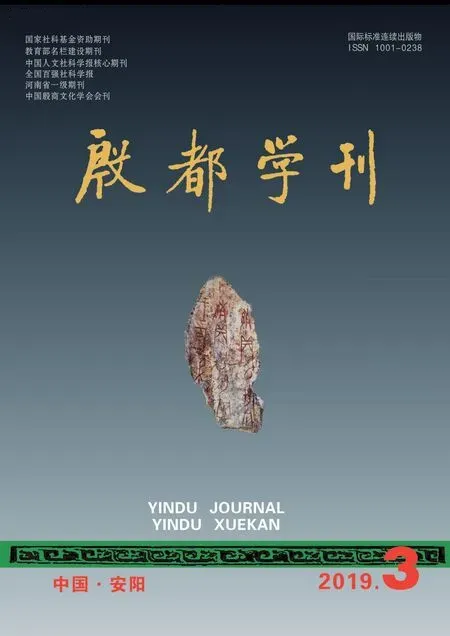春秋时期齐国晏氏家族与陈氏家族关系考论
——以晏子和陈桓子的关系为核心
贾海鹏
(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0)
晏子(约前578年—前500年),氏晏,名婴,字仲,谥平,春秋晚期齐国夷维(今山东高密)人,曾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位君主,显名诸侯。
陈桓子(生卒年不详),名无宇,谥桓,又称田桓子(1)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陈氏先人“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陈公子完之苗裔,亦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位君主,是田氏奔齐后的第五代家族首领。其父田须无(即田文子),妻为灵公之女,其子田开(即田武子)和田乞(即田釐子)。
同为齐国三朝重臣,晏子与陈桓子之间无可避免地有着许多交往。前辈学者多认为田氏家族对国人采取“以家量贷,公量收”的恩惠措施,与公室争民,欲取而代之。而晏子则力谏景公“以民为本”、“以礼治国”来对抗田氏家族。故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斗争。
笔者不以为然。刘式今先生曾说过:“晏子的思想极为矛盾,他欲用维礼企图挽救他事齐三世统治者的命运,但他又痛恨王室的骄暴而同情人民,这两种心情使他的忠君与恤民的思想交织在一起达到了高潮,形成了既痛苦又残酷的斗争。晏子面临着一生最艰难的抉择,只能是流水落花春去了。晏子对于田氏的态度其心情是极为微妙而复杂的”。[1]对此,笔者不但深为赞同,而且认为晏子对田氏家族既有支持又有反对,甚至可以说支持赞美的多,而反对抗拒的少。因文章主题不同,刘先生对此点到即止,没有继续做深入的探讨。学界对这一问题也多是一些只言片语(详见下文),鲜有学者进行专门研究。本文即以典籍记载为依据,进行详细分析。
一、晏氏家族与陈氏家族的早期交往
据史料记载,晏氏家族与陈氏家族在早期就存在着交往,而且关系亲密。
陈桓子登上齐国政坛的时间似乎比晏子早(2)晏子是在其父卒后才步入仕途的。。齐灵公灭莱时,晏弱(晏婴之父)担任主将。灭莱后,“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左传·襄公六年》)。灭莱是晏弱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在此过程中,无疑与陈桓子有着融洽的合作,否则也不会在灭莱后,将象征国家的莱国宗器交与他进献齐侯。
而在晏子参政早年,也曾与陈文子(陈桓子之父)有过交往。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晋之大夫栾逞(即栾盈)作乱于晋,来奔齐,齐庄公厚客之。晏婴与田文子谏,庄公弗听。”对待晋国乱臣栾盈被庄公厚遇之事,两人看法一致,且共同进谏,都被君主驳回,这难免会让他们彼此惺惺相惜。此事在《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中叙述得更加详细:“秋,栾盈自楚适齐。晏平仲言于齐侯曰:‘商任之会,受命于晋。今纳栾氏,将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图之。’弗听。退告陈文子曰:‘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这里没有见到陈文子的劝谏痕迹。不过陈文子的其他言论事迹在《左传》中多有记载,他是春秋时期一位难得的既知礼遵礼,又极具睿智的官员。孔子就曾用“清”来高度评价他(《论语·公冶长》)。我们不难想见,同为齐国的贤大夫,晏子与之交往,十分正常。在交往过程中,对他及其家族产生好感,亦在情理之中。正因为彼此信任,所以晏子在劝谏齐侯无效后,才会也才敢对陈文子说出“君自弃也,弗能久矣”这样的话。试想,如果两人关系不是十分融洽,平日不以诚相待的话,晏子怎么敢随便对他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语呢?要知道,当时在位的可是对晏子不太信任的齐庄公,而不是善于纳谏的齐景公。
由此可见晏、陈两家交情之密,相知之深。
陈氏家族中,与晏子交往最多的是陈桓子,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
二、晏子与陈桓子的直接交往
据《史记·管晏列传》载:晏子“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刘向《晏子叙录》亦曰:“晏子……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在记述其平生事迹的《晏子春秋》(谭家健先生认为该书所记“主要事实多属可信”[2])一书中,也处处可见他秉持节俭的言论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常常能看到陈桓子的身影。
出于各种缘由,齐景公经常赏赐晏子,而陈桓子就曾担任过使者。如:“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无宇致封邑晏子辞”(《晏子春秋· 内篇· 杂下第十九》)(下引该书,只注篇名章数)。而当晏子自己推辞不了的时候,也往往通过陈桓子向君主辞谢,才能成功(3)陈桓子的妻子是齐景公的姐姐,两人有姻亲关系。。据《左传》载,景公认为晏子的住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趁他出使晋国之际,“更其宅”。晏子回国后,“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公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昭公三年》)。另外,吴公子季札聘于齐时,曾对晏子说:“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晏子也是“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襄公二十九年》)的。春秋时期国君赏赐大臣,所派遣的使者多是经过深思精选的,或者是让梁丘据那样的宠臣担任(4)其实晏子与梁丘据之间的关系也颇为复杂,大致经历了先疏、再亲、后疏的过程,笔者认为景公让梁丘据担任使者赏赐晏子是在梁、晏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详见贾海鹏:《灵活中的坚定:从《晏子春秋》看晏子的社交艺术与社交思想》,《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或者是任命与所赐之臣关系融洽之人。显然陈桓子不是梁丘据之流,而景公能让他担任使者,说明他与晏子之间关系的和谐。再者,假如两人平日不相交好的话,晏子也不会屡屡把自己都办不了的事情托付于陈桓子。
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了陈鲍栾高四大家族的内斗。当陈、鲍氏打败栾、高氏,而分其家产的时候,晏子对陈桓子说:“必致诸公。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桓子听之,“尽致诸公,而请老于莒”(《左传·昭公十年》)。对此,前辈学者多认为“晏子的本意是想削弱陈氏势力,维护公室利益”(5)此类观点可参见:叶世昌、童丽:《晏子的经济思想》,王振民主编《晏子研究文集》,齐鲁书社,1998年,第158页; 邵先锋:《<管子>与<晏子春秋>治国思想比较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第187-188页等。。笔者并不赞同。因为晏子向陈桓子抛出的是自己安身立命的理论精华——“义利观”。这样高妙的处世哲学曾让他本人历仕三君而受宠,纵横政坛50余年而获荣,如果对方不是值得深交之人,晏子是不会如此以诚相待赠以哲言的。否则,他至少可以不闻不问,甚至积极主动地支持陈桓子吞并栾、高氏的财产。这样,按照晏子自己的理论,陈氏也会很快步其后尘,走向衰亡,岂不是更如公室之意?此事在《晏子春秋·杂下第十四》中也有类似记载:
栾、高不胜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君不能饬法,而群臣专制,乱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货,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婴闻之,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栾、高不让,以至此祸,可毋慎乎!廉之谓公正,让之谓保德,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怨利生孽,维义为可以长存。且分争者不胜其祸,辞让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尽致之公,而请老于剧。
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陈桓子把打算分栾、高家产的想法首先告诉了晏子,征求他的意见,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对晏子的信任。而晏子却在大乱刚过,局势不稳的情况下,敢于直言批评陈桓子,“君不能饬法,而群臣专制,乱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货,是非制也。”对此,陈桓子非但没有丝毫不满,反而诚心接受,足见两人交情匪浅。更值得注意的是晏子说“栾、高不让,以至此祸,可毋慎乎!”“且分争者不胜其祸,辞让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这很明显就是用自己高超的处世哲学劝导陈桓子避祸趋福,以求长久。陈无宇也是个极具智慧的人,他很快就明白了晏子的意思,并听从之。战化军先生曾说:“在此之前,接连败亡的齐国大夫无一不是最强者,这不能不给比较开明的陈氏敲响警钟。所以,陈无宇确实从内心接受了晏婴的劝说,深刻认识到了‘让’的重要性”。[3]除了把栾、高氏的财产“尽致诸公”外,他还“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从者之衣屦,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与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孙捷,而皆益其禄。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国之贫约孤寡者,私与之栗”,后“穆孟姬为之请高唐,陈氏始大”(《左传·昭公十年》)。看来其结果并非“不以某一个政治家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正如晏子所料,田氏家族得到了福报,从此走向强盛。
《晏子春秋》中晏婴对陈无宇的另一席话可作为旁证:“婴闻之,节受于上者,宠长于君;俭居于处者,名广于外。”(《杂下第二十》)晏子虽是在解释自己因何屡屡不受君赐的缘由,但同时也是对陈桓子的谆谆劝导。
当然,一向主张君子“和而不同”的晏子也有批评陈桓子的时候。如在景公面前就“衣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栈轸之车,而驾驽马以朝,则是隐君之赐也”(《杂下第十二》)为自己辩解,而终使景公罚陈桓子饮酒;说他“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今若子者,昼夜守尊,谓之从酒也”(《杂下第十三》)、“去老者,谓之乱;纳少者,谓之淫。且夫见色而忘义,处富贵而失伦,谓之逆道”(《不合经术者第十五》)等。然而这些都是小节,多属当时贵族们的通病,不足以影响两人之间的感情,甚至还隐约蕴含着晏子对陈桓子的谆谆劝告之意。
王绪霞教授曾道:“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晏子和陈桓子的关系基本上是比较融洽的。”[4]此说很有见地!
三、晏子在他人面前对陈桓子及其家族的评价
据史料记载,晏子主要在齐景公和晋叔向两个人面前谈论过陈桓子及其家族。
(一)与齐景公谈论陈桓子及其家族
据《问上第八》载,景公曾问晏子后世谁会拥有齐国。晏子认为可能是陈无宇的后人,并解释道:“公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其与士交也,用财无筐箧之藏。国人负携其子而归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与人利,而后辞其难,不亦寡乎!若苟勿辞也,从而抚之,不亦几乎!”
除此之外,关于陈氏,晏子与景公还有一次广为流传的经典对话: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敢问何谓也?”公曰:“吾以为在德。”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6)《晏子春秋·外篇·重而异者第十》中也有相似记载。
司马迁认为此时对百姓施以恩惠的是田无宇之子田乞,《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曰:“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粟)(禀)予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不管是田无宇,还是田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田氏家族的行为深合晏子“以民为本”的治国方略,所以即便是在与景公的谈话中,他也不禁流露出了对田氏的赞赏。
(二)与晋叔向谈论陈桓子及其家族
如果说面对自己的国君,晏子对陈桓子及其家族的褒扬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当其出使他国,与别国贤大夫私聊之时,晏子的言论就更能流露出他的真实想法了。据(《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子出使晋国,叔向从之宴,相与语。叔向问齐国的现状。晏子感叹道:“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接着详细地列举了理由:“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履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最后他断言:“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
这里将公室的骄暴与田氏的慈惠进行了鲜明对比,最后竟然直接说:百姓对田氏家族“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足见晏子的感情倾向。
《晏子春秋·问下第十七》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此处晏子更进一步说道:“昔者殷人诛杀不当,僇民无时;文王慈惠殷众,收恤无主,是故天下归之。民无私与,维德之授。”他竟然把景公暗喻为“诛杀不当,僇民无时”的殷纣王,而把田氏比作“慈惠殷众,收恤无主”的周文王,其思想更是明了。
在这里,我们附带讨论一下晏婴对司马穰苴的举荐。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载,跟陈无宇一样,司马穰苴也是田完的苗裔,陈氏家族的成员。齐景公之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对于这件事情,后世学者都把它当作晏子“举贤任能”不避出身的佳话来看待。笔者当然承认此说,然而还认为这与晏子和田氏家族的良好关系有关。司马穰苴虽是“田氏庶孽”,但毕竟为“田完之苗裔”,且与田氏嫡亲关系紧密,甚至可以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否则,在其功成名就被进谗言导致抑郁而死之后,田氏嫡亲(如田乞、田豹、田常等)也不会由此怨恨仇家,并为之报仇雪恨了。更有甚者,齐威王(田和)之时,“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他还“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从而让该书流传千古,大放光彩。由此可见田穰苴与田氏嫡亲关系之密切。
如果晏子真心想要维护公室,削弱甚至消灭田氏势力的话,当时就不应该举荐田穰苴为将军,可以另谋退兵之策。即便因形势所迫非荐不可,亦应在晋、燕兵退之后,设法解除穰苴的兵权,不让田氏继续坐大。然而很遗憾,在史料的记载中,我们非但没有看到晏子的此类行动,反而看到了田穰苴打退敌军回国以后,被景公“尊为大司马,田氏日以益尊于齐。”后来,还是“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这其中根本就看不到晏婴的影子。
由上可见,晏子与田氏家族的交往真的非同一般。
四、晏子思想倾向陈氏的深层缘由
(一)与他“以民为本”的核心治国理念有关
晏子执政之时,甚至在其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田氏家族都尚未形成后来那样强大的实力。清代学者赵青蔾就曾说过:“逮后陈恒弑君,孔子请讨,曰‘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则齐民之未尽归陈也明甚。”[5]已然预见田氏将来会取代姜齐政权的晏子,作为国相完全可以谏言景公凭借国君手中的权势削弱甚至消灭田氏家族,以除后患。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对此,韩非子批评道:“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夫不处势以禁诛擅爱之臣,而必德厚以与天下齐行以争民,是皆不乘君之车,为因马之利,释车而下走者也。……景公不知用势之主也,而师旷、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简公受其祸”(《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笔者以为,作为姜太公和管仲法律思想的继承人,晏子不是不知道使用权势削弱甚至消灭田氏家族,而是另有它因,这与其“以民为本”的核心治国理念关系密切。
“以民为本”是晏子治国方略的总纲。他曾说:“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遗道?苟遗民矣,安有正行焉?”(《问下第二十一》)“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莫下于刻民”(《问下第二十二》)等。“民本思想是晏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与理论基础。既是他制定‘治国方案’的出发点,又是他实施‘治国方案’的归宿点。”[6]现实中田氏家族对百姓的种种恩惠与君主公室对人民的骄汰暴虐之间的鲜明对比让身处政坛数十年的晏子感受颇深,这就不能不让处处倡导“以民为本”的他思想有所倾向。然而,作为姜齐世民,三朝老臣,晏子内心深处对姜氏政权仍然存有极厚的感情,所以才会谏言景公“以礼治国”,来抑制田氏势力的发展。他所说的“礼”指的是:“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土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其实质就是希望社会各阶层都依礼而行,各安其位,不要僭越。同时,晏子也十分清楚,以景公的昏聩无能是不太可能彻底贯彻他的“以礼治国”理念的,更争不过田氏。事实也确如此,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晏子数谏景公,景公弗听。” 这就使晏子的思想感情陷入了矛盾。张福信先生曾言:“晏婴是维护姜齐统治的,但是,他也着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强大势力的威胁。他一方面劝谏齐景公要警惕和抑制这种势力,一方面又顺乎形势的发展。”[7]齐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就是以田氏家族为代表的。郑晓华先生说的更为明确:“身为大臣,晏子看到统治集团的暴虐、腐败、荒淫误国,同时又体察民间疾苦的深重,预感到齐国必然被田氏取而代之的结局。晏子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力图维持旧制度,但是出于对民众利益的关照,对新兴的陈氏集团又表现出极大的谅解和容忍,不得不采取折中、调和的态度。既对人民的苦难表示深深的同情,又对齐国前程忧心忡忡;欲挽救时弊,又表现得无可奈何。”[8]
晏子在内心矛盾的痛苦中不断挣扎,感情逐渐倾向了田氏。齐景公十六年(前532年),陈、鲍氏与栾、高氏相争,“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四族召之,无所往。其徒曰:‘助陈、鲍乎?’曰:‘何善焉?’‘助栾、高乎?’曰:‘庸愈乎?’”(《左传·昭公十年》)由于栾、高氏属公族,故“晏子的态度看似无甚偏颇,实质上则是对陈、鲍讨伐公族的一种默认”[9](p393)。当时诸公子均出奔他国,公孙中强惠如子雅、子尾者也先后于齐景公九年(前539年)和齐景公十四年(前534年)去世,国内的公族力量因此变得非常薄弱。按常理,作为相国的晏子应该帮助公族栾、高氏击败私家陈、鲍氏,这样公族的实力才能稍稍得以保存,然而他却“四族召之,无所往”,实质上就是在帮助陈、鲍氏。其原因正如沈长云、白国红两位先生所说:“陈氏将爱民付诸实践,而公族则日益背弃之,深怀爱民思想的晏子在关键时刻倾向于陈氏实属当然。”[9](P393)
(二)与他开明进步的君臣思想有关
作为春秋著名贤大夫,晏子有着开明进步的君臣观念。在崔杼弑庄公时,他曾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可见,晏子认为国君和大臣都是为社稷而存在的。如果君主不为社稷谋福祉,残暴地欺凌民众,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作为良臣,应该时时处处为社稷着想,为国家尽忠,而不是君主和公室私仆。这就是他“君臣观念”的开明之处。这样的思想使他不会对一个不为国家社稷、不爱黎民百姓的腐朽政权死守愚忠。
此外,据《晏子春秋·问上第十九》载,晏子曾对景公说,忠臣可以“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并进一步解释道:“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奚死焉?谋而见从,终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之,是妄死也;谋而不见从,出亡而送之,是诈伪也。故忠臣也者,能纳善于君,不能与君陷于难。”即君主如果能善于采纳忠臣的意见,就不会遭遇危难,更不必出亡在外,这样于己于臣都有益处;忠臣的职责在于祸患产生之前就进言献策,保国护君,而不在于灾难产生以后为君赴死,陪君出亡。如此开明进步的“君臣观”,加上“以民为本”思想,就有可能让晏子产生谁能防患于未然,谁能善待忠臣,谁能为国家百姓谋福祉,就在政治上偏向谁的想法和做法,所以他在尽力辅佐尚能纳谏的齐景公的同时,还与施惠于民的田氏家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一旦公族与田氏发生冲突,在反复权衡后,他的感情天平则会倾向爱民重民的田氏家族。
(三)与他明哲保身的处世法则有关
晏子执政齐国50余载,历仕3位性格不同的昏君庸主,且多次直言进谏,没有高超的明哲保身技巧是不可想象的。孔子就曾说过:“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晏子可谓能远害矣”(《杂上第三十》)(7)《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亦载此说。。晏子自己也承认:“行莫贱于害身也”(《杂下第二十二》)。他十分清楚,若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必须首先保护好自身及家族的生命安全。故晏子在平日的言行举止及处理国内外的大事上都处处谨慎,适度裁量。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在不同的场合,采取不同但却十分恰当的态度和方式。唐人杨夔曾评价道:“若平仲者,立于衰替之朝,有田、国之强,有栾、高之侈,时非曩时,君非贤君,当崔杼之弑也,能廷然易其盟,陈氏之大也,能晓然商其短,独立于谗陷之伍,自全于纷扰之中,人无间言,时莫与偶。”[10]由此可见,晏子全身处世技巧之高超!
晏子对于田氏家族亦是如此。他看到了姜齐政权的日渐衰落,看到了所侍君主的昏庸无能。对此,他已不抱太大的希望,故每每景公向他请教霸业之道时(8)如“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谏下第十五》);“景公问晏子曰:‘吾欲善治齐国之政,以干霸王之诸侯’”(《问上第六》);“景公问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业晏子对以不能”(《问上第七》);“景公问欲逮桓公之后晏子对以任非其人”(《问下第三》)等。,他往往都会先诉说一番国君和国内的不堪情形,然后劝景公治理好国家再图其它。其实,在晏子看来,景公能够享有国家、善终一生就已经很不错了,至于宏图霸业,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根本就不可能再现。与此同时,晏子也预料到田氏代齐的大趋势,故出于自身及家族未来的安全着想,主动向田氏伸出了橄榄枝。这就是为什么他虽在景公及叔向面前揭露田氏代齐的巨大危险,却没有运用权势及采取其它有力举措削弱甚至消灭田氏的重要原因。
然而,让晏子没有料到的是,他的子孙后代并没有他那样出众的聪明才智,所以才发生了在田常(即田成子)为相之时,“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悲惨事件。与齐国其他大族一样,晏氏也终未能幸免于难,这不能不说是晏子及其家族的历史悲剧。
五、结语
自齐国先后发生崔杼弑庄公、庆封灭崔氏、陈鲍高栾四族逐庆氏、陈鲍败高栾氏等激烈内斗以后,除陈鲍氏外,晏子几乎成了齐国政坛上的惟一支柱。然而,这位与管仲齐名的国相晏婴,却对陈氏的态度如此微妙暧昧。他也知道田氏没有“大德”,施与百姓的只是小恩小惠,所谓“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就是明证。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是陈氏的这些小恩小惠也并非真心为了大众黎民,而主要是为了达到排除异己、削弱公室的目的所采取的权谋手段。对此,司马迁进行了客观记述:“田常成子(即田乞之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相简公。田常心害监止,监止幸于简公,权弗能去。于是田常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这恰恰与晏子“以民为本”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既是晏子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
景公之后,历代齐君更加暗弱无能,晏氏渐衰,高氏被杀,国氏奔莒,鲍氏遭诛,陈氏益强,朝乏栋梁,加之百姓纷纷归附,“得民心者得天下”,于是“田氏代齐”就成了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