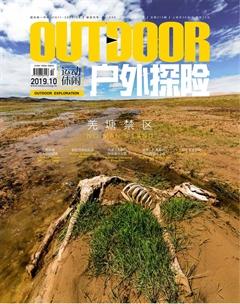失落的古城
王璐

太阳落下后,阳光还在群山上方的天空留恋了一会儿。长绒棉一般的云呆悄然出现在天边,被余晖映照成鲜艳的橘红色。几只白翎雀低飞掠过草原上空,匆忙返回远处的蒿草深处,那里是它们的归巢。不多久,光线渐渐暗淡下来,翠绿的青草、缤纷的野花都失去了颜色,稀疏的星星浮现在夜空中,在云朵的缝隙间偷偷眨着眼睛。草原上的夜晚来临了。
推开一道虚掩的低矮铁门,我和浩爷钻过铁丝护网,向着手机上卫星地图标定的位置前进。没膝的针茅蹭过长裤,柔软的草根在夜风中摇曳。现在是晚上十点半,月亮还没有升起来,白天清晰可见的兴安岭淹没在浓重的黑暗中。手机屏幕上,淡蓝色的定位光点标记着我们正在找寻的目标。强光手电射出的光束,像被浓稠的黑暗不怀好意地把玩在手中,消散在浓重的夜色里。
一阵风掠过草原,针茅叶杆此起彼伏地摇晃,天边的云朵露出一个缺口。一轮初升的下弦月从云缝中挤出来,将清冷的月光洒在寂静的草原上,群山的轮廓骤然出现在天边。
“快看。”浩爷拍了拍我的肩膀,指着沐浴在月光下的草原前方。
一座高大的白塔蓦然出现在黑暗尽头。
银白色的月光下,白塔矗立在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一座七层高的八角形楼阁式砖塔,塔身侧面雕刻着精美的天王浮雕,手持法器的天王力土沉默着,俯视着站在塔下的我们。塔檐下方缀挂着风铃,华丽的斗拱用砖石垒砌,小巧而精致。
“斜拱。”浩爷用手指着其中的一个斗拱,“这是辽代建筑的典型特征。”
他说的没错,眼前的白塔正是始建于辽代的建筑。我们站立在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的夜空下,这里是大兴安岭中段的一块草原河谷,在10世纪后期,白塔所在的地方是辽代的庆州古城。这里曾经有喧嚣的街道和民宅、香火旺盛的佛教寺庙,但如今城内的建筑荡然无存,化为半人多高的荒草。只有孤独的白塔在残墙环抱下,矗立在古城正中央。今天的索博日嘎镇是一座人口区区数干人的小镇,坐落在庆州古城遗址的西侧。很难想象,这里在1000年前是一座繁华的城市。
在传统印象里,历史上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逐水草而栖,大多没有筑城的习惯,但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即便是以游牧为主的匈奴与突厥帝国,通过20世纪的考古挖掘,也在漠北草原上发现了这两个民族修筑的城市。与南方民族围绕农业生产形成的城市相异,草原游牧民族构筑城市的目的,主要是储存通过贸易和战争获得的大量财富和物资,同时吸引周边地区的商人前来贸易。相比重视水利灌溉和农业耕种的汉族王朝,游牧民族建筑的城市更加重视政治和商业功能。
由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则同时兼有游牧和农耕的特性。契丹人的祖先以游牧和渔猎为生,在扩张中逐步征服了渤海国等东北定居政权,吸收了部分中原王朝的官僚体系。早期的辽朝定都在适合农业生产的西拉木伦河上潞可谷,之后又占据了辽东和华北等传统农耕地区,使得这个新生王朝成为了一个游牧一农耕复合帝国。
为了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整合在帝国框架内,辽朝皇室采取了二元管理模式,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通过整合农耕产业,辽朝得以克服单—草原游牧帝国经济的脆弱性,依靠农业生产获得的大量粮食储备,帝国增强了对抗自然灾害和外来入侵的弹性。辽朝因此能够挥师南下,与北宋王朝长期对峙百年之久。南方的汉族政权再也无法重演封狼居胥、勒石记功的壮举。
我们在塔下支起三脚架和相机。天上的流云已经散去,一轮弦月悬挂在夜空,灿烂星河的光芒下,白塔的塔身反射着牛奶色的银光。不知从哪个方向吹来的阵风,晃动着塔檐下的风铃,清脆悠长的铃声在草原上久久回荡。
古堡
时钟已过零点,我们正驾车行驶在暴雨中的霍阿一级公路上。
粗大的雨点敲击着车身,一道暗红色的闪电划破远方的天空,犹如被包裹在棉花中的叉状电流,这一瞬间,草原上的景物变得清晰起来。左侧的高压输电塔像是一具具被剥离血肉的巨大骨骼,矗立在草原之上;公路如同陡峭的天梯搭在山坡上,消失在山脊线的尽头。就在翻过垭口最高点的瞬间,汽车冲出了雨带,眼前的景象清晰得有些不太真实:
在视线的尽头,高大的烟囱、巨型饼干桶一樣的电厂冷却塔、高压输电塔像士兵一样整齐地立在草原,航空避撞灯在这些人工建筑物的顶端闪烁着,在地平线上方构成了一条闪耀的银河。烟囱喷吐的烟雾徐徐升空,在街道灯光的反射下,如同从地面涌出的流云。灯火辉煌的城市四周,又是无尽的黑暗,仿佛从草原上凭空冒出来的海市蜃楼。
这便是霍林郭勒,一座矗立在草原深处的工业城市。
霍林在蒙古语中指休养生息之地,而郭勒则意为河流。5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宁静的草原,霍林河蜿蜓流淌。1973年的一个冬天,当地牧民在附近一座废弃的古城中发现了一些金代陶器碎片。和这些文物在同一文化层中出土的,还有几块未燃尽的煤炭碎块。这引起了驻扎在这里的矿业勘探队员们的注意。从草原上收集来的牲畜粪便是蒙古族冬季生火取暖的主要燃料,而在古代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从外地长距离运输煤炭显然是相当不经济的行为。在古城文化层中发现的煤炭,无疑暗示附近存在着埋藏极浅的大型煤田。
次日清晨8点,下了一整夜的雨停歇了,大朵白云飘浮在天空。我和浩爷驱车向霍林郭勒城西驶去。翻过公路—侧的隔离栏后,我们徒步走向不远处的河谷。河谷尽头,是一座长满青草的巨大土山,山脊平坦而整齐,在平坦的草原上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涉过一条浅沟,前方出现了一道低矮的土墙。一块斑驳的文保碑半埋在草丛中。这,就是被称为霍林郭勒金代一号边堡的古城遗址了。
13世纪初,金朝末年。经历长达二十余年的部落战争,孛儿只斤·铁木真通过武力成功统一蒙古高原的各个部落,被推举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像一颗耀眼的星辰,在草原上迅速升起。不同于南方农耕民族依靠职业官僚构建的王朝体系,统一后的蒙古帝国架构更接近一个由众多蒙古部落组成的松散联盟。部落首领们有义务向大汗缴纳赋税、提供兵源补给,但同时,大汗也需要用赏赐来保持各个部落首领的效忠。因此,统一伊始的蒙古帝国随即迅速展开了对周边国家的征服战争。驰骋在草原上的蒙古铁骑,不只是为了昭示蒙古帝国的强大,同时也是通过战争获得土地和财富,维持这个新生部落联盟的凝聚力。
作为西部、南部边界与蒙古部落接壤的邻国,金朝开始遭遇来自蒙古高原越来越猛烈的进攻。这个由女真人建立的王朝立国已近百年,完成了从游牧渔猎转为定居中原的巨变。物质生活的丰富、长期的和平,使得金朝军队的战斗力快速下降,从马背上下来的民族已然不复昔日之勇。金朝军队无力在野战中击退蒙古骑兵的攻击,疆域也在蒙古军队一轮接一轮的进攻中,从大漠退缩到大兴安岭和燕山一线。失去野战优势的女真人在金朝的最后30年中,沿着大兴安岭修筑了一系列屯兵堡垒,希望借助山势和坚固的城池抵御蒙古人的不断入侵,我们面前的这座一号边堡,便是其中之一。

眼前的这座边堡是一座正方形的普通堡垒,周长800余米,没有瓮城。曾经高达5米的夯土城墙在夏季雨水的不断冲刷下,缓慢地化为草原上的一抔黄土。越过已经不足一米的残墙,半人多高的茅草在风中摇曳。8个世纪的血腥厮杀已成往事,曾经枕戈待旦的军事要塞里,五颜六色的野花正在昔日的城墙上尽情绽放。
无人机缓缓升向高空,我们这才发现,河谷尽头的那座高大土丘背后,竟是一座巨型露天煤矿——这是露天矿开采时被剥离的表层土壤,被堆积在矿坑周围形成的废渣山。
8个世纪前的某个冬日下午,在这座边堡墙头眺望的士兵们终于觉察到,曾经按时送来补给的车队永远不会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他们不知道,千里之外的都城燕京已被蒙古军队攻陷,皇帝带着大臣们仓皇逃向开封,没人再会想起这些依然在帝国北疆驻守的边军。恐慌在边堡内肆无忌惮地蔓延,士兵们纷纷逃离边堡,各奔东西。慌乱之余,一个用来取暖的火盆被踢翻在雪地,几块尚未燃尽的煤块闪烁着暗红色的光芒。
也正是在1973年的一个冬日,一位牧民为躲避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躲入了这座金代古堡的废墟。一桩不经意间的考古发现,几块800年前戍边士兵用来取暖的碎煤,竟然促成了这座蒙东地区最大露天煤矿的发现。这是历史阴差阳错的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天意呢?
当年发现这座煤矿的人们没有忘记它的功劳,矿坑开采区避开了古城的遗址。在无人机镜头的俯瞰视角下,古城就像是一块小小的豆腐,被三面包围在露天煤矿的渣山中,显得那么渺小。重型机械啃噬着地层深处的黑色石块,输送带将数千万年前形成的化石碎成粉末,送入热电站的燃煤锅炉中,汽轮机飞速转动,将电流通过高大的特高压输电塔传送到遥远的南方。过去的金戈铁马、田园牧歌成为昨日挽歌,如今的霍林河,已经成为一座草原上冉冉升起的重工业城市。
一阵风掠过古城,有一瞬间,我仿佛听到古城里传来一声低沉的叹息。

围栏与长城
有人在公路边冲我们招手。浩爷犹豫了一下,一脚刹车,在那人身旁停了下来。
“哎,摩托车坏了。”那人说,“能捎我一段路吗?”
这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头发上蒙上了层黄土,脸庞被草原强烈的阳光晒得黝黑。他穿着一身洗褪了色的迷彩服,斜靠在一辆路边停着的红色摩托车上。
“上车吧。后排有位子。地板上有些空矿泉水瓶,你得收拾一下。”浩爷点点头,指了指身后。
“谢谢你们。”那人搓了搓手,拉开车门,坐进车内。
“摩托车扔在这里不要紧吗?”
“没关系。这里一整天都遇不到几个人。”那人说。
正午的阳光炙烤着草原,公路上热浪蒸腾。前些天公路两边的茂盛草原已不见踪影,稀疏的风滚草插花一般点缀在裸露的地皮之间。偶尔在地势低洼的地方,被风卷来的黄沙堆积在这里,形成了不大不小的沙丘。
我們正行驶在锡林郭勒盟北部的草原上,从太平洋吹来的湿润水汽一路翻山越岭,经松嫩平原、大兴安岭到达这里时,已是强弩之末。这里的年降水量不足两百毫米,是温带草原向荒漠草原的过渡地带。
“你们是过来做扶贫吗?”坐在后排的男人忽然开口。
“不是。是去前面5公里的嘎查,找金代的长城。”我回答道。嘎查是蒙古语村庄的意思。
“我家就住在那里。”男人说。
“这么巧。师傅,能带我们去你家附近的长城看看吗?”
“行。你们帮了我大忙了,我还得感谢你们。”
我们聊了起来。后排的师傅是当地的蒙古族牧民,汉语讲得很流利。师傅说现在蒙古族从小学开始就上汉语课,嘎查大部分人的汉语沟通都没有问题。我听出师傅的普通话带了点东北口音,一问才知道,他前些年去通辽市打过一段时间的工。
“你说的长城离我家牧场不远,老人家都管这个叫界墙。但没啥好看,这几天风越来越大,城墙都快被沙子埋了。”师傅摇下车窗玻璃,盯着外面黄色的草原。“今年春天的雨水少,草都没有返青。”
在大多数人固有的印象里,长城几乎是从山海关到嘉峪关明长城的代名词。然而早在明长城开始修建的400年前,由女真人修建的金长城便已屹立在内蒙古草原深处。金代长城在中国境内的走向基本沿着大兴安岭和燕山,从黑龙江省的嫩江地区一路延伸到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东胜。如果说明长城是将农耕王朝与北方游牧帝国分割开来的界限,那么金长城便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用来抵御另一个游牧帝国进攻的防线。
进入20世纪后,人们开始重视明长城的修缮保护及旅游开发,赋予其更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但草原深处,历史更久远的金代长城却被逐渐掩埋在荒草中,在风沙吹袭中缓缓风化,雨水冲刷里慢慢倾颓。这里是被主流历史遗忘的角落。
“你们看,前面不远就是长城了。“师傅指着前方的围栏说。
和印象里建立在逶迤群山之巅的长城大相径庭,我们眼前的金代长城,不过是草原上一道略高出地面一米左右的土坎,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消失在遠方草原的尽头。
我们站在城下,能看到每隔70米设有一座凸出城墙的马面,用来形成交叉火力。土墙的下方有一道浅沟,当年建造长城的民夫和士兵们用挖取的黄土夯筑城墙,而用来取土的地方则利用起来,形成城墙下方阻滞骑兵的壕沟。如今,城墙已风化殆尽,几头山羊站在城墙顶上,好奇地盯着我们。从天空俯瞰,浅浅的壕沟、低矮的土墙和被风化成圆形的马面,像是一条串着珍珠的长项链,沉默地通向天边。
长城左右两旁,是延绵不绝的铁丝围栏,由于经常走车,围栏和围栏之间的公路已经被车轮碾成了寸草不生的裸地,汽车驶过后,车轮后方卷起滚滚黄沙,像是一条游动的沙蛇。从天空向下望去,辽阔的草场被挂着铁丝护网的围栏分割成了棋盘状的小块方格,每块方格都是一户牧民承包的草场,每家每户的牲畜只能在自家草场上放牧。原本一望无际的草原,如今像南方的农田一样被切割成了碎片。围栏内的不远处,一群山羊低头啃食草原上的植被,放眼望去,草原的绿色实在太稀少了。
“以前的草场不是这样的。”师傅点了一根香烟,脸色阴沉地说,“以前我们都是整个嘎查一起放牧,水源和水井都是共用,每隔几天都会赶着畜群转场,从来不让牲畜在同一片草地上吃太久。
“1996年以后搞了草畜双承包,草场都划成几千亩的小块分给每户人家头上。每家每户都扯起了围栏和铁丝网,牲口成天都在一小块草地上转来转去吃草,时间一长,草皮全都给踏坏了。”
“我小时候,夏天的草原上能有几十种草,五颜六色的野花遍地都是。现在你们看,草原上都是猪毛菜,要不就是狼针。羊吃了这些草,嘴都给扎坏了。”
猪毛菜是荒漠草原生长的一年生耐旱植物。这种植被的大面积出现,通常是草原严重退化的前兆。放眼望去,一丛丛猪毛菜像插花一样出现在草原上,几头山羊在沙土中徒劳地寻找已经为数不多的草根。
“从前草场遇到旱灾,还能赶着牲口去其他草场跑浩特(转场)。现在草场承包给个人,大家就都用围栏把自己家的草场围起来,生怕别人家的羊群进自家的草场吃草,人心全变得自私了。”
师傅叹了口气,不再说话。
我们三个人站在如蛛网一般密布围栏的牧场上,远处的旋风卷起黄土,在长城的残墙上打着转。

金莲川上的落日
在日落前的最后一小时,我们终于赶到了正蓝旗。
汽车在308省道上疾驶,车窗外掠过低头吃草的羊群和牛群,放牧人骑着摩托车,挥动长鞭驱赶着畜群,夕阳将他的身影镀上了一层金色。如今已经很少能看到骑马放羊的牧人,相比需要精心照料的马匹,不需要吃草的摩托车显然更受当地人的喜爱,炫目的工业产品正在飞快改变草原民族的生活习惯。
草原终于恢复了久违的绿意。公路两侧不时出现奇怪的圆形耕地,像有人用圆规在草原上整齐画出的一个个圆形。这是近年引进到草原上的节水农业技术,通过水泵将地下水抽出来,再通过喷灌机进行灌溉。种植的农作物大多是玉米,作为圈养牲畜冬季过冬的饲料。现代技术使得利用地下水资源进行稳定的农业生产成为可能,千百年来一直属于游牧民族的草原,第一次出现了成片的耕地。曾经在马背上的牧民开起了拖拉机,成为了草原上的农民,农民和牧民的界限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



窗外的牧场渐渐远去,眼前出现了一大片河滩湿地,黛色群山的身影在更远的北方若隐若现。我们向往已久的金莲川终于到了。
晚风拂过草原,空气中有了一丝凉意。正值大暑时节,这里依然体会不到南方的暑热,我们顿时明白元朝帝王将这里作为避暑夏都的原因。驾驶游览车的蒙古族司机吴巴图师傅四十来岁,也许是想找回年轻时纵马在草原上驰骋的感觉,他将车开得飞快,开满金莲花的河滩与闪电河的蛇曲从我们眼前疾速掠过。
“我年轻时就在这里放牧。放牛,放马,也放羊,但羊不能放太多。羊蹄子太尖,会把草踩坏,对草场不好。”吴巴图师傅说。对面车道,一辆相同颜色的观光车朝我们驶来,两位司机先后按了一下喇叭打招呼。“那个司机也是我们嘎查的。景区被评上世界文化遗产后,这里就不让放牧了,我家里的马都卖给了别人,我们改行当上了司机。”
2012年后,金莲川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为保护遗址,周围1700平方公里的草场被列入禁牧区和缓冲区。原先草场设在这里的牧民们被重新搬迁安置,离开了他们熟悉的草原。在技术和商业利益的推动下,今天的内蒙古草原不再是往日单一的牧业经济,工业、农业和商业正在急速向草原进军。我想起了霍林郭勒金代边堡旁那座巨大的露天煤矿,正蓝旗草原上茂盛的喷灌玉米饲料地,以及眼前这位由牧民变成了员工的司机师傅。
金莲川曾是元代上都所在地。14世纪中叶,蒙哥汗攻打南宋时在钓鱼城去世,经历短暂而激烈的内战后,蒙古帝国分裂為四大汗国。元世祖忽必烈在东亚和蒙古高原建立了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习惯在草原生活的元朝皇室不能忍受华北地区盛夏时节的暑热,遂于现在的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营建了规模庞大的上都,形成了极具元朝特色的两都巡幸制。每年四月暑热初至,元朝皇室和大队护送人马便从大都出发,前往百里之外内蒙古草原的上都避暑。在凉爽的金莲川河滩度过夏季后,又在九月前后返回大都(北京)过冬。夏去秋来,元朝皇帝们就像候乌—般,往返于草原和中原之间。
“宫殿的所有殿堂和房间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宫殿的一面朝城内,一面朝城墙,四面都有围墙环绕,包围了一块整整有16英里的广场。”
1275年的一个夏日,21岁的马可-波罗在大都觐见大汗忽必烈,在他的游记中写下了这段文字。上都城墙周围看不见中原地区常见的大片耕地和村庄,它是一座修建在草原河滩之畔的巨大城市,在它的鼎盛时期,除了前来避暑消夏的元朝皇室贵族外,还驻扎有大量随行的官员和护卫军队。上都不仅是元帝国夏季的政治中心,更是多条驿道汇集的交通和商业枢纽。
13世纪的蒙古征服消灭了曾经林立在陆上丝绸之路的诸多国家,统一后的蒙古帝国使得欧亚大陆之间的洲际长途贸易再次通畅。欧洲的商人在付清折合商品总价10%左右的商业税后,便可在沿途有蒙古军队巡逻的驿站之间畅通无阻。来自东西方的商品和技术沿着草原商路往返传播,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来临的前夜,草原上的蒙古帝国就已悄悄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
从城南进入上都遗址,宽大的城墙缺口暗示着这里曾是元朝皇帝进入上都的明德门。尽管历经了7个世纪的雨水侵蚀,残存的城墙依然有8米之高,向我们展示着这座城市被毁之前的宏伟规制。我们在宫城入口的御天门遗址前升起无人机,随着高度的爬升,一座宏大的草原城市缓缓出现在监视屏中:上都的外城周长超过8000米,接近一个正四方形。城北群山环绕,蜿蜒曲折的闪电河在城市的南方缓缓流淌,在夕阳的映照下闪闪发光,灿烂的晚霞将西边的天空涂抹成一片通红。上都所在的金莲川以河滩遍地盛开的金莲花得名。在闪电河畔,夕阳的余晖和盛开的金莲花将河滩的湿地染成一片金黄色,整个河谷仿佛在落日中燃烧。
“小心,别跌下栈道了。”吴巴图师傅的身影出现在我身后。他指了指眼前金色的花海,“附近有沼泽。”
“谢谢师傅。”我说。
“我年轻时在这附近骑过马,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他的眼睛望着远方的草原出神。景区公路上,一辆电瓶观光车正停在路边。
“唉。我家已经没有马了。”他说。
暮色将至,我站在宫城中心的大安阁遗址上向南眺望,巨大的城市遗址里荒草萋萋,野花在宫殿的台基脚下热烈开放。孤独的城墙屹立在闪电河畔,向潺潺流淌的河水诉说7个世纪前万邦来朝的往事。视线顺着上都的中轴线无限延伸,越过无尽的草原,翻过绵延的燕山山脉,我仿佛看到在地平线尽头,另一座灯火辉煌的伟大都市,在华北平原的北方召唤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