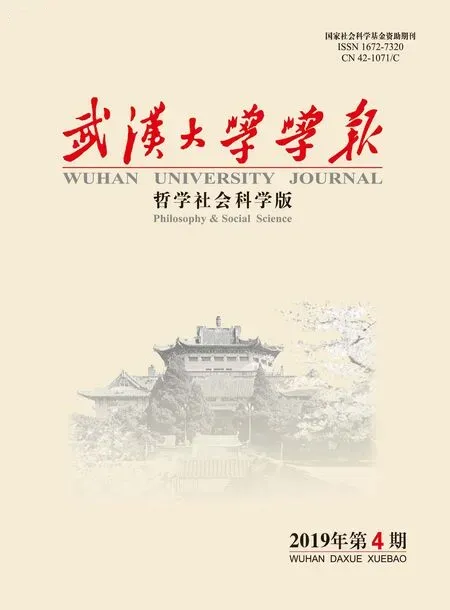元代散曲的“野逸”之趣
查洪德
十多年前,散曲研究的前辈学者吕薇芬先生发表题为《拓展散曲的研究领域》的文章,强调要加强元代散曲的文体研究,特别强调散曲文体风格的研究[1]。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散曲学科独立,到21世纪初,几十年中,研究者对散曲的文体风格多有论述,吕薇芬再作强调,应该说,在她看来,元代散曲的文体风格,仍有继续研究之必要。吕先生论文发表至今又过了十多年,这一研究未见推进,可见这一课题需要研究又难以推进。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重提这一话题,作尝试性的探索。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概括元代散曲的文体特点呢?
前辈与时贤对元代散曲特点的概括,有“俗”“谐”“俏”“辣”,以及古代学者概括的“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豪辣灏烂”等等。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多种趣味远不同的概括?这些概括各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元代散曲的特色?对现存元散曲作品的覆盖面各有多大?这些概括能不能体现元散曲的精神?我们能否找到合适的概括?
我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是:存在趣味远不相同的多种概括,说明对元散曲文体特点的认识还需要更进一步。元散曲有谐、有俗、有俏、有辣,但又不仅仅是谐、是俗、是俏、是辣。我们需要找出能够涵盖谐、俗、俏、辣,而又高出谐、俗、俏、辣的概括。这个概括应该是——野逸。用“野逸”这一概括,对元代散曲作品有更大的覆盖面,体现了元代散曲的基本精神。
在展开论述以前,有必要对已有研究作一检视。
古人“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等概括,不能体现元散曲的文体风格。
散曲一出世,就表现出与诗、词等迥然不同的鲜明风格。最早关注散曲特点的,是元人周德清、钟嗣成、贯云石、杨维桢等。但周德清、杨维桢论曲,目的十分明确,即要将这种野而不雅、逸而非正的文体加以规范,引向雅驯的、符合规范的“正”途。在《周月湖今乐府序》中,杨维桢说得很清楚:
夫词曲本古诗之流,既以乐府名编,则宜有风雅馀韵在焉。苟专逐时变,竞俗趋,不自知其流于街谈市彦之陋,而不见夫锦脏绣腑之为懿也,则亦何取于今之乐府可被于弦竹者哉![2]
崇雅抑俗,以“风雅馀韵”为标的,导向明确。可以说,杨维桢是以诗眼观曲论曲。周德清是一位尚雅论者,他撰《中原音韵》,为元曲创作建立规范。其自序说:“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3](P229)这是他作《中原音韵》的缘起。他要“正”的“言语”,绝不仅仅限于音韵,他要扭转的,是曲的创作与编选中“务取媚于市井之徒,不求知于高明之士”的不“正”现象[3](P230),使之归于“正”途。所以他在《中原音韵·作词十法》中提出:“造语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则迂,不文则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耸观,又耸听,格调高,音律好,衬字无,平仄稳。”[3](P289)其中“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至今被用作元散曲风格的概括。需要明白的是,这并不是周德清对元曲特点的概括,而是他给曲作提出的标准。不是元曲客观存在的面貌,而是他主观设置的理想。如“格调高”云云,便非元散曲所具有,“衬字无”,更直接与散曲特点相悖。周德清的这些表述,没有客观反映元代散曲的文体特点。但杨维桢、周德清的这些批评说明,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元散曲的特点,也即其野逸精神。他们要努力的,就是要消除野逸,回归雅正。在此后的明清两代,这种思维一直支配着曲论家。
第一位准确把握散曲美学特征的学者,应该是曲学家任讷先生。他认为:“曲以说得急切透辟极情尽致为尚,不但不宽弛,不含蓄,且多冲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则全然暴露于词面……此其态度为迫切,为坦率,可谓与诗余相反也。”接下来,他在词与曲对比中揭示散曲特点,这应成为经典之论:
词静而曲动,词敛而曲放,词纵而曲横,词深而曲广,词内旋而曲外旋,词阴柔而曲阳刚。词以婉约为主,别派则为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则别体为婉约。词尚意内言外,曲竟为言外而意亦外。[4](卷 2)
他非常重视散曲文体特点的把握。他以为,在散曲豪放、清丽两派之中,体现散曲特色的是豪放:“盖元曲之文章,本以用意、遣词,两俱豪放不羁者为主,其余种种,虽概目之为别调可也。”[4](卷2)可以这么说,任讷先生没有使用“野逸”一语,但他感受到了元散曲之野逸特色[5](P169-172)。
此后不少学者对元散曲的特点进行了很有见地的描述和揭示,大致说,人们对元散曲那种随心所欲、任情挥洒、不受拘束、不可羁勒,以及或朴野疏旷、或诙谐滑稽,甚至荒诞不经、俗白直露等特点已经充分认识。可以说,学者们的研究,已经触及了元代散曲“野逸”的特点,特别是罗斯宁《元曲的“蒜酪味”和“蛤蜊味”》一文所说:“它雄健、质朴而带有‘野性',与传统文学迥异,故而别有风味。”[6](P396)“野性”当然是“野”,与传统迥异而“别有风味”也就是“逸”,就差用“野逸”两个字来概括了。
尽管古今曲论家没有使用“野逸”一词,但元散曲的野逸精神早已为曲论家所认识并从不同方面、用不同概念进行了揭示。如果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把握“野逸”之意,“野”而非雅,“逸”即非正,则“野逸”就完全包含了“俗”“谐”“俏”“辣”等概念。
一、“野逸”概念之追溯
“野逸”是中国绘画史研究者评元人绘画使用的概念。中国绘画史上有所谓“野逸派”。“野逸派”形成在清代,但美术史研究者上追其源,根据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评五代画家“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7](P31),认为五代就有“富贵派”与“野逸派”。绘画的“逸气”说出现在元代,因此,美术史家用“野逸”概括元代文人画的特点,潘天寿先生如此评价元代画家:
故从事绘画者,非寓康乐林泉之意,即带渊明怀晋之思。故所作,以写愁怀者,多郁苍,以写忿恨者,多狂怪,以鸣高蹈者,多野逸……既不以技工法式为尊重,亦不以富丽精工为崇尚,任意点抹,自成蹊径。……故以技工论,元人不能以草草之笔,得唐、宋繁密工整之长。以笔墨论,元人能以简逸之韵,胜唐、宋精工富丽之作。[8](P156-157)
其实,“郁苍”与“狂怪”体现的精神,都可含括于“野逸”之中。“草草之笔”则是“野逸”技法特点。在元代,富有“野逸”精神的绝不仅仅是画家,它是元代文人散诞生活状态的写照,表现了文人的精神风貌,也体现在元代文学艺术的诸多方面。元代文人多有以“野逸”命名其亭阁者,如野逸亭、野逸轩、野逸堂等。中国古人原本是戒“逸”的,《尚书》就有《无逸》篇,而元人却以“逸”为尚,可见其时代精神的独特性。元人甘复为陈氏野逸轩作记说,文人“谢事而归于野也,枕石栖谷,玩花草,弄云月,无求于己,无责于人,而与世外之士相往还,澹然乎物之表,盖非有意于逸而逸将有以自至者,其势然也”[9](P536)。这是元代文人向往的生活状态。诗人戴表元《赠江西复初陈秀才》诗云:“盱江江水清可渔,山栖野逸多长裾。西归洗尘酌江水,客来谈诗碧云里。”[10](P511)他们喜欢、享受这样的生活。元代的诗学主张是多元的,其中也有赏野逸者。如元好问论诗,欣赏辛愿(字敬之)其人其诗:“性野逸,不修威仪。贵人延客,敬之麻衣草履,足胫赤露,坦然于其间,剧谈豪饮,旁若无人。”[11](卷10)人如此,诗亦如之。如辛愿为人那样犷放之野,在元诗中也多有,如李泂辞官归去,有诗云:“野马脱羁鞅,倏疑天地宽。临风一长鸣,风吹散入青冥间。”[12](P568)表现出李白式的狂野放逸。元诗的野逸精神在元末诗歌中体现得更明显,文学史家章培恒论元后期诗歌新变说:
首先在于初步冲破了“儒雅”的框子,承认并追求感官的享乐、以此为实际内容的炽烈的生活,同情并讴歌由此生发的七情六欲,作品的基调往往是乐而淫、哀而伤,强烈的感情多伴以炽烈、艳丽的色彩,而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来增强感情的激荡。[13](序言P6)
这就是元诗的“野逸”。与诗相比,更充分体现“野逸”精神、最富“野逸”之趣的,是元代散曲。
为了能比较全面地把握元散曲的“野逸”之趣,还有必要对“野逸”“野”“逸”概念作一些考察。
“野”本义是郊外,与“野”组成的词语,有旷野、草野、荒野、村野、朴野、拙野、鄙野、狂野、犷野、蛮野等,身份低微,鄙略质朴者为“野人”,不居官、不当政者为“在野”。这些都与美学意义上的“野”有关联。在人们的观念中,质朴、天然而不加修饰为“野”,不合礼仪、不拘礼法为“野”,放浪不羁、不受约束为“野”。《论语·雍也》载孔子之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4](P61)这本是论人,后人也借以论文。“野”用于文学批评,应该在六朝时期,钟嵘《诗品》评左思之诗:“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15](P9)“野”是质朴而乏文采之义。在六朝及其以前,以“野”论人论文,都多负面义。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疏野》一品:“惟性所宅,真取弗羁;控物自富,与率为期。筑室松下,脱帽看诗;但知旦暮,不辨何时。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16](P28)对真率自然、谢绝雕饰、倘然适意的作品予以肯定。“野”于是具有了正面的意义。到宋代,人们推崇无味之味,崇尚素淡质朴之美,“野”被高度肯定,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六录陈知柔《休斋诗话》“诗要有野意”一条:
人之为诗,要有野意。盖诗非文不腴,非质不枯,能始腴而终枯,无中边之殊,意味自长。风人以来,得野意者,惟渊明耳。如太白之豪放,乐天之浅陋,至于郊寒岛瘦,去之益远。
这是宋人理解的诗之“野”。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下了一个判断:“野者,诗之美也。”[17](P250)不过,诗之野与曲之野,风味还是不同。
“逸”本为奔逸、走失之义,与本义较近的,有狂逸、放逸等词语。与“逸”组合而成的概念还有很多,如俊逸、冶逸、奇逸、宏逸、富逸、清逸、秀逸、疏逸、超逸、闲逸等①卢忠仁《审美之境:美子二十八说》对“逸”有专门讨论,他列出“逸”表现形态有高逸、野逸、放逸、超逸、幽逸、闲逸、飘逸、雄逸、俊逸、遒逸、秀逸、旷逸、神逸、散逸、荡逸、纵逸、奇逸、冷逸、狂逸、傲逸、古逸、癫逸。[18](P64-65),以“逸”论人则有逸人、逸士、逸才、逸致等。“逸气”是中国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曹丕《与吴质书》称赏刘桢(字公干)“有逸气”。何谓“逸气”呢?钟嵘《诗品》对刘桢的评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19](P133)指出了“逸气”多方面的表现,其中“高风跨俗”是核心。唐皎然《诗式》卷一《明势》对“逸格”也即超凡之格有具体描述[20](P11)。又其《辨体有一十九字》言:“体格闲放曰逸。”[20](P69)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又有《飘逸》一品:“落落欲往,矫矫不群。”“御风蓬叶,泛彼无垠。如不可执,如将有闻。”[16](P39)这些都是对诗学“逸”风格的揭示,也可以用以解释曲之“逸”。古人论画,有所谓逸、神、妙、能四品,逸品,即崇尚意境,无法而法。以往谈论元代文人之“逸气”或“野逸”,关注的是元代画家,画家中又集中在倪瓒。明人唐志契对绘画的“逸品”作了较详细的阐发,并表达了对能“写胸中逸气”的倪瓒(字元镇)的崇高敬意,其《绘事微言》卷下《逸品》说:
山水之妙,苍古奇峭、圆浑韵动则易知。唯“逸”之一字最难分解。盖逸有清逸,有雅逸,有俊逸,有隐逸,有沉逸。逸纵不同,从未有逸而浊、逸而俗、逸而模棱卑鄙者。以此想之,则逸之变态尽矣。逸虽近于奇,而实非有意为奇;虽不离乎韵,而更有迈于韵。其笔墨之正行忽止,其丘壑之如常少异,令观者泠然别有意会,悠然自动欣赏。此固从来作者都想慕之而不可得入手,信难言哉!吾于元镇先生不能不叹服云。[21](P27)
倪瓒(元镇先生)的“逸气”说确实是一个很难分解的概念。其说出自倪瓒《跋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22](P302)美术史家据此以为所谓“逸气”即不求形似、注重达意。这显然太过简单化了。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据此看,“逸气”乃是一种横放奔突、难以羁勒之气。后人也多如此理解,如明人评李白:“天才踔发,逸气横出。龙骧鹏抟,不可控执。”[23](卷41)“太白雄姿逸气,纵横无方,所谓天马行空,一息千里。”[24](卷17)“逸气”之义还不仅如此。唐代的张怀瓘《书断序》描述书法家灵感来时书写自如神妙不可知的状态说:“及乎意与灵通,笔与冥运。神将化合,变出无方。虽龙伯挈鳌之勇,不能量其力;雄图应籙之帝,不能抑其高。幽思入于毫间,逸气弥于宇内。鬼出神入,追虚补微,则非言象筌蹄所能存亡也。”[25](P14)“逸气”表现为巅峰精神状态下个体精神的极度张扬和在创作中的发挥。
倪瓒的“逸气”,既是贯注于画中的精神气韵,又蕴含有心灵的寄托。如夏文彦在《图绘宝鉴》所言:“逸品皆高人胜士寄兴寓意者,当求之笔墨之外,方为得法。”[26](P2)倪瓒品他人之画,就能求之笔墨之外的寄兴寓意,他有《题郑所南兰》:“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22](P260)尽管这里他没有使用“逸气”一语,但他借以表达的,是其“胸中逸气”。
在元代,写胸中逸气的不仅是倪瓒,不仅是画家,散曲家更多地写“胸中逸气”,这“逸气”的含义,当然也是多方面的,只是以往我们没有从这一角度去解读。
“野逸”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很早,在陈寿《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十九、释支遁《支道林集》卷下《上皇帝书》都曾使用,这些与我们讨论的内容关系不是很密切,略而不述。与我们研究相关而较早使用“野逸”概念的,是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其《能品上六人·陈谭》评陈谭山水画“野逸不群,高情迈俗”。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的,是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论:“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在“野逸”一词出现之前,早就有表现“野逸”意趣的文字,如《论语·先进》春风舞雩表现的就是“野逸”之趣,此后如《庄子》,如屈原之作,都呈现野逸风貌,只是所体现的是不同意义的“野逸”。
“野逸”也用于书法评论。“野逸”在书法理论中指一种狂放恣肆的艺术风格,它是书家潇洒不凡人格特征的体现,它可以产生无穷的韵味。它的范畴大概可以分为三个理论层次:一是指书家潇洒超拔的艺术人格;二是指审美体验中自由的心灵境界;三是指狂放苍莽的格调韵致。野逸之品格由于能表现大自然奔腾不息的内在生命及人格风范和艺术境界,而被历代论艺者所推重[27](P394-395)。
“野逸”(及“野”“逸”)含义太过丰富复杂,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些梳理归纳。在语词类工具书中,其基本义项有三个。我们借鉴这些解释,略作阐发。
其一为纯朴闲适。举例如唐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这一义项偏重在“野”:由远离都市之乡野引申而来的质实不文,纯朴无华,以及乡野生活的宽闲适意。元散曲中符合这一义项的作品很多。
其二为放纵不羁。举例如唐陆龟蒙《甫里先生传》:“先生性野逸,无羁检。”这一义项更能完整体现“野逸”之意:“野”与“逸”都有放浪恣肆纵意而为不可羁勒之意。在绘画、书法以及诗歌中的野逸,偏重于这一义项。上文所引很多材料适合这一义项。元散曲中符合这一义项的作品数量很大。
其三为隐逸的人或隐居生活。这一义项更偏重“逸”:隐逸、闲逸、宽逸,就如《诗经·卫风·考槃》“考槃在涧,硕人之宽”那样自在安闲和为所欲为。符合这一义项的作品,在元散曲中几乎占据主流。
我们还可以从“野逸”相对概念来认识“野逸”的含义。
其一,“野逸”与正统对。清代绘画与野逸派相对的是正统派。正统派注重笔墨趣味,致力于摹古中求变化,强调灵活运用古人笔墨技法。野逸派则强调独抒性灵,个性鲜明,风格恣肆横放。两派形成在清代,但两派之源却很久远,其基本旨趣在元代之前早已存在。元散曲表达的基本精神取向是非正统的,这一点对理解元散曲的“野逸”相当重要。
其二,“野逸”与富贵对。这来自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黄家富贵,徐熙野逸。”郭若虚揭示了富贵与野逸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源于两种不同的志趣,并进一步指出不同志趣、不同风格的形成,在于画家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况。元散曲描写的生活环境,表达的人生意趣,多山间、林下、水滨、茅舍和寄身其中的平淡旷逸生活之乐。
其三,“野逸”与精细、法度对。画之逸品,如倪瓒所言,乃“逸笔草草”。与之相对的富贵派则形象准确,描绘精细,生动逼真。主流的元散曲作品是疏放、富有天然之趣,谢绝雕琢的。后期散曲逐渐走向精工,但就元散曲的主流说,整体的特色仍表现为野性的疏放。
另外,“野逸”还与雅正对。元散曲长期不能获得文学史的正宗地位,与其非雅正有关。
在对“野逸”概念作了上述梳理、考察后,我们应该会对元散曲的野逸之趣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可以相信,用“野逸”来概括元散曲的文体特征,是比较合适的。比如散曲的非正统性、非主流性,一直存在于批评家的观念中,如吕薇芬先生所言:“在重视文学教化作用的中国,散曲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学。”[1]
二、元散曲“野逸”之趣的表现形态
“野逸”(野、逸)的含义是复杂的,元散曲表现出的情态、风貌也是多样的。这些情态、风貌和精神,不管是契合了“野逸”哪方面的含义,都可以说它具有“野逸”之趣,我们把这看作“野逸”之趣的不同表现形态。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把元散曲“野逸”之趣的表现形态,分为狂野肆逸、疏野旷逸、朴野恣逸、乡野恬逸、闲野俊逸、野思逸想、俚野荒逸七种。元散曲中狂放的、纵恣的、荒诞的、质野的、俏皮的、尖刻的、俗趣搞笑的、直白浅露的,元散曲对传统观念的叛逆、颠覆常规的、戏说野评历史的、游戏人生消解传统人生价值观的,都可纳入“野逸”这一概念之中。“野逸”涵盖了元散曲绝大多数作品。
1.狂野肆逸。狂肆、狂傲,个体精神极度张扬,近乎为李白式的野逸。在元代这样一个精神控制弱化的时代,人们尽可以表现自己的疏狂,而忽略他人的评价,“尽疏狂不怕人嫌,是我平生喜处。”(刘敏中[正宫·黑漆弩]《村居遣兴》)[29](P218)谨小慎微,左顾右盼,不是元曲家的性格,也不是元散曲的特点。他们在曲中常声称“傲王侯”:
邯郸道,不再游,豪气傲王侯。琴三弄,酒数瓯,醉时休。缄口抽头袖手。(卢挚[商调·梧叶儿])
住一间蔽风霜茅草丘,穿一领卧苔莎粗布裘,捏几首写怀抱歪诗句,吃几杯放心胸村醪酒,这潇洒傲王侯。(王德信 [商调·集贤宾]《退隐》套之 [后庭花])[29](P110,293)
“邯郸道”即红尘中名利之途。没有了名缰利锁,完全可以蔑视权贵,诗酒潇洒“傲王侯”。奇人贯云石写出狂肆野逸之作很正常,他潇洒天地间,又觉天地小,其 [双调·清江引]云:“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29](P368)也许更有资格疯狂的是无名无位因而也就完全无拘无束的村夫,无名氏的《村夫饮》写出了一个彻底疯狂的场面:
宾也醉主也醉仆也醉,唱一会舞一会笑一会。管甚么三十岁五十岁八十岁,你也跪他也跪恁也跪。无甚繁弦急管催,吃到红轮日西坠。打的那盘也碎碟也碎碗也碎。(无名氏[正宫·塞鸿秋]《村夫饮》])[29](P1663)
曲写的是村夫,但表现的是曲家狂肆的精神。文人们也学这样的疯狂:“大叫高讴,睁着眼张着口尽胡诌,这快活谁能够!”(王德信 [商调·集贤宾]《退隐》套之 [青哥儿])[29](P293)
这类作品的特色,是俗?是谐?是俏?是辣?恐怕都不准确。合适的概括,是野逸。
狂肆类的野逸之作,在元代散曲中给人强烈的感受。文学史上表现狂肆的作品也有一些,但像这样肆无忌惮之狂,元曲之外没有。
2.疏野旷逸。这是疏旷类的野逸,表现的是曲家无挂碍的疏旷与豁达。他们忘情世事,使自己沉醉于远离官场、远离是非、没有凶险的自我世界。与前一类不同,这一类是旷达,是“狂”与“旷”的区别。前一类的“野”,表现为野性的狂。这一类的“野”,多表现宽闲之野的疏旷,人是怡然自得的。
同样是远离官场,远离是非,上一类表现出无拘无束为所欲为的狂,这一类表现为身心轻松宽适自在的旷,世界是宽松的,也即是所谓疏野。这其实是厌弃了官场争斗后,享受无心机事,无是非、无争斗,也没有凶险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身心可以完全放松。张养浩 [中吕·朝天曲]叙述了这一心理路程:“挂冠,弃官,偷走下连运栈。湖山佳处屋两间,掩映垂扬岸。满地白云,东风吹散,却遮了一半山。严子陵钓滩,韩元帅将坛,那一个无忧患?”[30](P98)这些作品,很多都是表现彻悟人生后的旷达。没有进入过官场的白朴,则完全享受身心宽适的野意,其[双调·沉醉东风]《渔夫》云:“黄芦岸白蘋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点秋江白鹭沙鸥。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31](P180)元曲家看惯了“朝承恩暮赐死”的无常,他们劝自己不要参与其中,做一个旁观者:“身不出敝庐,脚不登仕途,名不上功劳簿。窗前流水枕边书,深参透其中趣。大泽诛蛇,中原逐鹿,任江山谁做主。孟浩然跨驴,严子陵钓鱼,快活煞闲人物。”(汪元亨[中吕·朝天子]《归隐》)[29](P1381)窗前流水与枕边书,多么好的组合!在宽闲中享受自然之适而又不失文人雅趣。
在这类作品中,不能不说的是马致远的名篇[越调·夜行船]《秋思》套数[32](P83)。这是人人熟知的名作,不再引述。同样的意思,他在[南吕·四块玉]《叹世》作了简单的表达:“两鬓皤,中年过,图甚区区苦张罗?人间宠辱都参破。种春风二顷田,远红尘千丈波。倒大来闲快活。”[32](P13)忘却世事,遁迹江湖,躲避灾祸,享受自然,这是元曲家说得极多的一个话题。
这类作品体现的精神,是俗?是谐?是俏?是辣?都不好说。应该说,是野逸。这一类作品中,有些旷达是装出来的,是不能忘情世事而故作不关心,有时会露出愤激。但愤激之作,就不属这一类了。
3.朴野恣逸。朴野是元散曲重要的特色,特别是前期作品,大多朴野本色。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习惯的朴素天然来概括这一特色,但“朴素”不能表现这些曲中活泼恣肆的一面,朴素而活泼,是为朴野。“恣逸”或说恣睢,则表现这类作品随心任情的特点。这便是“朴野恣逸”。如关汉卿[南吕·四块玉]《闲适》:
旧酒投,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哈哈,共山僧野叟闲吟和。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闲快活。(关汉卿 [南吕·四块玉]《闲适》)[33](P1658)
这样的语言充分体现“朴野恣逸”的特点。
曲家有时还故意将自己塑造成愚憨丑陋的形象,像鲜于枢 [仙吕·八声甘州]:“从人笑我愚和戆,潇湘影里且妆呆,不谈刘项与孙庞。”“闷携村酒饮空缸,是非一任讲。恣情拍手棹渔歌,高低不论腔。”表现愚憨的同时,也写出了恣逸。他所在的环境,与愚憨的人也是相衬的:“生涯闲散,占断水国渔邦”“竹篱旁,吠犬汪汪”[29](P86-87)。在这样的环境中,不需要聪明,一切思虑与心计都是多余的。曲家自称“除了衔怀,百拙无能”(曹德 [双调·折桂令]《自述》)[29](P1079)。
与前两类相比,朴野恣逸类散曲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对无知无识混沌状态的向往和语言的朴野。
这类作品可以说俗,但俗不能揭示其本质特点,也不能显示其在俗文学中的独特性。其本质特点,是恣睢的野逸。
4.乡野恬逸。这一类描写乡野环境的恬静安逸,以客观描写为主,几乎感受不到曲家情绪的宣泄。有的几乎是纯自然景物的描写,很少有人的活动,即使有人,也是画面中的背景而不是对象,人是自然景物的一部分而不是活动于自然环境中的主体,如杨果[仙吕·赏花时]套数之[赚尾]:
晚风林,萧萧响,一弄儿凄凉旅况。见壁指一似桑榆侵着道旁,草桥崩柱摧梁。唱道向红蓼滩头,见个黑足吕的渔翁鬓似霜。靠着那驼腰拗桩,瘿累垂脖项,一钩香饵钓斜阳。[29](P8)
这一切都是从曲家眼中写来,曲家把自己隐藏起来,读者几乎感受不到曲家的存在。这类散曲即使是写动景,给人的感觉也是静的,描述的总是一幅乡野乐居图。如鲜于必仁《潇湘八景》中的《渔村落照》:“柴门红树村,钓艇青山渡。惊起沙鸥飞无数,倒晴光金缕扶疏。鱼穿短蒲,酒盈小壶,饮尽重沽。”人、物、景浑然为一,人是无思无虑的,是景的一部分。
也有写人或以人物活动为主的,人也是充满乡野之趣的,典型的如卢挚[双调·蟾宫曲]《田家》:
沙三伴哥来嗏,两腿青泥,只为捞虾。太公庄上,杨柳阴中,磕破西瓜。小二哥昔涎剌塔,碌轴上淹着个琵琶。看荞麦开花,绿豆生芽。无是无非,快活煞庄家。[34](P103)
古朴、淳厚、无事无非、无争无斗,人们活动简单而快活,这可作“乡野恬逸”的形象图解。曲家眼中的农家生活,安然泰然,无所求当然也无所不足,曲家陶醉于乡野的水国渔乡、柴扉山庄之中。
有的曲家干脆要走进水边林下,置身其中,体验类似于上古逸民的快乐。贯石屏 [仙吕·村里迓鼓]《隐逸》套数就是如此:“我则待散诞逍遥闲笑耍,左右种桑麻,闲看园林噪晚鸦。心无牵挂,蹇驴闲跨,游玩野人家。”“绕柴扉水一洼,近山村看落花,是蓬莱天地家。”[29](P387-388)这套曲中的“我”是一个体验生活的外来者。他向往陶渊明式的隐逸,但他与陶渊明不同,他本人不属于“水边林下”,因此他之对于水边林下、田园山野,有与陶渊明不同的着眼点和感受,他感觉乡居生活是新鲜的,所作的事都是有意为之的,是其体验的内容而非生活的一部分。
这类作品也多俗,但“俗”不能体现其精神。
5.闲野俊逸。这一类似乎不好把握。因为一般说来“野”与“俊逸”好像是矛盾的,有没有既有野趣而又俊逸的作品呢?姚燧有[双调·寿阳曲]和[双调·拨不断],郑振铎评:“他的《寿阳曲》:‘谁信道也曾年少',和《拨不断》:‘破帽多情却恋头'诸句,还不失为俊逸之作。”[35](P445)姚燧之作不是野而俊逸的典型,典型的如马致远[双调·新水令]《题西湖》:“渔村偏喜多鹅鸭,柴门一任绝车马。竹引山泉,鼎试雷芽。但得孤山寻梅处,苫间草夏,有林和靖是邻家,喝口水西湖上快活煞。”([尾])[32](P247)曲写得俊逸潇洒,让人想象曲家的风流俊爽,但曲中又确实充满野趣。
元散曲中有大量写山间水滨田园乡野生活的作品,其中一些作品中的山间水滨田园乡野,是文人化了的,甚至是文人想象的,是失真的。这类作品,从用语,到格调,到作品中表现的情趣,都是文人化的,乔吉[玉交枝]《闲适二曲》之一就是:
山间林下,有草舍蓬窗幽雅。苍松翠竹堪图画,近烟村三四家。飘飘好梦随落花,纷纷世味如嚼蜡,一任他苍头皓发,莫徒劳心猿意马。自种瓜,自采茶,炉内炼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闭上槿树篱,醉卧在葫芦架,尽清闲自在煞。[36](P281)
这是曲家想象的理想空间,是文人的乌托邦。山间林下全涂上文人理想的色彩,美如图画,乐比理想国。像卢挚的 [双调·沉醉东风]《秋景》,王伯成 [越调·斗鹌鹑]《春游》之 [圣药王]等,都是如此。用周德清所谓“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见前引)评价这样的作品,确实还合适。
张养浩这类作品也不少,如[中吕·最高歌兼喜春来]《诗酒欢娱》:“对一缕绿杨烟,看一弯梨花月,卧一枕海棠风。似这般闲受用,再谁想丞相府帝王宫?”[30](P16)尽管在有些作品中表现出对无思无虑境界的向慕,但他们要的不是真正的无思无虑。他们的无思无虑是超越思虑的大智慧。渔樵自由,只是身的自由,渔樵没有思想。士大夫有思想,但不自由。他们想既有士大夫的思想,又有渔樵的自在。如此身也自由,心也自由。不仅人在宽闲之野,心也可以海阔天空,那才是他们真实的愿望。“谁人共,一带青山送。乘风列子,列子乘风。”(卢挚 [双调·殿前欢]《八葫芦》)[34](P132)
6.野思逸想。这是思想的野逸:出格的甚至异端的思想。元代文人喜欢海阔天空的奇思异想,先圣前贤的遗训,历史定评,都可以质疑。戏说历史,野评人物,揶揄先贤,颠覆圣训,在元散曲中时时可见。元曲家薛昂夫有[中吕·朝天曲]22首,都是野评历史的,我们选其中一首来读:
卞和,抱璞,只合荆山坐。三朝不遇待如何,两足先遭祸。传国争符,伤身行货,谁教献与他?切磋,琢磨,何似偷敲破?[29](P705)
卞和泣玉的典故,史有定评,元代曲家却将之颠覆了。类似这些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翻案之作,在元散曲中多有,如批评甚至讽刺屈原,为什么要投江,太傻,死得毫无价值:“恨尚存,人何在?空快活了湘江鱼虾蟹,这先生畅好是胡来。怎如向青山影里,狂歌痛饮,其乐无涯。”(张养浩[中吕·普天乐]《乐无涯十咏》之七)[30](P87)一般说,元曲家总是否定屈原,肯定、赞赏陶渊明,白朴[仙吕·寄生草]《劝饮》两句:“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31](P179)可以作为元曲家这一态度的概括。
一些戏说历史、妙解、趣解历史的作品,让人读了不由发笑,如姚燧[双调·寿阳曲]《咏李白》:“贵妃亲擎砚,力士与脱靴,御调羹就飧不谢。醉模糊将吓蛮书便写,写着甚?杨柳岸晓风残月。”[37](P571)这包袱甩得太出人意料,又幽默异常,叫人越想越觉得可笑。这类作品数量较多。为什么元代曲家要颠覆千百年历史定评?20世纪的研究者已经有不少讨论,在我看来,是因为元代文人普遍意识到个体生命的价值。对于一个文人来说,自古所谓的君臣相得,风云际会,所谓的士为知己者死,都是依附于政治的人生价值观,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否定。元代文人充分认识和尊重个体生命价值,对上述传统价值观念表示了怀疑甚至否定。如马致远所言:“臣事君已忠,君使臣以礼,哎!这便是死无葬身之地。”(马致远《陈抟高卧》第三折)[38](P107)在元散曲似乎荒诞的调笑与游戏笔墨中,蕴含了严肃的思想意义。这种珍贵的思想观念,在中国古代没有能够充分发展起来,也是历史的遗憾。元散曲家在戏说野评历史中表现出的思想的野逸,特别值得珍视。这一类可说“俏”,但以“俏”概括,似乎会消解其批判价值。还是具有叛逆性的“野逸”更能体现其精神特质。
7.俚野荒逸。元散曲有一些格调低下甚至低俗的作品,也“野”也“逸”,姑且概括为“俚野荒逸”。这是元代散曲中客观存在的,研究中无法回避。
当然,这类作品也并非可一概弃之如粪土,任中敏《曲谐》卷一《元曲中奇秽》专谈此类作品:“元人作曲,完全以嬉笑怒骂出之,盖纯以文字供游戏也。惟其为游戏,故选题措语,无往不可,绝无从来文人一切顾忌。宏大可也,琐屑亦可也。渊雅可也,猥鄙亦可也。故咏物如佳人黑痣、秃、指甲等,皆是好题目,了不觉其纤小。所描摹者,下至佣走粗愚、倡优淫烂,皆所弗禁,而设想污秽之处,有时绝非寻常意念所能及者。”他接着举例说:“无名氏 [红绣鞋]十一首,所写全是厮婢间奸情丑态,而开章明义云:‘老夫人宽洪海量,去筵席留下梅香,不付能今朝恰停当。款款的分开罗帐,慢慢的脱了衣裳,却原来纸条儿封了裤裆。'阅尽能不为之哑然掩口乎?”[39](P1118-1119)又其《残元本阳春白雪》云:“上述无名氏[红绣鞋]中,别有隽妙可意之作。”他举“背地里些儿欢笑”等作,说:“诸词都足资一粲,以其传情写态,俱能刻画入里也。”[39](P1119)他所举其中一首如:“款款的分开罗帐,轻轻的擦下牙床。栗子皮踏着不提防。惊得胆丧,诡得魂扬,便是震天雷不恁响。”[29](P1693)写男主人要跟丫鬟偷情,趁夫人睡着要溜下床的惊魂一瞬,确实很传神。这类不伤大雅又传神写照的作品还是有一些,当然也说不上多大价值。真正“俚野荒逸”甚至可以称作鄙野荒逸的,是那些确实低俗的东西。这类“野逸”,表现有野、逸的负面义。
三、后期“清丽派”曲家的野逸之作
“野逸”涉及观念与风格两个方面。所以,“野逸”与按风格特征为散曲所作的流派分类,即通常说的豪放派与清丽派,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野逸”未必一定豪放,清丽与“野逸”也不存在排斥关系。但就一般的感觉说,“野逸”还是豪放多一些,清丽之作又如何表现为野逸呢?特别是后期清丽派,一般认为后期清丽派散曲走上了词化之路,还会有“野逸”之趣吗?所以,有必要专门对此作一些考察。
学术界一般以乔吉、张可久为后期清丽派最主要的代表,其他还有徐再思、刘庭信、孙周卿、周文质等,人数是比较多的。我们选其中几位,考察一下他们具“野逸”之趣的作品。
先看乔吉。乔吉是元代散曲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朱权《太和正音谱》评乔吉散曲:“如神鳌鼓浪”“波涛汹涌”。李开先认为,朱权所评,“特言其雄健而已,要之未尽也”。他眼中的乔吉散曲,是:“藴藉包含,风流调笑,种种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繁;句句用俗,而不失其为文。”[40](P298)他们都认为,乔吉散曲具有野逸的特点。读乔吉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就能感受到朱权所说的神鳌鼓浪、波涛汹涌之势,确实不乏野性之力,如:
鹏抟九万,腰缠十万,扬州鹤背骑来惯。事间关,景阑珊,黄金不富英雄汉,一片世情天地间。白,也是眼;青,也是眼。(乔吉 [中吕·山坡羊]《寓兴》)[36](P265)
不仅有不可羁勒的野性,还表现了决不屈己从人的狂傲野逸之气。乔吉清丽之作也有野意之美,[双调·折桂令]《荊溪即事》:“老树支门,荒蒲绕岸,苦竹圈笆。寺无僧狐狸样瓦。官无事乌鼠当衙。”[36](P236)写足了荒野之趣。
乔吉性格有孤傲的一面,有放浪的一面,又有潇洒的一面。孤傲、放浪、潇洒,表现在作品中,都成为野逸之气。这样的作品,在乔吉散曲中相当多,如[中吕·山坡羊]《自警》:“清风闲坐,白云高卧,面皮不受时人唾。乐跎跎,笑呵呵,看别人搭套项推沉磨。盖下一枚安乐窝,东,也在我;西,也在我。”潇洒而自在,自由便是人间最大的快乐。但他自己毕竟活得是一个遗憾,“酒兴诗颠”会发出“苍天负我,我负苍天”的浩叹([双调·殿前欢]《里西瑛号懒云窝自叙有作奉和》)。乔吉也有感受历史虚无、消解庄严与神圣的作品,如[双调·折桂令]《丙子游越怀古》等。现实的富贵与功名不仅是空的,而且暗藏凶险,最好的人生选择是躲避:“急跳出风波大海,作个烟霞逸客。翠竹斋,薜荔阶,强似五侯宅。”[36](P305)闲野乐逸,轻松自在,这就是烟霞醉仙。乔吉有些像柳永,也是长期混迹于青楼。以俗言俗语写青楼社会,充满俗趣,当然也带野意。他有 [南吕·一枝花]《私情》《杂情》两套曲,《私情》之 [梁州第七],写想偷情却不得上手,写得情态毕现,尚不流于低俗。乔吉有不少讽世之作,讽刺尖刻泼辣,也表现为野意。
张可久有“野逸”之作吗?有,任讷先生说张可久有“由清疏而入豪放”的作品,还有“逸情远慨,跃跃纸上,得豪放一派之正,而并足以见作者胸襟境地者”[39](P1181),这样的作品无疑具有“野逸”之趣。任讷所举作品是[双调·殿前欢]《次酸斋韵》二首,其二如下:
晚归来,西湖山上野猿哀。二十年多少风流怪,花落花开。望云霄拜将台,袖星斗安邦策,破烟月迷魂寨。酸斋笑我,我笑酸斋。
这是次贯云石韵之作,其大开大合的风云气,也即我们说的满含野性,应该与贯云石原作有关。任讷还说到张可久名作[正宫·醉太平]《无题》(人皆嫌命窘),评此曲“悉排典语,独铸俚词,而能极尽其妙,浑然元人风度者”,“痛愤之深,嘲骂之烈,得未曾有”[39](P1182)。可能是张可久最富有野意的作品。
其实,张可久曲有野意并非任讷最早发现,与张可久大致同时的大食惟寅有[双调·燕引雏]《奉寄小山先辈》,赞扬张可久曲作:“气横秋,心驰八表快神游……诗成神鬼愁。”[29](P1117)尽管主要是评价其声名与影响之大,但也让人感到张可久曲作的气势气象,绝非一味清丽文雅。张可久散曲中不乏有如此气势气象的作品,如[双调·庆东原]《和马致远先辈韵九篇》其五:
诗情放,剑气豪,英雄不把穷通较。江中斩蛟,云间射雕,席上挥毫。他得志笑闲人,他失脚闲人笑。[41](P519)
其喷薄而起的气势,可使读者血脉偾张。这是和马致远韵之作,可能与马致远原作有关。张可久散曲中有仙逸之气的比较多,如:
一方明月杏花坛,剑气霞光烂。回首蓬莱自长叹,佩秋兰,黄精已够山中饭。劳心又懒,干名不惯,归伴野云闲。(张可久 [越调·小桃花]《山中》)[41](P258)
如果将“野”“逸”分开来看,张可久“野”趣不及乔吉,而“逸”趣则往往过之。
乔、张二人之外,徐再思、孙周卿、周文质、刘庭信等人,也都有富于野逸之趣的作品。
四、“野逸”趣味之营造
转换角度来看以往对元散曲特点的概括,“俗”“谑”“俏”是风格特色,同时也可看做是营造“野逸”之趣的手法:俗的语言、谑也即荒诞的手法、“俏”或“诮”即诙谐与讥讽,都是营造“野逸”趣味的手段。
简单地说,元曲家营造“野逸”之趣的手法,就其主要的说,有以下几种。
第一,荒诞。元散曲中给人印象特别深的,是荒诞。荒诞,就是对事物作极度夸张、离奇、变形的描写,用失真的形象给读者强烈的感受。突出的例子有王和卿[仙侣·醉中天]《咏大蝴蝶》和他的[双调·拨不断]《大鱼》,既荒诞又滑稽搞笑的是同调的《胖妻夫》:“绣帏中一对儿鸳鸯象,交肚皮厮撞。”[29](P41,45,47)荒诞手法在元散曲中比较常用,特别在讽刺类作品中更常见。荒诞的,也是野逸的。
第二,讥讽。讥讽在元散曲中是很大的一类,其中有讥世与讥人。论曲者言曲有多种“体”,卢前《散曲史》归纳为二十五体,其中“托咏物以暗中讽刺者,为讽刺体;托咏物或咏事,明作嘲笑者,为嘲笑体;专嘲笑风流,警戒飘荡子弟者,为风流体(此体名见《诚斋乐府》);谑浪淫亵,无所不至者,为淫虐体……”[42](P9-10)其实这些都可看做讥讽。其中讥世之作,如张鸣善有直接题作《讥时》([双调·水仙子])之作四首,其一云:“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29](P1282)使用荒诞手法讽刺。这样的作品,野逸之性十足。还有一些讥讽之作,具有现实社会批评意义,其野逸更不必说。如刘时中[双调·殿前欢](其二)写官员下乡的丑态,无名氏[双调·清江引]《讥士人》对无才无德文人的讽刺。这样的作品,以正立意,“野”性“逸”气都体现在大胆抨击上。讥人之作更是千姿百态、万花千木。贪婪、吝啬、守财,在元代这样的人可能不少,有一类曲专讽这样的人,也特别有逸气。曲作使用荒诞手法,引人发笑,如无名氏 [正宫·醉太平]《讥贪小利者》[商调·梧叶儿]《贪》《嘲贪汉》等。以笑谑代怒骂,给人强烈的印象。这类尖刻讽刺,以无名氏作品为多,其内容本身就具野意。
第三,愤世与自讽。愤世也是元散曲中一大类,有些作品特别具有逸趣,如:“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渰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白朴[仙侣·寄生草]《劝饮》)[31](P179)有些作品由愤世而转为自嘲自讽,以怪异与荒诞对抗社会的不公,如钟嗣成的[南吕·一枝花]《自序丑斋》套曲,其[梁州]云:
子为外貌儿不中抬举,因此内才儿不得便宜。半生未得文章力,空自胸藏锦绣,口唾珠玑。争奈灰容土貌,缺齿重颏,更兼着细眼单眉,人中短髭鬓稀稀。……清晨倦把青鸾对,恨煞爷娘不争气。有一日黄榜招收丑陋的,准拟夺魁。[29](P1371-1372)
他的[正宫·醉太平](风流贫最好)也可做如此观。自我调侃,自我贬损,表现自己的怀才不遇,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这“野逸”之趣从调侃来。
第四,代特殊人(物)立言。如代歌妓、代嫖客、代乞丐、渔父樵夫立言,这其中有不少名篇,如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代嫖客、杜仁杰[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代庄家、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代迎驾农夫。代乞丐立言的如钟嗣成[正宫·醉太平]。代物立言的也有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如姚守中[中吕·粉蝶儿]《牛诉冤》、刘时中 [双调·新水令]《代马诉冤》等。
第五,以独特的语言制造“野逸”效应。其中口语、俗语的运用,研究者谈得已经很多,这些都给人以野逸之感,如“倒大来”“省可里”“颠不剌”,以及“呀剌剌”“扑簌簌”“懒设设”等相声词。运用衬字营造野逸气氛,是元散曲的重要特色,王廷秀 [中吕·粉蝶儿]《怨别》套数之 [尧民歌]:“呀,愁的是雨声儿淅零零落滴滴点点碧碧卜卜洒芭蕉,则见那梧叶儿滴溜溜飘悠悠荡荡纷纷扬扬下溪桥……”[29](P318)大量使用衬字且是相声词,又多叠字,制造一种声音效果,形成野逸的效应。同样手法的作品如周文质[正宫·叨叨令]《悲秋》:“叮叮噹噹铁马儿乞留玎琅闹,啾啾唧唧促织依柔依然叫,滴滴点点细雨儿淅零淅留哨,潇潇洒洒梧叶儿失流疏剌落。”这真是一篇独特的秋声赋,完全依靠声音的摹写,写足了浓浓的秋意。
在语言运用上要说的话很多,比如散曲形式的灵活,韵脚可以平仄通押,又不避重字重韵等,都有利于野逸之趣的营造。各种俳体、巧体的运用,也可以营造诙谐、幽默、俏皮的效应,也即“野逸”之趣。
“野逸”之趣可以概括元散曲的基本特色,它涵括了以往研究者对元散曲特色的各种概括。“野逸”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元散曲不同的作家作品中体现的“野逸”之趣有多种表现形态。“野逸”是一个涵盖面比较宽的概念。尽管如此,它也难以涵括元散曲的所有作品,不能说元散曲都具有“野逸”之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