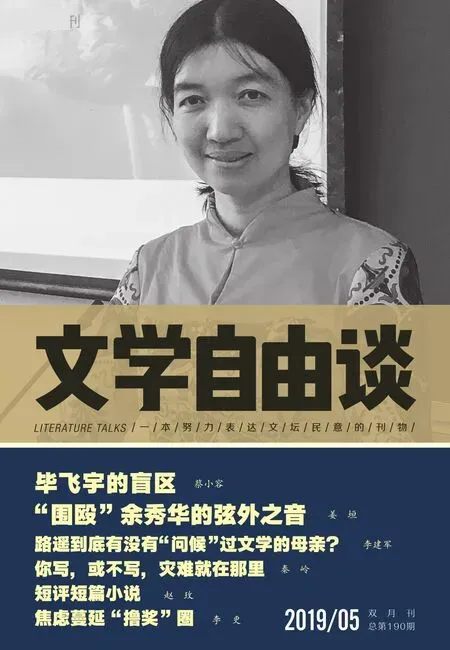三心二意文学奖(外两则)
□方英文
西安的夏天很热,如同几十年前一个阵营的报纸上,描绘的另一个阵营的日子,实在难熬。现在好了,秋天来了,且还颇有眼色地下了些细雨。
送目秦岭,烟岚着淡墨色。那里面有很多隋唐遗迹,如李世民宾天的翠微宫。现如今,竟有不少隐者。
我听说有两个和尚,一个法号三心,一个法号二意。三心善绘画,二意迷书法。两个寺只隔一个小山垭,一小时路程不到。所以隔上一两天,二僧各自卷了作品,碰头互赞,切而磋之。
物质生活不成问题。布施者较多,以家庭生活不和谐的少妇为主。
昨天,《三门峡日报》刊登了王晓峰先生评论我的长篇小说《群山绝响》的文章,题目叫《往日画卷,黎民颂歌》,谬奖有加。同版有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五部获奖作品的综述。评奖结果如赌局揭碗,狂喜者少数,失落者众多,一时间质疑嘲讽声此起彼伏。这再正常不过,因为文学评奖不同于体育赛事。体育竞技只要尿检没问题,上场一比拼,强弱立现,天下尽服。
几个月前,《群山绝响》也曾被出版方申报了上去。我说好嘛,好比过去的乡下,勤劳者每天早早起来,拎着筐子出门拾粪呢,拾得着拾不着自然两说了,但出门拾粪总归是一个好习惯啦。
《群山绝响》去年2月出版,半年内加印两次。纸媒上的评论文章,字数已超过小说文本。这是让人欣慰的,毕竟是我拿毛笔写了三年,又修改了两年,才交付出版的。
确也产生过获奖幻想,只是一闪而逝。获奖需要三个“靠”字:靠作品,靠人脉,靠气候。而我这类系统之外的业余作家,反复研判自身,结论却是“三不靠”。
说到茅奖,印象里,历届评奖,除了有个别军方作家获奖,其余得主似乎全为系统内作家。这也合乎情理,因为文学早已行业化了。好比钓鱼协会颁奖,获奖者只能来自本协会内部;上台领奖的忽然夹杂了一个“驴友”,岂不怪哉!
浏览网友质疑,我也觉得此次茅奖的结果过于集中了。一是获奖作品全由北京出版,二是获奖作家皆为北京户口。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一个小区域文学奖,等于“北京市民茅盾文学奖”。北京固然重要,但是之于辽阔的中国文学版图,之于上千家出版社,之于数万部长篇小说,北京市民的文学再强大,也不至于强大到可以挟泰山以超北海吧。
稀释奖章的含金量,或者相反,缩水对方的荣耀感,启动精神胜利法,是平衡心理、获取快乐的艺术窍门。也是道家手段,延年益寿,眨眼一风吹过。
2019年8月21日,采南台
达人休矣
饭桌上与初识的男士女神互加微信,是当代生活风尚之一。加了微信之后并不交流,甚至终生都不再见,亦属正常。全因当时现场,需要营造氛围也。人之一生,此种一饭之缘者,是无法统计的。
当然加微信也并非全在饭局上,动车上邻座互加也不稀罕。日前参加一个文化活动,楼道休息时,朋友介绍一位女教授,互加了微信。我吸烟,女教授垂首查看手机。我的“朋友圈”设限三天,却也有十来条。好在一概毛笔原创,内容不过百字之内。教授很快翻完了,轻声赞道:有意思,哈哈,有意思,微信达人哦!我有点茫然,竟不知如何回应。因为说来惭愧,我竟不知“达人”啥意思。
现就“达人”一词请教“度娘”。字数不少,容我以词条范式精炼如下:
一、指显贵的人;
二、指通达事理的人;
三、指豁达豪放的人;
四、网络新词,指某一领域出类拔萃的高手,或上线时间长、内容更新频率高的网民。
反复比照,确认自己属于末句所说的“内容更新频率高的网民”——顿时羞汗喷射!可不是吗?圈里的官人、钱人、名人,基本不发或极少发微信。一句话,成功者、精英们,一概不吱声而宁静致远噢。陶然于微信者,我等网民也。
其实在7月23日,我就发过这么一条微信:
“每天发微信,是为人民服务呢还是我自己需要?结论是我自己需要。所以我要斗私批修,少发微信,免得人民(当然我也是人民)讨厌我。”
——证明自我虽有警觉,却未痛改。现写此文,正肃纲纪。
如实交代,我的微信朋友圈获赞量是比较大的。一天不发,夜里准会收到私信询问缘故,称其不见我微信,一天便少个节目,睡不着。明知巧言娱我,偏又装信,于是继续频发。假若真的不发,对方断不至于病倒,警察断不至于抓我。总之,发微信是我个人需要,归类恶习,小利人而大害己嘛。
由是联想到开会。比较讲话者与听会者,二者谁最需要开会?以我几十年开会之体验,去年才恍然大悟:讲话者需要开会。开会是他们的职业,讲话是他们的上班。所以开会之于讲话者最重要,之于吾等“吃瓜群众”听会者最次要。
十个会议中的九个会议原本可开可不开,事实上都开了。什么原因?讲话者要上班呀。频发微信也是各自需要。有人凭开会讲话拿工资,乃“职责所在”;而频发微信者毫无报酬,岂非脑子进水、匪夷所思?
此恶习尤其浪费光阴,让我五年来少写两本书,尽管写书也终究意思不大。且伤眼睛。微信一发出,手机攥紧,屏幕死盯,急盼点赞与留言。好比顽童朝人堆里扔个空瓶子,随即双手背后假装没事,只等骂声飞来才开心呢。挨骂属于另类点赞,创意挨骂更是营销术之一。酒足饭饱之余,不想个法子让“圈儿”里反响个啥,憋得慌哦。
2019年8月4日,采南台
《群山绝响》题外话
出生于农村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女,是热衷于《群山绝响》的读者。他们从小说里看到了自身的往昔生活,或者从父辈嘴里听来的絮絮叨叨的陈年琐事,如今,则因小说的形象化与极具细节化,而留下比较完整的对于那个时代的印象与认知。
这部长篇我用毛笔写作了三年时间。冷冻了一段时间开始修改,断断续续修改了两年时间。
我的妻子不怎么读我的作品。但是这一本《群山绝响》,她连看两天,读完了,非常稀罕地夸赞了几句——要知道在多数妻子眼里,丈夫大抵是种乏善可陈的动物。不过妻子同时批评,或者说质疑:当时的农村真有这么苦吗?我一参加工作就在人民公社机关,工作了两年,天天下乡,感觉没这么严重嘛!我说你是1979年由县城下到农村公社工作的,而我小说写的是1976年——时代变了,尽管不是后来的巨变。但根本原因是,你是城里吃商品粮长大的,我是乡下吃农业粮长大的,有切肤感受的只能是我、而不是你。妻子不再吱声。
正月十五,我在微信上晒元宵,说我小时候只从大人嘴里听说过元宵、粽子、月饼、年糕之类的节令美食,生活里却不曾实见过。一位女作家留言,说我夸大其词,称她记忆里并非如此。我说你也是城里吃商品粮的,知道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典故吗?
网上不时看见一些言论,说那时很平等。此说不无道理,只是表述欠完整与确切。妥帖的说法似应这样:那时的“商品粮”之间比较平等,那时的“农业粮”之间比较平等;但是“商品粮”与“农业粮”之间,那就大不平等了。八亿“农业粮”的人均收入,不到一亿“商品粮”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啊!因此农村人的生活可想而知。那个时代,真正诱惑底层人的神话是——跳农门,吃商品粮。
但我,并不想以“诉说苦难”为基调来写我的这部长篇,何况纵向比较民国战乱年代,新中国的光景简直好得很了!再说文学作品有别于“灾情报告”,它有着天然的“美学义务”。我侧重书写的是黎民之朴素、伦理之亲爱、地域之旖旎、乡风之别样——特别是生命之如草芥且坚韧。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四大关节点:1911年帝制终结,1937年全面抗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6年毛主席逝世。《群山绝响》写的是1976年,故事从生发到终结仅九个月,即从周总理去世到毛主席去世期间。壮丽国史自有史家书写,微末民生当由作家填补。
我自以为完成了某种使命。我无愧于生我养我的至亲与土地,对得起培养我的师友与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