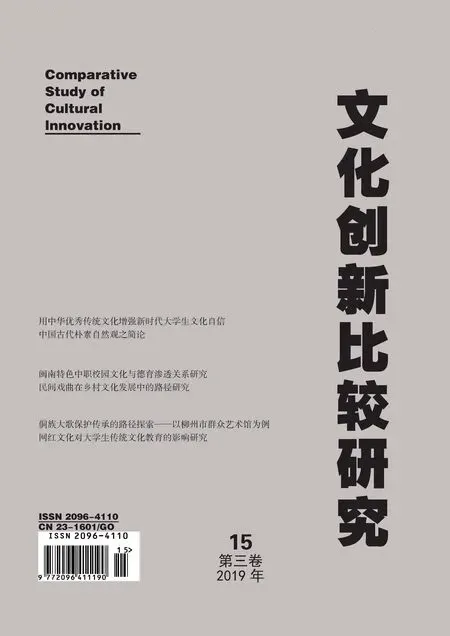审视理性专断与精神病院照顾之憾
——从院舍照顾到社区康复
刘 芳 徐兴文
(1曲靖师范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云南曲靖 655011;2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 650504)
人类对精神疾病的理解经历了从超自然到自然,从监管到治疗,从机构化到去机构化,从机构照料到社区康复,从疾病到一种状态的转变的历程。[1]长期以来,精神疾病患者是基于院舍照顾,在漫长的院舍服务发展过程中逐渐的弊端,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福柯理性化思维,重新审视精神病院照顾,试图从学理逻辑寻找人性的回归,以及为精神疾病康复服务的探索找到理论皈依。
1 理性化身的精神病医院
5世纪的西班牙便出现首家为疯癫者服务的医院,随后这种方式迅速传播到巴黎、维也纳、莫斯科等其他欧洲城市,更多的精神病人进入到专业机构。8世纪的阿拉伯国家,则开始在一般医院里开设病房为精神病人提供服务。据有关文献记载,早在15、16世纪便开始了对精神病院的禁闭,由于麻风病的减少,很多麻风病院被进一步改造成精神病院,用以收治精神病人,此类禁闭的精神病收容机构,成为了臭名昭著的“疯人院”,在这些疯人院里,精神病人过着非人一般的生活,甚至在一些国度,这类精神病监禁机构,成为招揽、取悦游客的工具,他们把观看精神病人残暴、发狂以及怪异行为视为消遣和娱乐,在这种低俗的品味中构建了社会人对精神病人的监禁与歧视,这类精神病院实质上背离了服务精神病患的初衷,因院舍内外恶劣环境,进一步加剧了精神病人的社会隔离。
19世纪伊始,疯癫开始被“囚禁”在所谓纯粹理性的道德话语脉络体系之下,疯癫开始具备道德意义,被视为道德过失的效果,疯癫者依附于理性秩序之下,不断的被定义、建构并强迫其认同并挣扎于远离疯癫的力量之中。针对精神病患的理性已经不再关怀疯癫是什么,而是如何让疯癫者回归受约束的日常生活。这种从道德上的否定到理性上的否定过程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精神病人态度的显著特征,道德上的否定尚且还为精神病人回归正常生活与劳动提供了可能性,即使他们被等同于游手好闲之辈或流浪乞讨之人,依然可能被新教伦理精神所改造,而理性上的否定,精神病患除了送往疯人院被监禁已别无他路,疯人被理性视作完全的异己,成为受制于理性须被其约束的非理性的破坏之力。[2]迎接疯癫者的便是那象征人道主义精神的图克以及皮内尔的精神病院。
2 精神病院照顾之憾
2.1 规训还是治疗?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提出全景敞视主义,用以解释个人受到某种绝对的监管的社会现象,因为全景敞视建筑,看似减轻了对特殊人群的刑罚,但却使“监视”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被看者承受被监视被观察的孤独,个人隐私无处遁形。权力通过这种监督与管理方式无所不在,虽然M医院的外部结构严格来说不能称之为全景敞视主义,但从病人内部活动空间来看,至少从内部结构来看,布局与结构还是类似于全景敞视主义式的。许多病人活动在很小的一块空间里,其中两个侧面是门,防止其它区域的病人出入,另外两个侧面是窗户,也就是医生的办公室,屋顶是透明玻璃。虽然仅有的一点空间没有被分为福柯所说的一个个小的囚室,但是他们完全暴露在医生的视线之下,医生透过窗户可以观察活动室中每个病人的情形。这样的安排使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医生的权力通过这种结构进行微观运作,权力散布在每个病人的周围,即使医生不在注视的他们,那种不确定的、无法预知的注视的目光似乎也将病人们规训、驯服,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的产生一种真实的征服。它在减少行使权力人数的同时,也增加了受权力支配的人数。所以,作为理性化身的精神病院与其说在用理性的方式治疗病人,不如说它在披着理性的外衣下监视、规训病人。
早在20世纪初,比尔斯(C.W.Beers)根据他本人患精神病住院三年的经历撰写了《失而复得的心》一书,使人们了解到当时的精神病患者在类似监狱的精神病院中所遭受的非人折磨,并主张结束这种所谓的“看护”和“管理”。[3]
2.2 治疗疾病抑或加重疾病?
理性关注的是如何使病人回到规范的日常生活中去,而整个社会也只承认一种合理的思维方式——理性的思维方式。所以,一个人的思维或行为如果不符合所谓“理性的”、“合理的”方式,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送到医院中进行治疗,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去医院进行治疗也可能无形中的受到权力的控制甚至使病人加重或衍生出其它疾病?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人大多都不是自己主动来接受治疗,而是被家人、警察等具有社会控制功能的人送进来的,这本身已经违背了病人的意愿,甚至可能侵犯了病人的人身权利。我之所以说我们侵犯了病人的人身权利,并不是说这样就不对,因为这完全是按照社会正常人的思想行为标准进行的一种社会权力控制,我们每个人都尽量把自己塑造成在其他人看来符合社会正常期望的方式去思考、去生活,也就是说,这是社会上“正常人”统治的社会,它把不符合社会对正常人期望的那些人视为“异端”。于是,社会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将这些人集中起来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符合社会正常标准的“正常人”。
然违背意愿的强制性治疗、不可预测的药物副作用、封闭式的治疗环境、亲密关系的中断、可能暴露的隐私、社会歧视等等,这些形塑在各类权力下的压迫与束缚,无疑对病人而言形成新的挑战。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社会精神病学家温(John Wing)等人便觉察到因长期监禁于精神病院的患者呈现的所谓“精神病院综合征”(Institutionalism),它以精神病患者缺乏主动性、感觉木讷、倒退畏惧、屈从权威以及对精神病院的过度依赖为特征。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亦指出,在州立精神病院中,精神患者被贴上愚昧、耻辱和变态的标签,缺乏人情味的治疗使患者的尊严和个性荡然无存,甚至导致疾病的恶化。[4]
3 从去机构化运动到社区康复
基于当前精神病院照顾存在的局限,如封闭式环境带来对人性的压迫,长期封闭,缺乏交流的人文环境,导致服务对象与社会隔绝,出院后难以回归社会,过正常化生活。因此,呼吁从封闭性环境到开放式环境,更加包容的社区康复模式。20世纪50-60年代的“去机构化”运动追求患者有尊严的康复与生活,着重社区冲拳、尊重人权的理念、提升病人生活品质、促进其社会适应、获取社会资源,过正常化生活成为其重要特征。然去机构化运动也带来诸多非议,精神卫生保健从大型精神病院分离,大量曾经收治于此的精神疾病患者走出机构获得“自由”,却沦为无家可归之人,他们丧失了精神病院保护屏障,尚未得到社区的监管与看护,加上缺乏必要的康复指导与服务,药物依从性显著降低,疾病复发率由此攀升,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麻烦,针对精神病人以及正常民众的不安全性要素都增加了。而秉持“尽量避免机构安置与非必要的隔离,精神病人应该和社会上其他人一样,享有尊严和权利,而不应该因为有障碍而受到排斥”[5]的理念的“以社区为中心的服务”(Community·centered service),成为寻找“去机构化运动”的必然落脚点。WHO在《精神卫生政策与服务指南一组织精神卫生服务》中明确指出“改善精神卫生服务应该由大型的卫生服务和社区机构来提供。集中的精神病院必须被其它更为适合的精神卫生服务所取代。”
精神病患在一个正常化的生活空间中,能够更好的重新获得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成为社区康复倡导的重要理念。[6]大量的研究证明,精神疾病患者开展各项社区康复服务,可以在预防精神残疾的发生或者减轻精神残疾程度方面有积极的作用,它可以使精神疾病患者因病丧失的家庭和社会功能得以最大的恢复,自身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劳动能力得以最大的发挥。同时它也节约医疗资源,减轻社会和家庭的经济负担,降低危险行为发生率,对社会安定、家庭和谐均起着积极作用。[7]因此发展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服务,开展综合治疗,是促进患者达到医学、心理、社会以及职业全面康复的重要手段。
——以离婚纠纷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