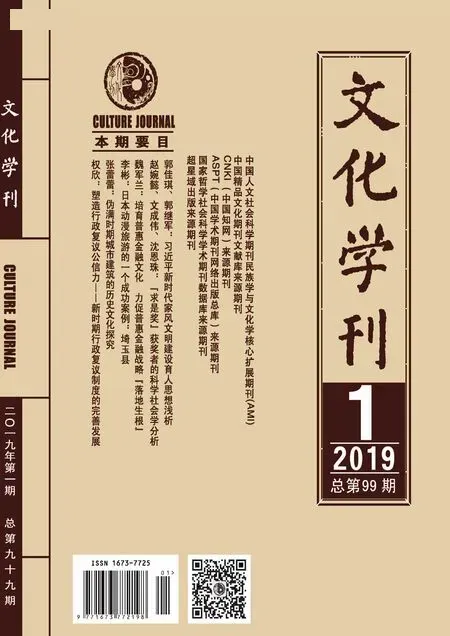明清贵德地区移民文化研究
薛舒凡 刘 斌
明代贵德城孤悬海外,兵源和粮草运输成为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政府在贵德地区实行移民戍边的政策。伴随着大批移民的迁徙,中原的汉文化也随之到来。进入之初就与当地的原始文化形成对立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最终,在清代完成两种文化间的调适,形成特有的移民文化。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贵德地区的移民文化进行简单的论述。
一、移民文化的雏形
贵德地区移民文化在明代处于一个初步的形成阶段,大量的屯戍移民带来江左文化,与当地的原始文化开始接触并进一步产生反应。
江左文化最早可以追溯至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许多中原的士子、大夫将中原文化带到了江左地区,与当地文化经过几百年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化圈——江左文化圈。到了明代该文化圈已经基本稳定,但随着邓愈攻克河州,随军而来的江左文化第一次进入了青藏高原。江左文化进入贵德地区应该和屯戍移民有关,根据研究可知,贵德十屯的屯戍民和“河州四十八户”移民大多是来自江左淮泗地区。《循化志》的记载:“明初立河州卫,分兵屯田,贵德共十屯,保安有其四。屯兵之初,皆自内地拨往,非番人也。故今有曰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余亦有河州人,历年既久,衣服言语,渐染夷风,其人自认为土人,而官亦日之为番民矣。”[1]大量移民的进入带来了江左文化中二郎信仰文化、龙王信仰文化、文昌信仰文化,而其中的回族带来了伊斯兰文化,这些文化在进入之初与当地的原始文化形成鲜明的对立,但江左文化曾经一度引导当地的原始文化。后来,随着交流的深入,江左文化与当地的原始文化开始融合,形成独特的移民文化。
换一种说法,明代是贵德地区文化调适的开端,到了清代贵德地区的文化调适最终完成。
二、移民文化的形成
清代贵德地区的移民文化,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民族的交流,逐渐形成了各种民族文化和平共处的多元化的移民文化。总的来说,贵德地区的文化按宗教来分可以分为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民间信仰文化;按民族来分可以分为藏文化、汉文化、蒙文化和回族文化。下面以宗教为分类依据对贵德地区移民文化作一个简单的概述。
(一)佛教文化
由于贵德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其佛教文化出现了两种分支:其一为讲究“渐悟”的汉传佛教,其二是以“顿悟”为主的藏传佛教。从微观上来看,由于该区域少数民族较多,因此藏传佛教的影响力较之汉传佛教大。但从宏观上来看,两种佛教文化共同促进了佛教文化在该区域的影响力。据资料统计,1958年宗教改革之前全县共有藏传、汉传佛教寺院、本教寺院五十七座,有僧侣(包括信徒)两千四百九十九人,活佛四十人,拥有大小经堂二十七座一千三百八十间,佛堂十三座二百五十间,昂欠十四院七百七十一间,僧舍三百一十五院四千四百七十七间,其他房舍一千二百零一间;拥有各类牲畜一千二百九十五头[2]。
1.汉传佛教
在今天的贵德县境内可以找到的汉传佛教寺院只剩一家,那就是位于河阴镇贵德城北城墙内的大佛寺。但如今寺内已经没有僧人居住,可以从侧面看出汉传佛教在当地的影响力正在逐年减弱。但在历史上关于贵德地区汉传佛教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至一首唐诗——《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塞口连浊河,辕门对山寺。宁知鞍马上,独有登临事。七级凌太清,千崖列苍翠。飘飘方寓目,想像见深意。高兴殊未平,凉风飒然至。拔城阵云合,转旆胡星坠。大将何英灵,官军动天地。君怀生羽翼,本欲附骐骥。款段苦不前,青冥信难致。一歌阳春后,三叹终自愧。”从诗中可以看出佛寺规模的壮大,佛殿修筑在山脚下,而佛塔屹立于山顶,展示出当时汉传佛教寺院的庞大。结合该诗的写作背景,天宝十二年(753),哥舒翰率领军队收复了河西九曲之地,与其同行的边塞诗人高适,陪同哥舒翰来到了贵德西游佛寺,并登山上塔,眺望河山,有感而发,故作此诗。这说明在唐代的贵德地区就已经存在汉传佛教的身影。在之后的数百年里,由于该区域的汉族人口减少,汉传佛教的影响力也在削弱,直到明代河州四十八户移民到此,才使得汉传佛教得以恢复,到清代汉传佛教在贵德地区进一步发展,不过与藏传佛教相比较,其影响力有限,一般主要分布在汉族的聚居地区。
2.藏传佛教
清代贵德地区的藏传佛教可以分为“宁玛派”和“格鲁派”两大派系,为了进一步说明该区域文化职能的多元性,笔者在两个派别中各选一个代表性寺院进行阐述。
“宁玛派”寺院选取位于今尖扎县坎布拉乡的阿琼南宗寺。在清朝的康熙年间,康巴地区的佐钦寺的创建者班玛仁增大师来此修行,见这里风景秀丽,便在此修建了南宗寺。后来由古浪仓活佛主持寺院事务。历任主持的努力,为藏传佛教“宁玛派”在贵德地区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根据记载,该寺院人数最多时可以达到五百多人。
“格鲁派”寺院选取位于今贵德县河西乡瓦家村的瓦家寺,该寺的藏语名称为“瓦家扎仓彭措达杰朗”,翻译过来就是“瓦家扎仓圆满兴旺洲”,当地人因为其地点位于瓦家村,故也称其为“瓦家扎仓”。该寺院的活佛除了加毛活佛外,还有娘埃活佛、觉活佛和德吉活佛。在清朝雍正元年(1723)爆发的罗卜藏丹津叛乱事件中,瓦家寺中的僧人介入罗卜藏丹津事件,僧侣被绞杀,寺院被焚毁,而现在的寺院重建于1986年。但瓦家寺中幸免于难的僧人则在罗卜藏丹津事件后被清政府授予度牒,继续在贵德地区传播藏传佛教。据《青海记》载,当时有僧侣9人,他们都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传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总之,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共同构成了贵德地区的佛教文化,成为清代贵德地区多元移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道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
在清代贵德地区移民文化中,由于地域和民族原因,道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度小于其他文化,故将这两种文化放在一起叙述。
贵德地区的道教同样起源于明代,是河州移民带来的文化,其信众并不太多,直到万历年间修筑玉皇阁后才开始普遍流传,到了清代道教文化已经融入在贵德地区汉族的生活习俗中。汉族人民生活中的打庄廓、盖房子、婚丧嫁娶等,都会请道士来家中查看风水,选择黄道吉日,诵经祈祷,这些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现在贵德地区的人民生活中依然可以见到。
伊斯兰教进入贵德地区的时间应该是在明朝永乐年间,具体原因史书中没有详细记载,笔者推测可能与河州卫指挥使刘钊奏调回族迁至河阴的史实有关。贵德地区的伊斯兰文化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是贵德厅城附近;一是康屯和杨屯。据记载,在清代道光年间,贵德厅城附近建有一些清真寺,但在随后“甘陕回变”中大多都被焚毁,而信众(回族)被迁至西宁或康杨地区。而康屯和杨屯的伊斯兰教一直在发展,“甘陕回变”虽然使其遭到破坏,但在随后较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恢复。康杨地区的伊斯兰教信仰新教,即乾隆年间马明心创立的哲合林耶派。少数回族群众信仰老教,即格底木派。虽然教派不同,但丝毫不影响伊斯兰教在贵德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屹立其间的杨家清真大寺和康家清真大寺,正是这一文化传播的最好见证。
总之,道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虽然在贵德地区影响较小,但同样是该区域多元移民文化的组成部分。
(三)儒教文化
儒教文化,也可以称作儒学文化,主要分布在贵德厅城内,以河阴书院和文庙为代表,是清代官方文化的一种展示。
河阴书院,修建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其名称与所处的地点关系密切,在中国古代,“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河阴书院因地处黄河以南得名。其办学的宗旨,书院门口的对联将其阐释得恰到好处:“讲学以明伦,日所遵行,不越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穷经原致用,无非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在这副对联中,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观和经世致用的时代观,宣传了儒家的思想。在贵德厅所管辖的屯寨中也设有儒学机构,使儒学更好地在下层民众中传播。乾隆十二年(1747),西宁佥事杨应琚、知府刘洪绪和所千总彭韫,在刘屯、王屯和周屯分别设置义学。义学,是面向全社会的,无学费或适当交纳少量的学费,旨在普及儒学,使儒家文化深入人心。到了光绪年间,贵德地区的义学就达到十一处。至于义学的经费,则是由政府划分田地,设置学田,该地收上来的赋税全部用于学校,反映清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也从侧面反映出儒家文化的特点——官方推行。
文庙,又称孔庙或文宣王庙,是专门用来祭祀和供奉孔子的庙宇,可以看作是儒学发展的标志。在清代,河湟地区对孔子的尊崇达到了顶峰,各地大肆修建孔庙。贵德地区的孔庙是由贵德厅同知安福、训导张玉成在嘉庆元年(1796)修建的,但在同知年间毁于“甘陕回变”,随后贵德厅同知蒋顺章于光绪三年(1877)重新修筑。文庙的修筑,一方面体现了官方对儒学的推动,另一方面体现了对教育的重视。不过,此时修筑的文庙核心建筑——大成殿与玉皇阁,呈现前后交错的态势,无疑使人感受道教与儒教的进一步融合,也是该区域内文化融合的一个缩影。
总之,贵德地区的儒教文化在官方的推动下发扬光大,成为该区域的正统思想,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儒教文化为清代贵德地区移民文化添加了不可或缺的新元素。
(四)民间信仰
贵德地区民间信仰的源头应该是前文提到的江左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变异,形成了独特的民间信仰文化。如果按地域划分,可以分为刘屯的文昌信仰、王屯的龙王信仰、周屯的二郎信仰。下面通过对这几个典型的民间信仰的分析,进一步论述贵德地区的移民文化。
刘屯的文昌信仰,是一种融合性的信仰,是将江左文化中的文昌信仰与当地的藏传佛教相融合形成的一种新的信仰文化。在漫长的文化融合过程中,人们为了实现精神有所寄托,准备在离刘屯不远的暗门处修建文昌庙,但不知为何最终却将文昌宫修筑在今贵德县河西乡的下排村。笔者在调研中听到了一段颇为传奇的故事,可以看作是民间用来解释选址变迁的原因。当年修筑文昌宫时所用的文昌神像是由传说中“能夹上簸箕升天,骑上板凳过河的仲家龙爷”[3]从遥远的四川梓潼县背回来的,放在原先准备建庙宇的暗门旁,可是谁知夜晚狂风大作,山洪暴发,将神像从暗门冲到了今天文昌宫所在地,当地百姓认为是文昌神发威,不满意人们的选址,要自己选择庙宇,于是人们便将文昌宫改筑在现在的位置。神话传说不足为信,但也可以看出文昌信仰在刘屯甚至贵德地区的影响力。文昌宫从整体布局来看是典型汉式风格的建筑,以正殿所在位置为对称轴,山门、牌楼及亭台楼阁都是传统的汉式风格,但其内部装潢和局部布局又体现了藏式风格。所以,从文昌宫的建筑上也可以体现出文昌信仰是汉藏文化融合的新型信仰。刘屯的文昌信仰除了表现在文昌宫上,还展示在一年一度的庙会之上。按照习俗,每年农历六月十九至二十四日是“文昌爷下庙巡乡”的日子,当地百姓会按照习俗进行接神、祭神的活动。这种活动一直延续至今,可见文昌信仰在当地的影响力之大。
王屯的龙王信仰,与文昌信仰一样也是一种新型的融合性信仰。以中国文化中龙的形象为原型,结合佛教和道教的理论,形成了一种新的信仰。龙在东方和西方文化中都有存在,不过二者形象有着天壤之别。西方的龙一般以黑色的形象示人,代表着邪恶与阴谋;而东方的龙是一种正义的化身,主宰着自然界。在龙的形象上,又加上了佛教的“八部天龙”之说和道教的五行八卦的理论,最终形成了龙王信仰。不过传入贵德地区后又与当地的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原龙王文化,这种文化从王屯龙王庙的布局和一些祭祀活动中可窥端倪。王屯龙王庙的整体建筑风格与内地的龙王庙相差无几,但其中的煨桑炉和壁画却有着浓厚的藏式风格,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王屯龙王庙的祭祀活动主要分为龙王池背水、青苗绿会和四月八会,在这些活动中都是由王屯和周边的藏族村落一起参与祭祀,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汉藏文化共同展示出相互并存、互相吸收而又各美其美、共同发展的姿态,形成了一幅和谐共存文化图。[4]
周屯的二郎信仰,是一种通过自身的内部调试以适应周围文化环境的一种信仰。从地理位置来看,周屯、刘屯、王屯有其独特的地方,周屯处于一种被藏族文化所包围的态势。明代的屯戍军从内地带来了江左文化中的二郎信仰,但一种单纯的汉族信仰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就必须对自己进行调整,使自己能与周边的文化和谐共处。首先,从庙宇的建设上,除了与内地二郎庙相似的设施外,还增加了唐卡、哈达、净水、壁画等体现藏传佛教文化的设施。其次,在神灵的设置上,二郎神由原先的武神、战神转变成为藏传佛教的守护神,普遍被周围的藏族群众所信仰。最后,体现在节日的庆贺上,每年的“四月八会”和“六月会”,周屯的人们都会抬着二郎神到附近的藏传佛教寺院去拜访活佛,这既体现了周围的藏族群众及藏传佛教对二郎信仰的认同,又可以更好地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
三、族群互动中的文化调适
“文化调适即是当外来作用足以改变生境性质的前提下,处于该生境中的民族文化在改变了的生境诱导下,作出了系统性的内部结构重构,使该文化对新作用的反馈由无序定型过渡到有序,从而达成与生境相适应的过程。”[5]随着明代移民带来江左文化,其依赖的环境,由江南水乡变成了青藏高原,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迫使其发生改变。除了依存环境的改变外,接触的人群也由单一的汉族变为了多元的民族。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江左文化在明清两代开始产生变异,以适应所处的环境,逐渐形成了以江左文化为基础的,融合藏、蒙、回等多元文化的新型文化,可以看作是文化调适的完成。众所周知,历史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合力形成的,从清代贵德地区移民文化的调适中,可以说文化的重构是多种因素重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