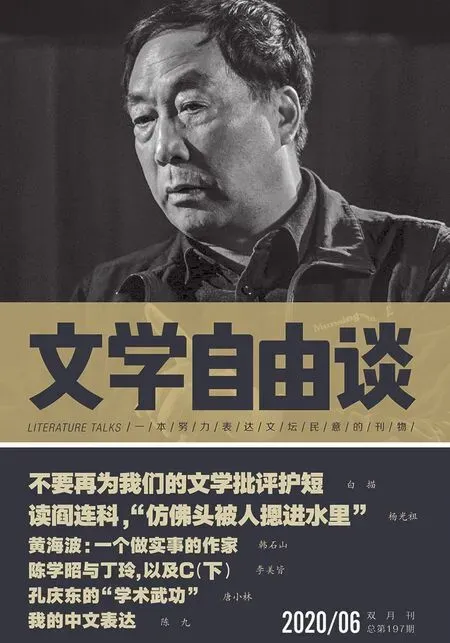陈学昭与丁玲,以及C(下)
□李美皆
(接上期)
4
不好意思,我曾经凭着直觉怀疑C是丁玲。
1948年6月15日,丁玲到了西柏坡。妇女代表们要在这里集合,然后一起出国去参加第二次世界民主妇女代表大会。此时丁玲已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毛泽东对她很肯定。16日,丁玲给陈明的信中写道:
他(指毛泽东)并且说我是同人民有结合的,我是以作家去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我是代表,代表中国人民。陈学昭也去,却只能做随员,因为她没有做工作,不懂得中国人民,不能做代表。
从丁玲这些话中,看不出对陈学昭的友善。
妇女代表团延迟到11月才出发。但8月,陈学昭就接到出国通知,不是去参加这个会,而是出国工作,不料临行又发生了变故。第二次世界民主妇女代表大会12月1日在布达佩斯开幕,丁玲出席了,陈学昭没有出席。
我隐隐觉得,丁玲信中透露出某种信息。尽管,1949年初她们在沈阳相处甚好,很谈得来,陈学昭走时丁玲还很是舍不得。
丁玲在新中国文坛的地位是显赫的,担任文协副主席、党组组长及中宣部文艺处长、《人民文学》副主编、《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陈学昭是全国文联理事、作协理事、浙江省文联副主席,虽然也很突出,但与丁玲不可同日而语。1952年丁玲获得斯大林文艺奖,更是迎来高光时刻。1955年以前,丁玲频频出国和参加外事活动,而陈学昭只出国一次。
其实丁玲与陈学昭都不那么适合当领导。既能写作好,又能当好领导的,女作家中大概最数铁凝了。丁玲与陈学昭则不能兼顾。陈学昭在担任浙江大学党支书时,因为处理问题有点简单直接和偏激,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丁玲好在有陈明帮她处理一些具体事务。
在胡乔木的鼓励下,陈学昭到茶区体验生活。1953年她血崩腹痛,只能弯腰走路,还坚持上茶山。陈毅和聂荣臻到杭州时,特意去看望她,并劝她到北京疗养,她都坚决不离开茶农。为了心无旁骛,她甚至把女儿留在北京直至1955年小学毕业。为深入工农,为工农写作,她真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了。同为作家,尤其是同为女作家,陈学昭怎么可能会不渴望写出一本如丁玲获得斯大林文艺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的书呢?当时,每一个有上进心的作家都想在某一个领域里,拿出一本“独门绝技”似的作品,作为交给党的答卷。
1952年夏,陈学昭到北京,应丁玲邀请,住到丁玲家里,在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春茶》,等于是驻所作家。陈学昭还在所里参加了第一次文艺评级,被评为文艺二级。陈学昭在文研所从事专业写作总共不到半年时间,1954年初,文研所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
和平环境下,丁玲与陈学昭依然密切交往并且成为好朋友——这在女作家之间是难得的。但我也读出陈学昭并不那么情愿到丁玲身边的味道。陈学昭本来住在好友家,有一天出去办事,回来好友说,丁玲派人来把她的行李物品搬走了。
……说她家里房子宽敞,要陈学昭住过去。丁玲专门给陈学昭腾出一间屋子,并询问了她正在创作的小说《春茶》的修改情况,帮她出些主意。(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29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陈学昭在丁玲身边,必然要天天目睹丁玲的风光,这种滋味会好吗?那么,丁玲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首先是她想团结一批作家,壮大自己的山头。当时是陈亚男跟妈妈一起搬到丁玲家的,而且陈亚男就睡在丁玲和陈明房间里的小床上。
待我渐渐长大开始明白事理,提起丁妈妈怎么会突然想着接我和母亲到她家去住宿这件事,母亲这么回答:不晓得她是风闻,还是有人吐露给她,抑或凭感觉吧,得知我在1942年批《三八节有感》时,为她说了好话,也许是表示友情吧,她待我热情。(陈亚男《我的母亲陈学昭》,244页)
作家孙犁始终坚持作家宜散不宜聚。丁玲是出于好心,但好心未必办成好事。曾在文研所工作的徐刚回忆这一时期的往事时提到:
当时文研所的条件不具备养这些老资格的大作家,如陈学昭、周立波等同志;工作上也没有必要养这些作家,而应该空出名额培养师资。没有条件养硬养就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这样那样的矛盾也构成了文研所改成文讲所的一个因素。(徐刚、邢小群《丁玲与中央文学研究所》,《山西文学》2000年第8期)
在徐刚看来,陈学昭在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激烈地批判丁玲,便是在所内不干具体工作,又因个人原因积聚了“私愤”。
使我怀疑到C是丁玲的,就是陈学昭的这次揭露与批判。
1955年8月,中国作协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在杭州的陈学昭被召到北京。
在8月13日的会议上,陈学昭发言,揭发了丁玲很多问题,一些内容是耸人听闻的,包括:丁玲在杭州跟她说,检查《文艺报》是“整了陈企霞,也整了我”;丁玲说:“你应该有一本书,草明、白朗都有一本”;丁玲说白朗历史上有问题,但仍被重视,历史清白有什么用;丁玲说“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说的,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是没有份的”;丁玲说洛甫地位不如李富春,过去犯过错误;丁玲憎恨周扬,在小组会上骂周扬卑劣无耻,见周死了孩子,心里高兴等等。
陈学昭的突然揭发,让丁玲又是惊讶,又是气愤,又是悲哀。老朋友怎么也会落井下石?善良的陈学昭怎么也从背后捅上一刀?后来丁玲在1956年8月写的辩正书中,专门用了很大篇幅来反驳陈学昭,认为她的揭发都是“捏造的事实,过火的认识”,“陈学昭的发言,不是造谣,挑拨,就是极力夸大渲染,歪曲当时情况”。
第二年,调查小组的丁宁去杭州,找陈学昭核对她揭发的那些材料时,她说:“我去年会上说的那些话都不作数!”(李向东、王增如《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丁玲“询问了她正在创作的小说《春茶》的修改情况,帮她出些主意”,与陈学昭揭发丁玲说“你应该有一本书,草明、白朗都有一本”,不正可微妙对应吗?这种帮助和鼓励的正解,是丁玲在关心陈学昭的创作。负解呢?则是丁玲在显示自己已有这样一本书,所以有资格来指导陈学昭,这既显示了自己的优势,又是在提示陈学昭的短板:你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而这,正是丁玲“一本书主义”罪名的风起于青萍之末。
1983年7月,陈学昭撰写《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一文,回忆了她1955年到北京学习并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的经过:
这天下午,小组长Y叫我进一间小屋子里,该是这次学习的领导同志们的办公室吧。进门靠右边有一对沙发,他先坐在靠里的一张上,要我坐靠外的一张。他开始对我说:“丁玲和你这么要好,你们平常谈些什么?”我回答:“没有谈什么,她忙她的,我忙我的。”这实在是真实的情况。“你好好想想,她和你谈些什么?你不讲,对你没有好处!”Y的口气很严厉,带着威胁。接着,他站起来,我也站起来,向门外走时,他站在门外的走廊上,对我说:“你好好想想!”
次日午后,这位小组长又找我到那间办公室里去,副组长也进来了,坐在一张木椅上,面对着我。组长和我还和昨天下午那样分坐两张沙发,我坐靠外的一张,他靠里。Y对我说:“你想过没有?丁玲平常对你说些什么?”“说些什么?”我反问了他一声,他呆了一下。我说:“我忙着写《春茶》,她鼓励我写好工农兵,她说白朗已写出了一本,草明也写出了一本,她也写出了一本。”Y不出声了,而副组长在微笑着。“好吧,再去想想!”Y站起身来,说,我也就立起来,向门外走了。
过了两天吧,这天下午,通知召开大会。大家都按时进了会场。我进场时,前面都已坐满,我坐在最后几排里。主持大会的同志宣布第一个发言人是Y。接着,Y走到台前,声称目前重要的任务是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并说这是“陈学昭揭露的”……他刚说完,报名发言的人一个又一个。我站起来要发言,几次被阻止。终于,我不管台上的人还在讲话就站了起来,在自己的座位上大声讲了,我把Y如何逼问我和丁玲同志之间谈过些什么话,我对Y如何回答等等,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并坚决表示对党对同志们负责:丁玲同志没有讲、没有提倡“一本书主义”,并声明这样的会,我拒绝参加。
我刚说完,正要走出会场,会场里有好些人站起来,也有人在议论,会是开不下去了。我不管作协这次学习后来搞些什么名堂,只在宿舍里看点书,仔细想想这两三年来文艺界所经过的事情,感到这一次批判所谓“一本书主义”,其实是早有安排的。
陈学昭女儿陈亚男也回忆母亲曾对她说:
实际上,我们这些女作家,平时确实各忙各的,根本没时间串门。大概就是1952年初秋那次到北京,丁玲把我们母女接到她住处对面留宿,估计就是那时给人留下印象——我与丁玲关系挺好的。可是这一次不同了,我们只有吃饭时在一起,两人谈起来,我说正在修改长篇《春茶》,丁玲鼓励我把《春茶》写好。显然,我是被盯上了。(陈亚男《我的母亲陈学昭》,245页)
陈学昭所说的“这一次”,就是指当时正在进行的学习,开始是为了批判胡风反党集团,编成小组进行。陈学昭写道:
记得当时有个规定,不能外出串门,这大约是为了防止彼此之间交谈情况,互相包庇、隐瞒。每天都是学习,或是自学,或是小组会,或是大会批斗,或是小组长找去谈话,事实上是动员交代。
不管怎么说,“陈学昭揭露的”,就这样使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达到了高潮。
亲历者徐刚说:
陈学昭同志的发言揭发的材料最多,也批判得最激烈。我感到她有泄私愤的味道。(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120页)
“私愤”何来?徐刚没有具体说。就笔者看到的或许可以导致“私愤”的事实,可以列举一二。
1951年7月31日,丁玲作第二学季“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单元学习总结的启发报告:
小资产阶级想方设法篡位,想以小资产阶级统治世界,改造世界。我们警惕性要高。……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 虽写的是小资产阶级, 但就以小资产阶级的面目出现。而我们却往往更容易为其他的作品所欺骗。(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216页)
这是对《工作着是美丽的》公然以小资产阶级面目写小资产阶级进行点名批评。
丁玲1983年12月8日给陈学昭的信中却说:
你的《工作着是美丽的》是一本好书,五十年代初出版时,有人对你提出较多的苛求,我是不同意的。文学作品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和表现方法,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读者群。只要能引人向上,能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就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一本书,可能工人农民不喜欢,而知识分子读了却能引人入胜。一本书也许老革命家欣赏,而工人农民却一时不能领会,这有什么重要呢?我们不能要求每本书都写得像《圣经》,也不能要求每本书都能雅俗共赏。《工作着是美丽的》一般知识分子都能欣赏,而且能从中得到教益。
陈漱渝在《宽厚的人是美丽的——丁玲与陈学昭》中针对这段内容评说道:丁玲当时是中宣部的文艺处长,她的话是有影响力的。
《工作着是美丽的》初版是1949年,再版是1954年,丁玲说“五十年代初出版时”,不知是指哪个版本。若是后一个,则当时丁玲已辞去文艺处长之职。但无论如何,丁玲当时的“影响力”仍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正反两方面的说法一汇总,却很难确定是什么样的“影响力”。也许褒贬都曾有过,因为场合不同。人不会只用一种腔调说话的,尤其在一个政治气候特别炽烈的年代。在丁玲当时的位置上,根本没有可以随便说说的话,不知道她当时意识到了没有?
丁玲也有女人的感性,肯定会留下很多“口实”。一旦清算她的机会到来,那些嫉妒她的人,会趁机发泄;那些为她的骄傲所伤的人,找到了以牙还牙的机会。一个具有成熟的政治头脑的人,即便面对沙僧这样的群众,都能想到“野百合也有春天”,但丁玲显然不是这样的人。
丁玲被批判后,在给儿子蒋祖林的几封信中,表露了异样的心情。
一封信里说到巴尔扎克的《贝姨》。她称道巴尔扎克对嫉妒的化身贝姨这个典型人物刻画之深刻,谈到人的嫉妒心之可怕,出于这种阴暗心理,可以不择手段。(李灵源、蒋祖林《我的母亲丁玲》,9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
看到这里,我脑子里出现了陈学昭,同时想到了丁玲与陈学昭文坛地位的种种差距——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永远无法求证了。
陈学昭是个颇有文明教养或者说有法式优雅的人,她给自己的侄子写信都称“您”。 陈学昭也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她有很多亲情浓浓层次很高的朋友,比如张琴秋、孔德沚(茅盾夫人)、陈宣昭等。1955年接待萨特与波伏娃时,鉴于他们俩的特殊关系,陈学昭特地关照工作人员,给他们安排一套有两个房间的房子,两个房间要既独立又相通。这种人性化的细节,绝非“女斗士”所为。
那么,陈学昭为什么在1955年悍然揭发丁玲?丁玲与陈学昭之间,只是因为嫉妒、文艺批评等,就变成了塑料花姐妹吗?我总怀疑有更蹊跷的原因。因此,我联想到了使陈学昭爱情命运发生转折的C,她会是丁玲吗?
5
其实我求证的过程远比上文所写的曲折。我最初只看到陈学昭说,是一位女“同行”,且与“李某某”亲近的,根本不知道她的代号是C,也不知道“李某某”是李立三。
当时同在东北的女作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丁玲。当看到这位女“同行”被称为C时,我就努力求证丁玲有没有可能在哪里被称作C,无果。又看到“李某某”是李立三时,便求证丁玲与李立三有没有密切的交往,还是无果。那么,这个C如果不是丁玲的话,又会是谁?
我不是一定要求证C是丁玲,相反,我更想排除C是丁玲。我不是丁玲的什么人,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长期的“相处”中,已经产生了灵魂上的亲人的感觉,我对丁玲的人格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和相信,绝不愿意这种把握和相信被打破。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失去信心,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如何排除C是丁玲的可能呢?如果能找出C是谁,自然就排除了。
这个问题如此困扰我,使我揭不开谜底就无法开始关于丁玲与陈学昭的任何写作。从陈学昭和丁玲的资料中,我已经找不到什么线索了。我改变了路径。既然李立三是确定的,那么,我可以从考察李立三那一时期的活动入手,来探寻与李立三有交往的女作家。
1946年,草明到东北不久,在哈尔滨曾找过时任东北局干部部部长的林枫,要求下乡搞土改,像周立波、马加那样任区委书记或区长。林枫思索再三说:“去农村的作家已经很多了,去部队的也不少,惟独没人去工厂。今后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城市领导农村。李立三同志刚从镜泊湖发电厂回来,说那里工作开展得很好,你到那里去深入工人生活吧。”(《草明,工业题材写作的奠基人与开拓者》, http://www.lnzx.gov.cn/lnszx/Newspapers/wenshitiandi/2015-01-13/Article_42697.shtml)
这是我首先看到的李立三与作家的关系,尽管间接到几乎无关,但我还是得到了某个提示码。继续查资料我发现,的确,草明到镜泊湖发电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以此为原型写出了第一部描写工业题材的中篇小说《原动力》(1948年6月出版)。李立三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草明是工业题材的代表性作家。1951年8月,草明又出版了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火车头》,这也是她的代表作。1955年所谓陈学昭揭发丁玲的“一本书主义”的由来,即丁玲对陈学昭说“你应该有一本书,草明、白朗都有一本”,草明的这一本,就是指《火车头》。
接下来看到的资料,使我豁然开朗。《原动力》写完后,蔡畅交给草明一个任务:辅导毛岸青提高中文水平。毛岸青刚从苏联回国,住在同样从苏联回来的李立三家里。因为离开中国太久了,他的中文已经生疏,组织上曾安排他到中文系学习,但他在同学中太引人注目了;当时东北的局势还不稳定,安全起见,东北局保卫科建议他不要在外面上学,而由草明到住处(即李立三家)来辅导。
陈学昭写道:“是那位同行,她和李某某很亲近,她对李某某说我去巴黎不是为工作而是为了个人事情。”
草明是“左联”时期的老作家,1941年“皖南事变”后,与丈夫欧阳山撤退到延安。草明也曾经很有锋芒,比如在《创造自己的命运》一文中,毫不留情地批判那些攀附老干部甘心回归窑洞家庭的女性。草明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深入工厂,文学创作完成了转变。草明也是在延安因丈夫移情别恋于她的亲妹妹而离婚,后来孑然一身,这与陈学昭命运几乎完全一样。但陈学昭差点不是这样,只是因为一个偶然,才成了这个样子。
1952年10月之后,丁玲因腰痛到旅大(即现在的大连)和鞍山去疗养,陈明全程陪同。疗养期间,草明前去看望,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草明似乎并不瘦,不过更干了。我的确是同情她的,不过我心里想,我母亲29岁就开始独身,到现在已经74岁了,身体还那么健康呢!
丁玲对草明的同情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方面,丁玲确实比草明和陈学昭幸福。陈学昭虽然最终还是不幸,但她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在她最后一次出国未遂之前,因为蔡畅的赞赏,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蔡柏龄,非常优秀,还是独身,与陈学昭有故事。“蔡大姐赞扬柏龄的话已经传遍了,几乎党内外人人都知道,而且总是牵连着我。”有故事的人,尤其是故事即将迎来幸福结局的人,对于匮乏者是极有可能形成刺激的。
熟悉文坛运动史的人,一定联想到了一些因为某种揭发(至少是原因之一)而瞬间坠入地狱的人,比如老舍。看来,某些人会做某种事,并不是偶然的。有的人一生的遭际就验证了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很容易为其做出开解:虽有可恨之处,但毕竟是可怜之人呀。细想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可怜,就要忽略其可恨吗?人类精神的全部斗争,一代一代坚持不懈,所指向的不就是那可恨之处吗?它们或许看起来并不多,然而已经够人类辛苦和为难的了,何苦还要有那么多轻描淡写的原谅呢?
我素来是不愿意跟研究对象的亲近者发生联系的,宁愿自己费劲去查资料。我不能说不信任人家,那就说不信任自己吧;我是怕自己受到一些主观因素的干扰。但是这次,我觉得有必要问个清楚,毕竟,我能确定的还只是C这个符号而已。我通过热心的朋友联系上了陈学昭的女儿陈亚男,忐忑地打电话过去。她的爽利明达,超出我的预期,甚至使我对陈学昭的感觉都提亮了许多。我相信,家教这个东西,一定是言传身教的结果;这样的一个女儿,绝不是一个阴暗逼仄小里小气的母亲能够培养出来的。我谨慎地用了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来代替《工作着是美丽的》中的陈学昭和何穆的化身,陈亚男则直接说的是陈学昭和何穆。我感觉可以放松地跟她交流任何关于她母亲的问题,她是心里没墙而敞亮的人,绝不人为设限,所以易于沟通。
我原本就是一个不会绕弯子的人,何况又凭直觉判断,跟陈亚男不必绕弯子。于是,做了必要的说明后,我直接问:C是不是某某?她说,是的。正是我喜欢的直接和简洁。我说,您介不介意我在文章中直接写出来C是谁?她沉吟了一下说,还是不要。我说,好的,我尊重您的意见。
我告诉她,我是有多么紧张,担心C是丁玲,所以才欲罢不能地探究;这下我放心了,真心谢谢她。她说,丁玲是一个大气的人,她不会做这种事。她还以同样的真诚说,感谢你对我母亲的研究。她听说我自己从旧书网上买她和她母亲的书,便着急地说,不用买,我给你寄。我说已经买了。我不好意思再跟她说,因为买的是旧书,我放在微波炉里消毒,差点起火。几天之后,我还是收到了她寄来的书,在扉页上特地贴了一张纸,那是她手写的订正,并且附了短函,告诉我参考哪篇文章。我还跟她谈到是什么机缘使当时的C跟李某某关系较近,她说话能影响到他。这也解开了她心里的一个疑惑。
陈亚男说,蔡柏龄当时有女朋友,一个为他打字的女人,虽然他们尚未结婚,但她也不会那么容易放手的。陈学昭出去是做妇女工作,并非为了跟蔡柏龄结婚,她也知道他有女朋友,只是想当面跟他说清楚当年是怎么回事。即便她去了他们也不一定会结婚,她还是要回来的。她还有统战任务,就是把蔡柏龄这个科学家劝回国。
饶是如此,又令人有点释然。不过,果真在巴黎见了,结局谁知道呢?
6
再回到1955年的丁玲与陈学昭。
我已经排除了丁玲与陈学昭存在过节儿的可能性,那么,陈学昭为什么会如此激进地批判丁玲呢?
首先,我觉得这是女人的感性使然。女人的感性使陈学昭想到啥说啥,毫无遮拦。她大概想得很简单,从延安开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使她习惯了,根本没想到对于丁玲的批判是那么严重的一个事件。陈学昭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苏联,写苏联养鸡场:“产蛋室如果正好挤满了,那么要生蛋的鸡就会在产房门口等待着,他们绝不随地乱生蛋。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鸡也被训练得这样聪明守秩序。”这固然是可笑,但陈学昭不是一个虚伪的人,我从中看到的是她可爱的天真。内心越诚实的人,说话越直率和不考虑后果。
其次,我觉得这与当时的文坛格局有关。陈学昭在对丁玲的揭发中几次提到周扬。当时丁玲与周扬的矛盾是众所周知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丁玲的这场批判的始作俑者就是周扬。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是高过丁玲的。那么,陈学昭对丁玲的揭发,到了周扬那里,就是一种“立功”的表现。周扬此后确实对陈学昭非常关照。1957年陈学昭被打成右派时,周扬曾想保她。1961年,周扬夫妇到杭州,约见了陈学昭,陈学昭的处境马上得到好转,第二年就摘掉了右派帽子。
陈亚男说,这件事搞得陈学昭心事重重,一直想找机会跟丁玲解释。紧接着,1955年9月,萨特和波伏娃应邀到中国访问,陈毅指定陈学昭陪同。波伏娃提出要看望丁玲,也是陈学昭陪同去的。
见到丁玲,母亲自然想起平时就困扰着她的“一本书主义”这件事,可是毕竟有任务在身,她只好放弃了这次机会。……过了一年,母亲在第二期《文艺报》上见到一篇专论——《斥“一本书主义”》,仔细阅读后,母亲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陈亚男《我的母亲陈学昭》,247页)
陈学昭的揭发,自然是令丁玲寒彻心扉,但陈学昭内心也不轻松。1956年夏天,中国作协派丁宁去杭州找陈学昭核对材料,住在陈学昭家中。一天夜里,丁宁从睡梦中惊醒,只见陈学昭身着白色睡袍站在她的床前,充满痛苦和悔恨地说:“我去年会上说的那些话都不作数,都不作数。”
却不料又过了一年,即1957年,母亲在浙江成了右派分子,丁玲同志在北京成了右派分子之后去了北大荒。现实十分严酷,非但没有把她们拉拢,相反却隔离得更远。1955年一别,两人再也没有联系。(陈亚男《我的母亲陈学昭》,247页)
1957年,陈学昭因仗义执言浙江省委“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被打成了右派。周恩来和周扬曾请浙江不要把陈学昭划为右派,还是未能改变结果。她曾向周恩来反映茶农问题等,早已得罪有关方面。对陈学昭的处分是: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生活靠写作自给。陈学昭得知这一结论后的心理活动是:“如果一九三七年我再去巴黎,在东方语言学院工作,最大的罪名也不过是脱离政治,但政治可以躲开,战争却是躲不开的。”(陈学昭《浮沉杂忆》,61页)她说的战争躲不开,是指1940年巴黎沦陷,法国也在二战的乌云笼罩之中。当然,那时中国也是在战争之中。
丁玲受的处分与陈学昭基本一样。但陈学昭1961年摘帽了,丁玲直到“文革”结束时才摘帽。1960年7月,陈学昭得到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的通知,但省文化局告诉她不要参加。丁玲也得到通知,并且被告知可参加可不参加,她参加了,却只是遭到一场冷遇。“文革”中,无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都被批为“大毒草”。
……直至二十四年后的1979年,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闭幕晚餐会上她们才见了一面。(陈亚男《我的母亲陈学昭》,248页)
当时是邓颖超出现在晚宴上,大家都向她奔去。陈亚男写道:
就在这时,母亲忽然看到了让她牵肠挂肚的另一个人——丁玲同志。丁玲妈妈在我们左前方正朝着邓妈妈所在的餐桌走去。情急之间,母亲与丁玲妈妈匆促地相互招呼,显然此处不是说话的时机和地方。这次虽然没交谈,从报纸上,两人都已获悉各自的处境得到明显的改善。(陈亚男《我的母亲陈学昭》,248页)
陈漱渝写的是:丁玲告诉陈学昭,这两年周扬见了她,客气了一点。——看来,她们还是有交谈的。
电话中我小心地问及陈学昭为什么揭发丁玲,陈亚男说,她没有听母亲讲过这个事情,母亲很少讲这方面的事情,但她表示过,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没有存心害过谁。
虽然陈亚男所写的,基本是把这件事当作一个误会或误伤,但是,她在关于母亲的回忆录《我的母亲陈学昭》一书中,特辟一章《与丁玲是知友》,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丁玲与陈学昭的友谊,可见其用心良苦。从她亲切地称呼“丁玲妈妈”,从她对二人友谊的尽心描述,可以隐隐感觉到她的某种心理。她是一个善良、正气且正统的人。
1982年,《文艺报》第三期发表丁玲的《五代同堂振兴中华》。丁玲在文中把现有中国作家分为五代,并且把陈学昭归为第一代,自己归为第二代。陈学昭看到后很感动。
母亲感觉到丁玲同志思想开放,豁达明理,感觉到评论的大气和权威性。“她太谦虚了,把她自己放在第二代……”母亲感慨丁玲文品高尚,慨叹她思路这么快就跟上形势,慨叹之余,心头的遗憾依然未能释去。(陈亚男《我的母亲陈学昭》,249页)
1983年5月,丁玲到杭州开会,探望了陈学昭。丁玲的姿态是很高的。同为女人,她或许也是出于对陈学昭孑然一身的同情。丁玲有她的脾气个性,但肯定是一个大气善良的女人。
陈亚男写道:
两位女作家痛痛快快地倾谈了一个下午。分手的时候,她们紧贴着对方的面额,相拥而别。(陈亚男《我的母亲陈学昭》,249页)
这个年纪,见一次少一次,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事实证明确实是),毕竟同在革命阵营和文坛并肩了大半生,无论有过怎样的纠葛,这样的缘分,也是修得的“同船渡”。
丁玲去世后,陈学昭在《别时容易见时难》中写道:
丁玲同志坐在一只小沙发里,斜对面的一只沙发,黄源同志坐着。我的房间极小,我要把自己坐的木椅子给陈明同志坐,他客气,坐在小桌子边的一只小方凳上。丁玲同志和我,两个人都凝视着,她凝视着我,我凝视着她。我觉得她比以前胖了些,但精神饱满。
陈漱渝写道:
两位老友相互对视,似乎给人以“纵使相逢应不识”的感觉。不过,1983年丁玲的境遇已经有了很大改变。虽然为她彻底平反的中组部通知直到1984年3月才下达,但丁玲早已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了副部级待遇。根据陈学昭的描述,她当时的境遇仍很潦倒,以致陈明来家只能坐在小方凳上。
就在这次会见时,丁玲谈到她当年4月曾应法国政府邀请到巴黎访问,碰到了著名作家西蒙娜·波伏瓦。……波伏瓦特意托丁玲转达她的问候,这对于潦倒中的陈学昭无疑是一种安慰。丁玲告别时坚决不让77岁的陈学昭送她,一边健步如飞地下楼,一边说:“我会再来看你!”不料竟成永诀。
1983年8月,陈学昭得知有人在大量复制她“文革”中的“检查交代材料”(拨乱反正后本应销毁),即请有关方面查处。关于此事,《人民日报》12月5日发表文章《还想秋后算账么?》。丁玲8日读到此文,马上给陈学昭写信表示愤慨与同情,并高度赞扬了陈学昭一生的道路和写作。丁玲的严词足以证明,尽管受了几十年苦,归来依然是那个敢说话的丁玲。当然,丁玲的愤慨还在于,对待这样的问题,经历过的人都会有同理心,反右、“文革”中,哪个没有一堆“检查交代材料”呢?哪个不忌讳曝光呢?
她们的晚年还在创作,主要成就是回忆性写作。铭记陈学昭一生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下卷和她曾经寄予厚望的《春茶》的下卷,虽然是拨乱反正后出版的,却是在反右以后偷偷写作的。《工作着是美丽的》1982年又出了续集,但较为粗疏,几乎就是提纲。历史的境遇使她的人生只来得及写个提纲了。她坦陈:“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足足有十多年没有可能拿笔,实在荒疏了,即便写一点什么,那是生病起不来床,在床上偷偷地写的,事实上,我已不会写什么了……”(陈学昭《天涯归客》,68页)她看了自己1929年即五十年前所写的鲁迅,还感到亲切生动,情不自禁地感慨:“然而现在要我写,却再也写不出来了。”(陈学昭《天涯归客》,69页)我问陈亚男,韦君宜的《思痛录》您看过吗?您觉得母亲最后有没有什么反思?她说,没看过。我想,陈亚男是一个朴实而守分的人,可能不会想那么多。
丁玲1984年开始筹办《中国》,向陈学昭约稿,陈学昭寄去一篇怀人文章。1985年2月4日,丁玲给陈学昭写信,寄回她的稿子,同时寄上一本《中国》。她在信中说,《中国》编辑部觉得文学性少了一点,不愿发,我又把它转到《光明日报》,他们也退回……信中还提到,蒋光慈的爱人吴似鸿在浙江绍兴,一直守寡,生活艰难,希望陈学昭能给予帮助;而且,她已经写信给吴似鸿,请她去杭州找陈学昭。“我以为你还是能理解她同情她的。至少在精神上有点慰藉,你不嫌我太唐突了吗?她也不一定来,如果看你,望接待她一下,如能在文联说一句半句话,也许有些效果。”丁玲不揣冒昧地请陈学昭关心吴似鸿,说明她没把陈学昭当外人。丁玲也不认识吴似鸿,只是吴求助于她,她就尽力帮助罢了。
1986年3月4日,82岁的丁玲去世,80岁的陈学昭写作悼文《别时容易见时难》,结尾写道:
自从3月4日起,我天天想起她!我们从1957年开始就完全被隔绝了。丁玲同志!我们何时再见呢?!你在哪里?我只能梦想着您!我只能在梦中再见您!在我的心里,您永远活着!
这些话,只是煽情吗?不,我看到的是她内心的翻腾,是老友的去世对她的触动。
陈漱渝写道:
丁玲虽然对陈学昭的发言(指1955年的批判)甚感诧异,但她了解那个畸形岁月对人性的扭曲。她本人不也做过违心的检查,给自己无限上纲吗?于是她选择了对陈学昭宽容,因为她明白,宽容是美德,而不是懦怯。她不愿意轻易割舍革命岁月中结成的珍贵情谊。这种情谊来自于今生的缘分,来世不会再有。陈学昭也感激丁玲对她的宽容,她在回忆文章中说,丁玲根本没有计较被她揭发这件事情,甚至谈到周扬时也是微笑着的。宽容者的微笑,是人世间最美丽的表情。
但我相信,陈学昭内心有个梗从未完全消融。即便没有说出来,这也是有良心的人的心债。所以,她才会在丁玲去世后的那段时间天天想起她。
人老去,往往会出于花好月圆的愿望,做一些“倒带-修带”的工作,好把一生的句号画圆。她们的晚年,都有往回“倒带-修带”的心态和言行,都曾努力粉饰友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仍然反对某种善意的涂抹。老来落幕,砖变成蛋,外光内软,固然结局圆满,可是,真相在哪里呢?好心善意不能代替事实真相。
我也想顺应这种善意,然而,终究觉得,真是善的基础,首先是要真。如果不以事实为依据,只能带来历史认知的更大的迷失。
我还发现,陈学昭和何穆离开延安又回来这件事,在陈学昭和何穆各自的资料中都是不一样的。陈学昭自己坦言,他们是因为不能适应延安,尤其是何穆在筹建中央医院的过程中与周围产生矛盾,才离开延安的。
关于陈学昭的文章中说:
那个时代社会给予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是那样的狭窄,时隔一年多后,1940年12月底,陈学昭、何穆这对年轻夫妇,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从重庆折回了延安。当初离开延安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再回到延安,否则,何穆临走时怎么也不会把自己带来的包括那台手提式X光机在内的一些医疗器械,作价800元卖给了边区医院。(朱鸿召《留洋作家陈学昭三进延安》)
关于何穆的资料中,则说:
1939年7月底李富春通知并委托他筹建中央直属医院。……9月下旬,何穆受组织委托,亲赴重庆招聘医护人员和采购药品及医疗器械。
何穆到达重庆后,得到了主持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的周恩来的热情支持和帮助,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完成招聘人员和购置药品及器械的任务。周恩来亲自和到延安工作的医务人员谈话,与何穆一道制定了返回延安的方案。1940年底何穆回到延安,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办公厅主任王首道宣布中央决定:任命何穆为中央医院院长。(《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建校70华诞缅怀何穆同志》,http://szztjy.czmc.com/info/1014/1091.htm)
性质不同的两个版本,你信哪一个?当然,结果是一样的,他们最终都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了。但过程的曲折,是否一定要捋直呢?
何穆回转延安,肯定是与中央医院院长的任命有关,陈学昭所写可以印证:
H(即何穆)愿意再去延安,因为收到了傅连暲医师的信,说中央医院的院长还留着等他去当。(陈学昭《天涯归客》,157页)
傅连暲可不是普通的医师,他是中央总卫生处处长,相当于卫生部长。
丁玲与陈学昭的晚年友谊当然是积极的。在她们之间,都有一种想要圆满的愿望,也说明对于彼此还是基本认可的。这不是对任何人都能做到的。
1949年7月,在北平共同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丁玲、陈学昭、草明、曾克四位女作家留下了合影。她们都是去延安的女作家,都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都经历过创作的转型,都想交出自己的一份文学答卷……她们是很多历史的共同在场者,个人史的重合处也很多,这,原本是多么难得。谁能想到,她们会有一些这样的分叉与聚头呢?
我跟陈亚男谈到了女作家们的这次同框。我说,看起来每个人都是那么自然。陈亚男说,陈学昭是那样的,心里有数,但不会在面子上过不去。
陈学昭确实在《心声》中说过:“我对伤害过自己的人的态度:误会伤害,可以原谅;存心伤害,不能原谅,但不报复。”陈亚男说,1980年代C到杭州,与陈学昭见过,就是淡淡的一次见面而已,没有什么深入交谈。陈亚男当时不在家,没见到C。
她们所处的是一个动荡的大时代,在剧烈冲撞的历史环境中,人性会复杂得多,有些东西是处于“小时代”的人无法感受的。出于一种共情性和带入感,我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置换到那个时代自问:如果是我,会怎么样?会比她们表现好吗?我觉得,自己很难小心翼翼把话说得令各方面满意,在各种运动中不可能轻松过关,唯一能守住的底线,就是不主动害人罢了。
丁玲去世五年后,陈学昭也去世了,享年85岁。这一代革命女作家都很长寿,她们的生命力之顽强,一如她们的精神力量之强大。
陈学昭留下丧事从简的遗愿: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骨灰撒入钱塘江。这种简洁令我激赏。
林白曾写道,她的一位女同学认识陈学昭,她这样描述陈学昭的家:房子里空空的,只有孤零零一张桌子。
陈学昭的大归,总是顽固地令我想到这个情境:空空的房子,孤零零的桌子……(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