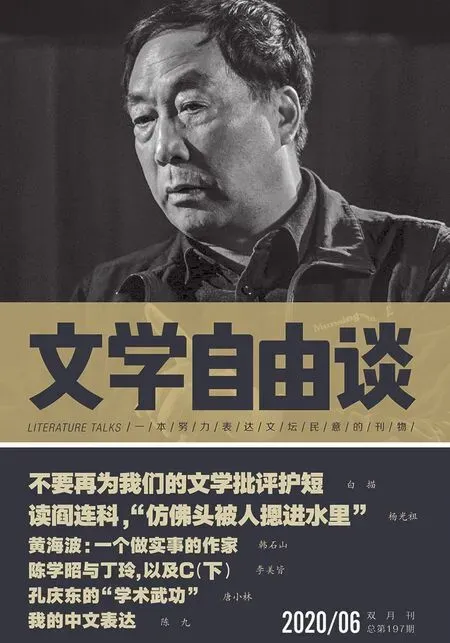也谈邵燕祥先生的身世、学历与文笔
□萧跃华
韩石山先生大文《邵燕祥先生的身世、学历与文笔》(载《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4期),于邵先生去世第三天在“文学自由谈”微信公众号上推送,可谓读者了解邵先生其人、其文的“及时雨”。国庆前夕,我慕名请韩先生为某史料作题跋,两次造访他的潺湲室。韩先生翻出拙编《昏昏灯火话平生》(三联书店,2019年4月)给我看,上面又是横线又是批注,足见他撰文时参考拙编做足了功课。韩先生说:“这本书编得不错,代表了邵先生的水平。”我明知这话奖掖成分居多,但未能免俗,心里乐呵呵的。
我不知道算不算邵先生的忘年交。我曾一本不落地搜集了邵先生的全部大作,并逐一请邵先生签名题跋,然后撰写简短书话。我们合作的《旧锻坊题题题·邵燕祥卷》(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就收入邵先生大作九十七部。2013年以来,我跑过邵寓至少五六十趟,还都不是一般的蜻蜓点水,每次就书人书事等话题有较长时间的海阔天空。邵先生突然辞世,韩先生预期他的文章“若错得离谱,我倒是希望邵先生拍案而起,怒斥荒唐”的愿望落空了。我作为邵先生逝世前两个月授权征集、选编、注释《邵燕祥书信集》的晚辈,有义务就韩文中语焉不详、稍有出入处作适当补充和修订,进一步丰富、完善邵先生的“身世、学历与文笔”,以告慰邵先生的在天之灵,不知韩先生以为然否?
身世——“于无家处有乡愁”
邵先生1933年6月10日出生北平,祖籍浙江萧山。祖父邵嘉谋(1864—1931),字勉卿,八岁读村塾,勤学不辍;屡试不第,设馆授徒;而立之年不再应试,夫妇以耕织所得培养三个儿子。蔡东藩先生遗文《邵勉卿君行述》记载:勉卿公急公好义,牵头集资修补西徐坂、茅潭坂两处塘圩,修缮从本村到临浦镇的三里官道,得到乡亲们称道。“惟生平俭于自奉,蔬食未尝饱,布衣未尝暖,家人或劝谏之,则慨然曰:‘时丁荒乱,遍野哀鸿,吾侪得免冻馁足矣,吾宁出有余以活人,毋专图己活也。’”
积善之家,德泽后世。综合《邵燕祥生平自述》《胡同里的江湖》《邵燕祥诗歌创作年谱》等权威资料可知——
大伯邵骏(1883-1970),字步超。早年在清末著名企业家叶澄衷先生出资创办、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任校长的上海澄衷学校供职,提携仲弟到沪读书。抗战胜利后,著名学者马一浮先生主持的四川乐山复兴书院南迁杭州,大伯晚年即长期在复兴书院工作。
父亲邵骥(1891-1964),字志千。1908年入上海同济德文预备中学,1911年入上海同济大学医科,毕业落户北京。1918年任北京大学法科门讲师,教授德文文学和作文,兼任北洋政府天津陆军医官学校教官,后供职南京政府交通部北平档案保管处、山东烟台兼龙口航运管理处。抗战期间,赋闲北平。抗战胜利,托庇胞弟出任南京政府联勤总部北平总医院上校军医正。新中国成立,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教育处、人民卫生出版社工作。
三叔邵驹(1906—1970),字季昂。1925年浙江医专毕业,同年2月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特别支部书记,继任国民通讯社社长。1926年9月26日,与社员姜长林、杨尚昆、周德洪、赵冶人同时被军阀孙传芳逮捕。社员旋即交保释放,邵季昂经胞兄营救八十多天后出狱,错过了原定11月与谢雪红(首任台盟主席)、杨尚昆等同船赴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的机会。他不顾家人劝阻,奔赴武汉找党。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南洋并退党。抗战前回国,官拜国军联勤部军医署供应司少将衔司长。上海解放,代表国军向陈毅部办理移交手续后,被安排至浙江省卫生厅工作,后逐级下放至萧山临浦卫生院。“文革”中不堪凌辱自杀,1979年平反。杨尚昆曾派人到萧山了解其情况。
母亲程瑛(1908-1986),家谱记载“继北平承斌公幼女”。邵父原配朱氏,来北平后患精神病送还萧山,由伯父一家监护,1942年病故。邵外祖父承袭“奉国将军”爵,抽大烟(鸦片)抽光了产业。邵母说不清楚属哪一旗,也从不愿提及满族出身。她以为丈夫前妻亡故,却不知道他一直按期寄钱供给前妻。
韩文“身世”说,五处可商榷:
之一:“不过,看样子不是去了德国人办的医科大学,多半是去了德国人在上海开的医院,从最基本的医疗事务做起,一步一步做成医生的……邵先生的父亲,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北京城里做事。”
邵父科班正途出身,一毕业就落户北平。
之二:“这个母亲,不光是有文化,还是个大家闺秀。”
邵外祖母三十多岁出嫁为妾,三十八岁生邵母,不久老头子病逝,寡母孤女被前房儿子赶出家门。外祖母带着伶仃幼女在禄米仓被服厂做“缝穷女”。邵先生看到母亲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写的《粥厂巡礼记》剪报,推想“早年母亲一定有过牵着外祖母衣裾到粥厂的棚子接受施舍的辛酸”,也“正是早年沦为城市贫民的磨炼,使母亲看似柔弱而实坚强,什么日子都能过,不叫苦,不乞怜,对穷苦病残的人有同情心”。邵母的文化只能拜家贫落魄而又识文断字的母亲所赐。邵先生属“祖”字辈,祖父给二孙取名祖望、祖荫。邵母不以为然,起名燕平、燕祥,标志着出生地——古燕京。邵母没有“贵妇的做派”,却有家庭妇女的主见。
之三:“她的妹妹,即邵先生的四姨,是个很有身份的女人……这里说的西华厅(萧按:应为“西花厅”),就是后来中南海里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处。”
邵先生《西花厅》开门见山说:“这个西花厅可不能跟中南海里的西花厅相比,那是周恩来长期办公的地点。这个西花厅是条小胡同,在东四演乐胡同东段……西花厅四号住着‘四姨儿’,谁的四姨儿?我们弟兄姐妹都这么叫,但我母亲娘家早没人了,她没有姐妹。四姨儿比我母亲要大着十几二十岁,从我记事就有‘小五十’了。”四姨儿姓惠,旗人,清瘦清瘦,寡母孤女。她们或许同病相怜,抑或沾亲带故亦未可知。四姨儿并非“很有身份”,靠“吃瓦片儿”维持生活。
之四:“母亲为二婚,姐姐哥哥乃与前夫所生。”
邵母初婚,育有两儿两女,之前有过两个儿子不幸夭折。
长女邵燕生1926年出生,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生物系,先后在华北人民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郑州市总工会、郑州市劳动局工作。
长子邵燕平1928年出生,后改名邵平,南京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肄业,参与中共南京市委地下党组织,后长期在《新华日报》和江苏少儿出版社工作;编审。
小女邵燕祯1939年出生,后改名邵焱,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先后在《辽宁日报》、外文出版社、《新观察》及《中国妇女》工作;编审。
之五:“说了这么多,只是印证,实情与我最初的猜测是相符的,这是个有身世的人。只是其身世,不在父亲这边,而在母亲那边。”
邵先生出身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与姐姐、哥哥同上收费昂贵的教会学校,从经济基础看“在父亲这边”多一些。当然,母亲的坚韧与善良对他影响不小。可否说两边都有、不分伯仲?
邵先生根在萧山,但直到1982年5月才第一次回故乡。“祖屋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被日寇焚毁,房基地上,一井犹存,当是我家世代汲饮过的家乡水。从小就知道我家祖居临浦下邵村。走到天涯海角我也是下邵村的村民。不论称绍兴府萧山县还是杭州市萧山区,我都是个萧山人。”他沿着父亲少年离乡时走过的路,从浦阳江边走到临浦,写下《山阴道》《新土》二诗,略表忆旧和怀新之情。后来又邀胞兄重游故里,写下《再回萧山有感》:“莼鲈故事感千秋,生小京门旧巷稠。何问岐山封召邑,况从汴水下杭州。不劳典史查三代,已自尘嚣集百忧。一井独存庐墓灭,于无家处有乡愁。”
“于无家处有乡愁”。我与萧山图书馆馆长孙勤女士联系,她允诺在馆内设两百平方米左右的邵先生展厅,并表态可与有关部门协商建立“邵燕祥文学馆”。我面报邵先生,他说:“文人、作家的馆太多了,应该多给科学家建建,我就不凑热闹了。”
学历——“苍茫大块任盘桓”
邵先生最完整的学历是六年小学。前四年半在灯市口油房胡同的育英小学,这是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办的小学,师资力量雄厚,即使北平沦陷时,仍保持独立校风;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后,即被敌伪接管,改称灯市口小学。1943年12月,邵先生转学盔甲厂小学(以胡同名之,即原汇文一小)。这所小学跟附近的汇文中学、慕贞女中一样,同为教会所办。邵先生在这两所小学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日本宣布投降,邵先生考取的市立九中恢复卫理公会办的汇文中学。他初二化学课需补考,托请老师介绍以同等学历报考育英高一,暑假结束转入高中。
可邵先生高一又因三角课不及格需留级。他决定放手一搏,跳二级参加“高考”。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公费,考上自然好,没考上也无所谓。北大、北师大考场失利后,邵先生1948年8月10日转战中法大学。他持营口第一中学高二成绩通知单证明参加入学考试,没人拆穿这个冒牌的“东北流亡学生”。国文阅卷老师是游国恩先生高足、大一国文课教授萧雷南先生,他给邵先生打了高分。邵先生尽管数理化成绩不理想,但还是金榜题名,被录取为法文系一年级新生。
我曾听邵先生与吴小如先生聊过六十多年前数学考试不及格的往事,记录整理成《“我们都是好学生”》,刊发于2009年10月30日《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头条。
邵先生的“有期大学”读了不足一年,就开启“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无期大学”。他“由一种精神的召唤,一种情绪的驱使,一种反叛心理的指引,以至一逞好奇冒险的冲动”,朝思暮想“山那边哟好地方”。他初一独自办过《五十年代》壁报,由四张十六开纸拼成,毛笔抄写。后应邀给《奔流》壁报投稿,参与《自由周刊》壁报创办,小小年纪就以能写著称“民主堡垒”。
取法乎上,人生大幸。邵先生最初接触的中共地下党员仇焕香、高庆赐、周世炎、李营等,人人品学兼优、深孚众望;他走上文学道路遇到的良师益友沈从文、周定一、黎凤、吴小如等,个个学为人师、文为典范。他在《世界日报》发表《为清苦教师请命》,配合地下党发动的尊师运动;暗访街道公共和军事设施,为绘制军用地图、迎接古城解放提供资料;参加迎接解放军入城,宣传中共的“约法八章”和城市政策;撰写《警告美帝新闻记者》《美国人民的耻辱》,驳斥美国记者所谓北平市民有“欢迎征服者”传统的攻讦。“千万个美名写成一个,写上天安门,大字毛泽东。”邵先生发自内心地欢呼,发自内心地拥护,发自内心地紧跟,“我正步走上了‘为政治服务’,‘以歌颂为主’的道路”。
邵先生牢记沈从文先生教诲:“要从事文学写作,就要像长跑一样,不能够跑跑就停,要跑到底。”顺境是他施展才华的舞台,逆境是他汲取营养的大学。那二十一年的“另册生涯”,邵先生“浮沉于矛盾的思想感情漩涡之间,坚持各体写作和练笔”,为后来驰聘文坛储备了充足的能量和弹药。
韩文“学历”说,三处可商榷:
之一:“转学在三年级结束,还没有上四年级的时候……从住处的变化推测,定然是外祖母死了,没必要住那么大的院子。”
邵先生五年级上学期快结束时转学。他家住的院子不是外婆家的,而是邵父所置,外祖母随女儿来到邵家。邵家搬离萧乾先生眼中“有钱人住的胡同”,是因邵父1938年从“山东龙口回到古城,一度被日本占领军拘讯,后来放回。我只听说是一个名叫安陶(读音)的人所告发,说父亲与南方的国民政府保持关系云云”。邵父不事伪职,坐吃山空,不搬不行,并非“没必要住那么大的院子”。邵先生告诉我:“船板胡同多余的房子出租给(伪)北大教授了,如果日本再不投降,我们家就难以为继了。”
之二:“高中三年,若没有初中的跳级,原本1950年毕业,这一跳级,1949年夏天就毕业了。上学还是做事,几乎没有犹豫,是想上学的,且想上的是北京大学。”
邵先生高中只读了一年。北平和平解放,他“早就不想再留在学校读书”。他的革命引路人仇焕香先生远路迢迢骑车来家,一反平时鼓励的口气说:“我看你还是继续上学的好。你不是立志学文学吗?那还是要多读书,打好基础。”邵先生嘴里答应“我再想一想”,3月16日拔腿逃离中法大学,前往铁狮子胡同三号的华北大学报到,随后乘“闷罐子”前往河北保定,6月1日选调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之三:“落榜后,受进步同学怂恿,便报名参加了革命,先去设在石家庄正定县的华北大学集训。”
邵先生十二三岁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包括从“其文网总有疏空处”偷运的毛泽东著作,接受并认同共产党的主张。“‘干’革命和‘干’文学,在我都是1946年起步的”,而且“自带‘干粮’”。1947年“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也可说走上革命道路。——一个重大标志是我在同年10月参加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邵母对儿子又怜悯又无奈地调侃说:“你真是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了。”可见他参加革命自觉自愿。邵先生晚年说:“战争和灾难的动荡年代使人早熟,锻炼人应付社会生活和独立活动的能力;变化多端的政局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则使人政治上早熟,使人增长善观察、知进退、团结多数以打击敌对力量的政治智慧。”想想红小鬼、小八路,此说不无道理。
邵先生《八十初度》云:“夜来云气欲排山,晓拭长空特地蓝。回首百年成转瞬,凌空千仞是遥看。来生哪似今生重,形下何如形上宽。漫道初飞曾铩羽,苍茫大块任盘桓。”好个“苍茫大块任盘桓”!邵先生盘桓在广袤大地上、浸润在人类文明中,既读“无字之书”,又读“有字之书”,水平远远高于文凭。
文笔——“空发议论欠华章”
邵先生“小时了了”,少年成名。他1946年4月20日写下两篇短文,其中小品《鸟语》刊发在4月29日北平版《新民报》副刊(张恨水主编),杂文《由口舌说起》刊发于6月7日锦州《新生命报》副刊(刘曜昕主编),这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品和杂文,随后在北平、天津两地报纸副刊发表了系列描红补白之作。1947年初,邵先生改弦更张,9月29日首次发表新诗《失去譬喻的人们(外一首)》(载沈从文、周定一主编《平民日报·星期艺文》)。他谦称:“我在20世纪50年代一度得以冒出头来点缀文坛,甚至由此浪得虚名,是以许多文学前辈退出创作为代价的。”
这位早熟的诗人二十岁前后出版诗集《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八月的营火》《给同志们》《芦管》。如果不是“已内定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他访苏归来整理并已看过清样的《第四十个春天》,也会配合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出版发行。
《歌唱北京城》稿费旧币二百五十万元,邵先生全部捐献志愿军买飞机。《八月的营火》(原题《七月的营火》,收入此书并作为书名时,正值反胡风运动,为避嫌改“七”为“八”)首印十万册,加印三万册,是邵先生诗文集单行本印数最大者。《芦管》乃邵先生与王蒙先生订交见证。邵先生1955年秋“初晤王蒙,他笑着向我念道‘一支歌吹得小河涨水,一支歌唱得彩虹出现’,这是《芦管》的收尾,也是我和王蒙订交之始吧”。
邵先生用《中国又有了诗歌》自我平反已是1978年1月,同年11月由广播文工团调《诗刊》任编辑部主任,1981年1月任《诗刊》副主编。1980年6月,经人民文学出版社诗歌组组长、老诗人刘岚山先生提议,出版了包括未刊稿在内的诗选《献给历史的情歌》。从那时起,邵先生出版了《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在远方》等二十多部诗集、诗选和诗评诗话集。
1984年秋,邵先生“以‘惹不起,躲得起’的犬儒心态,决心跳出是非之地,乃向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请长假’,不再参加和过问《诗刊》的编务”。他重新执笔写杂文,“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其中有我对历史的反思,也有对现实的发言”。
这是杂文写作的黄金年代。邵先生上承何满子、曾彦修(严秀)、虞丹诸前辈,下启蒋子龙、鄢烈山、朱铁志诸新秀,所谓“瞻前顾后”,拟然“盟主”(此为杂坛公认,并非自封),其文风之明快犀利、锐敏泼辣、隽永睿智,深获读者好评。他出版六十多部杂文随笔集,其中《忧乐百篇》名列全国第一届优秀杂文(集)奖榜首(不记名投票),《邵燕祥随笔》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杂文奖。
《人民日报》举办“风华杯”杂文征文,邵先生以《大题小做》应征,又拔得头筹,还得到多位作者“唱和”,其中马识途先生大作标题《小题反做》。邵先生作《读〈小题反做〉赠马识途》:“歌罢清江气尚粗,夜谭反做见功夫。岂因墙角猫扑鼠,勘破人间鬼画符。领导未闻曾闹事,群氓难得不糊涂。杂文已是无多用,何况街谈巷议乎!”
到了人人都是评论家的互联网时代,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上更多着墨。《沉船》《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旧信重温》《邵燕祥自述》《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找灵魂〉补遗》……邵先生的十部人生实录,既是他的心灵史,又是他的忏悔录。他可能不是写这类题材的早起者,但比谁都写得多、吆喝多。难友找上门来求题签、作序、写书评,他来者不拒,某些序文、读后感长达八九千字。这是邵先生告别人世前用“文字化石”给后人的交待。
《邵燕祥诗抄·打油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之《自序》曰:“曾有人说,我的杂文比新诗好,我的旧体诗又比杂文好。这是夸我的旧体诗。我却不这么看。”邵先生怎么看?或许觉得都不错吧!文章是自己的好。名人也是人啊!
韩文“文笔”说,三处可商榷:
之一:“汪的碎,有时让人惊异,难免会有刻意为之的嫌疑。邵的碎,碎的自然,碎的精妙。”
汪曾祺先生与邵先生似不在一个频道,没有可比性。如非用一个秤砣衡量,汪先生的文学成就,包括优美的文笔,自然不在邵先生之下。邵先生作为当代著名的诗人、杂文家、思想者,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他写《汪曾祺小记》是发乎内心的。如果他健在,是不会接受“扬邵抑汪”的“谀辞”的。“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韩先生素有“文坛刀客”之称,是知道下笔出刀的轻重的。
之二:“他是写过一部自传专书的,名叫《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这个定位,先就错了。应当是个人无所谓大与小,时代也无所谓大与小,‘相看两不厌’就好了。”
邵先生这部大作荣获“腾讯·商报华文好书”2016年度特别奖,加印五六次。文无定法。他请韩先生“审视一个小人物走过大时代的足迹和心迹”,说的是知心话。他赠我的大作题跋:“一个人的回顾、反省,一时怕难达到应有的历史高度,不过只要汇入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思考,千百万人对中国当代史(二十世纪史)的认识终会获得不断的深化,这是可以预期的。我相信。”他乃抛砖引玉,希望千百万难友拿起笔来,丰富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思考。
不管你承不承认,人有“大小”之分,时代有“大小”之别。“侯宝林以我从未见过的果断,指挥我们说:‘立刻就走,不吃饭了!’”这难道不是大时代小人物命运的最好注脚?我们怎能忽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谁大谁小”!
之三:“约稿的人多,游玩的地方多,也就难以静下心来,写这样既见才情又见心志的大作品……这是一个世家子,就该享这样的福,就该是这样的命。”
邵先生“硬件”不够世家子弟标准。他名满天下,“粉丝”众多,自有烦恼和无奈。他对我说:
我现在什么都是放慢节奏,主观上如此,实际上总做不到。因各种琐事,仍是疲于(不算奔命,而是)忙乱。比如昨天收到来件后,就想打一回复,但想多说几句,便暂搁下来。上午约定远道来的老友前来畅叙,确一尽欢。下午二时许始散,略略收拾杯盘,一从外地来的三十年前结交的山西作者,因事来京又即将离京,临时来小坐,于是话旧说今。到晚餐后,我已无心坐到电脑前面了。一天天常是类此的循环反复。一个一个地看,都是我所乐意接待(或接办某些事情,有的是电话,有的是电邮授命),但加到一块,总感应接不暇,心余力绌。
约稿、作序、写字、签名、题跋、出席各类活动……邵先生的“热闹”,多属被动而又难以推却。我发现,他晚年的承诺不少打了水漂,非不为也,力不逮也。邵先生《马年正月初九雪后散步》曰:“一生长短好评量,小节拘牵大节狂。纵是温文非尔雅,空发议论欠华章。但知常识但常理,不隐山林不庙堂。囊里有诗皆俚俗,江湖市井任徜徉。”他自知“应接不暇”,很难写出韩先生所希望的“大作品”。但他“空发议论欠华章”的两三千万汉字,是占据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席之地的。
我和韩先生一样,十分乐见邵先生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但他也是人,只能完成力所能及的使命和任务,而不能尽我们(也包括韩先生)之所愿。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2020年10月16日于旧锻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