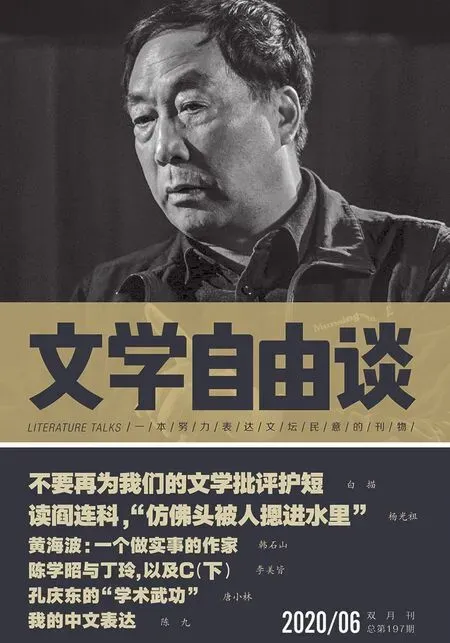我不是那个徐志摩
□岳洪治
就像走夜路,不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一样,走在人生的路上,你也不会知道,自己明天会碰上什么事情。自从韩石山先生从我的一本诗集里,“发现了一个徐志摩式的诗人”之后,相熟的朋友见面时,便会嬉笑着说:“哎呀,这不是当代徐志摩吗?”弄得我总是红头涨脸,不知说啥才好。
朋友间的玩笑,大可不必当真。但面对读者质疑的目光,却不能不坦诚地做出交代。
《遇见——岳洪治诗集》是记述我往日爱情的一本诗集,也可以看作我的爱情自白书。在书稿报告中,有如下的介绍:
《遇见》是诗人唱给情人,唱给妻子,唱给曾经的恋人和梦中女郎的小夜曲。
诗人发自内心的爱的倾诉,纯真热烈,一往情深,如醉如痴,其中有些篇什,曾被谱曲传唱。
纯真圣洁的爱情,是幸福婚姻的基础,美好人生的保障。这一卷美丽的诗篇,是诗人爱情生活的投影与升华。
——譬如花中之蜜,雨后的虹霓,是恋爱中人不可错过的恩物。
在诗集的《后记》里,我不但坦诚述说了为什么会写这些诗,还勾勒出自己诗意地栖息红尘中的一幅剪影:
诗意地栖息红尘中,这卷小诗
是我青春之树散落的缤纷花瓣。
——我的爱情的自白书。
《遇见》出版后,师友们给予了热情关注。韩石山先生在《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3期上,发表了《寻找一个徐志摩》。这话,乍一听,好像早已作古的徐志摩又轮回转世了似的。再往下看才知道,原来,韩先生是要找一个“诗风与徐志摩毕肖的诗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过《新月派诗选》的责任编辑。在徐志摩以下,新月派的诗人还有闻一多、朱湘、饶孟侃、孙大雨、邵洵美、林徽因、陈梦家等,总共十几位。要说他们诗的主张相同、风格相近,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若要让我指出,其中哪一位是诗风“与徐志摩毕肖”的诗人,我也只能交白卷。两个“诗风毕肖”的诗人,在同一流派中都属罕见,难道说,在新月派消散多年以后的今天,却会突然出现一个“诗风与徐志摩毕肖”的诗人吗?
可是,这个诗人,却偏偏让韩先生找到了。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居然认定:这个诗人,就是《遇见》的作者。文中写道:“我翻来翻去,多读了几首洪治先生的诗,且一读之下,竟读进去了,竟读完了,竟惊异自己,终于在中国当下的诗坛上,发现了一个徐志摩式的诗人。”
我得承认,作为徐志摩诗集、选集和全集的编辑,我对徐志摩其人、其诗,不可谓不熟悉;不仅是熟悉,而且还比较喜欢。然而,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把我与百年新诗运动“唯一成功了的”徐志摩(韩石山语),联系在一起。虽然不敢承认自己就是韩先生要寻找的那个徐志摩,但是,对于文章对《遇见》的“即时性”和“怜惜情”,以及“对世相的鞭笞”等特征的评论,我还是认可的。这样说,不仅因为《遇见》中的诗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样的风格特征,还由于,徐志摩的爱情诗善于把“深深的情,化作淡淡的惜,而这淡淡的惜中,又有着深深的情”,且能完美地表现出来——这也正是我多年来所希望达到的一种境界。
自然,在我写下《遇见》这一本爱情诗的时候,是并不曾想到作品的“即时性”“怜惜情”和“对世相的鞭笞”的。我只不过是因为心中有爱,所以写下了爱的诗章;只不过是因为对某些龌龊之人、缺德之事,心生愤懑而又无可奈何,所以写下了鞭笞世相的诗章。总而言之,在职务写作之外,我的诗和文章,都不是为写而写,而是有感而发、因事而作的。真没想到,韩石山先生却从中看出了以上这些风格特征,而这些特征,碰巧又和徐志摩的诗风比较接近。
韩先生认为,《遇见》的作者,“多少年来一直坚持写诗,且一直坚持走徐志摩开创的中国新诗的路子”,可谓当今诗坛上的一个“虔诚派”,也就是“徐志摩这一派”的诗人。因而,对我而言,阅读韩先生对《遇见》的批评,就有了一种揽镜自照的感觉了。
可是,看来看去,镜中人还是原来那个平庸无为的读书人。我不仅不是那个徐志摩,而且,被称为诗人,也使我感到有些脸红呢。
但是,朋友们仍然把我当成诗人,对《遇见——岳洪治诗集》,给予了热情地关注。
在韩石山先生为《遇见》撰文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章燕教授写了《生命中的遇见激荡出永不熄灭的火花——读岳洪治诗集〈遇见〉》(载《博览群书》杂志2020年第10期),诗人、诗评家、《中国诗界》执行副主编蔡启发先生也写了《纯洁的爱情——岳洪治印象及爱情诗集〈遇见〉艺术欣赏》(载《中国诗界》2020年夏季号)。报章的推介,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了这本诗集。于是,朋友会面时,又有人问我:你怎么写了一本爱情诗?听那口气,好像是说,把属于个人私密性的作品公之于世,不啻出自己的丑,聪明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听罢,我只能一笑了之——譬如有人告诉你,你的容貌与“标准国民”的长相不一样,你能对他说什么呢?
然而,想到和这位朋友有着同样想法、存在同样疑问的读者,一定还有不少,在这里,我就把自己写爱情诗的经历,和关于爱情的思考,坦诚地说一说。
人活着,是不能没有爱情的。自古以来,爱情诗的写作,就是人类文化和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编《诗经》,把以爱情诗为主的“国风”列在首位;《圣经·旧约》里的“雅歌”,也是爱情诗。恩格斯指出过这样一个事实:两性间的爱情,在最近八百年间,“已经成为一切诗歌都环绕它旋转的轴心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德国诗人歌德也曾坦言:“我歌唱的主题,最主要的乃是爱情。”我国五四新文学发轫期的诗人如胡适、徐志摩、汪静之等人的新诗,也都以爱情诗为主。以上例证,都说明了一个事实:爱情,从来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正是因为人生与爱情结了不解之缘,文学才会与爱情结下不解之缘。
一个人生命中如果没有爱情,就像一棵树没有花,也没有果实,那会是多么无趣的人生、多么失败的存在啊!一树繁花、满枝硕果,显示着一棵树生命的丰盈和旺盛的活力。同样的道理,只有那拥有爱,并能够传递爱的人,才会是一个生机勃勃、精力健旺、永远年轻的男人或女人。因为,爱情是一种最高尚的情感,你的人性必须接受它的检验与矫正。
就像阳光会让一棵树不断地向上生长一样,爱情会使你的人性不断向上,使灵魂更纯洁,使你成为一个更善良、真诚和趋于完美的人。
既然爱情如此重要与美好,为什么还会有人讳言爱情,甚至把公开谈情说爱视为不雅之举呢?为什么有人会认为,把爱情诗公之于世是出自己的丑呢?这种现象,正如恩格斯在《格奥尔格·维尔特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一文中所指出的,不过是表现了“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而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因此,一些人对爱情诗侧目而视,是并不足怪的。
再简单说一下我为什么会写爱情诗,是以一种怎样的态度与追求写爱情诗的。
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长环境,严重影响了我的性格,使我从读书识字开始,就习惯了用文字同世界对话,也同自己对话。昨日的疑惑与愤懑,今天的欢愉与烦忧,都留在了我的笔记本上。久而久之,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就变得愈来愈差。一个胆小、羞涩的少年,虽然也曾遇到一些我爱的和爱我的异性,但是,也许会是美好的因缘,由于我内向的性格,致使它们未曾开始,就一次次烟消云散了。
然而,正所谓“雁过留声,水过留痕”,许多美好的遇见,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逝。往昔,那一张张“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面影,一个个温馨美好的瞬间,都永远地留在了我生命的路途上,留在了记忆的深处。就像春天到来的时候,草儿要发芽,花儿要开放一样,我用一支笔,把一次次与爱神相逢的喜悦与忧伤,记录下来,用诗行讴歌爱情的圣洁与美好。日积月累,就有了这一本爱情诗集。
我的爱情诗,是爱的倾诉、心灵的歌唱。每一首诗的诞生,都是当那美好的爱情,像愉快的轻风一样,轻盈地吹过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落到纸页上的。每一首诗,都是自然地生长出来的,都是我的一个浪漫而温馨的梦。但是,我在写下这些爱情诗的时候,也有我的追求——这也是我全部文学写作所共有的追求,就是《遇见》封底上我所说的:
我推崇淳朴与真诚的品质,我的诗
是要以真实质朴的情感,努力写好
——“人与诗”这两个字
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要写出好作品,先要做一个好人。好好写作,好好做人,写好“人”与“诗”这两个字,这是我一生要努力攀登的一个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