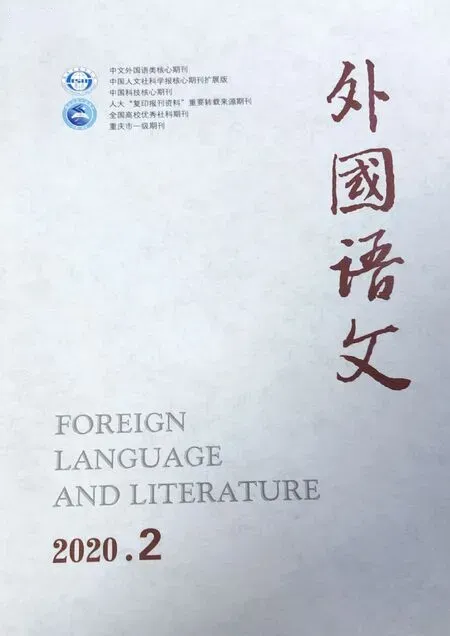论德里克·沃尔科特诗学中的传统观
张从成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
0 引言
在《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艾略特批评了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做法,认为当时对一位作家与前一代作家的差异进行比较的时兴方法是一种自我孤立;他认为文学批评中不应该强调一时新颖的差异,而应该强调从古至今的永恒性部分,那就是传统。作家的新奇昙花一现,虽然比重复好,但传统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艾略特的传统观涉及对于历史的感觉,而对于历史的感觉又涉及对于过去的过去性(pastness of the past)和过去的当下性(the presence of the past)的理解。他认为,一位作家在创作时,头脑里不但要装着自己时代的作家作品,而且要装着整个欧洲文学的作家与作品和自己国家文学的作家与作品。艾略特所说的传统,包括永恒的部分、历史的部分以及永恒部分和历史部分的融合。一件新的艺术作品进入经典的序列,将会改变既存的伟大作品序列的顺序,使整个序列得以重新调整,从而达到原来的经典与新的经典的一种契合(conformity)(Eliot, 1921: 45)。由此可见,艾略特的传统是伟大的作品序列,或者成为原来的经典和新的经典契合后的一个序列。
那么,如何认定经典呢?在文章《什么是经典?》(What Is a Classic?)中,艾略特同样强调了传统的重要性,并且检视了欧洲传统中维吉尔、莎士比亚、弥尔顿等经典作家以及其他一些还未达到其经典标准的斯宾塞、蒲柏、乔叟等作家;艾略特甚至认为著名的诗人荷马和但丁的经典性不如维吉尔(Eliot, 1975: 123,129)。艾略特本人对于让经典文学在博物馆保持静止不动不感兴趣,而是觉得这些经典在每次生成序列时需要被重新阐释、重新翻译和重新排序。同时,他也意识到他的这种论点要得以支撑的话,他必须要很好地掌握来自传统的语言技能,所以在他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中经常有大量即兴用典,表明其阅读的广博和精深。例如,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序曲》《小老头》《夜莺中的斯维尼》中艾略特经常使用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典故;而在其名作《荒原》中,他旁征博引,在四百多行诗句中 , 用典近百处,语言包含拉丁语、古希腊语、德语和梵文,内容涵盖莎剧经典、但丁《神曲》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是新旧经典契合的一个典型例证。
纵观这些变换增长的经典序列,我们会发现,这是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文学经典的传统。由此我们不禁要问,欧美传统之外的作家会如何看待这种传统?例如,一个被殖民地区的作家会如何对待这种传统?这正是加勒比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所面临的问题。针对艾略特的传统观,同时针对英美的殖民,加勒比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诗人求索之加冕》(TheCrowningofaPoet'sQuest)一书中,沃尔科特坦言自己早期受艾略特的创作影响。该书作者宝拉·洛里托(Paola Loreto)也不止一次强调了艾略特对于沃尔科特的强大影响(Loreto,2009:23,29,67,68,71)。在《诗歌理论》(PoetryinTheory)一书中,编者约恩·库克在引入沃尔科特的关于其传统观的文章《历史的缪斯》(The Muse of History)时认为其文学批评中的传统观是对艾略特的传统观的转换(Cook, 2004: 420)。本文试图探究沃尔科特诗学中的传统观。艾略特的传统观首先指文学传统,包括何为文学传统以及如何对待文学传统的问题,但也可以指文化传统(1)请参看韦勒克文章《T. S.艾略特批评》 (The Criticism of T. S. Eliot)。韦勒克谈到艾略特传统观中的古典主义倾向时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艾略特的古典主义是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而不只是一个文学批评的问题。”(Wellek, 1956: 432);然而沃尔科特不只是照搬艾略特的传统观,而是对其加以改造来应对被殖民者文化传统被压制、被损毁甚至缺失的问题,沃尔科特的这一传统观也表现于其诗歌和戏剧的创作之中。
1 沃尔科特的“古典派”传统观
尽管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每一种文化都有权利通过自身的文化书写来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以免成为强势文化的附庸,但是对于曾经被殖民的国家来讲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西印度群岛,其历史更为复杂。西印度群岛的原住民本是土著印第安人。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首次航行中,西印度群岛便出现在欧洲人的视野之中。15世纪末,西印度群岛被西班牙占领,而后这个群岛相继沦为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丹麦和美国的殖民地。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土著印第安人几乎被屠戮至尽,殖民宗主国又从非洲贩运黑奴,这些黑人及其后裔就变成该区主要劳动力,而黑白混血人种形成了新的民族,有着新的语言,其中一种就是克里奥尔语(Creole Language),也就是沃尔科特在创作中有意使用的语言。这些由外来的人口组成的世界后来被用来泛指美洲,包括被英国殖民后变成美国的北美洲。在西印度群岛的历史上,美洲被称为“新世界”,而欧洲、亚洲和非洲被称为“旧世界”(Parry, J. H. and Sherlock,P. M., 1971:i)。所以,要确立现在加勒比人的文化身份是一个问题,因为现有的加勒比人都没有文化的根基,成了漂泊的浮萍。如何建构自己族群的文化身份?如何书写自身的历史,这些都是加勒比人,包括西印度群岛人所面临的难题。对于西印度群岛的作家群来说,这也就是在创作中如何对待传统,如何通过写作来建构自己身份和族群身份的过程。
由于自身原有传统的消亡,这里加勒比海人的所谓传统,实际上指的是西方欧美的传统。对于西方传统的态度,被殖民者内部有着巨大的意见分歧。在其《历史的缪斯》(The Muse of History)一文中,沃尔科特比较了被殖民者中对被殖民经历反应不同的两类人的观点——这两类人都是政治活跃分子、作家以及艺术家。这两类人基于对西方传统不同的观点分别叫作古典派(the classists)和激进派(the radical)(Walcott, 1998: 36)。沃尔科特是古典派的代言人。可以通过对照与激进派相对立的观点看出古典派的传统观:古典派对于西方传统很崇敬,但对于“新世界”的观点也出乎意料地开放和包容;而激进派则一味地沉溺于自身无法恢复的历史。因为对西方的文学传统充满崇敬,古典派的写作就被错误地当作是对于混血儿的偶像崇拜,其实他们和激进派一样有着被殖民的经历,所以古典派其实也是西方传统的牺牲品,但是古典派有些类似那些打破自己文学传统的文学先辈,即在打破传统前他们是对传统保持着敬畏之心。相比之下,激进派却倔强地厌恶西方的传统并粗暴地加以拒绝。当然,古典派也并非对西方传统恭顺敬服,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即对于西方传统的傲慢,因为这种傲慢比粗暴地拒绝更让人不快。他们知道如果公开地与西方传统斗争,西方传统可能会永久地保持优势。文学的真正进步是“孝敬的冲动”(filial impulse),是一种表面上尊崇但内心反抗的姿态, “成熟而冷静的态度应该是同化每一位祖先的特点”(Walcott, 1998:36)。这不禁让人想起霍米·巴巴所提到的“狡猾的谦恭”(sly civility):就像表面顺从而内心桀骜的姿态一样,在西方的符号与其在殖民地指义(signification)之间存在这种误读图景,让其管理统治的正当性以尴尬的局面收场(Bhabha, 1994: 135)。
由此可以知道,沃尔科特诗学中的传统观就是利用深深影响自己的西方传统——尤其是西方文学传统——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这种发声是故意的误读,是对西方传统的一种解构,而这种误读与解构也是与古典派代表沃尔科特的身份相符合的。沃尔科特的混血杂交的身份是非常不幸的,他曾说他的两位祖先即非洲的祖先和英国的祖先都“无法给这个私生子,这个杂交人,这个西印度人带去骄傲或洗清耻辱” (Walcott, 1998:9)。但是,正是这种居间混杂的身份给表面上遵从帝国传统而实际上颠覆和解构帝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前提。帝国为强调种性的纯正,极端恐惧混血和杂交,由此狂热地设计了许多防止跨越界限的条款,例如防止异族通婚等,而混血身份实则僭越了种族界限,颠覆了种族分类。因为沃尔科特的这种身份,沃尔科特诗歌创作也被发现有着 “居间”的特征,因而具有有利视点来评判种族问题(Burnett,2000: 19-20)。
以沃尔科特为代表的古典派看到了新世界所提供的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古典派对于过去的历史问题和现在的问题视而不见,而是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期望对于压迫者的传统即西方传统有所吸收而改变现状。激进派的观点则是一味关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和压迫所导致的损坏。其结果就是,由于被压迫者所经历的悲剧性的遭遇和痛苦让他们无法做出调适,长久地纠缠于过去的历史而无法面对现在和将来(2)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2014年出品的电影《三十二》中所讲诉的经历,电影人欲给中国现存的慰安妇拍一部纪录片,期望她们讲述出当年的苦难。然而,当走进她们的生活时,最初惊诧于她们生活的平静,而后发现她们深埋于内心的伤痛和向前行走的意志的顽强,这种感动让导演将拍摄对象当成亲人,再也无力主动要她们去挖掘她们深埋内心的伤口。这正如沃尔科特上面所说的,即如果沉溺于伤痛,就无法继续前行。。
2 古典派传统观的时间和历史概念
我们知道,艾略特的传统观是历史性和永恒的融合。然而,以沃尔科特为代表的古典派传统观拒绝历史具有时间性的观念,认为其原初的概念就是一个神话,是种族的部分回忆。对他们来讲,历史就是虚构,依靠诗神缪斯的创造,依靠记忆的编织。换句话讲,过去的历史在他们的记忆里已经不存在或者说由于过于惨烈而变成失忆,而现有的生存必须又要让他们有一个历史的根源来安慰他们自身以有继续前行的动力,所以虚构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书写历史的方式。尤其是一个过去历史被完全毁灭了的民族,其过去的历史事迹,即使全是虚构,也能起到一种心理补偿作用,这是因为“一部具有编年记忆性的小说或一首这样的诗歌,都带有一种通过激发想象而把被压缩的现在和传统中的过去联系起来的能力”(Boehmer, 2005: 188)。 所以沃尔科特所代表的古典派蔑视时间性的历史,认为新世界与旧世界是同步进行的。在古典派的视野中,人的现有生存是基本的和最主要的,而不是被束缚于痛苦的过去。在他们看来,历史和我们小说虚构一样,变成了记忆和想象的发挥。越遥远的事实,就越容易化入历史的神话。沃尔科特在迈阿密大学所宣读的论文《加勒比海:文化还是模仿?》(“The Caribbean: Culture or Mimicry?”)中,就强调了历史的无关联性和想象力的必要性:
加勒比海文明的历史不是相关联的,不是因为它此时没有被创造,也不是因为它是肮脏的历史;却是因为它从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的缺失,和种族的失忆,现在需要的是想象,想象就是必需,想象就是创造。(Walcott, 1974:6)
但是在《历史的缪斯》中,沃尔科特提出了一种对于现有书写历史的警觉:“我们作为一个种族越成长,我们就越会意识到历史是书写的,是一种没有道德约束的文学,在精确的算计中种族的自我是不可消融的,一切都要看我们在作这种虚构的时候是基于英雄的记忆还是基于受害者的记忆。”(Walcott, 1998:37)在沃尔科特看来,历史缺乏道德准则,可以随意被书写,主要是看写历史的人是加害者还是被害者。作为殖民地历史建构的文学也是一样,加害者书写的文学也就是西方帝国的文学,它最多可能是一种有原主人后裔所书写的关于悔恨的文学;而被害者由于其痛苦的自我无法消融,执着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经历,就产生了一种控诉和绝望的文学,或一种由原奴隶的后裔所书写的关于复仇的文学。两种都是对于历史的缪斯的臣服。
这两种文学虽然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但却因为久争不决而变得陈旧或者由于化为悲痛而消失。激进派所持的观点却是,既不解释也不原谅历史。它们拒绝承认历史中的传统具有创造性。第三世界的很多激进派诗人对于历史抱着耻辱和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认为历史是一种悲剧,即是对于过去的错误的一种记录。被殖民者只是备遭摧残、备感失望的伟大历史的残片;所谓的新世界,其实是旧世界的延续,因为它是旧世界中的压迫和恐怖暴力的产品。历史就是控诉和绝望,加勒比海地区因为陷入过去所发生的遭遇而无法自拔。他们的实际处境就是历史就是一场与过去与不同意见的人的一场无休止的争论,历史就是悲怆的事件和感性的同情。
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在其1962年出版的游记作品《重访加勒比》(TheMiddlePassage:TheCaribbeanRevisited)中,声称“历史是建立在成就和创造的基础上的,在西印度群岛没有任何创造” ( Naipaul, 1969: 29)。从而引发了包括沃尔科特在内的若干作家的抗议,他们认为,如果基于奈保尔对于西印度群岛的历史描述,只有帝国残暴的加害与民众毫无出息的忍受,按照“历史是丰碑和创造成就”的定义以及“西印度群岛没有任何创造”的声明,西印度群岛人就应该被排斥在历史之外,这显然是他们不能接受的,这被沃尔科特等人认为是一种关于历史决定论者的观点,让持此观点的人成为历史的奴隶(Baugh, 2012: 64)。激进派一味回忆被殖民之前的纯粹洁净的历史,但是在沃尔科特来看,激进派的态度必然就是冷嘲热讽,愤世嫉俗,而于事无补。当然,激进派态度和行为的结果就是对于过去暴力历史的深深的绝望,对于过去辉煌的丰碑和残留的废墟的迷恋。对于他们来说,文明就和那些过去的建筑或废墟文物相关,他们会着重注意殖民主义留下的断壁残垣以及由此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他们会囿于过去的历史而无法超脱,选择了一种对于信仰产生恐惧的政治的人道主义。
古典派既将历史作为神话,又将当前作为历史,即围绕他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就是历史;并且为了他们自己的幸存的益处,历史可以被重新想象和建构。新世界就是崭新的经历,它和过去已经断裂,它需要幸存的人们重新思考和建构。而他们对于人性的认识也完全是亚当似的,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可以通过繁衍后代而重生,古典派也认为加勒比国家在遭遇了重重劫难之后也能够奇迹般重生。所以在古典派的视野里,痛苦后的蜕变更新是主要的摆脱痛苦的方法(Walcott, 1998:38)。
当然,古典派也能认识到被殖民的过去历史,但是对其怀着一种深深的恐惧,处于一种权宜之计将其虚无化,或者在其意识里作为受害者将这段历史同化。所以,对于古典派来讲,他们被殖民主义践踏后就无法再回到其曾经的洁净纯粹的历史,唯一的办法就是截断过去;而现在的生活对他们来讲,有着痛苦但是至少还有对将来期望的甜蜜。所以他们拒绝把进步当成一个不可知的神话,因为对他们来说,过去无法探索,但是至少将来是可见的充满希望的,并且对将来的各种可能性充满严肃和敬畏。他们对于文明的观点就是文明不是关于物质的,而是关于精神的,也就是说文明是由不断更新前行的思想组成的,而不是由历史的废墟和倒塌的丰碑组成的。作家所能做的就是通过重构文学传统而让过去宗主国的文学传统变成被殖民族群的一部分,从而可以更新和适应并且做出改变,由此应该着眼于将来,而将过去的信仰用新的方式同化以用于自身,即重构历史和建立身份。沃尔科特由此将历史定义为“并非纪念碑上的文字、帝国的统治庆典或游牧部落羞辱人性的记录,而是一个关于个人、文化及终极意义的自我救赎与自我认同的故事”(Walcott, 1998:42) 。如何自我救赎和自我认同?沃尔科特本身的创作正是改造西方文学传统为自身所用的典型例子。
3 沃尔科特漂浮的文化身份
尽管德里克·沃尔科特是著名的加勒比诗人兼剧作家,他却深受西方文学传统的影响,其标志之一就是他于1992年10月8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被西方认可的一个醒目的标志。瑞典皇家学院对于他的诗歌创作评价很高,认为“其诗歌作品光辉耀眼,致力于历史的视野,产生出多文化融会的硕果”(Anon,1992)。沃尔科特创作甚丰,包括十多部诗集和三十多部戏剧,其中包括《绿色的夜》(InaGreenNight)、《海葡萄》(SeaGrapes)、《星星苹果王国》(TheStar-AppleKingdom)、《仲夏》(Midsummer)、《奥美罗斯》(Omeros)和《另一种生活》(AnotherLife)等著名作品。
沃尔科特生于西印度群岛的圣卢西亚岛,自幼丧父,在父母朋友的影响和有很好文化修养的母亲的培养下,很早就对写作和阅读感兴趣。后来,他在圣玛丽学院、圣卢西亚大学和西印度群岛大学就读。后又任教于圣玛丽学院和牙买加学院。大学的环境让他有着一个很好的了解世界文学尤其是欧洲文学的机会,也让他有时间进行诗歌和戏剧的创作。其创作先后多次获得重大文学奖项,结果就是其作品在西印度群岛之外广泛流传(Breslin, 2001: 38)。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沃尔科特却因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以诗歌赖以生存而离开故乡,去美国纽约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波士顿大学担任教职,同时在圣卢西亚岛保留了自己的住处,往返于美国和故乡之间,同时进行创作和讲学。
沃尔科特自身就显示出一种分裂漂浮的文化身份,他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非洲人,就像在其自传体诗歌《另一种生活》中“分裂的童年”部分所表现的那样,沃尔科特从童年时代起就是分裂的,被非洲黑人种族遗传、英语文化传承以及殖民地语言政策所分裂,因为当沃尔科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圣卢西亚岛的主要部族是讲法语的,而诗人所在的少数部族却是讲英语(Walcott, 2004: 220)。这种黑人与白人、本土和西方、臣属群落和宗主国家的二元对立同样非常明显地表现在他的其他诗歌、剧作以及文学批评中。如其诗作《远离非洲》:
我,被两种血液所毒害,
分裂直到血脉,将转向何方?
我曾经诅咒
那醉醺醺的英国治安官员,在这
非洲和我喜爱的英语之间如何选择?(沃尔科特,2004:7)
从中我们可以读出几重矛盾:被看成不受教化的野人的当地部落与殖民官员的矛盾、非洲和自己喜爱的英语之间的矛盾以及他对于自己种族之根非洲的矛盾心态。其实,沃尔科特这种矛盾和分裂持续一生。他的出生地是圣卢西亚岛,却在牙买加大学受教育,毕业后又搬往特立尼达,最后离开故土去美国大学授课。他身上有着非洲、英国和荷兰血统,精通英语和本地土语包括克里奥尔语,熟悉法语和西班牙语。从小的身份危机和文化冲突,让沃尔科特成为一个典型的“流散”作家,即现代流放中的知识分子、流亡作家所处的“中间状态”,既不能完全融入新环境,也不能完全脱离旧环境,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缅怀故乡,极具伤感;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又成为巧妙的模仿者和秘密的流浪人(Said, 1996: 49)。当然,沃尔科特的“流散”经历也让他作为作家的人格面具得以分裂并相互矛盾,这一点沃尔科特自己也承认过(Breslin,2001:3)。这种分裂及矛盾的结果让沃尔科特有了对于传统的不同认识。
4 对于西方传统的挪用与颠覆
西方文学传统的基础就是西方的语言,其中以英语为首。通过想象重构身份和历史的时候,语言就成了能够综合合成(synthesis)的工具。但是对于语言的态度,激进派和古典派也有分歧。对于激进派来讲,书写历史的语言和文学创作就是一种奴役,因为所用的是殖民者的语言,所以他们认为被殖民者由于受到主人语言的压制而无法讲出真实的声音,就像法农所说,西方白人的语言可以将黑人象征化(Fanon, 2008: 8-27)。以沃尔科特为首的古典派认为,加勒比海的语言因其历史原因能够采纳来自各个方面的最好的影响,这也正是沃尔科特在创作中所依赖的条件。
沃尔科特在《历史的缪斯》中评价了两位法国诗人对他的影响,一位是曾在法国驻北京大使馆任职的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他曾由于“诗歌意象让人神思凌空,久远回想,以神奇的虚构方式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而获得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Anon,2019)。与沃尔科特相似,他也写过一首诗《克鲁索的形象》,反映笛福笔下的鲁滨逊离开小岛后在城市的凄凉生活;其实这种局外人和流亡的主题贯穿了圣琼-佩斯的所有诗歌。另外一位就是艾米·塞沙勒(Aime Cesaire),即是法语文学中创建“黑人性格运动”的作家之一。这两位诗人,一个富有,一个贫穷;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他们的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沃尔科特的认识里,他们的文学已经超越了各自的背景而走入了文学的新世界,因为伟大的文学史是超越具体的历史时间和个人背景的(Walcott, 1998:49-51)。正因为不执拗于拒绝使用殖民者的语言,沃尔科特获得了一种态度的解脱,他在使用语言的时候运用自如,他的语类颇多,从雅致古语到俚俗方言,从文学俗调到鲜活口语,他都能娴熟自如地运用;比喻新颖,观察敏锐,思路独到,内涵丰富,文体博杂,词汇繁多,内容厚重,风格大气,这些都必须要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才能完成。
最重要的是,沃尔科特受过良好英式教育,这不但没有成为他的枷锁,而且让他挪用西方传统并从内部解构了西方的传统,从而让西方的传统变成了加勒比海作家写作传统的一部分。这种解构是如何进行的?如何让被殖民者的声音真正传达出来?阿希克洛夫特(Bill Ashcroft)认为,要寻找真正殖民地人民的声音非常困难,其中一种省力的方法就是将后殖民文学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当然,后殖民文学不可能是完全的殖民地声音,极有可能是殖民话语与被殖民话语的混杂,因为后殖民文学事实上运用的是殖民者的语言,不过,在阿希克洛夫特和他的研究者们认为,经由挪用、 变形、转换以后,后殖民文学文本一样可以表现被殖民者的声音。其后殖民理论著作《逆写帝国》正是通过对于“重置语言”和“重置文本”等修辞方法的分析,呈现小写的殖民地地方英语对于大写的西方中心英语的抵抗过程(Ashcroft, Grifths and Tifn, 1989: 7-11)。这也是沃尔科特在其创作中所使用的方法。它借助西方经典文本的话语权和言语模式,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通过杂糅、挪用和模仿等策略,建构出历史来代替消亡的过去,确认自己混杂的文化身份,以颠覆西方帝国的权威。正如沃尔科特自己所说:“就像那些帝国聪明地盗用被征服人民的财宝,被征服地的人民应该有足够的理智还以颜色。”(Milne, 1993: 62)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其诗作《“飞翔号”纵帆船》(The Schooner Flight),诗中主人公沙比恩其实成为诗人自我形象的典型写照,他的黑白混血水手身份喻示了加勒比人过去被殖民与沦为奴隶的悲惨经历;诗歌描述了他们今天寻找自己历史和身份时所遭遇的困境。这就展现了和艾略特所说“过去的过去性和过去的当下性”完全不同的情形(Kowalik, 2015: 34)。而其策略也完全不一样,《“飞翔号”纵帆船》从内容、形式和语言都表现为典型的混杂:
《纵帆船》内容混杂表现在:史实与现实、城市和海洋、过去和现在、新老世界、生与死、现实和梦境等混杂交织一体,打破时空界线,从荷马的古希腊到沃尔科特的此时此刻,从爱琴海到加勒比海,从古老欧洲到殖民前的非洲。形式的混杂表现在:传统的诗歌形式与现代派技巧、大量暗示、象征典故比喻反讽及双关等运用上,写实反讽意识流魔幻兼有之。书写方式多样,包括对话,叙述,独白。语言混杂表现在帝国流畅典雅的“大写英语”(English)与变异不同的、土腔鄙语的“小写英语”(english)的运用(包括西北非语言、加勒比方言、进口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克里奥语等)上。(王苹,2009:78)
其史诗巨作《奥美罗斯》(Omeros)大胆模仿《荷马史诗》《圣经》《神曲》等西方经典,挪用并戏仿其中的形象、情节和原型,然而这些只是手段,该诗作的更大意图是让其成为加勒比海主人叙事(master narrative),通过复杂戏仿,构建出新的风格,以让本诗和《草叶集》及《失乐园》相比更加具有加勒比海特色(Callahan, 2003: 4)。各种不同历史时空的文化元素犹如碎片被抛入文本世界,再通过作者的想象力织缀一体,成为一部精美的艺术品。“通过细针密线的互文性手法,将有着不同起源的文化碎片精心编织在一起,织出了一部具有丰富内涵和多元文化色彩的加勒比后殖民史诗。” (张德明,2007: 81)《奥美罗斯》全诗共七卷,挪用了《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名字和背景,如阿喀琉斯(Achilles)、赫克托(Hector)和海伦(Helen),讲述阿基琉斯想象中的非洲寻根之旅,结果变成但丁式的地狱之旅,当他回到现实中的圣卢西亚岛,却发现这里为了逢迎各地旅游者而变得愈加商业化。在诗中阿基琉斯和赫克托被转化为圣卢西亚岛的两位渔民,而海伦也变成一个渔村姑娘;诗中还出现了四个荷马的形象,包括一黑一白的两个彼此相对的荷马,真实的美国画家荷马以及诗人的朋友荷马。这种对于史诗的挪用和模仿最终将读者带入到现实场景:“让个人记忆上升到民族集体记忆的高度,并将其与西方经典文本中的片断连缀起来,形成一种互相关联、派生、映射、暗示的互文性语境,从而使本土发生的普通事件获得充分的历史价值,颠覆西方主流历史话语的宏大叙事。” (张德明,2007: 83)
5 结语
沃尔科特曾深受诗人和评论家艾略特的影响,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也成为沃尔科特的传统观的来源渠道(Loreto, 23)。但是,沃尔科特利用艾略特西方传统对其自身的影响,对西方传统进行颠覆和解构,从而发出加勒比海作家自己的声音。从这种意义上讲,沃尔科特的传统观确实是对艾略特传统观的一种改造。当然,对于西方传统的颠覆并不是要彻底消灭那种传统,而是打消一种等级观念,从而带来一种众生平等的态度,为文学以及诗歌的真正交流打下基础,并为文化的平等铺平道路。诚如沃尔科特在《历史的缪斯》里所说,“伟大的诗人不愿意与众不同,也没有时间要去独创,他们的独创只有在他们吸收了他们所阅读的所有诗歌之后才会出现。”(Walcott, 1998: 62) 这正应和了T.S.艾略特传统观的初衷:没有哪一个诗人或者艺术家能够独自具有意义,一个诗人或者艺术家的影响以及人们对于他的欣赏来自他和那些已经逝去的伟大诗人或者艺术家之间的关系。难能可贵的是,在许多西方学者从欧美文化居高临下的审视下,沃尔科特能超越很多人无法超越的种族和政治的藩篱,对传统问题沉思关照,并最终超越历史,回归人性和自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解脱和自由。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