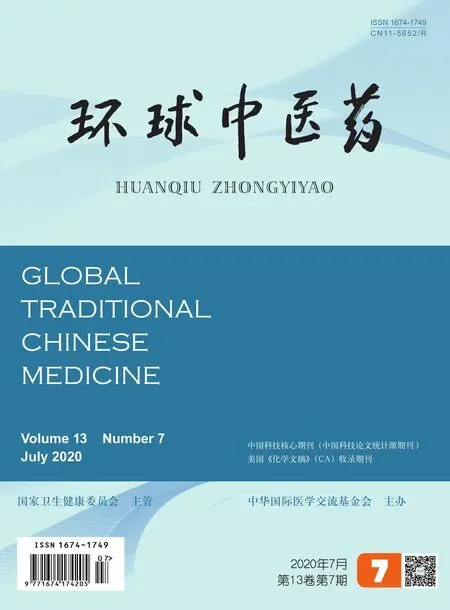“辨证”的实质是对人体系统功能信息关系的描述
薛公佑 马淑然
“辨证”一词始见于明清,各医家对此用法不一。秦伯未、任应秋等前辈对前人“辨证”理论进行整理后,将之编入中医院校第二版教材,“辨证”理论自此成为了中医学的独特方法论[1-2],它是中医天人合一、整体审察、三因制宜思想的体现,它的提出是特定历史时期下中医学传承与发展的需要。时至今日,它却有演变为“教条”的僵化趋势[1]。为适应辨证模式与诊疗思路创新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再对辨证的本质做一回溯,使其更好地服务临床与中医学理论的传承。本文以六经气化理论为基础,对“辨证”理论源头《伤寒杂病论》中“证”的概念作一分析,阐明“辨证”与相关概念间的关系,试用系统科学语言对其本质做出符合当前需要的新诠释,以解决“辨证”理论遇到的现实问题,使其在新时代中继续发挥传承中医学理论的作用。
1 “辨证”溯源
中医学的辨证论治思想源自于医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今日临床所用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等辨证方法,其思想皆根源于《伤寒杂病论》。其中八纲的内涵实际上要大于辨证体系范畴。在中医院校第三版教材之前的版本中,八纲与辨证和诊法处于并列的关系,是一种认识分析人体的宏观思路,被纳入辨证理论体系之中是受到了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临床上单纯应用八纲辨证也无法直接指导临床[3],故本文不对八纲做辨证层面的论述。
辨为分辨之义,容易理解,“辨证”概念诠释的关键在于“证”。“证”这一概念在《伤寒杂病论》一书中的篇名中多有提及,《伤寒论》中如“辨太阳病脉证篇”到“阴阳易差劳复脉证”,《金匮要略》中的篇名基本以“某某病脉证”为体例,有些篇章如“奔豚气病证治第八”则省去了脉,加上了治。但书中凡篇名之中带“病”的篇章之中,皆会加上“证”。《伤寒论》条文中首次提到“证”这一概念的条文是“太阳篇”中讲述医生误治之后,需“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由书中篇名的体例,可知“病”与“证”关系密切,由条文之中“随证治之”可知“证”在指导疾病治疗中有着关键引导性的作用。对“病”和“证”这两个概念,医圣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但可以依据文义做出解释。
先言“病”。病是指某种具有一定规律的病理过程,它有着一种或多种典型的症状或体征,所谓症状是病人主观感知到的异常反应,体征是医生可以观察到的病人身上的表现。[4]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病则可以理解为人体出现的不符合其正常生理的状态。细考文义,可知《伤寒论》篇名中的六经之病为广义,《金匮要略》诸篇篇名中的病则多为狭义。探讨六经病需要先回答何谓六经。关于六经本质,历代医家的观点可分为“六经经络说”“六经地面说”和“六经气化说”三种,其中柯琴为代表的“六经地面说”回答了六经何以能为百病立法,已经为后世医家所认可[5],张令韶、陈修园等医家进一步提出“六经气化说”,说明六经的本质是六种无形的“气化”。所谓“气化”,乃是机体形神非线性互动之后产生的涌现过程,体现为功能,可以说是系统质层面的存在[6]。《内经·至真要大论篇》将之概括为“寒(太阳)、热(少阴)、火(少阳)、风(厥阴)、湿(太阴)、燥(阳明)”。一言六经之“气化”,则“气化”之下的经络、脏腑、经筋、皮部乃至情绪、味觉等俱在其中,若是仅仅将其理解为具体的经络或是脏腑,则缩减了六经的概念,即张令韶所说的“无形可以赅有形,而有形不可以概无形”。以太阳篇为例,其篇名“辨太阳病脉证篇”可以解为“论‘太阳气化’处在失常状态下的脉与证之辨析”,其余篇章也皆可仿作此解。而篇内诸病多为狭义者,是一种或多种症状组合归纳而命名,有的直接以症状的名称来命名,《金匮要略》诸篇的病名如肺痿、咳嗽、奔豚等则皆是属于狭义之“病”。由此可以发现广义的病(机体生理失常状态)包含了狭义的病(机体产生的具有典型症状或体征的病理过程),表现于症状与体征(病人的感受或医生检查所得的表现)上面。
再言“证”。分析完“病”以及其相关的“症状”“体征”概念后,可知“证”不等同于上述四种概念的任何一种,以“太阳篇”柴胡证条文为例。典型的柴胡证为“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又有“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等或然证,病人出现这些表现,皆可以小柴胡汤治之。此处,医圣并未将这些症状总结为病名,而是仅以症状与体征言之。陈修园注解此节为“太阳之气不能从胸出入,逆于胸膈之间,内干动于脏气”,是说太阳之气化转输失常,干扰在内之脏腑功能,“当籍少阳之枢转而外出也”。下节“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结于胁下……往来寒热,休作有时,默默不欲饮食……小柴胡汤主之”是在讲“太阳之气结于胁下而伤太阴、阳明之气,亦当籍少阳之枢转而出”。由此知医圣此处所言柴胡证的本质乃是“少阳枢转不利,以至于太阳之气不能正常循行”,换言之即信息不能正常传递,功能出现失常,故都以小柴胡汤治疗,调整少阳“气化”。《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六经气化是功能与信息最高层面的概括,故“证”的本质乃是患者机体当前阶段功能信息间的关系,也属于对机体的状态的概括,功能信息所属的系统层次有不同,但其追溯的最高层面则是六经。由此可以得出另一组概念层次关系:证(患者机体当前阶段功能信息间的关系)是广义的病(机体的生理失常状态)在特殊情况(患者有主诉,承认发病)下的称呼,它体现在狭义的病(机体产生的具有典型症状或体征的病理过程)的过程之中,表现为症状与体征(病人的感受或医生检查所得的表现)。再以《金匮要略·奔豚气病症治第八》为例,此篇首言奔豚、吐脓、火邪、惊怖四病皆起于“惊发”,是说此四种病起因相同,病机相似,但是表现出的症状、体征有异,故而分为四病。随后便单以奔豚一病论述。此病有奔豚汤证,陈修园注解,谓其发自肝邪,为少阳“气化”不利,又有桂枝加桂汤证,此证源于肾寒,属少阴“气化”不利,又有欲作奔豚之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证,此证为发汗伤心液,而肾气欲动,亦可追溯于“少阴”气化。所以判断“证”实际上就是在判断功能信息关系。
2 “辨证”本义
由上节可知,脏腑辨证与六经辨证并不冲突,脏腑与六经气化在中医学理论中都是功能信息系统,六经气化的层次要高于脏腑,而证的本质是机体当前功能与信息间的关系,所以脏腑辨证与六经辨证的差别就在于前者以脏腑功能系统作为了追溯的最高层次,而后者则选择了更高层次的六经气化。后世如叶天士创立的“卫气营血”辨证,其“卫气营血”的内涵也是涌现产生的功能系统而非是如西医学概念中的实体脏腑器官、血液等体液。由此系统学概念可以对辨证的本质做出新的定义——辨证的实质乃是通过收集患者的资料、症状、体征等现象层面的信息,按中医经典理论对患者机体当前阶段的功能信息关系的情况进行描述。因为关系变动不居,这种描述一开始便具有时间动态性,既需要描述何以产生这种联系,又要预判接下来关系会怎样的变动,后者在临床中更为重要。判断过程所用的论证逻辑,便是中医学的阴阳五行等哲学层面的理论及脏腑、经络、气血、体质、病因、病机等生理、病理理论。
现行中医诊断学教材将辨证的实质解为“辨病因、辨病位、辨病性、辨邪正关系”,有学者认为,辨病位是将疾病定位到脏腑,认为五脏是中医学理论的核心,五脏的功能与形质变化是一切机体“证候”表现的根源,辨病性是将疾病以八纲归类,辨病因是将病因分为内部原因(根本)与外部原因[7]。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混淆了“证”的概念与“病”的概念,未认清人体功能系统间的层次。“证”是机体当前阶段功能信息间的关系的概括,这种关系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若将之简单的以位置、性质、病因做分析,是将动态的人体系统看做了静态的,将动态变化的“证”看作了相对静止的“病”。“病”作为一个被总结出来的病理过程,它的成因、性质与位置能够以这种方法进行分析,而“证”则不然。其次,五脏为中心的理念有待商榷。脏腑理论地位的提升实际上受到了建国后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西医学影响力的提高,导致中医学教材在编辑时更强调功能与物质实体对应,中医学的脏腑虽然也是指功能系统,但在西医学中亦有可以与之部分对应的实体结构概念,同时也为了适应教学的标准化以及研究的需要,脏腑辨证的地位便越来越突出,其下的证型数量也越来越多[3]。同时因与现代医学接轨的需要,致使中医学界不断以证候对应西医学的病名,病名诊断是现代西方临床医学的学术核心,西医学认为疾病本质是细胞病理性改变[8],到今天还在将疾病本质向更微观的层次拓展,其病名正是前文所提到的狭义的病,它只是由特定症状、体征总结出的典型的病理过程,不管所选取的指征是通过什么手段观测到的,它都只是形质层面的现象而已,没有上升到功能关系层次。这其实反应了中西医不同的本质认识论,中医是以变动不居功能关系为本质,西医则是以相对静止的实体物质为本质。概括来说就是时空本位选择的差异[9]。
3 “辨证”理论当前之困境
有学者将当前“辨证”所遇到的困境归纳为辨证论治出发点局限化、辨证论治思维狭隘化、辨证论治证候不精准性以及辨证论治诊治模式固定化[2]。辨证论治出发点局限化是指以症状和体征为出发点进行辨证,它导致了三个后果,第一是使辨证偏于静止,在急性发病过程中其体征变化瞬息万变,难以把控,第二是同时按照现有的辨证模式来进行临床诊疗,遇到症状不明显的患者会导致辨证难以自圆其说,第三是面对无症状、体征的患者或者是出于养生保健目的患者,甚至“无证可辨”。第一个后果是由于当前部分临床工作者对“证”的概念与狭义的病的概念辨析不清所致,将本应动态把握的功能信息关系理解为了近乎静止的病理模型;第二与第三点则是由于中医学辨证理论发展的“实体化”倾向[3],将“证候”病名化。辨证思维狭隘化是指过分纠结于症状、体征等有形的表现,对还未表现出严重情形的潜在疾病无从下手,出现这种现象亦根源于辨证理论发展的“实体化”倾向。辨证论治证候不精准性是指辨证的主观性太强,同一个疾病可能有多种病机分析,都有其合理性。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部分临床工作者未能将“证”,即功能信息关系追溯到最高的层次,前文已经提到,脏腑作为功能信息系统其层次实际上要小于六经气化系统,特别是在复杂疾病(此处指广义疾病)面前,无法执简驭繁,概括本质。辨证论治诊治模式固定化是指当前临床存在着死守辨证论治,排斥其他诊疗模式的现象,并进行症状、体征—证候—方药,三个层次间的强行对应。前者可归因于西医学影响下导致的模式化倾向,后者则是由于证候的病名化。
综上所述,“辨证”理论的发展与应用出现各种困境的原因归结到底只有一点,那便是是长期以来在社会各种因素影响下,“辨证”本质内涵的扭曲。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澄清“辨证”概念本质并结合现代语境对其进行新诠释来解决。
4 “证”义推广——新辨证观的价值
前文对过往辨证的实质定义为“通过收集患者的症状、体征等现象层面的信息,按中医经典理论对患者机体当前阶段的功能信息关系的情况进行描述”。若是摆脱当前僵化的、病名化的辨证模式,回到对功能关系的把握中的话,中医学理论同样适用于没有主诉的人。此时该定义可推广为“通过对检查对象进行多层次地信息收集,按照中医经典理论对受检者机体当前阶段的功能信息关系的情况进行描述”,也就是判断前文所提出的广义的病。
医学讲究“无主诉不成其病”。但是客观看来,有些人虽然还没有主诉,其身体却未必是健康的,其机体的功能关系可能已经在引导着人体系统向着不稳定状态转化。功能源自于物质实体,物质实体也可以反映功能。当功能关系出现变化时机体也必然会产生反应,只是变化可能很微小,难以为人所察觉。解决这种问题,完全可以应用现代技术,更加广泛、多层次地收集信息。不少学者基于此提出了微观辨证的概念,即在临床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引进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从微观层面上认识机体的结构、功能和代谢特点,更完整、更准确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10]。以妇女妊娠为例,脉象与腹部隆起这些明显的体征要过两个月甚至更晚才会显现,而激素的变化在一周之内就能发生。可以检测的实体结构还有经筋、皮肤等。以经筋为例,《灵枢·经筋》中讲到手三阴经筋的循行轨迹皆过胸中,三者出现异常,皆可导致其循行部位出现转筋疼痛,以及胸腹部位的瘀积性疾病,如手少阴经筋病可致“伏梁”,手太阴经筋病可致息贲、吐血,手心主(即手厥阴心包)经筋可致胸痛息贲。当前,心梗的预测是医学界所面临的难题,其发病机制为心肌严重缺血,发作时可伴有疼痛。按照经典记载,手三阴经筋出现异常皆可导致心区出现“郁闭”征象与疼痛,那么由各种原因所导致的心区的“郁闭”应也可以反映在经筋上。笔者在随北京一灵砭术中医医学研究院院长宋振虎学习砭术时,发现心肌梗死患者的手三阴经筋处多可触及结节、条索之类的病理产物,经治疗后条索消去,心脏症状也可大幅缓解。其中机制值得深入研究,完全可以应用微观辨证的思路,对经筋采用相关仪器检查,判断经筋循行部位组织的状况,依据经典中的理论推导受检者当前的机体的功能关系,即对其“辨证”,这样或许可以实现心肌梗死的早期预防。
总之,“新辨证观”是对中医“辨证”思想的新诠释。其创造的用意是使日渐僵化的辨证模式恢复到对功能关系变化的审查上。这样一来,中医学的临床治疗再次变得灵活,研究思路也可以回到以时间本位认识看待人体的传统模式。概念语境的转变有助于其与现代成果沟通,在与现代医学接轨的同时维持概念的准确性,不被异化。由此亦可促进现代医学技术整合进入中医学体系之内,更全面地收集信息,促进未病防治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