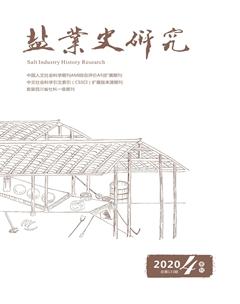一盐多制:清代新疆盐制视野下的国家、地方与民众
刘超建 王恩春

摘 要:基于清代新疆一鹽多制视野下对国家、地方与民众之间互动与依存关系的研究,可以深入地探讨终清一代,新疆作为中国主要产盐区之一,却长期被排斥在国家引岸制度区域之外,及在不同区域之间、不同民族之间、城乡之间实行不同食盐制度的深层次原因。新疆作为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稳定是国家、地方政府考虑的首要前提。一盐多制,尽管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新疆盐制的近代化,但却对维护新疆社会的长期稳定具有一定作用,国家、地方与民众三者利益基本得到了保障。
关键词:一盐多制;清代新疆盐业;课归地丁;引岸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20)04-0026-06
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使其成为中国池盐、滩盐与石盐的重要产区。新疆食盐地理分布特点有三:一是分布广,“新疆固产盐之奇区也,有盐滩焉、有盐山焉、有盐地焉、有盐池焉,以所谓无百里外无盐产者可也”①,据统计,清末全疆产盐点共129个②,1958年勘探数据为253个。二是储量大,全疆食盐总储量约在632亿吨以上,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三是盐质参差不齐,开采成本低。就新疆食盐质量来看,池盐最佳,石盐次之,滩盐最差,总体盐质尚佳;就开采而言,只需日晒分化或凿山而得,无事煎熬。尽管新疆食盐有分布广、储量大、盐质佳、成本低等优点,但长期因所谓“无尤裨国计”,被排斥在清代全国十一个主要产盐区之外。“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蒙古、新疆多产盐地,而内地十一区,有尤裨国计。十一区者,曰长芦、曰奉天、曰山东、曰两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曰四川、曰云南、曰河东、曰陕甘。”③ 十一区所产之盐属于官盐,有固定销售区域。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新疆才成功搭上了引岸制度的末班车,其个中原委与真相,目前学术界还极少有人揭橥。本文试分析清代新疆一盐多制,探讨国家、地方与民众三者之间的互动与依存关系,藉以抛砖引玉,并敬祈方家指正。
一、听民自采与课归地丁:食盐制度的在地化
清代新疆产盐区众多,一方面解决了当地民众所需食盐问题;另一方面因产盐区多,分布广,增加了政府管理的难度。再加上其他因素,清代新疆、蒙古与西藏一样,不属于引岸制度推行区域。根据史料梳理可以发现,疆内不同地区,因居住区内民族不同,所实行的盐政制度亦有区别。总体来看,以光绪二十八年为界点,不同区域内的产盐区采用了不同的管理方式。
(一)盐区私有与听民自采
清朝统一西北,历经康、雍、乾三朝80余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勘定新疆,新疆再一次纳入中国版图。为维护西北地区稳定,清政府根据各聚居区内民族分布情况实行了多种制度:以回、汉为主的乌鲁木齐地区实行郡县制;维吾尔族聚居区实行伯克制;游牧的哈萨克、布鲁特蒙古诸部及哈密、吐鲁番维吾尔人实行札萨克制①。实行不同制度的目的是对民族上层,如亲王、苏木、台吉、各级伯克、大地主、大商人、阿訇等实行笼络与牵制。基于这种目的,其辖区内的产盐区仍沿袭旧制,归其私有与管理。哈密、吐鲁番之回王、郡王所辖之民众,都在其所拥有的雅木什葡萄沟、洋海胜金口、托克逊南湖等盐矿采食食盐,自行运用②。蒙、哈、维吾尔各族王公、台吉、宗教人士、各级伯克辖区内之盐池与盐矿,一般是辖众向他们缴纳盐钱,开证放盐或献纳或承担杂役后,才可以在盐区内自采自食。精河蒙古王公、哈密札萨克和硕亲王、鄯善鲁克沁亲王、莎车县大地主买买色提与吾守尔等都拥有多个产盐区。莎车阿瓦提盐区,“旧为买买提库万赛的拉等之祖开卖,至今仍之。价以大小驮计,大者值红钱五六十文,小者三十文”③。他们拥有多个盐区,对辖区内的民众、领地都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占有盐区,不仅是王公等向民众攫取、勒索财富的一种途径,而且亦是对其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
“听民自采自食”,贯穿终清一代。即使民国时期,新疆财政厅对盐业实行了统一管理,在北疆地区的达坂城、唐朝渠、玛纳斯湖、精河、红雁池、艾比湖北等处设立盐场,派员驻场,管理食盐收放;而除对南疆的库车、拜城、温宿的矿盐和加依多拜的湖盐、巴楚的滩盐设卡照章纳税外,而其余地区由于盐湖、盐滩与盐矿分散,不易管理,盐税由田赋代征,随粮纳税。食盐允许自由采食,不再纳税④。
新疆建省后,大量的回、汉等民仍到南疆地区进行屯垦、经商,而且,城市中也有大量市民。对于他们的食盐需求,地方官为了照顾维吾尔族民众之生计,由他们进行贩运,价格较为低廉。同时规定,汉、回民众及市民只能从维吾尔族盐贩手中购买食盐,不准进入盐区进行采食。
(二)课归地丁
新疆建省以前,为避免出现民族矛盾,清政府对南疆地区实行了不利于各民族交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民族隔离政策”,禁止回、汉等民众进入南疆经商、垦殖,严禁回、汉通婚和杂居等。哈密与吐鲁番地区,因与内地之间的交流较早,有大量的汉族与回族居住,对于他们而言,同样亦不能进入盐区自采自食,只能向维吾尔族盐贩购买食盐。而对于以汉、回为主的乌鲁木齐地区,清政府则采取课归地丁,“按丁计盐,按盐计课”⑤,将盐税按丁随田赋一并征收,这样可以任听商贩,以便利民。吐鲁番、鄯善等地的维吾尔族盐贩,几人或十几人结伙,赶着若干毛驴驮运食盐到阜康、吉木萨尔、奇台、木垒等地贩卖。在城镇多是以现金售卖,乡村多是以盐换粮①。
“按丁计盐,按盐计课”,亦是地方官乐于推行的一种制度。因为官盐区内,政府对地方官的销引与盐课都要进行考成,而多数官盐区,常常私枭充斥,造成官引滞销。因邻私而兴起无穷之争讼,且按欠引与欠课分数给予地方官相应的惩罚。如顺治十年(1653)间,朝邑县知县杨宏泰、山阳县知县王之牧都未完成额定销引而被罢官②。所以,光绪三十四年,即使在迪化、精河、鄯善、巴里坤、疏附五处开通盐务,且获利甚厚的情况下,“焉耆、塔城、温宿各府、厅、州、县均经请试办,而当道罔知其利,倦于提倡,延宕不果行”③。
二、由专商到引岸:盐政的近代化
獨特的地理地貌使新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因此,新盐不像蒙盐那样,凭借其便利的水路交通,贩运至晋、陕、甘等地,一度侵晋越淮而达楚境。蒙盐“味胜,皆乐于食买”④,对淮引造成较大冲击。蒙盐“越境行销,而(河东解盐)池盐转不能行销于晋省,遂至越、楚、豫,淮引历年为滞”⑤。鉴于此,官府于嘉庆十一年(1806)恢复了河东解盐的专商制度⑥,且划晋北大同、朔平等府、州、县为蒙盐专销之区,以解决蒙盐对内地各省的贩私问题。而作为独立地理单元的新疆地区,因交通不便,与内地之间因盐贩私事件几乎不能发生,但食盐制度仍沿袭旧制,不如蒙盐在嘉庆年间就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盐政体系。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二者之间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边疆地区推行新政,使得地方财政几近空虚,各地不得不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开源节流,以解决地方财政问题。新疆地区,地瘠民贫,除赋税外,就只有改革盐政,征收盐税。于是专商与引岸制度被提上日程,开启了新疆盐政的近代化。
光绪二十八年,新疆开始在一些主要湖盐产区,如精河之艾比湖、永集湖、忙各布鲁湖,达坂城东盐湖与大、小盐湖、鄯善七角井盐湖、巴里坤盐湖等实行商包商办,征收盐税。精河艾比湖盐池原为蒙古亲王所有,后由商人承包,商贩向其纳租取盐,任意采销。达坂城盐湖亦由当地大户扬大喜、马福振两人以八顷田的代价作为盐税,取得盐湖的开采经营权。他们雇工采盐,设立私营盐场。“场商主产盐、收盐;运商主行盐,盐贩主销盐;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⑦ 光绪三十四年,新疆革新盐务,实行盐税分区包商承办,至宣统二年(1910),为官督商办者三,“精河岁包定额征银一万四千四百两;迪化岁包定额征湘平银五千一百两,现在甫经改办官销;鄯善岁包定额征银二千数百两,此包定额者也”⑧。包商承办为引岸制度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宣统元年,新疆将迪化、精河、鄯善、巴里坤、沙门子、塔城等北疆地区之盐湖及南疆地区的温宿、库车、疏勒、莎车、和阗等部分盐质优良、产盐丰富的盐区实行引岸制度。根据行政关系,新疆分为省、道、县(直隶厅、州)三级引岸,划定食盐销售区域,固定产销关系,以便于食盐管理,增加盐税收入。根据史料,笔者将该时期新疆所制定的三级引岸制与盐税收入情况列为下表。
引岸,亦称为引地,是政府为便于食盐管理与盐税征收而给请引行盐的各级盐商划定的专卖区域。盐商在专卖区域内的食盐销售享有绝对的垄断权。根据上表可以看出,清末新疆引岸制度在全疆已经推行,但南疆大多数盐区虽划定了专卖区域,除疏附县塔什密里克石盐外,其他盐区并没有征收盐税,仅是为了便于食盐管理。
清末新疆推行引岸制度,仅对迪化、鄯善、精河、镇西、疏附5地9个盐区征收盐税,既划定了销售区域,又制定了固定税率。如迪化、鄯善、镇西盐区均照精河盐池盐法之例,“每百斤定章抽税银六钱”,所征之盐税,“禀请立案,永作本地办公经费”①;巴里坤湖盐与疏附县塔什密里克石盐盐税征收无定额,而对于塔什密里克石盐,则“禀请准每百斤抽租银二分五厘,充作本地公立汉语学堂经费”②。省城迪化设盐店,分销达坂城官盐于奇台、昌吉、呼图壁、阜康、孚远、绥来等县。民国初年,基本延续清末引岸之法,迪化区的食盐生产、销售统由官办,盐税年年增加。仅乌鲁木齐地区,所征收盐税从民国元年(1912)的7900两增加到民国五年的28100余两③。
清末新疆盐政制度发生了较大变革,其历经课归地丁、自采自食至官督商办、包商承办至引岸制度的推行。有清一代,尽管清廷并没有改变新疆一盐多制的状况,将全疆盐政纳入到国家统一体系中来,但在部分地区开启了盐政近代化的尝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疆盐业的发展。
三、国家、地方与民众对盐政变革的反应与互动
新疆食盐具有盐区多、分布广、盐质优、储量大、成本低等特点。既然如此,为什么直至终清之世才将其纳入国家统一的盐政体系呢?时人王树枬等认为:新疆“斥卤之利如此大,而鹾政之所以未兴者,何哉?盖自乾隆中叶,新疆毕隶版图,历嘉、道以来,多计在兵事而未遑他愿。改省以后,大局粗定,亦未尝计此,盖当时协饷充足,固无庸他虑耳。迩来人户较多,加以新政繁兴,协款不继,榷山泽者,遂因之计及。”① 王氏将其分成三个阶段,说明新疆盐政不兴之原因。其实,王氏之观点,一定程度上亦说明了国家、地方与民众之间的反应及互动关系。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首先,清中央历经康、雍、乾三朝80余年才平定了西北之乱。勘定新疆之日亦是康乾盛世之时,乾隆深知西北动乱对于清王朝稳定有重要影响。因此,新疆毕隶版图,采取了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即军政双轨控制体系,重点在于军事控制。天山南北设官驻兵,除总理新疆军政事务的伊犁将军外,还分别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喀什、叶尔羌、和阗、阿克苏等地设置办事大臣、领队大臣或都统,即王氏所说“历嘉、道以来,多计在兵事而未遑他愿”。其次,清代新疆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因此,其军政经费来源除赋税外,主要是依靠清中央与内地各省的协济,即协饷。乾隆二十四年勘定新疆,正值康乾盛世之时,国富民强,清政府对各省份有足够的控制力。因此,自乾隆形成定制的协饷,各省都能够及时足额地拨解至新疆,满足军政经费开支的需求,即“协饷充足,无庸他虑”。再次,新疆虽然地域广大,但人口稀少。统一之初,全疆共计人口不足25万人。其中,南疆维吾尔族人口约22万,北疆地区不足3万人②,属于典型的地广人稀之区。即使照内地官盐之例征收盐税,对于军政经费开支来说,这仅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而且新疆人口少,食盐需求量小,所以使得“运盐无利,疆省立法犹可缓也”。而至清末,“疆民户四十余万,口二百余万,均不可以淡食。而驼羊数千万,又必待盐而后生活。按丁计盐,按盐计课,岁十余万。”③ 人口增加与畜牧业发展,是食盐市场扩大的主要内在因素。最后,维护西北地区的稳定,除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外,笼络民族上层人士,保护他们既得利益,又要防止其势力进一步扩大,也是清政府重要的措施之一。
就地方政府来说。自新疆统一至建省前,清中央与各省协济新疆之饷,能够满足军政开支之需,维持正常运转,所以,新疆各地方官员也倦意推行盐政。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爆发了全面危机,中央政府不仅要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而且还要应对国内各地区人民起义。国内外战争及各种赔款使得清政府财政体系处于崩溃的边缘。协款不继,新政繁兴,使一向依靠协饷维持军政运转的新疆地区之财政顿时陷入了困境。开源节流是新疆地方政府首先采取的措施,因此,盐政改革被提上日程,地方官员亦由倦意推行转变为乐于推行,甚至是积极提倡。由于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减弱,地方督抚也趁机掌握了盐务实权。各省督抚负责地方盐务机构的设置及官员的任免。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在短期内还未形成稳固的中央政权,盐务管理各自为政,管理混乱,营私舞弊情况极为严重④,新疆地区则更是如此。
就民众而言,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选择食盐趋向于去贵就贱,这也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引岸制度的推行,导致盐价上涨,因此,他们常常弃官盐食私盐,此亦属于无奈之举。如阜康、奇台、吉木萨尔、呼图壁等无产盐区,官盐的销售点大都设置在城镇与较大的聚落,而广大农村、牧区获取食盐就较为困难。每年夏季,吐鲁番、鄯善等地的维吾尔族商贩利用毛驴驮运私盐,在交通不便的乡村与牧区,以粮、皮毛换盐,这是大多数汉族、回族村民与牧民获取食盐的主要渠道。一旦缉私较严,私盐贩运中断,人民生活被逼无奈之时,他们要么偷挖就近的黑碱和硝盐代替食盐使用,虽味涩且苦,但也只能忍受下肚;或相率淡食或临时购买少量官盐,毕竟小民来钱不易。相对于南疆地区而言,终清一代,食盐制度的变革,对辖区内民众利益影响不大,课归地丁与自采自食,直至新中国成立之时,仍是其主要的食盐制度。
纵观有清一代,新疆食盐制度的变革,虽至清末在北疆与吐鲁番、鄯善及南疆(无税额或无定额)几个主要盐区实行了引岸制度,但课归地丁、自采自食、商租包办等在南疆地区同时存在,即一盐多制并没有消除。不可否认,一鹽多制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疆盐业的商业化与市场化进程,不利于新疆与内地食盐制度的接轨,但同时国家、地方与民众三者之间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实现。终清一世,清政府虽因无新疆盐税而减少了财政收入,但总体上保持了新疆社会的稳定,而对于民众而言,稳定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得以改观。
四、结 语
清代新疆食盐制度经历了听民自采与课归地丁至专商到引岸制度的变迁。即便如此,直至新中国成立之时,并没有实现全疆盐业制度的统一。食盐制度在不同区域之间、不同民族之间、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即一盐多制仍得以存在。不可否认,这种状况一方面有力地维护了新疆社会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不能纳入国家统一的盐制体系,严重制约了新疆盐业的近代化。实际上,也是在一盐多制的形式之下,国家、地方与民众之间形成了互动与依存关系,且三者之间的利益不同程度得以实现,最终也促进了引岸制度的推行,对新疆盐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王放兰)
Abstract: As one of Chinas major salt-producing regions, Xinjiang had been excluded from exclusive sales area of salt and implemented multiple salt systems between different areas, nations and cities. We could find the deep reasons by the research of the interaction and dependence between the country, local government and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Xinjiang s multiple system of sal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Xinjiang is an important frontier region and the regional stability is the primary prerequisite for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consider. Although hinde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Xinjiangs salt industry, the existence of a multiple system of salt has a certain effect on maintaining long-term social stability in Xinjiang and guarantee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local government and people.
Key words: multiple systems of salt; the salt industry of Xinjiang during Qing Dynasty; salt tax levied according to population; exclusive sales area of sa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