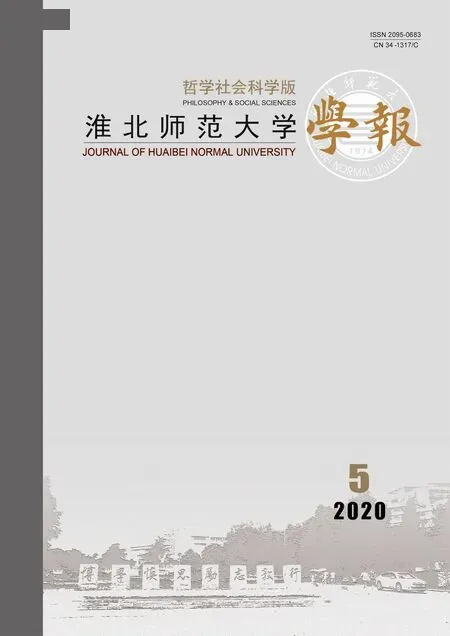“未及访晤”:吴宓与吕碧城旅欧交往始末
葛文峰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作为诗人、诗歌评论家,吴宓原本计划遴选民国诗词佳作,并附作者小传及诗词评注,编辑一部《近世中国诗选》。后因故未能实现,退而“择尤存粹,录入《空轩诗话》”,[1]177意欲自行出资印行。1935年初,《空轩诗话》撰编完毕,内容涉及潘伯鹰(1904—1966)、王国维(1877—1927)、吴芳吉(1896—1932)、吕碧城(1883—1943)等数十人。吴宓坦言,《空轩诗话》所录全凭诗词创作,绝无私谊干扰:
近年职任编辑,恒多先见其诗,后识其人。每睹佳作,急予刊登。然后到处辗转寻访,久久始得踪迹。先以通函,继乃订交。由文字之雅,终成密契,年深迹累,情好益笃。是故予乃以诗得友,非仅以其为吾友而遂誉其诗,袒私阿好之讥,予实知免。[1]177-178
诚如吴宓所言,通过“以诗得友”的方式,他先后与潘伯鹰、常燕生(1898—1947)、萧公权(1897—1981)、王荫南(1905—1944)等人结识,成为好友。
《空轩诗话》之“三十四”所记为吕碧城,述云:
吕碧城女士字圣因,安徽旌德人。《信芳集》诗词游记一卷,民国十八年出版。其后又有增改,印成中国书式。分钉二册。中华书局印售。凫公署名孤云作长文评赞之,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九十一至九十二期。[1]228-229
凫公即潘伯鹰,《大公报·文学副刊》评赞吕碧城的长文题为《评吕碧城女士〈信芳集〉》。吴宓是潘氏诗评的首批读者。吴宓先读诗评,再读《信芳集》,继“孤云”之后,于《空轩诗话》“吕碧城女士”篇中重评《信芳集》,录入《琼楼》《天风》诗二首,《六丑》《望湘人》《望江南》等词十首,并予以简评。以入选《空轩诗话》诗词数量计算,吕碧城当属佼佼者。这足见吴宓对吕碧城诗词的推崇。
依常理观之,吴宓当与吕碧城以诗词相识,继而“以诗得友”,成为诗朋词侣。其实,他们真正意义上的交往发生在旅欧期间,关系不甚密切,乃至一度交恶。学界鲜有深入述及吴、吕交往旧事。笔者拟以吴宓日记为中心,钩沉吴、吕旅欧不同寻常的交往始末。
一、《信芳集》“深契于心”:旅欧的吴宓欲访晤吕碧城
1929 年,“孤云”发表吕碧城《信芳集》评论文章时,吴宓在中国北平,吕碧城已旅行海外多年,当时已身在欧洲。1926 年9 月,吕碧城开启了欧美之行。先从中国启程赴美国旧金山,游览各地数月,1927 年2 月12 日,从纽约乘轮“奥林匹克号”,横跨大西洋,抵达法国巴黎。在欧洲,吕碧城常住瑞士,行踪遍及法国(巴黎)、瑞士(日内瓦、蒙特勒、史特雷萨)、意大利(米兰、罗马、佛罗伦萨、波隆那)、德国(柏林)、奥地利(维也纳)、英国(伦敦)。吕碧城以欧美旅行所见所闻为素材,赋诗填词以纪行,仅海外新词就多达百余首。潘伯鹰及吴宓所言《信芳集》实为内容丰赡的增订版。《信芳集》初版刊刻于1918年,分“诗”“词”两部分。1925年再版时,增补“文”,与“诗”“词”计三部分。1929年,在友人黄盛颐的主持下,《信芳集》再次增订,由北平中华书局出版。“词”部增添吕碧城新近所填海外游记词,又增“游记”内容,以容纳其记录欧美旅行的散文《鸿雪因缘》(又名《欧美漫游录》)。
《吕碧城年谱》中记载:“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辛未),四十九岁。三月二十三日,旅欧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吴宓于日内瓦致函吕碧城,约会晤。并随函钞示自作之《信芳集序》(未刊稿)……”[2]585。由此可知,吕碧城收到吴宓主动提出为《信芳集》作序的来信,并约会面。事实上,3月23日的吴宓并不在日内瓦,而在巴黎,当日有在巴黎“赴校上课”、卢森堡公园散步的记录。利用清华大学的教授休假机会,吴宓于1930 年9 月至1931年9月旅欧一年。他先在英国牛津大学研学(1930.10—1931.1),继而在法国巴黎大学研读(1931.2—1931.7)。在游学期间,吴宓短期游历德国、瑞士、比利时等国多地。
吴宓关于吕碧城的较早记述出现在1929年9月12日的日记中。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当日下午与陈心一办理离婚协议的前后经过,篇幅极长。关于上午的活动,记述简略,其中有“9—10(时)访何世伦(理之)。于崇善里十一号。又晤其友徐振武君,省政府秘书。取得《信芳集》及评稿等而归”[3]283-284。吕碧城《信芳集》刊行未久,吴宓即入手一册。同时获得的“评稿”,应为潘伯鹰所撰《评吕碧城女士〈信芳集〉》,一个月后见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10 月4 日,吴宓“又访潘式(笔者注:潘伯鹰)于交通大学,付以《文副》稿费($30)”[3]299。此处“$30”或为潘伯鹰评述《信芳集》长文的稿费。吴宓欧洲之行,或携带《信芳集》,以便随时阅读、评注。笔者所见《信芳集》(1929)为私藏本,封面题有“敬伯仁兄将有欧州之行,特此赠别,弟端。己巳年仲冬”字样。“伯仁”系何人,不可考;“端”乃邢端(1883—1956),晚清甲辰科进士(1904)、书法家,曾任清廷翰林院检讨。己巳年即1929 年,《信芳集》出版发行未久,“端”(邢端)便将以欧洲纪行诗词、游记闻名的吕碧城新作赠与即将旅欧的“伯仁”。这从一个侧面可以证明当时《信芳集》的流行程度。所以,次年吴宓旅欧,携带《信芳集》也符合常理。深受英国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纪行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启示与影响,吴宓在游欧之前便有创作游记诗歌的计划,打算将旅欧经历汇编为“欧游杂诗”,及时寄回国内报刊发表。在吴宓致浦江清的信件中,频频出现寄回诗作的记载:
《欧游杂诗》已成十二首,俟后写寄。(1930年9月24日莫斯科)[4]163
十月五日由伦敦寄上挂号函并《欧游杂诗》1—16 首,想已收到,并付刊矣。今寄上昨所作诗(《牛津欧战纪念诗三首》)并记,祈细加校阅,即付刊登。(1930年11月12日牛津)[4]166
兹再寄上《欧游杂诗》三篇(馀续寄)祈代裁代粘。(1931年1月1日牛津)[4]170
吴宓的“欧游杂诗”共计50 余首,先后刊登于《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向读者展示异域风情与社会画面,后收入《吴宓诗集》第十二卷。
1931 年2 月5 日起,吴宓在巴黎大学研修,日记中经常出现“赴校上课如恒”的文字。是日深夜,“寒甚,乃归旅馆。读《信芳集》”[5]186。2月13日的日常活动极简,只有两行文字,记载“上午9—12(时),赴校上课。午饭后,访陶燠民。伴陶君行至Alliance 上课。归函吕碧城女士”[5]190。因文献佚失,吴宓、吕碧城之间通信内容已无从查阅。幸而吴宓日记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交往信息。
3 月23 日的《吴宓日记》以长篇记述了他为《信芳集》撰写序文一事:
近拟作《信芳集序》(或《书后》),大意如下:(一)《信芳集》确能以新材料入旧格律,所写欧洲景物,及旅游闻见感想,宓今身历,乃知其工妙(李思纯《昔游诗》及《旅欧杂诗》亦然)。而其艺术及词藻,又甚锤炼典雅,实为今日中国文学创作正轨及精品。(二)《信芳集》确能以作者本身深切之所经验感受,痛快淋漓写出,而意境却极高尚,艺术却极精工,即兼有表现真我及选择提炼之工夫。集中所写,不外作者一生未嫁之凄郁之情。缠绵哀厉,为女子文学作品中之精华所在,然同时作者却非寻常女子,其情智才思,迥出人上。其境遇又新奇,孤身远寄,而久住欧洲山水风物最胜之区。如此外境与内心合,遂与屈子离骚(集名亦取此书),又似西方浪漫诗人之作。所谓美丽之生活,方可制成精工之作品也。(三)人生福慧难兼。即或享受实在之幸福,一生安乐满足,而平庸不足称述。此其一途。又或身世凄凉,遭受屯艰,苦意浓情,无所施用。而中怀郁结,一发之于诗文,却产出无上作品。其生活之失败孤苦,正其艺术创作之根基渊泉。此另一途。二者不可并得,惟人所择,若如吾侪自命超俗而雅好文学之人观之,则宁取第二种途径,而不顾第一途,但自已须出之自然,非可矫揉造作耳。由此以论,《信芳集》作者,诚足自庆自慰,而不必自恨自伤矣。(如罗色蒂女士之身世及诗,亦符此例)。……外此集中佳篇,宓拟详作批注,以质示友朋,或质作者,不具录。(明日,复吕碧城女士一书,约会晤,并以此段底稿钞示。)[5]213-214
在民国诗坛词坛,吴宓与吕碧城均为坚守旧体诗词格律、却又赋以全新内容的代表者。他们以格律旧体诗词书写新事物,抒发新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诗学特质。吕碧城一生游历海外长达十年之久,是一位对域外国度具有深刻“异己”体验的旅行者。其海外诗词凝结着她“对于充满‘差异性’的异国形象的观看和体验”,[6]是中国传统旧体诗创作中少见的书写方式。吴宓诗歌批评思想以“以新材料入旧格律”论点著称。早在1915年,他便提出“谓今日诗文,均非新理想、新事物,不能成立;而格律辞藻,则宜取之旧。……又尝谓居今世欲以诗文名家,无论如何均必得有世界知识,及洞晓中国近数十年来之掌故。否则心劳日拙,成就难期也”。[7]408吴宓坚持诗词创作应以旧体格律为正宗,但是在内容方面,必须“以新革旧”,赋以新理(思)想与新事物。“新”即在空间上将世界诸国纳入其中,在时间上具备时代新意与风尚。吴宓借旅欧之机,接触新思想,亲历新事物,创作“欧游杂诗”便是实践他的初衷。吕碧城欧洲(海外)新诗词正符合吴宓“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观点,加之吕氏有“上比李易安”之称,尤其工于辞藻,更备受吴宓推崇。待周游欧洲各地之后,吴宓对吕碧城的纪行诗词更有切身感悟。《空轩诗话》如是评述道:
其词较诗尤胜。所具特点,为“能熔新入旧,妙造自然”云云(笔者注:潘伯鹰评语)。予平日论诗,词同恒主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予又曾游欧洲,有《欧游杂诗》之作。故于《信芳集》中之诗词,独有深契于心。[1]228
吴宓之所以将《信芳集》赞誉为“今日中国文学创作正轨及精品”,还因为其中抒发了吕碧城的“真情实感”。吴宓素来强调诗歌乃是诗人真实情感的流露,他在创作之时,发现“《欧游杂诗》材料极富,然难得一贯,必须以自己强烈之感情,为全诗之骨干及精神”[4]170。彼时吴宓深陷与陈心一离婚、与毛彦文(1898—1999)苦恋的感情纠葛之中。在评注《信芳集》时,他自然地从婚恋嫁娶的角度解读吕碧城诗词,认为其中的哀婉悱恻“不外作者一生未嫁之凄郁之情”,系“表现真我”。在吴宓眼中,大龄未嫁女性必然凄苦孤寂。吴宓设想与毛彦文婚事不成,两相分离之后,“彦年老未嫁,终身郁苦,谁为解慰”[5]216?他相信,即使诸如毛彦文、吕碧城这样的知识女性,如果脱离了婚姻,孑然一身,必然会孤苦寂寞、情绪抑郁。所以,吴宓阅读《信芳集》,放大了其中悲情,乃至以同情之心劝慰吕碧城“不必自恨自伤”。
3 月26 日全天吴宓均有评注《信芳集》的记载:“上午10—12(时),批注《信芳集》。下午1—2(时),续成之”[5]218。27 日的日记记载了吕碧城针对23日吴宓信件的复函。云:
晨,接吕碧城女士来快信,谓宓昨函言及未嫁之情,有意侮辱,于是大肆责骂。彼盖认宓为上海报馆中无聊文人。然未嫁何伤,胡为愤怒若斯?于是宓对于吕碧城女士,又极为失望。夫宓以Superior man 自待,每以Superior man 或woman 期人,而动多舛忤,反资怨谤,诚可伤心。遂即复函解释,并劝读《学衡》,以知我之为人。并云,《信芳集序》不作,亦不来访云云。宓因以真心至理待人,处处失望而招责怨。如彦如贤,又及吕君,使宓痛伤无地。[5]219
由此可见吴宓毛遂自荐所写的《信芳集序》激怒了吕碧城,根源在于以“未嫁”解读全集。一是吕碧城已年近半百(49 虚岁),单身生活却被小她十余岁的吴宓横加评论,着实令人恼怒;二是吕碧城已于前一年(1930)在欧洲正式皈依佛门(法号曼智),居家修行,更无意于尘世感情。此时正值与毛彦文的感情困顿之际,吴宓又致陈仰贤(1913—1999)书信,招致对方误会,以为这是一封示爱信,遂恼怒不已,几欲绝交。自感被误解,吴宓在3 月7 日日记中记述了接到陈仰贤回信之后的心情:“我固以贤为超俗之女子,为仁厚柔和,只知理想恋爱而不知权术计虑之人。今读此函,颇失望(disillusioned)矣!宓始无向贤求爱之心,今后更必止步,严守规范”[5]203。吴宓自认是超凡脱俗之人,性情率直,也以为陈、吕为超俗的女性(Superior woman)。但是,吴宓在书信中屡屡冒犯、激怒她们,苦恼至极,遂有“如彦如贤,又及吕君”之语。对于《学衡》,吴宓既是主编,又是主笔,发文颇多。《学衡》杂志及吴宓文章最能显示吴宓学识才华与价值观念。为消除误解,吴宓故而有“劝读《学衡》,以知我之为人”之语。吴宓曾在《学衡》发表《我之人生观》一文,提出“实践道德之法”有三条行为规则:克己复礼、忠恕、中庸。道德之于婚恋,忠恕至关重要。他指出当时知识分子婚恋不和的根源:“相凌相傲,各跻各攀。于是婚姻难成,空闺独老,仳离脱辐,怨偶綦多,……此皆由于不忠不恕之故也”[8]。
即使是一同赴欧的陶燠民(?—1934)也责备吴宓言语过于草率,不知避讳,容易伤及他人心情。这又使吴宓更加苦闷,旋即于次日写信向浦江清诉苦。
江清仁弟:
宓因将游瑞士,曾函吕碧城女士,欲往访论文。因素赏其词,故于函中赞美之。乃彼误会,且不知宓为如何人,而以宓为上海报馆中无聊文人之流对彼有所求或慕色,或贪财,有所利之,来函盛气侵凌,宓甚为懊恼。……总之,世间人(尤其今之中国人,无分男女)总是把人看做坏人,而真正好人乃蒙欺侮、冤屈。又世人作文作诗,都是说假话。其文中所表示者,与其人之心性行事大相径庭。惟有吾人,要文行一致,因此自苦而见恼于人。难哉!
1931年三月二十八日晨巴黎,宓上[4]184-185
在此,吴宓并未详述吕碧城“误会”“盛气侵凌”的原因,只字未提他以“未嫁”惹恼吕氏的经过。吴宓又以“文行”相异,暗指诸如吕碧城一类的作家作品并非真情实感的抒发,而“都是说假话”。质而言之,吴宓对吕碧城诗词评价自有公允、中肯之处,但是,仅就其过于直率的言说方式,已然是不知委婉融通,故而不可避免地“见恼于人”。
二、“更不能访矣”:吴宓与吕碧城同在瑞士
1931 年4 月13 日,吴宓从巴黎前往瑞士旅行。中午抵达日内瓦,与叶企孙一道,入住英国人开设的“美景旅馆”(Hotel Bellevue)。[5]24514 日早晨,迁至费用较低的“基督教旅客招待所”(Christian Hospices),节省开支。吴宓与叶企孙全天出游,先后游览卢梭故居、日内瓦大学图书馆、植物园、动物园、阿维纳公园,最后于卢克公园久坐,观湖景。当晚,吴宓致毛彦文信函写完之后,又给吕碧城写信:“函吕碧城,请其将宓前次钞寄拟作《信芳集序》之稿,仍寄还我”。[5]248距上次吕碧城信中“大肆责骂”吴宓,已半月有余。此时的吴宓身在日内瓦,而吕碧城居住于蒙特勒,两地均在日内瓦湖沿岸,相距不远。若无3 月间因“未嫁”之事而“交恶”,吴、吕这两位同在瑞士的中国诗词名家,极有可能以地利之便而会面。但是吕碧城曾在信中告知明确吴宓“不必来访”,彻底消除了会晤的可能。因此吴宓只能去信要求寄回《信芳集序》稿件,不再提及“往访论文”。
16日,吴宓一行环游日内瓦湖,经过吕碧城居住的蒙特勒。他写道:
Montreux(笔者注:蒙特勒)为湖东端一大市,犹湖西端之Genève(笔者注:日内瓦);然为商业游乐居住之地,风景不佳,店肆栉比。宓三过其地,未下电车。吕碧城女士居此,更不能访矣。[5]254
蒙特勒为日内瓦湖东岸小镇,风光旖旎,气候宜人,是著名的度假胜地。4月旅行至此的吴宓所言蒙特勒风景不佳,而吕碧城游记中多次言及常居之地的宜人风景。在“芒特如之风景”一文中,吕碧城不惜笔墨,详细描绘了蒙特勒“背山临湖”的美景:
晨兴,纵览风景,全埠为光气笼罩。盖湖光山色,益以朝霞积雪混合而成,色彩浓厚。……此则瑶峰环拱,皑皑一白中,泛以姹紫,湖面靓碧微腾,宝气氤氲,漫天匝地,而楼影参差,花枝繁簇而隐约见之。须臾,旭日高升,晴晖烁眼。……近处古迹有锡兰堡(Castle of Chillon),古为此城要塞。内储十五世纪各武器,及军犯囚处。大诗家别伦(Byron)曾有专篇咏之。[9]1-2
吕碧城笔下的蒙特勒不仅自然风光美不胜收,又以历史名胜闻名。她关注到的“锡兰堡”,即令吴宓流连忘返的“熙隆堡”(Château de Chillon):“此Château 植立湖中,与岸隔深沟,木桥连之,风景至美”[5]249。湖光山色之中的古堡,又有著名诗人拜伦名篇《熙隆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Chillon)为之增色,吴宓登堡之后专门赋诗一首,并购古堡画册,寄回国内在《学衡》刊发,以志纪念。云:
诗人所盛称,神奇郁古垒。
圆塔深入湖,一湾临绿水。
岭背桃花发,雪山对面起。
晃漾波晶莹,凭窗静可喜。
人间此仙源,岂陷劫尘里。
战血染碉楼,黑冤沉狱底。
画盾献赤心,系镣存道揆。
英烈往事空,风景千年美。[10]46
诸如此类吕碧城、吴宓先后游历并有文字记载的景点尚有数处。4月17日,吴宓“游观Genève市中Rhône 河(笔者注:罗纳河)上诸桥(桥数凡七,《信芳集》中有诗咏之);以铁闸(可分卷)所成之瀑布”[5]256。吕碧城“有诗咏之”的是《日内瓦湖短歌四截句》“其二”,诗曰:“循环数七桥,七桥有长短。桥短系情长,桥长响屧远”[11]207。这是吕碧城荡舟于日内瓦湖之后所作的纪事诗。早在她初到日内瓦时,便对这座城市的整体印象进行记述,在《日内瓦》一文中详细记载了市容市貌,表达了她对这座“山水驰誉寰球”城市的喜爱之情。日内瓦湖长且窄,湖面上连通两岸的桥梁给吕碧城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两岸相对,通以七桥。桥皆坦阔如辇路,但愈近湖尾,而桥愈短”[11]204。18 日,吴宓从日内瓦前往尼翁(Nyon)一日游,乘缆车登雪山。攀登雪山途中,“自Bsssins(巴森)以上,则大雪,如冬日,遍地皆白;幸电车内有热气管,可御寒;忆吕碧城‘一时寒热同消受’,甚觉其真”[5]260。此时吴宓所忆为吕碧城在蒙特勒登雪山、那不勒斯观火山后所填《蝶恋花》中句,上阕云:“为问闲愁抛尽否?收得乾坤。缥缈归吟袖。雪岭炎冈相竞秀。一时寒热同消受”[11]107。吕碧城登雪山之后随即前往意大利旅行,在密兰(米兰Milan)小住二日,又赶往拿坡里(那不勒斯Naples)参观旁贝(庞贝Pompei)古城和维苏维欧(维苏威Vesuvio)火山。面对“日夜燃烧不绝”“如斯巨焰”的火山,回想起几日前蒙特勒登雪山的寒冷记忆,吕碧城感慨道:“计予自蒙特如至拿坡里,相隔仅五日。两地观山,一雪一火,寒热悬殊,赤白相判,极宇宙之伟观矣”[11]218。“两地观山,一雪一火”即词中的“雪岭炎冈”,寒热悬殊让词人切身体会到“一时同消受”。吴宓踏访吕碧城先前旅游旧地,并忆起《信芳集》中颂咏的诗词,可见他对吕氏诗词的熟稔以及不能会晤吕碧城的遗憾。
当日下午约4 时,吴宓乘火车到考贝(Coppet),步行至斯达尔夫人别墅(Château de Mmede Staël)。斯达尔夫人(1766—1817)身出名门,是18、19 世纪之交法国著名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曾在巴黎、日内瓦开办文化沙龙,名震一时。1928年春夏之际,吕碧城访斯达尔夫人别墅,填《浣溪沙》以抒怀。词曰:
知是仙游是梦游,春痕依约彩笺收。芳尘回首恨悠悠。
山水有缘温旧迹,钗钿无地证新愁。伤心何独牡丹侯。[11]122
吕碧城将才华横溢、容貌出众的斯达尔夫人比喻为“牡丹侯”,词中感叹斯达尔夫人晚年不幸人生遭遇的同时,也抒发了词人自己的伤感之情。吴宓也赋诗二首,题为“日内瓦湖畔斯达尔夫人故宅”,以记故宅主人的身世才华与别墅格局。诗中有云:
福慧谁兼有?才命果相妨。
夫人生名门,英气吐光芒。
寰中驰藻誉,后世诵瑶章。
嫁得金龟婿,难觅有情郎。
晚婚世交讥,真爱心恒伤。
沧桑阅奇变,十载走仓皇。[12]250-251
“才命果相妨”化用自《史记》慨叹贾谊的诗句“才命两相妨”,“瑶章”“金龟婿”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典故、意象。由异国风情而联想及中国文化,以比较文学的视角创作诗歌,是典型的跨文化诗学的体现,佐证了吴宓“‘以新材料入旧格律’,更是以中国眼观西洋景”[13]82。
对斯达尔夫人及其好友雷克敏夫人(Mmede Récamier,1777—1849)的寝室、信札手迹、装饰与画像对比之后,吴宓发现斯达尔夫人喜好艳丽奢华,字迹矫健飞舞,似男性书法。他对这两位女性的外貌进行了对比。
吴宓眼中的斯达尔夫人身材雄健,容貌英俊奇特,颇有男子气概。他特别在一旁标注“比较、参阅(cf.)吕碧城”。旅欧的吕碧城衣着时尚、前卫,短发浓饰,言行果敢。潘伯鹰评点《信芳集》时,称赞吕碧城“皆豪纵感激,多亢坠之声,……兼有刚气”[2]553-554。以“容貌”而言,吴宓印象中的吕碧城与斯达尔夫人均为貌美又具男性气概的奇女子。
在游览斯达尔夫人别墅的当晚,吴宓收到吕碧城来函,对吕氏的态度与感想一并写进了日记中。
归Hotel des Familles 后,接来函如下:……(2)吕碧城函,仍为无理之发怒,以婚姻为“兽性”。又斥宓不懂文词,不看全集,甚至教宓以“椿萱”=父母!宓怒;然复短函,极和且静,言我现无误会,请彼此释然可矣。予一年来,对女子完全失望,Winter与叶崇智之鄙视女子,实缘经验。即如吕君,宓之为她费力已多,且欣赏其词,逢人揄扬;今夕游Coppet,且思吕碧城=Mmede Staël。夫吕君与梁、袁私交甚厚,其故友且为传说;此等事宓并不以为非也。而人本半神性,半兽性;人之有性欲,不足为耻。吕君自鸣清高,谓思及婚姻,便是禽兽;此伪也,抑亦过刻之论也。况婚姻恋爱,以情趣为主,文人诗人咏歌甚多;岂必婚姻便为性欲满足而已乎?宓赞吕君为屈原,而吕君乃谓宓侮辱她有兽性……;冤哉!于是知(i)世之持论过高者,其内实甚卑鄙;(ii)人之发为诗文,作伪者多,非皆如吾辈之表现真情;故不可以文取人。(iii)女子不宜奉承奖倍,只可取适吾意;如其无理,绝之忘之可也。今后宓当聪明,而不再自苦矣![5]262-263
吕碧城对于吴宓提出的“未嫁”一事仍旧怒气未消。吴宓自信身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与中文系主任,被指责“不懂文词”时也心生愤懑。虽然他以平静的心态再次致函吕碧城,希望调和误会。但是,一直推崇《信芳集》的吴宓对吕碧城其人大失所望。一是对于吴宓的肯定、赞誉之词,吕碧城并不以为然,由“未嫁”之事而全盘否认吴宓评语。二是吴宓认为《信芳集》最成功之处在于“不但描绘景物,又必须表现自我。情意丰融,方合。此《信芳集》之所以为可称也”[1]228。而此时吴宓认为吕碧城其人及其诗词“文行”不一,作者秉性与诗词创作大相径庭,以致他得出“不可以文取人”的结论。至此,吴宓反思自己一厢情愿却备受冷遇的举动,自称对于吕碧城“绝之忘之可也”,却始终未曾对“未嫁”解诗一说做出道歉。整体而论,吕碧城旅欧创作诗词,既有个人情感的描写,又有家国情怀,其“情意”表达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吴宓的“未嫁”评语有以偏概全之嫌,至少“小姑终老不是惟一原因,更不是重要原因”。[14]48
4月22日,吴宓返回巴黎,结束了瑞士之行。
结语
1931年4月24日,吴宓又接到吕碧城来函,二人的误解依旧没有消除。
昨又接吕碧城复函,不肯寄还原稿,谓已撕毁(妄也,盖中国人之挟制耳);且云,如宓文中不及吕名,则吕文中亦不及宓名,请放心云云。盖中国人只知应付,外交,手段;而不知感情了解,又何独责彦哉?[5]269-270
吕碧城是否撕毁吴宓所撰《信芳集序》原稿,已不可考。但是在吴宓看来,这成为吕氏挟制于他的一种手段,对她的误解进一步加深。从吕碧城传世诗词文集中看,她确实没有任何提及“宓名”之处。
事实上,吴宓并未对吕碧城及其诗词“绝之忘之”。1933 年,《学衡》刊登《欧游杂诗》(第一集),吴宓在序言中言及代表性旅外诗词除了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附载篇什之外,“近年有吕碧城女士之《信芳集》及李思纯君之《旅欧杂诗》,均为之甚工,且已裒集成帙”[10]1。在《吴宓诗集》(1935)中的“欧游杂诗”(卷十二)与附录《空轩诗话》中,吴宓对吕氏海外游记诗词的肯定、赞赏评价一概如旧。
1937年5月8日,吴宓最后一次记录与吕碧城的交往:“上午接吕碧城女士,由香港山光道12号,寄来《晓珠词》20 部,索宓《诗集》,遂又寄一部与之”。[15]123从确切邮寄地址可知,养病于香港的吕碧城应该是直接将新出版的《晓珠词》寄予吴宓,非经由他人转交。这次吕碧城主动联系、赠书于吴宓,吴宓也以《吴宓诗集》回赠,表明二人已经释然旅欧期间的不愉快交往。《空轩诗话》中对于此段经历,吴宓如此记述:
《信芳集》作者,自戊辰以来,奠居瑞士日内瓦即丽满湖畔,时复出游各国。予在欧,以人事匆促,未及访晤,仅曾通函而已。[1]228
吴宓或许反省自己当年言及“未嫁”一事的唐突,抑或不愿详述曾经的尴尬,将“未及访晤”的原因以“人事匆促”一笔带过。倘若旅欧的吴宓与吕碧城通函顺利,并会晤于瑞士,他们或许有更深入的诗词探讨与唱和,成就民国诗坛词坛一段佳话。然则,吴宓与吕碧城交往全因“未嫁”之语而生嫌隙,即使同在瑞士,具有天时、地利之便,却无人和之机,终究“未及访晤”。
吴宓“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主张是中国近代诗词发展转型期的代表性诗学思想。吕碧城以欧美游记题材融入旧体诗词亦为民国文坛中的海外诗词佳作。前者以诗学批评闻名,后者以诗词创作著称,两者如果正常交往,以诗词批评与创作进行深入而广泛的交流与切磋,则彼此裨益良多。他们身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却又置身时代巨变的环境之中,性格多重而矛盾,既保守又开放,既苛刻又包容。吴宓缺乏与女性交流的变通之法,吕碧城又过于对“未嫁”一事耿耿于怀,从而导致误解一时难消,最终致使他们旅欧期间这一段纸上交往并不顺利,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