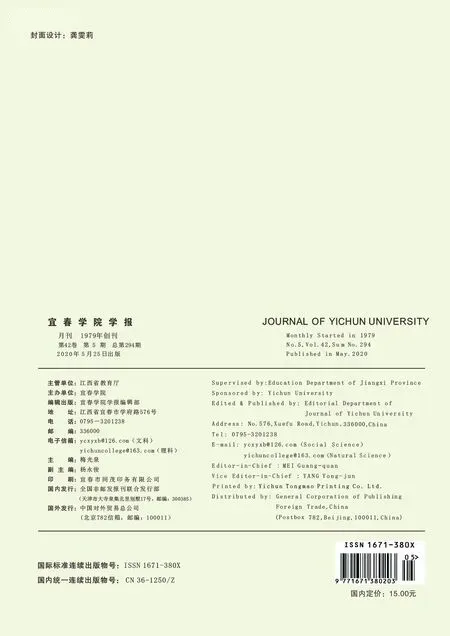《六祖坛经》与汉文佛教大藏经的关系研究
白 光
(江苏师范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一、问题的提出
佛教源自印度,兴盛于中国。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形成许多各具特色的宗派,而禅宗则日益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佛教一般将佛的言教称为“经”,禅宗的《六祖坛经》以“经”命名,由此可见它在中国佛教的地位。《六祖坛经》随着禅宗的发展而演变,在唐宋间便形成许多版本,影响遍及南北和海外,其中的一个表征便是被编入佛教大藏经,从而使得《六祖坛经》的入藏成为《坛经》研究的重要领域。
佛教大藏经主要是对佛教经典文献的汇编,汉文佛教大藏经则主要是对汉文佛教经典的汇编。从所收的文献上看,唐代以后由于中国佛教宗派开始汇集自宗经典,诸如天台宗和禅宗亦开始编纂藏大藏经,这推动了汉文佛教大藏经将汇集的范围扩展至中国佛教宗派经典。后来的大藏经逐渐收录禅宗经典,与中唐时期提倡“禅教一致”的宗密禅师曾编写过《禅藏》[1](P398)有一定关系。从文字载体上看,汉文佛教大藏经经历了一个从写到刻的阶段。[2](P5-13)[3]宋代以后开始以写本大藏经为底本进行雕刻印刷,现存大藏经即主要以宋代以后的刻本为主。多年以来,随着人们对佛教大藏经的编纂和研究的深入开展,人们发现,现存的刻本大藏经及其经录直至明代才将《六祖坛经》纳入其中。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有学者提出《六祖坛经》虽然影响很大,但是它的入藏很晚;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六祖坛经》因为入藏晚,所以它的影响并不大。这些说法的基本判断是:《六祖坛经》入藏很晚,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判断并不符合实际。
从现存所见的《六祖坛经》版本来看,明代入藏的版本只是《坛经》版本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从此时期版本的入藏只能推导出此时期并未将此前的其他版本入藏,而推导不出其他版本在以前未曾入藏。明代之前大藏经是否收录过《坛经》,应结合唐宋时期的《坛经》版本以及相关入藏记载加以判断。另外,虽然现存唐宋时期的大藏经及其经录是判断的重要根据,但判断的根据不能仅限于此;而且即便以之为根据,也应注意其中的问题。因为佛教大藏经本身也有一个从产生到续刻以及翻刻乃至毁版改刻的演化过程,例如本文后面提到的民间所刻《碛砂藏》,它虽然始于南宋,但一直延续到明代还在进行中[4](P79),所以不能将现存的某部大藏经或特定时期的经录简单地等同于该部大藏经的所有版本。从《六祖坛经》入藏的角度看,现存唐宋时期的大藏经中虽然没有发现《坛经》,但并不能据此推出《坛经》未曾被曾经存在过的大藏经所收录。事实上,历史上也存在过一些证据可以证明有些大藏经曾经收录过《坛经》,只是后来又被删除了或丢失了。
实际上,明代最早入藏的《坛经》版本也比较复杂。从明代洪武五年至永乐初年,存在着从准备刻藏的校勘到先后勘刻初刻南藏、永乐南藏两部大藏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坛经》先后出现了洪武六年所刻密庵本、初刻南藏本以及永乐南藏本。人们一般只讨论初刻南藏本与永乐南藏本的关系,而不触及它们与洪武六年本的关系。实际上,如果不了解洪武六年本产生的内容、背景及其渊源,也很难理解后二者在入藏时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又由于在民国初年发现的初刻南藏中尚存一部以“用”字编号的《六祖坛经》,但是后来却遗失了。这不仅使得初刻南藏到底收入了几部《坛经》成为问题,而且也使得初刻南藏本与永乐南藏本的关系模糊不清。因此,关于现存永乐南藏本《坛经》的产生及其与初刻南藏本、洪武六年本的关系也需要加以辨明。
二、《六祖坛经》在唐宋时期已入藏
二十世纪初,人们在敦煌文献中发现大量早期禅宗文献,而这些禅宗文献往往与某部经论连写,这正是“经是佛语,禅是佛意”的禅教一致论在经典组织方面的表现,所以有学者认为有些敦煌文献很可能乃是《禅藏》的遗存[5](P393)。在敦煌地区出土的唐代禅宗文献中,《六祖坛经》就是其中之一,其中就有两个写本是与《佛说大辨邪正经》相连写[6](P86-140)。
从敦煌本《六祖坛经》自身所述来看,这种版本的《坛经》多处提及自身具有着“传宗”的功能,如云“无《坛经》禀承,非南宗弟子也”[7](P28)。从禅宗早期在传承方式的变化来看,这是继续《楞伽经》《金刚经》以及“法衣”等之后的新型传承方式。根据禅宗祖师谱系等内容的渐次演化过程,一般认为敦煌本《坛经》版本形成于《历代法宝记》(775年)和《曹溪大师别传》(约782)之间,是现已发现的《坛经》版本中最早者。值得注意的是,“《坛经》禀承”这种传承方式开始主要在以惠能弟子法海为代表的“南宗弟子”中传播,此种《坛经》中所保留的传承信息,所谓“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漈,道漈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受此法”[7](P45-46)便是证据之一。证据之二是,在公元787年[8],在今广西罗秀山一带修行的惠昕禅师为了方便一般人学习而将一卷本的《坛经》加以述说和编排,从而产生一部新的二卷本《坛经》,可称为惠昕本,其中虽然将突出韶州法海禅师的内容进行了删除,但是依然保留着相似的《坛经》传承谱系,所谓“洎乎法海上座无常,以此《坛经》付嘱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圆会”[7](P87)。同时,从中不仅可见这两种版本流传渐广,也能预见其以“南宗”相标榜所隐含的排他性将会导致的批评。现存的批评资料主要有二:一为出自惠能弟子慧忠禅师,他认为南方人将惠能《坛经》进行改换成传宗经典的做法是“添揉鄙谈、削除圣意”,不仅有违于惠能言教,而且有“惑乱后徒”的危险[9]。二是为怀让禅师的再传弟子大义禅师撰写碑铭的韦处厚,他在碑铭中提到“习徒迷真,橘枳变体,竟成《坛经》传宗,优劣详也”[10](P715),对《坛经》传宗也持贬损态度。实际上,这些批评资料不仅能反证《坛经》传宗本在唐代中期流传和影响程度,这些批评资料所蕴含的对于禅宗经典所持的谨慎态度也会对编辑《禅藏》的宗密禅师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宗密禅师为《禅藏》所写的序言中提到这样的编纂原则,即“集诸家之善记,其宗徒有不安者亦不改易,但遗阙意义者注而圆之,文字繁重者注而辨之”。[1](P412)应该说,正是由于这种“不改易”的做法,所以人们看到敦煌文献中所具有的《坛经》只有早期的传宗本而没有惠昕述编本。然而,由于完整的《禅藏》尚未发现,所以《六祖坛经》与《禅藏》的真实关系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加以确证。
经过惠昕所编的《坛经》虽然没有被《禅藏》所收,但是却在后来被纳入到大藏经中,这在1153年由晁子健助缘所刻的“军”字函《坛经》中可以得到证实,[7](P49-65)只是尚不知这部入藏的《坛经》所入的是何藏而已。
另外,随着惠能南宗的繁盛,惠能禅宗日益成为禅宗的主流,作为惠能言行语录重要代表的《坛经》也渐次形成多种抄本和更多版本,除了敦煌本和惠昕本外,活跃于后唐咸通年间的陈琡也曾“自述《坛经》三卷”,并被纳入藏经之中,五代时期的王仁裕在《玉堂闲话》中对之加以记述时,尚且提到“今在藏中”。有学者推测,这部《坛经》可能就是被唐懿宗在咸通年间所编修的大藏经收入的[11]。这部《坛经》虽然现在尚未被发现,但是北宋时期的郎简为契嵩所校勘出的《坛经》所写的序中便曾提到,契嵩所校勘对象正是某部“曹溪古本”,而且校勘后也是“三卷”[7](P235)。加之,近年来发现的洪武六年本《坛经》中所存的一些校勘记,特别是其中一则提到“原本末句字迹舛错未录,姑阙以待者”,笔者曾推测此本为现存最接近契嵩校勘本者,而且确实有某部字迹有错的“曹溪古本”[12]存在。这部“曹溪古本”如果就是三卷陈琡本的流传本的话,那么现存属于契嵩本系统便可谓是其进一步的演变了。
契嵩本的三卷本《坛经》今已佚失,亦很难推测它是否曾被后世某部大藏经收入。但是,在宋辽之际,依然有关于《坛经》曾被大藏经收录的佐证资料。如《佛祖统纪》即记载说,辽代在审定经录的过程中将“《六祖坛经》《宝林传》等皆于焚弃”[13]。辽代所审定的大藏经录中的《六祖坛经》版本虽然至今未见其遗存,但是民国期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的《金刻大藏经》中则发现了《宝林传》的刻本,其编号为“秦”,而且在第八卷中尚存“新编入录”四字。[14]从千字文顺序上看,《六祖坛经》曾经以“军”字为编号,处于“秦”字之前,以此亦可证明传至辽代而尚未被审定的大藏经录不仅存在《六祖坛经》《宝林传》二书,而且在经录中的排序也是《六祖坛经》在前而《宝林传》在后。
三、永乐南藏本《六祖坛经》的入藏
《六祖坛经》虽然在唐宋之际的入藏还有待新资料的进一步证实,但是在明清之际入藏的许多问题已可以辨明。这一方面是由于明清之际的所有大藏经的雕刻均将《坛经》收入,而这些版本又几乎都流传至今,从而为研究《坛经》在这一时期的入藏问题及其源流关系提供了基本的资料;另一方面则在于这些入藏的《坛经》版本多数携带者有关校勘的作者、时间以及校勘记等内容或信息,从而为深入认识《坛经》入藏及其变更的缘由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近年来,受惠于现代科技在影像和互联网技术方面的成就,国内外许多图书馆将馆藏的《六祖坛经》公之于众,许多书商也将收藏的《六祖坛经》版本置之于市,加之许多师友的慷慨帮助,笔者搜集到了不少新的《坛经》版本,其中一些便与明清之际《坛经》入藏相关者,如明代洪武六年翻刻的密庵本、天津图书馆藏明代嘉靖时期翻刻的永乐南藏本、明万历年间所刻的元代宗宝本、清代全真道龙门弟子栗守约所刻憨山德清校勘本、清代同治十一年如皋刻经处本等。将这些版本与前面讨论的可能被入藏本的《坛经》相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别是,其中的一些版本是在官方组织下进行校勘而入藏的,并不单单是个人校勘行为的结果。其中,与明代最早发起校勘活动和开刻大藏经密切相关者,是洪武六年本和永乐南藏本,而永乐南藏本已经成为人们讨论《坛经》入藏问题的焦点之一。
洪武六年本《坛经》属于宋代契嵩本系统,经过密庵的修订后,在明清两代经过多次重刻,现已发现的三种重刻本均是对明代洪武六年本的再翻刻,时间在清代,分别为1869年、1889年和1898年,属于同本异刻而差异不大。其中的1869年本为在韩国的刻本,最早由韩国学者朴相国进行过介绍[15],但长期未被学者注意。2013年底,笔者在台湾访学期间于图书馆发现有1898年翼化堂本的胶卷图片,并搜索到韩国图书馆已经将朴相国所介绍的版本在网络上公开,后来又从吴孝斌先生处获赠1889年本。从台湾回来后,笔者对这种版本进行了对勘并结合其他资料作了初步的研究,指出该版本可能是现存《坛经》版本中最接近宋代契嵩校勘的本子,发现此本与其他本相比,其特异之处是含有不少属于“校勘记”的内容,其不仅对于理解《坛经》思想有所帮助,而且对于认识《坛经》流变过程中的“以注入文”、“从俗至雅”以及“佛经化”也具有重要价值;除此之外,笔者还根据此本的流传时间而推测该本“密庵附录”中的“密庵”有可能是指宋代的密庵咸杰禅师。[12](P88-99)
密庵咸杰禅师是南宋时期的著名禅僧,属于临济下第十三代,深受宋孝宗的敬重而活跃于当时,是临济禅系传承者和看话禅的早期教学者[16],对于江浙禅宗的影响非常大,而洪武年间深受朝廷重用的禅派也主要是临济僧人[17],所以由密庵助缘刻行的《坛经》能够在洪武五年组织校勘藏经的第二年便被加以翻刻。另外,明代早期大藏经所采用的底本主要是在洪武年间依然在续刻中的《碛砂藏》,《碛砂藏》以刊刻地在“碛砂”而得名,而在碛砂创立佛教道场的寂堂禅师即是密庵咸杰的弟子。[3](P259)也就是说,密庵的禅系与《碛砂藏》存在有一定的关系,而《碛砂藏》又被明刻官藏作为底本,所以密庵本《坛经》在洪武六年的翻刻,便有可能是人们拟将此本作为入藏之本的表现。如果这种推测是成立的,人们选择密庵本入藏而不是其他版本,也可能与这种版本所表现出的更为强烈“佛经化”倾向有关。在密庵本中的一则校勘记便明确指出,“六祖所说之法既尊为‘经’,则其体格言词与语录行状塔铭之文固当有异”,因此主张应该将惠能弟子法海等改称“比丘”而非“禅师”。[18-19]
然而,密庵本虽然有一定的流传,但是似乎并没有被随后的明代大藏经收录,现存初刻南藏、永乐南藏以及永乐北臧中均无之。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当与参与初刻南藏和永乐南藏禅宗文献校勘的净戒有直接关系。
净戒禅师也是临济宗的传人,属于十八代,与密庵都属于临济下杨岐一派,不同在于密庵属于杨岐下虎丘一系而净戒则属于大慧一系[20]。在初刻南藏“誉”字函《古尊宿语录》卷八之末的校勘记中,净戒认为大藏经中除了应该收入禅史文献外,也应该收入禅语文献,认为“《古尊宿语》诸录,实后学指南,又不可无者,乃依旧本誊录,重加校正,《传灯》重复者去之。谨以《六祖坛经》列于首,南岳、马祖四家语继之;而颐公所未收者,则采《广灯录》诸书,以联《尊宿语》;自南岳至晦机等,又通得四十二家,共四十八卷”[3](P382)。其中特别提到拟将《六祖坛经》置于禅宗语录的最前面。学者研究认为,其千字文编号亦应为“誉”[3](P394)。由于作为禅史代表的《景德传灯录》与宋代以后流行的《六祖坛经》等语录存在一定的重复,所以净戒提到一条重要的原则,即“《传灯》重复者去之”。《六祖坛经》主要分为两部分,前者为大梵寺传法授戒,后者为惠能与弟子的机缘故事,后者多与《景德传灯录》相重复,所以经过净戒校勘的《坛经》版本只有惠能大梵寺传法授戒部分。主持禅籍入藏的净戒对《坛经》进行校勘时,并没有选择洪武六年所刻的密庵本而是以元代光孝寺住持宗宝所编本为底本。[7](P171)其中的具体原因虽然在净戒的校勘记中没有提到,但是从净戒本与密庵本的文本对照中,依然可以推导出二者并非完全没有关系。例如,从附录内容上看,净戒本《坛经》如密庵本一样,也将《坛经赞》纳入到《坛经》中,这种做法在之前的版本中并未有之,净戒本这样做应该是参照了密庵本的结果。另外,从校勘内容及其立场上看,密庵本中将惠能的一些弟子从“禅师”改为“比丘”的这一特别做法,在作为禅宗代表的净戒禅师看来或许并不能体现禅宗的特点,故而没有沿用。这可能是净戒转而以宗宝本为底本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看,由净戒禅师校勘出的《坛经》有三大特点,其一是仅取其所依据的元代宗宝本《坛经》的前六品内容,即惠能大梵寺说法传戒的内容;其二是修订了关于“自性三身佛”的顺序及其表述;其三是修订了关于“自性西方”的表述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净土信仰在明代的流行以及对于禅宗的影响。[21]
现在的现代净戒校本《坛经》有两部,一为柳田圣山《六祖坛经诸本集成》所收的“明版南藏本”(下文简称柳本),一为天津图书馆所藏嘉靖时期所刻永乐南藏本。天津图书馆所藏嘉靖南藏曾经由李国庆先生加以介绍[22],龙达瑞先生留意后并对其中所含有的《坛经》进行了拍照,且发现此本与《六祖坛经诸本集成》所收本有所不同。笔者经过详细比对,通过其中的刻经功德记及印章,发现二者均为永乐南藏本的民间重加印刻本;通过对照二者的内容,发现二者最前面的几页完全相同而柳本印刷已显得模糊且补刻字体已改为“宋体字”而非早期带有写经色彩的字体,而改用“宋体字”又是永乐南藏在后来被补刻的重要表现[7](P417),故而可断定柳本是对天津图书馆藏本所用版本的修补,也就是说天津图书馆所藏南藏本所依据的版本更早;从经文内容上看,二者除了个别字体上的差别外,柳本仅多出一个“相”字,位置是补刻的第一字;从板式上看,二者均为折装而每列17字,但由于天津图书馆所藏南藏本在刊刻时是照着写本进行,此本在将近经末部分中有一列为18字,柳本在补刻时将其作了更正,故而导致其后每页文字向后推一格,直至出现偈颂为止。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洪武五年开始校勘而最终开刻的初刻南藏完成后不久便因寺院大火而有毁损,所以初刻南藏在世间的流传很少。[7](P406)民国时期,在四川省上古寺发现其遗存后,据支那内学院僧人德潜的抄录,吕澂先生曾加以整理和研究,列出《六祖坛经》与《万善同归集》、《明觉语录》等经典在“用”、“军”二函之中[23],似乎初刻南藏中除了被编为《古尊宿语录》一部分的《坛经》版本外,在还有一部编号为“用”的《坛经》。遗憾的是,此部初刻南藏所收录的《六祖坛经》已经遗失而不见于后人整理的经录中[24]。即便如此,根据初刻南藏从整体上乃是对于宋代《碛砂藏》的翻刻,而《六祖坛经》在唐宋之间便被编入“军”字函中,故而如果德潜以及吕澂的转录不误,便可推论初刻南藏本《坛经》“用”字编号的由来并非出于偶然,应该是受以往已收录《坛经》的大藏经影响所致。从历代大藏经的卷帙数目以及《坛经》曾被剔除的事实来看[4](P1150-1551),大多宋藏的末函接近“军”字函,而《金藏》则超过之且尚含着《宝林传》,这也能从一个侧面印证《六祖坛经》在明代之前已经入藏。但是,由于永乐南藏以初刻南藏为底本,净戒在初刻南藏版《古尊宿语录》的校勘记又提及曾将《六祖坛经》列于《古尊宿语录》之首,而《古尊宿语录》的编号为“誉”,再加上现存永乐南藏中《六祖坛经》(“密”)和《古尊宿语录》(“勿”)正好也是相连的,这样便在学术界出现了初刻南藏所刻《六祖坛经》的编号到底为“誉”还是为“用”的问题[3](P393-399),甚至学者比较保守地认为《六祖坛经》的初次入藏是在永乐南藏中。[25]
由于净戒校本《坛经》最早被纳入明刻大藏经中而广为流传,所以成为明清之际的大藏经版《六祖坛经》的重要源头,不仅对大藏本《坛经》造成直接影响,而且对民间所刻版本也有一定影响。有关明清之际《坛经》入藏及其源流关系,笔者将另外撰文研究。实际上,由于《坛经》在禅宗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所以《坛经》的入藏不仅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个文化事件,其反映的不单是人们对《坛经》和禅宗的肯定和推重,也透露着中国佛教宗派乃至与其他教派关系在新时期的变化,这特别表现在明清入藏本《坛经》对于“自性西方”部分的校订之中,值得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