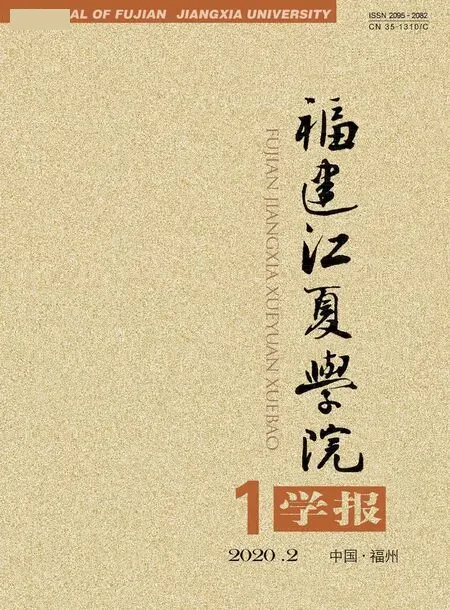战争主题与身份重构
——以林芙美子《浮云》为对象
戴玉金
(龙岩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龙岩,364012)
1868年,日本积极推动明治维新,提出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三大口号。一时之间,以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思潮快速涌入日本。在这样的思想冲击下,一方面,日本兴起了自由民权运动,民主宪政的思想得以传播开来;[1]一方面,传统守旧的封建等级观念被否定,立身出世、自由平等的思想开始融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樋口一叶、津田梅子、与谢野晶子为代表的一批女性杰出人物的登场,日本女性开始挣脱性别的枷锁,走向自我觉醒、自我表现、自我解放的场域。在这一批人物之中,林芙美子(1903—1951)作为杰出的知识女性之一而备受关注。
林芙美子的一生,经历了3个时代,即生于明治,长于大正,成名于昭和,被评为昭和时期三大女性作家之一。基于个人体验,林芙美子撰写了不少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横跨诗歌、传记、小说、散文、戏剧等诸多领域,尤其是以《流浪记》《浮云》《晚菊》为代表的一批小说。日本学者高山京子对林芙美子的评价是“日本的女性文学始于紫式部,樋口一叶将其升华,进而被林芙美子最大程度地加以继承。”[2]371将之推到日本女性文学系谱的重要位置。围绕林芙美子的前期研究,学术界或是关注林芙美子的战争记忆,突出反战意识[3]或者饥饿体验[4];或是探究林芙美子的独特的“流浪”意识[5],尤其是女性意识与生态观念[6],作为林芙美子女性书写的代表之作,也是日本战后小说中的一部杰出之作[7]97,历经3年创作、出版于1949年的长篇小说《浮云》则是一部极具文学史非凡意义的文学著作。
一、战争主题的返迁书写
依照《浮云》这部小说的文学范畴,或许我们可以提到中国学者柴红梅提出的“返迁文学”这一范畴。所谓“返迁文学”,是指“记录从战败到历经磨难返迁回国痛苦体验的文学作品。”日本人“即便身体回到日本,但是曾被祖国欺骗与抛弃的怨恨、丧失‘真正故乡’的迷茫、无国籍漂泊的不安,曾为殖民地人的体验……所有的一切将永远成为日本‘返迁民’解不开的心结,这使得他们最终不得不面临自我丧失的残酷现实”[8]。这样的文学作品包括了以“伪满洲”为对象的安部公房《野兽们奔向故乡》、三木卓《炮击的焦土上》,以台湾为对象的西川满《地狱的谷底》,也包括了林芙美子以越南为书写对象的小说《浮云》。
《浮云》这部小说以日本战败为宏大背景,讲述了战败遣返者幸田雪子自越南大叻返回日本东京,与主人公农林技师富冈兼吾之间的爱恨情愁的故事,整篇小说构筑了越南大叻的美好回忆和故乡东京的残酷现实这样“对立”的空间,凸显了以富冈为代表的日本男性中心的等级秩序与以雪子为代表的日本女性诉求身份认同彼此互为“悖论”式的图式,揭示了女性追求自由解放而被边缘化的困境,乃至整个战争给予人类,尤其是女性的痛苦与危害,谱写了一曲战争主题下女性追求身份认同、确立自我意识的挽歌。
首先,作为“返迁体验”,战争带给日本人的,就是战败初期犹如噩梦一般走向“堕落”的“切身体验”。与所谓的“拥抱战败”不同,这样的场景不仅体现为战后东京成为了“废墟”的直观感受,同时也是日本人陷入“不安”的心绪累积。小说之中,被遣返回国的雪子在车站“茫然地眺望着周围的战败惨象”,周围是“烧焦的废墟”,此时的她感受到的是“日本已经变了样”,“往日的东京生活已经改天换地”,“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从前的模样”。[9]5不仅如此,周围的人们“每张脸都显得那么苍白,那么无力,无数了无生气的面孔在车厢中叠加,简直像一趟搬运奴隶的列车”[9]4,就这样,雪子失去了自我,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精神和生活状态之中。对此,经历战败而被遣返回国的富冈也深具同感:“战争让我们做了一场噩梦……制造出一群不知何去何从、没有灵魂的人……不是吗?我们都堕落成了一群不伦不类的人。”[9]113陷入噩梦、不知何去何从,没有灵魂,只能堕落下去,就此成为战后日本人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其次,战争带给日本人的,较之这样“堕落”更为残酷的,就是不可逃避的“死亡”。在此,林芙美子描述了坚信“战争必胜论”的典型人物——加野的悲惨命运。小说之中,加野在越南大叻谈论战争之际,曾提到“当然打得赢啰。事到如今,不可能打败战吧……要是万一打了败仗的话,我干脆破腹自杀算了”[9]40。但是在日本战败,被遣送回日本之后,雪子前去探望病危的加野,“仿佛在迥然间目睹了一场人世的巨变”。出现在眼前的“曾经长着一张圆乎乎的娃娃脸”的加野变得“胡子拉碴”,显得“苍黑而瘦弱”,“好像突然老了十岁”,“简直就像加野长着另一个人的面孔”[9]144,加野失去了往日的健康和活力。生活的窘困,悲惨的境遇,令他陷入疾病的痛苦,饱受精神折磨,也让他意识到过去的自己“已经在战争中死了”,战争令加野的身心被“折磨得破败不堪”,犹如“一具活死尸”。[9]145最终,“曾是那么狂热的爱国者,坚信着日本不会战败”的加野“死后却以一场基督教的简单葬礼而告终”,成为了“一名战争的牺牲者”。[9]173牺牲与死亡,也就是“战败者”不可逆转的命运。
再次,战争带给日本人的,不止是堕落、死亡,同时也还出现了“异化”,也就是产生了戕害人类、杀害同伴的“怪物”。小说之中,雪子在写给富冈的信函中提到,富冈是“一个杀人的人”。正是富冈个人的缘故,导致富冈的太太、加野、阿蓉、阿世、青吉都“陷入了不幸”,富冈总是“让别人做牺牲品,自己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9]181。在经历了战败而陷入生活和感情困境之后,富冈意识到“自己这些年来在波澜起伏的苦斗中渐渐失却了人性。自己是一个心灵只剩下了空壳的人,一个躲藏在长着肉身的假人身后,借着魔鬼的心脏在走动的怪物”[9]256。尤其是在目睹雪子如此强韧的生命竟然也招致“毁灭”之际,富冈“像个孩子似的呜咽着哭了出来”,质疑着“人到底是什么?到底应当怎么做人?”[9]272竟不禁“想象着自己宛如浮云的身影。那是一片不知将会在何时、何地,消逝于瞬息之间的浮云”[9]275。“浮云”在此凸显出一种象征性的内涵。人是什么,如何做人,也是林芙美子来自心底的最大诉求。
事实上,林芙美子为了渲染“战败”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一个隐喻性的表现方式。一方面,小说之中提到了主人公雪子在越南大叻住着豪宅,享受着“天国”一般的生活,就好像“沉迷在海市蜃楼中一般。”[9]20这样的描述既与战后东京的“废墟体验”形成了鲜明对比,也隐喻性地预示了这样的“天国”生活会犹如“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一方面,雪子的内心充满了“不安”,犹如“不经意闯入空无一人的豪宅,心中渐渐产生了一种被惶惑不安所占据的感觉”[9]20,还预感到“大概用不了多久,日本人就会遭到报应”[9]89。所谓“报应”,也就是隐喻性地表露出日本帝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充满罪恶、无比残酷,而这样的暴行的“报应”也必将返还给战败的日本人。
与其说战争,倒不如说是“战败”,让日本人走向了堕落,走向了死亡,走向了“异化”。通过《浮云》这部小说,林芙美子把经历战争而返迁回日本的士兵与女性的空虚内心,把饱受战争伤害的疾苦与困境融入到小说的主题之中,并采取隐喻性、象征性的表现手法揭示了战争使人失去了人性和自我,使人的灵魂伴随着战争而逐渐消失,只剩下一个躯壳的“根本事实”。正如小说一开始所引用的,“倘若理性为万物之依据且万物即理性,假如放弃理性并憎恶理性为最大之不幸……——舍斯托夫”[9]1,战争固然是“一个不堪承受的重负”[9]213,但是正如俄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舍斯托夫(Lev Shestov,1866-1938)一直探究的“人的拯救”问题一样,如何回归“理性”,如何回归“自我”,应该就是林芙美子期待通过这部小说试图再现的核心主题。
二、性别差异的身份构建
战争语境不仅构筑起《浮云》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也书写了极为独特的返迁体验。不过,作为女性作家,尤其是针对女主人公雪子,小说始终贯穿了一种“女性主义”或者“性别”的视角。在这部小说中,男女间“非对称”的二元对立,以一种社会制度的方式、一种性别差异的悖论介入女主人公的生活,凸显女性失去多重性“保障”的悲歌,即没有安定的经济保障、社会保障和精神保障。
不可否认,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雪子自乡下抵达东京,被姐夫伊庭强奸和占有,而后为了摆脱伊庭而不得不远离东京,来到越南大叻。到了大叻之后,雪子与有妇之夫富冈相恋,一直到战争结束,富冈早一步回到日本,雪子追随之后返回东京。但是,在二者关系出现裂痕之际,“寂寞难耐”的雪子竟然与街上邂逅的西方人——乔发生了一段莫名的关系。后来,雪子再度回到前情人伊庭身边,并偷盗巨款,再度追随富冈到了日本最南端的屋久岛。这样的自戕性的堕落,最终导致雪子走向毁灭。在去屋久岛的途中,雪子意外地染上恶疾,最终病逝于屋久岛。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雪子始终在伊庭、富冈、乔这样的“男权势力”之间漂泊流浪、徘徊游离,找不到真正的爱,也得不到真正的爱。空虚颓废、漂泊堕落,成为了雪子一生的真实写照。
迄今为止的不少研究,皆将批判的对象指向父权制社会,指向男权中心主义,而忽略了日本女性的身份认同。或者说,迄今为止的研究聚焦于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而忽略了作为女性自身的身份定位的“重层性”。雪子与男性之间的“悖论”固然重要,而男主人公富冈与女性——具体而言,就是妻子邦子,情人阿蓉、雪子、阿世之间的“感情纠葛”则成为了一个研究的盲点。因此,通过这样的一系列女性自我形象的剖析与研究,或许我们可以认识到日本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的心路历程,也可以揭示出战后日本底层女性的求生意识与心底控诉。[4]
第一类女性,富冈的妻子——邦子,可以说是一位“贤妻良母”式的传统女性。自明治政府通过法令的形式确立下“贤妻良母制”的价值体系以来,日本女性就被贴上了繁衍后代、贞洁温顺、慈爱包容、甘于奉献的“道德”标签,并最终被抽象化地定性为女性的“天性”——母性。[10]作为富冈的妻子,邦子在富冈被派驻国外任职期间,留在日本悉心照顾着富冈的父母,任劳任怨、忠贞不渝,默默无闻地支撑着整个家庭。但是,含辛茹苦期盼到丈夫的归来,却又遇到来访的情人“雪子”。尽管察觉到了丈夫的出轨与背叛,邦子依旧忍辱负重,支持着丈夫的事业,始终不离不弃。即便是跟随富冈的父母回到老家,罹患重病,邦子更是“一声不响地忍受着病痛,也不做手术”。最后,得不到丈夫富冈丝毫关爱的邦子“被悲惨的生活折磨得没有人形”,在“惨不忍睹的状态下咽了气”,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告别了人世”。[9]206不言而喻,处在以男性为主宰者和统治者的日本社会环境下,处在以男性绝对话语权为核心而形成的道德、伦理和法律的规范下,具备了“贤妻良母”一切条件的邦子丧失了女性应有的话语权,不得不牺牲主体的自由,换取卑微的生存权。[11]182在富冈的眼中,妻子邦子不过是一个“外人”,只是一位“有名无实的妻子”,富冈也根本“就没有把邦子当做妻子对待过”[9]206。即使妻子患病死亡被安葬,作为丈夫的富冈也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悲痛,反而油然而生出一种“干爽利落的心情”,而且“越发感到一身轻松”。妻子的一切在他的心中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9]213。正是通过邦子的传统女性形象,凸显富冈非正常人的扭曲心理和精神状态。
第二类女性,就是作为女佣的、也就是被玩弄、被遗忘的越南女性——阿蓉。阿蓉是富冈作为农林技师被派往越南大叻工作期间的女佣,也是富冈寂寞无聊之际为了满足自己生理需求的情人。小说之中,林芙美子对阿蓉的描写不多,只是通过富冈的回忆提到自身和阿蓉的关系:“只是出于情欲的一时之欢”。即使到后来得知阿蓉为自己生下了孩子,富冈也还是无情地抛弃了她。在他的眼中,这一段关系只是“逢场作戏”的“旅情”而已。但是,这一事件却深刻地伤害了阿蓉,尽管阿蓉得到了与富冈分手之际的一部分金钱补偿,但却要经受未婚私生“混血儿”的耻辱而遭受他人的歧视,备受精神的折磨,且一生不得安宁。不言而喻,阿蓉就是林芙美子刻画的被男性玩弄,进而被抛弃的女性的代表,处在战争的语境下,这样的女性也只能陷入到无情的悲剧之中。
第三类女性,则是富冈在越南交往的第二个女性,也是富冈欲罢不能且又藕断丝连的小说女主人公——雪子,也是一位为了爱情而奋不顾身、忘却一切的女性。雪子最初留给富冈的印象,是“眼前这个言语上极为相同的同族女人”,这一点极为可贵,且与越南女——阿蓉存在着“天壤之别”。[9]36正是这样的“同族意识”,令两个难以忍受孤寂的人走到了一起。不过,等到二者回到东京,陷入穷困“潦倒”的富冈失去了往日在越南大叻的“朝气”,对雪子更是“心中感觉不到任何波动”,还萌生出一个“为什么雪子没死”的可怕想法。对于富冈和雪子来说,今后的去向“两人无从说起,只好忘记一切现实”[9]50。但是,在面临妻子病逝无钱下葬的窘困之境,富冈前往雪子住处借钱的时候,他却感受到雪子又恢复了往日在越南大叻期间的“风韵”,“身段变得年轻而丰满”[9]207。尤其是在得知雪子还“竟如此深爱自己”的时候,富冈又与雪子“达成了一次无上完美的心痛分享”[9]209。就这样,一次意外的重逢令两人的感情死灰复燃,也导致雪子为了富冈而偷窃了教会的巨款,并追随富冈去了屋久岛,最终悲惨地客死在那里。如果说雪子是一位游离于秩序之外的女性,故而无论是旧的秩序还是战后的新秩序都容不下她的话[5],那么,在富冈的心中,雪子则不过是一个“猎奇”的对象、心灵“慰藉”的对象,更是一个被利用的对象而已,也就不过只是“陌生人”的存在而已。[9]193
第四类女性,即是让富冈一见钟情、自由奔放、追求自我的理想情人——阿世。战败之后被遣返的艰难体验,令富冈和雪子产生了绝望的想法,相约一同前往伊香保殉情。在此,富冈意外邂逅酒馆的老板娘——阿世。面对阿世“丰满的肉体”,富冈一见钟情,开始考虑“今后的生活”,“寻死的打算已经消散了”。[9]127正因为阿世的出现,富冈又一次抛弃了雪子,且对雪子“无背叛后的歉疚之感”,还“空想着杀死”雪子。[9]128作为一位“家制度”下的反叛者,阿世不是一位愿意安分守己、“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其充满活力的青春和叛逆不训的个性让富冈一见钟情。“阿世没有化妆的脸上闪着润泽的光”,“阿世灼热的眼光”让富冈“只想借着阿世的诱惑重新活一次,甚至有一种焦灼的兴奋。”[9]128阿世的本真和自我给予了“战败者”富冈曾经的活力和强烈的欲望。阿世也为谈吐得体、魅力十足的富冈所吸引,不顾一切地背离了丈夫青吉,逃到东京与富冈同居。阿世的背叛行为无疑是对丈夫权威的蔑视和挑战,更是冲击着丈夫青吉无法承受的底线。正是因为这一层底线被践踏、被侮辱,故而阿世最终被丈夫活活勒死。在此,林芙美子刻画了一位为了追求本真的自我而走向叛逆传统、脱离家庭,但是终究摆脱不了家制男性的控制,最终付出代价而走向死亡的女性形象。
三、女性形象与战后文学
承前所述,林芙美子在描述男性权力主导下的性别差异的同时,也塑造了以妻子邦子、女佣阿蓉、情人雪子、情人阿世为代表的多样化的女性人物,并构筑起了以贤妻良母、被玩弄的女性、憧憬至爱的女性、追求自由自我的女性这样的重层化的女性形象。不言而喻,这样的女性形象的建构,应该说既是林芙美子文学创作之中的一种独特构思,也是“战败返迁”这一特殊背景下的真实写照。不过在此,我们也要提示一点,就是通过这样的人物塑造与形象构筑,林芙美子为战后的日本女性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参照体系。换言之,就是日本女性应该如何进行一种与战争诀别、与过去诀别的新的女性形象。而且,这一独创性的构思也引导了战后日本的女性文学,乃至战后日本文学,构筑起了以女性形象塑造为核心的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线。
作为“战后文学”的出发点之一,林芙美子创作的《浮云》这部小说也存在着不少值得审视与批评的地方。
第一,就这部小说的战争语境而言,无疑它是以战后日本社会的混乱颓废为刻画对象,细腻地描述了战后日本人虚无漂浮不定的精神、身体的缺失感与游离感。[12]虽然这部小说没有过多地描写战争硝烟——战争在此成为了一大背景——却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阴影和悲凉,尤其是战争给予日本人的巨大痛苦与悲惨记忆,这样的痛苦与记忆不仅留存在日本人的心底,也留存在作为“返迁者”的往返地域,即作为“外地”的殖民地——越南与作为“内地”的返迁地——东京,构筑起了处在二者的“张力”之间的强烈性对比与夸张式的想象。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返迁者而言,殖民地反过来成为“乐园”一般的存在,而作为本国日本则是沦落为“地狱”的存在。
第二,就这部小说所刻画的多样化的女性人物、重层化的女性形象而言,这部小说尽管也间接地印证了战后初期日本民众普遍存在的“受害者”意识[3],但是时至今日,林芙美子的女性书写依旧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不言而喻,在整个世界的女性书写中,女性作为受害者或者说“女性是证明民族受难的证据”[13]成为一道法则。正如评论日本Yoko Kawashima Watkins《So Far From The Bamboo Grove》展示的一位日本女性的记忆一样。战争期间的日本女性尽管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因为她们乃是加害国的一员,所以“一直被剥夺了倾诉苦难的权力和机会”[14]。换言之,即便是参与战争宣扬或者走上战场,她们也依旧是战争下不变的“受害者”。就此而言,采取女性叙述的方式,可以更多地获得同情与认可,这或许是林芙美子的一点构思之所在。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林芙美子几乎不曾更多地去关注阿蓉这样的越南女性的“悲剧”,也忘却了“南京大屠杀”这样重大事件中被大量戕害的中国女性[15],更不曾深入剖析战争何以令女性成为“受害者”的责任问题,这一点也是林芙美子这部小说的盲点所在。
第三,如果只是书写战争语境,只是刻画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女性或者日本人,那么,这部小说也难以称为“战后文学”的出发点之一。所谓“出发点”,应该是将战争遗留下来的一切痛苦与所有悲伤皆加以遗忘,从而转换一种心境,重新开始人生。就此而言,林芙美子的文学创作与其是为了缅怀过去,倒不如说更带有一种“未来指向”。正如中国学者杨本明所指出的,林芙美子对底层女性给予人文关怀,对女性自身的命运采取了哲学思考的态度,彰显战后这一新时代的女性的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11]4
作为战后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小说之一,林芙美子的《浮云》无疑为战后日本女性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提供了巨大启示。尤其值得称道的一点,即林芙美子以超越常识的个人经验,就父权制度规训下的女性生态进行书写,对性别差异构造下的悲剧化的女性地位进行控诉,对追逐爱情而不可自拔的女性意识表述同情,对游弋于婚姻制度之外的叛逆女性形象的塑造加以确证。就在这样的人物刻画与身份构筑的背景下,林芙美子展现了自身对于日本社会、对于战后这一时代的颠覆和超越,既张扬了处在道德与性别压抑下的女性欲望,也开辟了日本女性普遍而独特的私语空间,[11]3还重新审视了新时期女性的身份地位,更重构了女性群体的主体认识与自由观念,故而也具有被收录到“战后日本文学史”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