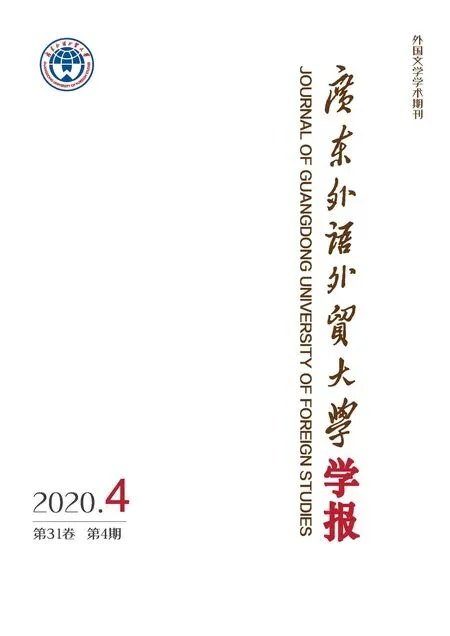追逐与逃避:《纸人》中的“承认”问题
肖霞
引 言
一九八三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 1911-1993)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不久,瑞典文学院资深评委仑奎斯特(A. Lundkvist)公开声称自己反对戈尔丁获奖,一时间,戈尔丁毫无选择地身陷评议旋涡。虽不乏实至名归的议论,但认为戈尔丁过于走运的声音时有耳闻。一九八四年,喧哗余波中,《纸人》(ThePaperMen)出版。小说主要以作家巴克雷的视角叙述了巴克雷与美国某大学教师塔克之间的纠葛:二人因传记授权委托书产生矛盾,以互相毁灭终局。学者们如塔克般被展现丑陋猥琐的时刻并不多见,评论圈反应纷纷,多数从塔克的立场思考:有人对号入座,认为作家污蔑映射自己(Carey, 2009: 415);有人直接用“作家的复仇”为副标题,大力为学者正名,认为作家对美国高等教育和美国文学研究界最多是知其皮毛,最糟是所知有误,塔克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教授(Dick, 1987: 135),只是英国人对美国学术之林傲慢的老一套看法的化身 (Boyd, 1988:186);有人委屈地说,没有学者的阐释,戈尔丁那些晦涩文字不会有如今的明晰性,“为何要把朋友写得野蛮粗俗呢?”(Jones, 1984: 675)
考虑到戈尔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无法安享荣誉,反而遭受言论风暴的强烈冲击,我们当然有理由认同上述观点,把《纸人》看作怨怼恨意的载体。但就笔者所见文献来看,对《纸人》的研究始终未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戈尔丁塑造道德卑劣的塔克算是对学术评论圈的嘲讽报复,为什么巴克雷的精神画像也毫无人格魅力,无法令人同情?作为小说叙述人,巴克雷畏首畏尾的躲避,猥琐可憎的过往,冗长乏味的反思,怒意澎湃的报复仅仅是戈尔丁用来发泄多年积累的对文学评论界的怨气吗?
作为故事中叙述人,巴克雷的所思所为可以比较充分地暴露在读者面前。他的离婚,他的逃避,他的冷漠,他的沉郁、无助、愤怒、挣扎和顿悟,线性历时或者组合共时于一个与多个时空断面,共同构建了一个集象征概念与血肉热度于一身的人物,记述了一个被塔克射出的子弹终止了的被他人承认、被自我承认的过程。从“象”上看,巴克雷不过是一个疲于应付生活的作家,但从“征”的角度审视,用保罗·利科的“承认”过程来定义,巴克雷是一个畏缩在自己制造的甲壳中,遇事只会逃避,得不到他人认同性承认,同时也无法认识自己,得不到自我承认的现代人。虽然良知的判断力量可以偶尔帮助他承认自己,但他最多不过是刚刚踏上呈现自我以承认自我,构建列维纳斯意义的伦理主体道路而已,远非摆脱了现代原子个体的生存困境。
甲壳中的巴克雷
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离不开承认。在《承认的过程》的“前言”中,保罗·利科(Paul Ricoeur,2005: x)提出,在语法层面上,动词承认有一个从主动态到被动态的反转:我积极地承认事物,承认他人,承认自我,同时也要甚至是要求被他人承认。他用三个大标题来勾勒承认过程的三个状态:作为认同的承认;自我承认;相互承认。这三个状态并非一种历时性排列,而是描述了构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人在世界中进行主动态行动或遭受被动态行动的意义。以获得承认的情况来衡量巴克雷的生活,几乎看不到任何积极成果。
巴克雷的人际关系结节甚多,纠结无解。婚姻中,他与妻子口角不停,终因妻子见到他多年前情人写的暧昧纸条而离家游荡;父女感情上,他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女儿,形同陌路;在意大利与同居伴侣相处时,他否定对方的宗教感情,最终被扫地出门。所有事情,因果相承,多是巴克雷行为选择的结果。即使妻子因他婚前与人暧昧的纸条离家,巴克雷也不算委屈,因为当时他正与另一个女人进行婚外情。这是妻子对婚姻不满的一次大爆发,尽管有偏差,但对事件性质的把握分毫不差。
如果不算塔克,巴克雷没有朋友。塔克接近巴克雷为的是获得传记写作授权,积累个人晋升的资本,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他把巴克雷物化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根本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责任:凌晨偷偷翻捡巴克雷家门外垃圾桶,希望窥见巴克雷其人其事;为收集资料,未经允许,每见巴克雷都私下录音;多次制造偶遇接触巴克雷,为了拿到授权独家撰写巴克雷传记,不惜以新婚妻子作为交换,不惜设计救命骗局。至于被追逐的巴克雷,自然要尽力保护隐私,小说主体部分的追逐与逃避就此展开。
对于小说纠葛的核心——那份传记授权文件,巴克雷言语上态度明确,不肯签字,但行动上信号意义模糊。他与塔克聊天喝酒相约晚餐,并对塔克献上的妻子欲拒还迎,使塔克一次次在希望失望中轮回。小说第十二章,经历了被塔克救命再次逃避之后的巴克雷阴郁反思,决定旧地重游,满足塔克的需求,却在闲逛中发现,大雾里臆想的悬崖根本不存在,栏杆断裂自以为命悬一线时离草地仅咫尺之遥,不可能有生命危险。塔克曾经探查过道路,必定清楚地貌,当时拼力相救,只是一种欺骗。于是,巴克雷一改约见的初衷,借传记授权委托书侮辱戏谑塔克,令塔克扮狗叫,舔舐盘子,却又在迫使塔克牺牲尊严换取委托书后不久收回授权,打算亲自撰写自传。塔克付出金钱、付出时间、付出尊严却一无所获,终于忍无可忍,枪击巴克雷。整部小说终止于巴克雷一个未完成的句子,巴克雷与塔克、与其他所有人矛盾扭曲的关系可能永远停留在了那半个句子上。
列维纳斯(E. Levinas)提出对自我的认知必须结合他者的视角,我们对他人面貌的“回应(response)”意味着我们对他人负有的“责任(responsibility)”。“response”与“responsibility”这两个英文词共享一个词根明确说明了二者的关系。但列维纳斯(2005: 98)认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称,我对他人负有责任,即使以死相酬,也不等待回报;“他人与我勿须互相回应,正是因此,我为他人所役;也正是基于此,我是一个‘主体’。是我,支持着所有人”。巴克雷无力正确回应自己对他人的责任,无法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构建一个列维纳斯意义上的主体。事实上,他在小说前十章的自叙中,经常处于一种面对他人的“无思”状态,隔膜厚重,除了逃避,束手无策。这里所说的“无思”并非说巴克雷毫无思考,他记录事件以及情绪或思绪,却未曾真正思考过如何承担责任,支持他人。争吵中,巴克雷的意大利情人愤怒指责他心里只有自己,总是说:“我,我,我的,我的”(Golding, 1984: 20)①。除了掩盖自己的旧日丑事,巴克雷不在乎任何事:妻子愤而出走,那就让她走;女儿伤心离开,那就让她离开;情人恼怒赶他出门,那就走人。他从一个旅店辗转到另一个旅店,处处安身,又无处安身。
巴克雷的一个朋友这样描述:“你这一辈子都在制造一副甲壳罩住自己,就像螃蟹、龙虾一样”。他无法与亲近的人和睦相处不仅因为他不爱他人,而且因为他用一副甲壳防备他人。在小说第二章,巴克雷明确陈述了自己的处事策略:“我把逃跑当作对任何问题的答案”,妻子发现暧昧信件后,他逃到俱乐部过夜;与意大利情人严重冷战时,虽然想到此时离开可能激化矛盾,他还是启程参加研讨会,结果返回后发现自己的东西被扔在门外;塔克纠缠,他仍然次次选择逃跑。这种逃跑不可能解决问题,不可能获得任何他人的认同,只能一步步众叛亲离,成为“老小丑,老混蛋”“孤独专家”“纸人”。“纸人”中的“纸”,可以指任何带有利益诉求的纸张。《纸人》中巴克雷与塔克都要靠纸上文字谋生,最终为了一纸传记授权协议,互相摧残,生死谑斗,生动表演了互不承认关系中的每一个个体为私利蝇营狗苟的可悲可怜和可恶。
舍勒(M. Scheler,1997: 160)曾说过:“现代人的‘社会形象’和说话、行动的社会自我犹如一件不可穿透的外罩,覆盖在他那真正‘内在’自我的个人的活跃之上”,巴克雷为自己打造的正是舍勒所说的“不可穿透的外罩”。塔克千方百计要获得传记授权,虽然目的只是获得教授头衔,但手段却是要揭开外罩,公开巴克雷的过往,两人的关系由此陷入僵局。他们在追求自我实现、获得社会认同的道路上,摒弃对他人的关照,在主客对立中寻求自我,深陷对抗他人的泥潭,结局可想而知。
无力承认自我的巴克雷
巴克雷表现的正是霍尼(K. Horney,2011: 43)讨论的现代社会自我孤立人格的典型特征,他“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做出决定,不以任何方式在感情上与他人发生关系”。这种回避人的神经官能症是人们试图解决内心冲突时,无意识用来制造和谐的一种方式,也是“感情麻木愚钝,对自己之所是、所爱、所恨、所欲、所想、所惧、所怨、所信都无所知”,与自己越来越疏远的一种方式。“甲壳”“外罩”之下,巴克雷又是一副什么样子呢?
对于主观性来说,永远保持其无法克服的外在性的事物就是超越的。如此,共有四个超越存在:世界、上帝、自我、他者(赵汀阳,2011: 147-153)。在巴克雷的主观体验中,重要的超越存在是他者与自我。对于他者,巴克雷既敏感又迟钝: 他对不利自身的信息极为警觉,一旦有问题立刻行动,可惜所谓的行动不过是逃跑;迟钝表现在无法理解他者,无法回应他者,他者是巴克雷意识之外的超越存在,这一点前文已谈及。此处所要分析的是那个操控当下巴克雷的自我超越存在,或者说是处于不同时空与当下自我分离的旧日自我与当下巴克雷的同一性和矛盾性。过往时空节点上的巴克雷当然是他本人,但实体存在已经无从寻觅,能够触摸到的不过是一些语言和想象的建构,是不同价值观念指导下的认同在自身中的意识显现,是一种无法被当前巴克雷控制的超越性存在。在小说大部分篇幅中,处于过去时空点上的巴克雷已经成为一种当下巴克雷不可触碰的虚构存在,是巴克雷的当下“我思”指挥他遮蔽的一种存在。巴克雷非常抵触探究那个旧日自我的面目,使之成为自身意识中的他者。他的当下意识一方面服务于已被视为他者的自我,努力遮蔽其面目;一方面在形势逼迫下不得不开始理解、接受、承认这个他者自我,巴克雷的痛苦就在这个矛盾中产生。
与其说巴克雷糟糕的人际关系是因为他无法得到妻女、情人、友人等他人的承认,毋宁说他不愿敞开自己,获得当下意识对于他者化了的旧日自我的承认而导致的结果。在躲避塔克、逃离外在他者的过程中,巴克雷行为的核心意图便是捍卫这个自身中的他者自我不被发掘,不被曝光。但是费心遮蔽不但没有能够掌控这个他者自我,反而沦为其奴仆,与他人与自我都越来越疏远。巴克雷回避塔克的原因很容易被归结为塔克追逐手段之寡廉鲜耻,但令人费解的是,待妻女情人均不上心,未曾施以安慰体恤的巴克雷,对待塔克的追逐显得拖泥带水。他一面躲避塔克,一面又在塔克设计的各种偶遇中欣欣然与他喝酒聊天相约游览。每当两人关系似乎更进一步,可以深入谈话了,巴克雷便做贼心虚一般立刻溜走。他没有任何义务满足塔克,根本不必如此鬼祟。这说明在巴克雷意识中,最是不能触碰的不是塔克,而是他内心中那个羞于被塔克窥探、深埋于今日巴克雷意识中并控制了巴克雷当下与未来行动选择、享有一种超越性存在无法被敞开的旧日自我。周围人对巴克雷的负面评价实际上已经被巴克雷认同,他以“自我贬损的方式内化了这种形象”(Ricoeur, 2005: 214)。不但总是用负面词语定义自己,定义自己的写作,而且畏缩于甲壳,坚决不肯接近那个被贬损了的他者自我禁区,无论何时他都不愿意回忆,不愿意反思。
更糟的是,通过责任转移,巴克雷把自己对内心他者自我的忌惮不知不觉外化为塔克。塔克成为一种代表巴克雷他者自我的异己力量,逃避塔克便是逃避对他者自我的探究,对他者自我的拒绝直接导致了对塔克的拒绝。所以,塔克施救,巴克雷以为自己悬崖逃生后,不感恩、不庆幸、不后怕,而是“愤怒、仇恨和恐惧”,“咕哝不清地谴责:‘我好像欠你一条命’”。“谴责”一词不合常理,“愤怒、仇恨和恐惧”也是当时情境中极为乖张的情绪反应。这表明,塔克救命所触发的是巴克雷对逼迫他接近自身他者自我的强烈怨恨。舍勒(1999: 401)认为“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的自我毒害”,这种不利己也不利人的“自我毒害”是巴克雷错误回应他人与自身伦理关系的关键原因之一。一旦他不肯承认自身中异己性存在,反而把它外化为塔克,他会误以为解决了塔克就解决了自己惧怕的自身中的异己。承认塔克的救命之恩,显然在道义上巴克雷有责任报答,最好是应允塔克梦寐以求的传记授权,但令旧日自我曝光,对巴克雷来说极为可怕。所以塔克的救命之恩不会缓解这种导向错误的怨恨,反而加剧了它的活动,使巴克雷无计可施,只能再次迅速逃跑。
直到经历恍惚梦境,疾病袭击,教堂顿悟,认识到“我们是什么并不由我们做主”,承认“我. 是. 罪”,达到某种程度的自我承认之后,巴克雷才打电话约塔克再次见面,准备借着与塔克沟通结束这一切。节外生枝的是,巴克雷旧地重游发现塔克的救命之恩不过是一场欺骗,原本不得不迫近自身中他者自我的巴克雷突然获得了一个延迟曝光、再次挣扎,同时为不肯敞开自己而遭受的折磨进行报复的道德立场。于是巴克雷提闸放洪,让蓄积已久的怨气裹胁各种情绪垃圾汹汹而去,伤人害己,更加远离了承认自我、承认他人的轨道。由于这是一个更加错误的逃避行为,巴克雷报复塔克之后,发现原本就勒着自己的那根想象中的钢丝现在“不仅是紧,而是紧紧勒进胸口的肉里”。转移责任的怨恨所造成的“自我毒害”在这段描写中表现得极为明确,他的心灵未曾因报复得到任何慰藉,反而遭受了更大的痛苦。
经过与塔克几个回合的追与逃,通过对救命事件真相的发现,历经报复后的幻梦、反思,巴克雷感觉“我已经毁了,不属于人这一族类了,只是人的魂灵与记忆”。用黑格尔主奴辩证法话语来解释,此时的巴克雷已经沦为一个自身中他者自我的奴隶,存在的任务便是服务于那个自身中的他者,以至于完全失去自主性。对自我的承认在这里几乎是彻底失败了,但巴克雷毕竟还在抗争,努力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我承认。报复塔克后的痛苦,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巴克雷内心中潜在的承认自我的需求和欲望,这种需求和欲望曾帮助他放弃染指塔克的妻子,也帮助他最终决定写出自传文字交给塔克使用。但遗憾的是,塔克用子弹关闭了巴克雷刚刚开启的这扇承认自我、承认他者的大门。
“敌人是谁”与“我是谁”
“人们根本不理解,自我认识自古以来便被看成是‘最困难的’,例如,尼采便说过一句无比深刻的话:‘每个人都是距离自己最远者’(这是对认识而言,我不妨补充一句:这恰恰是因为他在实际上是‘距离自己最近者’)”(舍勒, 1999:380)。巴克雷的故事,正可以诠释舍勒这句话。《纸人》中表现的是社会洪流中原子式存在的现代人所面临的最大困难:获得他人承认、获得自我承认及互相承认。
戈尔丁小说里的人物各有自己的优点、缺点和特点,与戈尔丁的人文关怀息息相关,《纸人》中的人物也不例外。巴克雷这个形象绝非一个酗酒漂泊的作家这么简单,塔克也绝不仅仅是戈尔丁发泄私愤的一个工具。贴近《纸人》中的情境,身处文学工业场的人们可能不由自主就选择塔克或者巴克雷的立场,去寻找与自己对立的“敌人”。然而,如果我们稍微站得远一些,或许可以找到问题的真正根源,脱离这种损人害己的对抗困境。
《纸人》中最大的矛盾是塔克与巴克雷为了传记授权而起的纠缠,但二人之间原本并无根本性冲突。塔克的追逐是为了承认,他需要通过巴克雷获取教授头衔、学术圈声誉等成功标志。巴克雷的逃避和报复本质上也是一场关于承认的斗争,其核心症结是对自我的承认。事件表层的悖谬是,巴克雷承认自我的方式是保护自身中他者自我的私密性,这与塔克希望得到承认的途径恰好背道而驰。巴克雷选择了使他误入责任转移歧途的自保措施,无法在回应他者的过程中构建一个负责任的伦理主体,而塔克的追逐也根本没有考虑巴克雷作为一个他者的诉求。二人在获得承认的角力过程中从不考虑自己对对方的责任,矛盾日渐加深,终于爆发为不可解的仇恨。如果仅止于上述叙事内容,这分明只是一个文学评论者与作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如果从“象”转向“征”,从报复打击等具体任务具体情境阐释转向巴克雷与塔克所代表的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内心中他者自我之间普遍的矛盾对立,把思考的问题从“敌人是谁”转向“我是谁”,《纸人》中的人物隐喻便呈现出一种更为深刻的内涵。
对巴克雷来说,“敌人是谁”这种问题仅仅剖开了表层,是一个“象”的问题,巴克雷要躲避的人,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算是他的敌人。这种现代原子式个体必然对他人充满疑惧,不但与他人隔阂日深,而且自身最终也会在永无休止的怀疑与焦虑中与自己产生巨大的隔膜和疏远,乃至分裂,无法理解内心自我,无法理解自身行动目的,最终丧失生存的意义感。抗拒塔克等他人接近,保护自我的初衷因策略不当而遭受自身中他者奴役的巴克雷,便是一个典型例证。一个又一个心理学家,从弗洛伊德、荣格,到卡伦·霍尼、艾里希·弗洛姆等都对现代人在社会中与他人互动表现出的各种神经症进行过精辟剖析,并由此得到广泛关注。所以,思考“我是谁”,进而决定我要如何与他人互动,不仅是巴克雷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所有现代人要解决的问题。建立一个可以定位个体精神和肉体意义的谱系,确定“我是谁”是一切行为关系的肇始之处。在没有确定“我是谁”之前便确定“敌人是谁”显然是舍本逐末,根本不可能理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走出他人的地狱,摆脱四面树敌的困境。
从这个意义上讲,《纸人》不是戈尔丁粗率任性发泄不满的工具,巴克雷也不仅是“一段不滑稽的闹剧、单薄如纸的人物构成的粪色叙述”(Boyd, 1988: 188)的主人公,一个极为自私、幼稚、褊狭、不负责任的人,他是一个可以与戈尔丁许多小说中的象征性主人公媲美的形象。海因斯(Hynes,1985: 99-100) 称戈尔丁小说为“道德范式(moral models)”,认为戈尔丁不是伊索那种寓言作家,而是如加缪、卡夫卡一般,可以跻身二十世纪重要的象征性小说作家之列。戈尔丁“拥有的各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之一就是能够使人物是抽象概念的具象,却不会成为抽象概念本身”。综观戈尔丁的创作,相较于戈尔丁受到评论界赞赏的前期著作中的马丁和萨米等人物,巴克雷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毫不逊色。
小说题目《纸人》在英文中是复数,如果逐字英汉对译出来是“那些纸人们”。任何载有文字意义的纸片:日记、书信、账单、传记授权书、巴克雷发表的小说、塔克希望写出的传记等等,俨然规定着人,描述着人。巴克雷肯定不是唯一被困于纸片叙述境地的人。塔克也深陷叙述魔魇,不顾一切追求纸上叙述带来的利益,把自己的存在完全外化在纸片叙述上,从根本上物化了巴克雷也物化了自己。巴克雷与塔克的纠葛就是丧失了认识自我的能力,无法正确回应他人,只顾对付各种“敌人”的众多现代人的生活写照。因这种人际关系导致的焦虑、恐慌、怨恨、愤怒等等负面情绪每时每刻都在为人们制造或大或小的痛苦。无论何时,我们翻开报纸、打开网页,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这种互不信任、互相指责、互不承认的叙说。《纸人》是戈尔丁为现代个体的生存状态提供的艺术摹写,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现实表达,所喻示的是现代背景下个体辨明自身获得承认的困难。那些因塔克这个人物可能的映射引发的猜测议论或许并不多余,对于巴克雷与塔克的不光彩行径的抨击或许并不离题,但都没有击中这部小说的要害,走入作品的真正象征寓意。
结 语
阅读《纸人》,人们需要思考的是个人构建他者承认、自我承认的过程中抵死抗拒的时刻,尴尬恐惧的时刻,猥琐算计的时刻。在每一时刻,一定会有内在与外在的他者的参与。如何与内在他者自我和外在他者互动,担负起列维纳斯所说的每一个主体对于他者的伦理责任,完成适当的承认,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思考的人生问题。尽管巴克雷认识到问题症结的时刻姗姗来迟,以至于被塔克持枪射击,生死难卜,但他苦苦思索,艰难走出自己借以逃避的内心甲壳,通过给塔克书写自传材料来承认自我也承认他人的努力,是古稀之年的戈尔丁呈现的一系列人生困境可能的出路之一,值得所有身处各种二元对立矛盾中的人们深思。
注释:
①本文中出自小说《纸人》的引文由作者根据Golding W.1984. The paper man[M]. Londen: Faber and Faber翻译,此后不再一一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