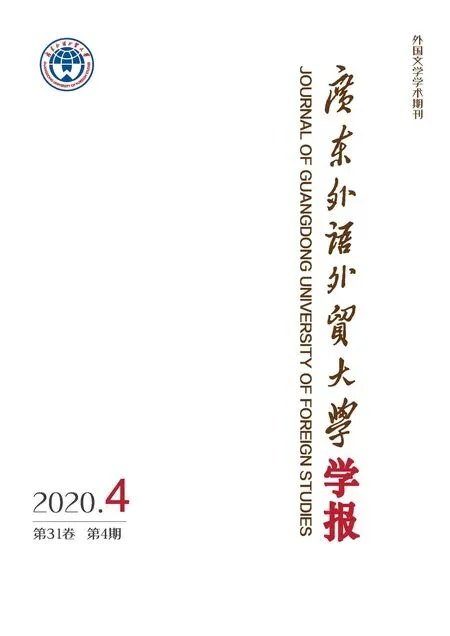《被掩埋的巨人》中的地点记忆与身份认同
刘杰
引 言
近年来,记忆研究的热潮逐渐转向社会文化学领域,地方作为承载记忆的媒介之一也逐渐受到关注。地方承载记忆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罗马人借助场景提升记忆之术,场景与形象共同构成了一种内在空间,储存记忆。地方与记忆之间的辩证联系随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记忆理论的兴起逐渐受到关注。弗朗西斯·叶芝(Yeats Frances Amelia)从建筑中看到记忆,认为“最常用的记忆场景是建筑类系统”(Yates, 1966: 3);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992:38)初次提出记忆在社会中的建构作用;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989:5)提出“记忆之场”,认为记忆在特定的地方生成一种历史的连续性并能够延续下去;扬·阿斯曼(Jan Assmann,2015:46)基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提出了“文化记忆”概念,“文化记忆通过文字或非文字性的、已被固定下来的客观外化物发挥作用”;之后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2016:344)提到,“虽然地点之中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是它们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是因为它们能够通过把回忆固定在某一地点之上,使其得到固定和证实,它们还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这种持久性比起个体的或以人造物为具体形态的对时代文化的短暂回忆更加长久”,深刻阐述了地方或地点的记忆媒介作用。文化记忆的研究不仅在于记忆的建构作用,还聚焦于记忆在不同媒介中对个体或集体产生的影响。因此,文化记忆“成了建立个人和集体身份认同的关键”(Antzem, et al, 1997:7)。
日裔英籍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作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之一,创作了大量有关记忆的小说。二○一五年石黑一雄出版《被掩埋的巨人》(TheBuriedGiant),该作品一经出版便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石黑一雄以公元五六世纪的后亚瑟王时代为创作背景,以一对不列颠老夫妇的记忆追寻之旅为轴线,不断揭开被掩盖的真相,隐喻性重塑英国民族初型时期的文化记忆,唤起人们对混乱时期英国民族共享过去的无限想象与追忆。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束少军(2015)首先探讨了“记忆碎片化的伦理情境下个体与集体在记忆选择上面临的伦理困境”;王岚(2018)认为作品以隐喻的方式书写了记忆与历史,“倡导文化多样性、文化融合和对非本族文化的宽容”;郑佰青(2018)认为小说记忆书写维度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记忆、遗忘、创伤等;艾迪塔(Edyta Lorek-Jezińska,2016)从创伤叙事视角解读作品,探讨“文本的缺场与忧郁,揭示出哀悼过程的复杂性”;凯瑟琳·伍德(Catherine Charlwood,2018)从记忆的心理学角度分析叙述者的角色和读者对文本的反应,认为石黑一雄延续记忆与民族的主题。本文从文化记忆视角切入,探析小说中不同地方上所承载的记忆在建构民族共同过去以及身份认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借助不同地方的所见所闻,石黑一雄将宏大的历史与人物命运编织在一起,以奇幻的方式书写了那段空白的历史,展现了个体在阴暗复杂的历史变迁中对身份的追寻与认同。本文聚焦于巢穴、修道院、巨人冢三个地方,探讨石黑一雄如何将文化与记忆元素写入不同地方,借助地方重塑文化记忆,使个体进入新的身份认同。
巢穴:“他者”驱逐与身份焦虑
石黑一雄对巢穴的细致描绘,折射出地方具有排斥“他者”的功能。地方和事物是记忆重要的触发要素,引发人物对身份的焦虑,使追寻记忆成为必然。石黑一雄将民族的文化记忆象征写入了巢穴的建筑、生活用品等具体物体之中,以第三人称及第一人称视角展现出来,同时巢穴内所发生的事件也成为刺激记忆的触发器,促使主体不断唤醒遗忘的记忆。人是记忆的活载体,他们的交往对记忆的延续与传承有重要的作用。而村民集体陷入失忆,过去的一切处于失语状态,营造了一种异常记忆氛围,成为一种特殊的记忆符号。随着主体对地方的情感移入与记忆的反射,各种符号组成一幅重要的图式,绘制成“他我记忆”,触发主体的身份危机,真正意识到搭建过去与现在桥梁的必要性。
巢穴内的位置分布塑造了“他者”的存在,消除了地方认同感。作为不列颠民族村民的居住场所,巢穴是凝聚着家族记忆与文化的地方,可称作“代际之地”(Generation-enorte)。阿莱达·阿斯曼(2016:346)认为“赋予某些地点一种特殊记忆力,首先是他们与家族历史的固定长期的联系。这地点便是‘家庭之地’或者‘代际之地’”。首先,埃克索夫妇在家族之地被边缘化,形成他者之分。巢穴呈现开放式布局,所有人集中在“大室”中取暖生活,然而埃克索夫妇却不知为何居住在巢穴的最外围,“住所受自然侵袭较多,大家晚上聚集的大室中烧着火堆,但他们几乎享受不到”(石黑一雄,2016:5)①。地理位置上的疏远带来了心理上的排斥。由于缺乏交流,老夫妇无法探究出无意识遗忘的缘由,从而引发对“他者”身份的质疑与自我身份的焦虑。其次,作为“家庭之地”,巢穴固化了过去的记忆,老夫妇偶尔闪回的记忆,意识到儿子的缺场,陷入自我忧虑,触发了身份危机。无意识遗忘的过去在长时间的潜伏和遗忘状态下并没有完全消除,相反以一种特有的“新鲜”状态掩藏于主体的意识中。巢穴的当下生活激发埃克索夫妇的无意识,引发对“他者”身份的焦虑,记忆的诉求变得尤为迫切。
巢穴对外来者的规避与驱逐构成了特殊的文化事件,引发主体对记忆与身份的忧虑。人,作为记忆的活载体,他们的运动可以为地方注入新的活力。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2013:145)曾说道:“行为者之所以能够表现出唤起重要回忆的能力,是通过他在意识中建立一道保护他远离一大堆相互间没有关联的回忆的屏障而完成的”。行为者即每个个体都是自我记忆的能手,石黑一雄借助人的运动,将掩埋的民族记忆带入记忆遗忘之地,制造“他我记忆”与自我记忆的共生矛盾,引发了个体的身份焦虑。不列颠人居住的巢穴附近出现流散的人,他们身披黑色斗篷,遮遮掩掩,形迹可疑。巢穴内的所有居民看到他们,便将他们驱赶出去。他们的异常着装完全区别于不列颠文化,而且自称是撒克逊人,让村民心生疑虑。比特丽丝出于好心与他们进行交涉,却被村民视为“施咒”行为。流散人群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本身所带来的交流记忆构成一种外来文化,对巢穴内部的自身文化造成冲击,促进了记忆的流动。正是巢穴对流散人群的驱逐与排斥带来了“他我记忆”,使比特丽丝更加坚定旅行的意志,引发了主体对过去记忆与身份的焦虑,促进了对遗忘记忆的追寻。
巢穴内部利用地方特权剥夺个体的物品使用权,进一步加深了个体的身份焦虑,促进记忆的运动。在巢穴中,蜡烛是重要的生活用品,能够点亮黑暗。而埃克索夫妇却被剥夺了使用蜡烛的权利,比特丽丝的身体意识中充满了对蜡烛的渴望,当她收到小女孩送的粗短蜡烛时,她小心守护,在混乱中开心地对埃克索说道:“这是我们的,埃克索!我们再也不用在黑暗中坐着了”。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描写了火花的意义“在灵魂的深处产生了事情的原始图像”(冯亚琳,等,2012:171)。火焰是对一种无法支配的认知能力的表征,它能够点燃记忆之网,在时间的长河中让遗忘与荒废凸显出来。而现实是埃克索夫妇被剥夺回忆的主动权,他们的传统认知能力被摧毁。埃克索夫妇的蜡烛禁忌是由村落的议事会一致讨论通过的,这加深了埃克索夫妇的他者认同,刺激主体的自我记忆,去追寻一切之根本。蜡烛禁用条令作为“他我记忆”的客观外化事件将主体转化为记忆的媒介,激活了隐匿的过往,点燃了身份危机的焦虑之火,将记忆的承载者向外驱逐,找寻记忆的真相。
修道院:“野蛮”暴露与身份想象
修道院记录着残暴的过去,成为特定时代下的社会存在,刺激了个体的记忆力,使个体走入身份的想象。这种想象来自僧侣们的异教仪式展演与修道院记忆痕迹的“挖掘”。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记忆术便具有将不可信的记忆转为可信记忆的强大功能,这主要依托于记忆与空间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图像与空间融为一体,作为记忆媒介,逐渐转化为将建筑物视为记忆象征。修道院在小说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石黑一雄将记忆写入修道院内具体的人和物中,成为特殊的记忆形象,它们的空间化作激活器刺激个体展开身份的无限想象。
修道院内的仪式展演存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引发主体对所指的猜疑。在文字还未出现之前,信息的承载者并不是书籍,而是一些专职的承载者,比如萨满、吟游诗人、祭司等等,他们本身拥有一种从“日常生活和义务中抽离的特质”(扬·阿斯曼,2015:48)②。生活在修道院的僧侣们是上帝荣光与仁慈的传承者,本应是探讨学问并传递知识的“知识分子共同体”(intellectual community),事实却恰好反之。埃克索和维斯坦无意中发现这些知识分子的黑暗秘密,根据不同寻常的木屋与铁笼,他们猜测人在一种仪式中把自己锁在笼子里喂食山里的鸟,铁面具用来防止眼睛被残害。扬·阿斯曼(2015:51)指出,文化记忆的内容与“发生在绝对过去的事件”相关,以“被固定下来的客观外化物”为载体,借助“文字、图像、仪式等进行的传统的、象征性的编码与展演”实现。修道院内所进行异教仪式在能指层面是神圣的、仁慈的,而所指却是野蛮的现实,亵渎了基督教的宗旨。“仪式通过集体力发挥作用,而集体力也通过仪式产生作用”(Emile, 2008:411)。扭曲的忏悔仪式,使修道院的僧侣成为一种凝聚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记忆形象,蕴含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激发失忆个体对仪式背后真相的探索。
僧侣们经由异教仪式所遗留在身体上的痕迹上升为文字式的回忆隐喻,增强了记忆的“密集性”,使相关联的语境与指向性得以释放,逆向抵制了遗忘。有关“文字隐喻”的阐述源远流长,柏拉图将“蜡板”视为记忆的表征,这也为亚里士多德的“印章”隐喻提供了灵感。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借用“羊皮纸”隐喻回忆的逆转能力。不论是蜡板、印章还是羊皮纸,都肯定了记忆的内向性系统运作。尼采(2015:295)持相反观点,他认为记忆不是写入心灵的而是写入身体的,“只有不停疼痛的东西,才能够留在记忆里”,痛苦是一种加强记忆的工具,因此,伤疤、疤痕成为一种身体文字,直击承受者的心灵深处。僧侣们借助仪式达到遗忘过去的一致性,而肉体上的痛苦与痕迹使修道院的僧侣们分崩离析,以神父乔纳斯(Jonus)为代表的部分僧侣认清“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不会获得宽恕”(153),而院长一派却仍固执己见。僧侣们将遗忘的过去外化于身成为文字痕迹,固化了集体成员的共同记忆,抵制了“社会性的第二次死亡(遗忘)”(Aleida A, 2011:171)。这些身体文字是对记忆的呼唤,激起失忆个体对当下的质疑与过往的想象。
文化记忆的“图像”媒介也可以映射到修道院的整座建筑中。维斯坦与埃克索等人在修道院内的参观,展现了个体大脑中存储的“回忆形象”对事物、环境的观察和感知的影响。修道院内的石塔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记忆符号不断刺激外来者的存储记忆。扬·阿斯曼(2015:30)提出,记忆建立在概念与图像融合的双重基础之上。石塔内墙上痕迹不断激活储存在大脑之中的文化记忆图像,战争时期的景象在维斯坦眼前几乎复活,让他以动态的眼光看待眼前的实景。维斯坦不仅是观察者,也是一名模仿者。石塔在维斯坦眼中是一个流动的战场,这里布满了各种陷阱;当大量敌人进攻石塔时,撒克逊的武士沿着台阶一边防御一边撤退,台阶的宽度只允许两人站立;在出口有壁龛并藏有火把,当敌人逼近时,撒克逊武士便将火把投到壕沟中,很快石塔便成为一片地狱火海,不列颠的敌人无路可逃,而撒克逊的武士借石塔后的干草逃脱。维斯坦识别出同族人遗留下的遗产,读懂了石塔内的建筑艺术。在面临布雷纳斯爵爷的捕杀时,维斯坦模仿族人的战斗方法得以逃脱。修道院内虽保留着表面的传统关联,但其原本意义被僧侣们的异教仪式与石塔的特殊构造打破,对重塑掩埋记忆有积极作用。记忆在重塑的同时伴随着个体对身份的想象,一方面包括埃克索对过去社会中骑士身份以及家庭中背叛者身份的想象,另一方面是维斯坦对撒克逊民族集体身份的想象。
巨人冢:“权利”消解与身份认同
地方既担任储存和唤醒个人与集体记忆的重要责任,也承担着记忆的刻写与重构的义务。墓穴是古老历史和文化的见证与象征,墓穴的“挖掘”过程中“保存了创伤性过往的威胁潜力”(冯亚琳,等,2012:125)。巨人冢是一座典型的墓穴,延续了亚瑟王的权力,母龙是操纵遗忘大屠杀历史的权利中心。石黑一雄借助维斯坦之手完成最高的仪式——屠龙,消解了权利的中心,打开了文化记忆的核心,巨人冢得到新生,从而使遗忘的记忆重新刻写,过去与现在重新连接。詹姆斯(James William,1950:332)曾指出,“身份认同不止包含当下的我,也涉及过去的那个我”。复归的记忆让个体与集体在共时和历时双维度上建立起一种连续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不是分裂的,而是集体的。石黑一雄希望借助宽恕式的“遗忘”建立不列颠与撒克逊民众集体统一的共同体意识。
纪念碑是过去的物质性体现,以石头的形式永久固定下来,成为一种“文化文本”。处于遗忘状态的共享过去依托于“文字、仪式和纪念碑”等文化形式,有助于“身份的凝结”,同时具有“重构能力”。石冢中引人注目的便是那座奇特的纪念碑。石黑一雄以第二人称的视角向读者介绍巨人冢,给读者一种直观的感受。“你们有些人会有隆重的纪念碑,让活着的人记住你们受的罪。有些人只会有粗糙的木头十字架或者彩色石块,其他人呢,就只能藏匿在历史的阴影中。无论如何,你们都是一个古老进程的一部分,所以当初立巨人冢,有可能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地方很久以前发生过的类似悲剧——年轻的无辜者在战争中遭到屠杀”(273)。石冢作为一种特殊的记忆载体,蕴含着记忆的活力,触发个体大脑中的存储记忆。当比特丽丝走到石冢前,低着头面对石块,像是道歉一样,埃克索看到这一幕,只有愤怒与恐惧涌上心头,因为他们的儿子早已死去,他们的婚姻曾有背叛,这座无名的石碑象征着创伤的过去,是抵制遗忘、激发记忆的触发器,彰显了文化记忆在载体重现与社会过程中的张力。
新生的巨人冢揭示了过去生命的痕迹,石黑一雄欲借新生的巨人冢建构新的历史生命力,使之“崇高化”,从而走入新的身份认同。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提出崇高的历史经验,具体指的是主体在时间意识中的情感体验。“崇高”属于康德美学中的一个概念,与“优美”相对应,含有痛苦和恐怖的意思,崇高的历史经验更在于融合在心情和感受中,经历文化创伤的个体主观上有遗忘的倾向,但过去依旧储存在纪念碑、博物馆这样的记忆空间里。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创伤虽挑战了身份,但最终对身份持有敬意,然而崇高却要求我们放弃原来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创伤催生了记忆,而崇高催生了遗忘”(Ankersmit,2015:318)。个体要承认过去,克服创伤,应该将过去“崇高化”,立足当下,选择性“遗忘”,从而进入建构新的身份。安克斯密特发现了历史意识的本质:“我们之所以能够超越过去,必要的条件是能讲述一个最终的故事,其内容是关于我们恰恰由于讲述此故事的能力而放弃的东西——因而,那也就是对创伤性经验的克服”。埃克索向船夫讲述了他们的婚姻裂痕,承认曾经的复仇心理,最终选择“遗忘”创伤,使两人之间爱情走向“崇高化”。维斯坦虽然心中的复仇火焰高涨,但是情感与行为上有将过去“崇高化”倾向。维斯坦屠杀母龙之后面露难色,感慨自己与不列颠人有了感情,变得软弱。此外,维斯坦还“特赦”了不列颠人埃克索夫妇,友善地提醒他们如何逃离接下来的腥风血雨,同时坚守与埃克索夫妇的约定,埋葬了高文的尸体。这一切表明承认过去并选择性“遗忘”创伤,有助于个体走出创伤并建构新的身份,两个冲突矛盾的民族也会有共建和平框架共存的可能。这种崇高化的倾向隐含石黑一雄对当下世界的隐喻,拥有共同创伤的国家或民族间若能超越创伤的过往,便有共建未来的希望。
结 语
本文聚焦于巢穴、修道院与巨人冢三大地点所承载的文化符号的转化,展现了石黑一雄通过记忆的地点媒介重塑过去,并阐述重塑的记忆对人物身份的建构作用。在巢穴中,石黑一雄营造了一种集体失忆的文化氛围,异常的事件与物品都表征着文化记忆缺失的危机,这直接导致身份认同的焦虑,使得唤回记忆、找寻文化的关联成为必然。修道院以其不寻常的“神圣”刺激个体的记忆力,承载文化记忆的身体文字、图像痕迹以及仪式展演在动态中带来记忆的闪回与真相的外露,从而引发个体对身份认同的无限想象。巨人冢象征着一切的终结,屠杀母龙的仪式让整片大地得以新生,两个民族之间在历史真相面前又将有新的未来。石黑一雄借维斯坦屠龙后在复仇上的犹豫,表明经历文化创伤的国家或者民族有突破创伤、和平共建的希望。同时个体直面创伤过往,并选择性地“遗忘”创伤,才能够构建新的身份认同,走向未来。总之,石黑一雄通过地方之上所承载的文化符号重塑民族间的文化记忆,试图将民族文化创伤“崇高化”,从而进入新的和平框架,帮助个体建构新的身份认同。
注释:
①小说《被掩埋的巨人》引文均出自:Ishiguro Kazuo. 2015. The Buried Giant [M]. London: Faber & Faber.随文标明页码不再详注。该版本的中文参考译本为周小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出版。
②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的专职承载者自身具有一种不同于常人的特质。详见扬·阿斯曼.2015.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