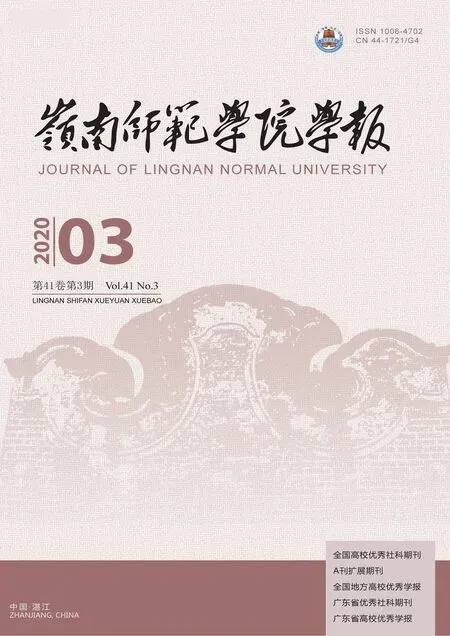《英国病人》中的暗语地图
高 家 鹏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英国病人》(EnglishPatient)是由加拿大籍斯里兰卡裔作家翁达杰创作,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的小说。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已经将后殖民理论与翁达杰进行联合阐释,无疑,这些阐释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但这些阐释往往拘泥于抗暴与反权威话语,通常的论文模式总是“结论先行”,用理论的办法反推论据的研究方法,势必会造成结果与事实的偏差。所以,运用地理学学科知识和后殖民理论对《英国病人》进行解析是一种全新的方法,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相比于笼统的“后殖民”框架更为高效、精准。同时,《英国病人》创作于文化地理学新兴发展的时期,并且该书本身也释放出相当剂量的地理学元素,将《英国病人》置入地理学与后殖民的关系中,能让普遍文化与个体知识上产生跨界对话。
一、地理学:殖民符号
《英国病人》有着无处不在的地理学元素,从小说发生的背景来看,《英国病人》中艾尔玛西的故事发生在埃及的城市和沙漠中,具有文化地理学理论中“地理景观象征”的意义,象征着翁达杰意识观念中缩小版的东方世界[1]212。从人物上来看,小说中有埃及阿拉伯人、纯粹的土著贝都因人等人文地理学元素。从情节上而言,小说的波动起伏就是围绕着地理知识的战争价值而存在的,小说的战争背景中,英德两国为了沙漠的地理信息兴起了间谍战,艾尔玛西受伤前被英军扣留,受伤后被盟军间谍卡拉瓦乔审问都是因为重要的地图知识。所以说,《英国病人》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对地理知识的再言说,地理学可谓全方位渗透进了这部作品,而地图是小说地理学表现的重要窗口。
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论述了早期帝国殖民扩张时期地理学的地位。帝国主义指的是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2]7,殖民的行径虽然是丑陋野蛮的,但本质却是对不属于宗主国的、遥远的、本地人居住的土地的“谋划、占领以及控制”,殖民者的一切就是为了土地。这些土地给予了宗主国新兴殖民贵族巨额的财产收入(如《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安提瓜)。在金钱的驱使下,与土地直接相关的地理学在这种国家层面的“谋划”之下蓬勃发展。
看似孤立的地理学与殖民实践有着相当程度的历史依赖,与非洲大陆的殖民和探索活动直接促进了欧洲现代地理地质学会的产生,在地理学会发展之后,又“反哺”了欧洲宗主国的殖民效率。如法国在1875年召开了国际地理学大会,主办人声称“上帝交给了我们一个认识地球并征服它的任务”。在1880年到1895年,法国的殖民地数量激增,从100万平方公里急剧增加至950万平方公里,其殖民地遍布整个南半球[3]46。在欧洲殖民史的文献中,地理学、至少是现代地理学可以说是由殖民行为直接促使并形成的。而作为殖民副产品的地理学科,则“理所应当”地为殖民的行径提供信息援助,甚至试图在学科内涵的领域去佐证殖民行动的“正当性”,所以地理学几乎就是殖民国家“帝国意志”和民族逐利心理的产物,绝对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术学科。
《英国病人》直接表述出了隐藏在地理学研究之后的“帝国意志”(imperial mind),小说中进行埃及勘察和地图绘制工作的“伦敦地理学会”表面上是一群地理爱好者自由策划的、由私人资助的学术协会。但实际上,该协会并不纯粹,和英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开着实际由政府出资购买的飞机,被协会的成员当作救星的杰弗里就是英国政府安插进入协会的间谍,间谍卡拉瓦乔直接进入了该协会充当助理,而他甚至没有任何学术背景。
“伦敦地理学会”于是就存在着三种身份,首先,它是由一群学者建设起来的学术机关,在这学术机关的背后,是第二重身份,即英国人的战略“前哨站”,英国从1936年渗入该学会,很可能因为意大利同年入侵埃塞俄比亚让英国感到北非的殖民地位遭到了法西斯的撼动。第三重身份,就是英国人的殖民统治的信息采集机构,所谓“帝国的问题就是实际拥有土地的问题”[2]106,土地的地图信息就是殖民的根脉,是殖民政府绝对不愿泄露的绝密知识。
《英国病人》毫不遮掩地表述出“伦敦地理学会”的学者实际上就是一群拿着测量仪和相机的文化殖民官。“伦敦地理学会”的勘测活动中一项重大的任务就是地理命名。学会勘测的活动主要在沙漠之中,撒哈拉沙漠的土地上,仍然有许多未被欧洲人认知的地域。这些地理学家的命名行为直接阻断了地域与当地人之间的“说”的联系,赤裸裸地剥夺了当地土著自由言说与表述地域的权利,埃及成为了“东方化”埃及,从地理词汇的侵蚀我们可以窥视殖民的一斑。玛格丽特·琼斯指出,英国经常利用裹着学术外表的学科进行殖民行为,如英国对锡兰的殖民统治时期,就彻底颠覆了锡兰效率高、符合国情的传统护理学,锡兰的护理学中的社区特色被殖民者逐渐取缔、同化[4]149。《英国病人》中隐晦地提到了土著与这群学者的对立,“他们的首要信条——依旧不向陌生人透露沙漠的秘密”[5]132。土著隐隐感到了这些地理探究活动的灾难性后果,选择了用“沉默性抗暴”回应,用消极、不配合的态势回复变向殖民行为。这也难怪“国际沙漠学会”的勘察活动处处受阻——“九天遭遇三次沙尘暴”,作为整体的土地与殖民者所宣称的符号脱钩、分离,产生了类似于不契合的“不适感”。翁达杰将这种脱钩的感觉物化成自然现象,小说中的自然或者天时永远不会站在殖民者这一边,无论他们采取的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殖民措施。
“命名”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具体来看《英国病人》的“命名”,能察觉出翁达杰用“命名”戏仿了欧洲国家的早期殖民行径。“国际沙漠学会”的学者对于地点的命名,并不像该学会所宣称的那样严谨、科学,而是将很多主观臆断的名称强塞到土地之上。“他们一度用爱人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经过的地方”,翁达杰笔下的地理学会会员时常用女性的名字来进行命名,这在殖民话语体系中有着特殊意义。欧洲殖民者几乎集体地用形容女性的特定形容词来表述殖民地的一些特征。因为殖民的统治需要土地,更需要使用土地进行收益活动的殖民地居民。而殖民地居民的数量与女性的生育能力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2]106。
女性的生育被视作一种维持殖民地运行的手段,殖民被当作一种商业活动,一种能够让底层人民推倒自己的阶级标签,成为新阶级的主动选项。甚至还有些许追逐荣誉的探险移民,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法国移民的特点上,法国政府为了宣传殖民活动,将移民定义为开疆扩土的“崇高使命”。在宗主国流行的追逐金钱和“荣誉”的殖民态势必然导致了移民以男性为主,以美国弗吉尼亚州为例,因为过度依靠移民来维持殖民地的运营,使得该州在17世纪的时候男性单身率高达28%。并且佐治亚州在1740年才逐渐摆脱性别比例失调的困扰[6]23-24。殖民急剧扩张的市场和殖民地性别失调的现象让殖民活动的话语体系产生变化。主要体现在政府文官、作家、诗人等掌握话语权的阶级人士在表述殖民时无意识地与女性生育联系在一起。如“丰收的”“多产的”这类暗喻女性生育能力的词汇常被用来表述帝国统治下殖民地的毛皮贸易和经济作物农业。而“性欲旺盛的”(sexual desire)、“淫乱”(promiscuous)等歧视、曲解女性的词汇则被用来揶揄土著女性,披着神秘面纱的阿拉伯女性深受其害[7]94。喜好表现殖民帝国英雄的吉卜林就不厌其烦地将女性的生殖特点反复比作她们从属地位的“佐证”。
《英国病人》剥离了殖民史中地理学的“学术面纱”,将地理学从学术伪装中调至“权力知识”的范围之内。通过词汇、话语的累积暗示了殖民者对于土地无穷的欲望,同时,该作考古了殖民词语与有关北非土地的能指实质的“不适感”,用这种“不适感”表述出殖民者与北非土地脱钩的现象。翁达杰邀请读者参与了对于宗主国的解构,思考话语、话语生产出的知识与土地上的生活世界的关系,进而反思了战争之外、历史之外的地理学的话语结构。
二、地理:视域中的“明与暗”
帝国的任务就是控制土地、控制关于土地的一切,但帝国任务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连帝国意志本身,都不是绝对坚信能够全盘掌握殖民地。在地理的框架之下,帝国对殖民地在地理学科以及地理学话语等知识层面是压倒性的、全盘胜利的,但帝国从来不放心对于殖民地地理视域的掌握,对于外来者而言,殖民地存在着很多模糊不清、无法界定的地段,以殖民地题材小说《黑暗之心》(HeartofDarkness)为例,作者康拉德总是有种冲动,将模糊不清、未加界限的世界纳入到小说人物、一个名叫马洛的白人的对话之中。福斯特在殖民小说《印度之旅》(APassageToIndia) 中更是直接说,“在印度,你什么都分辨不出来,你只要提一个问题,就会使它消失或者融进别的什么东西里”[8]86。这些崇尚欧洲中心论,殖民色彩浓厚的白人作家都有着强烈的冲动,去将殖民地中模糊的、神秘主义弥漫的地段纳入至宗主国话语体系,但结果往往不尽人意,帝国收纳下的殖民地话语也通常止步于对殖民地人民的刻板印象词汇。所以帝国无论是在殖民地话语收纳程度所代表的人文地理之上,还是在工具理性影响下,对地段信息所代表的地图图像的构建上,远远比不上帝国对殖民地在其他方面的成就。
迈克·克朗认为,地理空间的视域对抗会反应到文学作品当中,他指出,19世纪英国的侦探小说(detective fiction)和二战前后流行于洛杉矶“黑夜小说”("noir"fiction)就是文学与地理视域结合的典型例子。在侦探小说中,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侦探主角要拨开城市的层层迷雾,小说中的城市甚至每一块砖、每一块石都是隐含破含线索、尚未探索出的秘密。而在黑夜小说中,富人的世界是光明可见的,而穷人的生活则成为视域死角中的黑暗世界。迈克·克朗罗列出的文学地理学的现象揭露了城市管理者对于城市控制信心不足的心理,白昼、黑夜所象征的两个阶级视域是水火不容的[9]60。
如果将翁达杰置入文学地理学的话语中,《英国病人》处在“明”的是殖民者等外来人员,而这群外来人员几乎都是由白人组成(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小说的光明世界形成了种族包围,即以艾尔玛西为首的白人群体包围住了唯一的少数族裔锡克人吉普,而本该处在“暗”中的穷人则被替换成当地土著。《英国病人》刻意剥削了土著人的言说资格,贝都因人、埃及人在小说中是没有语言的权力的,他们或是隐藏在埃及的闹市之中的商人,或是无尽的沙海中沉默不语的先知,或是闷声干活,为殖民者服务的司机和向导,以至于土著人的心理活动都是排除在小说的文本之外的。黑夜小说之中城市的底层人民的黑暗在《英国病人》蜕变成了被压迫族裔言语的缺失,这种言语的缺失造成了视域的差异,土著人总是包裹在神秘之中,小说表达出以地理协会为代表的白人试图彻底征服这样的神秘,想要将他们视域中的一切黑暗清扫干净,但他们与贝都因人对话的失败和地理协会的解散则宣告“黑暗”仍然独立存在于北非的土地之上,外来者在统治土地方面虽然成功,但却没有真正体认本地族裔。
“黑暗”(darkness)实际上是非欧洲的世界在反抗帝国主义,“黑暗”归根结底是独立性质的(autonomy of its own)[2]30这种黑暗的性质在小说中体现最明显的是贝都因人。贝都因人是北非土地上最神秘、“黑暗”并且也是最具有独立精神的民族。小说中涉及的贝都因人在北非国家观念产生前就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抗暴史,14世纪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赫乐敦就称贝都因人是真正的阿拉伯人,远在伊斯兰文明进入北非前就有了自己的文明[10]39。贝都因人在各个国家中,主动或被动地成立了隶属于伊斯兰政权的沙漠巡逻队(Desert Patrol),为伊斯兰政权戍卫最恶劣的沙漠地段,可见贝都因人痴迷于以沙漠绿洲为活动中心的部落社会体制,即使是为这些异族政权服务,也是植根于沙漠环境中。但在这些伊斯兰政权的国家中(约旦、埃及、叙利亚),贝都因是被排斥在统治权力之外的,以至于中东国家在20世纪初还在苦恼于如何将贝都因人纳入国家体系,变成政权能接受的好公民(good citizens)。1922年成立的埃及政府是受英国把持的傀儡政府,而这个埃及人为主体的政府或许标志着英国人对阿拉伯文化的埃及人成功驯服。但贝都因人却让殖民者无法把控,可谓是北非土地的“黑暗之心”。
翁达杰在《英国病人》中,将贝都因人的“黑暗”和神秘性表述到了极致,在小说中具体从医术和军事两个方面表现了贝都因人。艾尔玛西被贝都因人治愈的过程就是充满神秘主义的,磨碎的铜雀骨粉被贝都因人用来治愈烧伤,将艾尔玛西双手抬起,“意味着从空中攫取力量注入自己的身体”[5]7。有关贝都因人表述的一切,都是和西方人所接受的“文明”“科学”相驳斥的,贝都因人的形象甚至呈现出萨满化的倾向。同时,贝都因人的军队则在小说中的白人殖民视野中呈现出更多的不可控性,贝都因人救下艾尔玛西的目的是为了让他识别缴获的枪械子弹型号。贝都因人的军队缴获的枪支有轴心国德国制造的,也有北非自由法国使用的法国枪械,但他们的军队却完全没有和欧洲国家军队对接,贝都因人如此珍重他们仅有的欧洲人艾尔玛西就能证明这点,赛义德的“对位阅读法”(contrapuntal reading)理论认为,“读者必须开放性地理解被作者排除在外的东西”[2]67。那么贝都因人在北非战场上绝对是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状态,而且很有可能无差别攻击同盟轴心双方以博取生存和独立地位(缴获同盟轴心双方的枪支)。北非殖民地上展开决战的德意英三国都无法控制住这一小撮神秘、“野蛮”“阴暗”的贝都因人,殖民者绘制的文化地图中,贝都因人不仅是缺席失位的,而且具有相当的威胁性。
因此,《英国病人》讨论了地理视域中的明暗原则,殖民者、土著被翁达杰置入了文化地理学里城市富人与穷人对立的视野公式中,作者将“暗”的重心放在北非土地上最特殊的民族、贝都因人之上,展现出独立于混乱中的北非战场的土著力量。如果说,小说关于伦敦地理学会描述是作者对战争背后的地理殖民渗透的揭露和讽刺的话,那贝都因人就体现了作者对“地理-视域”信息独立的深切关怀,贝都因人在小说中的胜利则告示了土著人在殖民博弈中可加以利用的先天信息优势。
三、地理图像暗语与居间困境
翁达杰对于地理以及地理背后的后殖民意识的接受是完全可以溯源的。
翁达杰不仅是一名小说家,更是一位诗人。翁达杰对地理的重视,缘于他对诗歌中图像的不懈追求。加拿大学者洛林·M·约克就指出了翁达杰与图像的关系。翁达杰甚至有过一段短暂的电影制作人和摄影师的经历,并且他对二十世纪的绘画以及美术批评理论曾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他的著名诗歌《七个脚趾头的男人》就是直接启发于画家悉尼·诺兰的一系列绘画[12]94。翁达杰作为文学评论家的时候,经常使用“草地上的午餐”(Lunch On The Grass),奥林匹亚(Olympia)或者天梭(Tissot)这样绘画术语来类比文学作品。翁达杰对空间和构图的敏感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说,他非常着迷于评论、塑造空间与图像。翁达杰自己坦白,他的很多小说都起源于一次图像丰富的梦境,《英国病人》的创作动机甚至是翁达杰的一场梦,他梦见了一个男人从天空中燃烧而降的图景[12]168。翁达杰对于空间和图像的关注使得他对地理学科的文学运用有了意识上的基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翁达杰对于地理学科“静态”意识的崇拜。地理学科研究内容就是生态,是客观固定的对象。相较于研究人和群体的社会学以及政治学,地理学科呈现出对于静态的图像(地图和地理学所使用的航拍照片等)的重视,人在体认该学科时,显示出更多的稳定性。洛林同时指出,翁达杰的诗歌创作甚至是完全基于静态崇拜之上的。翁达杰1973年创作的诗歌集《杰利鼠》(RatJelly)就是一部关于变迁与固定的寓言。其中一篇诗歌《金刚遇上华莱士·史蒂文森》(KingKongMeetsWallaceStevens)中,读者就被邀请“拍两张照片”:一张是“胖胖的”“慈祥的”诗人的静态照片,另一张是“再次迷失在纽约街头”的康先生的动态照片[11]101。所以,翁达杰对于地理学科的接受,可以通过“绘画-摄影-图像-静态-地理”的接受逻辑来理解。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英国病人》会吟唱出对于古埃及遗迹、沙漠地图等相对“静止”的物体的赞美颂诗。
如果结合小说创作的时期来看,《英国病人》创作的90年代的背景,正是地理学蓬勃发展,70年代中激进的人文地理学在学者的整合规划下,在九十年代蜕变而出的文化地理学迅速占领的地理学的学术话语。英国权威学术出版社布莱克维尔公司在90年代就决定出版一套人文地理学的学术专题著作集。其中以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S·邓肯为主的四位教授主编的《文化地理学手册》(A Compan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被英国地理学界誉为“全面覆盖人文地理学科的奇书”。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无论是文化地理学的开山之作《文化地理学手册》,还是由后起之辈迈克·克朗攥写的《文化地理学》,都集中探讨了当时正“兴风作浪”的后殖民主义,而且两本书的研究几乎完全是基于文学作品的文本之上的。
创作意识上,翁达杰对地理学科的静态性质有着执着的追求,在创作的背景上,欧美流行的人文地理学与后殖民思潮在高度整合之后,成为了研究成果基于文学文本的“文化大类学科”。《英国病人》的地理学元素不仅是可以溯源的,而且呈现出“静态崇拜”和“学科架设”的两大特征。
这样的特点,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翁达杰作为流散作家的独特性质。学术界很早就有对翁达杰的“流散性”定论,他的小说早就被学者指出“严格地履行了流散文学的公式”,其流散的特征被学者们反复论及。《英国病人》最体现流散小说的“流散型”的就是女护士汉娜照顾艾尔玛西的圣吉罗拉莫别墅,住下了卡拉瓦乔、辛格、汉娜、艾尔玛西这四个不同族裔的人,小说体现出的的民族多元化和民族合一的整体意识就是流散小说的现象和目的所在,也有很多学者指出,锡克族扫雷兵辛格就是翁达杰在小说中的种族化身,因为二人都有印度裔血统,而且都和白人世界有着很深的联系(辛格与白人汉娜恋爱,翁达杰在加拿大定居)。但目前的学术界对翁达杰留有一个尚未探索的空白,《英国病人》像一个殖民作家的作品那样,执迷于表现贝都因人的“黑暗”。作为作者的翁达杰时而寄居于艾尔玛西的身体里,用类似于康拉德的德裔白人视角质疑地理学会的行径和间谍的反人道拷问,又时而困顿于种族歧视的困境中,在辛格的身上刻下了抗暴白人话语权的印记。翁达杰在《英国病人》中的这种身份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首先要确定一点的是,翁达杰绝不是一名与白人共谋的少数族裔流散作家[12]67。《英国病人》中艾尔玛西、辛格、汉娜和卡拉瓦乔四人经历着类似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冒险(Hero’s Adventure)叙述,四个人物都处在自我重新评价和寻找新身份的任务之中。圣吉罗拉莫别墅发生的故事始发于英国病人的身份缺失,而英国病人的身份重建不仅需要艾尔玛西个人的记忆,而且其他三人也起到了填补作用。《英国病人》这部小说从哲理上思考可以看作是作者在质问离群之人,能不能凭一己力量达到自己的虚构身份状态(own invention)。可见《英国病人》绝不是一部白人话语指导下的无意识创作,是有意识的身份探寻。但辛格与艾尔玛西又确实在作家视角之下存在着调度失效的矛盾。翁达杰显然不是殖民者的共谋犯,那为什么《英国病人》的流散作家话语表现出不纯粹和摇摆的怪象呢?
《英国病人》关于北非战争的叙述能够解释作者话语身份摇摆的现象。轴心国是悍然发动二战的作恶者,在小说中卡尔马乔对德国的切肤之痛能体现出轴心国的负面形象。但北非战场上,以英国为首的同盟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绝对正义的那一方。英军极端敌视德裔的行为致使艾尔玛西被迫将地图出卖给德国人,也就是说,邪恶的德军反而是艾尔玛西能够与情人见面的救星。《英国病人》对于北非战场的描写呈现出“反英雄”的倾向——德军不是纯粹意义的作恶者,同时,盟国的行径也让人生厌。而在双方战乱的夹层之中,寄居的是一群数量少的可怜、蛰伏起来的贝都因人。沙漠之中的一切遗迹和象征生命的绿洲,都是属于贝都因人的,这批最为纯粹的阿拉伯人才是翁达杰所支持,赞美的一方。
《英国病人》中,贝都因人是翁达杰所崇拜的“静态”的化身。首先,贝都因人在种族历史上,有着漫长的、静止不动的特征。千百年来,贝都因人都是部族制的游牧民族。其二,贝都因人是中立,居间的,这是静态事物的性质之一。贝都因人抗争史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了,时至今日,他们一直未正式进入任何阿拉伯国家政权的中心,永远处在游离、陌生的状态。其三,在图像与画面上,贝都因人在小说中一直在满足翁达杰的图像构建欲望。“别墅”(villa)这一章节中,艾尔玛西因烧伤只能观察贝都因人,而不能说话。翁达杰巧借这一机制让贝都因人与火、沙尘、岩画这类有着强烈视觉效果的元素一同出现。而且,伴随贝都因人出现的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颜色词汇,如“黑色的山谷”,贝都因跳舞的孩童的“蓝色的亚麻布袍子”,“身子像道黄色的闪电”。贝都因人的存在,恰恰是翁达杰“静态-图像”崇拜的宣泄点,作者通过贝都因人,构建出了他的梦境图像。
所以,《英国病人》中看似摇摆不定的流散话语是模糊的假象,翁达杰从未向白人话语妥协。他的困惑和身份认同迷局通过他崇拜已久的图像得到了宣泄和解决。在图像、地图以及衍生的地理话语中,翁达杰得以建构出呈现序列化的“静态”话语,在殖民与反殖民中,寻找到了建构画面的“第三条道路”,翁达杰给流散作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表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