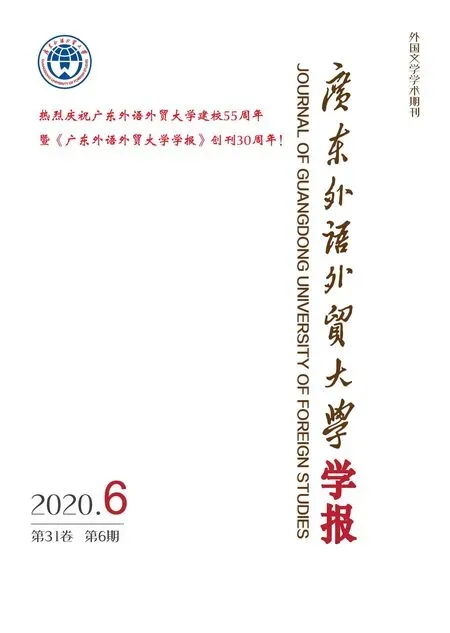从《英国病人》看翁达杰在世界主义视域下的文学书写
王玉 陈妍
引 言
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是一位以诗闻名的加拿大作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其长篇小说《英国病人》(TheEnglishPatient)的发表令他在小说界占据了毋庸置疑的地位。《英国病人》因其高超的叙事技巧、错综复杂的时间空间线索、惟妙惟肖的蒙太奇式手法,获得了国内外读者的追捧,也吸引了诸多文学评论家的目光。一九九二年,翁达杰凭此书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荣膺英国“布克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并于二○一八年获得金布克奖历史最佳小说奖。在书中,翁达杰用诗意的语言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四个饱受战争摧残的人聚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所破败的别墅之中的故事。由于涉及战争背景,翁达杰在小说里引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主题。目前国内学者对此书的研究多集中于后殖民(张健堃,2015)、身份认同(梁海洋,2010)、精神分析(吴丹,2017)等领域,鲜有人注意到翁达杰在小说中对于主人公民族性身份的“解构”是为了更进一步的“重构”,即在更广阔的世界主义视域下重构主人公“世界公民”的身份。
“世界主义”作为一种宽泛的哲学概念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应追溯到倡导“大同世界”思想的孔子以及主张“人类应该共同建立一个整体性的、以理性为基础的世界国家”的古希腊斯多葛学派。此后,随着各民族之间联系的加强,“世界一体”的概念逐渐普及开来。十八世纪末,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永久的和平:一个哲学计划》(PerpetualPeace:APhilosophicalEssay)的论著中提出各国都应实行共和制,并建立一个“和平联盟(a covenant of peace)”(Kant,1903:134),实行普遍有效的世界主义的法律,并以此作为指导原则,用以保护人们不受战争的侵害,“世界主义”的观念由始对文学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十九世纪,德国大文豪歌德开始使用“世界文学”这样一个术语,呼吁大家把目光投射到本国以外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去。由此,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慢慢发展起来。到了二十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世界主义”思潮再次兴起。在这一思潮中,不少研究者以世界主义基本理念为纲,根据自己所研究的学科特点对其加以发散与阐释,并延伸出政治世界主义、文化世界主义、批判世界主义等等不同的探究视角。国内外由此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理论成果。国外理论著作如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的《世界主义:理想与现实》(Cosmopolitanism:IdealsandRealities)、托马斯·博格(Thomas Pogge)的《世界贫困与人权:世界主义者的责任与变革》(WorldPovertyandHumanRights:CosmopolitanResponsibilitiesandReforms)集中探究了世界主义理想在现实世界的可行性。而国内学者如王宁(2014:26)在《世界主义、世界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中,从文化和文学角度对争议颇多的世界主义概念进行了新的建构,积极宣扬世界主义研究对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强调“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越是有可能成为世界的”。事实上,由于世界主义的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侧重点。那么,世界主义究竟是单纯的哲学概念还是一种政治理想?加纳裔哲学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在他二○○六年出版的著作《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伦理学》(Cosmopolitanism:EthicsinaWorldofStrangers)中跳出了传统的政治研究范围,转而将世界主义定性为一种“伦理道德”,在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他以散文式的语言写作,结合自己的个人经历与对国际形势的思考,表明世界主义的重心是全球化的伦理道德问题,并详述了自己眼中世界公民应负有的对陌生人的道德责任。
对于阿皮亚而言,世界主义并非是政治口号,而是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伦理方式,这也为文学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将借助阿皮亚实践性的世界主义构想,细读《英国病人》中关于反殖民和身份认同的细节,探讨其中的世界主义倾向,并探究翁达杰世界主义理想的不足之处。
反对殖民主义的世界主义
随着资本经济的发展,无限地扩大利润和收益成了资本家们的首要需求。为了获取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将经济政治势力扩张到欠发达国家,强占其人力与资源,开启了臭名昭著的殖民历史。殖民主义源自资本扩张的需要,往往带有很强的民族自我中心意识。西方殖民国家将自己视为“主体”和“中心”,带着极端的民族观念,将西方世界外的其他民族排除在外,肆意加以奴役和剥削,使他们沦为自己的殖民附庸。在殖民地,西方世界的“主宰们”秉持民族优越感,毫无顾忌地压榨和歧视被殖民者,让他们一步一步成为殖民中毫无话语权的“他者”。在殖民文化中,世界从来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强弱分明、地位不均等的各个部分,弱者只能被奴役,成为无处申冤的受害者。
从广义角度看,世界主义是与殖民历史完全对立的。因此,在《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伦理学》中,阿皮亚(Appiah,2010:24)提出:“我们不应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干预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价值就自然成为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工具”。在谈及欧美国家对周边国家的文化侵略时,他使用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个论断,并坦承“文化帝国主义塑造了边缘区域群体的意识” (Appiah,2010:111)。由此可见,阿皮亚认为,世界主义理想实现的第一步,就是反殖民、反帝国主义。
与其相对应,在《英国病人》中,翁达杰首先通过对殖民主义的强烈批判,流露出对世界主义的向往。小说中备受殖民主义迫害的当属扫雷兵基普。作为一个印度锡克人,他从小在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侵害中长大,因此,他表现出种种“西化”的特性:钟爱英国红茶,喜欢没完没了地哼英文歌曲,习惯打卡纳斯塔牌。在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将自己归类为“最优秀的种族”,宣扬“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Said,2003:40)。这样一来,被殖民的印度人在灌输中接受了“白人至上”的观点,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漩涡,开始模仿和攀附欧洲文化,掉入“文化殖民”的陷阱。基普就是一个“英国化的印度人”的代表。虽然他拥有精湛的拆弹技术,毫无怨言地为英国军队出生入死,但他融入西方文明的梦想却不可能实现。因为种族,即使他拥有过人的智慧,他也不可能被当作一个真正的“文明人”。他努力让自己贴近英国文化,模仿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他有非同一般的克制力,可以对白人的侮辱不置一词,也可以在有色目光里默默忍耐;他甚至“能看到所有事情背后的合理性”(翁达杰,2012:194)。在西方度过的几年内,他“已经认了英国人做父亲,像一个孝顺的儿子一样听从父亲的号令”(翁达杰,2012:209)。但他的顺从并没有换来认可,相反,“在英国的部队里,从来没有人在意他的存在……这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无名的异族人,属于一个隐形的世界”(翁达杰,2012:191)。
然而,翁达杰并不仅仅满足于树立一个殖民话语下隐忍的受害者形象,在他的笔下,基普这个“孝顺的儿子”,逐渐有了自我意识,开始“睁开眼睛”,做出一系列带有反抗意味的行为。第一次,在圣母玛利亚海洋节中,基普看见圣母玛利亚雕像的那瞬间,立刻“举起步枪,透过瞄准器注视她的脸”(翁达杰,2012:75),这个带有宗教意味的挑衅行为,成为他反抗的起点;第二次,他趁着英国病人不注意,“用剪刀把他助听器的电线剪断了”(翁达杰,2012:111);最后一次反抗则是最彻底的一次反抗,听闻美军在亚洲的土地上投下两颗原子弹时,基普举起枪,愤慨地对准英国病人,吼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我在我自己国家的传统中长大,但是后来,更多的,是你们国家的传统。你们白人那个小小的岛国,你们的风俗习惯,你们的书,你们的行政长官、你们的理性,把世界其他地方都变成和你们一个样。你们的一举一动代表标准。我知道如果我搞错了该用哪根手指握茶杯,我就会被赶出去。如果我打错一个领结的结,我就出局了。就是那些舰船给了你们这样的权力吗?还是因为你们有历史记录和印刷机?(翁达杰,2012:274)
此处,躺在病床奄奄一息的英国病人,与举着武器愤怒呐喊的印度扫雷兵,共同构成了一幅对比鲜明、颇具震撼力的画面。衰落的英国病人预示着衰落的殖民帝国,而觉醒的基普则象征觉醒的千千万万殖民地居民。像基普一样的东方人,在痛苦中意识到,白人绝不会将原子弹投向自己的土地,白人也绝不会站在亚洲人民的角度思考,所谓的“白色守护神”,只是一群自私的利己主义者。最终,基普彻底与白人文明决裂,与欧洲大陆决裂,与白人情人汉娜决裂,踏上了返回印度之路。他的形象是千千万万印度人的缩影,他的回归标志着被殖民者自我意识的回归,也预示着各民族独立的浪潮即将到来。
翁达杰对基普形象的塑造,也折射出他自己对殖民主义的强烈反对与批判。白人对其他种族的殖民始于白人过于极端的民族意识,以民族来划分不同集体,以民族来决定区分对待的原则。而这大大破坏了“整体世界”的概念,人类无法再实现世界主义原则倡导下的平等与共同发展,无法追求世界主义背后支撑的人本精神。由于狭隘的西方中心意识,英国等殖民大国始终只能桎梏于一个民族范围内的道德观和公正观,肆意剥削外国公民,不能站在人类整体命运的宏观角度去思考掠夺行为的破坏性,这与倡导“包容差异、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世界主义背道而驰。在《英国病人》中,翁达杰通过对殖民行径的无情批判,从反面烘托了世界主义整体价值观的必要性,并以此告诫读者:以西方的价值观来强行干预其他民族的价值取向是完全错误的。过激的民族观念只会导致文明的冲撞甚至毁灭,唯有世界主义原则才能在最大范围内争取全人类的共同进步。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反思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否互相吞并才是唯一可能的道路?事实上,人类文明多式多样,丰富多彩,企图用一种文明压制其他文明以获得“一致”是极其愚蠢的做法。不少民族只能在自己本民族内贯彻和平与正义,却转而对其他民族采取截然不同的剥削行为。在不断反思下,人类对建立一个“世界通用的正义原则”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早在十八世纪末,哲学家康德(1903:128)就曾提出建立人类共用的世界主义法律,以维持长期和平。这一乌托邦式的构想虽然在当时争议不断,却给早期“世界主义”哲学奠定了一个基本内核:和平与正义。阿皮亚的世界主义思考也保留了此内核,倡导避免冲突,维护人类和平。他在书中引用了罗伯特·西伯雷(Robert Sibley)的观点并加以认同:“世界主义作为一种道德追求,将我们具体关注的范围,扩展到遥远的、一般意义上的‘别人’。并且,我们被告知,他们是我们的地球邻居。这种观念可能给予我们一种温暖而模糊的感受,但是,它绝对不会驱使我们发动一场战争。……世界主义的道德判断,要求我们像对待邻居那样,去对待地球上的任何人”(Sibley,2000:8-9)。据此,我们可以得出阿皮亚世界主义构想的第二个重点:反对战争,提倡人类的普遍之爱。
在《英国病人》中,作者将自己反战的态度通过书中诸多人物之口表达出来。艾尔麦西对战争深恶痛绝:他用烟纸将《历史》这本书中关于战争的部分全部贴起来,并形容二战为“野蛮人与野蛮人的交战”(翁达杰,2012:249)。他无心参与战争,并十分感激沙漠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远离战争的乌托邦。然而,战争全面来袭之时,沙漠也沦为战场,考古小队被迫解散。对所有的考古队员来说,这个乌托邦终究崩塌了,而他们也被迫回到战争的现实中。艾尔麦西的好友、同是考古学家的麦多克斯,在回到祖国后,参加了一场充满沙文主义论调的教堂布道。布道中,“牧师语调欢快地称颂战争,祝福政府和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们” (翁达杰,2012:234),麦多克斯难以忍受,认为这种言辞侮辱了教堂的神圣,于愤怒中开枪自杀。
除了正面表达自己的反战态度,翁达杰还通过细致描绘二战中主人公的沉痛经历来展现战争对人性的摧毁性打击。在战争中,艾尔麦西被误认为是间谍,痛失搭救凯瑟琳的机会;汉娜失去了孩子、爱人和自己的父亲;卡拉瓦乔失去了拇指和对陌生人的信任;基普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此外,战争不仅带来了触目惊心的身体创伤,也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口,异化了人的情感——首当其冲便是汉娜。作为一个战地护士,在全书开头部分,汉娜就被定义成了一个众人难以理解的“怪人”。战争结束在即,她拒绝跟随大部队撤退,以照顾艾尔麦西的名义,坚持要留在一所破败不堪、危机四伏的旧别墅中。在悉心护理艾尔麦西的过程中,汉娜得到一种极其珍贵的“被需要感”,这种被需要感让她在这场摧毁性的战争中重温了人类情感的热度。因此,她对艾尔麦西表现出超出医患关系之外的热忱,这段关系几乎像一个信念一样,让她远离了人群,独自守在荒凉的佛罗伦萨。不仅如此,汉娜亲自书写了一张便条,藏在书柜顶端的旧书当中,而那便条表达的居然是对父亲旧友卡拉瓦乔深切而隐秘的爱。这不禁使人联想到汉娜在战争中失去了深爱的父亲,因此她将这种特别的眷恋转移到与父亲年纪相仿的卡拉瓦乔身上。幸而在书的后半段,年轻的锡克士兵基普的出现将汉娜拽出了这种扭曲情感的泥潭。两个饱受战争残害、相互依靠的年轻人终于相爱,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可歌可颂。但是,翁达杰并没有给他们安排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最终,由于不可调和的种族冲突,基普返回印度,另组家庭,而汉娜虽然不发一言地接受了基普的离开,却始终形单影只、独自一人。至此,汉娜曲折的情感叙述最终结束,而她看似颇为混乱的爱情线索也让不少读者困惑不解。事实上,翁达杰如此书写,是为了尽量完整展现战争对人类情感的异化。汉娜变得不再像汉娜,而汉娜又仅仅是千千万万个汉娜当中的一个。人类沦为战争工具,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人性被抽离了应有的温度,而情感也被肆意地压制和扭曲。
翁达杰以细腻的笔触一点点揭开战争给人带来的情感异化和心理创伤,让人为之动容。他深切反思战争的恶果,并为战争受害者们提供了一种疗愈方式,即人类之间的普遍之爱。这与阿皮亚的世界主义思考恰好吻合——阿皮亚曾提出“生而为人,我们必须要对陌生人尽到应尽的义务”(Appiah,2005:228)。在他眼中,世界主义是一种伦理道德,每个人都对陌生人负有伦理责任,每个人都应对他人付出爱与关心。在《英国病人》中,虽然外界战火纷飞,但在圣吉罗拉莫别墅内,四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主人公却组成了一个特殊的集体。在这个集体内,每个人都抱有跨越种族、疆界的普遍之爱,不吝付出自己的关怀。卡拉瓦乔以父亲般的爱,引导汉娜一步步克服心理创伤;基普与汉娜建立了一段浪漫的爱情关系,并互相治愈;印度兵基普救了卡拉瓦乔一命,而卡拉瓦乔深深铭记在心,甚至在多年后在街上见到东印度人都会主动提供帮助。
别墅外的战场上满是血腥的厮杀,而别墅内的集体中却充盈着人类最初始、最本真的美好情感。在这里,翁达杰通过这两幅场景的对比,表露了自己强烈的反战意愿和对人类普遍之爱的向往。他站在世界主义的高度,试图倡导和建立这样一种普遍之爱——在这种普遍之爱的影响下,人们可以从民族、种族、地域、宗教等等一系列特殊制约当中解放出来,真正用整体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将陌生的人类同胞当作自己的友邻。
民族、国籍一向被认为是某个个体身上所具有的区别性的标签,也是寻找社会归属感的重要元素。民族主义者为单个民族谋利益,坚持强调民族、种族具有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一个族群的意识形态,难以改变。在这一点上,世界主义与其截然相反。阿皮亚(Appiah,2010:114)在《世界主义》一书中指出,“世界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既尊重差异,也尊重真实的个人,还尊重以信念形式表达的人类感情”。在世界主义视域下,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们不应该再拘泥于狭隘的民族视角,而是统一遵循共有的正义原则,尊重并关注世界上各式的差异性文化。民族、种族、宗教作为特殊标签,并不是不复存在,而应被纳入更大的“世界视角”之中,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找到自己最根本性的身份认同,即“世界的一分子”“世界公民”。阿皮亚将“世界公民”形容为“跨越边界的信奉者”——“他们相信跨越国界的人类尊严,他们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他们与其他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士分享这一思想……他们还抵制其祖国推崇的狭隘民族主义。他们不会为了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投身战争,不过,一旦国家有碍于普遍的公正,他们愿意投身反对国家的运动”(Appiah,2010:137)。总的来说,世界主义者的主要目标,就是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发扬普遍、无差别的公平正义思想,抹杀过分强调的民族标签。
在《英国病人》中,翁达杰这种“抹杀民族标签”的意识尤为明显。作品一开始的悬念就在主人公艾尔麦西的身份。他从飞机坠落,浑身烧得面目全非,没有任何可供辨认的身份线索,凭着一口流利的英式英语,他被标识为“英国病人”。随着后文他的回忆慢慢展开,他匈牙利贵族的身份也浮出水面。虽然艾尔麦西本人并不重视民族和国籍的区分,但是他“匈牙利人”的身份在关键时刻给了他致命一击——在凯瑟琳身受重伤、急需救助之时,艾尔麦西向驻守的英国部队求救,却被怀疑成外国间谍,被逮捕关押,痛失搭救凯瑟琳的机会。在这里,翁达杰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国家和民族的身份居然演变成衡量人是非善恶的标准,变成了影响前途命运的关键要素。不少民族主义者叫嚷的道德要求仅仅适用于一个固定民族或国家的内部,一旦超出范围,所有的正义追求就会沦为空谈。
小说中,“地图”这个意象出现了数次。欧洲的白人被称为“地图绘制者”,而相似的,艾尔麦西也宣称地图上的黑点是“殖民者为了扩大势力范围所推动的”(翁达杰,2012:138)。众所周知,地图象征着疆域,地图上的国境线则将地球的土地分割成不同的政治碎片。殖民者为扩大自己的领地而大肆攻城略地,使不同民族间兵戎相见,极端民族主义论调甚嚣尘上,不同民族间的平等交流沦为空谈。在翁达杰笔下,地图也成为狭隘民族观的代名词。故事中的艾尔麦西,作为一个地图测绘专家,却坚持声称:“我全部的渴望就是走在一个没有地图的地球上”(翁达杰,2012:253)。
艾尔麦西,作为承载作者“世界主义情怀”最重要的人物,从始至终都拒绝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陷阱。他始终认为国家和民族的身份只是束缚,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世界公民”,只有广阔的沙漠才是他的唯一烙印。在沙漠里,他所在的考古小队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然而并没有民族的隔阂和划分,所有人怀抱着对大漠同样的痴迷和热爱,拢聚成一个精神共同体。即他自己所描画的:“我们成了没有民族的人。我开始憎恨民族。民族、国家使我们变得畸形……擦掉我们的姓氏!擦掉我们的国家!这些都是沙漠教给我的”(翁达杰,2012:135)。他抛弃了狭义上的社会身份,却拾得了广义上的人的根本特性。
仔细观察翁达杰笔下的人物,读者应该很容易发现他所描绘的“世界主义共同体”并不仅有这个沙漠研究组织。在战火纷飞的欧洲,在炮弹刚刚侵袭过的土地,四个身份完全不同的人——加拿大护士汉娜、加拿大盗贼卡拉瓦乔、印度扫雷兵基普,还有匈牙利探险家艾尔麦西,聚集在意大利一所破败别墅中。翁达杰设置的这个集体本身就有很强的隐喻意味:地域、国籍、职业跨度如此之大,看似毫无交集的四个人,却同样在一场不人道的战争中饱受苦难,同样留在并不安全的别墅,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在乎年龄、性别、国籍、宗教,不在乎任何身份标签,仅仅收容了经历同样战争创伤、同样失去支撑人生根基的一群人。他们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享受着这个独立空间的和平,脱下伪装慢慢流露出在战争中已经消磨殆尽的感情;他们扔掉狭窄自私的有色眼镜,走出令人困惑的身份束缚,以真正注视另一个“人类”的目光来安慰彼此。在这个狭小破败的空间里,四个人终于超出拘泥于自身的视角,站在整体性的角度来反思战争、追悼苦难。在这一时刻,每个人都成为无根无基、漂泊于世的自由人,也最终扫除了以往在特定社群的局限性,以世界的一分子的身份存在,蜕变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
无根漂浮的世界主义
对于世界主义者而言,国家似乎不再重要,也不再是必要的社会身份标签。然而,阿皮亚在世界主义构想上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将世界主义定性为“有根的世界主义”,即基于爱国主义基础上的世界主义。爱国主义并不等于民族主义。阿皮亚对民族主义十分警惕,但对爱国主义极为推崇。他将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看作人的情感选择,而非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国家诞生的意义是为公民服务,规范和稳定公民生活,而公民对国家的爱并不是道德上的绑架,而是真实的信念。他抨击一些极端世界主义者“彻底抛下国家民族和世俗的家庭”的做法,认为他们只是借着自由的名义来推诿自己应尽的责任。试想,如果一个人背离祖国、抛妻弃子、忽视友邻,那么他怎么可能拥有世界主义的胸襟,无差别地去关心地球上的陌生同胞呢?世界主义本身就暗含着伦理要求: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不仅承担着对亲人朋友的责任,还会心怀天下,承担起对陌生人的责任。因此,他们不可能是断根浮萍——对他们而言,抛弃自己的原生文化是绝对错误的,唯有成为“有根”者,才能更好践行自己的世界主义理想。
反过来看《英国病人》,我们很容易发现翁达杰世界主义构想的不完全性:与阿皮亚相反,他所宣扬的世界主义是一种“无根世界主义”。艾尔麦西所属的沙漠探险队几乎都是无根的世界主义者:他们背井离乡、抛家舍业,在广袤的大漠里成为漂泊的游子。在描写艾尔麦西的好友麦多克斯时,翁达杰(2012:158)如是写道:“他毕竟是个属于沙漠的人,离开家乡萨默塞特郡的马斯顿马格纳村,改变所有的风俗习惯,就是为了靠近海平面,靠近沙漠的干燥”。
麦多克斯是这群“世界公民”的代表,他们身在异乡,有意脱离自己的原生文化,并将沙漠视为自己的唯一归宿。他们是翁达杰寄托世界主义理想的载体,由此可见翁达杰本人世界主义观不够完全,是具有“无根性”的。但翁达杰在行文中也并非对无根世界主义毫无质疑。他在书中借艾尔麦西之口提出了一个新名词——“世界混血儿”。艾尔麦西坦承,之所以自己和印度兵基普如此投缘,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世界混血儿”,都“生在一个地方,又去别的地方生活”(翁达杰,2012:173),这是翁达杰对于“世界公民”质朴性的概括。这两位“世界混血儿”在翁达杰的笔下是有所不同的。艾尔麦西全然离开了原生文化环境并抹去自己身上的国家痕迹,而基普虽然从小在白人文化的侵蚀里长大,却并没有切断和祖国的联系;他一直戴着锡克族的手镯和头巾,维持着具有民族风格的装扮;他保持着很多印度式的生活习惯,并经常提到自己的家乡和亲人。而在文末,他意识到西方殖民者的真面目,愤然离开欧洲,决定返回祖国,开始新生活。可以说,基普虽然是个西化的印度人,但他对自己国家、民族、亲友的爱是无可置疑的。他虽然漂泊在欧洲,却并没有斩断原生文化的根,没有遗忘自己的来处,他的世界主义思考是“有根”的。
虽然翁达杰在字里行间更加推崇“无根世界主义”,但他也明白这种“无根世界主义”过于理想化,对人类整体的和平与发展并没有突出的作用。他甚至设立了基普这样一个例子来进行收尾,这似乎表明了他在“无根世界主义”和“有根世界主义”上进行了一番斟酌。不过,翁达杰世界主义构想的不完全性与他自己的个人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他出生于斯里兰卡,身上流淌着荷兰人、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等多个民族的血液,少年时同母亲一起移居伦敦,完成中学学业,后又前往加拿大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并最终移民加拿大。他本人复杂的身份背景导致他难以拘于一个固定的国家的思考范式,因此更倾向于认同无根世界主义的理念。虽然在这一点上有所偏颇,但他坚持书写人类集体共同面对的问题,书写隐藏在身份标签下人类的真正情感,是值得称颂的。他在《英国病人》中塑造的多国籍、广地域、试图摆脱国家与民族标签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思想和形象的化身,也是寄托他“世界主义”理想的虚构完成体。
结 语
作为“无国界作家”中的重要一员,迈克尔·翁达杰根据其自身多元文化背景,在代表作《英国病人》中融入了强烈的世界主义理想。在小说中,翁达杰刻画了印度扫雷兵基普的形象。通过描写他具有代表性的“边缘人”经历,翁达杰痛斥了殖民历史的丑恶,对西方中心主义论调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另外,反战亦是书中一大重要主题。翁达杰另辟蹊径,没有将故事时间定位在二战全面爆发时,而是用文本集中表露二战行将结束时所有幸存者的遗留心境。通过详叙战争受害者们的心灵创伤,翁达杰毫不留情地指出,战争会给人性带来难以估量的破坏性影响。对战争中的人性与情感的深刻解读,使《英国病人》成为和平与正义的号角,吹响了一曲“世界性道德”的颂歌。除此之外,翁达杰还致力于抹除民族标签,提倡超越民族与国家身份,以真正“世界人”的目光去审视全球问题。他巧妙地塑造了“沙漠探险组织”“别墅中的四人集体”这样的“命运共同体”,呼吁人们抛开狭隘的民族观念,摒弃固定社群的局限性,达成一种真正的“超越民族之上”的世界主义理想。虽然他忽视了世界主义的“有根性”,宣扬的世界主义理想也不具有完全性,但他书写的人类集体性问题,无疑是具有时代价值的。
翁达杰在《英国病人》中超越了以往后殖民文学中对于“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思考,表达了自己“撕下民族身份标签,追求人类集体正义原则,做回真正的世界人”的渴盼。在当今时代,跨民族、跨国家的文化交流愈加频繁,各国通过交流对话达到“和而不同”境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翁达杰的世界主义思考必定会为建立和谐共生、多样发展的国际秩序带来有益的启示。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必定会超出文学鉴赏的范畴,拥有时代发展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