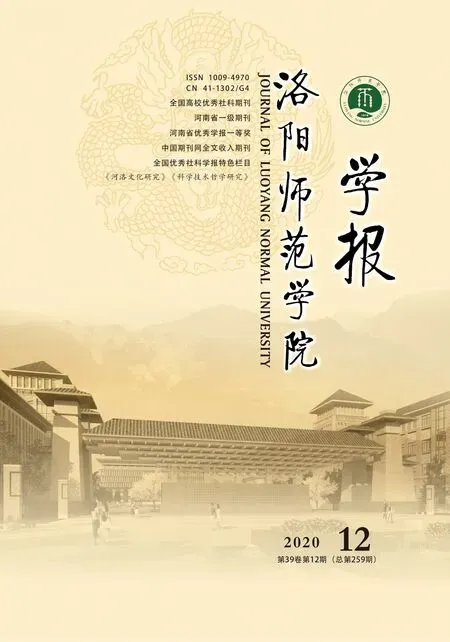论《二十四诗品》中的人与自然之美
季雨欣,廖述务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一本集文学创作论与文学批评论于一体的“综合宝典”,它是对晚唐之前文艺创作的一次历史性总结。同时,它掀开了晚唐之后文艺创作洪流的历史序幕。《二十四诗品》对诗歌风格的规整与分类,是对艺术创作中主观与客观、文与质、浓与淡、人格美与自然美等一系列美学问题的探索与汇总。至今仍难以被文论界的其他艺术作品颠覆和超越,作为文论史中的艺术精髓与灵魂瑰宝,它在中华文论的历史长河中依然光芒不减,熠熠生辉。
一、对自然之境的一往情深
《二十四诗品》中司空图对文学创作中的自然之景、自然之境以及由此而生的自然之情的探求与肯定不问可知。司空图深受老庄哲学思想的影响,他将道家哲学所推崇的自然哲学发展延续并渗透至自己的艺术创作与鉴赏之中,使《二十四诗品》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极具自然之美与自然之境的“自然文论史”。
曹丕和陆机曾言:“文非一体,鲜能备善”[1],“体有万殊,物无一量”[2]99。司空图以其卓越的智慧将庞杂繁复的唐诗进行汇总整理和分类,杨深秀《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五十首》中“王官谷里唐遗老,总结唐家一代诗”足以体现《二十四诗品》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司空图将各种风格的唐诗进行汇总,整理分类至“二十四品”,包括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诸体毕备,不主一格”,司空图喜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以自然之景、自然之境来喻艺术风格,他以“荒荒油云,寥寥长风”[3]8来喻雄浑之风的浑灏壮阔,以“犹之惠风,苒苒在衣”[3]42来喻冲淡之风的清微淡远,以“雾余山青,红杏在林”[3]42来喻绮丽之风的清秀明丽,以“青春鹦鹉,杨柳池台”[3]63来喻精神之风的清明神气等,都是司空图运用比喻和象征手法的典型范例。在司空图看来,自然不仅是艺术创作的灵感与来源,更是艺术作品表现的内容和方式,司空图的《沉著》篇中就有“如有佳语,大河前横”[3]20,他坚持艺术创作离不开自然之景的触发,真正好的诗句总是“俯拾即是,不取诸邻”[3]48。正如康德所推崇的崇高与壮美,自然之景能够引起人类内心的那种巨大力量和气魄,激荡诗人的内心、激发诗人的思索,使其文思泉涌,产生创作的灵感和欲望。司空图对于艺术创作中自然的定义并不局限于自然界及自然景物、景象,而是扩展至万事万物,包括社会历史背景及个体的现实生活。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推崇艺术创作的模仿论,亚里士多德肯定了艺术模仿现实、模仿自然与模仿人类行动和生活的艺术创作论。柏拉图虽认为艺术是永远无法真正反映真实而绝对的理式世界,但依然肯定了现实在艺术创作中难以取缔的地位及作用。黑格尔曾说:“生命的自然事物之所以美,既不是为它本身,也不是由它本身为着要显现美而创造出来的,自然美是为其他对象而美,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4]160相比于自然美,黑格尔更推崇的是艺术美,他坚持自然美是因人而美,这也同样表明自然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自然之美恰恰是有待诗人发现的艺术美。
自然是艺术表现的内在与核心,更是艺术创作的手段和方式。司空图对于“道法自然”的艺术创作论推崇备至,他认为艺术创作应遵循自然与无为的原则,文学语言不可过分雕饰,“薄言情晤,悠悠天钧”[3]48“如月之曙,如气之秋”[3]76,诗之风格应如明月之洁净皎洁,如秋风之净爽清穆,这也是对曹丕诗赋欲丽说后,文人对于形式美过分追求的一种消解与反拨。刘勰与钟嵘分别提出过“自然妙会”与“自然英旨”的文学创作理论观,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将绮丽归为一品,然司空图笔下的绮丽并不是错彩镂金般的艳丽辞采,而是清丽秀雅的艺术风格。“神存富贵,始轻黄金”[3]42,司空图推崇的绮丽乃是艺术精神与创作情感的富丽,是创作主体的主体意识与人格境界上的富足。纵观唐诗极具清丽、自然之美的诗歌作品数不胜数,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杜牧的《山行》、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维的《清溪》等,都是对以自然为美的理念的推崇与实践。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与司空图的清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司空图的绮丽既是绮丽又是清丽,在绮丽之美中融入了一种自然之韵,绮丽与清奇相合,内容与形式相谐,在追求语言形式的同时也不摒弃对人格精神的追求,这也是司空图辩证唯物主义艺术观的渗透与体现。
二、对人格之境的眷恋追求
对诗人人格境界的评判是中国文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孟子推崇“知人论世”,魏晋时期对于人格美的推崇达到了文化历史上的高潮点,人格美与精神美被提升至与创作美、艺术美同等重要的地位,人格美甚至被视为艺术美构成的重要因素。骨势、骨气、骨力本是用来形容人格境界的术语,后被引入文学理论成为评论文学创作的专业用语。钟嵘的《诗品》开启了文学史上以品论诗的高潮,以品论诗可以追溯至《汉书·古今人表》,它是《汉书》中的最后一篇,实是新制,在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它以古代人物为经,以品第人物为纬,将九品分至九栏,由“上智”至 “下愚”,品第标准是以人的品行为主,参之以事功大小与学术水平高低,由人及诗,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不再被创作者身份背景与社会地位左右,以品论诗不仅是品诗更是品人。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将诗之文类分至二十四种,这不仅是对诗品的划分,更是对人品的规范,“手把芙蓉,泛彼浩劫”[3]25的畸人是高古人格的标识,“落花无言,人淡如菊”[3]29的佳士是典雅人格的象征,“落落欲往,轿轿不群”[3]109的高人是飘逸人格的代表,“体素储洁,乘月返真”[3]33的幽人是洗练人格的标志。司空图对“诗以治心”的文艺价值论甚为推崇,他十分重视诗的社会价值、作用和影响力,这与孔子对文艺社会作用的推崇不谋而合,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5]109柏拉图也有着相似的见解,他用吸铁石与铁环的关系来比喻文艺的本体作用和功能,诗就像是吸铁石,它可以将灵感无限传递。同样,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作用也可以传递给无数的读者使其深受感染。司空图认为,好诗传达的不仅是诗人创作时的情感和精神,更是隐藏在文字之下的人格与灵魂。文艺作品不仅是作家艺术观和创作观的体现,也是作家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展现,作家的人格魅力可以透过文字传达给读者,使读者受到鼓舞与感染将意念转化为行动的内驱力进而付诸实践。
时至晚唐,政治黑暗、社会混乱、人心幽暗,社会极度混乱,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争名逐利的小人无处不在。诗至晚唐,魏晋时期轻靡华艳、虚无空洞的诗风再次卷土重来,《二十四诗品》的横空出世既是对雄浑高古、冲淡洗练、纤秾缜密、疏野清奇的诗风的呼唤,更是对高古典雅、豪放自然、沉着劲健人格修养的唤醒与追求。《冲淡》中“阅音修篁,美曰载归”[3]8的隐士,《清奇》中“神出古异,淡不可收”[3]76的可人,《疏野》中“控物自富,与率为期”[3]71的仙人都寄托着司空图想要超脱黑暗现实,摆脱世事纷争,疏放自然,寄情山水的高古志向和雄奇风骨。钟嵘的“诗缘情而绮靡”、陆机的“感物言志”、刘勰的“情志说”都肯定了客观现实与内在情感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黑格尔曾说:“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情致打动的是一根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力量。”[4]160而文学作品正是作者意志情感与志向追求的传达与表现。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营造了一种极具空间艺术的空旷感,上至碧云明月,下至筑屋松下,上有娟娟松树,下有涓涓细流,大至沧海,小至尘埃,四季更替,春华秋实,斗转星移,在如此雄浑壮阔的宇宙空间中“具备万物,横绝太空”[3]1,万事万物得其环中。司空图希望诗人之心能如“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6]的大鹏鸟遨游于天地之间,“观古今于须臾,抚沧海于一瞬”[2]36,不畏世俗、不惧强权,保持自己高洁的精神气概,深于情者,将对宇宙和人生怀着某种至深且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悲伤是悲天悯人的伤怀,快乐是深入肺腑的体验。这种精神上的憧憬、自由、解放才能让我们的人生绚丽绽放,以宽阔的胸襟与气度接纳这个世上的万事万物,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体会它的深沉,体味它的情深,真正让生命境界与宇宙意识在我们的脑海中释放光芒。正如陶潜的清真、嵇康的侠情、阮籍的佯狂、杜甫的蔼然。“艺术的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一呼一吸,微笑相伴,悦怿风神,悠然自足。”[7]
三、对人与自然之辩证关系的客观肯定
诗至唐代意境理论渐趋成熟,皎然提出“取境”和“造境”。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三境说将诗之境界划分为物境、情境、意境三类。刘禹锡也提出“境生于象外”的美学命题。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有言:“今王生者,寓居期间,沉浸益久,五言所得,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3]125在对待诗之意境的问题上司空图坚持思与境偕。思是神思,主要指诗人创作时的心理活动,与“心” “意” “情”相连;境是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与社会之境,与“景” “物” “象”相偕。思与境偕强调的是诗人主观情思与客观世界的和谐统一,是自然与由自然所激发的主观思想情感的交融。对于文学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二中曾说:“情景名为二,其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8]文学创作恰是作者发现自然之景、探求自然之境的过程,文学作品则是景与境、思与情融合的产物。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9]杜甫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溅泪的并非花,惊心的也并非鸟;冯延巳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不语的也并非花;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妩媚的更不是青山。所有的感慨皆是作者主观情感的外化,是作者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超越性再现。
在司空图看来,诗境的形成是难以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的,正是自然触发了创作者的主观情思,艺术作品是心与物、意与象、情与景、人与自然的相织交融。关于意与象的关系《易》中有记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0]510“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10]495万事万物代代不穷,生命轮回永不停止,意与象、物与我也是融合为一生生不息的,正如司空图在《疏野》篇中所言:“但知旦暮,不辨何时。”[3]71日月交替往复,万事万物与我永久相伴,不必在意今夕何夕何月何年。人与自然相织相融密不可分,缘起于物、情始于境,《乐记·乐本》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音之所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11]钟嵘《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2]《文心雕龙·明诗》也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3]司空图在《豪放》篇中说:“真力弥满,万象在旁”[3]58,司空图认为创作之时只有万心存万物,诗人的万丈豪情才能弥散奔放。司空图在《精神》篇中说:“欲返不尽,相期与来。”[3]63他坚信诗人唯有在自然界不断地探索、找寻和发现新的境界才能联翩袭来。他在《形容》篇中说:“俱似大道,妙契同尘。”[3]96司空图宣称唯有体悟了融贯万物的大道,笔下的万事万物才能精微入神。他在《自然》篇中说:“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3]48司空图认为好诗总是信手拈来的,并不需要刻意追求,好的诗篇是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只有这样诗篇才能创造出美妙的诗境。
司空图在《含蓄》篇中说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3]53这与刘勰所推崇的“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司空图认为文学语言应以追求含蓄减省为核心,尽求自然减少不必要的雕饰和人工造作的痕迹。《论语·卫灵公》中有言:“辞达而已矣。”[5]248《论语·雍也》中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5]78孔子反对文章中过度的修饰,在他看来作品中的文与质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统一的,朗加纳斯曾说:“一篇文章的思想和文词是相互依存的……就真正的意义来说,美的文词就是思想的光辉。”[14]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应该和谐恰当,文采与质朴配合恰当才能成就好的文章。因此,司空图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在达到含蓄之境的基础上追求韵外之致,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3]125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于朴实中见别致,于质朴中见华美,寓浓于淡、于淡现浓,这才是司空图所推崇的真正具有韵味的诗。严羽《沧浪诗话》中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15],《易·系辞上》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10]478,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3]125,以及文学史上的诗无达诂、意在言外等理论的提出都标志着文学理论家们在文学创作中平衡自然与人为因素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我。自然是新鲜的自然,是物之自然、诗之自然、我之自然。自我是深情的自我,是自然之我、艺术之我、自由之我。司空图试图告诫我们,艺术当与自然同行,通过对自然的体味传达出人生的最高境和时代的最强音,艺术与人生都在为达到“真”与“诚”而进行着不懈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