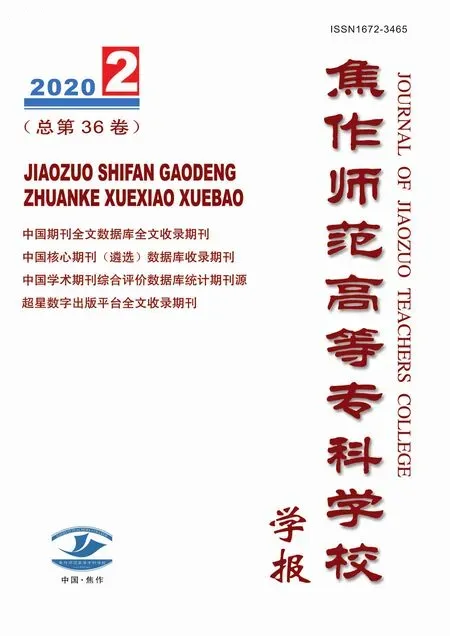李式赌片的突围表达
——以《妈阁是座城》为例
杨 静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西方有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神话,我国有孙悟空偷吃蟠桃的传说,好像都在告诉我们:贪婪是人的天性,欲望是人的本能。赌博源于欲望的冲动,赌徒因贪婪而行动。 赌博题材的电影在我国并不罕见,尤其以香港最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晶导演拍摄了一大批赌博系列的电影,如《赌神》《赌圣》《赌侠》等等。虽然同是以“赌”作为影片核心,但与王晶式的男人在赌场叱咤风云书写传奇的赌片不同,李少红的《妈阁是座城》以其十分细腻的女性视角,展现了光怪陆离的赌场风貌,揭示了身处欲望之中的人情人性。影片的女主角梅晓鸥是澳门赌场中的一名叠码仔,她每天穿梭于赌场之中,见惯了形形色色的赌徒和他们永不满足的欲望。在赌场中她遇到了三个与自己纠葛不断的男人,即使被抛弃、被欺骗,她也仍对感情抱有幻想,但当她一次次的深陷其中后才发现,赌徒终究是赌徒,对金钱和欲望的渴求才是他们生存的要义。
一、对于传统赌片的突围
赌片作为商业电影的一个类型,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风靡一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票房成绩。这些影片以影坛偶像为主角,故事情节奇特,牌技花样炫目,骗术奇思妙想,故事充满娱乐性。尤其是许多赌片的高潮,集中在影片结尾 show-hand(摊牌)的那场戏,情势逆转,跌宕起伏,主角光环笼罩,金钱美女在握,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赢得最后的胜利,深受大众追捧。1989年,电影《赌神》以3 600万的年度冠军票房一举将导演王晶扶上了香港赌片开山鼻祖的位置。自此以后,两岸三地导演便对赌片趋之若鹜,香港赌片进入 “黄金时代”。《赌圣》《赌神》《至尊无上》《赌侠》《千王之王》《澳门风云》等一系列讲述赌博的影片层出不穷,这些电影有一个共同点:描述的都是职业的赌徒,展现的都是光怪陆离的赌场赌术。由元奎、刘镇伟联合执导的《赌圣》讲述了大陆青年星仔误打误撞卷入香港赌王洪光和台湾赌王陈松的争斗后,历经一番波折最终赢得了比赛的故事;王晶的《赌神》讲述了赌神高进与在新加坡有“赌王”之称的陈金城在牌桌上决战的故事;《澳门风云》讲述了石一坚与小冷本是亦敌亦友的师徒,但小冷学艺到手后竟然反过来与石一坚对决的故事。李少红却另辟蹊径,以女性导演特有的细腻,从女性情感入手,通过讲述梅晓鸥与三个男人的纠葛一生来表达赌博对人的影响,呈现出一部异于传统类型的赌片。影片中赌博的镜头并不多,但是一个“赌”字始终贯穿全剧,与情感高度融合,赌中有情、情中有赌。影片的旨归在于表现赌博对人一生的改变和影响,却少见男人们在赌桌上叱咤风云的画面,而是从梅晓鸥、史奇澜们细微的感情和生活中得以体现,相较于以往的赌片,更深刻地揭示了人情人性,疏离了对赌术牌技的表现。
不仅是赌片主题的不同,女性角色到了女性导演的手里,也得到了不一样的塑造。《赌神》中的女性角色珍妮是赌神高进的妻子,因美丽而遭高进堂弟高义的强暴,并被其失手杀害,由此也引发了一场高进与高义之间的“战争”。导演一定程度上将珍妮塑造成了一位祸水式的形象,将女性角色定位为悲剧发生的来源。《赌圣》中的女主角绮梦,她是台湾赌王派遣的美女卧底,她的出现致使男主角星仔想倒戈帮助台湾赌王;香港赌王绑架了绮梦来胁星仔,星仔因此无心赌赛,直到三叔救出绮梦赶到赛场,星仔见爱人无恙,才大显神通战胜对手。这里的绮梦俨然一位貂蝉式的女性形象,身不由己为男人们所摆布。《澳门风云》中景甜所饰演的洛欣是一位中国女公安,虽然是正面形象,但也只是一个配角,影片的核心内容还是赌场中“厮杀”的男人们。由此可以看出,以往的传统赌片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都是负面形象或者不重要的配角,女性形象的塑造大多是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用女演员为影片“增色”,女性始终扮演着男性的“他者”,处于被看的地位。而《妈阁是座城》的主角是梅晓鸥——一个女性形象,故事内容围绕梅晓鸥的感情生活展开,这打破了以往女性形象处于“他者”的地位,突破了传统赌片的叙事模式。李少红不是单单地展现赌场纸醉金迷的生活,也不仅仅是讲述梅晓鸥波澜起伏的感情,而是试图将梅晓鸥的爱情故事融入到欲望之城中去,用一个女性的视角去展现赌博对人性的摧残,从而使影片落足到戒赌的内核,这无疑是一次十分新颖的尝试。
二、性别视域下对“赌”的认识
妈阁,Macao,澳门,一座空气中都充斥着欲望气息的城市,城中的男男女女都经受着赌博的熏陶。赌博本就是人难以泯灭的本性,尤其对于妈阁这座光怪陆离的欲望之城、游戏之城而言,城外的人很容易走进来,城里的人却很难走出去,叠码仔梅晓鸥就是如此,与其纠葛的三个男人亦是如此。不同的是,男人在赌桌上叱咤风云,他们的欲望无外乎就是金钱,而梅晓鸥却更像是一个情感场上的“赌徒”:前夫卢晋桐因为嗜赌而抛弃她,史奇澜、段凯文沉溺赌场欺骗她,使梅晓鸥替他们背上了巨额的债务。妈阁不仅指代行政及地缘意义上的澳门,更是一座无形的欲望之城,一座因赌博而生之城。赌场有庄有闲,情场有输有赚,筹码越高,输的代价就越大。梅晓鸥一次又一次陷入感情的深渊,无法自拔;而段凯文们却可以在赌桌上酣畅淋漓豪赌一场,输光了就潇洒的离去,即使再回来,也是出于对赌桌的留恋,与感情无关,与女人更无关。
与梅晓鸥爱恨纠葛的第一个男人是她的前夫卢晋桐,当然,他也是赌场中千千万万的赌徒之一,当他的妻子梅晓鸥到赌场劝他回家时,他一脚将有孕的梅晓鸥踢开,这一“踢”,踢断了两人的感情、踢散了两人的婚姻。影片对于卢晋桐的赌博行为并没有做直面的描述,只是通过梅晓鸥的回忆,告诉观众是因为卢晋桐嗜赌才导致两人的婚姻结束。即便这样,观众还是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他的“赌性”:他坐在赌桌旁移不开视线和身体,他无视孕妻的呼唤甚至对其加以伤害……后来,卢晋桐戒赌与否,影片并没有交代,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卢晋桐的心中,赌博、金钱和欲望是要大于一切的,至少比爱情、婚姻和家庭更重要。段凯文是梅晓鸥的一个客户,身价上亿的房地产大亨,儒雅、有文化,然而也深陷赌场不能自拔。赌徒的欲望是无穷的,赢了想再赢,输了想翻盘,段凯文就是如此。他在赌场一掷千金,赌输了就拆东墙补西墙,一次托底让梅晓鸥为他背上了几千万的债务,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别墅。段凯文是影片中嗜赌如命的男人,他几乎没有想过收手。赌场助长着他无休止的贪欲,即使输到倾家荡产,他仍觉得还能翻盘。他有一种执念,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拗。但是,他将这种执拗全部投入到赌博之中。虽然他和梅晓鸥之间的感情是模糊的、不明显的,但是梅晓鸥敬重他、仰慕他,把他当做真正的朋友,他却一次次的利用、欺骗梅晓鸥。在他心中,感情远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金钱实在,显然,他只是一个赌钱的人。史奇澜是梅晓鸥在去北京找刘总催债时认识的,他原本是一个天赋异禀的雕刻家,心中却一直向往着澳门赌场纸醉金迷的生活。他去了澳门,进了赌场,爱上了梅晓鸥,但爱情在赌博面前太过渺小。与段凯文不同,史奇澜发自内心的想过戒赌,他之所以赌博,是因为欲望之外还想有新奇的体验,不纯粹为了金钱。在轰轰烈烈赌了一场之后,他开始醒悟了。为了戒赌,他去了广西柳州的一个山村,专心做着雕塑。这里与充斥着物欲横流的赌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能否认的是,史奇澜与卢晋桐、段凯文并无本质区别——皆为金钱和欲望而赌。
“女性并不是生就的,而是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这样说到。梅晓鸥与赌博的渊源由来已久。她的祖父嗜赌,败光了家业,她的身体里流淌着赌徒的血液;结婚后,丈夫卢晋桐嗜赌成性。离婚后,梅晓鸥独自一人抚养儿子,或是出于对卢晋桐的报复,或是迫于生计的压力,梅晓鸥选择了赌场叠码仔的工作。“叠码仔”就是赌徒与赌厅之间的掮客,靠抽取佣金为生。梅晓鸥本是最厌恶赌博的人,却偏偏因为工作而每天和赌场赌徒打交道。这种纠结形成一种循环,使她一生所抗拒的东西又时刻在环绕着她。这种处理使作品表现出宿命感。更有隐喻意味的是,影片将切口对准了梅晓鸥屡战屡败的情感生活,即使她是叱咤职场的女强人,也逃不过感情的羁绊,同时这也是许多女性所面临的情感困境。“在女性特有的感性心理特质影响下, 她们都要经历从女性意识觉醒到义无反顾的逐爱之路, 继而后知后觉, 不得已反求诸己。”[2]梅晓鸥身处欲望之城却不赌钱,对感情抱有执念,相对于男人在赌桌上的豪掷千金,她更愿意将自己的身心托付给男人,尽管被一再伤害,仍不改初衷。陷入感情无法抽身的女性也是无脑的赌徒,只是男人赌钱而她赌感情罢了。
三、欲望下的人性书写
“赌”是人性的试金石,能撕开所有的伪装。卢晋桐在赌桌上也曾好言好语对梅晓鸥说话,可一旦输了钱,他便将一切责任归咎于梅晓鸥带来的晦气,对有孕在身的妻子拳脚相加,毫无人性。离婚后的两人再无联系。在电影的前半部分,卢晋桐只存在于梅晓鸥的叙述之中;卢晋桐的再次出现,是在梅晓鸥到海南找段凯文催债时居住的酒店里。显然,卢晋桐的眼神里、话语里带有悔恨之意,这种悔意更体现在他对儿子的依恋上。虽然赌博将其人性泯灭到只剩下对金钱的追逐,但毕竟血浓于水,亲情占据着他的心田。史奇澜对梅晓鸥是有感情的,可这份感情经不起赌桌的考验。走进赌场的史奇澜近乎丧失理智,抛妻弃女、自我作践、坑亲骗友。赌到一无所有的他被梅晓鸥拯救,最终戒赌成功的史奇澜选择回归家庭、抛弃梅晓鸥,走出了欲望之城。史奇澜对梅晓鸥还是心存真情的,段凯文则是始终眼睛只盯着金钱。他永远将自己伪装成谦谦君子——在欠下几千万债款时还能气定神闲地给梅晓鸥讲述渔翁得利的理论;在被梅晓鸥几度追着要债时,身无分文的他还能自然地说出“明天就给你打款”。在贪婪欲望促使下,人们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会赢。段凯文一次又一次走进赌场,就是因为他想赢,并觉得他能赢。在人性面具层层剥落之后,为了所谓的翻盘,他仍谎称要竞标土地,在骗了梅晓鸥两百万后转身又坐到了赌桌旁;为了“还”梅晓鸥的债,他将作废的地契拿给她抵债。段凯文为赌疯狂,失去的不只是自由,更是人性。
对欲望的追求是人的本能。根据弗洛伊德的“原欲说”,“‘原欲’与自我(它遵循现实的要求)和超我(它遵循社会规范的要求)之间的永不缓解的冲突必然产生挫折和焦虑,因为‘原欲’的能量是不灭的 ”[3]。正如史奇澜一边在赌场“厮杀”,一边还想脱离“赌海”。前者是原欲所致,后者是自我与超我对其约束,“原欲”与自我、超我的冲突造成了他矛盾的性格。为了让别人相信他戒了赌,便告诉梅晓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尽快还上欠她的债,于是,他心安理得地去南边的赌场玩托底,更不惜将自己的表弟拉下水。终于,在现实和社会规范的双重作用之下,他选择了逃离。当梅晓鸥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偏僻的深山里专心做雕塑,这是他的第一次逃离。后来两人同居,梅晓鸥帮他办雕塑展,两人的日子逐渐过得有起色时,再一次路过赌场门口的梅晓鸥向史奇澜讲起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戒赌——赢了就收手。史奇澜再一次冲进赌场,与以往不同,这次他的确赢了钱就走出了赌场。可游戏是人的本能,“原欲”是永远存在的。史奇澜内心也是深知这一点,所以他选择了第二次逃离:取得妻子原谅,回归家庭。他抛弃了救他于水火之中的梅晓鸥,回到了北京,既然心理上无法摆脱赌欲,就从地理上远离这座城。
执迷不悟的不只是在赌桌上流连忘返的男人们,梅晓鸥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感情”的赌场。她的人生被三个男人划分成几个阶段,看似是三个男人闯入她的生活,实则是她自己掀起了一场以感情作为筹码的人生的赌局。梅晓鸥把感情赌注下在了赌徒身上,可谓是更加的孤注一掷,不留余地。但影片将梅晓鸥的形象塑造得过于理想化,她本是职场上的女精英,阅历丰富,客户无数,却偏偏不可遏制、没有理由地爱上了赌徒史奇澜,为他还债,帮他戒赌,甚至不惜背上第三者的骂名。如果说梅晓鸥对史奇澜的付出是因为爱情,那还情有可原,即使这份爱情来得太没有缘由,那么梅晓鸥对于段凯文的好,从动机上则让人无法理解。段凯文背着她玩托底,输了之后又利用她,她为此背上了几千万的债务,为还债她甚至卖掉了自己的别墅;但当段凯文冠冕堂皇编着理由再次找她借钱的时候,她仍然于心不忍,又借给他两百万,俨然一副圣母形象,这也与史奇澜几度雕刻的艺术品“白圣母”前后映照。
影片的结尾,卢晋桐患癌而亡,史奇澜回了北京,段凯文进了监狱,梅晓鸥的生活又恢复平静,好似一切都未发生过。但是,妈阁这座纸醉金迷的城市,每一天每一分钟仍然上演着史奇澜、段凯文们的闹剧,仍然进行着人性的自我撕扯,而史奇澜、段凯文们,则会继续寻找新的欲望,继续沉溺其中, “人的欲望总是无穷尽的,对欲望的满足总是暂时的、有限的、相对的。即使一种欲望已经实现,已经得到满足,又会产生新的欲望和追求,人的欲求是无穷无尽的,永远无法全部满足的,这样人生的痛苦就永远无法消除”[4]。影片中的赌场是男人们欲望的发泄地,也是梅晓鸥工作的地方,史奇澜们将这里看作是钱、是欲望,但对于梅晓鸥来说,这是她谋生的地方。男人们带给她的是无尽的失望,在感情上她一败涂地,唯有工作能给予她安全感,所以即使在情场上豪赌一场,结束后她还是要回归工作,以坚韧的姿态去面对生活。这是一部关于赌博、欺骗和爱的现实文艺片,坚韧的女人、暧昧的情感依旧是李少红式的电影风格,只是受现实元素冲击的较为明显,爱与欺骗是现实的,诱惑和深渊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