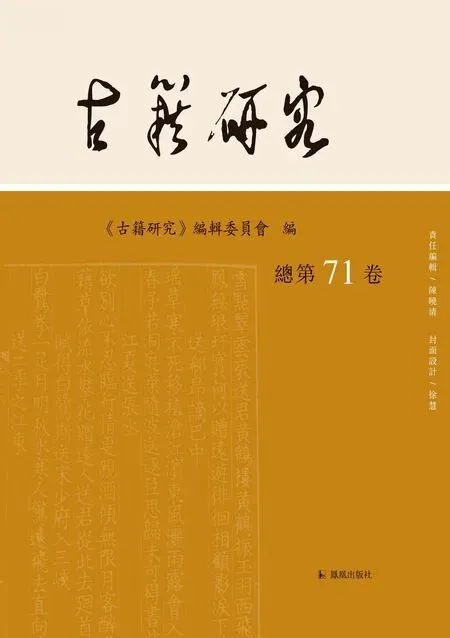蕭子良與西邸文士的精神生活*
——以“邸園”與“邸寺”为中心
李 猛
關鍵詞:蕭子良;邸寺;邸園;講經;精神生活
蕭子良開西邸,是南朝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前學界討論已經非常充分。本文希望從西邸選址以及西邸中的“邸園”與“邸寺”,來討論蕭子良與西邸文士在西邸的各類活動空間及其展開的文學和佛事活動,藉以討論他們的精神生活。日本學者中嶋隆藏曾撰寫《蕭子良の精神生活》一文,主要討論蕭子良與佛教信仰相關的精神生活(1)[日]中嶋隆蔵:《蕭子良の精神生活》,《日本中國學會報》第30集,1978年,第72—86頁;中譯本收入方旭東主編《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徐送迎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但只是偏向於哲學與宗教方面,也很少涉及西邸文士,所以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一、 西邸的選址
據《南齊書·蕭子良傳》,蕭子良的西邸在鷄籠山,《南史》徑謂之“鷄籠山西邸”。永明五年,子良正位司徒之後,纔正式移居西邸,其時西邸已然建成,那麽選址與動工開建,應該在蕭子良任護軍將軍、車騎將軍兼司徒的時期,即在永明二年正月至五年正月之間(2)(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三《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52頁、56頁;卷四《蕭子良傳》,第772頁。。那他爲麽什要將自己的府邸建在鷄籠山呢?其實,在蕭子良之前,宋文帝劉義隆即爲其愛子建平王宏立第於鷄籠山: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食邑二千户。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鷄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二十四年,爲中護軍,領石頭戍事。(3)(梁)沈約:《宋書》卷七二《建平宣簡王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858—1859頁。
宋文帝劉義隆對建平王宏“寵愛殊常”,甚至連“建平國職”都要“高他國一階”;元嘉二十九年,太子劉邵與始興王劉濬巫蠱事發,宋文帝欲廢立,就曾欲立宏爲太子,却因其長幼非次而未决(4)(梁)沈約:《宋書》卷七一《王僧綽傳》,第1850—1851頁;同卷《徐湛之傳》,第1848頁。。由此亦可見宋文帝對劉宏之寵愛確實殊常。又據《高僧傳·僧遠傳》,劉宏之子建平王劉景素曾謂“棲玄寺是先王經始”(5)(梁)釋慧皎著,湯用彤點校:《高僧傳》卷八《齊上定林寺釋僧遠》,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319頁。,而棲玄寺在鷄籠山東北(詳下),則宋文帝爲建平王劉宏所立之第應當也在鷄籠山東,甚至有人認爲棲玄寺乃建平王宏捨宅而建(6)(清)劉世珩:《南朝寺考》卷三,光緒三十三年聖廎叢書本。。宋文帝於鷄籠山爲劉宏所立之第,號稱“盡山水之美”,這恐怕是宋文帝選擇於鷄籠山立第的重要原因。蕭子良之所以將自己的宅邸建於此山,恐怕也是緣此。任昉在《竟陵文宣王行狀》中,對西邸的環境就有濃墨重彩的描述:
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猿與壺人争旦,緹縸與素瀨交輝。置之虚室,人野何辨。……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7)(梁)蕭統編,李善等注,俞紹初等點校:《新校訂六家注文選》卷六任彦昇《竟陵文宣王行狀》,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917—3919頁。
據此可知西邸依鷄籠山中的林、巖而建,環境清幽,而且蕭子良還曾作《山居四時詩》歌詠之,並在《序》中詳叙鷄籠山的卉木之奇、泉石之美。蕭子良此詩,王公多有唱和者,尚書令王儉作《竟陵王山居讚》,盛讚此山居乃是蕭子良之濠梁(8)(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三六《人部·隱逸上》載《竟陵王山居讚》:“升堂踐室,金暉玉朗。亹亹大韶,遥遥閑賞。道以德弘,聲由業廣。義重實歸,情深虚往。濠梁在兹,安事遐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52頁。。隨郡王蕭子隆亦作《山居序》,謂“西園多士,平塞盛富,郯、焉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娱,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9)(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卷二四引,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569頁。以子良山居比漢梁孝王之西園,誇讚子良山居中文士之盛,是篇應當也是唱和之作。當然,參與唱和的人肯定還有不少,只是大部分唱和詩文没能保存下來。
鷄籠山有山水之美,當然與其地形與位置有關。據顧野王所編《輿地志》,鷄籠山“在覆舟山之西二百餘步,其狀如鷄籠,因以爲名”(10)(宋)張敦頤著,張忱石點校:《六朝事迹編類》卷六《山崗門》引,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94頁。。在城西北六七里,高三十丈,周迴一十里。(11)(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一七《山川志》,《宋元方志叢刊》第2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562頁上。西接落星岡,北臨棲玄塘(12)(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江南東道二·昇州上元縣》,第1782頁。。因爲是山水形勝之處,故自東晋元帝葬鷄籠山之陽以來,這裏先後成爲東晋明、成、哀四位皇帝之陵(13)(唐)許嵩著,張忱石點校:《建康實録》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28頁。。鷄籠山正臨玄武湖,宋文帝元嘉後期,以黑龍嘗見玄武湖,黑龍是大瑞,故改鷄籠山爲龍山(14)《六朝事迹編類》卷六《山崗門·鷄籠山》,第94頁。因黑龍祥瑞而改鷄籠山爲龍山事,《宋書》未載,而《宋書》卷二八《符瑞志中》確載黑龍祥瑞事:“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黑龍見玄武湖北,苑丞王世宗以聞。元嘉二十五年五月戊戌,黑龍見玄武湖東北隈,揚州野吏張立之以聞。”第800頁。。而在未改名之前,宋文帝曾徵儒士雷次宗進京,在鷄籠山爲其開學館:
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詔曰:“前新除給事中雷次宗,……宜加升引,以旌退素。可散騎侍郎。”後又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15)《宋書》卷九三《隱逸·雷次宗傳》,第2293—2294頁。
《建康實録》確載宋文帝於元嘉十五年十月“立儒學於北郊,延雷次宗居之”(16)《建康實録》卷一二,第432頁。而此處的北郊,當即指鷄籠山,蕭道成與兄蕭道度均在鷄籠山從雷次宗受業,治禮及《左氏春秋》,將近四年(17)《南齊書》卷四五《衡陽元王道度傳》,第873頁;《南齊書》卷一《高帝紀》,第3頁。。雷次宗回廬山後,宋文帝再次徵其還建康,却並未將其安置在原鷄籠山儒學學館,而是爲之另建招隱館於鍾山西巖之下,而儒學似亦隨之遷至鍾山招隱館,故《景定建康志》引《宫苑記》載“儒學在鍾山之麓,時人呼爲北學,今草堂是也”(18)《景定建康志》卷二八《儒學志·前代學校興廢》,第1797頁下。。草堂,即草堂寺,寺乃汝南周顒於鍾山雷次宗舊館所造(19)(唐)道宣撰,郭紹林校注:《續高僧傳》卷六《梁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83頁。。除雷次宗的儒學學館最初在鷄籠山之外,四學中的玄學、史學、文學三館似乎最初也都在鷄籠山及其附近,《宫苑記》載:“玄學在鷄籠山東,今棲玄寺側;史學、文學並在耆闍寺側。”(20)《景定建康志》卷二八《儒學志·前代學校興廢》引,第1797頁下。據此可知史學、文學在耆闍寺側,而耆闍寺實在鷄籠山之西。另前文已述,棲玄寺在鷄籠山東北,與《宫苑記》相合,却與《宋書·何尚之傳》稍有不同:
(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何)尚之爲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黄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21)《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第1734頁。
既云“南郭外置玄學”,則玄學應在宫城城墻之外。據《宋書·何尚之傳》,何尚之之宅在南澗寺側。南澗,即落馬澗,在建康秣陵縣東南,水下秦淮(22)《太平寰宇記》卷九《江南東道二·昇州江寧縣》,第1777頁。北宋之江寧縣,本南朝之秣陵縣。。何尚之立宅南郭,聚生徒、授玄學,學士慕道而來,竟有“南學”之謂,可見其盛。而“南學”之稱,實與雷次宗之“北學”相對應,可見其影響頗大,可與雷次宗媲美。另據《建康實録》,立儒學的次年即元嘉十六纔立玄學、史學、文學三館,當時學館多因人而設,頗疑何尚之所立之玄學與雷次宗之立儒學有相似的境遇,也曾前後隨所立之人而遷移。而鷄籠山當亦有玄學館,兩種記載可互相補充,實際上並無實質性的矛盾。宋文帝死後,時局動蕩,國學時廢。至泰始六年(470),宋明帝詔立總明觀,置祭酒,仍設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23)《宋書》卷八《明帝紀》,第167頁;《南齊書》卷一六《百官志》,第351頁。《南史》卷三《宋明帝紀》謂四學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82頁。,四學逐漸制度化。
永明七年,竟陵王蕭子良上表請爲“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24)《南齊書》卷三九《劉瓛傳》,第755頁。的當世大儒劉瓛立館,推薦的地址就在西邸附近。子良此表,《藝文類聚》卷三八有節録,題作《求爲劉瓛立館啓》,歸任昉名下,當是任昉受蕭子良之命而作:
(劉)瓛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集。臣第西偏,官有閑地,北拒晋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黌塾。薄蓺桑麻,粗創茨宇。(25)《藝文類聚》卷三八《禮部上·學校》,第695頁。
蕭子良的本意是在其西邸偏西的官家數畝閑地上,爲劉瓛新建館舍,以爲學館,即所謂的“粗創茨宇”。然而,齊武帝蕭賾似没有聽從其意見,而是以“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應是考慮到新建學館費時較長。揚烈橋乃運瀆六橋之一,位於孝義橋之南、西州橋之北,王僧達曾於此處觀鬥鷄鴨,則此宅第距蕭子良之西邸較遠(26)《建康實録》卷二載:“運瀆舊有六橋:孝義,本名甓子橋。次南有楊烈橋,宋王僧達觀鬥鷄鴨處。次南出有西州橋,今縣城東南角路東,出何后寺門。次南有高曄橋,建康西尉在此橋西,今延興寺北路東度此橋。次南運瀆臨淮有一新橋,對禪靈渚渡,今之過淮水橋,名新橋,本名萬歲橋。”第49頁。,距劉瓛的故宅亦較遠(27)據《建康實録》,檀橋在建康東尉蔣陵里,宋元嘉十一年,宋臨川公主曾於位於縣城東一里處的檀橋造竹園寺,第429頁。《六朝事迹編類》卷七《宅舍門·劉子珪宅》亦載“檀橋,在今縣東二十五里青龍山之前”,第113頁。。然而畢竟是某亡故公主之宅第(“故主第”),條件甚好,故劉瓛謂之“華宇”而不願居住,只是作爲講堂。可惜劉瓛不久就去世,這處學館後來逐漸被始安王蕭遥光與江祏於蔣山南爲吴苞所立之學館代替(28)《南齊書》卷五四《高逸·吴苞傳》,第1041頁。。
學館之外,寺院也是鷄籠山重要的景觀,而且多緊鄰學館,前引《宫苑記》已明,玄學在棲玄寺側,史學、文學並在耆闍寺側。而棲玄寺在覆舟山西南、鷄籠山東北,耆闍寺在鷄籠山西。此外,歸善寺也在鷄籠山之東。歸善寺東經棲玄寺門,北至後湖,以引湖水,即是運瀆;而自歸善寺門前東出至青溪者,名曰潮溝(29)《建康實録》卷二,第49頁。《南朝寺考》謂永初中置北寺於歸善寺側,係誤“北市”爲“北寺”。,交通甚爲便利,故其位置甚爲津要。運瀆連接歸善寺與棲玄寺,可見兩寺至少是有些距離的。但《續高僧傳·隋丹陽攝山釋慧曠傳》却載“歸善禪房,本棲玄精舍,竟陵文宣之餘迹”(30)《續高僧傳》卷一《隋丹陽攝山釋慧曠傳五》,第346頁。,這裏道宣似有將二者混同之嫌,從歸善寺有蕭子良之“餘迹”來看,他與歸善寺聯繫頗深。如此一來,在蕭子良開西邸之前,在鷄籠山附近至少已有三所寺院。(31)《六朝事迹編類》卷六《山崗門·鷄籠山》載“山中有佛寺五所”(第95頁),具體是哪五所不詳。此後,蕭子良又在西邸之中修繕有普弘寺、邸山寺等幾處邸寺(詳下)。此外,鷄籠山在劉宋的官方祭祀中,也佔有一席之地。據《宋書·禮志》,宋明帝劉彧曾“立九州廟於鷄籠山,大聚群神”。(32)《宋書》卷一七《禮志四》,第488頁。
由上可知,鷄籠山緊鄰玄武湖,其山水之美得到當時王公貴胄的青睞,玄、儒、文、史四學之學館也曾設於此地。同時,鷄籠山也是建康西北郊重要的宗教名山,在其周圍至少有五所重要寺院。與位於建康東郊的鍾山相比,鷄籠山距離建康城更近,而這恐怕纔是宋文帝爲愛子建平王宏立第於此、永明初蕭子良選擇在此地建府邸的最重要原因。這一點,在蕭子良身上體現的更爲明顯,永明二年,蕭子良以護軍將軍兼司徒,同時還須“鎮西州”(33)《南齊書》卷三《武帝紀》,第52頁;《南齊書》卷四《蕭子良傳》,第772頁。。永明四年,子良由護軍將軍進號車騎將軍,並未解鎮西州,至永明五年子良正位司徒纔解鎮西州(34)《南齊書》、《南史》蕭子良本傳均未載解鎮西州事。據《南史·鬱林王紀》,永明二年蕭子良移住西州,南郡王蕭昭業亦隨住;及移西邸(五年),蕭昭業則獨住西州(《南史》卷五《齊本紀下·廢帝鬱林王》,第135頁)。如此,永明四年,子良當亦鎮西州。。將府邸建在鷄籠山,不僅有“山水之美”,而且寺院、學館密佈,很符合蕭子良本人的志趣,况且此山與距離建康城與西州城都很近,來往便捷。當然,將府邸建在都城西北郊,也方便子良與諸大德(尤其是建康以外)的往來。既處在政治中心,又與絶對的政治中心有一定的距離。
事實上,在永明十年(492)領揚州刺史(治所在東府城)之前,蕭子良的活動中心大多在都城之西。永明八年,荆州刺史巴東王蕭子響殺上佐,都下匈匈,人多異志,蕭衍、范雲等人均認爲蕭子良與揚州刺史豫章王嶷應各鎮一城(即石頭城和東府城)以安民心,此議得到蕭賾的認可(35)《南史》卷五七《范雲傳》,第1417—1418頁。。豫章王嶷受命鎮東府,雖是職責所係,但早在永明七年他就已請求還第,齊武帝已命豫章王世子蕭子廉代鎮東府(36)《南齊書》卷二二《蕭嶷傳》,第462頁。。蕭子良也早已正位司徒,故而這種臨危的應對方案,既反映了蕭子良其時的政治地位,也從側面印證了蕭子良在都城以西的責任與勢力。
二、 “邸寺”與“内堂”
蕭子良信奉佛法,尤其是在永明中後期有很多護持佛法舉措,也深度參與了齊武帝整頓佛教(37)參拙文《論蕭子良永明中後期的奉法與弘法——以蕭子良與諸人來往書信爲中心》,《文史》2015年第3期;《論齊武帝永明中後期對佛教的整頓》,孫英剛主編《佛教史研究》第1卷,2017年。。雖然並非蕭子良所有奉法與護法活動的地點都在西邸,但可以確認的是,西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動中心,其中相當一部分活動是在西邸舉行的,包括招集高僧於西邸義集、齋講等。而此前的研究對這一點關注很不够,或者説是區分度不高。西邸之所以能承辦如此多的法會、齋會、齋講等較大規模的佛事活動,當然是因爲蕭子良在西邸建有寺院,並招請名僧駐錫,而這些寺院往往被稱爲“邸寺”。如普弘寺,裴子野《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行狀》(以下簡稱《智稱行狀》)即載:
朱門華屋,靡所經過。齊竟陵文宣王顧輕千乘,虚心八解,嘗請法師講於邸寺,既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38)(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二三,《大正藏》第52册,第269頁中。按“行狀”二字,宫本作“碑”,宋、元、明本作“碑并序”,而此卷開頭之目録則作“誄”。觀此文的内容與格式,是行狀而非誄。
《高僧傳·釋智稱傳》亦載此事:“頃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弘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承旨。”(39)《高僧傳》卷一一《釋智稱》,第438頁。據此,《智稱行狀》中的“邸寺”,當即普弘寺。而據僧祐《略成實論記》,蕭子良請僧祐與智稱於普弘寺講律,事在永明七年十月至八年正月二十三日之前。(40)(梁)釋僧祐著,蘇晋仁、蕭鏈子點校:《出三藏記集》卷一一,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405頁。既稱邸寺,則普弘寺當在蕭子良西邸之内似無疑。智稱受蕭子良之邀在普弘寺講律,席下僧衆竟達數百,可見普弘寺頗具規模。普弘寺之外,西州法雲寺也被稱爲邸寺,沈約《齊竟陵王發講疏》即載:
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内之法雲精廬,演玄音于六宵,啓法門于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41)《廣弘明集》卷一九,《大正藏》第52册,第232頁中。
實際上,永明元年蕭子良仍在南兖州刺史(治廣陵)任上,本不在建康,其行止明顯與“集名僧於帝畿”之語不合,故此“元”字很有可能是訛字。《法苑珠林》卷二《千佛篇第五·感應緣》即載:(子良)以永明七年二月八日於西第在内堂法會,見佛從東來,威容顯曜。(42)(唐)釋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一二,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440頁。按《法苑珠林》所載爲子良法會之地與沈約所載稍有不同,前者是子良感夢之所,爲叙述需要,特將地點從邸内的法雲精廬移至西第内堂,事雖有可以神化傾嚮,但舉行法會這件事情應當確有其事。其時間和地點都與《齊竟陵王發講疏》基本吻合,筆者曾據《法苑珠林》卷二《千佛篇第五·感應緣》所載蕭子良“以永明七年二月八日於西第在内堂法會”以佐證“元”字很有可能是“七”字之形訛(43)拙文《僧祐〈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録〉考論》,《國學研究》第41卷,2019年。。《南朝寺考》即謂法雲寺在西邸之内。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永明元年正月壬子(三日),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蕭子良遷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從正月三日到二月八日,期間有一個多月,且京口(今江蘇鎮江)距建康甚近,加上二月八日是當時重要的佛教節日,重要的法會多於這一天舉行(44)參陳志遠:《辨常星之夜落:中古佛曆推算的學説及解釋技藝》,《文史》2018年第4期。。所以,蕭子良完全有可能先回京述職,於二月八日集名僧開講,結束之後再從建康赴任南兖州。果如此,則此次講席在永明元年,此“上邸”當非鷄籠山西邸,而是西州府邸,而“邸内法雲精廬”亦即西州府邸内的法雲寺。現在看來,後一種可能性較大。
小莊嚴寺。齊梁時期有兩個莊嚴寺,故須辨析。一乃劉宋孝武帝大明(457—464)中,宋孝武帝劉駿之母路太后於宣陽門外大社西藥園所造之莊嚴寺(45)《建康實録》卷八引《塔寺記》,第225頁。。此寺有七層塔(46)《南齊書》卷五三《良政·虞愿傳》載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宫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第1010頁。此既言“孝武莊嚴”,則此寺塔或爲孝武帝劉駿爲其母路太后所建。,頗具規模,且高僧雲集,建元中齊高帝蕭道成曾親至此寺聽僧達講《維摩經》(47)《南齊書》卷三三《張緖傳》未載僧達所講爲何經,第665頁;《南史》卷三一《張緖傳》確載講《維摩經》,第808頁。。而在此寺之前,謝尚於永和四年(348)捨宅造寺,即名莊嚴寺,故路太后將其改名爲謝鎮西寺。另一在建康定陰里,本是晋零陵王廟地,後來建康屠户鄒文立“罄捨家資,迴買此地”(48)《法苑珠林校注》卷六四引《梁京寺記》,第1916頁。,並於天監六年(507)請北來的道度禪師建寺。梁武帝賜名“小莊嚴”,還“施宣揚之門,以爲講堂”(49)蕭綱:《梁小莊嚴寺道度禪師碑》,[高麗]沙門義天《釋苑詞林》,録文參陳尚君師:《高麗僧義天〈釋苑詞林〉殘卷存六朝唐宋釋家遺文考録》,收入陳允吉編《佛經文學研究論集續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89—716頁;《弘贊法華傳》卷五,《大正藏》第51册,第24頁下—25頁上。。梁武帝既施宣陽門作爲小莊嚴寺的講堂,則大、小兩莊嚴寺似乎相距並不太遠。因天監六年道度禪師所建之寺乃是新寺,且梁武賜額“小莊嚴”,故文獻中便以“大莊嚴寺”稱路太后所建之寺,以示區别。而《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録》(以下簡稱《蕭子良法集録》)乃是蕭子良永明時期的弘法記録(50)詳細考證可參拙文《僧祐〈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録〉考論》,《國學研究》第41卷,2019年。,所以《西州法雲小莊嚴普弘寺講》中的小莊嚴寺,應非道度禪師所建之小莊嚴寺,而是路太后所建之寺。然宣陽門距西州甚遠,距西邸則更遠,所以《西州法雲小莊嚴普弘寺講》中“西州”似並不能統攝“小莊嚴”與“普弘寺”,而只用以修飾法雲寺。頗疑問蕭子良在西州或西邸曾另建一寺或道場,名“小莊嚴”,文獻中僅此一見,只能聊備一説。
不管是西州,還是西邸,法雲寺、小莊嚴寺與普弘寺,都是蕭子良於府邸所建之寺或供養之寺,在當時甚至被稱爲“邸寺”,故與蕭子良有比較緊密的聯繫。另據《比丘尼傳·邸山寺釋道貴尼傳》,蕭子良還曾爲道貴尼建頂山寺:
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善相推敬,爲造頂山寺,以聚禪衆。請貴爲知事,固執不從;請爲禪範,然後許之。於是結桂林下,棲寄畢世,縱復屯雲晦景,委雪埋山。……年八十六,天監十五年而卒,葬於鍾山之陽也。(51)(梁)釋寶唱撰,王孺童校注:《比丘尼傳》卷四《邸山寺釋道貴尼傳》,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21頁。
蕭子良爲道貴尼所造之頂山寺,具體位置不詳。道貴尼雖然固辭此寺之寺任(即“知事”),却答應作爲該寺“禪範”,長期駐錫此寺。從“結桂林下,棲寄畢世”以及“委雪埋山”等語來看,此寺確實建於山中。《釋道貴尼傳》並未言道貴尼移至他寺,當終於頂山寺。然而,《釋道貴尼傳》題曰“邸山寺”,傳中又言爲造“頂山寺”,當爲一寺無疑。加之“頂”與“邸”,音與形均不相近,故寶唱這裏應當是一寺兩稱。如此,則頂山寺或建在鷄籠山之山頂,故寶唱又以邸山寺稱之。
以上諸寺之中,法雲寺與普弘寺地位尤其重要,蕭子良命學士“總校玄釋,定其虚實”時,即選擇“於法雲寺建竪義齋”(52)《續高僧傳》卷五《梁揚都建元寺沙門釋法護傳》,第147頁。。而諸寺之中,尤以普弘寺講席最盛。《續高僧傳·释僧旻傳》載“文宣嘗請柔、次二法師,於普弘寺共講《成實》”(53)《續高僧傳》卷五《梁揚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傳》,第154頁。,則蕭子良命僧柔、慧次等法師抄《成實論》即在普弘寺。據僧祐《略成實論記》,蕭子良於永明七年十月,在普弘寺先後請柔、次二法師講《成實》,又請僧祐、智稱二法師講律(54)《出三藏記集》卷一一,第405頁。。而這也體現了永明五年蕭子良移居西邸後,兩個邸寺地位的交替,即西邸之邸寺普弘寺取代了西州邸寺法雲寺的位置。
除了寺院之外,蕭子良在西邸之内還有内堂,前引《法苑珠林》載“永明七年二月八日於西第在内堂法會”,則内堂應該是一個規模不太大的道場,既以内堂爲名,應與卧室不遠。而據《高僧傳·釋僧辯》,蕭子良卧室不遠即有佛堂:“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同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著工恒日。”(55)《高僧傳》卷一三《齊安樂寺釋僧辯》,第503頁。蕭子良做夢之後遂即到佛堂,説明這個佛堂距其卧室並不遠,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卧室隔壁或附近。如此看來,這個“佛堂”很有可能就在“内堂”之中,或許就是同一個地方。至十九日晚,再次“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次旦即招集京師善聲至西邸“作聲”(詳下)。十日之内連續感夢,如此頻繁,頗能反映蕭子良當時的精神狀態。
實際上,像蕭子良這類佛堂或供養佛像的内堂,在當時的蕭齊皇室中頗爲常見,如顯陽殿就有玉佛及供養,只是規模稍大,顯陽殿原本爲太后寢殿,但建元、永明時期均無太后,故齊高、武兩帝將其作爲供養佛像之地。文惠太子蕭長懋的東宫也有供養佛像之所、講經之所,玄圃園也有供僧人安居的道場(56)參見拙文《論蕭子良永明中後期的奉法與弘法——以蕭子良與諸人來往書信爲中心》,《文史》2015年第3期。。豫章王蕭嶷臨終交代後事,其中就有“後堂楼可安佛,供养外国二僧”(57)《南齊書》卷二二《豫章文獻王傳》,第417頁。。值得注意的是,永明七年二月九日,蕭子良在内堂舉行法會,“見佛從東來”。
三、 邸寺與邸園中的佛事活動
普弘寺、邸山寺與法雲寺既爲蕭子良所建之“邸寺”,故必然是西邸文士經常光顧之地。依托這些邸寺,蕭子良纔可以在西邸開展各類齋會、義集等法事活動。據《南齊書·蕭子良傳》,永明五年蕭子良移居西邸之後,主要的佛事活動與文事活動,也都相陸續移到西邸:
移居鷄籠山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58)《南齊書》卷四《蕭子良傳》,第772頁。
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是蕭子顯總結的蕭子良組織的三類最主要佛事活動。學界對“造經唄新聲”關注最多,此事對佛教音樂與佛教文學的影響尤大,中外學界對此事的討論也很多,從陳寅恪開始,到當代學者(59)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王小盾、金溪:《經唄新聲與永明時期的詩歌變革》,《文學遺産》2007年第6期。孫尚勇:《釋僧祐〈經唄導師集〉考論》,《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3期。吴相洲:《永明體的産生與佛經轉讀關係再探討》,《文藝研究》2005年第3期。[美]梅祖麟、梅維恒:《梵文詩律和聲病説對齊梁聲律形成的影響》,原載《哈佛亞洲學報》,收入《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第508—509頁。,對這一問題已經有比較充分的討論。但是,他們對此事的緣起與具體地點並没有太多關注。正如學界此前所關注的,此事與《高僧傳·齊安樂寺釋僧辯》《出三藏記集·經唄導師集》等所載可以印證,也都注意到西邸,但並未注意到此事的性質,亦未注意到西邸有寺院存在。其實,此事在出土文獻中也有印證,事見《大隋太尉晋王慧日道場故惠雲法師墓志》:
齊竟陵文宣王令問令望,兼外兼内,夢感賢聖授《瑞應》新聲。□高祖武皇帝□弘舍衛,述作迦維,敕諸寺沙弥四百人,就至心寺智淵經師,學竟□□集三百餘聲,并贊唄六十四首。法師少年,獨標□□,啓送温雅,飛時□遒。梁武□定,由斯價重,請業之徒,恒至數百。(60)《慧雲墓志》清道光年間出土,原石已佚,北京大學圖書館與揚州博物館藏有善拓,王其禕、周曉薇:《隋代墓志銘匯考》有録文,此處引文據陳志遠録文。
該墓志拓片漫漶不清,“竟□□集”四字,陳志遠推測當爲“竟陵法集”,將其與竟陵王子良集僧製梵唄新聲聯繫起來,並試圖利用《慧雲墓志》將齊與梁陳之間經唄的傳承的缺環打通,誠有卓識(61)陳志遠:《六朝的轉經與梵唄》,《佛學研究》2017年第2期,第100頁。。愚以爲“法”字,作“第”或“所”字更爲妥帖,更符合當時的表述習慣。《出三藏記集·經唄導師集》録新安寺釋道興所撰《竟陵文宣王第集轉經記》,《高僧傳·釋僧辯傳》亦載“集第作聲”。無論是“第集”還是“集第”,均是强調地點在蕭子良西邸,只是具體在哪座寺院不詳。從梁武帝蕭衍命“諸寺沙弥四百人,就至心寺智淵經師”學蕭子良主持製作的梵唄新聲,不難看出蕭子良此舉在齊梁時期的影響。
造經唄新聲之外,蕭子良還積極“招致名僧”至西邸,並延請他們“講語佛法”。招致之名僧,大多來自建康其他寺院以及建康郊區的寺院,如修冶城寺請鍾山延賢寺的釋智順至駐錫(62)《高僧傳》卷八《梁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第335頁。。當然,也有不少是地方州郡的名僧,如始興郡赤城山的釋慧明:“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挹,頻遣三使,殷勤敦請,乃暫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63)《高僧傳》卷一一《齊始豐赤城山釋慧明》,第426頁。釋慧明在始興郡赤城山造石卧佛與猷公像,後因山中禪修屢有靈應之事,爲蕭子良所知,故多次遣使敦請慧明至建康,慧明入京以後應當在西邸的某一個寺院駐錫。
至於蕭子良請名僧講語佛法的内容,則主要有《成實論》《維摩經》以及《十誦律》《法華經》等經。其中蕭子良請名僧講《成實論》與《維摩經》,基本都是在西邸的某所寺院,而且都有既定的目的,如請僧柔、慧次二法師於普弘寺共講《成實論》,主要緣於他不滿于《成實論》“近世陵廢,莫或敦修,棄本逐末,喪功繁論”的現狀,遂請僧柔、慧次等高僧抄撮九卷成爲新的本子。而蕭子良請名僧講《維摩經》,則更是如此,與永明七年他感夢於佛前詠《維摩》有非常直接的關係,前文所論蕭子良在西邸集名僧製梵唄新聲即緣此。永明八年蕭子良請净暉尼於西邸講《維摩經》(64)《比丘尼傳校注》卷三《净暉尼傳》,第143頁。。另《續高僧傳·釋智藏傳》還載蕭子良曾召集二十餘義學名僧講《維摩》:
太宰文宣王建立正典,紹隆釋教,將講《净名》,選窮上首,乃招集精解二十餘僧,探授符策,乃得於(智)藏。年臘最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罔或抗衡;道俗翕然,彌崇高譽。(65)《續高僧傳》卷五《梁鍾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傳》,第169頁。
《净名》,即《維摩詰經》。雖然道宣未明確交代時間,但大致可以斷定在永明七年蕭子良感夢後不久。蕭子良這次招集二十餘義學名僧講《維摩詰經》,與《高僧傳·釋僧辯傳》所載“集第作聲”似並非一事,不僅參與的僧人不同:後者所集乃是龍光寺普智、新安寺道興、多寶寺慧忍、天保寺超勝、安樂寺僧辯等“善聲沙門”,而這次所請乃是精解《維摩詰經》的義學高僧;而且内容側重點也有所不同:後者重在製作新聲,而這次重在“敷述義理”。據《比丘尼傳·净暉尼傳》,蕭子良永明八年還曾請净暉尼於西邸講《維摩經》(66)《比丘尼傳校注》卷三《净暉尼傳》,第143頁。。蕭子良本人於《維摩詰經》用力甚多,不僅請名僧講《維摩詰經》,還親自抄寫、抄撰、注疏《維摩詰經》近三十卷(67)《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録》中有《受維摩注名》一卷;《自書經目録》所載子良自書《維摩詰經》有:《大字維摩經》一部十四卷、《細字維摩經》一部六卷;《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抄經録》又詳載蕭子良抄《維摩詰經》有《抄維摩詰所説佛國品》一卷、《抄維摩詰方便品》一卷、《抄維摩詰問疾品》一卷,總計二十三卷。而《歷代三寶紀》《大唐内典録》《開元釋教録》等録均載子良“《抄維摩詰經》二十六卷”,詳細論述參拙文《〈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録〉考論》,《國學研究》第41卷, 2019年。。另外,蕭子良對僧律、僧制也非常感興趣,《蕭子良法集録》就録有《注優婆塞戒》三卷,《述受戒》共卷,《宣白僧尼疏》《與暢疏》共卷,《與僚佐書》并《教誡左右》一卷,《教宣約受戒人》一卷,《示諸朝貴〈法制〉啓》二卷,《受戒》并《弘法式》一卷。《廣弘明集·悔罪篇序》所提到的《布薩法》《净行儀》,這些法、式、制、教等類作品,在永明中後期集中出現之同時,蕭子良還請釋僧祐、釋智稱等人在西邸講律,請法獻、僧祐至三吴等地講律,都與其律學思想及其對佛教僧團的管理理念有關。
值得一提的是,蕭子良廣請名僧至建康、西邸講經,在當時影響極大,以至於北魏、交阯等國僧人紛紛慕名前來,如北魏釋曇準“承齊竟陵王廣延勝道,盛興講説,遂南渡,止湘宫寺”(68)《續高僧傳》卷六《梁揚都湘宫寺釋曇準傳》,第196頁。;交阯僧人釋道禪“聞齊竟陵王大開禪律,盛張講肆,千里引駕,同造金陵,皆是四海標領,人雄道傑。禪傳芳借甚,通夜不寐,思參勝集,簉奉真詮。”(69)《續高僧傳》卷二二《明律·梁鍾山雲居寺釋道禪傳》,第820頁。可見當時講席之盛况。因爲講席的規模甚大、參與者衆多,故而蕭子良一方面命其故佐徐孝嗣與國子祭酒何胤掌知齋講及衆僧事(70)《南齊書》卷四四《徐孝嗣傳》載:“爲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虜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竟陵王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廬江何胤掌知齋講及衆僧。”第858頁。據《梁書》卷五一《處士·何胤傳》,何胤曾任蕭子良司徒右長史(第735頁),則何胤亦爲子良故佐。,一方面委冶城寺釋智秀掌“選諸名學”以參加“西邸義集”等事宜(71)《續高僧傳》卷五《梁楊都宣武寺沙門釋法寵傳六》,第151頁。,因“競者尤多”,所以主事的釋智秀多“先悦後拒”,因而遭到宣武寺釋法寵的嘲諷。
除了延請僧尼發講外,蕭子良也會參與甚至親自發講。《廣弘明集》卷一九收沈約所撰《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竟陵王解講疏》《又竟陵王解講疏》三篇(72)《廣弘明集法義篇總録》載三篇之題分别爲“齊沈約《爲竟陵王發講疏並頌》”、齊沈約《爲竟陵王解講疏二首》,似更符合當時擬題習慣,《廣弘明集》卷一八,《大正藏》第52册,第221頁中。。據《齊竟陵王發講疏》,這次發講的地點是法雲寺,從文中“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與文末“自法主已降,暨於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73)《廣弘明集》卷一九,《大正藏》第52册,第232頁中。高麗初雕、再雕刻、金藏均作“法主”,宫、宋、元、明作“法王”,當以“法主”爲是。參陳慶元《沈約集校箋》,第244—245頁。來看,蕭子良應爲法主,雖未必一定是主講之人,但應該會參與講經之後的論議。《又竟陵王解講疏》中有“仰惟先后,禀靈娥德”一語,鈴木虎雄據以考訂這兩篇《解講疏》主要是爲其母裴氏(建元四年四月後蕭賾被追尊爲皇后)追福,而《發講疏》則寫於永明元年二月(74)[日]鈴木虎雄:《沈約年譜》,馬導源譯,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8—19頁;曹道衡、劉躍進《南北朝文學編年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240頁)與林家驪《沈約事蹟詩文繫年》(《沈約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50頁)只均將《發講疏》繫於永明元年正月,於兩篇《解講疏》則未論及。。似乎未注意到“發講疏”與“解講疏”乃是一個講經法會的完整環節,而講經一般會持續數天,解講之後還會舉行法會,所以《發講疏》與《解講疏》並非作於一日,而是相隔數日(75)《永陽王解講疏》即載:“菩薩戒弟子陳静智稽首和南……謹於今月十三日,解講功德,仰設法會。并度人出家。……奉造靈儀,即日鎔鑄,用斯福善,上資清廟聖靈。”(隋)灌頂:《國清百録》卷二,《大正藏》第46册,第800頁中。此點蒙上海師範大學曹凌兄告示,謹致謝。。
另,《蕭子良法集録》中有《西州法雲小莊嚴普弘寺講》并《述羊常弘廣齋》共卷、《抄成實論序》并《上定林講》共卷、《會稽荆雍江郢講記》一卷、《講净住記》一卷、《開優婆塞經題》一卷、《布薩》并《天保講》一卷。其中《會稽荆雍江郢講記》,筆者曾考乃蕭子良請當時名僧出都講法,故其講師均非子良。(76)拙文《僧祐〈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録〉考論》,《國學研究》第41卷,2019年。《西州法雲小莊嚴普弘寺講》《上定林寺講》《天保講》,也均爲蕭子良主導的發講,但並不能確定講者是蕭子良本人還是他延請的高僧。而《講净住記》與《開優婆塞經題》,因與蕭子良所撰二十卷《净住子》直接有關,故其主講應是蕭子良本人;至於發講的地點,則很有可能是在西邸的某所寺院。
不管發講還是解講,或者解講後的布施、捨身、發願,乃至造像(77)蕭子良還有造像活動,《廣弘明集》卷一六有《齊竟陵王題佛光文》,其文“皇齊之四年日子,敬制釋迦像一軀”,乃是爲蕭道成追福而造釋迦像一軀。另據《出三藏記集》卷一二《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録·雜圖像集》有《宋明帝齊文宣造行像八部鬼神記》《佛牙并齊文宣王造七寶臺金藏記》,知蕭子良還曾造行像八部鬼神與七寶臺金藏,而後者乃是爲供養佛牙。、舉行龍華會等法事活動,都會舉行相應的齋會。而從以上討論的講經活動看,蕭子良舉行齋會的次數甚多,這也與《南齊書·蕭子良傳》所載相合:蕭子良“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78)《南齊書》卷四《蕭子良傳》,第700頁。湯用彤先生早就注意到此條記載,認爲躬自爲衆僧賦食行水,也是一種捨身。(79)湯用彤:《漢魏兩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17頁。另這裏的“邸園”值得注意,此應該是西邸中的後花園,但邸園顯然不止是蕭子良與西邸文士們遊玩賞景、賦詩唱和之地,也是重要的宗教活動空間。《廣弘明集》卷三載王融所作《棲玄寺聽講畢遊邸園共七韻應司徒教》:
道勝業兹遠,心閑地能隙。桂燎鬱初裁,蘭墀坦將闢。虚檐對長嶼,高軒臨廣液。芳草列成行,嘉樹紛如積。流風轉還逕,清烟泛喬石。日汩山照紅,松映水華碧。暢哉人外賞,遲遲春將夕。(80)《廣弘明集》卷三,《大正藏》第52册,第352頁下。
從題目“應司徒教”來看,這首詩顯然是王融應司徒蕭子良之命所作。蕭子良携帶王融等西邸文士在棲玄寺聽講,結束後遊西邸後園,見山間美景、園中春色(從“遲遲春將夕”可知此詩作於暮春時節),因命王融賦詩,參與賦詩應不止王融一人,只是其他人的詩文無存。
蕭子良另有《遊後園詩》:“托性本禽魚,棲情閑物外。蘿徑轉連綿,松軒方杳藹。丘壑每淹留,風雲多賞會。”(81)《藝文類聚》卷六五, 第1161頁。“轉”、“方”兩字恰到好處,可以清晰看到詩人對季候初變的切身體悟,詩作於初夏無疑。又據《梁書·柳惲傳》:“(惲)幼從之(嵇元榮、羊蓋)學(彈琴),特窮其妙。齊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爲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晋相謝安鳴琴在側,以授惲,惲彈爲雅弄。”(82)《梁書》卷二一《柳惲傳》,第331頁。可知蕭子良西邸有後園,他常與諸文士、名僧遊賞、唱和賦詩。由這兩首詩可知後園景色甚爲秀美、别致,固是文士賞會的好去處。《謝朓集》中有《遊後園賦》,題下注云“奉隨王教作”。故此後園或荆州官邸後園,《賦》又云“追夏德之方暮,望秋清之始飆”(83)(南齊)謝朓著,曹融南校注集説:《謝宣城集校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7頁。,作於夏末無疑。可見二人之詩賦寫作時地均不同,故謝朓《遊後園賦》與子良《遊後園詩》恐非同題之作。
四、 邸園、邸寺與古齋、書齋:蕭子良西邸文士的活動空間
邸園與邸寺之外,蕭子良還在西邸建有古齋、書齋與士林館,這些都是他與西邸文士重要的活動場所。《南齊書·蕭子良傳》載子良“敦義好古”,“于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物以充之”(84)《南齊書》卷四《蕭子良傳》,第771頁。。後蕭子良爲通著名徵士何點,即贈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85)《南齊書》卷五四《高逸·何點傳》,第1034頁。《蕭子良行狀》亦載此事,謂“贈以古人之服”,《新校訂六家注文選》卷六,第3918頁。。前文已述,蕭子良在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86)《南齊書》卷四《蕭子良傳》,第776頁。,如此大的工作量,顯然需要爲這些文士提供一個抄撰圖書的場所,且既曰抄五經、百家之書而成千卷之書,則所抄之書更不止千卷(87)當時抄書乃節抄,參蔡丹君:《南北朝“抄撰學士”考》,《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6輯,2014年。,西邸須有這麽多藏書(即便是借書抄撰,也需要有藏書之處),據此可知西邸當有藏書、抄書之書房。
蕭子良對抄撰圖書一事頗爲重視,命其司徒右長史陸慧曉參知其事(88)《南齊書》卷四六《陸慧曉傳》,第892頁。,在抄書的閑暇之餘,蕭子良還會命沈約、王融等人賦詩文並同題唱和。《初學記》卷一二有梁沈約《奉和竟陵王抄書詩》,此詩抬頭即謂“教微因弛轡,推峻屬貞期”(89)(唐)徐堅等:《初學記》卷一二《職官部下·秘書監第九》,第296頁。,可知沈約此詩乃是奉竟陵王蕭子良所作;而詩既題曰“奉和”,則蕭子良本人也有《抄書詩》。《藝文類聚》亦有王融《抄衆書應司徒教詩》:“説禮固多才,惇詩信爲善。巖笥發仙華,金縢開碧篆。”亦爲五言詩,惜只存兩韻。僅從現存兩句韻脚來看,很難斷定王融此詩與沈詩爲同題唱和之作。如果王融與沈約兩首抄書詩非同題唱和,就説明蕭子良命僚佐抄書賦詩,就至少有兩次以上。除了抄書,蕭子良還命人編撰書,如命王僧孺撰衆書,命沈約撰寫《高士傳》(90)《藝文類聚》卷五五有梁王僧孺《謝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啓》,第989頁;卷三七有沈約《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第665—666頁。。
提到抄書,這裏稍微提一下蕭子良的書法,日本京都毗沙門堂藏有鐮倉寫本《篆隸文體》,題下有“侍中司徒竟陵王臣蕭子良序”,國内外學者對此卷舊鈔本頗爲關注(91)[日]山田孝雄:《典籍雜考》,東京:寶文館,1956年,第68頁;(日)阿噪哲次:《蕭子良〈篆隸文體〉寫卷の研究》,高田時雄編《中國語史の資料と方法》,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4年,第2頁。饒宗頤:《張彦遠及其書法理論》,莫家良編《書海觀瀾——中國書法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文物館出版社,1998年,第16頁。張天弓:《論蕭子良〈篆隸文體〉日本鐮倉鈔本》,《張天弓先唐書學考辨文集》,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9年。。近來,童嶺重新討論此卷鈔本,考訂此書作於永明三年至十一年(92)童嶺:《京都毗沙門堂藏蕭子良〈篆隸文體〉舊鈔本考——兼論南齊建康皇室學問的構成》,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1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5月。。而根據序中所題蕭子良之結銜,此時間似不妥。蕭子良永明五年正月戊子(二日)方正位司徒,此前分别以護軍將軍、車騎將軍兼司徒;且永明十年正月戊午(一日)蕭子良領尚書令,後改領中書監,五月又領揚州刺史。故這一結銜顯然在此之前,而此書應寫於永明五年至九年間,這就意味此書極有可能作於西邸。蕭子良在序中謂“慮夫後生不廣文習,今搜校秘府,採索民間,所得之書,六文之外有二十有三體。又博尋史傳,傍搜子集,其在爲書,悉無遺算。”則爲撰此書,蕭子良還曾搜集秘府與民間的相關書帖,亦頗有總結古今書體之意。
古齋、書齋之外,蕭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館,使工圖其像,(王)亮亦預焉”(93)《梁書》卷一六《王亮傳》,第267頁。。除了圖才俊、時賢之像,蕭子良還圖先賢之像,事見任昉《竟陵文宣王行狀》(下文簡稱《蕭子良行狀》):
山宇初構,超然獨往,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遊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94)《新校訂六家注文選》卷六任彦昇《竟陵文宣王行狀》,第3919—3920頁。
除了先賢像,還圖有列女之像,因有人建議而删去,任昉既並未交代圖先賢像的具體地方,所以並不清楚是西邸的書房、古齋,還是普弘寺等邸寺。據《高僧傳·釋寶亮傳》,蕭子良還“圖其(釋寶亮)形象於普弘寺”,蕭子良請寶亮爲法匠,寶亮後移駐靈味寺,此前應駐錫在普弘寺。在此期間蕭子良“接足恭禮,結菩提四部因緣”(95)《高僧傳》卷八《梁京師靈味寺釋寶亮》,第337頁。,故而蕭子良纔會在普弘寺圖其形象,而該寺所畫的高僧畫像應當並非寶亮一人,應該還有其他高僧。據此,《蕭子良行狀》所謂的“圖之軒牖”之地或爲普弘寺。此外,任昉只是説“匹婦”亦取,但並未明確交代究竟是哪一類女性。而至宋釋道誠編集《釋氏要覽》,就明確説“昔者南齊竟陵文宣王圖先賢形貌於書房壁,俾若神對,其中有烈女之像。時有客曰:‘君畫烈女,似好色不好德也。’文宣遂削去謝之。”(96)(宋)釋道誠:《釋氏要覽》卷二,《大正藏》第54卷,第280頁中。地點從比較模糊的“軒牖”明確變成了“書齋壁”,女性也由“匹婦”也成了“烈女”。對比兩處記載,釋道誠的文字其實多改自《蕭子良行狀》。多出的兩處内容其實也並不甚可靠,恐怕是釋道誠自己增改,而從匹婦到烈女的轉變,也反映了宋以後時代風氣的變化。
以上從蕭子良西邸的選址原因切入,重新討論蕭子良與西邸文士在西邸及其周圍各類場所開展的各類活動。蕭子良之所以在鷄籠山立西邸,不僅因爲其山距宫城與西州較近,且有山水之美,更重要的是鷄籠山及其周圍集中排列了不少寺院以及劉宋元嘉中所立儒、玄、史、文四學館及其舊址,附近還有東晋元、明、成、哀四位皇帝之陵。而且,在蕭子良之前,宋文帝劉義隆即爲其愛子建平王劉宏在鷄籠山立第。再加上齊高帝蕭道成及其兄曾在鷄籠山從雷次宗受業,這恐怕也是蕭子良選擇鷄籠山的重要原因。永明五年蕭子良移住西邸後,由於蕭子良積極弘護佛法,西邸遂成爲當時最重要的佛教活動中心之一。西邸中既有普弘寺等邸寺以及内堂、佛堂等道場,又有鷄籠山中及其附近的邸山寺、棲玄寺、耆闍寺等寺。這些寺院與道場,既是蕭子良召集高僧講經、齋會、捨身、發願之地,也是不少西邸文士的聽講之所。
西邸之中還有後園,時人亦稱之爲“邸園”,不僅是賞景遊玩、賦詩唱和之處,也是齋會的重要場所,王融所作《棲玄寺聽講畢遊邸園應司徒教》反映的就是蕭子良與西邸文士某天的日常生活:赴棲玄寺聽講——講畢遊邸園——在邸園賦詩唱和,既有聽僧人講法等宗教生活,也有詩文唱和等日常生活。而類似聽講等活動,在當時應該頗爲頻繁。當然,蕭子良與西邸文士的活動,並不限於此,他們還會在西邸的古齋與書齋之中抄經、抄撰衆書,而抄書之餘也會賦詩唱和等。此前學者雖然都關注到西邸作爲蕭子良與西邸文士的重要活動空間,但並没有注意到西邸及其周圍竟有如此豐富的活動空間,活動空間的拓展,在西邸文學中當然也會有所體現。
與建康東郊相比,建康西郊在空間大小、自然景觀與人文宗教景觀等資源方面都遠遠不及(97)關於建康的東郊,可參魏斌:《南朝建康的東郊》,《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3期;拙文《製作哀榮:南朝僧尼碑志之興起》,待刊。。衹是距離宫城較近,即距絶對的政治中心更近,更方便蕭子良與建康内外的僧尼以及皇室、權貴、文士等人接觸。加上竟陵王蕭子良居“不疑之地”,在建元、永明時期政治地位不斷上升(98)關於蕭子良開西邸之緣起及其意義,可參拙文《蕭子良西邸“文學”集團的形成——從政治與職官制度的視角出發》,《學術研究》2019年5期。。故而位於建康西郊的西邸,依托司徒府和西邸及其周圍寺院,在永明時期成爲重要的佛教中心、政治中心,可謂盛極一時。然而,一旦蕭子良因政治鬥争失敗而去世,西邸的佛教中心、政治中心之地位不再,西邸文士也隨之四散,其作爲重要活動空間的西邸便失去其意義。即便如此,在梁陳時期,西邸仍然是許多僧尼與文士懷念的對象,而西邸也逐漸成爲一個重要的文化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