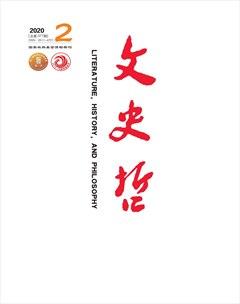受之以荀 纠之以孟
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
编者按:“孟荀二分”可谓传统儒学的基本格局;相分自然相争。作为当代儒学学术之近源,宋明儒学之主流一方面奉孟学(性善论、自律、内在论)为正统,另一方面斥荀学(性恶论、他律、外在论)为异端,极力强调孟、荀在人性论等方面的重大分歧。流波所及,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继续坚持上述判分,甚而在宋明儒学内部进一步严判正宗与别子,以至朱熹等宋明主流儒者思想中的“他律”因素无处遁形。但跳出宋明传统及其当代余绪,现当代的学术史研究者们则越来越倾向于将孟、荀等量齐观,并进而触及到了一个极具理论雄心与学术史抱负的重大课题:能否找到坚实的学理根基“统合孟荀”?进入21世纪以来,直接或间接涉及“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的学术探讨,在汉语儒学研究界持续激荡。其中,李泽厚先生于2017年抛出的“举孟旗,行荀实”宏论,再度挑动了学界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关于孟荀关系的新一轮研讨热潮。大而言之,“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事关“四书与五经关系之重估”“儒家道统再定义”“天人关系重思考”“政治与道德关系再厘定”“古今中西关系再协调”等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有鉴于此,本刊特推出郭沂、刘悦笛、梁涛三位先生的一组笔谈,冀望推动学界进一步聚焦并深化对“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课题的探讨。
关键词:儒学重建;天人统与人天统;心统情性;兼祧孟荀;从尊孟抑荀到同尊孟荀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专家 山东曲阜273165)
儒学从来都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从历史上看,儒学的发展,有时候是为了回应社会现实的挑战,如先秦原始儒学是为了回应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动而创建起来的,而汉代新儒学则是为了回应秦汉一统的新局势而提出的;有时候是为了回应外来文化的挑战,如宋明新儒学就是为了回应佛教的挑战而重建的。然而,当代儒学的发展,既面临着社会现实的挑战,即近代以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挑战,这就是西方文化之冲击。当然,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由西方文化之冲击而造成的,因而这两种挑战是交织在一起的。本文试图从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着手,来探讨儒学的当代重建的问题。
一
就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而言,我以为儒学的当代重建,面临两项重要任务:一是接受、吸纳西方现代性,从而实现现代转型,以回应现代化的挑战;二是挺立人的主体价值,从而纠正、修复现代化的缺陷,以解决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问题。
所谓西方现代性,主要是新文化运动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现在一般表述为民主政治和知识论。接受、吸纳这些现代性,一直就是现代新儒学的目标,牟宗三先生提出的“三统并建”、“内圣开出新外王”等命题,即为此而设。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近年来儒学界内部出现了一股拒斥上述这些西方现代价值的潮流,我期期以为不可,认为这不但不能维护儒家的尊严,对儒学的当代发展而言,也是十分有害的。道理很简单,尽管这些西方现代价值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合理性,更是显而易见的,正好可以弥补儒学之不足,其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不是偶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着几百年来的世界潮流。借用孙中山先生话说:“世界潮流,浩浩蕩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儒学如果不能顺应这一潮流,就会故步自封,从而失去生机。
应该如何接受、吸纳西方现代性呢?鉴于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和宋明时期的儒学重建极其相似,诸如都要应对外来文化的严峻挑战和传统文化的严重失落等问题,因此,或许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启示。
在我看来,宋明时期的儒学重建大约经历了三个境界。第一境界为“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程颐《明道先生行状》)。此境界展现了宋明儒家充分学习、消化和吸收各种学说尤其道家、佛家的心路。第二境界为“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程颐《明道先生行状》)。这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归宗于六经,二是从儒家传统中挖掘有效的资源。第三境界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外书》十二)这意味着在前两种境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思想和新哲学。
依此,儒学的当代重建,也将经历类似的三个境界:首先是充分学习、消化和吸收西学,第二是深入挖掘儒家传统中现代性的资源,第三是建构新的哲学体系。
如果说宋明儒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佛教心性论,其使命是吸纳佛教心性论,并发扬光大儒家传统中的心性论资源,从而在此基础上重建儒家心性论的话,那么,当代儒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作为现代性之基本内容的民主政治与知识论,其使命是吸纳西方民主思想与知识论,并发扬光大儒家传统中的民主思想和知识论资源,从而在此基础上重建儒家民主思想和知识论。
问题是,在儒家传统中,是否存在民主思想和知识论的资源呢?对此,人们一般会持否定态度。笔者却以为,早在两千多年前,起源于不同地区的三个轴心文明已经对人和社会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也埋下了各种各样思想的种子。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一俟条件具备,其中某些思想的种子就会萌生、发芽、成长。作为中国轴心文明的代表性学派,先秦时期的儒学大师们,已经为我们埋下了民主思想和知识论的种子了。
笔者认为,轴心文明时代儒家民主思想和知识论的种子主要存在于荀子所代表的传统中。充分挖掘这种宝贵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型,从而有效地回应现代化的挑战。因而,我们应该像宋明新儒学借助于思孟心性论来接受、吸纳佛教心性论那样,借助于荀子的民主思想和知识论资源来接受、吸纳西方现代民主思想。这种儒学当代重建的路径,我称之为“受之以荀”。
不过,经过数百年的迅猛发展,现代化的弊端和缺陷也日益彰显,并引起人们的忧虑,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因之而起。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评,主要在于由现代化所导致的精神失落、价值扭曲、人为物役、环境恶化、核弹危机等方面。因此,挺立人的主体价值,从而纠正、修复现代化的缺陷,以解决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问题,构成了儒学当代重建的另一任务。
如何医治这些现代病呢?我认为,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原始儒学的另一个传统,也就是孟子所代表的传统,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良药。这种儒学当代重建的路径,我称之为“纠之以孟”。
二
不过,最早明确提出道统论而成为理学先驱的韩愈早有言:“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昌黎全集》卷十一)自此以后,荀学被排除在道统之外,成为儒学中的异端。如果真是这样,荀学自然难以承担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以重建儒学的重任。但事实远非如此!
让我们先来看什么是道和道统。在儒家思想中,道为人当行之道,即人道。此道有两层含义。一是客观之道,二是观念之道,即由往圣先贤认识客观之道所形成的一套观念,而这套观念又表现为一套概念系统和行为准则。按照荀子的说法:“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人之所以道”,是说人们用来遵循的道,即客观之道。“君子所道也”,是为君子所言谈的道,即用语词表达的道,也就是观念之道。因此,道为各种道德范畴之总称,也就是说,各种道德范畴都属于道。如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以仁、智、勇为道;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以忠、恕为道;子思说:“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以五种人伦为道;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以孝弟为道;荀子说:“道也者,何也?礼义、辞让、忠信是也”(《荀子·强国》),以礼义、辞让、忠信为道。这就是说,所有这一切,莫不是对客观之道的发现,莫不属于道的范畴。客观之道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藏,需要求道者去不断地挖掘、发现和弘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因此,道统之道,乃观念之道。所谓道统,就是往圣先贤求道、弘道的足迹。
在儒家看来,人道乃天道的体现,因而观念之道来自对天人之际的追究。既然如此,那么既可自上而下地“推天道以明人事”,又可自下而上地“究人事以得天道”,这是往圣先贤求道、弘道的两种基本路径。由此,道呈两统,由前一种路径所形成的传统可称为“天人统”,由后一种路径所形成的传统可谓之“人天统”。
道之两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祝、史二职。祝和史可谓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祝与天、与神打交道,其思维方式是“推天道以明人事”,所以属于天人统。史官和人打交道,其思维方式是“究人事以得天道”,所以属于人天统。在六经中,《易》代表祝的传统,其究天人之际的主要方式为“以天道而切人事”或“推天道以明人事”,属于天人道统;《诗》、《书》、《礼》、《乐》、《春秋》代表史的传统,其究天人之际的主要方式为“以人事而协天道”或“究人事以得天道”,属于人天道统。孔子上承夏商周文明之精华,下开两千年思想之正统,无疑是道统传承的枢纽性人物。在早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主要继承了《诗》《书》《礼》《乐》之人天道统。自“晚而喜《易》”,孔子又将重点转向继承和发扬《易》之天人道统。进入战国,儒家开始分化为两系。一系承《诗》《书》《礼》《乐》《春秋》之人天统和孔子早期思想,本之以圣人之教化,从而论性情之原,礼乐之生,可谓之教本派。此派创自公孙尼子,继之以《性自命出》《内业》,而集成于荀子。另一系承《易》之天人道统,融合孔子中晚期之思想,本之以天命之善性,从而论情心之变,教化之功,可谓之性本派。此派创自子思,而集成于孟子。
由此可见,不管是孟子,还是荀子,不但皆得孔子之真传,而且皆承孔子之前之古老传统,都是道统的继承者、弘扬者和集大成者,在道统传承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孟学和荀学,堪称儒学史上的两个典范。
既然如此,自韩愈至宋明儒家为什么厚此薄彼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学术修养,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隋唐时期,佛教取代了儒学独尊的地位,成为显学。那些有志于复兴儒学的学者明白,佛教是靠心性论征服中国的,而在传统儒学中,具有比较丰富的心性论资源,可以开发出来与佛教心性论相抗衡的,正是思孟学派,即我所说的天人统。所以,挺立思孟,提出道统学说,正是为了满足当时的现实需要。
三
然物换星移,时过境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已非佛教心性论,而是来自西方民主思想和知识论,因而回应挑战的武器也应该由天人统中那种心性学说转变成道之另统,也就是以荀学为代表的人天统所蕴含的民主思想和知识论了。
为什么说荀学蕴含着民主思想的种子,可以成为接受、吸纳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桥梁呢?换言之,“受之以荀”何以可能?
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往往有其人性基础,民主思想也不例外。它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承认人是有缺陷的,所以需要各种规范、制度乃至法律的制约,而认识人性的缺陷,也正是荀子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有关荀子性恶的学说,人们耳熟能详,兹引《荀子·性恶》篇首段足以说明问题:“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既然如此,如何才能建设一个健全的、和谐的社会呢?荀子接着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师法”中的“师”为师长,“法”当指下文的“法度”。看来,控制人性之恶的途径有二,一是师法的教化,二是礼义的引导。前者相当于现在的国民教育,后者相当于制度建设。礼是一种外在规定,其作用相当于现代法制,可以说是一种软性的制度,在中国古代,起到了宪法的作用。不过“法度”的含义较广,当包含道德、礼制、法制等各种规则。
然而,师法和礼义又来自何处呢?荀子认为:“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荀子·性恶》)就是说,礼义、法度等皆由圣人所制定。这一判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应该来自历史的经验。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周公制礼作乐”了;在西方历史上,美国国父们讨论签署《独立宣言》,早已传为佳话。
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平等。就此而言,虽然儒家不主张权利平等,但人性和人格的平等,却是为大多是儒家学者所坚持的。在这方面,荀子多有论述。如:“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荀子·荣辱》);“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正因如此,荀子主张“涂之人可以为禹”:“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
更难能可贵的是,荀子认为,通过个人的努力和修养的提升,人的社会地位也是可以改变的:“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
至于荀子的科学观和知识论思想,更是显而易见的。在那个宗教和迷信思想流行的时代,他断言:“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天论》)正因如此,对于一些怪异现象,荀子能作出理性的解释,如:“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荀子·天论》)
在荀子看来,客观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荀子·天论》))因而,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而人也具备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徧也。”(《荀子·解蔽》)那么,“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荀子·解蔽》)由此,荀子对心的认识能力、人的精神世界,乃是名实关系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如此等等,都体现了荀子的科学精神和知识论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荀子的民主思想和知识论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和知识论既有相通之处,又有相异之处。但其相异之处构不成我们否定其为民主思想和知识论的理由,这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思孟心性论不同于佛教心性论从而否定其心性论的性质一样。这种差异意味着两者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就像思孟与佛教心性论的差异意味着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一样。因此,荀子的民主思想和知识论可以成为儒学接受、吸收现代西方民主思想和知识论的桥梁,就像当年宋明理学家以思孟心性论为桥梁去接受和吸收佛教心性论一样。
四
与荀子相反,孟子主张人性是善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荀关于人性的看法看起来针锋相对,势不两立。那么孰是孰非呢?其实,他们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如果说荀子发现了人性中消极的、丑恶的一面的话,孟子则发现了人性中积极的、美善的一面。
孟荀的人性论都是中国人性论长期发展的结果。根据笔者的考察,中国古人至迟在殷周之际就开始探索人性的奥秘了。不过,当时人们对性的认识主要还限于经验层面,即血气之性,也就是后儒所说的气质之性。在各种血气之性中,与道德关系最密切的,当数情感,因而作为情感的性尤其受到重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性即情也。此种性,也被称为“情性”。就情性对道德的作用而言,当有积极和消极之分。
殷周之际的人文主义思潮,形成于周初政治和文化精英对夏、商两代覆灭的反省,因而从逻辑上推测,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应该的消极的、可能导致恶的性。在《尚书·召诰》中,我们读到:“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孔安国传:“和比殷周之臣,时节其性,令不失中,则道化惟日其行。”(《尚书正义·召诰》)从孔传看,所谓“节性”,就是节制情欲,类似于《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思路。《尚书·西伯戡黎》亦云:“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郑玄注曰:“王逆乱阴阳,不度天性,傲狠明德,不修教法。”对此,阮元进一步解释道:“‘度性与‘节性同意,言节度之也。”(《揅经室集·性命古训》)既然这种性需要节制,那么它一定是消极的、可能导致恶的性。这是荀子人性论之渊源。
当然,积极的、能够导致善的性也没有受到忽视,这主要表现在“厚性”之说上。《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谏周穆王曰:“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用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何为“厚性”?依韦昭注:“性,情性也。” 至于“厚”,则与《国语·晋语一》“彼得其情以厚其欲,从其恶心,必败国且深乱”中的“厚”字同义,正如韦昭所注:“厚,益也。” 在这里,“厚其性”指促进、培育、发扬性情。在“彼得其情以厚其欲,从其恶心,必败国且深乱”中,“厚其欲”是反道德的,故此“欲”是消极的、能够导致恶的性,而在“懋正其德而厚其性”一语中,“厚其性”是高扬道德的,故此“性”无疑为积极的、能够导致善的性。这是孟子人性论之滥觞。
可见,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情性既有积极的、可以导致善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可以导致恶的一面,孟荀不过分别继承和弘扬了这两个传统而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和荀子一样,孟子的人性论也就情性立论。孟子的性为“恻隐之心”等四端,而“恻隐”正是一种情感体验。因此,和荀子的人性论一样,孟子的人性论也属于气质之性,而后儒以孟子人性论为义理之性之典范的成见,是需要重新考量的。
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恶从何来?孟子指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原来罪魁祸首是“耳目之官”,即情欲。“耳目”等感官没有“思”的能力,故为外物所遮蔽。外物陈陈相因,最终导致堕落。孟子进一步分析道:“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 朱子注云:“贱而小者,口腹也;贵而大者,心志也。”在孟子看来,既然“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那么对于人人所固有的“四端”,就不必外求,也不必借助任何手段,只需当下体认,便可获得。这种体认,孟子谓之“思”:“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这里的“人人有贵于己者”指的是什么呢?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一方面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一方面说“仁义礼智……弗思耳矣”,可见“思”的对象,正是仁义礼智这些本心或善端,即“四端”。至于“思”的主体,当然是“心”:“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思则得之”的“之”,当然也是“四端”。
从这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出孟子对西周以来人性论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他一方面将那种消极的、可以导致恶的情性归结为耳目之欲,名之为“小体”,另一方面将那种积极的、可以导致善的情性归结为心之思,称之曰“大体”。我们也不难发现,孟荀对恶之来源的看法也是一致的,那就是耳目之欲,只是孟子不以之为性而已。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作为“耳目之官”的“小体”就是生理需要、物质享受,是人和动物共有的;而作为“心之官”的“大体”是精神寄托、价值诉求,是只有人才具有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
让我们把思路拉回今天。用孟子的观点来反观现代化,只能让我们感叹,现代化的种种弊病,都被两千多年的孟子不幸而言中!现代化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影响,最明显的是极大的物质享受,包括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但这一切,所满足的不过是孟子所说的“小体”而已。在这同时,现代化给我们带来了诸如精神失落、价值扭曲等等为后现代主义所诟病的种种问题。这个过程,不正是“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吗?不正是“以小害大”吗?不正是“养其小者”吗?
因此,如欲克服现代化的种种弊端,必须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告子上》)这反映在儒学重建上,就是“纠之以孟”,即用孟学来纠正已被扭曲的现代化。
原来,现代化和后现代这两种看起来势不两立的世界思潮,分别与孟子所讨论的两种人性是相对应的(用今天的眼光看,不管“大体”还是“小体”,皆为人性),现代化所满足的主要是“小体”,后现代所追求的则是“大体”。既然二者都有其人性基础,那么它们就都有其合理性,那种有你为我的思维方式是不可取的,因而承认并发挥其合理性,克服并抑制其弊病,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对于儒学的当代重建来说,这意味着“受之以荀”和“纠之以孟”是同时进行的,其结果是,统合孟荀,开出儒学的新境界、新时代!
[责任编辑 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