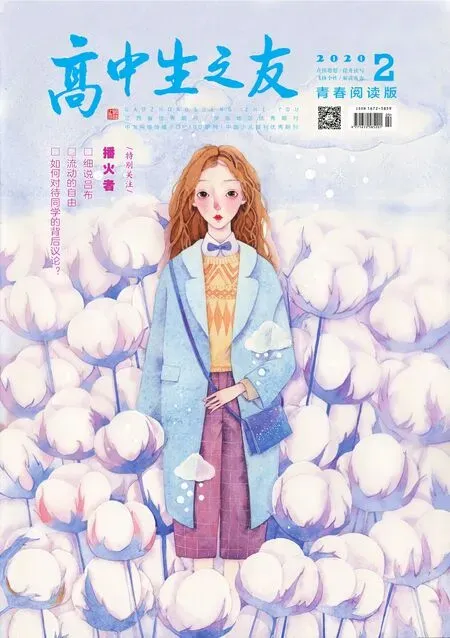亡国帝王,多少“离愁”
——聊聊李煜的《相见欢》
○卓 晖

本篇文章,我们来聊聊李煜的《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作品短短36 字,凄切婉转,哀感顽艳。后来,《相见欢》词牌因之衍生出《上西楼》《西楼子》《秋夜月》等别名,就像《念奴娇》又名《大江东去》,《一剪梅》又名《玉簟秋》一样。千古绝调的深远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一
此词是李煜降宋后所作。它不像“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车如流水马如龙”那样脍炙人口,却细致入微地反映了词人囚居汴京的日常情绪,比之其余经典,别具一番滋味。
南唐衰落起于昏聩的中主李璟,彼时朝廷党争剧烈,国内币制紊乱,赋税沉重,对外穷兵黩武,摒绝强援。等到其执政末年,把江北十四州割让给后周,南唐不过苟延残喘而已。后主继位,面对一个烂摊子,只能徒唤奈何。
李煜绝非庸懦之主,当国势日蹙之时,能维系南唐十五年不坠,实属不易。然而,他礼佛靡费内帑,不能取缔朋党,对社稷倾灭也要负责。所以,失国之后,他内心的悔恨定然强烈。
思忆故国,点检往事,无可奈何,既悔且恨,李煜怀着复杂的情愫,度过了生命最后两年多的时光。
二
鉴赏这首《相见欢》,须知其地其事,方能识其境其情。
明代李濂《汴京遗迹志》记载:“净慧院,在大梁门外西北,南唐主李煜归宋,赐第于此,煜卒后为寺。”大梁门即阊阖门,是内城通向外城的要路,朝臣一般住在外城。此文并未点明净慧院距离城门多少里,我们大可推知应在一里之内,从城头就能望见。
净慧院后改造为寺,唐五代的寺院建筑布局大体为“一殿二楼”,大殿居中,西北角为经楼,东北角为钟楼。李煜崇好佛法,北宋朝廷赐予他的宅第仿照佛寺修建,完全合理。
《相见欢》中提及“西楼”,结合李煜“独自莫凭栏”“小楼昨夜又东风”“高楼谁与上”等词句来看,我们能判断他应该长年累月蜗居西北经楼之上。
为何他不住在大殿,而住在经楼呢?笔者猜想,这是出于强迫。李煜被严格监视,宅前有老卒守门,他人非奉旨不得面见。由此推测,手无寸铁的昔日帝王起居于一隅小楼,一举一动正好方便窥探。
知道后主被软禁的地点,品读这首《相见欢》,也就更加明晰了。那么,让我们从头开始,细细品读吧!
上阕以“无言独上”起头,既然词人独自登楼,没有对话者,何以要点明“无言”呢?原来,这“无言”是说他的心事难以言喻。以此二字引领,全篇翻涌的情感竟归于默然,令人击节叹赏!
李煜既然居住在院落西北角的小楼,那么梧桐树必在偏东或偏南方位。细品词句,词人应是同时看见残月和梧桐,面朝东南。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梳理出词人的心理变化。
他在午夜之前回到西楼,登楼时默然无言,心情尚算平稳。不料,放眼看见东天如钩秋月、楼前深院梧桐,一派凄清冷寂,瞬间胸中生发连绵不绝的愁绪。
此月此树,为何让李煜感慨万千?因为残月既能照临汴京,就能照临金陵。因为梧桐树种在深院之中,就像李煜被软禁监视。因为他面朝东南,那正是眺望故国的方向。词人的一颗心,多希望向钟山、秦淮飞去,但他只能在这清秋好景时节,慨叹失去自由、虚耗生命。词中一个“锁”字,会不会让你陡觉悲凉,甚至触目惊心?
上阕至此,词人由景生情,胸中涌动着千言万语,又以极其凝练的文字倾注到下阕去了。
下阕的要点在于“离愁”。李煜借离愁类比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乍一看,不免失之孱弱;再一想,就知其精妙了。
古人念及离别的亲人、故旧、爱侣,远在天涯,关山难越,自是无奈;暌违既久,重逢无期,难免怨恨命运无常,世事播弄;回想往昔相聚,情深义重,又往往生出未能善待对方的悔意。
无可奈何,又恨又悔,是不是和前文解析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非常相似?
其实,在李煜囚汴的词作中,离愁并不鲜见。例如,《破阵子》说辞别宗庙,《望江南》忆南国春秋、旧游上苑,另一首《相见欢》惋惜“林花谢了春红”,更不用说《虞美人》之“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浪淘沙令》之“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字字句句无不浸透了亡国血泪的离怀别恨。
尤为紧要的是,这首《相见欢》用精妙绝伦的六个字直写离愁。“剪不断”,是言此情连绵不绝;“理还乱”,是言此情不堪疏解。也就是说,这首《相见欢》实则写出了李煜囚汴的素常心态:情绪持续低落,不时被特定的人、物、情境挑起一阵阵痛苦、凄恻,无法排遣。
在给金陵旧宫人的信中,他说:“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这一句痛语,与词作相参,你能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李煜的悲哀?
这种悲哀与离愁神似,却远比离愁广大深挚,已不能用言语贴切地表达。于是,全词的结句破空而至,力透纸背,“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李煜实则已将内心的苦楚表达得淋漓尽致了,此处却扭转一笔,并不说透。唯其不说透,才能与开头的“无言”巧妙呼应,构成完整的艺术结构,后人读之,才能体会那欲语泪先流的至情、默默无言的襟怀,词作的意味才能历经百世而悠悠不绝。
三
虽然我们常常将诗词并举,但诗与词存在明显的区别,区别在哪?
来个有趣的假设。假如把杜甫的《登高》、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都改成《鹧鸪天》词牌,将颈联分别写作“秋万里,客常悲,百年多病独登台”“家何在,云岭边,雪拥蓝关马不前”,两位先贤是不是要吹胡子瞪眼,戟指质问:“如此一改,诗风何在!”
没错,诗与词的区别正是在风格。诗可以气象万千,词却被粗略地分作婉约、豪放。为何如此?因为相对于诗,词是“通俗”的。它必须自然流畅,拒绝沉郁顿挫、奇崛险怪等语言,风格不免有趋同之嫌。所以,我们简直不可想象杜甫、韩愈会填出怎样的词作,却完全可以理解李白能够写下《忆秦娥》《菩萨蛮》这样的杰作。
李煜的词与太白的诗,都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周之琦用“天籁”形容李煜的词,此论深得我心。想象一下,你置身于山水之间,聆听松涛起伏,鸟鸣云端,溪泉幽咽,鱼跃澄潭,这些声音没有经过任何渲染雕琢,却能唤起你心中难以言喻的情感。
自然到完美,自然到直抵人心,这正是南唐后主笔下之妙处。
他写美人,“云一緺,玉一梭,淡淡衫儿薄薄罗”,用简练笔触勾勒,如云雾盘结的发髻上斜插着一支梭形玉簪,生动真切。
他写美景,“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队春”三字,乍一看,下笔随意了些,那岸边野生的桃树李树,怎么可能整整齐齐排作一队?细思之,李煜当时身为皇子,平日宴游欢乐,娇娃艳姬岂非排作一队队,在他面前歌舞?他将欣赏佳人的观感,代入桃红李白的景致,整个画面是否因之添了三分旖旎呢?这样的联想很任性直接,却很巧妙贴切,带有孩童的敏锐。
王国维说,后主“不失其赤子之心”。李煜的自然恰恰在于此,“赤子之心”带给他敏锐通透的天真之眼。用之写人状物,尚且如此明丽隽永,用之抒情,可真要感天动地了。
正是这天真之眼,让李煜用“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用“朱颜”“花月”“孤舟”“月明楼”“胭脂泪”和“雕栏玉砌”等看似纤弱的意象,承载了厚重的历史和痛苦的灵魂。
也正是这天真之眼,让他在囚居之时,依然遵从内心,不断唱出自己的痛与恨,最终被宋太宗鸩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