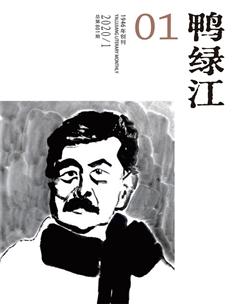孙犁晚年创作初探
吴嘉韵
摘要:20世纪70年代后复出的孙犁,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期:作品数量庞大,文体丰富多样,写作风格和面貌发生了极大转变。历史断裂与人生晚途成为孙犁晚年言说的主要冲动:历史断裂冲击了孙犁一贯秉持的理想化的道德和文化价值认同;人生晚途催发了孙犁对过往生命经验的体察与审视,二者构成了孙犁晚年写作的内在规约。
关键词:晚年孙犁;人性论;文学人生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创作空白期后,1976年孙犁重新执笔,开启了全新的创作历程。此时孙犁已经是63岁高龄,但至1995年宣布封笔前,他笔耕不辍,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作品结集约一百五十余万字,其中又以《芸斋小说》[1]、《乡里旧闻》和杂文的成就最为突出。
此一时期孙犁的写作风格和面貌发生了极大转变:不再潜心小说创作,作品产出多为杂文、书论等;而为数不多的小说也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虽保留了以往散文化的特色,但故事性进一步淡化,几乎只剩下对现实和对个人内心的白描,“荷花淀”的诗意无处可寻;在以杂文为代表的其他创作里,孙犁不再反复讴歌“美的极致”,而是对“丑”和“恶”进行猛烈抨击,追问构成种种错位和怪状的历史成因和文化根由,文风尖锐犀利,具有很强的战斗性。
时隔二十年再提笔,晚年孙犁的创作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转变,其言说的冲动到底源于何处,它又是如何影响孙犁晚年的写作风格和面貌的?笔者通过研究《芸斋小说》、《乡里旧闻》以及一些代表性的杂文,结合孙犁的生平遭际和通信自述,试图寻找问题的答案所在。
一、历史断裂:重提伦理
对于孙犁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道横亘在心坎上的裂痕,它在直接阻断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同时,也粗暴颠覆了这批知识分子对历史、现实的固有认知及想象。十年动荡,孙犁也未能免于狂风恶雨般的身心摧残:他曾被数次抄家,做过清洁工,蹲过牛棚,受过无数次“传讯”及盘问。
“芸斋小说”中大部分作品都与“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有关。它虽被孙犁定义为小说,但实际上和《乡里旧闻》一样,在文体上都介乎小说与散文之间,真假难辨。按孙犁的解释:“我晚年所作小说,多为真人真事……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 [2],他似乎是默认了《芸斋小说》中所记人事的真实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再去审视《芸斋小说》,其所揭示的人世间纷繁复杂、丑陋晦暗的现象就更触目惊心:《三马》中聪明伶俐的三马因没有遵循造反派的指示而被逼喝药自杀;《小D》中本为地痞流氓的小D却以造反者的身份一跃成为革命掌权者……孙犁由此发出诘问:历史和现实为何会黑白颠倒?我们该如何追责,向谁追责?
在后来的散文《转移》中,孙犁就这一问题的认识做过一次比较完整的表述:“十年动乱,大地震,是人性的大呈现,小人之用心,在于势利,多起自嫉妒,卑鄙阴毒,出人意表。平时闷闷,唯恐天下不乱。一遇机会,则乘国家之危,他人之不幸,刀砍斧劫,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3]孙犁认为,“文革”是部分道德沦丧之人利用政治空隙肆意妄为,引发原有社会道德秩序全面垮塌的结果,是人性的恶经由社会制度的漏洞得以肆意扩大所造成的灾难。无怪孙犁晚年作品中“诗化”意识不断淡化,转而代之的是对种种人性恶的不满和揭露。
如何遏抑人性中潜藏的恶意?深深留恋着传统农业文明的孙犁寄希望于建构一套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以确保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行:“大局已定,则应教养生息,以道德法制教化天下。” [4]
在《乡里旧闻》中,孙犁构建新伦理道德秩序的愿望表现得更为强烈。在这部描摹从晚清到文革的华北农民众生相的集子里,孙犁一改“荷花淀”时期对农民自尊自爱生活的赞美和颂扬,熟练老到地描写了一系列农业文明破败过程中苦苦挣扎的农民形象,提出了当失却由战争环境催生的家庭和爱国主义纽带的捆绑后,到底要如何改造农民劣性的问题。
孙犁认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本就是由伦理关系连结起来的小型社会,伦理是本位,勾连起了相互间的义务关系,成为有效约束农民劣性的外在机制,因而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应该由新的乡村社会伦理秩序来制约农民的行为选择。同时,作为“一种自然规律”[5]存在的“因果报应”,可以作为维护伦理机制运作的软性强制力存在,起到警示和约束作用,于是《乡里旧闻》中孙犁几乎通篇都使用“因果报应”来解释每个人物的下场和终局。孙犁甚至还指出这些下场和终局存在历史循环的可能,表达了对“传统痼疾集体无意识式循环” [6]导致悲剧重演的隐忧。
在孙犁创作这部集子的1979年至1987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工业文明快速发展,极大冲击了传统乡村文明秩序;商品经济催生了一系列不良社会风气;资本开始介入文学运作……這些显然都对执守儒家传统道德标准的孙犁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他在《乡里旧闻》中委婉地通过“因果报应”来对事件和人物进行品评和定性,对善与恶进行隐性的价值判断,也许不只是针对中国乡村,不只是为改造农民劣性,还有对扭转当前因商品经济复兴而激发的私欲横行、冷漠麻木的社会风气的希冀。
不过,孙犁所抱持的以“伦理”为核心的价值标准过于一元化和理想化,使他对“文革”的邪恶与疯狂难以释怀的同时,又使他被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新的社会运行法则抛弃,不得不面对继50年代被政治边缘化后,在文化上的再一次被边缘化。
二、人生晚途:消颓与顽抗
不可否认,生命晚途这一独特的个体经验使“新孙犁”有了更为敏感和多维的文学触觉,情感丰富多层又复杂深邃。正如孙犁自己所说:“晚年对世事体会深了,偶一触及,便有入木凿石之感”。[7]
(一) 消颓:垂垂老矣与精神失落
1992年,已近耄耋之年的孙犁用“残破”二字为自己的大半生做注:“我的一生,残破印象太多了,残破意识太浓了。大的如‘九·一八以后的国土山河的残破,战争年代的城市村庄的残破。‘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残破,道德残破。个人的故园残破,亲情残破,爱情残破……” [8]如果说关于战争年代和“文革”的残破之感非惟孙犁所有,它也可能是每个身处其时的良知尚存的国人的共感,那么个人生命之途的残破则无疑是独属于孙犁的个人性体验。亲友故旧的相继离去,难以理清的家事纠缠,垂暮之年的力不从心,永无休止的疾病折磨,这些都成为孙犁精神消颓的重要诱因,深刻影响了孙犁晚年创作的感情基调。
复出后的孙犁不再潜心小说创作,为数不多的“芸斋小说”也带有明显的自传体特征,再不复当年的热情和野心。孙犁将这种在小说创作中过多提及自身,“急迫地表现自我”的行为解释成是“行将就木的征象”[9]。回忆成了孙犁晚年小说、散文创作的母题,在满足了孙犁确认自我价值的情感需要的同时,也完成了作为作家的孙犁向读者、作为人的孙犁向世人进行自我说明的愿望。
有的怀旧温和有力,带着对未来的热切期盼,有的怀旧却尽显疲惫伤感,透出消沉无力之感,孙犁显然是后者。无论是《芸斋小说》还是《乡里旧闻》,虽然也偶有温情片刻,但总的基调还是相当悲凉凄苦的。意识到自己进入生命晚途的孙犁,正不得不去调整和适应这种不可逆转的改变。一个独行于暮途的老人成为孙犁对自我的重要体认,其间夹杂的心酸、无奈、自嘲、消沉等多重复杂的情绪自不必多言。而疾病缠身更进一步消磨了孙犁的斗志,加剧了孙犁对生命衰老的痛感,并影响着孙犁的许多判断与选择,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孙犁对主流文化的态度。
孙犁晚年的创作和青年时期的创作之间有一个共通联系,即对主流文化的若即若离。青年孙犁对生活中诗意的捕捉,对个人情感的过多展露原本与战时特定的意识形态不相符合,但他对人性美尤其是互助友爱之情的独到发现、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暗合了当时团结统一,谋求抗战胜利的时代号召。孙犁的个人步调幸运而又巧妙地与时代步调达成一致,因而得到了主流文化的接纳和褒扬。如果说四五十年代的孙犁是无意找到了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空地,得以与主流文化亢奋激扬的声音相附和,那么七八十年代的孙犁,则是清楚地认识到其“文学自我”与主流文化圈的不相融,加之其性格淡泊,不好争抢,于是主动选择退守一隅,对主流文化表现出更为明显的退避:固守自己的文学和人生理想,不轻易附和和跟随某些文化潮流或文学思潮。当然,孙犁的退避除了有晚年气力不继,无意争辩的原因,还有其本人对现时社会变化不理解和不适应的因素影响,而这种不理解和不适应造成了孙犁的不合群,引致了他更深的孤独。
(二)顽抗:全面自省与冷眼批评
已近古稀之年的孙犁对名利一事越发看淡。在回顾往昔时,他不顾惜自己的羽毛,也不担忧后人如何评说,以一种包容开阔的胸襟将自己的大半生大喇喇地铺展在阳光下,这种自觉、全面、近乎严酷的自省,成为了孙犁晚年写作的独到之处:“也许是他年龄越大、阅历越深、对人生感悟越透彻,他不再回避或忌讳什么了,因而也就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和本质以及他自身的真实和本质。”[10]孙犁对自己为人错漏之处的不讳言,是内心清白坦荡的反证,也是对人性美的一次回归。究其一生,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孙犁都在致力于推动“荷花淀”所指涉的文学理想和人生理想的实现。尽管这在表层意义上与文革后的现代化大潮相违背,但毕竟现实环境还是松泛不少,孙犁也不至于再像50年代那样因恐惧而失声,在表达上更义无反顾了。
孙犁对于名利及其他一切世俗欲念的看淡,在“荷花淀”时期已有迹可循,但晚年人生阅历的增加和对主流文化的主动避让,使得这种“看淡”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孙犁有意将自己“置身事外”,对“读者”和“市场”漠不关心,是以获得了跳脱出人情世故的桎梏,冷静打量现实的资格。仿若“局外人”的孙犁,开始了对文坛、对社会的冷眼式批评,文字也呈现出一种有意为之的“脱缰”感,无所顾忌,直抒己见,因而出现了早年作品所不具备的尖锐犀利的风格。
深觉一切人性恶都是由“私”和“利”勾连出来的孙犁,对商品经济引致人际关系的变化,对市场资本介入文坛有着诸多忧虑,对文人间或相互奉承或争名逐利的现象很是不满,他一再地把矛头指向诸多畸形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对文坛上的不良风气进行猛烈抨击:“现在有的人,就聪明多了。即使已经进入文艺圈的人,也多已弃文从商,或文商结合;或以文沽名,而后从政;或政余弄文,以邀名声。因而文场芜杂,士林斑驳……文艺便日渐商贾化、政客化、青皮化”……必须承认,商品经济的确令“利益”因素深刻介入了人际关系,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但它也并非如孙犁所言的一无是处,甚至要予以抵制,现实生活也并非全然是阴暗和冷酷,孙犁仅由这些负面现象出发来对商品经济社会予以全盘否定,明显有偏颇和过激之处,不过其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深沉的人文关怀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和承续。
这种多于杂文出现的蓬勃生气,与生命衰退的消沉形成鲜明对比,是孙犁晚年创作中不可忽略的一抹亮色。孙犁对文坛和社会现实的主动介入,于批判和评论中显示出的强烈愤慨,与因生命颓势无法挽回而产生的感伤情绪形成强烈反差,显示出了孙犁对抗生命晚途所附带一系列消极情绪的战斗姿态。晚年的孙犁,就在这种拉扯中时而消颓,时而奋起,直至1995年孫犁放弃对死亡的抵抗,变得极端绝望和厌世,全面断绝与外界的联系,才逐渐走向了虚无和幻灭的终局。
注释:
[1]孙犁晚年的小说创作较为分散,时间跨度长,但各自出版时均列在“芸斋小说”标题之下,1990年1月这些小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以《芸斋小说》为名结集出版。
[2]孙犁著. 耕堂文录十种 老荒集[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06. 第90页.
[3] 孙犁著. 如云集[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03. 第29页.
[4] 孙犁著. 耕堂文录十种 老荒集[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06. 第188页.
[5] 孙犁认为,因果报应不一定是迷信,而是一种自然规律。参见孙犁著.孙犁全集 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379页.
[6] 刘佳慧.《乡里旧闻》与孙犁的晚年写作[J].小说评论,2014(04):171-175.
[7] 孙犁著. 芸斋小说[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0.01. 第163页.
[8] 孙犁著. 曲终集[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5.11. 第37页
[9]孙犁著. 孙犁文集 4 理论[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10. 第614页
[10]刘慧英.“荷花淀”的清香和人生的劫难——“芸斋小说”浅读[J].当代作家评论,1993(03):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