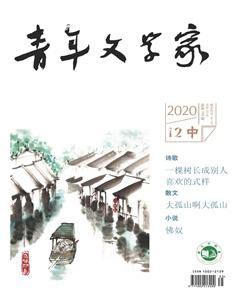写和重写、变与未变

摘 要:本文以汪曾祺跨时代改写作品中抽取原篇故事内容、改换题目进行重新创作的四组小说为研究对象,简要概括四组小说故事内容的变化和前后文本中相似情节的扩写、缩写现象,重点关注后期作品中增加的风俗描写;从人物形象的改变、后期作品叙述语言的简洁化倾向和前后文本之间的关联与变化出发,概括此类作品的改写特征;在此基础上,从其创作的选材、不同阶段人生经历对其创作心态的影响等方面探究其选择改写此类作品的原因;最后,总结汪曾祺跨时代改写作品的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跨时代改写
作者简介:张天(1997.6-),女,汉族,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指导老师:胡少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5-0-05
提到汪曾祺,读者熟悉他笔下的故乡、吃食和传统风俗;评论界关注其八十年代回归文坛后充满“和谐”、“温馨”和“烟火气”的作品,对其四十年代的创作关注较少,更鲜有人从整体出发研究其作品中的变化。但是,汪曾祺曾表示“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还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段”[1],希望研究者们不要孤立地看待他的作品,而从整体上把握他的写作。对研究者们来说,从汪曾祺完整的创作生涯出发进行研究,既可以体会其不同人生阶段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也可以完整感受其创作风格的形成过程和写作技巧的不断创新。汪曾祺曾在八九十年代对其四十年代的作品进行了改写,这些作品是从整体上研究其创作生涯的重要材料,我们可以从这些改写的作品中窥见汪曾祺创作上的变化。
一、汪曾祺跨时代换题改写小说概况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曾说:“沈从文是现代中国作家中唯一有改写习惯的一个。”[2]实际上,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也存在改写现象。其作品中的改写现象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对前人经典作品的改写、对自己作品的同题改写和抽取原篇故事内容,改换题目进行的重新创作。目前,对汪曾祺小说中改写现象的研究多以对比单篇作品前后文本间的改变为主,且关注前两类改写现象的研究者较多,专门论述跨时代换题改写作品中出现改写现象的较少。本文即以跨时代换题改写作品中出现的改写现象为研究对象,从它们的改写特征、改写原因和改写意义出发,论述汪曾祺改写作品中发生的变化和他在写作上的探索。根据笔者的统计,在汪曾祺全部的作品中,共有四组小说存在跨时代换题改写现象(详见表1.1)。
四组小说的故事内容都有一些变化。三版《异秉》的侧重点各不相同:《灯下》以白描手法描写众人晚饭后在保全堂闲聊的场景;1948年的《异秉》重在描写王二为搬店做的种种准备和底层人民的互相关心;1981年第二次重写《异秉》,主要讲述了王二勤劳致富的过程。《受戒》由《庙与僧》中讲述寺庙和尚们不拘礼法生活的单线索变为描写寺庙生活和小英子、明海两人美好朦胧感情的双线索。从《最响的炮仗》到《岁寒三友》,故事的主人公还是炮仗店老板,但汪曾祺把故事从无奈“嫁”女儿的悲剧改成了三位好友相互支撑苦中作乐的故事。1993年创作的《露水》则是从《邂逅》里“借”来了卖唱的一男一女,从对两人充满厌恶与嘲讽变为讲述两人相互扶持的温情故事。除了《露水》,其他三篇改写都把故事从单线结构发展为双线甚至三线结构。这种“多线作战”的形式,使故事内容更加丰富,也通过线索间的留白,产生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的效果。
此外,四组小说还存在对相似情节进行扩写和缩写的现象(详见表1.2和表1.3)。由表可知,汪曾祺在其后期创作的小说中增加了对故乡风俗的详细叙述,也补充叙述了一些前文本中未展开的故事情节;减少了大段抒情、叙述的文字,也删去了一些因故事主题改变而不再重要的情节。故事情节的删减和叙述文字的简洁化倾向都与汪曾祺不同时期创作心态的改变有关(后文将详细论述),这里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其后文本中增加的风俗描写。其后期改写的作品中都有一至两处对之前一笔带过风俗习惯的扩写。汪曾祺在改写时有意扩写与小说内容相关的风俗习惯,不仅是想向读者介绍现在可能已不存在的风俗、为作品增加特色,更因为在他看来,风俗意味着人情,写风俗也是写人。四十年代作品中作为点缀出现的风俗习惯,在八九十年代的小说中变成了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幫助营造故事氛围,更侧面塑造了人物形象。《岁寒三友》就扩写了《最响的炮仗》的放焰火场景。《最响的炮仗》仅向读者介绍了焰火的名字,《岁寒三友》则详细讲述了焰火里的故事和人们看焰火时的反应。这里也体现了汪曾祺提倡的“气氛即人物”,整个场景中一句未提焰火制造者陶虎臣,却句句都与他相关。通过这一情节,读者了解了当地放焰火的习俗,陶虎臣的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
二、汪曾祺此类跨时代改写作品的特征
(一)人物形象的变与未变
因是改写,除了《邂逅》和《露水》中的卖唱男女,剩下三组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姓名有所改变,形象、性格等特征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三个故事里的王二都勤勤恳恳的在熏烧摊子忙碌。从《庙与僧》到《受戒》,三个和尚只是多了名字,当家和尚仁山依旧又黄又胖,负责管理庙里的账簿;能师父仁渡还是精明能干,会“飞铙”,牌技一流;二师父仁海也仍和老婆在寺庙过着小日子。《最响的炮仗》和《岁寒三友》里的炮仗店老板从孟老板变成了陶虎臣,却依旧是那个热心公益、对孩子们亲切、有着好名声的老好人。
《邂逅》和《露水》中的卖唱男女却有很大的变化。《邂逅》是这样描述两人形象的:“从前这一带轮船上两个卖唱的,一个鸦片鬼,瘦极了,嗓子哑得简直发不出声音,咤咤的如敲破竹子;一个女人,又黑又肥,满脸麻子……男的鸦片抽成了精,没有几年好活了……这个女人没有人要……这个女人没有女人味儿!”[9]到了《露水》里,两人变成了:“男的是个细高条,高鼻、长脸,微微驼背,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浑身带点江湖气,但不讨厌……女的面黑微麻,穿青布衣裤。”[10]两个人物虽不像《邂逅》里高洁的盲人卖唱者那样引人唏嘘,但最起码不那么讨厌了。
四组作品中,只有这两个人物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因为《露水》只是从《邂逅》里“借”来了两个人物,实际是一个全新的故事;更因为其他三组作品中的人物本身就是美的、善良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汪曾祺创作心态上的改变。年轻的他觉得像卖唱男女这样的劳动者是讨厌的、不可理解的;因为下放劳动的经历,老年的他对劳动有了全新的理解,明白了劳动人民、底层人民生活的不易,对他们也多了一些包容。
(二)叙述语言的简洁化倾向
汪曾祺四十年代的作品喜用破折号和大段叙述。以《邂逅》一文为例,在盲人卖唱者出场前,汪曾祺先用了九段叙述为即将出场的盲人卖唱者做铺垫,第六段更连用三个破折号:“他停立在两个舱门之间的过道当中……自由地带。——他为什么不坐,有的是空座位。——他不准备坐……他好像有所等待的样子。——动人的是他的等待么?”[11]想象“他”为何停立在两个舱门之间的过道当中。如果这个故事写于八十年代,这九段应该可以浓缩为一句:船上有个盲人卖唱者。
叙述语言的简洁化倾向也与汪曾祺创作心态的改变有关。“汪曾祺四十年代小说绝大部分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约80%),而八十年代几乎全是‘第三人称。”[12]四十年代进行创作时,受西方意识流创作技巧的影响,他在作品中抒发“我”的主观情感和想法。到了八十年代,这一创作心态发生了变化,觉得“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一篇小说,在作者写出和读者读了之后,创作的过程才完成”[13],开始追求读者和作品之间的良性互动。出于这样的考虑,其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叙述变得较为克制,很多地方都是点到为止。而这一点点波纹,泛起了读者阅读时克制不了的情绪,两者结合,构成了完整、有张力的文本。
(三)前后文本之间的关联与变化
对比改写前后的不同版本,还可以发现一个重要变化:汪曾祺的叙述态度变得温情。他四十年代的作品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写作姿态,追求对现实的直接、深刻反映,八十年代后重写的作品在情节上可能是不真实的,但故事写得很健康、很美,反而更受到读者的欢迎。1948年创作《异秉》时,汪曾祺对王二的“大小解分清”,戏谑多于宽容。1980年再次重写《异秉》,对勤劳致富的王二多了一丝欣赏,对天天被骂、想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陈相公也多了一些同情。《最响的炮仗》里的孟老板,“卖”了女儿也只赚得全家半个月的生活费,未来要如何生活还不得而知。跟他有同样境遇的陶虎臣,却因为有两位好友,三人相互支撑,日子还有些盼头。《邂逅》里令人极度厌恶的卖唱男女,到了《露水》中不仅不那么讨人厌了,还拥有了一个月的好日子。年过花甲的汪曾祺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也越来越觉得“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14]。
汪曾祺说自己是个只会写短篇的小说家。也因为短,作品里的每个情节都是经过精心思量的。相较于八九十年代戛然而止却如平地惊雷的作品结尾,其四十年代对小说结尾的处理还不够自然。《最响的炮仗》以女儿坐着洋车走了,孟老板一个人走到荒地,放了一个最响的炮仗结尾。“这一带人全都听到了。没有一个人知道是怎么回事。”[15]故事在这里结束,荒地里巨大的炮仗声和“卖”了女儿孤零零的孟老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感到凄凉。可能是怕读者被这巨大的炮仗声震撼得回不过神,汪曾祺又在后面加了一段风俗叙事:“你们贵处有没有这样的风俗:不作兴向炮仗店借火抽烟?这是犯忌讳的事。你去借,店里人跟你笑笑,‘我们这里没有火。你奇怪,他手上拿的正是一根水烟媒子。”[16]这样一段风俗,确实冲淡了孟老板的凄凉,但又让人感觉有些不合时宜。1948年的《异秉》以“学徒的上茅房”结尾,到了1981年,结尾变成了“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哪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17]。较之前的版本,汪曾祺特意强调了这不是他俩去厕所的时间,两个渴望像王二一样过上好日子的下层人形象一下子立住了。
三、汪曾祺对同一作品进行跨时代改写的原因
汪曾祺曾多次谈到自己重写同一作品的原因。“为什么要重写?因为我还没有挖掘到这个生活片段的更深、更广的意义。”[18]重写一次,就是一次更深的思索。反复多次地思索,也就有了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书写。他也认为自己是个不擅长虚构的作家,创作时只写自己熟悉的事。在他看来,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日光之下无新事,就看你如何以故为新。”[19]
汪曾祺对作品的跨时代改写也受其人生经历的影响,不同阶段的经历让他对同一题材的作品有了不同的创作思路。汪曾祺童年时期家境殷实,是个不知人间疾苦的小少爷。三十年代末,受战乱影响,他被迫离家求学,半只脚踏进了社会。生活困顿,又看不到未来的出路,甚至一度想要自杀,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也充满了苦闷和寂寞。幸亏沈从文及时发现,反复劝诫他:“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20]这种心态对汪曾祺有很大的影响。带着这种心态,他逐渐学会了随遇而安,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即使被打为右派、被下放劳动,还觉得“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21]。这段经历也让汪曾祺真正体会到现实中的劳动生活和人情的可贵。七十年代末,“四人帮”倒台,很多人都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却因为曾参与创作“样板戏”成为怀疑对象,“写了大量检查,一度畏惧、委屈至极,欲夺去手指,以明清白”[22]。别的作家热烈歌颂新生活,他却发现自己与新生活格格不入。除了生活上的不适应,文学创作的重新出发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新时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骑兵列传》,符合当时的主旋律,却反响平平,反倒是重写的《异秉》受到了很多关注,也让他获得了安慰和鼓舞。他也因此决定回到自己熟悉的“旧社会”、在熟悉的生活中找寄托。
四、汪曾祺跨时代改写作品的意义
汪曾祺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里曾说:“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凈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23]他在八九十年代重写四十年代的故事,经过四十多年的沉淀,对当时的人事有了新的思索,即使是相似的题材,故事的思想性也有了新的变化。
虽然一直从自己的旧生活中取材,但汪曾祺一直在用旧素材写新故事。六十岁的他,带着从人生中获得的生活体验,重新书写他记忆中的故乡人事,用八十年代人的感情重写四十多年前的事。他从青年变成了老年,也对生活有了不一样的理解。“青年汪曾祺”的创作是恣肆的,各篇有各篇的特色,未形成统一的风格,在语言上也有一些弊病,是不够好的。到了八九十年代,汪曾祺创作出了读者和评论界都很满意的作品,也形成了自己的典型风格,这时候对自己之前的作品进行改写,并获得认可,说明他改写得很成功。虽然对四十年代作品中的一些弊病进行了修改,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其后期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一定高于前期的创作。解志熙曾指出从《灯下》到《异秉》,“失去了《灯下》原有意蕴的复杂性、开放性及其引而不发的艺术效果”[24]。
汪曾祺反复修改自己四十年代的作品,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不同阶段的思考融入作品,试图让作品更加完美。可以说,这类跨时代改写的作品,是他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从整体上串联其创作生涯的重要材料。这些经历了跨时代改写的作品,就像连接汪曾祺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创作的桥梁,我们也得以从“青年汪曾祺”和“老年汪曾祺”创作上的不同,感受其独特风格的形成过程。
注释:
[1]汪曾祺:《捡石子儿(代序)》,《汪曾祺全集(五)》,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3]较1946年版文字略有改动。
[4]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2页。
[5]同上,第66页。
[6]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9页。
[7]同上,第189页。
[8]同上,第328页。
[9]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10]同上,第377页。
[1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6页。
[12]钱理群:《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13]徐新媛:《论汪曾祺小说中的留白》,《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3月,第39卷第3期,第145页。
[14]汪曾祺:《千万不要冷嘲》,爱学术,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a1a89c49bc6bff8021e4a499fbea4983318947a18e7f9386.html(阅读日期:2020年8月28日)
[15]汪曾祺:《大淖记事》,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63页。
[16]汪曾祺:《大淖记事》,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63页。
[17]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1页。
[18]汪曾祺:《思想·语言·结构》,《汪曾祺全集(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1页。
[19]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20]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21]汪曾祺:《随遇而安》,搜狐,https://www.sohu.com/a/227836523_523104(阅读日期:2020年8月27日)
[22]郜元宝:《汪曾祺论》,《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第114页。
[23]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1页。
[24]解志熙:《出色的起点》,《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94页。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2]王瑜、原帅:《文学史视域中汪曾祺小说的三次重要重写》,《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第59-67页。
[3]龚静:《汪曾祺的“孟老板”和“陶老板”》,《文学报》,2017年10月,第12-13页。
[4]闫铭:《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重写、改写》,《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第92-99页。
[5]褚云侠:《<受戒>的周边》,《文艺争鸣》,2019年4月,第22-29页。
[6]祁颂冰:《论汪曾祺对其1940年代小说的重写》,《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7]阚萧阳、张志忠:《小说创作的成熟与作家责任意识》,《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第41-50頁。